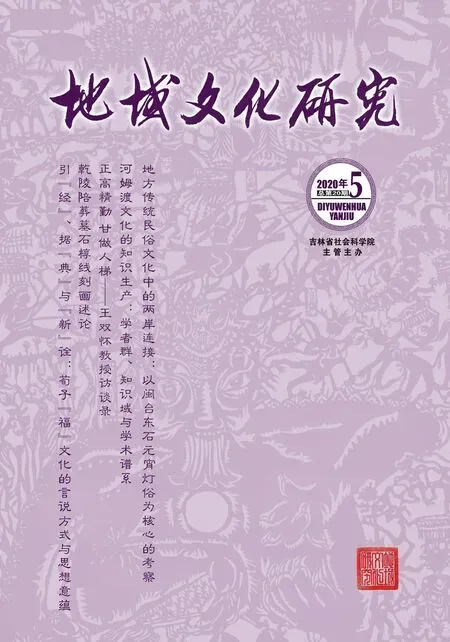杨嗣昌任职户部时的督理辽饷策略
——以《杨嗣昌集》为中心
学界对于杨嗣昌的研究堪称历史悠久,从明朝灭亡开始,学者们对杨嗣昌便以负面评价居多。他们大都认为杨嗣昌书生空言误国,排挤同僚加之“所用非人”、“嗣昌既终右文灿,而文灿实不知兵”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12页。、议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15页。、与后金(清)议和致其做大,是十足的“亡国之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部分学者又站在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杨嗣昌视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其奏请加派“剿饷”“练饷”将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制定“攘外必先安内”“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军事计划,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行为大加挞伐。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于杨嗣昌的研究趋向于客观、公允,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将杨嗣昌置于明末特殊的大环境下,来研究杨嗣昌当时的施政举措及其对明末财政、农民起义、明金战争的影响。
对于杨嗣昌的研究,学界目前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杨嗣昌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顾诚①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 张显清:《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文献》1980年第1期。、汤纲、南炳文②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白寿彝③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显清、林金树④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樊树志⑤樊树志:《晚明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都有提及。相关论文作者还有孙柞民⑥孙祚民:《张献忠智歼明督师杨嗣昌的斗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胡德培⑦胡德培:《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的典型形象——〈李自成〉中的杨嗣昌形象剖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等。此外,李超⑧李超:《杨嗣昌军事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和韩玉林⑨韩玉林:《杨嗣昌军制改革若干举措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0年。从杨嗣昌应对后金(清)及农民起义军的军事举措入手,详细分析杨嗣昌筹饷、募兵、练兵、军队配置及构成、用兵战法、军制改革等方面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效果和影响。吴樱⑩吴樱:《杨嗣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则论述了杨嗣昌的家世生平、任职经历、文学成就,并着重阐释了杨嗣昌在山海关防御后金(清)及出任督师镇压农民军的策略及其最后悲剧命运的原因。
杨嗣昌的文学成就及文献整理。1980年张显清在《文献》上发表了《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 张显清:《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文献》1980年第1期。一文,考证了《杨文弱先生集》的成书时间,并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述了该书对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价值。之后的学者开始注意杨嗣昌的文学成就及其文献整理情况,梁颂成在这一方面用力尤深。梁颂成在旧抄本《杨文弱先生集》的基础上,搜求有关杨嗣昌的各种文献,考订版本,辑校了《杨嗣昌集》杨嗣昌:《杨嗣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此外还将杨嗣昌的诗文辑录成《杨嗣昌诗文辑注》梁颂成:《杨嗣昌诗文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围绕着《杨嗣昌集》和《杨嗣昌诗文辑注》的整理,梁颂成还发表了《杨嗣昌的生平与创作》梁颂成:《杨嗣昌的生平与创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杨嗣昌集〉整理的底本及其版本考察》梁颂成:《〈杨嗣昌集〉整理的底本及其版本考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杨嗣昌集〉整理底本的形成及其遭遇》梁颂成:《〈杨嗣昌集〉整理底本的形成及其遭遇》,《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章,就《杨嗣昌集》所用底本《杨文弱先生集》的成书情况,编撰渊源及版本优劣等问题做了考证。
杨嗣昌的旅游文化理论。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张廷玉等:《明史》卷252(列传一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10页。不仅是明末重要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著作颇丰的诗人、散文家和旅游文学家。梁颂成对这方面的研究亦颇有建树。他在《杨嗣昌旅游理论述论》梁颂成:《杨嗣昌旅游理论述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一文中将杨嗣昌的旅游文化理论概括为:旅游资源的配置理论、风景名胜的评价理论、旅游观赏的审美理论、民俗旅游的开发理论等四方面并详细加以论述。此外还有《杨嗣昌山水旅游的观赏艺术》①梁颂成:《杨嗣昌山水旅游的观赏艺术》,《岳阳职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杨嗣昌旅游文学产生的内部原因》②梁颂成:《杨嗣昌旅游文学产生的内部原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等文章分析杨嗣昌在山水游记写作上取得的成就,并认为这些成就是与其本人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个人志趣以及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对于杨嗣昌的研究,学术界虽然起步较早,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对于杨嗣昌的专题研究仍不深入,杨嗣昌在明末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军事举措对明末的政局、农民起义、明金(清)战争的影响,甚至其死因都有很多问题没有阐释清楚,亟待解决。本文就以杨嗣昌本人文集为切入角度,分析其在任职户部时对军费筹集、使用、管理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梳理、概括其理饷策略,及其在解决为明帝国筹措对后金的战争经费的问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杨嗣昌集》与杨嗣昌
(一)关于《杨嗣昌集》
《杨嗣昌集》是梁颂成辑校整理的杨嗣昌文集。该文集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旧抄本《杨文弱先生集》,即北京出版社影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内所收《杨文弱先生集》为底本,同时参考《古今图书集成》、光绪《湖南通志》、嘉庆《常德府志》、陈楷礼辑《常德文征》、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明清史料辛编》等书辑校整理而成,包含杨嗣昌的奏疏、纪事、书信、诗文、杂著57卷,补录1卷、《武陵竞渡略》一卷、《薛文清公年谱》一卷,共计1303题(篇)。其中前4卷即是杨嗣昌任职户部时,有关辽东战事军费的筹集、加派、征收、转运、使用、出纳、核查情况的自陈和代部堂具拟奏疏,共有三十余题,本文既根据这些材料展开论述。
(二)关于杨嗣昌任职户部的情况
杨嗣昌无疑是明末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关于杨嗣昌其人的研究,已有前文介绍的诸多研究成果,本文在此仅作一简要的回顾。以时间为轴,杨嗣昌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参与了“三饷”加派、明后金(清)战和、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等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以其任职情况为线索,杨嗣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崇祯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五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52《杨嗣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09页。其任职于教育、财政、军政等重要部门数十年,日常处理公务时积累了大量奏疏、信札等文件,现均收录于梁颂成辑校本《杨嗣昌集》中。从其奏疏之后标记的日期看,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上《驳承天监参提佃户稿》时杨嗣昌已在户部任职,至天启二年(1622)五月《乞罢第三疏》为止,其至少在户部任职6年,历任福建司主事、江西司员外郎、新饷司郎中、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等职。本文即以这段时间杨嗣昌奏陈的督理辽饷相关建议和措施作为研究范围。
(三)关于明金(清)战争及杨嗣昌督理辽饷的背景
杨嗣昌任职户部的6年,历经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明神宗荒怠政务,二十余年不早朝,郊、庙仪式也多由大臣代替。史载:“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8页。各级机关缺员如此严重,中央决策和地方行政陷于瘫痪。此外,神宗还向全国各地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大肆敛财。“榷税之使,自(万历)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宷于京口……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余。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81《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8-1979页。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搜刮一方面使大量的商人破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恶化了经济形势,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污染了社会风气,在社会和官场上形成了贪财逐利、骄奢淫靡的不良思潮。
朝政如此糜烂,军队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由于财政紧张,拖欠士兵饷银的现象普遍存在,仅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天启七年(1627)间明帝国就拖欠北边各镇京运饷银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③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政治经济学报·经济统计季刊》,1936年1月第4卷第2期。杨嗣昌也在奏折中提到各镇欠饷情况:“辽东经略抚按则以战马三月无料告,蓟辽总督则以新兵缺饷难支告,顺天巡抚则以蓟辽缺乏至极告,宣大总督、抚按则以士马饥饿堪怜告,山西巡抚则以三晋民困已极告,盖皆两饷缺乏、见在候给官军。”④(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斟酌九边饷赏请帑第二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50页。即便财政稍有缓解,发下来的饷银大部分也被各级文武官员层层贪污克扣,能到士兵手中的寥寥无几。士兵生活困苦,典衣鬻箭,不断逃亡,军队缺额严重,比如“(宣府)额兵八万有奇,见在营伍不过三万有奇”⑤(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驳宣府补兵请用新饷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1页。,缺额近三分之二。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来应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明帝国不得不加派饷银,但这样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国家濒于机能坏死的绝境,故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⑥(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矿税之害》,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7页。
蛰伏东北的后金政权对明帝国的弊病洞若观火,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书七大恨告天”⑦《清太宗实录》卷4,天命三年四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历数明帝国罪状,誓师起兵伐明。准备不足的明军仓促迎战,丧师失地。“夏四月甲辰,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庚戌,总兵官张承胤帅师援抚顺,败没……秋七月丙午,大清兵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死之。”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0《神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页。
为了筹集军费发动反攻,明帝国于同年加派了辽饷。“户部以辽饷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请加派:除贵州地硗有苗变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1578)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应酬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一两四钱三分八毫零”。②《明神宗实录》卷574,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辛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0862页。“明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8《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3页。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辽饷加派范围扩大到盐课、关税以及杂项银两,到了崇祯四年(1631)“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8《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3页。
明帝国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设立了专门管理辽饷的新饷司。“户部尚书李汝华请立新饷司专理辽饷五百余万,而以本部原任主事鹿善继董其事,上从之。”⑤《明熹宗实录》卷1,泰昌元年九月甲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8页。杨嗣昌在户部任职期间也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也多次在奏折中阐述辽饷的管理和使用意见,其中亦可窥见其理饷策略,笔者将在下文中加以论述。
(四)杨嗣昌任职户部时的理饷措施
据上文所述,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明帝国为筹集与后金作战的军费,在全国强行加派辽饷,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共计加派五百二十余万两。其中扣除在永、顺、登、莱、保、青等府的蠲免和截留,“应征加派不过四百八十万”。⑥(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4《述辽饷支用全数并乞罢第一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76页。但是这笔辽饷对于愈演愈烈的明金战争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杨嗣昌在奏折中提到:“计臣管饷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启元年十二月终止,截数通算,京发外兑、本折、粮价、买运等项,臣一部独用新饷之事,共计七百八十九万四千七百七十九两九钱零。又自天启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终止,截数再算调募、扣留、安家、器甲、行粮等项,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饷之事,又计一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六两零。盖臣管饷十六个月,实算臣部用银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六两零……夫此十六月中,臣部分请帑金不过二百一十万,应征加派不过四百八十万,今用九百二十五万有奇,则有二百三十五万不知来处。”⑦(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4《述辽饷支用全数并乞罢第一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76页。可见,即使加派辽饷并加上皇帝拨发的内帑,辽事用饷尚缺二百三十五万两之巨。最后还是靠着杨嗣昌等户部官员“檄催如火,案驳如山,委身殉职,穷力任怨”⑧(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4《述辽饷支用全数并乞罢第一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76页。才勉强保证了军饷的供应。实际上,杨嗣昌在户部任职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筹集、管理和使用捉襟见肘的军饷并使之效率最大化,以保证辽东军前供应,这实是“巧妇为少米之炊”的难题。
二、杨嗣昌的筹饷策略
鉴于辽饷并不能满足辽东战事的全部需要,而且杨嗣昌也清醒地认识到大规模的强行加派极易激起民变,长此以往,无异于饮鸩止渴。“辽东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处?岂可不为料理,但恃催科?目今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将来只恐百姓已自做贼,谁为用我催科者?”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2《南直催饷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31页。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加派辽饷之外,找到其他的筹饷途径。杨嗣昌开辟辽饷来源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金花银。
(一)金花银充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明军惨败于萨尔浒,举国震惊,明帝国不得不正视后金这个崛起于东北的民族政权。加强辽东防务,抵御后金的进攻成为重中之重,时议辽东增兵至二十余万②(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陈言兵饷疏》,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9页。。“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为二十万大军供应军饷的任务,自然由户部负责,而仅仅依靠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派的辽饷是远远不够的。为缓解户部“当此呼吸危亡,数万金钱到手辄尽”的窘迫局面,杨嗣昌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十八日上《复留金花等银充辽饷稿》,请求明神宗允许户部截留金花银用作辽东军饷。
杨嗣昌提到的金花银,其创制始于周忱。明宣宗时他在江南地区试行田赋实物税粮折征白银,米四石折银一两,解之南京充俸,取得了“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53《周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14页。的良好效果。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副都御史周铨、户部尚书黄福、江西巡抚赵新等建议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其折价比例亦是一比四,“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8《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5-1896页。,此后遂为定制。万历六年(1578)时明神宗还曾一度提高金花银的数额“每季加银五万两一应买办。”⑤《明神宗实录》卷74,万历六年四月丙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611页。虽说设置金花银的初衷是希望官民两利,官员省去赴南京关俸的奔波和商人剥削之苦,百姓也免于运粮和“加耗”的负担。但实际上金花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7页。,就是说自正统以后一百余万两的金花银只有十余万两用于支付官员的俸禄,余下的有司无权过问,全部收入“内承运库”这个皇帝的小金库之中,用于皇室的开支和消费。杨嗣昌亦在奏折中指出金花银原非皇帝私用之物,且有用作军事应急储备金的先例:“臣等详査《大明会典》,内府金花原系国初折粮银两,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禄,各边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嘉靖二十二年,题准三宫子粒及各处京运钱粮,不拘金花折粮等项,应解内府者,一并催解太仓银库,悉备各边应用,不许别项挪借。可见祖宗朝金花一项,原非内府之物,即改解之后,未尝不专贮济边。”⑦(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复留金花等银充辽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3页。同时也希望明神宗“仰体祖宗之意,俯念危辽万分紧急”,准许户部截留金花银“可备辽饷十分之二”。杨嗣昌的奏疏有理有据,且辽东新败,亟须饷银布置防务,但以敛财而闻名的神宗回答他的只有“不允”二字。
请求截留金花银碰壁的杨嗣昌,退而求其次于同年八月十二日又请求神宗将往年各地拖欠未能征解入库的金花银一百余万两“俯赐臣部转行抚按催解太仓,以济辽饷万分之一。”他认为此举能感动百姓,使其“节缩衣食,输纳涓埃,共助辽东饷军讨贼”,“则此拖欠累年未经解到银两,或得一二接济,未可知也。”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算调募辽兵请借拖欠金花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8页。但是即使是请求截留仅存在于账面上的拖欠金花银,同样没能得到神宗的允许。
(二)物资折银充饷
明帝国的官私手工业都比较发达,为了保证生产的持续性,其在南北两京设置了大量的仓库来储存从各地征收的手工业原材料和制成品。“两京库藏,先后建设,其制大略相同。内府凡十库。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岁进百万两有奇。广积库,贮硫黄、硝石。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贮甲仗。赃罚库,贮没官物。广惠库,贮钱钞。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绸绢。六库皆属户部。”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6页。这些生产原材料和物资大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且征收入库之后往往不能马上加工成成品,故极易因长期贮存导致腐坏、霉变。所以明帝国将暂无生产计划的部分原材料和物资折成银两征收,等到需要使用这些材料时再招商购买,而平时折征的银两存入太仓库以备边事需要。杨嗣昌以此作为凭据,建议将手工业原材料和物资折征银两充作辽东军饷。他先是列举出了一些先朝成例来增加说服力:“又査《会典》,浙江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解到本色黄白蜡,倶送供用库收,折色黄白蜡,解太仓银库济边。嘉靖十年,题准今后各处起解京库物料,果系本地无产者,许于批文内明开某物折征价银,到京召商上纳。如有余银,送太仓库交收,以备支用……可见祖宗朝内府供应诸项稍有赢余,即发太仓济边。”然后进一步提出了将丝绢、蜡茶等折银征收并催解太仓充饷,等到辽东局势缓解,再恢复征收实物:“如湖广等处丝绢,福建、浙江等处蜡茶……不若折价解京,宮民两利。见今准折一年,催解太仓,以备新饷。以后分别本折,仍赴内纳。”③(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复留金花等银充辽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3-4页。“合无比例,将浙江、福建、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隶、苏、松、常、镇、徽、宁、池、太、扬等府,广德等州,査照见征事例,有无某项若干,尽与折价催解太仓,以备新饷,稍俟一二年,复还旧额。”④(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复留金花等银充辽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4页。手工业原材料和物资折征银两一方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辽东前线急需的饷银,在操作上也不存在困难,因而很具有可行性。但同样没有得到神宗的同意。
(三)赏赐充饷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在位仅月余的明光宗驾崩,由其子朱由校继之,是为明熹宗。按照惯例,新帝继位,要向九边将士颁发登基赏赐。杨嗣昌鉴于当时“海内民穷,新旧派粮,十分未完四五。太仓扫尽,新旧请饷,万分不给二三”⑤(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斟酌九边饷赏请帑第二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50页。的情况,希望熹宗体谅百姓疲困、加派拖欠、太仓乏银、各镇欠饷的窘境,“堪怜部库之穷,暂补正供之缺”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斟酌九边饷赏请帑第二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51页。,将“今次赏赉银两,发与九边,准作新旧饷银,臣部照数扣抵。或者天恩优厚,必欲覃敷,则以十分之二三作赏,以十分之七八作饷”②(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斟酌九边饷赏请帑第二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51页。,即将此次登基赏赐的财物,全部或部分充作九边军士的军饷,一方面缓解户部筹饷的压力,另一方面亦可补贴九边军士的欠饷,以提振军心。这个筹饷办法同样也不失为合乎财政实际的良策,但被熹宗以“这登基恩赏,累朝旧制,岂得挪为别用?”为由驳回。
(四)请发内帑
在金花银充饷、物资折银充饷、登基赏赐充饷等筹饷办法均被皇帝拒绝,且辽饷捉襟见肘、军士嗷嗷待哺的情况下,杨嗣昌只得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至天启元年(1621)连上九疏请帑,请求皇帝拨发内帑银接济辽饷。内帑主要是贮存于内承运库中的金花银、三宫子粒、皇庄收入等,但是大宗仍是明神宗二十余年间靠矿监、税使巧立名目,搜刮而来的财物。步进智、张安奇在《顾宪成高攀龙评传》中认为“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③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而赵翼则认为:“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④(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8页。,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罢天下矿税令旨,先年开矿抽税,为三殿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近因辽东奴酋叛逆,户部已加派地亩钱粮,今将矿税尽行停止。”⑤《明光宗实录》卷2,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子,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25页。如果将矿监、税使设置的起止时间定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则这笔帑银的总数将超过一千万两。而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则总数为七百万两,“当他(明神宗)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96页。这里提到的转移给各部,即是应杨嗣昌的九道请帑奏疏,明光宗和明熹宗拨发帑银交由户、兵、工三部用于辽东战事。据杨嗣昌之子杨山松的记载,前后共计拨发四百五十万两,⑦(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请帑第五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55页。后接按语“山松曰:此后又有《请帑第六稿》,求其蚤发,得旨:发帑五十万。又有《九卿科道会题请帑稿》,合户、兵、工三部需饷四百万,得旨:允发一百万。因此一百万,户部不能分用。又具一《催发帑金稿》,再请发一百万,不允。又因河东已失,河西收什溃残,又具《九卿科道公疏》发挥请帑,得旨又发二百万。”几乎占明神宗20余年积累之数的一半。须知内承运库的帑银还要保证皇室和宫廷用度、赏赐以及一部分武官的俸禄,扣除这一部分支出,再拨发四百五十万两帑银,实在算得上是慷慨,而请发内帑也成为杨嗣昌最具成效的筹饷策略。
三、杨嗣昌的理饷策略
杨嗣昌不光在筹饷方面卓有实效,在军饷的管理、出纳和审计等方面也建树颇多,他提出了若干饷费管理策略,使军饷的管理和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一)杜绝妄请,专款专用
据上文所述,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起兵,明帝国加派辽饷来应对辽东的战事,截止泰昌元年(1620),辽饷已达五百余万两。除辽东之外的九边和内地军镇都觊觎这块巨大的蛋糕,希望借援辽之名,分得一部分饷银。仅天启元年(1621)就有宣府请求拨发辽饷二十万两用于招募新兵,以补充因援辽而调走的军数;蓟镇请求拨发辽饷加强山海关内各地的防务;山东、河北请求截留辽饷用于招募新兵加强真、保、登、莱等地的防务。杨嗣昌对此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痛斥这种做法,“今日天下大势,坏于旧兵不可为兵,旧饷不可为饷。地方一有事,则召新兵,一召兵则增新饷……此端一开,就此数十万徒设之兵,又当外增数百万徒糜之饷。”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驳宣府补兵请用新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2页。并且明确表示这些地区招募新兵补伍应使用本镇原额军饷,“若督抚臣能于额兵额饷精求实用,不致专靠新饷取快瓜分”②(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复议蓟门督抚增用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4页。、“至于补伍,则唯有用额饷”、“至于额兵补伍,原与新饷无干,无从办给。”③(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驳宣府补兵请用新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3页。或通过裁汰老弱,压缩开支来筹集费用,“每岁旷缺兵银十分解一者;州县应汰民兵项下,按籍沙法裁减十分解五者。”④(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复议山东河北增兵用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5页。而不是一味依靠请拨、截留辽饷,如果各镇都请发辽饷,而辽饷的数额是固定的,最后只能是“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处多一分则彼处少一分,此处占一项则彼处缺一项”⑤(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复议蓟门督抚增用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3页。,各镇都不能达到加强防务的目的。只有杜绝滥请,专款专用,这样加派的辽饷才能最大限度地在辽东战事中发挥作用。
(二)实兵实饷,严核严销
鉴于在明军中存在严重的虚报兵数,贪墨粮饷的弊端,杨嗣昌还提出了在辽东打乱原有的卫所、标、营等编制,统一以“道”为单位,将军队实际人数、饷费编制成册,使各级官员和军队将领“彼多索饷则不得少载兵,彼多载兵则不敢频失事,此可以功罪按者也。彼须调募则不敢讳逃亡,彼见逃亡则不能昧存省”⑥(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请立兵册清查辽饷确数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6页。,以达到节约饷费的目的。他在奏疏中具体阐述了编册的方案:“辽兵虽众,唯有新旧两端;辽地虽宽,唯有河东、河西两界。河东分辽阳、海盖、开原三道,河西分广宁、宁前两道,而道尽矣。某道之属,分城堡若干,而地尽矣。某城堡之内,分旧兵新兵若干,而兵尽矣。某兵之内,分食几钱饷银者若干、几两饷银者若干,而饷尽矣。如是种种之数,断自经略。交代一日为止,责令各道尽将所属城堡、见在之兵、见食之饷,编造总数、撒数册报经略。”⑦(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请立兵册清查辽饷确数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6页。从最基层的城、堡开始将兵员实数、所需粮饷统计出来,并逐级汇总于道一级,再上交给辽东经略,这样就可以统计出精确的军饷数字。造册完毕后“备申经略核实,挂号印发饷司。饷司照填底册一本存案,仍将道册转申到部,即将册内各道分管(调)城堡兵饷总数另具一揭发抄。其交代后,兵马或有更置,钱粮或有增拘,定为各道每月二次册移饷司、饷司每月二次册揭报部发抄之制,一如前式。”①(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请立兵册清查辽饷确数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6-17页。经过辽东经略的审核后,将兵册交由饷司和户部备案,如果数额有变动,再上报饷司和户部更改。这样可以“使朝野内外晓然,皆知辽东几道几城几堡几兵几饷。”②(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1《请立兵册清查辽饷确数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7页。既然道、经略、饷司、户部都得到确切的需饷数字,使辽饷发放有了依据,就可以减少以往明军虚报兵数、冒领军饷的弊端,提高了饷银利用效率。各级官员也知道军队实际人数,方便筹划战局。
(三)划分兵等,依等给饷
杨嗣昌于天启元年(1621)五月上《复议蓟门督抚增用饷稿》中最早提出了将兵马分等查核实数给饷的方法,“蓟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须剖析明白”③(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复议蓟门督抚增用饷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4页。,又在同年六月上《复辽兵加饷并查新旧各兵稿》中进一步提出将辽东现存新旧兵马核查实数后分为五等:“一等月给银二两,二等月给银一两八钱,三等月给银一两五钱,四等月给银一两二钱,五等月给银八钱。使新兵旧兵各以其技能受等,而不分新旧饷名色。”④(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3《复辽兵加饷并查新旧各兵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7页。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新兵旧兵各以其技能受等”既选出了可以冲锋陷阵的一等精兵,又按照评定的等级发放军饷,低等的士兵为了提高待遇,也会积极加强军事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通过分等考核,又将辽东新旧军队的确切人数核查出来,有利于遏制吃空冒饷的弊端,节约艰难筹集而来的辽饷,增加饷银发放的透明度。
结 语
杨嗣昌在任职户部的数年中,主要负责管理加派的辽饷,但辽饷并不能完全满足辽东战事的需要。为了筹集军饷,杨嗣昌还提出了金花银充饷、赏赐充饷、物资折银充饷等颇具可行性的筹饷策略,但都因万历皇帝的反对而作罢。直到万历帝驾崩,辽事愈发危急,杨嗣昌才通过请帑一途,才从泰昌帝和天启帝手中获得了辽东前线急需的饷银。可见再好的策略,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此外,杨嗣昌还构建了以“专款专用、实兵实饷、严核严销”为核心的饷费管理和使用体系,有效地遏制了用饷环节的弊端,提高了效率和透明度。虽然,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微不足道的,杨嗣昌最终也没能挽救明帝国于危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杨嗣昌所处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性而否认杨嗣昌的才能及其付出的努力。历史研究者应当将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对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探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