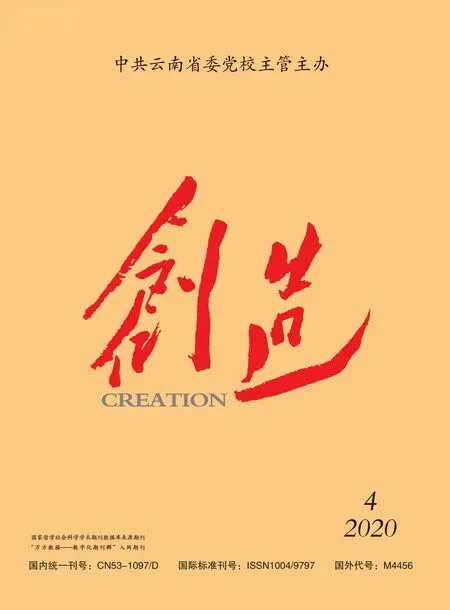云南特色文化艺术对东南亚、南亚的传播策略探讨
(昆明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云南 昆明,650214)
一、云南与东南亚的地理历史关系分析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桥”天然一体,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是我国横断山脉的延伸。奔流在东南亚、南亚群山之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我国的云南的怒江;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恩梅开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境伯舒拉山南麓,即云南境内的独龙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我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皆为经云南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
山川同脉、江河同源,加之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中国尤其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诸多族群都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曾经历了多次的融合与分化,有过血脉相融、文化互通的历史。就缅甸藏缅语各民族的由来而言,例如,克钦人即与云南境内景颇族的先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在距今1400年左右的中国唐代,景颇的先民就从云南西部进入缅甸,至今克钦人也喜欢用“景颇”自称;元明清时期分布在澜沧江、怒江流域的“力些”“傈苏”在明清时期有一部分南下经保山、腾冲到达印度、缅甸以及泰国,成为东南亚分布最广泛的彝语支族群;缅甸阿卡人的先民则是在公元6世纪以后从古代云南高原上的叟、昆明等族群中分化出来的,其中的一些支系在19世纪中叶后陆续迁徙至缅甸,其文化习俗中仍有与云南哈尼族类似之处。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长期发展起来的水陆交通,把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紧密联结在一起;第二,越南属“汉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国文化的薰染;第三,广布各地的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第四,众多的跨境民族,与东南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第五,佛教的传播,使中国与东南亚都进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二、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东南亚、南亚的交流与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曾给予东南亚各国直接、广泛、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层次的,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多个方面。
越南较早受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质农具、牛耕技术、手工技艺就开始传入越南。秦汉时期,用转盘制陶的技术和养蚕缫丝的技术传入了越南。除了直接的文化采借,越南人还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创新——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传入越南后,越南人用当地盛产的蜜香树皮制造出了“交趾蜜香纸”,纸质优良且带有香味,传入中国后很受中原人士的欢迎。魏晋时期,中原制陶术传入越南,当时能生产出精湛的彩釉陶和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制品。印刷术在11世纪左右传入越南,后来宋元两朝的《佛藏》 和《道藏》 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运用印刷术刊印了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可以说,商贸的往来推动着民间工艺的互动发展。宋朝时期,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物资主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其器型、风格、制作工艺等都对后世越南人制造同类器物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柬埔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也有近两千年历史。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陶器、麻织品、金属制品大量输往扶南(今柬埔寨境内),深受当地居民欢迎。唐宋时期,中国向真腊(柬埔寨)出口的商品除了生活用品的酒、糖等,还有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等,以至于后来的几个世纪,“唐风”(中国货)十分流行。元代,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锡腊,还有温州的漆器、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雨伞、木梳等,都十分受欢迎。
两千多年前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物质文化传入缅甸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入到缅甸,唐代估计就有“骠国(公元1—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
泰国受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较晚于越南、缅甸,但自公元6世纪有海上贸易以来,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规模超过了同期中越、中缅贸易,尤其是丝绸、瓷器和铜器。元代中国工匠将瓷器的烧制技术带到了泰国,对其后世宋加禄瓷器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公元15世纪之后,中国大批华侨从东南沿海移居菲律宾,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技艺,如缝纫、酿酒、制糖、印刷、建筑等,饮食习惯方面也对当地人产生了诸多影响。
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商品在唐宋时期较为丰富,贸易频繁,手工艺类的有瓷器、锦绫、绢、金银等。同时,大批华侨移居印尼,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中国的重大发明和技术也随之传入,并为印尼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如13世纪火药传入印尼,16世纪印尼能自制火炮;造纸术在16世纪传入印尼,17世纪后期雅加达有华人开设纸厂。
中国古代的文化技术,大都以输出的方式对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既提升了上述国家的文化技术水平,又作为文化交流载体,沟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手工业技艺。
除了工艺文化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化也从多方面影响到东南亚、南亚国家,中国的语言、文字、诗词、文学等都曾为东南亚各国人民所欣赏、接受和分享,传递出独有的智慧力量,渗透到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之中。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艺术交流的战略意义
(一)文化艺术交流是民心相通工程的有效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外交往、共谋发展的重大战略,以五通为基础,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并驾齐驱,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全方位、立体化工作格局。其中,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是其他“四通”的重要基础。通过增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塑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氛围,民心相通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
而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多样,既是各国民众间的才艺智慧展示,是民族自信心、民族情感的依托,更是文化理解、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官方组织还是民间交流,文化艺术从业者、爱好者都有一些共性:一是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热爱和坚守,二是对异文化的好奇与欣赏,三是对同为艺术工作者或爱好者的尊重,这些都可以成为“民心相通”的着力点,成为文化相互欣赏、彼此认同的重要基石。
(二)以文化艺术的多种交流途径为民心相通工程助力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在“一带一路”这个由不同族群构成的大区域中,文化以多样性和共生性为主要表现。各族群文化的相互理解、交融共进将成为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的基础与纽带。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的“亲缘关系”,云南民族民间诸多传统手工艺在历史上曾作为文化载体,沿南方丝绸之路与境外部族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交融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至今,民族民间手工艺仍是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艺术特征、技艺传承等呈现出的差异性、独特性正是文化价值所在。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世代相传的手工艺文化,且很多民族跨境而居,与东南亚、南亚同源异流的族群有着密切的民间文化交流,客观上形成了研究“一带一路”东南亚、南亚各族群之间文化交往、艺术影响力等问题的一条重要脉络。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渊源、美学元素、技艺特征、传承传播,以及手工艺文化中反映的深层意义等方面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挖掘生态环境、宗教信仰、民族历史等多元影响下形成的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特点,展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更有利于寻找到通过民间艺术交流与民族文化传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境内外民族认同的现实路径与具体方法,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为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合作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特色文化艺术多种形式的交流传播不仅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还将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形式,促进各领域的合作交流、互利共荣。推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把“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四、提升云南特色文化艺术的传播力与传承能力
(一)云南特色文化艺术在东南亚、南亚的传播策略
云南很多民族都是跨国界而居,因此民族文化的承载往往跨越国界,与东南亚、南亚有着根脉相系的关联,由此形成了一种以跨界民族为载体的区域、次区域文化生态群落。在这个文化生态圈中,相邻各国、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的文化,客观上相互影响、互为环境。在有10多个民族跨界而居的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这种跨国界的民族文化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考虑到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周边文化生态环境,并以此为基点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弘扬云南民族文化具有整合力、亲和力、感染力的传统优势,吸纳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内涵、拓展艺术样式,凸现区域文化特质,创造和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有强烈时代感又内含经典云南元素的文化艺术产品,是文化创新的可行之路。
为推动云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向产业快速转化,近3年来,云南省组织开展了建水紫陶传家宝设计大赛、华宁陶拉坯邀请赛、云南十大刺绣名村镇评选,云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企业、特色村寨、特色协会,云南省特色文化产业知名品牌评选等活动,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东阳以及意大利米兰、阿联酋迪拜、印度孟买等地举办云南特色文化产品万里行活动,扩大了云南省特色文化产业的影响,得到社会普遍关注,也拓展了文化市场。现在,玉石、建水紫陶、华宁釉陶、民族刺绣、斑铜、斑锡、乌铜走银、剑川木雕、红木木艺、香格里拉尼西黑陶彩陶等特色产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逐渐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趋势,经济效益显著,带动当地经济、旅游发展。光明日报与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在京召开文化产业走出去“云南样本”研讨会,总结推广成功的云南经验。为加强文化产业智库建设组织人员到上海考察学习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经验,举办了第五届全国版权经纪人专业实务培训班暨云南民族文化产品版权开发交易培训班、全省文化产业培训班、“工艺大师与设计创意名家走进云南”系列培训活动,促进骨干文化企业更新观念、拓展视野,提升特色文化企业创意设计水平。
同时,在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次区域、小区域经贸合作中,可以考虑举办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文化活动,来促进经贸合作的开展。较具可行性的如倡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民族文化节”“中老缅泰金四角合作区民族文化节”以及“澜沧江——湄公河飘流探险”“西南丝绸之路汽车拉力赛”等区域性国际文化体育活动,并使之与商贸、经济技术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一些历史上就已存在的跨界民族文化节日,如泼水节、目脑纵歌节等,应扩大范围,使之成为小区域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盛会。增大昆交会等国际商贸活动的文化含量,可以邀请东南亚国家的文艺团体前来参会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和传媒宣传,扩大云南的国际知名度,塑造云南开放、友好、亲和的整体形象,弘扬云南4千多万各族儿女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增大云南对东南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云南对外开放,加快次区域、小区域合作进程。在旅游业方面,利用云南与东南亚民族文化资源的共源性和互补性以及地理上的毗邻性,发展跨国旅游,以自然人文景观为线索优化区域间旅游线路和景点配置,力求既能突出各国、各地特色又能达到整体优化组合。与周边邻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旅游合作机制,实现与东南亚旅游市场的对接,使云南国际旅游业跃上一个新台阶。总之,发挥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云南民族文化区域优势,扩大云南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合作,对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促进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云南特色文化艺术的传承模式
就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手工艺文化而言,其传承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精英传播”,即由各民族中掌握了本民族传统技艺、学识渊博且有造诣的长者充当本民族文化主要传承者的角色;二是师徒相承、家族内技艺相传是主要的传承方式;三是依靠各民族传统节日、习俗、服饰、建筑等外显的文化形态充当传播媒介和物质土壤。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传统手工艺文化传承的外环境改变,生活方式的变革削弱了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传承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历史造诣、现实存在与未来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谱系。建立长效的培养、选拔机制是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有效途径。尤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传人,注重从造物理念、工匠精神、材料选用、技艺传授、审美装饰方面提升其文化内涵,以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提供文化交流机会等助力其提高艺术造诣,在创新中实现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使之成为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中坚力量,以“精英传播”的模式实现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同时,注重以科研带动传承,注重对少数民族手工艺的技术方法和艺术特色进行记录、整理、分类、研究,科学合理制定不同的传承保护方案。研究其在现实文化土壤下的生存空间、产业化可行性、传承传播价值等,遴选科技含量高、文化底蕴浓、具有比较优势的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的先行项目,将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理性结合,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传承。具体策略如下:
1.构建云南民族文化向东南亚、南亚传播的文化传承模式
开展云南民族民间特色文化传播、工艺传承、产业研发、中华文化对东南亚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与建设。通过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元素的系统、深入分类整理,开展云南工艺理论体系构建,在理论指导下,形成一批传统元素突出、现代设计先进的云南特色工艺品牌产品和文化名品。
2.研究梳理云南工艺美术在东南亚传播的路径与方式
调查研究中华文化在与中国山水相连并与云南有着长期交往历史的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条件和影响。掌握云南工艺产品在东南亚、南亚传播的路径与特点,深入了解云南文化产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云南民族民间特色工艺面向东南亚、南亚传播的思路与路径。通过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特色工艺品、文化创意产品在东南亚、南亚的表现方式与传播策略研究。
(三)高层次、深层次文化艺术交流互动的机制
当前,无论是官方互访还是民间往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还是较为传统,即以歌舞表演、非遗展示等为主要形式,其优势是易于被接受,但从长期促进双方、多方的文化互信,实现文化认同的目标来看,其效果还是具有局限性。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具有很多相近的东方文化背景,因为无论是小乘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抑或儒家文化,实质都属于东方文化圈。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家坡和马来西亚领导人都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也曾就儒学与伊斯兰文化交流召开过研讨会,但在亚洲经融危机后未能持续,未形成长久的高层文化精英探讨合作机制。云南作为多种民族文化的聚居地,先天具有不同文化交融、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历史经验,应积极发挥面对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的国际角色,积极倡导高层次、深层次开展对亚洲价值、东方文化价值的再探讨,以高层次、广泛的学术交流,艺术文化共同体打造等方式,倡导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研究,增进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文化了解,增进共识促进融合,增强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南亚的深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