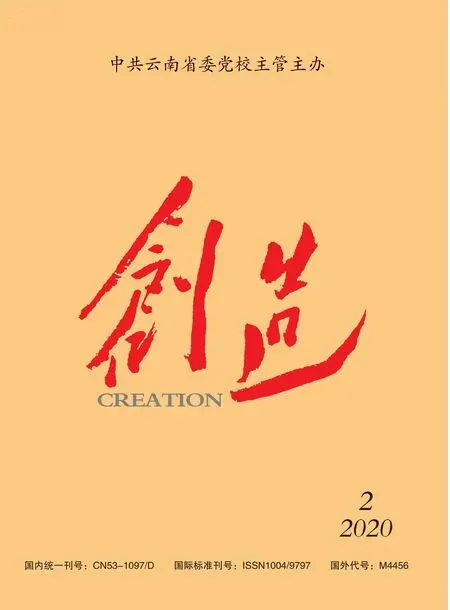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在处理曾静、张熙的文字狱案时的产物。满清政权自入关后,经顺治、康熙两朝数十年的治理,其统治已经得到巩固,但民众对于清王朝正统性的认识还不统一,以吕留良等人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仍然固守“夷夏之防”的传统民族思想。雍正六年(1728年),受到吕留良著作影响的湖南儒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清王朝,声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列举雍正帝十大罪状和雍正继位以来的各种灾异现象,指出岳钟琪作为岳飞二十一世孙且受到雍正猜疑,继而鼓动岳钟琪起兵推翻满清。岳钟琪将此事上报朝廷,雍正帝马上逮捕、审讯曾静,查出吕留良是幕后主使后,雍正帝一方面以“谋大逆”罪严惩吕留良家族,另一方面于雍正七年(1729年) 亲自发动了以华夷之辩、君臣之义为主题的大辩论。经过辩论,雍正帝将案件所涉及的材料和案犯供词等合成一部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并在结尾附上了曾静认罪悔过后所著的《归仁说》。雍正帝将曾静、张熙二人无罪释放,并让他们到各地宣传自己的归仁思想。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公开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清朝的正统性进行辩解、从而加强对全国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①但多偏向对清朝文字狱的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分析书中所体现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并对其局限性进行简要论述。
一、“华夷一家”的大一统观念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大力驳斥了汉族知识分子“夷夏之防”的固有思想,表现出了“华夷一家”的民族观。雍正帝认为:“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1]5-6他认为清朝已经实现了远超前代的大一统局面,不能再以“此疆彼界”来划分华夷。
雍正帝在讯问曾静时说:“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2]178雍正帝在这里驳斥了曾静等人“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的观点,转而强调了“天下一家,万物一源”的理论,认为无论中华还是夷狄,都生在同一个天地之中,都是被天地所孕育、涵养,“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因此中华和夷狄都有接受圣人教化的能力,“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乎”。[2]179可见雍正帝欲通过辩驳传统的“华夷之分”思想来论证他的大一统观点。
在此基础上,雍正帝提出“夷”只代表地域,批判了对于“夷”的文化歧视。他认为:“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2]4他一方面承认满洲是“夷”,“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2]85另一方面又极力淡化“夷”的文化概念,而着重强调其单纯的地域属性,“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2]696同时驳斥了曾静等人以衣冠分别华夷的做法,“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2]211从而进一步说明清朝的大一统对华夷界限的消弭,“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2]3
伴随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观念,雍正帝还提出以“诚”对待各民族的观点:“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2]256在颁行《大义觉迷录》之前,雍正帝就曾主张尊重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3]1101可以说是一种有极强包容性的民族和地域观念。
此外,他也批评了明代君主防范夷狄的做法,“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由此雍正帝认为,历代君主之所以防民防边,皆是因为“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2]255-256他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较为切中要害的,相比前代修筑长城以防御边患、严格固守“夷夏大防”的传统思想,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
雍正帝还认为,“华夷”的概念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2]9-10这种认识相比于前代可以说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在此基础上,雍正帝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大一统思想:“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10在雍正帝看来,在清朝远超前代的大一统局面下,再强分华夷疆界是一种不合时宜亦没有道理的观念。他的这种“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有利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二、以文化论华夷的正统观
在“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基础上,雍正帝进一步提出不应以地域或民族来作为评判君主的标准,而应当以“德”作为评判君主正统性的准则,“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2]1-2
随后,雍正帝举出许多事例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引用《尚书》中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孔子的“故大德者必受命”作为论据,并认为“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进一步推论出“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2]4-5以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传统的圣人入手,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地域、民族评判君主的做法。
在确立了以“德”作为评判君主的标准后,雍正帝评判明代气数已尽,“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而“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清朝取代明朝是“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的,并宣扬了清朝的一系列“德政”,“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由此得出结论:“是我朝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2]6-7,13-14雍正帝以清朝的功绩说明了清朝有“德”,从而肯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此外,雍正帝还为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了辩护。例如他对元朝就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2]16-17,可以说对元朝进行了较汉族知识分子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且批判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外夷”的文化歧视。他认为这种文化歧视事实上对国家的发展有害无益,“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只有对“外来之君”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够对政治建设有所裨益,“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2]17-19雍正帝以少数民族帝王的视角来看待对君主的评价准则,认为应以德行和功业而非地域或种族来评价少数民族君主,这番见识应当说是较前代更为高明。
雍正帝以“德”评判华夷的思想,事实上是一种以文化而非地域区分华夷政权的正统观,他在《大义觉迷录》中也多次借用韩愈“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的思想,强调以文化论华夷的观念,认为在清朝多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下,边疆少数民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礼仪和道德观念,“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2]80-81不应当再以“夷狄”对待。而清朝“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2]81更是早已成为华夏的代表,绝非“异类禽兽”。对于曾静所引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思想,雍正帝认为“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2]81-82对孔子之言进行了新的解读,进一步驳斥了以地域、种族强分华夷的传统观念。
三、雍正帝民族思想的局限性
尽管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表现出的民族思想,既有多民族大一统的包容性,又有以文化论华夷的进步性。但作为一位封建帝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许多认识上仍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这需要我们今天予以客观对待。
首先,雍正帝虽然提倡大一统局面下的“华夷一家”,不应对“夷”抱有文化歧视,但他自己仍然对除满蒙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用了许多贬低、歧视之语,比如他在驳斥曾静“夷狄异类,詈如禽兽”时就说:“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2]80这样的话事实上仍然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此外,雍正帝也时常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3]由此可见,雍正帝的“华夷一家”思想是建立在满洲作为统治核心、满蒙优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基础上,有其前提和局限。
其次,雍正帝为了论证清朝有“德”,过分宣扬清朝的功业和对百姓的恩惠,却对清朝入关前后的一系列弊政避而不谈。他一方面强调清朝是以无与伦比的德行而得天下的,“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另一方面又极力夸大清朝的功绩和“仁义”,不谈清朝入关前后的一系列过失,“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2]81-83雍正帝不承认女真曾接受明朝统治的历史事实,而是宣扬“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反而是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2]12以贬低明朝的正统性来洗脱清朝的“篡窃”之名。可见,雍正帝也将《大义觉迷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极力美化、粉饰清朝的统治。
最后,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归根结底,是以君臣伦理作为核心的。无论是“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还是以文化论华夷的正统观,都是为“君臣大义”而服务。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 中,从头至尾都在不断强调忠君的伦理道德,并将其作为“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2]21-22雍正帝在讯问曾静时说:“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2]254可见他以父子比喻君臣,无非还是要求民众无条件地服从君主,顺之则为良民,逆之则为奸民,从而大肆批判吕留良等明末清初的汉族知识分子,“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2]21由此也就找到了发动文字狱以统一思想的借口。
雍正帝认为,曾静不过是受吕留良蛊惑,“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圣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因此吕留良才是罪魁祸首,“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2]445-446因此对已死的吕留良等人开棺戮尸,并对其家族进行严惩,同时将《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2]25通过这种方式,雍正帝将“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的忠君伦理向全国广为宣传,并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专制。
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作为雍正帝处理文字狱案的产物,集中反映了雍正帝“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以及以文化而非地域或种族论华夷、以“德”评判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相比前代固守“夷夏之防”的传统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性,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雍正帝的民族思想是以君臣伦理作为基础的,雍正帝在提倡“华夷一家”的同时仍然无法消除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以及自身的民族优越感,并借此极力粉饰、美化清朝的统治,《大义觉迷录》也终究成为雍正帝借以发动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并巩固清朝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