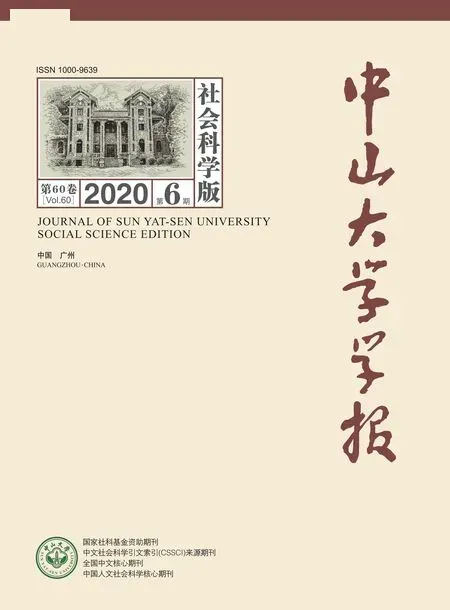读书不肯为人忙*
——胡守为教授学术访谈
胡守为,刘 勇
刘勇:胡老师好!我还记得2002年下半年修读您开设的课程的情形,印象中那是您最后一次给历史系的学生开课了。课程名称叫“陈寅恪著作研读”,后来大部分修课学生的课程报告结集成中山大学历史系刊物《学行》的特刊,题目是《陈寅恪著作研读论文选集》。您还有印象吗?
胡守为:记得很清楚。当时历史系领导希望我能给学生讲点课,我想到陈寅恪先生在我系任教二十年,他的重要著作如《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而他的学术近些年来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理应对此有所了解,于是我开了这门课。先由我对陈先生的学术背景作介绍,讲了四次。然后每位学生选读一篇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由同学评论、提问、质疑,或者借题发挥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再就讨论内容加以补充,最后形成各自的书面报告。没想到选课的学生有六十多人,人多不好讨论,最后确定入选十七八位,大约研究生与本科生各半。
当时我的想法是,学生选读这门课后,对陈先生的中古史体系的主要内容,比如东汉以来儒家大族与寒族的关系、意识形态(尤其是清谈和佛、道之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中本位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进士阶层的兴起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等等,能够具备初步的了解。同时,通过精读他的论文,学生对陈先生引证史料、推论循理的学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博大精深的学识和鞭辟入里的洞见,就不至于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浮泛的想象层面,而是通过亲自接触、切身体会,从非常具体的东西入手向他学习,有所启发兴起,从而进入史学研究之门。
一、从学生到助手的学研探索
(一)只有一个学生的选修课
刘勇:那也是我第一次修读这样的课程,细读和讨论史学典范论文,得下好多功夫才行,印象非常深刻。同样有印象的是,您当初学着做历史研究,好像就是在1950年代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期间吧?
胡守为:是这样子的。但在那之前,我已修读过陈先生的课,已经对我很有影响了。我是1947年考进岭南大学的,但那时候读的是化学系,第二年转到历史政治系的历史专业,后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就改成中山大学历史系了。刚解放那阵子,政治运动多,很多学生都没好好上课,跑到外面去参加运动。但我是绝对不能的,因为呢,有个学期只有我一个学生选课……
刘勇:您是说陈先生的课上只有您一个学生吗?
胡守为:对,只有我一个学生选他的课。大致是1950年,陈先生开的“唐代乐府”课,主要讲韦庄的《秦妇吟》,其中涉及唐朝末年运河一带的军事情况,同时探讨唐王朝覆灭的原因。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选修,我如果不去上课的话,就等于罢课了,所以我绝对不能缺席。这么一个有学问的大师上课,选课的居然只有一个学生,令人感慨!当然,那时候岭南大学的学生本来也不多,全校差不多才一千人,史学专业的学生更少,只有三人。除了中文系学生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有选读陈先生开的课程的。有一天,广东省委的杜国庠来校视察,问起陈先生的情况,学校要我去汇报,汇报完毕后,杜老指着我戏说:“你最值钱了,全校薪金最高的教授教你一个人!”
刘勇:一个学生的选修课,那你们是怎么上课的呢?
胡守为:陈先生是怎么上课的呢?当时他住在中大护养院旁边的东南区241号小楼,不是后来大钟楼对面的那栋东南区1号。我去他家上课的时候,助手告诉他:学生来了。他本来在楼下工作的,听说学生来了,就说声:“胡先生你来了。”——这个事情让我,那个,让我……我当时只是学生来的,但是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他都叫“胡先生”,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的——然后呢,他做什么呢?那时候是夏天,他在楼下书房工作,穿着唐装,他就拿着拐杖,慢慢走上二楼起居室,换一身夏布长袍下来,在楼下走廊里竖立的一块黑板前面,坐在椅子上给我讲课,有时候他还要去那个黑板上摸索着自己板书。这个啊……当时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走路也不方便,但就是这样,他还要特地上楼去换衣服,大夏天的穿一身长袍下来,对着我一个人讲课。这一点真是让我终生铭记!我教书和做学问,很多东西没学到,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里面!
当时他的助手程曦告诉过我,陈先生每次上课前,一定要程曦把课堂要讲的材料都先读给他听。那些材料其实他本来都熟悉的,只是便于他再做思考准备,然后再在课堂上讲,因此他讲课经常有新的内容。对着我一个学生,也是这样子。这种对学问的认真态度,令我难以忘怀。后来我自己教书,始终学习我老师的态度,认真备课,从不迟到早退,仪表要整齐。教得好不好不知道,但始终要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
我的看法是,陈先生不仅自己要做出好的学术研究出来,还要教学生,找继承人,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1950年六月六日教师节那天,我们历史政治系师生送了一面“万世师表”锦旗给陈先生。当时我们还合了影,你们大概都看过那张照片,我也在上面的(见图1)。他是当之无愧的。到什么时候他才不教书了呢?到大批判的时候。当时的学生不知道高低,贴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说他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书,是“误人子弟”!这一点最伤他的心!他在那么艰难的情形下,仍然竭尽全力教书和培养人才,但学生的大字报竟然说他“误人子弟”!这张大字报出来以后,他就不开课了。学校劝他教书,他也不教了。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学校,仍然努力著述。

图1 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师生欢送毕业同学合影① 载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卷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二)研究助手学做研究
刘勇:那后来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担任陈先生的助手的呢?
胡守为:1953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因病没能统一分配工作,留校休养。第二年,系主任刘节先生正式通知我任历史系助教。后来,由于陈寅恪先生原来的助手不辞而别,学校需要给他另找一个。主要有两点要求:一是了解他的学术历程,以便供年轻学人借鉴;二是向他学习做历史研究,同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当时我推荐了两位很有学问并且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的人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陈庆华,一位是武汉大学的石泉。学校就联系调人,但这两位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教师,原单位不愿放人。学校最后让我来填补,我自知不够格承担这个任务。学校说,那么我们先去问问陈先生,由他来决定。随后就由副校长陈序经先生去征求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他说同意。我就这样成了陈先生的助手。
在学做历史研究方面,陈先生要我补《资治通鉴》的唐代部分。我感到为难,因为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编《通鉴》时能看到的材料,很多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而且,明代学者严衍又曾写过《资治通鉴补》,对《通鉴》的遗漏讹误已作过补正的工作,我怎么再做呢?陈先生说,你用出土的碑刻资料、考古材料为主,辅以其他传世材料,就能把它补起来。这就是我做学问的开始,是从陈先生指导我读《资治通鉴》入手的。后来我教学生,也很注重让他们留意碑刻资料,也是根据老师教我的。除了这个之外,当时陈先生还嘱咐我学习名家的著述,先做一些笔记,从中选择一些问题,寻求自己的答案。选择的问题大抵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具体做的问题可以小,但是要有由小观大的意识。当时我很认真地读陈先生的著作,但感觉再要提出些什么新问题却很困难。
后来学校说,陈先生跟校外学者交谈的时候,你也要去好好听、好好学。我就问陈先生,你跟学者谈话的时候,我可以旁听吗?他说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旁听了一些这样的谈话。但我觉得很惭愧的是,他们谈的都是很深入的问题,当时没有录音机把它录下来,我只能力所能及地了解和记忆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西域史专家、北京大学的向达教授专程来广州向陈先生请教有关《大唐西域记》的问题。我旁听了,但由于基础太差,很多东西都记不住或半懂不懂,也没法完全记下来,只记得其中一项是,陈先生说玄奘有些梵文读音不准,因此在使用对音考证时就需要特别注意。陈先生懂多种文字,特别是古文字,但他很少用对音考证,这也是治学谨慎的态度。
今天说起我的最初学术经历,大致上就是如此。说起来我感到很惭愧,本来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应该有比较大的长进才好,可惜我学得不好,仍然很浅陋。所以,我在自己的著作里面,极少提到恩师,我不是不尊重他,而是面对这样的大师,我自己不敢认。但是,这些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二、在汉魏南北朝史园地耕耘
(一)转向汉魏南北朝史
刘勇:您刚刚介绍了您作为仅有的一个学生选修陈先生的“唐代乐府”课,以及您作为助手受陈先生指导做《通鉴》唐代部分的考补工作,但后来您的研究重心是怎么转到汉魏南北朝史的呢?
胡守为:陈先生在隋唐史领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研究里面,这两个时期是有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的。因为他着眼的并非某些孤立的事件,而是历史演变发展的整体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他的这个学术眼界和规模是很高的。从东汉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非常重要变化的时期。东汉还是门阀政治的时代,门阀占据政治、文化的主流。这个情况引起那些非门阀士族的反抗。以曹操为代表的庶族,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打倒了门阀士族,但是在文化上,门阀士族仍然居于领导地位。所以,曹魏集团必须要在文化上超越门阀士族,它才能比较长远地立定脚跟。对于这个变化,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清谈的演变》。门阀士族的文化,主要就是倚赖儒家的经典,所以庶族转而采用道家的学说,崇尚自然。儒家讲道德伦理,道家崇尚自然,从自然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社会。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关于才性、有无问题的分歧。才干跟人性的本质有什么关系呢?门阀士族讲究血统论,先天血统高人一等,后天的才干跟这个联系在一起,也高人一等,先天血统跟后天才干紧紧绑定,这个就是所谓世界起源于“有”——先天就有高下之分的,后天才干决定于你有没有先天高贵的血统。对这个问题,庶族当然不能承认,所以就采用道家的学说,崇尚自然,提倡世界起源于“无”。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一切东西的起源,叫做“无”,由“无”产生万物。人的起源也是“无”,所以人的本性是平等的,都是起源于“无”,而才干是后天的,后天的才干高下优劣,跟先天是否出身门阀士族,没有必然关系。从理论上论证这个问题的,就是所谓的玄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贵族阶段到庶族阶段的重要线索。这个长时期的变化直到唐代才真正演变结束,具体来说,就是结束于唐代中期科举制度的形成。
唐代的考试有两种办法。一是明经,背诵经典及其注解,类似于做填充题,填好就过关了。二是考进士,考诗文和对策。诗文是很考验才华的,里面有很多讲究,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边谈了很多,谈得非常好。所谓对策,就是发表你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比如,就像今天突然出现新冠病毒疫情,你认为该怎么办?当时有句话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的,已经嫌老了;五十岁考中进士的,已经算是很年轻的。言下之意,明经很容易,考进士太难。
所以,虽然最初修读的是陈先生开的“唐代乐府”课,他指导我做的是《通鉴》唐代部分的研究,后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到汉魏南北朝,但其实主要也是跟着陈先生对中古历史的整体性看法的脉络走的。
(二)岭南古史探研
刘勇:谢谢胡老师!我的专研领域是明清史,已经好久没有认真学学中古史了,听您这么一讲,感觉真是非常受益。我自己是在四川出生长大的,1998年念大学才跑到广州来,当时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语言、饮食、习惯都太不一样了。课余跑去五层楼(广州博物馆)玩儿,也很惊奇那里面陈列的古代岭南文物。在历史系资料室看到《岭南古史》一书,就忍不住拿来翻,后来才知道作者就是您。接下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关注到岭南古史的?
胡守为:因为我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一直都生活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应该对这片地方有更多了解,而中山大学就在这个地方,也应该让学生对这地方有所认识,所以开了“岭南历史”这门课。经过长期讲授,后来把课程讲义整理出来,就是这本《岭南古史》。同时我也关注一些专题,比如我一直留意赵佗政权的历史,最近我才修改完一篇旧稿《南越国史事辨释》,试着搞清楚从赵佗到赵建德的世系和政权情况,尤其是他们跟中原政权之间反反复复、虚虚实实的关系,希望可以纠正和补充《史记》《汉书》《通典》《通鉴》等传统文献的记载。
我觉得我们研究岭南古史需要留意一些东西,尤其是当我们长期身处岭南的情况下去研究它时。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后来的,尤其是现在的普通观念去想象那个时候。对于秦汉以前的中原王朝来说,岭南只是一个很泛泛的观念,实际上是没有实质性的行政管理的。秦始皇立三郡,但并没有真正的行政班子。直到赵佗,才真正有一套管理的班子,他的管理范围,直到今天越南的中部。
刘勇:我在岭南一晃也待了超过二十年了,平时也会留意一些本地的历史记载。但中古时期以前的岭南,文字记录相当少,在五层楼参观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对我们高度倚赖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来讲是很不习惯的,针对这种情况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胡守为:的确,岭南古史的文字记载很少,而且很分散。一方面,当然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熟悉传世文献,掌握文字记录。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考古的东西,搜集和利用出土的资料。这方面,最近几十年来广东已经有了比较可观的进展,南越国的资料出土了不少,我们对赵佗及其时代的了解,就超出了历史上的很多文字记录。秦汉时代,这个地方大都是部落民族,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掠夺和战争频繁。但赵佗把这种情况平定了下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所以汉高祖封他为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和辑百越”,就是说他使各族之间的掠夺争斗减少了,使得南越地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这是赵佗在南越的重要功绩。
(三)道教史研究
刘勇:我注意到,您整理出版的《神仙传校释》,上个月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字版。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道教史研究领域的呢?
胡守为:我留意道教史,既有陈先生的影响,也有我自己关注汉魏南北朝史和岭南古史的因素。汉晋历史本来就跟早期道教密切相关,谈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不能避开道教不谈,比如前面提到过玄学清谈,崇尚自然,有无之辨等等,都是如此。同时,道教跟古代岭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罗浮山,所以我在《岭南古史》里面专门有一章讲岭南早期的道教。
陈寅恪先生讲过道教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怀疑有些东西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我觉得这点很值得留意。我注意到,早期道教对水非常重视。东晋五斗米道的孙恩在战败之后,就是选择跳水自杀,据说后来还变成了水仙。道家说,水是属阴的,火属阳,水能灭火,阴克阳也。《神仙传》里面凡是讲到男女斗法的场景,肯定都是女的赢了,这也是所谓阴胜阳也。道教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水滴石穿”,水是阴性的,水滴虽小,但它能够把石头贯穿。这是道教非常特别的观念,很值得仔细探讨。
刘勇:您还研究过早期道教的政治倾向问题吧?
胡守为:是的。陈先生写过《崔浩与寇谦之》,我最近也在写一篇他们跟道教关系的论文。崔和寇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贵族政治。寇谦之对道教做了很重要的改革,改革汉末农民起义信奉的五斗米道。他认为这个不是道教真实的东西,他把儒家的礼法拿来取代五斗米道的条文,从而形成了天师道。改革的重点,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取代五斗米道的内容。其实当时在佛教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著名的法显和尚去印度取经,很重要的契机就是他发现中土佛典中有关戒律的内容,用当时的眼光来看是很不完备的,所以希望去找跟儒家规范比较能够协调起来的戒律方面的东西,这也是魏晋六朝文化的重要问题。
三、教书和做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
刘勇:您从1950年代就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这么多年来,请问您在开展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基本的考虑和做法?
胡守为:这个仍然得从陈先生讲起。关于教书和治学态度方面,前面我已经讲过一些了。我觉得现在介绍陈先生的学问,有的没抓住要点,比如强调他懂多少种外文。这不是主要的。他在德国留学时,专攻比较语言学,除学习多种古文字以解读古文献之外,还以西洋语言科学方法作为认识事物的办法,简言之即两种事物互作比较,得出其各自规律及特点。第二点是陈先生常用诗文来观察历史。他认为文化乃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①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他主张研究工作要“脱俗”,要摆脱“俗谛之桎梏”,即努力摆脱那些固化的常识、陈见、思维,致力于学术创新。他在欧洲学语言也好,懂多少种语言也好,都是为了研究工作能够“脱俗”,致力于把中国史学带到世界前沿。这才是最重要的。
前些年,清华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发言讲陈先生的学术启示。后来,《人民日报》的记者让我把发言整理给他们发表,题目借用了陈先生的诗句“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治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有创见。读书不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不是为了秀自己读了多少书,懂了多少东西,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这是他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当然,独立思考、学术创新谈何容易。尽管如此,我也始终坚持要求自己,希望在我自己做的研究里面,哪怕有一点点是别人没有讲过的、没有做到的也好。
刘勇:对于我们今天的读书、教书、做学问这些事情,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胡守为:对于当前学术界的情况,我觉得要留意的是,不要让浮躁之风漫延。所谓浮躁之风,是指不做实在功夫,标新立异。陈先生讲“脱俗谛”,首先就是不要受现在不良风气的影响,要立定志向,争取有所创新。我自己写文章,写好之后先搁置起来,不断思考、修改,最后不一定是最完善的,但应该是做到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竭尽自己的能力。这也是学陈先生的。
陈先生的论著常常用“稿”命名,也有这层用意,期待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臻完善。我当他的助手时候,其中一件工作就是协助他修订著作。有些地方他认为需要改的,叫我去帮忙查材料,然后读给他听。他的《元白诗笺证稿》里边,有一处就是提到我的:白居易《新乐府》中有篇《两朱阁》,里面讲到唐德宗的两个公主,但陈先生写书的时候还搞不清楚这两个公主的名字,只能有所推测,“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当时高教部正在统编教材和配套的参考资料,由于我们系的系主任刘节先生应调去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因此隋唐部分就分给我们系了,我作为年轻教师参加了这个工作,负责赵州桥、长安资料的编注。我在读《唐会要》《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时,发现了这两个公主的名字,我就告诉陈先生。因为在那之前,《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出版之后不久,陈先生就送了一本给我,还请师母题字钤印(见图2),我对里面的内容比较熟悉。后来,陈先生在新版里面还特别写了这个事情,“癸卯(1963)春胡守为君检出下列资料见告”云云②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29—230、378—379页。。我记得当时陈先生还有一句感慨,大意是说“十年迷雾,一朝复明”之类。这个事情同样体现了陈先生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这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图2 陈寅恪先生题赠胡守为《元白诗笺证稿》初版书影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广州: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1950年,岭南学报丛书第一种。扉页题字乃陈寅恪夫人唐代笔。
我知道我们历史系有个好传统,所有导师都要求指导的学生好好读陈先生的著作。当然不是要求大家都来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但通过读陈先生的著作来揣摩、提升自己的专业思维和方法,学习他那种做学问的精神,是很不错的。我读了这么多年陈先生的书,有些我还是没能读懂。他的著作确实深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兴趣、领域来进行吸收和消化。尽可能地先学步,努力提高一点点,然后再寻求突破。
《柳如是别传》问世以后,评论意见不一。后来我们学校召开过三次陈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我负责过相关的会务筹备工作,其中有一次就是专门讨论《柳传》的。我自己仔细读了两遍,有两点体会。第一是史学方法上的诗文证史。很多人不理解,怎么浪费力气去给妓女写史呢?但要注意的是,柳如是不是我们现在观念中的妓女,她有点像日本的艺伎,是陪客人吟诗作对、讨论学问的人,她的诗文写得很好,而且跟她交往的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学问家。陈先生就用他们留下的这些诗文来证明末清初文化、政治、军事上的大问题。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已经很成功地示范了“诗文证史”,但那本书里面都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各篇之间还不十分连贯。《柳如是别传》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大工程,是一气呵成、首尾贯穿的,对诗文证史的运用达到纯熟的境界。有明清史专家读过《柳传》后,跟我表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原话来的。第二是表彰自由思想。这个在书中的“缘起”部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仅非常欣赏钱、柳的才学,“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更认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妇女所具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尤其应该珍惜引申。
刘勇:《柳传》的确好难读。我们不少同学受到感召,从本科开始就雄心勃勃地试着去读它,当然啃不下来。我自己也反复尝试,除了诗文集之外,近年来我试着先集中读些明末清初的戏曲小说,比如《桃花扇》《再生缘》《儿女英雄传》等。回头再去看《柳传》,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柳传》蛮有些戏曲小说味道,而陈先生自己竟然也经常跑进书里面去打趣、揶揄、嘲笑一番。这是跟陈先生那些“研究”味儿明显的著作很不一样的,感觉上他既是在做研究,也是在写史,写传奇,写戏曲,写小说……我也在准备着给研究生开一门《柳传》研读课程。
胡守为:这个很好,应该要好好研读《柳如是别传》。是很困难,里面涉及到大量的诗文考证,各种各样的古典、今典,有些很细腻、很含蓄,难度很大,但应该要迎难而上,认真读它。
有人不理解陈先生的“繁琐考证”,那是因为还不明白那些考证的用意。陈先生认为,论史必须立足于史实,考证的用意就在此,往往还可以以小见大。我举一个熟悉的例子,比如关于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讨论白居易《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个事情,有人就认为,一个商人妇半夜三更跟白居易喝酒这种生活琐事,无关大体,不值得花笔墨去考证。但陈先生对这个事情的周密考证工作有他的重大关怀:一个是从中看出唐代社会文化的整体风气变化,高宗、武则天之后,那些由科举出身的士人,跟以前的山东士族相比更加放荡不拘礼法;而当时社会下层的女子没有地位,士大夫跟她们之间的去留离合,本属寻常,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也不以为意。第二个是根据唐代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来驳斥宋代洪迈评议白居易夜入商人妇船为不道德之说,认为他只是用宋代道学先生的礼教来非议唐代士子的风尚,从而也证明唐宋两代在社会道德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反映在男女礼法上就有很大不同。
我一生受陈先生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书和做研究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我们对这两件事情都不能不严肃对待。我在历史系和学校都做过一点行政的工作,尤其是做副校长期间,会比较忙碌些,但教书和做研究这两点是必须严肃对待的。第一,我是个教书人,做了行政以后,教书不能停,我要继续开课。而且我事先声明,如果跟我的上课时间冲突,我是不去开会的,我要上课。第二,当时我负责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正在统稿,我有个已毕业的学生帮忙在西樵山找了个地方,以便我和两个助手在那里“闭关”工作。我就告诉学校,我要去那里两个月,集中精力统稿。学校说开会怎么办?最后大家协调,开会时派车把我接回来,会议结束后就回去继续“闭关”。
今天就谈这么多吧。主要围绕陈先生的治学精神,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与诸位共勉!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正!
按:本文由刘勇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录音不清晰之处,主要根据胡守为所著《胡守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的有关论述酌补,个别内容另检相关资料予以充实、修订。初稿形成后,曾请胡守为先生审定。访谈过程中,承蒙黄友灏博士协助录音和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