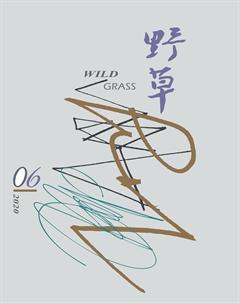秋日
存朴
清晨
清晨自黑暗脱胎。那些醒得早的人,总是最先迎来鸟鸣。几声鸟鸣,仿佛经受一番沉寂而得欢喜,仿佛幽闭之后,听到的第一声问候;这样的欢喜庄重和自然,这样的问候,流溢着类于重生的慰藉与欣慰。鸟声带来清醒,空中慢慢投射出来的光亮带来清洁之感,这样的清洁之光让人安心,也让人在推开门窗的一瞬,内心充满久别的温暖和希冀。秋天的鸟声总在低音部流连,清隽且细长,似乎浸染了夜的余绪和晨曦的洗礼,直到远处传来穿透力很强的斑鸠叫声,那棵高大繁茂的细叶榕枝叶间的鸟声突然就安静下来。鸟鸣引发而来的清正美好或思想力,如同某种沉默时的力量,足可匹敌二战时纳粹那种狂热喧呼的万众拥集场面,如同巴赫《马太受难曲》或沃伦诗歌《世事沧桑话鸟鸣》,足以抵抗一场巨大的纷乱。力量的持久与强大,很多时候,不是来自数量的多寡或声量的高低。
树木还是夏日那样,绿得沁人心脾,每一片叶子像婴儿的眼睛,天真而纯净,在晓风中眨动着。这是南方的细叶榕。老叶与新叶簇集于同一棵枝干,老叶深黛,隐伏在晦暗处,新叶在枝丫上层,绿而稚嫩,细细密密,初看就有婴儿眼睛似的特征。如果树枝里的鸟声再清亮一些,看那些叶子的感受就更深了。清晨看见这些树叶,总会想起从前爱人抱着儿子在老屋戏耍的情景,总会想起儿时,母亲带我去河边打水的情景。老叶复新叶,一代复一代,循环,更迭。
此时,天空完全敞亮。露珠在灌草上亮得耀目。露珠只有在光照里,才能成就其晶莹剔透的品质,又因晴光的持续不退,很快消弭于空气中。露珠的命运,像是打上了某种戒律,又像施了某种诅咒。如同人世间,越是璀璨夺目的事物,越是难以持久;越是质朴如草木,越是恒久如常。相对于草木历经春秋的韧性,“当下即永恒”,说的大抵是这种惊鸿一瞥的露珠,这种惊鸿一瞥的事物,映照着“存在”的良知和内质。
通往弘法寺的绿道人影寥寥。几位清扫工像寺前的扫地僧,每天早起清扫著这里的路面,细碎的枯叶和光同尘,在竹帚下翻卷;翻卷的枯叶之上,是清洁的晨光和蝴蝶。树林深处,寺里的钟声响起来,清晨无由地宁静着,又像打开一篇启示录之前的片刻静默。
清晨是一日之中与深夜时分相似,同样让人虔敬、感动与遐想不止的时刻。
果园
果园冷清在黄昏的天色里。在黄昏的天色里,果树的枝叶垂下来,垂下来,垂向同样冷清的泥地上。泥地上是一队蚂蚁,一队蚂蚁爬过几片残叶,往草丛中爬行。草丛低矮而芜杂,草色欲黄未黄,已经干败下去的,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藤蔓植物,它缠绕在草茎上,枯干的叶子黑中带灰。蟛蜞菊贴地蔓延,青叶之间,开出黄灿灿的细小花瓣,似乎生长的气息一直在果园里弥散。然而秋分之后的果园像人去屋空的旧日村庄,空落,沉寂。果树都有四十年以上的树龄。我见过果园最繁茂最热闹的季节,荔枝成熟时,山谷里人声鼎沸,摘果子的、看风景的蜂拥在果园,地上到处是零落的树枝和丢弃的果子。果园主人说,人们爱的是热闹,不是果园本身,爱的是那果肉进入口腹的满足,不是果树本身。从一九七八年种下第一株龙眼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山谷中这片斜坡就辟成了果园,种了龙眼、荔枝。几十年过去,果树们虬枝峥嵘,已经到了处变不惊的样态,像步入暮年的老人。
果园距离住所大约四里路,是我下班后最常去的地方。如果走路,到达果园时,夕阳行将落山,那最后的金色光芒,让果园神性一样迷人,每株果树都仿佛有着神的语言,一种爱与恩典、善与悲悯交织的语言,是远自古代经义、诗歌、艺术所传递下来的精神内核,是自然之界的布道——坐在果树边,我处于某种失语状态,直到那道金色光芒逐渐消隐,黑暗将果园揽入怀中。如果是骑行,十几分钟就能抵达果园,我有足够的时间访问那些果树。果树们相邻而生,枝丫相连,一片叶子,就是一个春天的消息,一枚果子,就是一个秋天的承诺。看果树的过程里,潜意识总是无端地将人事与果树勾连起来,记忆由此有了缘起和托付。有时候想起父母,有时候想起某个早年的亲邻好友。我想着他们有趣无趣的往事,想着他们说话的神态、语调和某几句话,想着他们的坟地。更多时候,记忆回到某个秋天,回到秋天落叶纷纷的山坡。我想起十几岁时的丘陵地上,乌桕树上缀满白蜡果,鸟雀云集,我们举着勾镰将果枝勾下来,再把白蜡果采下,拿去收购站换零花钱;西风吹过田野,晚稻涌起金色波浪;橘子也熟了,橘园充溢着季节之香;野葡萄也熟了,拐枣也熟了,还有柿子、石榴、野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个消失的秋天好像就在眼前复活,却难以说出关于秋天的全部,如同一个个故人好像就在眼前,却难以说清他们的全部。
表弟二十几岁时和邻村一个女孩相爱,女方父母嫌弃他家穷,全力反对。一个秋日的傍晚,表弟带那女孩走十五里山路躲到镇上来,母亲劝了半天,心一横,就留他们住下。后半夜,女孩的母亲循踪而来,在我家哭闹了一场,躲在阁楼上的女孩耐不住,自己走了出来,母女俩抱头痛哭,竟然回去了。表弟显然受到那个家族的恫吓,很多天不敢回家,每日耷拉着脑袋,跟随我们去山里砍柴。树林中有几株野柿子树,红彤彤的柿子悬坠在枝头,像一个个悬坠着的小小红灯笼。表弟爬上去摘柿子,神情一扫几日的颓废,淌汗的脸面笑嘻嘻的,像忽然之间得了什么好的消息。好几年过去,表弟终于娶了另一个女孩,发誓要把日子过好。农忙时,他租种了十几亩水田,种上烤烟、莲子,农闲就去福建做小工,每天搬运电网水泥杆,随着一儿一女出世、成长,他似乎要拼命一样的劳作。我在外地定居,彼此难得一见。最近的见面是两次,一次是二零零五年春天,我去探望垂危中的姑姑,一次是三年前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次葬礼,他匆忙来去,说是农事太紧,白天在田里忙,夜里在屋里“做莲子”(手工加工白莲),有时候忙得没空上床睡觉,累了就喝几口烧酒提神。他笑眯眯地说着自家的农事,像谈论别家的事情。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老家传来消息,说表弟在采莲时突发脑溢血,半天时辰就过世了,寿年仅四十九岁。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通往果园的路上走着,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砍柴的秋日,表弟攀爬在树上摘果子的身影,那么年轻。
我在果园里坐了很久,很久,直到看得见天上的星星,在一片秋虫声里,默默离去。
河与河水
河是人世的源头之一,河水是日常生活的《圣经》或凝神之际的《心经》。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住在河边。一条清澈的河流,有芦苇、蓼子花、茭白、垂柳护岸,有水鸟低回、鱼虾戏游,白日可以在水边放歌,可以入水濯身,夜里听河水拍岸、清水滔滔,可以安神,可以跟随它流逝的节律梦游四方。我想着这样一条河流的时候,已经失去这样的河流几十年。身居的这个临海城市,没有河流,只有人流车流,只有夜晚不熄的灯光之流,即便市郊山海相连之地,所见不过是海与天与山相接的景致。我钟情的那种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河流,那种可以与人相伴为居的河流,是几无重逢的可能了。
在赣南丘陵东北端一个叫小松村的地方,那里的河流没有名字,习称“河”,“去河边”“在河边”,人们日常里总是这样说着,后者说的,就是我家那样的人家。屋子临近马路,与河相距不过百十米,河对岸是大片水稻田,再远点是重重丘陵,山冈长满马尾松、杉树、黄檀、枫树、樟树、木荷树、红杉树,等等,灌草密集,野花野果繁盛。这样的生态环境,让那条河丰饶而清澈。河水发源于西边崇山峻岭之中,逶迤向东而南,好像一个巨大的“7”字,转折处,形成一个河湾,河湾边有个水陂,陂上一排大跳石,供人过渡。河湾东沿是马路、村舍、菜地、后山。我家的几间屋子独立于村舍最北端,去河湾、水陂、菜地的时间大致相当,不足半支烟工夫,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水与田野更为亲近。在我们家,去河边和水陂总是说成“去坝里”,去坝里洗衣服,去坝里洗菜,去坝里挑水,去坝里晒东西,去坝里割草,去坝里捞鱼。亲人去世,第一件事就是到河边打水给逝者洗身,逝者安葬后,最后一件事是在河边焚化旧物、冥纸和灵屋。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日子是如何围绕着一条河流展开,又如何把临水而居的生活往纵深处用心用力。这已是三十年前的光景了,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河与河水,以及沿河两岸的四时风物,融汇在烟火人间和梦境之中,凝聚成骨骼与血液,时间越久远,越是生动和清晰,让人痒痛不已,又无可如何。
我曾经在各种媒介上试图找到三十年前的那条河的点滴细节,也曾在画纸上、在文字里,试图局部还原河两岸的某些事物。那是一种怎样的徒劳之举。这个秋天,读一些人的山水画,马远、范宽、黄公望、虚谷、沈周、黄秋园、吴冠中,这些或古或今的画家画作,各有渊源,又自成一格,没有谁的一幅画可慰藉我时常想起的那条河流,我能寻找的,只是它们蕴含的绘画语言,草蛇灰线,伏行千里,那种怀念感尤为强烈。作为江西同乡,我后来对黄秋园先生的绘画特别留意。年轻时去亲戚家做客时,多次去过画家的故乡南昌县黄马乡,那里的白虎岭很像老家的山岭。记得一年秋间,我从梁家渡下车后,走了一个多小时,黄昏时的黄马乡特别美,半轮红日挂在白虎岭的峰际线,田野和村舍一片彤红,炊烟升起,稻田正在收割,稻草随意地堆垛在村道上,很像老家秋收的场景。那时我不清楚黄秋园先生的故乡是黄马,走在那样的村舍之间,我就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也许能走到一个辽远的地方,也许,再也走不回来了。
与老家那条河最近一次的亲近,是三年前葬完母亲那天,我们去河边烧灵屋。村舍已经扩展至河湾以北,从前遍生芦苇、茭白和杨柳的沙洲,空空荡荡,垃圾淤积,河面变得狭窄,河水不再澄澈,大跳石换成了水泥墩。若是站在对面的山岭上,看见的可能是一条细细的灰白的带子。烧给母亲的纸扎灵屋和旧衣物堆在河岸的沙滩上,当火光升起来,当乡村道士吹起唢呐,我们跪在沙草里,看见火光投映到浅浅的水面上,这个时刻,好像也在为那条河、为过往的一切招魂。
沙洲
闭起眼睛。看见一个男孩,正在沙洲的树林里游荡,前面低头吃草的黄牛像一位从容的伙伴。看见一群孩子,正在沙洲的树林中捉迷藏。风从河上吹来,风穿过密密的枝杈,让一群孩子的游戏意味深长。看见那些树,看见它们开出的白花、红花,看见它们的叶子在风里翻卷飞舞,看见它们在沙洲聚合出一团巨大的绿云。看见春日桃花的红、桐花的白,两种花,一前一后地开,前者总是让他想起《葬花词》,想到死亡,后者,卻总是让他想到热烈的、明朗的生长。他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想。他对潜意识毫无办法。
这些幻觉中的图景,不过是他散失多年的碎片,是让他至今困惑不已的某些线索,某些微茫又不可或缺的线索。他说不清“线索”的具体涵义,又似乎一旦离开这种“线索”,他便不再是他了。然而他清楚没有成为那个“自己”。他怀疑自己,如同他怀疑那些图景的最终消失。那些图景的最终消失,仿佛树上的叶子,一夜间全部被西风收走,如同一夜之间,大雪覆满原野。
秋分日那天下午,他坐在海边一座山上休息。他骑着山地车,从山脚一路往上。一路的绿树,花很少,他只看见路边的树上,紫荆、黄槐决明正在开花,紫荆花紫红,黄槐决明花金黄,更深的树林中,可能还有其他什么草木在静静地开花,他觉得那些花很陌生,那些花即便开在眼前,如此真实,都不是他想象中的往日的花,因而失了兴趣。他只想快点登顶,去更高的地方看看,看看秋分到了,南方天空的流云与山头的风有什么变化。到达目的地时,他累得气喘吁吁。他把车子靠放在一棵树下,坐在一块石头上,喝水,吹风。山上风大,空气干爽,流云好像被风吹得比往日更高更远,往天空深处飘移。他希望看见一行大雁,排成“一”字或“人”字从头顶飞过。他知道那是徒劳的。倒是此前的某个傍晚,他看见一队大鸟列队飞过东湖上空,那鸟阵,很像长途飞行中的大雁。他周围的一些徒步者也看见了,嘴里喊着“大雁”“大雁”。几天后,本地报纸发布了一则新闻,观鸟协会的资深专家在采访中告诉记者,那注定不是大雁,而是普通鹭鸶。他觉得扫兴。
这种时辰,他忽然就想起沙洲来,想起沙洲多年前的样子。几百株的桃树、梨树、油桐树,簇生在沙洲上,形成一片林子。树林间的沙地上,灌草齐腰丛生,鸟雀们在其间筑巢生息。林子里,春绽繁花,夏秋结果,临河湾的一面,杨柳满堤,河水流拂;林子西向是成片水稻田,乡村小道从田野穿过,往上游延伸……
沙洲曾经是他的伊甸园。他想起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就想起那些不曾谋面的前人。那些自称客家人的前人,定居到此,种下沙洲上那些树木,开辟出那些田地,让沙洲与河流、田野与树木围护着村舍,他觉得那是一群深谙“万物兴歇皆自然”的诗者。
沙洲的消失是从他们这代人砍树、垦地开始的。那些桃树、桐树、梨树、杨树、柳树,一株株被砍到,被连根拔起,被大火焚烧,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草木深处的田鼠、野雉、草兔、长蛇、水鸭、野鹭四处逃窜,一一成为刀下猎物,雀群被烟火熏得急急掠过低空,吱吱乱叫;沙土被深翻三尺,种上西瓜、豆角、辣椒、红薯、花生,或任由其荒芜着,蒿草一年年疯长。后来有人在那里种上巨峰葡萄,沙洲上竖起水泥栅栏、搭起木架,还没等葡萄长出来,一场洪水,就把葡萄树扫荡一空。还有人在上面养过黑山羊,也不知什么原因草草收场。不断有人打着沙洲的注意,盘算着各种计划,最终都是枉费人事。沙洲终究是荒败掉了。每年春夏,河流泛滥,浊浪排空,漫过沙洲,漫入稻田,那些禾苗、瓜菜夹杂泥沙汹涌地翻滚着、沉沦着。大水之后,沙洲一片淤泥卵石,空空荡荡,像遭劫一样。
他和他的同龄人,以及未至将至的人们,永远被逐出那个伊甸园一样的所在,从前的沙洲,成为他和许多人的“乌托邦”幻境。剩下的事情,就是像他这样,头脑里总是无端地产生关于沙洲的回望与自省。他知道年岁渐老,他早已不是他。他知道自己犯过的罪过和弃绝的事物,然而谁也无法阻止他想起沙洲,包括他自己。
秋日
这一日,骑行九十多公里,先是国道、县道,再乡道,再土路,来到一个山谷,道路就消失了,像一支独奏曲演奏到最后一个音符时的戛然而止。不必要掌声,因为孤身而行。
灌草下,一条小径若隐若现,不时可见千脚虫在泥地蠕动。树林深处,有片地势高阔的空地,长满蒲苇,蒲苇矮小,丛生着,杆叶柔弱,开着一缕缕白芒花,在下午西斜的阳光里,显得柔软而贞静。草地西边一条溪流细细浅浅,水很清冽,偶见一二片枯叶飘浮其上;溪床卵石累累,看得出夏季山水猛涨时的气势。
四野无人。春夏季来这里爬山、溯溪的人,一个都不见。
这是农历九月十五。寒露刚过,霜降还没到,山上还是有点秋天的味道。风吹树叶的泠然之声,树林深处的山雀啁啾,让几分冷寂感浓郁起来。好像有一声唿哨,从我的口唇之间脱出,应和着这样的时辰,这样的山野。
在草地找一块平缓地,架起帐篷,固定好地钉,铺好防潮垫和睡袋,再把山地车横放在帐边,天色就暗了下来。坐在帐篷里休息一会,到溪边取水,洗脸抹身,浑身的疲惫和尘埃似乎洗得干干净净,人也清爽许多。人一旦清爽,思维的枯枝就从地面弹起,在长空划下苍劲的一笔画痕,形似鸟翼的奋力一击。
这个叫象头山的地方,距离最近的小镇也有十几公里。我不担心夜里遇上什么动物,反倒不希望遇见同类,那种类于月黑风高的背景,曾经良久地侵染,修改着一颗良善到单纯的头颅,脆弱而害怕伤害,伤害他(它)者。置身黑暗的时候,请原谅我以幽暗之心丈量人世。
孤身,如镜中观心。
往嘴里送干粮时,触及胡须,胡须又长出一截。一日之工,密而粗硬,像年齿的疯长,疯长的年齿,像身边一刻不歇的溪流。一个盛大的秋夜君临身边。到这个季节,该开的花已经开过,该结的果子已经结过,该减省的必然会减省,该珍藏的必然会珍藏,该落下的树叶,也必然地落下。人也一样,走到年齿的秋季时,就是凉薄,也不失温煦在怀,一个清爽利落而金声玉振的季节,一个星空一样的精神指向。
不知理查德克莱德曼写下《星空》时想到些什么。作为听众,这首钢琴曲适合秋日,适合孤身时,适合秋日的山地,适合躺在帐篷里,平静地听。作为听众,我没有在钢琴曲的节奏和声音里想到太多。我只是觉得,《星空》配得上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看得见满天星星的夜晚,在一个叫做象头山的某个山谷中,在草地上,在溪流边。
夜深后,我把随身带来的某本书也放进了包里,关掉强光手电,睡去。当我醒来,起身拉开帐篷的时候,另一个秋日的初阳,正从溪那边的树梢上漫射下来。
乌桕树
隔一段时日,我会去附近的大和村看树。那是一株祭祀之树,深圳本地客家人唤做“伯公树”,树下有间一米见方的神龛,名“伯公庙”。目测树高约十米,树冠覆影二十来米,主干直径至少在五十厘米以上,树龄少说也是近百年之久。一株从表皮到骨骼透出森森古意的老树,只有不多的老人能脱口叫出名字——“乌桕”。客家话,“桕”字入声,轻而短促。我问过许多本地人,都说不上树名。也难怪,这株乌桕若非祭祀树(客家人通常把一株古樹视作土地神),恐早已化作薪柴之灰,连树兜也不会留下来。谁有闲心付诸在树木身上呢。城市扩张多年,大和村鳞次栉比的房屋与繁华的市声,把人们的早年记忆抹除,将旧事物连根拔起,即便“大和村”这个农耕时代的称呼,也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念叨着。
据说,几十年前平山挖土建房,本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请人在乌桕树下砌起一间水泥神龛,里面供奉着保佑地方平安的“伯公”泥塑,那树才得以留到现在。树一旦罩上神性,就有了某种无形的法力,某种无形的法力,容易让人畏而敬之,树被圈起来,被顶礼膜拜。比如二月二伯公生日、除夕日,树下必然地香火缭绕。有人身体欠安,或家中横遭灾逆,也去伯公树下祷告一番。好些年头里,伯公庙冷冷清清的,偶尔,附近租户将一包垃圾随手往树下一丢,惹得行人掩鼻侧目。本地人只在特别的日子里光顾这里,外乡人事不关己,来去匆匆,那树自然地与人世毫无关联的样子,自顾自地开花结果,自顾自地高大森茂。
岭南不似江南的露寒霜侵,乌桕树要到立冬之后落叶,果壳绽裂也在深冬时候。一个客居多年的江南人,怀揣故乡地理残片上几帧发黄的记忆照片,在《诗经》以降的精神遐想中,以凡人的眼睛看大和村那株风华不减的乌桕树。春夏看它一树绿叶,绿叶之间,开出串串黄绿花穗,柔秀而清丽。十一月风凉下来,看它一树秋色,隽永而深沉。立冬后,当红叶落尽,万叶千声,果壳尽裂,雪白的乌桕籽袒露在空枝上,点与线条,充满刚劲之美,与雀影相得益彰而成画幅之美。钢蓝色天空是它的巨大背景,阳光倾覆下来,一株古老的乌桕是如此地完备,内敛又张扬,缄默中蕴含内在力量,一种内在的修为之力,一种以身垂范的风度,似一位人间的大德。我想象它童年的样子,青壮的样子,想象它所经历的一切,时间仿佛从来不是它的困境,而它的阅历,比如大和村四十年前的丘陵冈上,鸡声、牛哞甚至隔山吹拂的海风与拍岸的潮汐,比如树畔的青禾、溪流、蛙声,都曾与之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而最终消失。许多事物最终消失,许多人都走了,它“而今千尺苍苍”,依旧花开果熟,那份孤独却更深重了。如一场梦境之旅,也如一部春秋史册。站在乌桕树下,我常常生出错愕与惊叹之心。
乌桕树春夏开花,花后结果,秋天一到,树叶褪青,青中透黄,黄而转红,红到尽处,纷然凋落,留下嶙峋的枝杈,枝杈间缀结累累果实,扁球形的小蒴果,夏季青色,入秋后变黑,霜降后果壳绽裂,露出白蜡果实,像雪粒落满枝头,点点清白。我们叫做“桕籽”。鸟雀们像人间过大年一样,在树枝上跳跃飞扑,如南迁过冬的灰椋鸟,这时候集群在树上啄食,像一伙饕餮者。想象乌桕树的一生,如同缅怀一位人间故交。是细密的小雨,催动乌桕树的春天。枝头的嫩芽,以强劲之力冲破虚空,日渐蓬勃的绿叶是大地与树枝延伸的想象力。为它而设的轻烟、朝霞、岭上的鹧鸪声,带来神秘的玄想。串串花序悬垂,正是时间的假设和预言。当初夏来临,一二声蝉音的宣叙调,唤醒旋律起伏的生命乐章。盛夏的乌桕树是一年之中堪称风华卓绝的时代,风中舞动的群叶与日光里的丰茂树影,仿佛人世的大好青春,那么迷人,迷人而充满幻象。风吹着吹着,风声就仿佛远了,叶绿着绿着,颜色就开始深了,日光照着照着,暮色就好像下来了。暮色是它的中年镜像。暮色是它的秋天图腾。在中年的镜像与秋天的图腾里,玉白色籽粒成为挽辞,成为弘一法师摄人心魄的绝笔,是执着的信仰,是对大地、季节、时间的回报、呈现或答案。
在老家赣南丘陵地上,我见过最倾心的一幕:冬天的暮光里,乡村公路两排虬枝峥嵘的乌桕树静默地蹲守着,公路上的白沙、树干上整齐的涂白、雪白桕籽与暮色和光秃而黢黑的树枝形成一幅对比强烈的黑白画面,旷野寒风中,乌桕树像无言的苦行僧,沿着乡村公路列坐——一九八三年冬天,我周末从乡村中学徒步回家,走到村道与国道交汇地段时,一抬头,这个画面突如其来地映入眼帘,某种孤独与温暖的感觉,一瞬间流遍全身。那时候多么年轻,许多人事毫不经意地被丢弃在岁月的风中,却在记忆中独独收藏着这个画面。记忆,会在某个莫名时刻呈现。在梦境里,在潜意识的漫游里,翻阅着它们,那些陈年的图景,忽然就生动起来。
梦里的妇人四十出头,身材高大,胸前与臀部平塌塌的,蓄短发,宽脸,颧骨略高,鼻子挺拔,穿一件黑色斜襟外套,配蓝粗布裤子,裤腿挽到膝盖处,打着赤脚,嗓门高亢而尖细,看上去就像一个男人。她笑嘻嘻地站在收割后落满乌桕叶的稻田里,秋阳照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照在旁边高大的乌桕树上,满树桕籽像寒梅著花,映衬出女人的卑微和拙朴……梦境就在这时消散。梦中的妇人没有名字,醒来后想,她是谁呢?
小时候是见过这个妇人的。她家在小镇上一条盲肠般的小巷里,一栋两层天井式临街老屋,破败的瓦顶和漆黑的杉木板墙,像一九七零年代的写照。那妇人当得上一个壮劳力,插秧、收割、犁耙,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走路时风急火燎的。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在乡综合厂做泥水工,老二是女儿,很早就嫁了,老三刚入学,放学后天天和我们一起给生产队放牛割草,一副天真頑皮的样子,全然不似他的父亲。妇人的丈夫沉默寡言,人显得高大精瘦,给人风一吹就要跌倒的印象。每逢圩日,便见那丈夫在乡供销社前面空地上给人手工染布,白色自织土布大都染成青色、蓝色,极少红色,颜色单调,工艺简单。一只大而深的圆铁桶,架在一个简易的土灶上,土灶里烧着木柴,烈焰熊熊;铁桶内沸水翻滚。那男人先是往桶内撒染料,再用一根长长的茶木棍子使劲搅和,待染料均匀地稀释在沸水里,就往桶内放布料,再盖上盖子,蒸煮一会,看看时辰差不多,再揭开盖子,用茶木棍搅和一番后,捞出布料,浸入旁边一口蓄满清水的大缸里洗濯,如此反复几次,直到染好的布料不再褪色,就抛晾在竹竿上晒干。他买不起工业染料,白染青时,染料是乌桕籽、铁砂和明矾之类,染出来的土布深黑色。白染蓝,则从河边采来蓼草,先发酵,再和生石灰一起蒸煮,染出来的土布蓝青色。据说白染红也是用的野草野花。每个圩日,老远就见染布档烟气腾腾,那丈夫低头弯腰忙碌着,脸面和身体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偶尔累了,他就坐在一把断了扶手的竹椅上,抽几口旱烟,被烟气呛得剧烈咳嗽,腰身佝偻在椅子上,像一只风干的大虾;那被染料浸染过的泥地,像漂染过的日子,黯黑而污浊。那年月,所有农业户口的劳力都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允许自主经营种地以外的副业。因为羸弱多病,据说队里允许他染布为业,每年给队里上缴一点副业收入。这样一来,大部分日子,他都蜷缩在屋里,里里外外靠那妇人操持。妇人和男劳力们一起出工,收工后煮饭扫地洗衣,农闲去山上砍柴,甚至做染料用的蓼草、桕籽,也是妇人操心。
桕籽可以做肥皂、蜡烛,乡收购站统一收购。每年秋天,当生产队集中劳力把远远近近的桕籽采收完,我们这些孩子就会聚集在树下,去落叶和泥地间拾桕籽。这个时节,那妇人就会拿一个布袋子,腰里别一把镰刀,跑来捡桕籽。只要我们在的地方,她从不和我们争抢,而是像猴子一样迅捷地爬到树上,去摘遗漏在树梢的桕籽,有时候遭遇树上的土蜂,她被土蜂蛰得脸面像馒头一样红肿,然而她似乎很快乐,像压根不明白日子的愁苦滋味。妇人站在秋天的乌桕树下,一头乱蓬蓬的短发,笑嘻嘻地仰头望着满树桕籽,卑微而充满生命野性,那是某种足以抵御贫寒岁月的生命韧性。
妇人的丈夫去世后,老大分家另过,留下妇人和老三度日。老三成婚不久,遭车祸意外去世。晚年的妇人孤零零地卧病在床,每天被浑身的痛楚折磨。来自骨头深处源源不断的疼痛,让妇人惨叫不止,直到最后一刻,那扇老木门里还传出压抑不住的嘶喊,令人心惊。那是一生积淀在身体内部全部苦痛的最终反抗。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