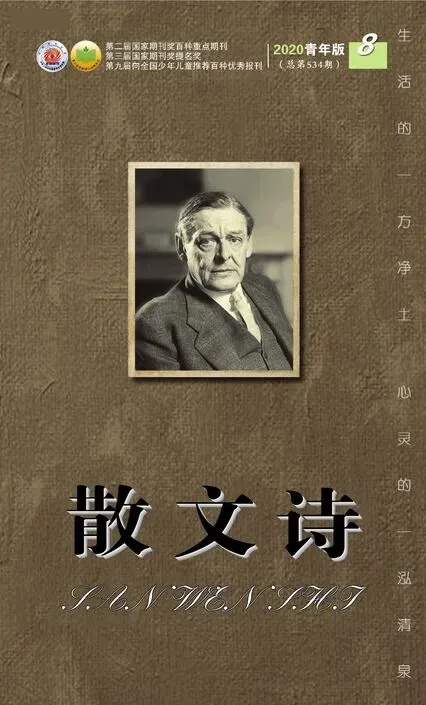草地上
花 盛[藏族]
草地上
草地高处,风独自奔跑。凋谢的花瓣,像失去母亲的孩子,带着泪珠在身后追逐,直到风翻过远处的那座山。
我途经之时,暮色将近。
在此之前,低垂的云朵蕴含着细碎的雪粒,一遍遍填充着生活的盲区。
那些柔软的花瓣拽着草叶唯一的血脉,依依不舍,但我们都经历了选择与别离。
羊群漫过,像我们一样,只顾利益的诱惑,对融化在血脉里的生命和爱视而不见。
深秋将至,我们又一次翻出记忆和烈酒。在这片草地上,这是我必经的事情——以此温暖心中或枯黄、或残缺、或冰凉的花瓣,以此宽慰亲人的离世和空空的家园,以此给自己重新画出心中斑驳的远方……
夜色已深,草地上零星的灯光像暗藏于心的秘密,肆意放大存在的意义。但除了天空辽远,剩下的便是无际的寂静。
在草地上生活久了,沉睡与苏醒只是一种表象,孤独与空旷只是自己给心灵划定的空间。
也许,当我们以草叶的方式重新活过,高原的风将是我们一同抵达远方最亲的人,它替你我铺开了生活的路,也替你我传唱着源自信念的力量。
幸福的草
一群羊,从草原带回湿润的空气。
面对主人的无视,它们咩咩地叫着,抖落满身青草气息,径自归圈。
一堆燃烧的牛粪饼,将世界一分为二:冷和暖。
冷是暖的手背,暖是冷的手心。
伸开是昨夜缝补的帐篷,线痕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蜷缩是落日掉进垭口时的背影,孤绝而茫然。
在一个人的生活里,一顶帐篷就是一座故乡的村庄,适合杂草丛生,也适合井井有条;适合肆意地活着,也适合禁锢所有的欲望。
我们把自己活成一棵草,在草丛里拼命挣扎,努力活成不一样的草。但草,终究是草,它的伟大和平凡,源自寂然的一生。
但我相信,被羊啃食的草是幸福的,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宿命,也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遇见与存活。
老 屋
老屋坍塌的地方已草色青青,它掩盖了漆黑的椽子,也隐藏了我们内心的愧疚。
父亲说,老屋和人一样,老了,身子骨到处都疼。
如果不是父亲的提醒,我们很难发现老屋的病痛。老屋像一个词语,单薄而深厚。
黛色的瓦,在时光里经历着春夏秋冬,似乎不曾褪色,不曾老去。像父亲的爱,沉默着,但却细致入微。
我沉迷于老屋的温暖,又羞于面对老屋的破损。
哗哗的水流声透过草丛,带着光亮挤进来,席地而坐。
或许,老屋终将是我们的归宿。缝隙间丛生的杂草,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一缕炊烟里牵出的火苗,像心中的灯盏,照见我们的归途和越来越少的时光。
苏鲁花
苏鲁花又一次迎来了夏日高原的暖风,阳光般热烈。
耀眼的金色在经历漫长的寒冷和风雪后,绽放生命本真的光芒。
一朵花,需要持久的等待和孕育,才能完成一场约定。
成片的云朵,羊群般擦肩而过。
一只疲惫的蜜蜂,停留枝头,捧出甜蜜的代名词。
柔软的馨香,让高原的冷峻瞬间多了一份温情和暖流。
在高原,我习惯于坚守,等待闪电划过苍穹,唤醒梦中的苏鲁花。
在风中,我习惯于打开自己——
让风穿越心灵,绘出生活的底色。
高原雪
用雪铸魂,碎小的雪花也能劈开生活的坚硬。
纵使经受断裂和破碎的疼痛,纵使难以逃避消亡的命运。
我们抛开侵肌的风,播下青稞和格桑花,它们长成生活的两个面——
一个是坚硬的骨骼,锋芒毕露;
一个是斑斓的日子,悠柔如溪。
一株青稞,在甘南漫长的冬日,储备梦想和力量。
一束格桑花,在草原宽厚的胸襟,根植幸福和传说。
在高原,我们接住了洁净的冷,也接住了凛冽的寒。
我们把日子分为白昼和黑夜,以此换取明亮的思绪。
高原的雪,虔诚的雪,信仰的雪——
我们是永生的雪。
宽 恕
近处的蚁群,远处的辽阔,构成高原的一个隐喻。
我们是隐喻的一部分,在低处以自己的方式打开现实的故乡与心灵的远方。
母亲说,故乡的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但却夭折于一场大雪。
雪消融后的土地上,厚厚的花瓣,像粉碎了的梦。
冰凉的夜晚,风孤独地吹,一日千里,也难以抵达故乡深处。
窗外的迎春花,被霓虹灯照亮,静默如雪。
在此之外,夜色漆黑而沉默,如一条河流,在时光里逆行。
我们的脚印,深浅不一,像故乡的一声声叹息,淹没遍地的创伤。
当黎明抵达后,我们一遍遍擦拭错乱的日子,归位秩序。
当破土而出的青稞覆盖荒芜的土地,我们又一次窥见轻浮的云层,缓慢越过。
那一刻,我宽恕了自己,也宽恕了蚁群般紊乱的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