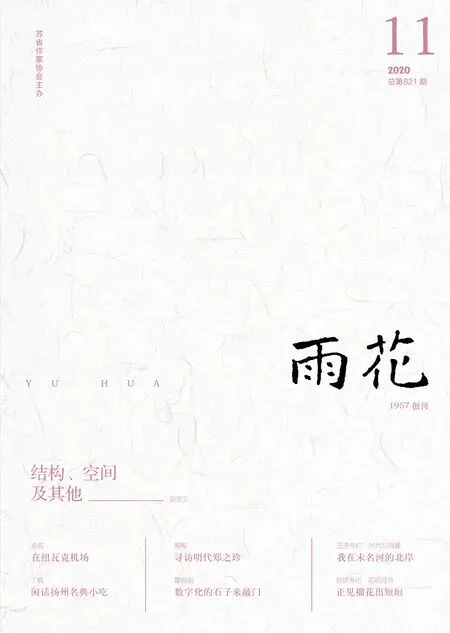灵魂与肖像
1.时代感
不能让每一部具体的作品都陷于时代之中。时代自身未必可以验证和完整地领略悬于时代上方的浩大时空。每一种具体的流淌都是潺湲或匆迫的,但每一种具体的流淌中都匿藏了完全意义上的死亡。注视时代时,我经常产生深远的惆怅之感,但是忘却它却可以使我心安。我不愿意让我的注视与水流的速度完全重合,我只愿意适时地关闭我的心襟。这样一来,时代之流才可以完全地覆盖我,我才可以完全地覆盖我。我未必愿意使全部的我裸露在外。所以,我有时会忽略时光的滴水。这使童年的我看起来未必幼小,这使老年的我看起来未必垂迈。我只想使我生活的意义变为烛火——这么说吧,我曾经拥有的命运未必记得我,我曾经丢弃的土地未必失去我。在水流的背后,一定有隐约的爱的遮光。
2.冲动之未完
我想写一个冲动的故事并以此感受时间之进退。但此刻时间不在那里。应该返回的人群都在旅途中停顿下来。太多的沙尘袭击你的头颅。你以寂静的草叶果腹。
3.荒旷人物外形
单调的写作和生活带给我们邂逅万物的错觉,因为万物并不充实,空虚和浮云游子意就是它的实质。我一生都在复述一些句子,但从始至终都不是在加强它。我找了多重角度只是剔除了它的尖角,但它仍未露出表面的形体和雕塑般的骨骼。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工作就是完全无用的——在外面我视之为矿井和木石的部分,都是那些役使天地的虫蚁在凝结和挪动它们。我们蜗居于一局部,如以空空寰宇之大蜗居于虫蚁之穴的一隅。那些时间的涨溢加速了物体的更新,但它们所覆盖的也只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一局部。较之我们肉眼所见,更应为我们悲惜的,当属那无数不见于珍藏的荒旷人物的外形。
4.昌耀(一)
读昌耀的诗,会觉得时间是通透的。旷古的草叶涌来,大地上慢慢地弥散出烟尘之气。
昌耀使用浑朴、原始的语言,或许正是因为他使用了这样原始、浑朴的语言,才使他的笔墨浓厚,有了山岳的青黛之色,有了沙漠的浊黄之色,有了使人一览之下再也无法忘却的泥土的颜色、沧浪之水的颜色。
最初蕴含在昌耀诗中的命运之感,不是平淡的逝水流年般的命运之感,不是蝇营狗苟的日常化的命运之感,不是我们现在才体悟到的纠结和不安,而是逼向云雾苍苍,植物婆娑,山峦层叠的天地之慨,而是诗人头顶穹宇、扶栏远眺时的命运之感。
天地的栏杆是腐朽的,粗粝的,因此从昌耀诗中可见之扶栏者的双手也是不羁的,粗粝的,未知命运之所往的。
昌耀的诗歌不是精细的,但却蛮荒,有力,如入浩瀚之地,苦思沉闷时的必然用语。他的行文天然地对应了西部的山川地理。因此,他是经受了山川风雨的锤炼而写诗的。
他写下的是命运的和歌?
昌耀诗中气韵最足,用语悠怅,但技艺的成分不浓。因此,他的诗不是平常的“写下”,而更近于午夜梦萦时内心撕裂的苦吼。
因此,他不低吟浅唱。他不是足够的文艺,也没有试图建立诗歌学说。但他的诗歌是无可置疑的经典。我觉得昌耀诗歌的锤炼之功与他对命运或命运对他的锤炼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他是缄默的,隐忍的,“天地之悠悠”的诗歌最难复制。几不可学。
昌耀诗不可学。昌耀不可学。
因此,我们只能以阅读他的方式临近他,但不能完全地“理解”他。我们无法看到诗歌的枝叶是如何在他这里萌芽、生长的。
因此,我们最该体验的,不只是他的诗,不只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命运与爱!
因此,二十年来,我每一次阅读昌耀,都带着苦闷和惊叹。二十年来,我每一次阅读昌耀,都带着命运之感:我们的爱,命运,生活!
每次读,昌耀总是生生不息。
每次读,昌耀都重新活一次。
因此,昌耀是以他同步于命运的手,写下了同步于时光的诗篇。昌耀诗的有效,正在于他的诗中生长着一条古老的天之际涯的河。
因此,昌耀命运的粗粝之感,正与残缺天地同契同喻。
5.昌耀(二)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首诗:缓慢而沉着的甬道。你激情的步履迅速在月牙的照射中苍老。你几乎从未圆满。或许,你天然有残缺记忆,如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所经历的?
你拒绝幸福?以全身心的力追求进而抛弃那圆满而使人幸福的?
然而那只是幸福的片面。生命无法自铸伟辞。只有离别和惨痛的苦难可以助力。你成为自己的精神而径自发生时,树叶枯黄已入秋冬。你看到它们的飘落了吗?纤尘负重于落叶之身,大地承纳你所有的压力和病痛。你看到它们返春时岁月的踊跃了吗?
你看到海洋的潮汐如母性的经血涌动,也是绿叶在吸收天地精气后所看到的。
它们浓郁如雾,又须臾凋零。它们都是自然的实体。但人类的精神有时空虚,你写下它空虚的实体。
有一年新岁乍见,你写下它新颖而将消逝的实体。
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诗:它的每一个四季都日达千钧。你如负轭的耕牛。
而西部的山峦也在年年筹集善款。
森林之目光修葺了神的栖所。人之站立和攀登的峰巅孕育了神的脊骨。它们以高海拔将人类文明的种子藏之名山。你西行到了自我心灵和身体的极地。在那里,你要以高昂的呼吸证明你的健康。
时间是狰狞的,如独虎拐过亭午。
你要以高海拔调试你心率的进退。而后,你以断绝归路的心年年扎营在故土之外的边关。那里苍山依旧,溪涧的深水喷涌灌溉田畴。
我站在西宁的街头感受那些深水的灌溉。
在夏日的黄昏,我徘徊在你曾经的居所一带。
是的,生活毕竟是这样的诗:它的铭刻以二十年为单位。我目睹那些劳役的句子长叶,长枝。二十年中你无法尽度世事沧桑变化,但你的诗句如养分充足的植木般长得很好。
那长天碧空上的鹰已经飞得很高。你看到它们落入飞翔尽头的样子了吗?在书写和耕犁的指向中你看到未来的样子了吗?
我阅读你的叹息。如今世间寥寥数人阅读你的叹息。当吟咏之力聚集时,我所阅读的就是你一世的叹息。
6.昌耀(三)
后来我终于明白,昌耀并不仅仅依靠倏忽而来的灵感写诗,而是追求灵感的合成。他将灵感变成压榨和淬炼过的铁石。
我终于明白,他那些句子的古老和传统之处恰恰与其时流行的前现代、后现代大不相同。他是能够依靠天地万物的本来面貌而取得能量平衡的人。
他使用复杂而古奥的语言恰恰因为他是朴素的。他总在思考人生本来的问题,如人在时间中的隐秘,命运与生死。
昌耀的抒情诗是瞬间雨水和孤愤中的夜色合作的抒情诗,其中有汁液淋漓的旧日和心海枯竭的今夕。
他为什么需要写诗?不,他并不比我们更为需要。昌耀写诗只是在对生活施加压力,压力促使他选择新的挖掘生命的方式。压力促使他选择新的释放生命的方式。爱与痛悔的责任与青海的夜色交织?只有写诗的责任可以扩展他的幻觉和冲动。
因此,他是诗人,凸出于荒旷世界的诗人,凸出于礼貌的、混乱的俗世的诗人,凸出于苦难和精神灵魂的诗人。
他比我们很多人走得都远。也比我们很多人走得都近。他就守卫在家门口方圆十里之处。却能看到、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风雨?
他能风雨无阻地生活下去。爱下去。死下去。他也能风雨无阻地做凸出于众亲友儿女的梦。他是孤单的。无人同他守岁的孤单。
他总是孤单的。无人识别他的孤单。无人拥抱他的孤单。寒夜独垂泪的孤单。午夜或白昼深睡却未知睡时时辰几何的孤单。
后来我终于明白昌耀诗歌的砝码了。他将自己全身瘦骨嶙峋的重量压在诗歌天平的这头,将汉语句型之力和美压在诗歌天平的另一头。
因此,他精细地酝酿着称量诗歌时自我感觉的平衡。他的生活化的精细也是他的诗歌写作的精细。他有效地把握着它们彼此间的平衡。
因此,昌耀只是一个隐蔽的、潜在的诗人。我们没有认出他来,就像没有认出日光下的新事,就像没有认出我们的祖父、邻居那么简单。
因此,他只能默默地选择“用语言支持自己”。用过时的恐惧填补岁月的空虚。那些瑞雪丰年的日子,是他默默用双手写下的。
两鬓苍苍十指黑的昌耀?天真得像个孩童的昌耀?暴虐的父亲:昌耀?单恋的情人:昌耀?因此我终于记得并且能铭刻他的诗了。
我终于可以忘掉并保持自己每如新读的惊奇。我终于可以既有深睡的休憩又有爱的休憩。我终于可以再次写关于他的诗了。
他是人间事物涌现。他是时间烟火涌现。他有写诗的大力但没有扛起生活的大力。岁月蹉跎,他终于变成了铁石之重在人间的存在和消散。
7.昌耀(四)
烟云四散。整个宇宙澄澈如蓝。
读昌耀,其实不仅仅是读昌耀,其实是在读“我们命运的层次”。随意翻卷的册页,犹如固定下来的青山,我们抬头俯首,皆遮不断的青山。
随意的翻卷……但逝水汤汤,但青光明媚……空阔和一望如碧的青山,高高大大的青山,诗人、牧人、过客匆匆,但又沉寂万年的青山。
千万种凝视,但已大体如是;笼罩在万众瞩目之下的青山。诗人皆已作古的青山。青山埋没了诗人之魂,但还是让春季的绿色“轻轻地划过去了”。
烟云四散。时代的旷古之意……
需要以一种特别的力写出“时代的旷古之意”?不,那青色的墙壁也从未描画。那天穹的“颜色的名字”从未描画。时代感只是一轮“儿时之月”。
轻轻地划过去了,春天的葱茏的颜色。
轻轻地划过去了,“时代的旷古之意”。在那些古镇的街头,流水的波纹也从未固定地形成。山峦的颜色澄碧……
轻轻地划过去了,我一眼望去扬尘如雾的青山。我一眼望去扬尘如雾的此刻青山!
8.昌耀(五)
无怪乎我会喜欢他的诗作,实在是于此大有心会。我不喜“诗之薄技”,但时时令我得启示的是——我从来都极珍视诗的“发掘”和“气息涌流”。
如果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世俗的方向,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会痛悔自己的无知,反而会热衷于嘲笑那些借故走开的人。田亩的阔达、鹰隼的飞翔,早已激不起我们的兴趣了,唯一使我们感到有意义的就是受百毒之侵的“人间”。
大诗人是一个自我的“整体”,切不可“寻章摘句”地看待他。
事实上,我如果能够不展开想象力,我就成功了。阳光的逼视如仪,正是如此从容地证明了这一点。
优秀的诗歌总会穿越时间的阻隔,就像专为无数的后来,无数的今天写下的。
9.昌耀(六)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局限性昭然在目。我们需要以突破自我的方式来突破它的防堤,需要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文学的)来突破生死之间的逼仄。或者可以说,使我们的足迹变得阔大的一个根由便是我们诞生和存在的渺小。我们不会满足于自我的本位而不思奔走,无论是地理时空上的挪移还是心灵内在的狼奔豕突——这种带有时间性的变迁填补着我们生命中不足语人的精神空缺。书写,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使我们的力量(须臾和虚无)得以呈现。很多年来,我都将西部诗人昌耀视为我精神旅途上的一个“僧人”,面对他的书写进行念诵,成为我寂寂长日中可以久久思之和憧憬的一类功课。但是,日常生活的纷繁忙碌,使我对他的阅读少之又少;即便如此,我也还是通读了他的全部诗卷,通读了关于他的传记。他的一切精神的昂扬和蛰伏都使我服气。(“我从文学的角度来读他。”)在这片土地上,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离我如此之近。昌耀诗歌对于命运的吁求与一切杰出的艺术家心灵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一再地向着自我灵魂的边境进行冲击,他用尽了他有限的呼吸和力。由他所书写的这片隆起的西部高原是超越时空的;他的不朽正由此而奠定。(我读昌耀如此,读卡夫卡如此,读佩索阿和策兰都是如此。在他们对于自我的深究和无以遣怀的“爱的狂热”中,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却更为张大的“时空”正是以另外的方式存在和建立起来的。)昌耀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高峰。他冲破了板结的地块,深挖出历史和时代裂隙中“诗”的涌流。
10.珍奇的诗也都有光芒的棱角
好诗是蕴意无穷的。你不能只从一个单一的角度读它。那样,就把它读死了。须知,它有无穷的活。
珍奇的诗也都有光芒的棱角。你每次读,都可以抓住一点,当完整的阅读完成,光芒就会汇集起来,如长虹贯日,真是罕有其匹。
珍奇的诗的丰富性,又是精简到极限的。它光芒的棱角所在便是他珍奇的极限(因此有迹可寻)。但是,陌生的初读仍是最佳和至高的阅读。(因为,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所以,初读好书尤其需要屏息凝神,最好在黎明初起时。好书的丰富,当与日出时洁净的光芒和晨露凝霜同质。
写诗亦如是。思维如电,它不会去去复来。形影难觅,因此你要力争保持自我清明的视觉。
11.绽开
光芒不会太多,它总有尽时。那全范围的覆盖是假的,你不要信它。我有时走到过路人待的那个路口,看到斜阳荒草,就像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不知道我的爱与生命有多长,但时间精确的点距却一天比一天固定下来。衰老和疲惫袭扰我的心。我只能告诉你,光芒是四角的怪兽。它到处都有,向四面八方,绽放涌动的花环。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那渐渐泯灭的光,就一定不会悲伤。你在生命河流中的水量尚且充沛,那需要重新划分的句子还没有爬上你的额头。但你也得明白,戏的后半场已经开始了。你早年射出的光线总得收回。你需要绘制你的现在。在大半寂静、只有极少喧嚣的角落里,你需要绘制你的语言和色彩。你需要为你的羽毛装一只疾动的盘子。时间向天际运行但你从不自知。那稠密的人丛中只有你还耽于光芒弥天的审美。你事实上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但你从不自知。匆促而空荡的夜色中带有时间渐变的征候,水瘦山长,你提灯行路而孤身四望。那场面上的星辰大海都有一个曲线书写的未来,你应该将你的徘徊铭刻陇上……那里春花静悄悄地绽开,你头顶的月色和白茫茫的雪,都在静悄悄地绽开。
12.聚集
那是卧牛的场地。那是风雨剥蚀的天空。那是披头士的舞。那是一枚韧性而弯曲的钱币。那是黑土包。几个孩子走过它的脚下。谁还认得它呢?
弯枝条低月亮都在聚集。那最美的孩童扯起黑土包。山峰和美都在聚集。低吟的苦诗和荆棘的引路都在聚集。
13.那些虚幻的碎影子并不坚实
那些虚幻的碎影子并不坚实。那些石头都是怪物转化。他们出落在这里的大地间,融入凡尘的落花。他们慌乱的脚步将早晨的风也踏乱了,等不来那些触目惊心的友人,也等不来失魂落魄的炽热之光。他们抓捕着什么,却空无一物。在整个世间,遍布了那种灰色蔓延的小路,尘烟滚滚,他们的睡眠和走动都修饰着战争(日复一日的尘烟滚滚)。我跟你讲,不识者都很荣耀,是很好的人。那些花丛中种植和埋葬的蚯蚓也很荣耀,它们经过的大地在被开垦过后再度恢复平静。沉浮无极的只是那些虚幻的碎影子。仅仅时隔百年又有什么要紧?当紫色的鹦鹉回头,他们跳跃着钻到三个大人的背面。一切都如同昨天。当跳跃的鹦鹉回头,他们跳跃着进入胡同狭窄而深广的日常里去了。我曾经目睹他们的生死,能想象到他们在眠床上酣睡的样子。那是在爷爷安详离世那年,春水泛滥,柳叶娇媚,行者并无疆界。当然,时间被限定在那种清奇生死里并不回头。你垂目四顾,时间多么宁静而小啊,它照射着但并不回应。隔过山去,又是一番人流涌动的街景。黄昏时分,那带头入夜的人也翻越峰峦去了。
14.苍老如古
不要担心有蚊虫吸你的血,不要担心天气阴晴不定。你无须知道:只要驻扎营地,你的心就会随日出日落一次次翻新。你无悔改的惆怅春天记得你,你瀑布前的裸体记得你。山中遨游的时间只是一棵棵葱茏青草。它们落在灰上?你无须知道:大夫们住的树梢就长在尖山顶。迎客松的树皮被刮削尽了,你浸湿自我的血落在元月。你医治百病的圣手如今已苍老如古。你优游如岁月,山中有大夫。那些事沉积在无人放牧的黄昏。大热量的厨房流出浓油。你看啊看啊,就是这些日子。黄蜂盛满灯油谢谢你。密雨、迷雾、泥污中的森林:一排雨后新笋谢谢你。
15.记忆收缩的枯井
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已经醒来。这段时间习惯了早醒。无论夜里多么晚睡,早晨一旦苏醒便睡意全无。我在书房里,黑暗敞开后的黎明看起来多么浩瀚啊。我知道曙光在前,但我只是身处日光升腾前的书房,它自身并不生产日光。时间之核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播报。仿佛,“记忆收缩的枯井,早已装不下一滴泪水”,而“人心纷纷如牢狱”,而书房的阳台永远朝向“时间的外面”。书房面对大千世界,书房面对如云的广漠。我从一数到十,再数到百。我并不喜欢这虚伪的、宁静的罗列。黑暗中透着人造的亮光。机械;绵延;持久。它们能把你惊动,从梦境里将你拽出。它们还只是守候在此刻的亮光。不保证时序在五百万年后仍如此守恒。你想象的万物是静悄悄地发生的,肉眼看不见的。你所注视的点滴,也并不是拥被围炉的昭示。我承袭先人既死的意志,并无守候之心地自处。它们,那些纹丝不动的黑暗,在五百万年前就是这样了。但是书房的建立、破败和流散却等不到五百万年的风云。云层深厚,它们只是一些微小的粒子。它们无法自我保持持久的动力和此刻的恒定共在……我突见晨曦渗透在黑暗中的灰蒙蒙的光在涌动。此刻,晨曦带走的露水和苦涩正一点一滴地找回来。你大可不必迷恋那些在晨光中叫嚣的人……
16.钟声
每一刻的钟声都不同。每一刻都有新旋律,寄居于它唯新的,不设限的未来。世界之大,但每一刻的钟声都不值得倾听,它的流逝——只是为了占有虚空。但你会有更多的,更多的钟声?
17.指路之人
我仍留恋风,瞬息而过的云层和短暂的剑刃。我经常会想起诗人雷预谟的荒唐一生。剪刀,锋刃,前往阿尔卑斯山脉路上的雷鸣电闪。时间是一柄尺子,令你蹲下,测出你弯腰时的灵魂之深。雷预谟是上古时间中最荒唐的诗人,他从不曾写出半个句子,但他的嗓音神鬼莫测。“要写,要写出那种句子。”我仍留恋,觉得自己疯狂的心才是对的。想起你时已是夜深。我紧紧衣领渡过河去——“要写,要写出神鬼莫测的句子。”我问过他此行向西多远,你忘记了吧?在葬礼的高处,有一个空心雷预谟在独舞指路!
18.沉默的疤
黎明的苏醒像一个正直的匪徒所为——就这样,我陪伴他终生,直到他溘然逝去。
秘密的水携带着秘密的红花、记忆的种子般的清芬、山岗上层峦叠嶂的事物——直到一切涌现的力冲决果蔬的防堤,直到一切爆破的力使夜晚的三原色冷凝下来。秘密的水携带着秘密的红花……
我多么爱这人间啊,无比精粹和杰出的爱,可以不罗列而达繁富与浓烈的爱!
独坐于黑暗中的未必是孤魂。孤魂是不朽的,但黑暗里的独坐却是浮云般的浊物。没有清风送别,只有黑暗里的、静止的、过于频繁的独坐。
生命只是梦想一刻的误食。生命只是一枝火焰的秀丽纹章。生命只是穷尽上帝之思的屋宇。
我与你相别,已然尽年尽月。我没有沉默,但却一直无言。我将自己沉默的疤融汇在了我的无言里面。
19.谈论思想的人
谈论思想的人心头总会奔腾着“思想的骏马”,但旷野无尽——谈论思想的人,将最大可能地与枯竭和单调为伍。骏马的奔腾没有止歇,但枯萎的河面却长存世间。嘉禾的生灭和离别长存世间。
20.旅行
如果时间夸大其词,我们也能沉浸其中。你理解错了“草木凋零”,但燥热的水分子在发出声音。你秘密的旅行建立,但空虚的时间在发出声音。
从那条通往旧日山顶的小径迈过积雪上山,你看那些骸骨因为饥饿而变得消瘦,他们存在于旧日秩序的内部而慢慢变得消瘦。
你此行的目的地未必同于万物。为此你惊呼时间的旅行,反复经历那些花儿的绽放。去年今日的晨光奔腾,它将那些余晖作为利息向你偿付。你懵懂而热烈地面向它……
你懵懂而热烈地,完全没有头绪地向前走去。
读它们遗留在风雨中的经卷吧。他们劲健的骸骨守护他们的经卷。在高山烈日下……
一些集体性的思绪在运行。旅途中同步赶工的建筑之声嘤嘤嗡嗡地响着。你热烈着,懵懂着。
祈祷之声也变得空旷。
那些用意志力筑成的划痕也变得空旷。
你瞧瞧那些帝王。他们拖带辎重的旅行。你瞧瞧诗人们含辛茹苦的旅行,哲学家孜孜以求的旅行。
没有终结之地和出发感觉的旅行。随处扬鞭奋蹄的旅行。这是一种特殊的旨意:便以此旅行来成就吧,在你发出呼救之声的下午,你听闻雷雨疾呼痛断肠,而天涯故土同在。
那些斜倚土墙、攀上屋梁的草木目睹你的旅行,它们沿着万物固有的轨迹复苏,年年缭绕盘旋,生之旅行的光潜隐在那里。如一阵阵风声葱茏,真实,写下万物本有的句子。
这些年你奔走于外,任田园荒芜。式微,式微,胡不归?那些屋脊上的草木负重沉浮,露于青天一线。
这些年你奔走于外,你看到那些时或阴晴不辨的青天了吗?
当你逗留于外,而故土草木横长,你看到那草木之畔、寓人灵慧的青天了吗?
21.乡愁之涌动
写作者在观察生活,但这仅仅是表象。在语词所能够做到的最深的承载中,写作者不仅能够看到被写者在击鼓,而且能够对它发出的压迫心脏的力度感同身受。也可以这样说,写作者只有拥有了被写者作用于写作一事上的明晰的鼓舞,写作的意义才能得以彰显。但是,山水之绘,上帝的创世都难以仅仅通过写作的时刻加以描摹。它们所拥有的最奇幻的高潮部分一定还有他物介入。
将写作的令人迷恋的部分集锦为云蒸霞蔚的创世纪应该是诗人中的诗人的事。他们在广漠上筑屋,并随着流沙消逝,随着广漠浮于原野。坚定的根被埋藏在数丈深的沙尘的底部。那一点一点的时间细纹就是诗人的头颅。它精巧地装饰着灌木和青草。
他物也是杂质,是测绘师心中突兀涌动的风云,是上帝的手足,是那些脸朝天空的人仰颈所感受到的天晕地眩感。他物是梦境里的赤松子。
时间,在诗歌中最为坚实而不容破碎。那司法神面对时间发明者的肆意渡河也会发怵。司法神难以明白时间运行的诀窍,他只是经常面对一些真实的故事而心有戚戚也。
众人奋力写出的丹青诗往往住在广漠和天穹的句子里。但风云激荡,它们年复一年地被冲刷。众人心头环绕的星球转动之声介于瞬息和瞬息之间,那些写作者,他们哽咽着失去重力,那种空虚感,是他们始终不泯的乡愁。
22.院落
他砌了最后几块砖,使他的院落最后成型。在此之前,一切都乱得不成样子。院子多小啊,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相信院子还会继续小下去,直至小到无形。他没有等来援军,也看不到日光起落时的金黄色。他相信就是为了达成这样无视日光升落的目标,他才搭建了这所院子。在村庄的外围,他是孤零零的建筑师。他的院子左侧便是悬崖,那里鸡鸣狗盗共度时日。院子外面也有孤零零的荒草,如果他夜游出门,也有一番好走。他有时会看到旅人夜渡,从悬崖的底部上升,变成荒草孤坟中的一颗星辰。灰突突的夜色中,有时也会看到他夜渡离梦,从院子的上空降落,变成一个羁旅于故土的游子。荒草识别旧物,流寓边关,潺湲如一场徐迂大戏。何处?何物?他砌筑院落的样子和鸟儿筑巢相似,他们都没有株瓣的辉煌,但同有一日两瞩目的感光。
23.吸引
我必须抛开你,让世界保持惊异。我流河里的血,隔断同你的联系。我们向来不相见,但我阅读你,用眼镜吸收。除去上坡的短路,我们只剩下一苇芦草,一座花蕾之距。那里密密麻麻地安排了查询的人群。你落座吧,一旦落座你便是我们的了。现在就是这样,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回到斜阳那里。看着你开开心心,这是对的。蛮牛也会首肯我们的做法。那山上的云雾也还记得我们,它们首肯的白色就是时间的正宗。那里自我们下楼后落雨。白色的夜晚,雨水打到了窗玻璃上。我们聆听窗外,红花绿叶之后,窗外一片洁白。
24.远天的轮廓线
要相信万物心灵自持的智慧和感觉的敏锐。不一定要,甚至千万不要追求完整和圆融——在那远天的轮廓线上,充满了峭岩和龋齿,它们没有来自造物之功,它们只是自身的生成和抵达。在那远天的轮廓线上,重装的黎明光芒万丈。它们有一种准确的黎明特性:荷负大地之重而有远天的光辉。但它们都不兼备黎明之明暗次第的完整,它们只是黎明灿烂之极的片面。
在远天的轮廓线上,唯时间是空荡荡的寰宇的巨子。但有时我们赋予时间某种具体的形态。它们是峭岩和龋齿的闪耀?是割裂和衔接了你我的万物声调。上帝虽然混融其中,但他以自我的容颜凸显了某种存在的局限。所以,上帝应该是无传记的人,但是,上帝有时又播下了某种文明的种子。
上帝的视角其实只是某种文明之神性的视角。上帝的视角中带有某种特殊的强调。上帝甚至对蛮荒之世心存怨恨,因此他才造出了人世的沧桑流变这一无限小的黎明。
唯造物是神之秘密命运的凹凸。但是人世的黎明无限小,人世的泥泞过于短暂,它没有生成铁锈的磅礴而肆意的闪光。
但是远天的轮廓线可在远眺中存在。它有独立的山峰、龋齿和峭岩般的美。它有雪霁后无可辩驳的白色形容。它有完全无悲喜和记忆的时间寥廓。它的时间寥廓才是自然天成。它没有落下任何人世的泥土的种子。在人世的山峰中观察远天的轮廓线,“吾自按捺不动”,才是最独立无羁的天地旷远和时间寥廓……
织造物丛生,在五月的迷雾中……
25.夜色撩人中浓密的雾
一开始,“神看着这存在”,后来才有人出面,将其放归人间。谢谢这些顾客,他们都心怀理想,唯有我,离开了最初的意志力,变得浑浑噩噩,“只知道一天中最早的晨曦的到来”。幸好有神的惠顾,他完整地沿袭、承纳了我的梦境。这是我最初的领地,夜色撩人中浓密的雾是我的梦境。那些人物都来自神的授意,他们盘踞了七个小时,为我的万古长夜涂抹沉重颜色。幸好有神的到来——今古转圜,他们制造了天地之间空茫茫的杯盘。
26.致意这些伟大的灵魂
致意这些伟大的灵魂可以让我深察世事如云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如今的生活即是他们曾经的灵魂图腾在此世和未来的延续。造物任凭语言和文字积存,因此造物是公正的。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的喘息的韵律离他们如此之近。这也是造物的公正所赐予我的某种神秘的征兆。我深信自己的思考中有虔诚的信服之念,因此我深信诗会去除和收纳一切。诗具备造物中以万物为刍狗的恒定表情,因此诗是人之信和天地间的公正。诗完成了我们所有不可能的情感,因此致意这些曾经以灵魂铸造诗篇的人也是致意浮云,也是向夜色致意,也是致意酷寒中的烈日在天。苍穹遥望,与我们晨曦中渐次抬升的目光互为造物的两端。
27.洗涤
天空晴朗,我用泉水洗涤。那众山聚集的穹星,像一颗颗珍珠被洗涤。我付出我爱惜的头颅和血液,用我的付出去洗涤。你当明白物体的指归即刻出发,来到当年那些群蚁的守卫之地,那地上的青草被洗涤。语言织造的绸布蒙上有灵的神圣,那是他们羞涩的眼神需要被洗涤。除去阻挡视线的灰尘,才是人间烟火里的城楼,那最高的十字语言被洗涤。除去众生有爱的悲伤,你食不果腹的梦寐语言被洗涤。2020年,你攀山越岭来到了这个世界,你的前躬的身躯是恐龙时代落下的灰烬之羽,你的恐龙时代广场需要被洗涤。众山抽搐无尽,静如磐石,滋润和托举众山的星球需要被洗涤。任凭星际运行于轨道,赋予它们秩序的宇宙被洗涤。上帝有时会发出瓢泼的语言,上帝张开的双唇需要被青草和花卉洗涤。那藤蔓攀援的柱子,需要被建设者须发张大的神情洗涤。此地人稠如海,从天空飘来,那惆怅而死亡的世纪之血需要被供奉和洗涤。
28.深厚不污的积雪
我有时会感激我狰狞而无畏的内心。我有时会感激我畏怯如鼠的内心。我有时会感激我高高大大的内心。我有时会感激我浩瀚如日月的内心。我有时会恐慌于我内心的落寞和静止。我有时会聆听并劝说我的内心。我有时会忘却,但更致力于平抑我的内心。我或许并无一颗彻彻底底的内心,我提出的所有内心中存在的愿望都是错的。我事实上只有一个澄澈的脏污之念。我内心的许多梦寐和愚钝都凸显了它在本质上的虚无不存。
29.某日,大河泛为金色
某日,大河泛为金色。而蔷薇花园的折光都集中在东墙角那里。如此明亮!我走过它外面的街区,仍能感到玄幻而明亮的折光。强大的种子被他们运载到地里,东墙角挖不倒它们,也无法埋葬它们。但是因为折光的存在,河流如同一口古钟,它沉闷而悠扬。我们走过街区的外面,广场上人声鼎沸。是谁在那里玩闹?那发声的大人也有他虚无的苦楚。在须臾之中露出胯骨的胖子,是他们的领袖?他一个人走来走去。时间的力量他已经忘记了。东墙角的光现在集中到几束花的花瓣上,它飞快地成长,集中了妖媚和芳醇。东墙角还曾经生长过数枝梅花,但记得它的人已经不多。现在只有一些无名花朵如虚幻的火开放在凡间。我们颤颤巍巍地前往旅行地,中途遇到了一些露营的人。他们都听说了那次战争。你瞧,他们都听说了。如果日出渡河,而东墙角的光可以升腾而至,那你便不必有任何担心。你起得虽早,但入睡得很快。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挽回你所失去的。是的,随时随地,在古东方的花园里,你右擎苍,左牵黄,心神奔突,肢体伸展。你还需要命令一只乌鸦返回它简陋的巢穴吗?独处无所长,我们要愤而离地。
30.万千复数
关于写作。其实我可能始终停留于起点上,以一个助跑的姿势度过终生,我始终没有真正踏上去往他乡的长路。但万物的光芒因为凝聚而突出,那最为凝重的露珠是不朽的。
关于露珠。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晶莹易逝,促成了它们的安息和不朽。
楼层下的阳光(金银大地上)涂满了异兽。它们俯瞰天空的时候正是时间的倒立泛滥之机。那些阴沉沉的草木影子、山水面容都在通天彻地的宇宙中漂浮。宇宙的空阔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珍奇花束。
每一个人的写作中都充斥着对自我写作的辩白。这是他的思维得以运转而不停滞的必然。在我们为建立一整幢大厦而努力的途中,万千星云图像集中在你的上空。正是它们在开启一种新生命:你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看守那些音速极快的呓语。
关于呓语。你匍匐得足够低才能看到它。你需要紧闭双目,才能逼近那个虚空中的图像。那些沟壑里有婴幼儿尸体。事实上,你见识过的死亡太多了。你软弱的同情心不足以解救,但它们反复地打开你的梦幻之门。你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造出梦幻语言的句子呢?
你软弱的同情心不足以解救……
关于重复:你要知道,寰宇周而复始,它并非一径地前趋而不回头。你记忆里有猛虎,它在荒寒的黎明中啸傲长空。那些涌流而来的猛虎声支撑他度过了七十二年。幻想就是这样诞生的。
那些被驱赶着离开原始森林的人群就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生殖。他们分辖着季节、水流、狂风和雷霆。你没有领受密语,你当然不知道他们以宁静的方式狂飙突进了一亿五千万年。
那奔跑在前的人也有错误。那暗自存蓄悲伤和欣悦的人也有错误。那逍遥而游的人也有错误。炽热的声色蒸腾着原始森林。那些喷涌而至的原始森林?
在我们视线的一个逼仄的空白处,隆鼻的祖母作图勾绘前生:那些繁盛的扭转乾坤的耕耘之锄。那些峰峦枝节……当然,她是万千人的祖母,集柔情的絮叨和霸王之气于一身。你见过她,在我们视线的一个逼仄空白处!
——怀念昌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