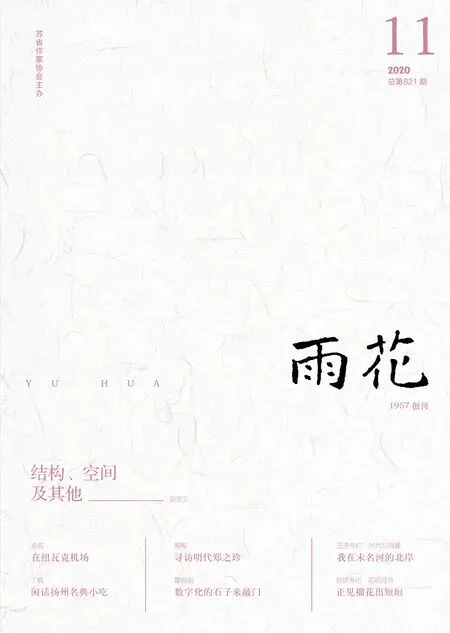喂海鸥
前不久,我再次见到了孔恰。我们有多久没见了?我问。
我完全不记得了,她说,我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用了,有十年吗?
“十四年了。真要命。”
我们坐在胜利大街一个叫作“沙漏”的咖啡馆里。我偶然看到这家咖啡馆在微博上的宣传,知道了这个地方。微博上有咖啡馆的地址链接,但我没能打开。我打通了上面留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孩介绍了好长时间我才弄明白确切地址,那个路口我从来没去过。后来,我带我的前女友来过一次。当然了,找咖啡馆还是让我费了一番周折。
我的前女友从郑州来东营。“我们一起跨年”,她是这样说的。虽然我劝了两次,她还是坚持要来。她来的那晚,恰巧有一位老领导有事找我。我们从机场直接来到沙漏咖啡,让她先在这儿吃点东西,我去去就回。等我回来找她的时候,她正弹着吉他坐在吧台边唱歌。而咖啡馆的老板,一个90 后的小伙子,已经成了她的粉丝。
“真的有十二年吗?”
“是十四年。”
“噢,真的有十四年吗?”
我和孔恰相识的年头还要长得多,准确地说,我们从初中二年级就认识了。因为她的母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可你一点儿也不显老,反而比从前更帅了。”孔恰叹了口气,“我们女人就不一样了,时间对我们总是特别残酷。”
十四年前,我还在政府机关做秘书。一天,孔恰打来电话,问我区医院是否有熟人。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得了什么严重的病。不是的,她解释说,是孩子。孔恰的女儿持续发烧,但又查不出原因,镇卫生院束手无策,害怕耽误诊治,所以决定转到区医院。我打电话联系了一位副院长,顺利地订到了床位。当时我正住在政府宾馆赶写一份紧急的会议材料,没有去医院帮她办理孩子的住院手续。为此,我感到一丝内疚,可毫无办法。我想孔恰的丈夫会陪着她的。
我已经做了四年秘书。开始的时候负责编写工作信息向市里报送,后来又撰写会议讲话材料。但我始终怀疑写这些玩意儿究竟有什么用处:加班熬夜好几天,一开完会就被人丢进垃圾桶。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好在,我提前写完了讲话稿,把它交给分管领导,等待提出修改意见。这样,我就有了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我决定去医院探望孔恰和她的女儿。我走出政府大楼,由于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走起路来两腿轻飘无力,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将要住院的病人。街角有一个小书店,我信步走了进去——我并不是想拖延见到孔恰的时间,多年来,只要看到书店就进去转一圈,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也许称为强迫症更准确一点。
书店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此刻,她正捧着一本书在读。我是这里的常客,彼此早已熟悉。在无所事事或心情欠佳的时候,我都喜欢去逛书店;把自己埋进书里,是我消解烦扰的方式——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我径直走到外国文学架前,先浏览了一番,又拿起一本库切的《耻》。回过头,那姑娘的目光正向我投来。“你可以把塑封拆开。”她说。而这正是我想问的。“他觉得,对自己这样年纪五十二岁、结过婚又离了婚的男人来说,性需求的问题解决得算是相当不错了。每周四下午,他驱车赶往格林角。准两点,他按下温莎公寓楼进口处的按钮,报上自家姓名,走进公寓……索拉娅从卫生间走出来,任浴衣从自己身上滑下,钻进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你想我了吗?’她问道。‘一直都想着哪。’他回答。”
我把书买下,走出书店。
太阳已经西坠,热力消散,即便直视也不再感到刺目。穿过一排栽种不久的苦楝树,走不了多远就到了医院。孔恰正坐在床边望着孩子的脸出神。刚刚睡着,她轻轻地说。我们来到走廊上。
“谢谢你帮忙。”一出病房门,孔恰就迫不及待地说。
我们来到走廊尽头,拉开的窗缝中窜进一股清凉的风。我背过身倚在窗边,看着空荡荡的走廊。由于逆光,孔恰的牙齿泛出一道银白的光。
“我们还用得着客气吗?”我打趣地说,“你该不会忘记我在你父母家吃过多少次饭吧。”
“那不算。”孔恰笑得很开心,“那怎么能算,那是在我父母家,你是去看望你的老师。”
可是,我为什么要那么频繁地看望我的老师,我为什么总要跑到你家蹭饭?我并没有说出口。我望着孔恰的眼睛,可以看见她眼角几条细细的皱纹。
“还记得你给我织的围脖吗?”我说。
我刚毕业不久,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镇上修筑公路。在工作的间隙里,我经常抽出时间去孔恰家。那时,她还要再等半年才能得到一个去乡镇学校当老师的名额。常常是晚上,我在孔恰家吃完饭,告辞出来,孔恰送我到院子门口,我们轻轻地碰一下唇,像呢喃的燕子。我从不敢,其实是从没想到要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轻轻地碰一下唇,我转身走掉,骑上新买的自行车,回单位宿舍。我知道,我并不是为了来吃孔恰的父亲做的猪肚鸡,或者蒸驴头(老头总是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只是想在走出院门后,与孔恰轻轻地碰一下唇。
有一次,孔恰的父亲不在家,她妈妈去厨房做饭,只有我们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起身回到自己的卧室,拿了一条长长的针织围脖出来,向门口看了一眼,快速塞进我的背包。
那天晚上,我把围脖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蓝灰色,正是我喜欢的那种颜色。羊绒线软软的。我脱了衣服钻进被窝,又把围脖系在脖子上,就那样睡着了。
“不记得了。”沉默了一会儿,孔恰回答。
“你很忙的吧?”她接着问。
“是。但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
“什么为了什么?”
“意义。我说我不知道这么忙有他妈的什么意义。”
“意义?”
孔恰转过头看着我:“要意义干什么呢?活着就是了。”
我想了想:“也许你是对的。”
旁边病房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端着药盒的护士。我闻到一股好闻的护士特有的气息,赶快把脸转向孔恰。后者似乎正在想着什么,眼睛里一片迷蒙。
孔恰的眼睛里一片迷蒙。她轻轻搅拌着面前的咖啡,一直到方糖彻底消失。我看着她的手指。与其他部位比起来,她的手指略显粗糙,也许是长久以来洗衣服或餐具的结果。而她长得最精致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她的眉毛。我知道她从来不用修剪眉毛。铁制的搅拌器碰在咖啡杯上发出轻微的响声。
我们坐在二楼一个靠近窗户的小小的隔断里。由于房间狭小,隔断更是局促。咖啡桌下面,我与孔恰的腿不时碰在一起。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让你永远猜不出画的是什么。而墙面故意刷成凹凸不平的样子,以显示主人与众不同的品位。世界上的咖啡馆基本上大同小异——它们总是要显得特别,到最后却几乎变成了同样的面目。
“你还是单身一人?”孔恰被我看得有点窘,她的脸有些微微发红。当然,也许是咖啡升腾的热气的缘故。
“是。”八年前,我的妻子离我而去。她实在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辞职,因为我已经从秘书升到了副主任,随时面临着进一步提拔。可我辞了职。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在那些无聊的公文里消耗时日。可我能干什么呢?显然,我也不是经商的料。
“我要做一个自由撰稿人。”我告诉她。
我每天窝在家里看书。我陷入疯狂的阅读之中。我想通过阅读把这些年来在公文写作中变得迟钝和麻木的心灵唤醒。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当觉得自己重新恢复了对语言的敏感之后,我拿起笔开始写小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大概写了十几个开头,可总是无法将任何一篇小说写完。我陷入无法抑制的失望和愤懑之中。每个晚上,我都在赶制那似乎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作品,而白天,不是睡觉就是喝酒。一年之后,我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她不能容忍自己和一个废物一起生活。也许任何人都不能。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孔恰说,“我觉得这里有点闷。”或许,她觉得她的问题可能给我带来了一丝尴尬,或不太舒服的感觉。其实没有。
我们拐上胜利大街。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之间,是密不透风的绿化带。我们慢慢地踱步,因为并没有急于要去的地方——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对晚饭后出门散步的夫妻。
“你现在还写诗吗?”孔恰对着我一笑,“我还记得你的一句诗。”她把那句诗背了出来,那是我十四年前给她写的诗中的一句。
如今我已知道了/怎样把一上午的时间/变得像一生那样漫长。
“是这样的吗?”
“是。”我故作爽朗地笑起来。这是我写给孔恰的唯一一首诗。在那首诗里,我虚构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个人,练习接吻。在我的想象中,那个女孩,就是孔恰。可是,另一个男孩是谁呢?当然,不可能有另一个男孩。不可能有这样的场景。那只是出于一个灵机一动的念头。我觉得这是个让人愉快的念头,以至于我每次想到这首诗,都想发笑。
孔恰的女儿出院后的一天,她忽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来感谢你的。”孔恰说。她想请我吃饭,以答谢我在她女儿住院这件事上帮了忙。哎呀,那真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也许孔恰只是以这件事作为一个由头,她想见我一面,就像我想见她一面一样。
我们一起喝了一瓶红酒。“红酒可以美容。”这是一个借口,而孔恰乐于接受这个借口。“我知道。”她说,“我喜欢喝红酒。虽然怎么喝也不会变美。”
事实上,孔恰是我们初中同学里最漂亮的女生(我们同级,但不同班)。而现在,她虽然已为人母,但比当初那个青涩的小女孩看起来更有魅力。
孔恰让我给她写一首诗。“你这个大才子,什么时候给我写首诗?”之前,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初中生活,以及一部分还有联系的同学。她还记得我从初二开始就在校刊上发表诗歌。
“不许赖账!”孔恰说。她拿过一张餐巾纸,让我给她打个欠条。
“欠孔恰女士诗一首,某年某月某日。”由于担心餐巾纸被划破,我的字迹模糊而又歪歪扭扭。孔恰开心地笑着,仔细叠起来放进包里。由于红酒的缘故,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喝了酒的孔恰特别爱笑。
“我们去银河公园遛一圈吧。”
红酒给孔恰的脸增添了好看的红晕。银河公园的风吹在她的脸上,使她微微眯起了眼睛,这样,长长的睫毛就在她脸上投下一小片朦胧的暗影。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让自己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
“我脸上长了什么?”
她故意把脸挡了起来。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拿开。我在她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像从前轻轻地碰一下唇。孔恰挣脱了我,把脸转向脚下的湖水。
也许,每个人那被轻易抛掷的青春岁月里都埋藏了一段若隐若现的情感。一开始,你认为那只是吸引,或者只是喜欢,到后来才发现不是,不仅仅是。可当你明白过来,往往已经晚了。
那天晚上,孔恰没有回家。她是有备而来——她丈夫刚刚出差了,要一周时间才能回来。而作为一个秘书,我在单位通宵达旦加班是常有的事儿。我们住进了公园旁边的一家宾馆。
孔恰说:“我要用一个晚上,来补偿你的八年。”
银河公园是东营的第一个公园。它破土兴建那会儿,我还在读高中。那时候,我经常骑一辆大金鹿自行车来这里转悠。我盼望能有一个幽僻的场所,比如一片繁花一片绿树一片碧蓝的湖水,让我抛洒多余的激情。我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会在湖边的宾馆里抱着一个失而复得的肉体。
“你碰到一个什么东西了吗?我戴环了。”
“是的。”
“就是乳房有点软了。要不,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是的。”
“你怎么就会说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晚上之后,孔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一片羽毛被疾风吹到了天边。我有时一个人去银河公园,在我们一起走过的小路上漫步,拨开伸展的紫荆枝条。我从公园的侧门出来,抬头寻找那家宾馆的某个窗口。那天晚上洗完澡之后,我曾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看到了幽深的夜空中升起一弯新月。
可是,那个晚上真的存在过吗?
我抢先伸手拨开伸到孔恰胸口的一根枝条,孔恰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是不是有一个蹲过监狱的朋友?”她说。
“已经出来了。出来两个多月了。”
“现在我们成了邻居。我见到过他几次,但没有说过话。”孔恰说,“我对蹲过监狱的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没必要,他只是因为一点经济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替别人背了锅。这种事常有。”
“他现在好像搞摄影了,出出进进总是背着一架照相机,有一个很长的镜头。”
“听说过。他常去黄河入海口的湿地拍鸟。有一大群热衷于拍鸟的人,有一些还是政府官员。说不定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接近他们,寻找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我说,“有时间我约他给你拍一组照片吧。”
“我又不是鸟。”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十几年前,孔恰跟随她的丈夫去了当年堪称荒凉的港口上的某个企业。现在,他是那家公司的副经理。在谈到她的生活的时候,孔恰的声音里有一种浓烈的倦怠感,仿佛那些日子浸透了海风的苦涩气息。在渐次亮起的路灯的照射下,她的脸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眼角处浅细的皱纹不见了,仿佛又回复到了我常常去她父母家蹭饭时的样子。我的大脑随即不可救药地停止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我相信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永恒。而对孔恰而言,那些日子只不过是岁月那不可阻挡的流逝,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许有,但她不会主动说出来,我也无法追问。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护城河边。“护城河”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叫法,随着城市的扩张,这条人工河几乎已经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我们沿着砌石台阶下到河边。河岸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倒映在水中的光影随着水波的荡漾而不停地晃动。不远处有一排木椅,我们走过去坐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吗?”孔恰直直地看着面前的河水,也许是映在河里的灯光。
“我知道你会说的。”
“如果我不说,你会不会问?”
“不会。”
“啊,你还是老样子。”
孔恰捡起脚边的一枚石子,使劲扔向河里。“咚”的一声,河里的光影破碎了,一圈圈地扩散,一点点地迸溅着,像溅起了无数星星。
“我想来想去,也只有和你说,再没有第二个人。”孔恰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她又扔出一枚石子,这次并没能扔进河里,而是掉落在岸边的碎石堆里。
“我不能不找个人说一说,我快要疯了。”她把身子转过来,“我女儿不是我丈夫的孩子。”孔恰深深地看着我,似乎这样可以进一步加重这句话的分量。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震惊。有一个瞬间我想,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才能让孔恰感觉到安慰呢?孔恰把头埋在自己胸前。我伸过手轻轻拢住她的肩膀。我能感觉到,孔恰的呼吸渐渐由粗重变得轻柔起来。
“你丈夫知道吗?”
孔恰没有回答——我也不需要答案。
“这件事,我闷在心里十七年了。”孔恰说。
我决定不再说话。也许孔恰并不是来寻求宽慰,她只是想说出它。如此,这件秘密就可以由两个人来承担。
下雨了。细细的雨丝垂落下来,落在孔恰的头发上。雨太细了,以至于孔恰要过一会儿才能发觉。雨丝也落在我们身旁的护城河里,河水没有泛起丝毫涟漪。
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当然。孔恰去了她爸妈那儿,她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我没有开灯。我站在窗边看了会儿外面的天空和楼宇,想起一个古老的词:万家灯火。然后返回身,又为它增添了一盏。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昨晚孔恰说的那件事。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有个人一直藏在她心里,才使我们俩的交往止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夜晚吧。今天是个大晴天。起床后,我用蒸蛋器蒸了两枚鸡蛋,用豆浆机打了两大杯豆浆——这是我的经典早餐。然后拿起喷水壶去阳台浇花。它们都长得病恹恹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让它们长得像公园里的绿植那样茁壮。可我已经尽力了。
阳台上的阳光让我想到了青岛的海滨。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我想,在这样的天气里,坐在青岛海滨的长椅上看书,该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二十分钟后,我背着背包下楼,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长途车站。包里放着惠特曼的日记选集。这个预言美国应当是碎片化写作的诗人,在他奔放的生活里总是有着释放不完的热情,对于大自然也是如此。
汽车驶离东营。路边的速生杨一片片地向后闪去。这种生长速度极快的树种,的确适合用作道路绿化。树林的边缘隐现出几处水洼,几只白色的鹳鸟站在水边发呆。再往前行,几座高大的烟囱扑入视野,那是一片化工厂。我收回目光,从包里拿出矿泉水和书,又拿出两块巧克力,剥开一块放进嘴里,把另一块递给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姑娘。
“不了,谢谢。”她对我一笑。当我再次把巧克力放在她抱在怀里的包上时,她没有再拒绝。
汽车将在路上颠簸四个小时。上一次去青岛,还是半年前,我去接一位从成都来的朋友。只不过那次是开车去的,只用了三个小时。
我始终不能明白,人的记忆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错位。比如,孔恰早已忘掉了那些流落在门口的轻吻。那条针织围脖她也认定只是我的幻想之物。我是否在我的脑海中推演了一种不存在的生活,然后就把那些场景深深地刻印下来,就像孔恰一再坚持的那样?对此,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相信它们就像这辆行进中的大巴一样真实。
我看了会儿书。由于车子晃动太厉害,眼睛很快就累了。我闭上眼,可毫无睡意。想和旁边的姑娘聊会儿天,又觉得有些唐突。整辆车上都是去往青岛的人。我们素不相识,目的也各不相同,却汇集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去往同一个地方,想一想,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恩赐:同行者的感觉减轻了我的一部分孤单。而时间,就在大巴不停的行进中一点点流逝,越接近终点,我就越有一种恐慌之感。
当我终于坐到海边长椅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海风仍然是温暖的,它吹在我的脸上、胳膊上,也吹在我手中拿着的书上。我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海边的景色使我把东营和东营的一切全都抛开了。我看到惠特曼在山坡上徜徉,或席地而坐,溪流潺潺,和风习习,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准备随时记下那浮现在心间的诗句。是的,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像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同一个时空之中。昨天的我已经死去,连同那晦暗不明的过去。尽管时间周而复始,但属于每个人的总是不尽相同。我坐在青岛海边这条木制长椅上——我记得,上次来青岛的时候,我坐的也是这同一条。我看着面前的大海,看到阳光随着涌向岸边的波涛一浪一浪地向我涌来。
我站起身,摸了摸背包里带的面包——我想一直走到栈桥那边,去喂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