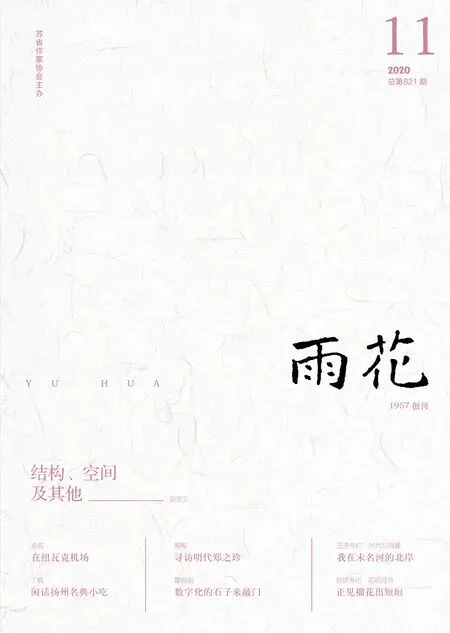迷魂记
1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今天聊到这么多,我也不会去和其他人说这件事。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包括弗洛伊德什么的,也咨询过一些心理和精神疏导方面的朋友,但是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什么工作压力太大、什么神经衰弱、什么电影看太多了有心理暗示之类的。但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所以,您向我预约了?”
“是的。我也是经由一些人介绍和推荐才找到您的。他们说您对于解决这类困惑特别有经验,和其他心理医生不大一样。”
“我和其他心理医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非要说不一样的话,我的收费可能格外高一些。”桌子对面的人发出了短促的笑声。
这倒不是恭维,我是听了不少人的推荐才来的。有些人是这个行业的资深者,有些是艺术或者影视圈的大牛。他们在采访间隙的闲聊中听说了我的这个问题,都不约而同提起这位医生的大名。“去听听他的建议吧,你会受益匪浅的。”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采访对象这样向我推荐,我才下定决心,联系上了这位医生。想到这,我看了看桌上的马克杯,杯子里还有一些咖啡,我抓起来一口喝完。我不是太喜欢这种带糖的速溶咖啡,如果有喝咖啡的必要,我更偏爱无糖的美式咖啡。我不喜欢甜食,甜味会让人昏昏欲睡,也会带来某种瘾,让人脑子不清楚。
我所坐的位置正好在房间的一角,足以看到整个房间的全貌。房间的灯光并不亮,厚重的窗帘让人看不见外面。透过窗帘隐约的光,能够看到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羊头,周边有一个圈,这无疑为整个谈话的环境添加了一点神秘色彩。房间的某个角落应该有一个音响,声音调的不大,放着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好像是某部电影中的配乐,好像还是个挺出名的中国作曲家的曲子。我记得今天外面阳光还不错。这应该是故意设置的,黑暗、神秘的雕像和音乐三者联合,给人带来某种慵懒的舒适感,让人可以放松地袒露心扉。桌子对面的人没有说话,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讲我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某个地方,就是那种自己从来没去过,但是又非常熟悉的地方。我上网查了查,网上的各种资料和视频说得很吓人,有些说得像恐怖电影一样,说这种记忆来源于往生。我觉得这是瞎扯,我不相信神神鬼鬼的这套东西,但我确实也遇到了我解释不清楚的一些情况。”
“您是在哪里遇到这种情况的?”
“在我的梦里。”
“我们都知道梦是由多种心理暗示组成的,您可能确实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在潜意识里,您是有可能有这种感觉的。”
“不不不,我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在梦里,我来到了一间房子里,我很清楚我没有来过这里,它更像是我闯进了另一个人的脑子里。最近有一个时髦的东西,叫沉浸式戏剧,我在梦里的情形就像这样。我好像就是那个人,身处一间屋子里,屋子不大不小,但是有点像广播的录音室,有各种乐器。”
“那应该是一个录音棚。你有没有梦到这个录音棚有什么特点?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扮演’的那个人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应该是在创作,正在创作一首歌。在梦里,它应该是某种有待完成的半成品。因为梦里的‘我’很兴奋,同时也很焦躁,一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或者是做一些标记。偶尔我会拿起手边的某样乐器,应该是一把吉他,弹上几个音,再继续写。”
“您为什么觉得这是在创作?”
“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
“还请您详细说一说。”
“好的,怎么说呢?我在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时候,也会有相似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某种‘直觉’。这么说或许不太准确,但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了。我看过一位著名的作家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具备创作才能的人,在创作的时候会被某种直觉所牵引。这种直觉不同于技巧、逻辑、常识和认知,是凭空生长出来的东西。网上有句话,叫‘被上帝抓着手创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确实很有意思。您对宗教有所涉猎吗?”
“我之前说我是无神论者。”
“啊,很抱歉,我可能没注意到。是这样的,在《圣经》里,人们被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而您刚刚所说的那种直觉,在宗教领域里,大概就被称为灵。”
“我不是很懂这些。”
“那也没关系的,我们说回梦吧。您做这个梦有多久了?”
“快小半年了,平均一个月梦见一回。”
“每个月都会做这个梦?”
“是的。而且这个过程也不断渐进,直到上个月,这个梦戛然而止了。”
“你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他完成了那首曲子,然后把曲子投递到了某个地址。过了一阵子,可能是几个小时,又或者是几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他很高兴。然后我就再没做过这个梦。”
“既然已经不再做这个梦了,您为什么而苦恼呢?”
“在这之后,我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这些事情可能都是真的。根据梦里看到和听到的,我去查了查,发现在我的城市里,确实有一个录音棚。而前几天,我去看了看,发现里面的布置和我梦里的几乎一样。”
“那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是啊,紧接着我又去了这家录音棚所属的公司,调查了一下这家录音棚。发现其实这家录音棚已经很少用于专业录音了。它建成不少年了,设备老旧、地段偏僻,已经没多少人在用它了,起码最近半年都没被使用过。我不死心,又去查了半年前的记录,发现它确实以日租的形式,被一个人用过。”
“这个人是谁?”
“我不清楚,我按登记的电话打过去是空号。我找了找和他认识的工作人员问了问,只知道他大概无业,在酒吧卖唱,年纪也不小了,三十多岁。交过一个本地的女朋友,不过后来分手了。”
“您的调查能力相当厉害!”
“算是职业习惯吧。”
“后来呢?您查出什么有价值的了吗?”
“信息太少了,他又是外地人,除了名字和基本信息,我没查到更多。我估计是个小人物,在之后的一些新闻里也看不到他,大概回老家了。”
谈话到了这戛然而止,对面的人点起了一支烟,似乎进入了某种思考的状态。我往后靠了靠,想抓起杯子,再喝一点咖啡,但杯子里已经没有咖啡了。我看了看桌子上,零散地堆放着一些糕点,房间里的灯光太暗了,我看不清形状和颜色。但我还是决定抓起一块放进嘴里。我之前没有尝过这种小东西,我确实不喜欢甜食,可这种不一样,虽然是甜食,但甜味和速溶咖啡那种廉价的甜不同,显得很高雅。我吃完一块,忍不住又抓起一块。在我吃到第三块的时候,对面终于开了口。
“先生,您的困惑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方便的话,您或许可以给我一些时间,我相信我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对症下药,解决您的困惑。”
我点了点头,准备起身离开。
“对了,先生,方便的话,您能把您查到的名字告诉我吗?”
“宋楚,唐宋的宋,楚河汉界的楚。”
“宋楚——好的。”
2
凌晨三点差五分钟的时候,宋楚总算站起身活动了一下,他摘下耳机,看了看手机的时间,发现有一个未接来电,三个多小时之前打的,还是座机号码,宋楚回拨过去,显示忙音。
昨天一大早,宋楚从管理员那里接过录音棚的钥匙,之后就一直在做手头这个DEMO(注:音乐小样,试样唱片,是歌曲未正式完成前的一个范例)。词曲已经完成了,而且他觉得完成得不错,这让他一直很兴奋。烦人的是现在正在做的编曲部分。有人说编曲就是给一首歌穿上衣服。照这个说法,宋楚奋战一晚上,才给这首歌穿上了裤衩。这主要是因为,宋楚对于预副歌的部分一直不满意。他在鼓点衔接之后是进一段贝斯去填充它,还是直接用电吉他做底音两个选项之间犹疑不决。为这个三十秒左右的预副歌,宋楚琢磨了有仨钟头,耗费了大半盒烟和小半盒中途点的外卖——这是他准备拿来当夜宵和早饭的台湾卤肉饭。经历长时间思考后,宋楚最终勉强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再抬头已经是这个点儿了。这比他想象中花费的时间要长,主要也是因为录音棚的设备落后,现有的设备不支持多音轨导入,宋楚只能一遍遍试,凭着记忆去摸石头过河,录一遍伴奏,再用话筒自己唱一遍,中间不能打磕巴,不然就得从头再来,容错率极低,即使是专业歌手和编曲人也很难做到一次成型。宋楚一个人鼓捣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这个录音棚现在归属于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为私立学校的小朋友们录制毕业歌,或是为新婚情侣录制婚礼用的MV。设备能用,但肯定不好用。宋楚一般一个月来一次,租金不便宜,以他的收入水平,一个月来一次已不容易,还要点头哈腰,提前打好招呼。宋楚一直没有正经工作,来这座城市,主要收入是靠各种走穴和在酒吧驻唱。没有正经工作和宋楚的臭脾气关系较大。他始终认为,在酒吧唱歌是混饭吃,在录音棚里录DEMO才是正经事。更何况,最近录的这段DEMO 宋楚自己比较满意,灵感来自于1986年日本的一部动画电影,叫《时空的旅人》,里面讲述了一个女子时空穿越的故事,从80年代穿越到二战战场,再从二战战场穿越到本能寺之战,概念先进,十分带感。时下电子乐正热,要是碰上灵光的公司,保不齐就火了。但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意味,最近几年,宋楚做的DEMO已经不少,广撒网、打招呼,甚至去人家公司门口定时定点蹲守音乐总监,录用率还是寥寥,赚到的钱还不够自己租棚子和设备。
宋楚遇到的情况同许多艺术家遇到的情况一样:不被赏识的才能百无一用,并不足以摆脱任何现实的窘境。这其实也是宋楚当下的困境,他现在已经三十有二,靠音乐来体面地活着,相比于大红大紫赚大钱,变成了一个更实际的梦想和目标,性价比也更高。用性价比衡量梦想,有辱梦想,可正因为有实际指望,和高远的目标相比,就更具有杀伤力。电视上的女明星只能可望,而隔壁学校长得像女明星的妞却可即,更容易让人付出行动去努力,这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也不是没人介绍别的活儿。有朋友介绍他去做婚礼的司仪,说有舞台经验,背串词就行,宋楚犹豫再三,还是没去。做酒吧歌手尚且可以说是兼职,且和歌手沾边,但去做司仪就难以自辩了。实际上,这种强烈的自尊心,让宋楚在生活里处处碰壁,前阵子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女朋友原先也搞音乐,但最后当了老师。她和宋楚熬过了春夏秋,却没熬得过没有指望的寒冬,在来年春天来临前和宋楚说了再见。宋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暗自关注着前女友的微博,时不时匿名去看看,终于有一天发现她发出的婚纱照。未婚夫和自己不太像,按图索骥一轮搜索,发现是个杂志的记者。宋楚起初有所不甘,后来发现男的其实也算半个作家,似乎还有几分才气,写的几首诗还确实不错,比自己之前遇到的沽名钓誉的文人好不少,因此他最终和过去和解。
虽说和解,但是过去的那些事情总是能在闲的时候冒出来,像是米饭里的沙粒,揉碎了硌人。宋楚一时间想出神,手机又响了起来,不过是邮件提示。他看到对方邮件的地址,点开邮件。邮件内容短小,措辞客气:
宋先生好:
您之前发送的DEMO(编号4/5那一组)我已经听过,希望与您进行下一步讨论,或许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您音乐中的一些奇特的想法。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本周六下午前往如下地址,期望与您见面,顺祝您生活愉快。
邮件下方附了一个地址,就在离宋楚住处不远的市中心。可这封短小的邮件却因为底下的署名而熠熠生辉。宋楚盯着这个名字许久,其间出去洗了一把脸,确保自己不是因为缺乏睡眠而产生了幻觉。
离周六还有三四天,宋楚忽然没了鼓捣音乐的心思,也没再去酒吧唱歌,人一下就空了下来。但他倒是没闷在家里抽烟睡觉,而是每天出门,早上从城东出发,一路行经人民广场、鼓楼、红舞台人民剧院、人民文化宫,抵达市博物馆,在博物馆晃悠一整天,然后在旁边的步行街随便吃一点,洗个澡回家。这种“无目的性”的城市漫游,让宋楚有了一种“专心搞创作”的心态(而且这让他很快乐)。他用手机随意记录路上所见的点点滴滴,包括但不限于路边随意搭建的窝棚、小区里的钉子户、有名艺术群落里无所事事前来度假的白领、阳光透过楼宇洒在地上的碎黄金。
周六上午,宋楚早早出了门,考虑到或许有个现场考查的环节,他把刻着自己名字的宝贝吉他和几本记录想法的乐谱都塞进了包里。去那个地方并不麻烦,地铁和公交都可到达,但地图上显示到站后还要行走四五百米。宋楚看了看,有一班公交直达,目的地在终点站,只是班次少,是X开头,叫X818,宋楚来这座城市十多年,从没搭乘过这班车。上车后,人并不多,宋楚找了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开始玩手机。刷微博,一个搞笑视频看到一半,睡意就忽然翻涌呛人,三五下将他淹没。
宋楚醒来的时候,已经站在站台了。估计是没睡醒,他头疼得厉害,竟然记不起是如何下的车,他低头看了看,所幸吉他包已经带下车。宋楚掏出手机,打开导航。导航显示地点在一个老式小区里。宋楚原以为四五百米的路应该会比较好走,谁知道百转千回,和迷宫似的。宋楚按照导航一步步迈进,穿过小区里外地人经营的果蔬市场、二手家具回收处、干洗与皮具养护店;穿过晾晒的床单被套和奶罩内裤、走道狭小逼仄的老式居民楼;穿过“初极狭、才通人”的小区走道,经过一小块广场和健身器材,又转了四五个弯,豁然开朗处有一小片林子,绿意盎然,榕树和棕榈相映,鸟啼阵阵。明明才走了几十米,旁边的闹市喧嚣像是另一个世界,宋楚莫名想到《哆啦A 梦》里的任意门,打开门,呼的一下就是另一个世界。这让他觉得不真实,但时候不早,快到两点半了,只好继续往前走。穿过林子,是一个中式庭院,黛瓦白墙,高得很,有一扇木门,样式古朴。上面有个牌子,上有俩字,篆体,好像是什么园,但具体是什么园,宋楚认不出来,前面那个字也不像施。宋楚在门前站定,按响了门铃。过了会儿,里面回音了:“宋老师对吧?请稍等。”声音不太听得出年纪,但温和有磁性,和宋楚想象的不大一样。过了会儿,木门吱的一声响,顷刻大开,宋楚走了进去。
3
天气预报说昨天晚上开始有寒潮,延续两天,所以下午出门前,我特意穿上了一件羽绒服,是妻子前不久托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学生家长买的。妻子出门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好说,采访预约在上午十点,但持续多久不清楚。妻子“嗯”了一声,在我耳边轻轻吻了一下说,今天包饺子,晚上等你回来吃。
我看了下手机,发现主编发来的语音,耐着性子全听完后已经快走到小区门口了。语音的内容主要是要求这次采访务必要重视,要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对待。主编这么急,是因为上个月的专稿反响平平。上个月采访的那个导演是个老狐狸,不太爱说话,回答问题规规矩矩,驾轻就熟,说什么都能圆回自己喜欢的话题,甚至聊到自己早逝的哥哥动情流泪,这一切和几年前的另一次专访相比,只字不差,不禁让人怀疑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排演。而对于杂志来说,反响平平是最糟糕的事情了,无人问津比被人破口大骂更为致命。专访是杂志的招牌栏目,可不能砸了。为此,编辑室与采访室开了两次内部会议,说要扭转颓势。主编亲自出马邀约,邀请到这回的采访对象。对方来头很大,给的头衔是音乐家而非音乐人,是好几部拿了奖的电影配乐的主要操刀者。而他最近配乐的一部电影刚刚获得某电影节的入围提名,史无前例,风头正劲。我大学主修中文,自己也写点诗歌,但对音乐不太了解,所以昨天晚上特意问了问妻子。妻子说,确实是个有才华的音乐人。我说,是不是像坂本龙一那样?她说,有一点,不过比他更不羁些,我说那就是和窦唯差不多?她笑了笑,说也不至于,他年纪太大了。我又去查了查资料,汇总成七八页纸,包括一些特有音乐流派的概况、发展历程,还有著名乐评家的点评,汇总以后往脑子里塞,不求理解,囫囵吞枣,像是临考的学生一样。整理完以后,妻子说,上次医生嘱咐你吃的药最近在吃吗?最近还失眠吗?工作压力别太大了,不行就先糊弄着了事。我答应下来,心里却一直惦记着。
等我走到路口的时候,主编又发来一个定位,说这是采访对象的住址。我看了看,靠近市中心,似乎在一个很老的居民小区里。好在那个地方本地人都很熟悉。时间过了早高峰,我打了辆车,直达小区门口。小区里挺热闹的,到处都是来往行人,烟火气足。我依照导航,走进小区,进去才知道里面宛如迷宫,七拐八拐,还要穿过一片林子。林子看似胡乱生长,实则经过精心打理。树木丛生,南北混杂,寒热交加,走到里面我才发现,原来整片林子只有一棵树,一棵老榕树,独木成林,枝丫伸进地里,吸收残败枝叶的腐殖营养,因此长得分外茂盛。我穿过林子,发现这里位置确实好——背靠两栋居民楼,正对一小块恰到好处的空地,既保证光照,又兼具私密性。
穿过林子,才看见房子,典型的苏州风格,但格局上却四平八稳,透过掩映的围墙能窥见宅邸的一角,里面开阔,似乎有山有水,又有数道间隔,这种设计看似传统,但实际混杂了很多现代元素。我走向前,发现大门锁了,找了半天才找到门铃,摁响后,那头传来声音,让我稍等,声音听不出年纪,但挺好听的。过了会儿,门开了,屋子的主人站在门内侧,笑盈盈地迎接我,这让我有些惊惶,连忙伸出手,却发现对方的手意外地宽厚、细腻、温暖且有力,我脑子里忽然蹦出来一个想法:这位音乐家应该还很年轻。但我先前查过资料,音乐家快七十岁了,去年还被曝光罹患某种慢性病,所以一下苍老很多。我抬头看了看他,发现他虽然有皱纹,头发花白,但穿着干练,腰杆笔直,眼角带着笑意,没有平时所见老人的迟暮感,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些。
他迎接我进门,进门后我才发现,在门外见到的不过是宅邸的一角。进门后,也是一片林子,不过比外面的林子更精致一些,路面由山石铺就,错落讲究。而宅子中央有一片池子,池面如镜,不起波纹,走近了才发现池子里养了不少日本锦鲤,而房子的主室几乎完全透明,墙面由单面透光的玻璃组成,架以白色的框架,现代感与古典庭院相得益彰。从设计到布局,细节处都很用心。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侧室,一个横架在池塘上,一个掩映在主室一边。屋子的主人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在介绍中他特别注意分寸,点到即止,比如这是会客厅、这是小花园、这是招待客人时用的餐厅,绝不让人产生夸夸其谈的印象。我对他印象不错,对市中心还存在这方宅子也十分愕然。但他似乎习惯了这种愕然,并不过分谦虚,以免给他人留下虚伪的印象。他将我引到客厅的沙发上,让我静候一会儿,他去处理一些事情。这让我有时间打量客厅的装饰。
客厅的一二层打通了,这让空间显得很开阔,配色主要以灰白为主,简洁却有些过冷。镜面是一色无缝的贴面瓷砖,干净得能透出人影来,而墙面上挂了很多画,大部分是潦草、凌乱的线条与奇怪符号组成的现代画,用色大胆,而在正对池塘的墙壁上,是一只山羊头,挂在一个画着五角星的盘子上。山羊头白骨嶙峋,却好像有生命似的一直盯着这间客厅。我觉得这样的陈列有种熟悉感,在某处我或许见过相同的摆设。我一边想,一边盯着羊头,或者说是我与羊头互相对望着,我忽然觉得有种眩晕感。这时,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这羊头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送给我的,他和我关系很好,启迪了我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我连忙回身,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手里端着一个木制托盘,上面有两杯茶,茶水绿莹莹的,还有一叠黑色点心。
我们坐在沙发上,音乐家将盘子放下来,说:“我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希望没有吓到你。”我说没有。他拿起点心,邀请我尝一尝,说这也是那位朋友送给他的一种小甜品,叫羊羹,味道不错,是用葛粉、面粉、红豆做成的。我喝了一口茶,吃了一小口羊羹。因为不喜欢甜食,我之前应该没有吃过这种小玩意儿,但这种甜品的味道却很熟悉。我想起了些什么,但来不及细想,我两三口吃完了手里的糕点,说出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他笑着说,音乐是听的,并不是说的,我尽量。我点点头,说,您其实也不必担心,就当是平常聊天。
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笔,说,那么我们就开始采访吧,刚刚进来看到您这房子真的吓一跳,这么大的房子就您一个人住吗?他说,算是吧,但是请了一位保洁员,她每周一、三、五会过来打扫一下,顺便给我带些食物和生活用品。我笑着说,您现在主要是居住在这里吗?他说,对的,到了这个年纪,不大走得动了,更多是根据不同人的邀约,进行一些创作。还有就是为自己的一些音乐寻找灵感。我说,其实我在来之前听过您的作品,发现您的音乐作品在不同时期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您早期的音乐配乐以钢琴独奏为主,后来尝试一些交响乐的风格,而我看您最新的作品——就是那部最新电影的配乐,又是以电子乐为主。他笑了起来,说,音乐这种事情,就像和不同的女人谈恋爱,不同年纪的男人喜欢的女人不太一样。我笑着附和,说,那您喜欢什么样的呢?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他却忽然严肃地开始进行思考,过了一会儿才说,年轻的时候喜欢成熟、丰腴的,到年纪大了,发现还是年轻一些的好。我打个比方吧,你应该没有很长时间吃不到肉的时候吧?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年轻时候经常半年都吃不了一次肉,每次吃肉都能把自己吃伤了。而肉吃多了,看见肉就恶心,就开始喜欢吃清炒时蔬。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比喻,觉得很新奇,说,那您现在呢?他说,人越老越像小孩子,说着拿起桌上的羊羹,往嘴里塞,缓慢咀嚼,仔细吞咽,仿佛在对待某种艺术品。
接下来,我问了几个准备好的问题,他一一回答了,只是说得很慢,夹叙夹议,掺杂了很多自己在世界各地旅居时候的见闻,而且经验老到——每当我提出的问题越界时,他就像是年长的水手,眼睛半睁半闭地蹲守在舵头,毫不在意,但总会在关键的地方,稍微用一用力,将话头扳回正常的方向。不过他很会聊天,聊天时鲜有冷场,比如他会主动提及和几位导演合作时无伤大雅的趣事,几位著名演员工作或娱乐时值得一提的癖好,同时向我展示几张老照片、几件纪念品。他很熟悉采访的这一套流程,通过不时补足的细节,让整个谈话充满趣味。
采访即将结束,他忽然提出要带我看看他的收藏品。“你或许会感兴趣的。”他主动将我带到宅子的侧室,说这里是他的收藏室。我原以为收藏的是书籍或珍藏版本的唱片,结果全部是乐器。里面按次序放着一架钢琴、一只麦克风、一架旧的手风琴、一支黑管,两旁则是各种各样的吉他,摆放得并不整齐,更离奇的是每一架乐器都配了一个模特。模特手持乐器,仿佛正在演奏。我细看,发现模特大多都做得很精致,虽然没有细节,但都精心通过简洁的线条隐隐透出生命力。他说,静置的乐器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每个都配了一个模特。说着,他饶有兴趣地向我介绍各个乐器的故事,像是给初学者做科普,但介绍时的用词却很奇怪,比如在介绍一架钢琴的时候会说:“这架琴很漂亮,也很调皮,很有情趣,会制造很多惊喜。”在介绍一把厚实的吉他的时候则说:“这把吉他是我最新的一件收藏,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现在很难找到这么纯粹的东西了,很年轻,很有活力,经常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想法和创意,有时会让我吃惊,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依次介绍了几件,都是如此,我将这种特别的介绍,理解成为一种独特的幽默,或是艺术家到了某个境界后进入的特殊魔怔。
离开侧室的时候,采访接近尾声,时间已经不早,我估计了一下,采访的内容足够支撑起一篇文章,就关上录音笔,准备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告辞。我喝了一口杯子里的茶,留下小半口,开口问:“很多评论家在讨论您的音乐的时候,经常感叹于您层出不穷的创造力,每个阶段都似乎是全新的,那么,请问您觉得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您这样不断创新和突破的秘诀是什么?”这其实是一句常规性的套话,因为即使是成熟的艺术家,也很难给出具体的答案。我采访过很多人,有些人说是勤奋,有些人则说是天赋,最离谱的说是来自上天的神启,也有说其他的。问这个问题是例行公事,需要写在访谈的结尾,并需要经由加工,总结成一句看似金科玉律但实则狗屁不通的话,以满足读者漫长阅读后迫切需要的总结陈词。
但他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陷入了漫长且仿佛不见尽头的沉默。沉默持续的时间很长,长到我能注意到夕阳沿着客厅内的落地窗缓缓滑落,窗外万物静谧,万物在沉默里陷入静止。可我能注意到他在思考,他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漫长地思考。可能是出于一位记者的敏感,我觉得他能给出一个好答案。于是,我也配合着这种长时间的、并不寻常的沉默。直到我觉得这种沉默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才终于开口,说,我觉得是“灵”。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出对于这种答案的疑惑,他就接着往下说,你对基督教有研究吗?我说,并不太懂。他开口道:这么说吧,人类进行创作时完全不可或缺的灵感、难以言喻的启示,都是来源于‘灵’。他们认为,只有少部分人拥有‘灵’,而且‘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枯竭。很多天才的创作者,为什么都像昙花一现,在创作出好的作品以后,再无佳构,就是因为‘灵’的枯竭。你刚刚问我有什么秘诀,我的秘诀就是保持‘灵’的充足。记得之前我和你说的那个欧洲朋友吗?他是最早和我说这些的,他还和我说,这种枯竭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听他的语气,似乎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种玄而又玄的宗教问题,而是某种可操作的技术问题。我的疑惑更多了,于是接着问:“您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想了想,说:“首先,我们需要寻觅这种具备特质的‘灵’,但这种‘灵’比较难寻找,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多人蝇营狗苟,纯粹的‘灵’越来越难找。”这并不是问题的答案,更像是一句抱怨,但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于是耐着性子等待。果然,他往后靠了靠,这时的阳光透过窗子,客厅大半被影子笼罩,他坐在那边的椅子上,影子罩住了他大半个身体,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客厅里忽然冷了起来,周围传出“嗡嗡”的声响,像有人在窃窃私语。
或许是几秒钟,又或者是几分钟,影子那边传出声音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我似懂非懂,只能顺着他的话往下说:“那您是认为,‘灵’的枯竭是有办法避免的,对吗?”“当然是有办法的了,不过请容许我保留这个秘密,可正如我刚刚所说,避免灵的枯竭,这就是我创作的秘诀。”说完,他从阴影里起身,余晖伸进客厅,把他的影子拉扯得很长。他没有开口,但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从宅子里出来后,一直到马路上我还在思考他的话。正是晚高峰的时候,我给妻子发了信息,说我采访结束了。妻子拍了张照片给我,照片里是包得整齐的饺子,鼓鼓囊囊,用菠菜汁点了头,亲切诱人。我快步经过地铁口,发现有人站在路口卖唱。他穿着邋遢,头发似乎很多天没有洗了,手握话筒,唱着一首我没听过的歌,似乎是原创。旁边有一个琴盒,里面不见吉他,只有两张二维码躺在里面,还有一小把硬币。我驻足听了一会儿,觉得唱得挺好,掏出手机,扫码付了二十块钱。他抬头看看我,触电似的立刻移开眼睛,低头说了句: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