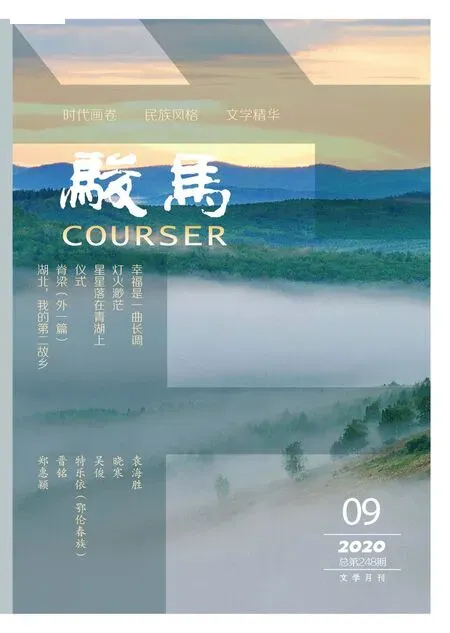幸福是一曲长调
■袁海胜
一
从阿斯哈图石林出来,汽车一路沿着热阿线走,两侧风景像幻灯片一样秒变。草原像一个喜欢炫耀的孩子,把好东西一样一样地拿给我们看。我的眼睛忙不过来,为不知该看哪一处风景而纠结。心里想,要是住下该有多好!
图嘎的三座蒙古包并排扎在公路边的草甸上,午后的蒙古包上镀了一层金箔,比阳光还耀眼。蒙古包上的陈年雨渍像地图。包前有半米高的木栅栏,上面挂一个木牌,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汉字:住宿、餐饮、手把肉。字被认真地描过几遍,墨渍逶迤,重影叠加。住宿餐饮透出通俗文化意味,手把肉是草原刮过来的一股风,挟裹浓郁的民族风情。
手把肉——胃肠随之蠕动,像有一只只小手伸出来,在寻找手把肉呢。人的欲望在食物面前表现得最尽职。
图嘎年纪不大,32 岁,脸色粉红,黄眼仁,褪色的半袖衫上印着硕大笑脸的猴。他搓手,裸臂晒成酱块的颜色,笑容像盛开的格桑花,这种花我原以为只有藏区有。图嘎的蒙古包前有一片在风中笑弯了腰的格桑花。难道我们有这么可笑?格桑花的笑有点放肆,而图嘎的笑极谦逊。
“你这可以住吗?”简板(笔名)假装严肃地问。
“当然可以!”图嘎指着自己的蒙古包,用生硬的汉话说:“有木床,也有火炕,随便住。”
蒙古包一侧竖起的白铁皮烟囱冒着乳白色的烟,我闻到一股烧劈柴的味道。
“要不就在这儿住吧?”我动心了,征询同行者的意见。
蒙古包的对面,正北或者东北,白桦树零散地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它们的身后就是茂密的森林,是大兴安岭余脉的一哨游兵。脱离大队人马的白桦树像逃兵一样兴奋,树干洁白,叶子铁绿,膝下有各种颜色的野花簇拥,很风光。一丛一丛的白桦树——的确是丛而非棵。这里的白桦树极少单棵,少则两三棵,多则四五棵相携,树干上有类似人的黑眼睛,或许是逃跑需要时刻观察。
羊群、牛群和马群在草原深处缓缓移动,场面像保罗·塞尚的笔触,阵线分明,离多远都能一眼辨识。它们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不屑与人类为伍,躲得越远越心安。
近处有几匹马驻足,眼睛水泊一样明亮,怯怯看着生人。白桦树上挂着木牌,写明“100块钱一次,绕草场边跑一圈”。马蹄在草地上踩出一圈醒目的白印,像绿地的烫痕。沦陷商业的蒙古马很无辜,心里惦念着自由自在的牧场。马头顶及脖颈的鬃毛没有修剪,一绺遮在眼睛上,肌腱饱满,有漂亮的马鞍加身。马旁边站着一位穿着鲜艳蒙古袍的男人,手搭凉棚朝我们这边看。
在草原上骑马驰骋是多少人的梦想,因为兜风时很容易把自己当成英雄。
“他是汉人。”图嘎指着穿蒙古袍的男人说。
我们很意外,也有点尴尬。
阳光下,厚重的森林,连绵的草原。野花仰着脖,花朵展开各种色彩。傲慢的白桦树,版画一样的牲畜群,冒着炊烟的蒙古包,还有用绳索固定在草地上的马……均是自然界里的珍品,与草原十分契合。除了我们,还有一群来自辽西朝阳的外地人。可我们也是追求美的人呀!否则也不会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想到此,心里稍安。
图嘎腼腆,缺少商人应和游客的机敏。他诚实地回答我们的提问,譬如手把肉八十块钱一斤,我们嫌贵。外表的清高代表不了内里的小家子气,图嘎脸红了,像自己做错了事情。他说:“羊是自己家养的,肉是今天新宰的,价格是景区统一定的。”
我们没人不相信他的话。来到草原,就到了说实话的天堂。我们是自己不相信自己,就像看到草原的美后偷着掐自己大腿加以验证,不相信眼前的这些是真的。
遇到好的东西如美景美物,人的第一感觉是怕失去,然后才是欣赏。
临走时我故意逗图嘎,问他:“手把肉多少钱一斤?”
图嘎极不好意思地说:“八十块钱一斤。”酱紫色脸庞上布满真诚。
二
景区内我没看到大片的蒙古包居住区,公路两侧蒙古包星星点点,都是为游人准备的。
图嘎说他家在巴彦查干苏木境内,住的是大瓦房。政府出钱帮牧民盖房子,把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图嘎的眼睛里闪着光。他说牧民几乎不骑马出行了,放牧时骑摩托车或坐越野车,骑马的大多数是到景区拉客人的商人。
他说的没错,高速封路,我们在克什克腾的乡间穿行,全是柏油路。
来阿斯哈图石林,车载导航把我们引进一条正在铺建的公路上,路基还没完全修好,路面有凸起的石头块,蹭得车底盘咔咔响,片羽(车主)心疼得啊啊直喊。唯梦(笔名)说她快颠散架了,到了一片开满野花的草甸上,才惊喜地把自己重新“组装”回来。
建桥铺路是民间大义。这条路要是修通,不仅游人去景区便利,公路两旁嘎查(村子)里的牧民更方便。生活质量的好与坏,路是关键指标。像达达线、热阿线,都很有名气。
我们所经的苏木和嘎查与吾地无异,平房和大瓦房交错,门前停着小汽车,院里竖着电视信号接收“大锅”,堆着啤酒箱子。富裕了的牧民想更富,纷纷来景区做生意。但他们心实,不适合做生意人。牧区的人,会把来访的客人当成贵宾,倾其所有招待客人。这是长生天的授意,他们一直遵循,并把自己骨子里的性情带进生意里。刚开始极不熟练,时间一长才顺过劲儿来。
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阿拉坦高勒草原境内游览。
这里是广阔的自然牧场,各种畜群在草原上自由游荡,看不到放牧的人身在何处。草甸子里有一条河蜿蜒潜出,也许是乌拉盖河,或者是阿尔苏巴拉河。河流是草原里的明星。河水矜持、羞涩、婉约……这样的词用在河水身上一点都不浪费。
天下有河流的地方才是好地方,草原也不例外。草原上的河流是长生天的恩赐,岸边吃草的牛群很幸福,也很安逸。
我们绕过一人高的水草,接近牛群,半道上片羽与一头突兀现身的花牛对视。花牛雪白的底衬上散布黄色的斑点,花而不艳,比例恰到好处。看得出长生天在设计物种时的精心。长生天设计动物时要比设计人用心,他让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极富诗情。色彩、皮毛、爪牙更不用细说。
花牛的眼睛清澈妩媚,片羽试图用语言和它交流,不妥。况且片羽说的是汉语。牛眼炯炯然。片羽的眼睛也不算小,但没法和牛眼比。少顷牛扭头离开,可能觉得不好玩。牛对人的观望不理不睬,它们眼里只有草。
我们抓紧时间拍照,人与牛合影,尽显谦逊。说实话自然界里人是最不谦逊的物种。
女士们快速地换装,外套、帽子、纱巾、伞。片羽带了五把伞,神奇地塞进装满物资的后备箱里。爱美也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牛还是老样子,慢悠悠地吃草,偶尔抬头看人一眼。人换什么样的衣服都不能让其动心。
夕阳跳上草尖,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这群忘我吃草的牛。
在景区(实际是牧场)我们路遇过好几波畜群,它们比游人惬意。我们想近身却不敢,猜忌它们野性和暴力。这样的猜忌好啊!让游人少些张狂和擅动。在车上看多文明。公路边上的马缓缓转过头,鬃发遮挡的眼睛温和明亮,没有一丝暴力倾向。不用化妆,马之俊无法言说。
三
临近黄昏,草原上的草木骤然金黄,像是把压箱子底的金袍子穿在身上。一尺多高的草尖上滚过黄色的浪头,茶碗大小的花朵和酒盅大小的花朵混在一起在风中晃来晃去,像是饮酒的牧民推杯。
小河变成金身,波光潋滟。我猜想水下的鱼是不是都变成了金鱼?河边斜插一个小木牌,劈开的红松,后背有褪色的鳞甲。牌上是生硬的汉字:禁止钓鱼。
真有鱼呀?我看着河水湍湍急流,想知道河水要把鱼送到哪里去。夕阳中木牌和字也变成了金色,让严厉的告诫像是一场时装秀。
夕阳下的草原太美了!我在心中感叹,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大伙都在看呢,你急着发表意见是什么意思?再说牧区的黄昏之美如此惊心动魄,说出来难免轻佻。
畜群全披上了金氅。它们在夕阳中默默地前行,像沉思的哲学家,要去赶赴一场盛宴。远处的桦树林隐现。云杉撑开身子,伸出手掌接纳阳光。色彩的分界线变得模糊。夕阳的纵容下,色彩在草原上肆意地流荡,搞得香气四溢、琳琅满目,醉意现矣。
成吉思汗曾告诫子民:“我的子孙不可居住在城市里面。”在草原的大美面前,这句话更显深意。
一个依赖大自然生存的民族,城市倒像是一个累赘。
我们在遥鲁海日罕山(汉译,半拉山)脚扎下营盘,是一个小的度假村,前后只有六座蒙古包,我们租下一个。
主人保利(音译)五十多岁,用细长的眼睛看着我们笑,他的眼睛里含着这个年龄少有的清澈,绛红的脸庞因为我们的到来变得更红。他的汉语说得生硬、不连贯,表达时加上了手势。
我问:“这里的手把肉多少钱一斤?”
保利推出右掌。我刚兴奋,他用支气管粘连的烟嗓说:“八十块钱一斤嘛!”
这里与图嘎的驻地相隔百公里,价格却一致。蒙古人骨子里的认真劲儿让人钦佩。
保利的家也不在这里,他说了一个很长的名字,我没记住。
每年七八月间,保利举家来到游牧部落经营度假村,秋天再回家收庄稼。他家还有一百多只羊,在离此不远的牧场。农牧商结合,给保利带来不菲的收入。
我说:“你家达到小康水平了!”对他挑起大拇指。
保利说:“依呵,是‘大康’!”他挑起僵硬的大拇指,对我眨了眨眼睛。
“大康”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保利比图嘎活跃多了。谈起经济,这位蒙古族老汉和汉地善谈的人没啥两样,脸上红晕久久不褪。
夜幕未合之际,保利的侄子用扩音器播放蒙古长调。这个度假村用一台发电机发电,突突突的轰鸣,恰巧成了蒙古长调的背景音乐。
蒙古长调低缓绵延,辽阔悠远。长调只属于蒙古族,只属于草原。一个强大的民族,特点之一是内涵深厚。蒙古意味着征服,意味着强悍,意味着豪放,意味着坚韧。而长调真实反映出这个强大民族的无限柔情——父母、马、羊群和草场,天空和河流……长调里最不能缺少的还有爱情。蒙古长调在调门的婉转悠长中,让我体会出蒙古语言的柔美和一个民族的悲喜。
我想,假如把蒙古长调翻译成汉语,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假如,还是假如,一个人站在城市的马路上扯着嗓子唱汉语版的长调,会被人当成傻子。原汁原味的蒙古长调只适合生长在辽阔的草原上。
四
夜幕降临,满天的星星像羊群一样无处不在。和辽西比,这里的星星大而明亮,像离人不远,走几步就能摘到。星斗灿然,迎面盯着你,让你手足无措。在草原的夜色里,一切都让游人猝不及防。如有一种声音,不绝如缕在耳畔环绕。当然不是耳鸣,也不是简板的呼噜声。我就当成是星星给我们发电报,嘀嘀嘀——摩尔斯密码,告诉我们天上的一些事情。
此刻,我们沉浸在酒香和歌声中。玩嘛,不尽兴也对不起草原的盛情。
简板和片羽商量着去给保利一家人敬歌,片羽选唱了《我和草原有个约会》,记不全歌词,用手机代劳。虽然很现代化,在礼节上稍有欠缺。但保利一家很感激,两口子跑到我们蒙古包里回敬。蒙语歌我们听不懂,只能从表情和身姿上感悟出一个民族深远的敬意。歌声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信使,激昂往来。
酒至微醺,虹姐伴着《鸿雁》的歌声,为我们跳起了舞,这是我在草原上看到的唯一的舞蹈。
雨敲打着蒙古包,告诉我们它的到来。不对呀?刚才还是满天的星斗。草原为我们变了一个魔术,演示她的神奇。蒙古包漏雨了,雨竟然用这种谋略和我们见面。雨滴落在酒碗里,泛起涟漪晶亮的脊。我固执地啃着一块羊骨头,有雨汽加盟更入味。这是一种草原的滋味,或许不仅是一种滋味,而是保存在岁月中的记忆和情怀。
半夜,保利家来了一伙蒙古族朋友,小度假村里顿时被酒香和歌声挤满。蒙古民歌像录音机一样,一首接一首地连唱,歌声顿挫有力,像心中有太多的快乐需要表达。草原的夜很静,因为有了酒香和歌声。这样的时光很安逸。我体味出蒙古族朋友内心的甜,像图嘎和保利。
保利说“大康”时,挑起的大拇指很豪迈,就像草原深夜里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