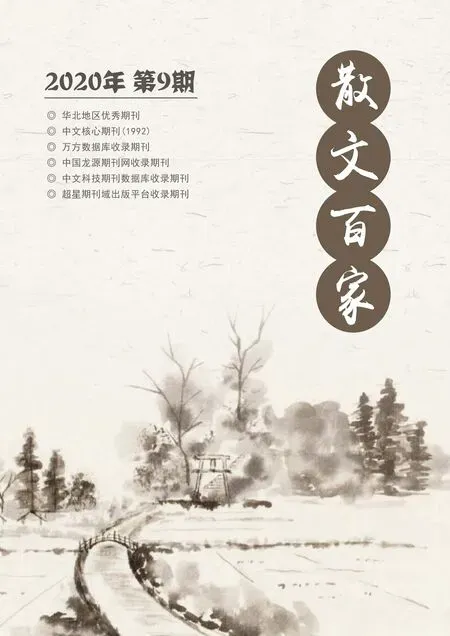信仰之后,重归生活
——评《受戒》
李青璇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个世纪80年代,文坛不断涌现新的思潮流派,作家风格各异,经过十余年的讨论与发展,作家风格逐渐固定并各自归类,汪曾祺却是其中的“异类”。他师从沈从文,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却崛起于后文革时代,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再到寻根文学的思潮中,形成了为其独有的一种文学风格,因此有人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也是他诗意风格的集中体现。在小说《受戒》中,汪曾祺用散而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闲适恬静的风俗民情图。成长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经历过抗日时期的战火连天,也曾在寺庙中躲避战火,感受到了来自佛家人的关怀。在这样一个佛学文化深厚的地方,寺庙于其,并不是一个高处云端的敬顺仰止之地,更多是以一个日常活动场所的身份存在,是他获取审美意识和人文积淀的场域。因此在《受戒》、《大淖记事》及其他作品中,汪曾祺将江南的灵气和水乡人民自有的淳朴淬于笔端,写成了一首对自然人性的赞歌。
《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庵赵庄的小村子里。13岁的小明子家里人多地少,而他的舅舅是当地荸荠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明海的父母便和舅舅商议,决定让小明子去当和尚。庵赵庄里的和尚,过着与俗家人相差无几的生活,一样的喝酒吃肉唱小调,得到了法名“明海”。明海第一次去荸荠庵的路上遇到了小英子,小英子是家里的小女儿,性格活泼。因为家住在荸荠庵附近,小和尚明海常与小英子一起玩耍。四年以后,小英子划船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接明海回来的路上,在芦花荡里,两人天真地表明心意。
故事在芦花荡里戛然而止,结尾处的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视角逐渐放远放大,庵赵庄在视野中只剩下小小的一个点,自然景色的优美给村庄的人情往来笼上了悠闲的颜色,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的,作品充满了水的感觉。
庵赵庄中的人情往来,仿佛是汪曾祺在书中为自己构建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桃花源”。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和尚唱小调是平常事,大姑娘、小媳妇跟着和尚跑了,也是平常事,汪曾祺用稀松平常的语气讲述这些不那么“符合道德常理”的平常事,对于事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如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对他们作道德评判。在这平淡的叙事风格中,汪曾祺表明了他对待后文革时代的态度,如何处理超俗与世俗的关系,在神权政治光芒消退后又如何自处。
受戒本是佛教徒出家时的仪式,要求出家人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戒。但这传统的戒律并未对荸荠庵的和尚们起到限制作用,二师父仁海可以接妻子在荸荠庵里消夏,三师父仁渡也因其会飞铙技艺而有多个相好,甚至是庙里的老方丈也藏着一个19岁的情人。汪曾祺在描写荸荠庵的和尚时,能够感觉到他对于这些和尚身上所表现出的至真人性持着赞赏的态度。无论是在从前还是当下,和尚都是被传统戒律规约着的群体,也是自然人性被限制最多的群体,但在庵赵庄中,和尚只是一种职业,能够像普通人一样释放自己的天性。“禁止”规约的淡化,给了和尚们享受“俗人”生活的自由,允许他们在追求宗教信仰皈依的同时拥有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愉悦。也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来自各方既得利益者强加的道德束缚,没有以正义之名进行的掠夺,才有了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清新感情的萌发。
汪曾祺在《受戒》一文中,回应了后文革时代超俗与世俗的关系问题。经历了文革的社会,是反面的庵赵庄,人情来往中充满了猜疑,规约来自四面八方,并且是带有行政强制力的规约,人们只能从处罚中判断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经过十年文革,神权政治的光芒消退,惯于听从命令、接受束缚的人民在突然到来的自由面前陷入迷茫,失语多年的人开口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久处黑暗的人也会害怕光明的出现。在新的时期,又应该用什么来规约文艺、规约思想?我们真的可以自由发言了吗?荸荠庵的和尚们能够“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让戒律枷锁停留在思想层面。但80年代的人们打破了十年的思想桎梏之后,又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思想规范呢?汪曾祺给出了答案——用自然人性中的宽容接纳不同。汪曾祺在《受戒》中花费最多笔墨塑造的“庵赵庄”,不仅是物理层面上的世外桃源,也是回应当时人们精神迷失的一个思想桃源。在这个小村庄中,信仰不是远在庙堂之上的神像,而是从自然人性深处焕发的光芒,是与世俗生活共存于自然天地之间的美好向往。同样是以自己的故乡为原型向读者讲述纯朴人性的故事,《受戒》与《边城》的故事走向却是截然不同的,茶峒的纯朴中隐隐蕴含着作者挥之不去的悲哀,翠翠前路的未知也暗示着自然乡村在工业时代将走上绝路。但汪曾祺的庵赵庄中,却没有这样撕裂的绝望,他有意屏蔽工业文明的影响,对现代文明秩序保持疏离态度,向读者强调自然自我真实才是生命的主宰,强调认识生活、感知生活应该源于肉身化的直接联系,如小英子那样,用膝盖测量善因寺门槛的高矮,用自己家的二亩地丈量善因寺的天井。个中人物的直接经验都是乡土世界中诗意化的生命景象,也是汪曾祺对世俗与超俗一问的回答。
江南的庵赵庄,是汪曾祺对被时代扭曲的一个“梦”的回忆和召唤,以“受戒”为题,回答的是“谁戒谁”的时代问题。庵赵庄、荸荠庵和善因寺的兼容、接纳之态,是后文革时期人们最应该拾回的态度。所谓普通人的信仰,并不是远离尘世去追求内心的纯净,而是在尘世之中,顺从人性的自然生长,回应人性的自然要求,在自然天地之间成长于超俗与世俗的融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