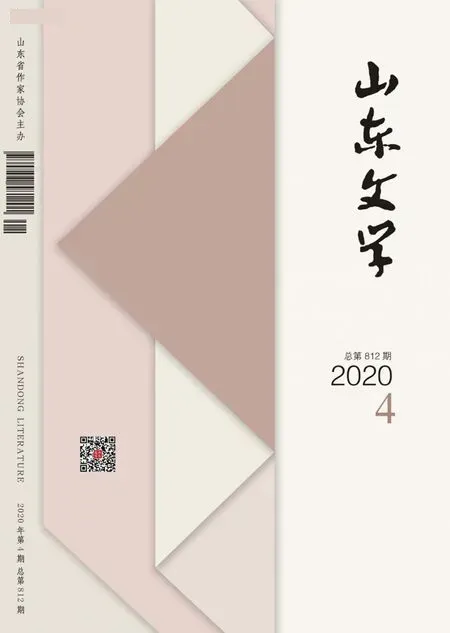衢江记
柴 薪
1
衢江从我居住的城市的西边流过,到二中附近折向北边流了一段距离再蜿蜒向东流去。我住在城市的北边,衢江就像一条胳膊把这个城市揽在她的怀中。因此,每天我都是在衢江温暖的怀抱中睡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到衢江边散步。尤其是在黄昏时分,我向西行走,衢江离我住的小区大约二里路左右。如果走得快些,到达衢江边,就会看见夕阳正好落在江面上,江面一片通红。如果走得慢些,夕阳已西沉了,江面上只剩下一片茫茫的暮色,仿佛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似的。这时,我就随意站在衢江边的堤岸上吹风,或者站在岸边的某一棵树下,听一听蝉声,然后,在黑夜来临之前,离开。
江山江和常山江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汇合后称为衢江。衢江古时称为瀔水。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喜欢旧时的称谓。瀔水悠悠流经龙游汇合了灵山江,流经兰溪叫兰江,一段有一段的名字,再流下去分别叫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蜿蜒流入东海,云蒸霞蔚,浩渺不知所终。
天下的江水都是相同的,但天下的江河却各有不同,水的命运也因此而千变万化了。
我居住的衢州,古称太末、信安、西安。衢江,古称瀔水。都是极其古雅的词。风雅千古,源远流长。草木葳蕤,鸟鸣花香,蝉声如织。在黄昏,我自西安门大桥东端沿着防洪堤坝向北缓缓而行。迎面走来一对年轻的恋人,男的五官英俊,帅气逼人,女的长发,眉清目秀,穿一袭白色的短裙,双腿修长,楚楚动人。这是属于他们的爱情,这一瞬我与他们相向而过,而我也早已过了这一截青青岁月。我离爱情越来越远了,不是爱情远离了我,而是我远离了爱情。这是因为,我的心已失去了最初的纯洁。
衢江堤坝边的草皮上,几场大雨之后,草木已经覆盖了路面。仿佛它们是从四面八方一下子赶来的,似乎它们一下子就走完了这世上所有的路。堤坝边的樟树、榆树、桂花树、杨柳树、梧桐树、水杉、香椿树、桃树、李树、梅树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葱郁茂密,欣欣向荣。花坛里的花木也争奇斗艳。信安阁前的小广场四周,种着银杏树,银杏的叶片很美。信安阁是新建的,气势雄伟,华美张扬,可惜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其实现在,就像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阅江楼等名楼也都是钢筋水泥构成的,有的还装了电梯。可是,我总觉得和以前的木质结构的楼比起来,似乎好像缺少点什么。走在木质的楼梯上和走在水泥的楼梯上感觉是不一样的;上楼的脚感和脚步声是不一样的;气味和气息是不一样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在木质的楼上抚一曲古筝唱一曲《春江花月夜》和在钢筋水泥结构的楼上唱卡拉OK是不一样的;余音绕梁和立体声环绕是不一样的;在木质的楼上远眺江景,喝着黄酒,吃着卤牛肉,啜着清茶,就着白色的墙壁挥毫题诗和在钢筋水泥构成的楼上喝着咖啡,用刀叉吃着牛排、通心粉,就着笔记本电脑写诗是不一样的;站在木质结构的楼上的我和站在钢筋水泥结构的楼上的我是不是同一个我。
沿着堤坝继续往北走,堤坝的右侧,有一片乱竹丛,细小零碎的竹叶,青翠茂密。竹丛中有一株柿子树,柿果累累,太沉重的苦涩与甜蜜。有一枝树丫被最近的一场大风刮断了,枝叶倒垂下来,已经枯死了。有一天早上,我曾在这附近的树上听到喜鹊叫,可是,今天没有,也许是太晚,喜鹊已经飞走了。树上到处都是蝉声,密集、尖锐,而又有莫名的空洞和喧闹。我在堤坝上行走,整个人仿佛被这无边的蝉声浮起,越浮越高,越浮越高,直到自己看不见自己为止。
西安门大桥一侧的江滨路旁,长着一排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大樟树。一株,二株,三株,十株,二十株,三十株,好像远远不止,我没有细数过,但这么多的樟树长在一起,的确蔚为壮观。黄褐色粗大的树身,高高的树冠,树冠上长着那么多的叶子。没有风的时候,仿佛每片叶子都一动不动。站在树下,你会感到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安静踏实的存在。树木的高度,时间的流逝,让你感到自身的生命在这种自然层面上的脆弱。
不远处靠近文昌阁的树林里,有一只乌鸦时断时续地喊叫。夏天的某天黄昏,我曾在那里听过它的喊叫声,不知这是不是夏天的那一只。但现在听来,不知为什么,我感到这喊叫声有点苍凉。这喊声唤醒我作为一个梭罗式的纯粹的自然主义者的某一面?我觉得,我似乎是从《诗经》中转世的某一个在水边的伐木者或者是在水边的捕鱼者,劳作之余,无名的歌者。在劳作之余,无奈地看着一个个擦肩而过的秋天。
秋天的大地是安静的。午后的阳光在衢江上闪烁,水光潋艳,如梦似幻。衢江那边的公园里树木密密麻麻,落叶在风中飘动,它们在空中停留的过程非常漂亮动人。
秋深了,虫声稀疏了,鸟鸣声也稀疏了,风声却清晰了,厚了。世界似乎开始变大,大得有点空寂,大得漫无边际。风声仿佛从衢江对面由远而近地吹过来,吹过防洪堤吹过大樟树吹过我的头发和脸然后从身边慢慢消失,不知吹向何方。风中又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迟疑地张望,然后慢慢到来,但最终却又停止了。这种感觉是什么?说不出来,只是眼神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有一个收破烂的中年人骑着三轮车从对面过来,车斗里有一扎破纸板,几个塑料瓶和易拉罐。他从我身边经过时,黄昏突然寂静了一下,似乎一条小船从衢江水面上划过,江面留下一片涟漪。
2
衢江流到沙湾的时侯,江面变宽变阔,江水也变慢变缓,江面如镜,波浪不惊,著名的浮石潭就在这里。原来横在江中的浮石若隐若现并在水位下降时浮出水面。如今,下游不远处筑了水坝,水位上涨,浮石沉在水下不见了天日,只剩下明太祖朱元璋与浮石的传说和这一片水域的广阔与苍茫。
沙湾的东面,过衢江那边有个叫徐家坞的村子,秋天的时候,我养的一条“银狐犬”,过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死了。伤感之余,我把它埋在这个村子后面的橘园里。我记得,我刚走到橘园时,一只大鸟从一条两边长满茂盛灌木丛和杂草的小水沟里突然飞起,然后迅速隐入附近的青枝绿叶之中。我没看清这是只什么鸟?我只看到它翅膀的羽毛是红黑色的,背部有一大片褐黄色。我想,一定是我惊到了它,不然它不会飞走的,不知道它会不会飞回来?
埋完“银狐犬”后,我绕过这个小水沟,准备穿过那片茂密的橘林回去。秋蝉在正午时分静悄悄的,它们只有在夕阳西下时才喧嚣起来。
那一瞬,我忽然发现整个橘树林静悄悄的,似乎整个徐家坞也是静悄悄的。
那一瞬,我忽然发现,夏天,寂静似乎被深深包裹在声响之中;秋天,声响则似乎被深深包裹在寂静之中了。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我曾来过这里。有许多不知名的昆虫在草木花丛中飞舞,很轻,很小。有蜜蜂、飞蛾、蜻蜓、蝉、还有蝴蝶,蝴蝶品种繁多,各色各样,五颜六色,色彩斑斓,大大小小的蝴蝶在草木花丛上飞舞。其实蝴蝶也是一种昆虫,它们有着小小的身子和大大的梦幻一般美丽的翅膀。不像蜜蜂飞动时嗡嗡作响,蝴蝶飞动时无声无息,翩翩飞舞,姿态惊艳,曼妙,像探戈,像华尔兹。蝴蝶骨子里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抒情诗人,像席勒,像雪莱,像普希金,像莱蒙托夫,像松尾芭蕉,像德富芦花,像朱湘,像废名,像徐志摩,唯美、柔软、脆弱、易逝、伤感。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秋渐渐开始渗透,渗透周围的一切,天空辽阔,大地遥远,只剩下草木开始枯萎,虫声消遁,飞鸟远走。
一切唯美的东西似乎都很脆弱。
唯美的东西似乎柔情似水似乎生来令人伤感。
去年秋天末尾的时候路过沙湾,在衢江边顺手折了一支芦苇,回到家里顺手插到铜瓶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也很快过去了。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铜瓶里的芦苇干枯了,失去了水分,变得金黄,变得愈加好看了。
一支枯萎的芦苇,它似乎没有生命了,可它仍在尘世,枝干锃亮,芦花苍苍,毛绒绒的,似乎比原来淡了一些,隐隐地似乎有那种来自天堂的温柔和洁净的光泽。
这支枯萎的芦苇,它通身的色泽,枯黄的色泽,深和淡的色泽,近乎于黄土,却比黄土素净。是那种久违了的遗忘了的朴素,是那种接近虚无的色泽,是那种生生的实在,是那种姿态的低,却不卑微。
这枯黄的色泽,淡而宁静,相对于《诗经》,相对于蒹葭苍苍,相对于有位佳人在傍,相对于水的淼淼泽润,风的抚慰,水鸟的嬉戏,蓝天白云的俯瞰;是微微忘却了干渴,忘却了悲欢,忘却了红尘,忘却了江湖,忘却了悲怆的世态和沧桑炎凉的人世。
铜瓶里的这一支枯萎的芦苇,干,轻,缥缈,仿佛空气中也充满了“干枯”的味道;渺渺的,仿佛是虚空的“木质”一样的空气,和曾经经历的,被微微隔绝了。这一支枯萎的芦苇,柔和、柔软而又坚硬,又微微有些遗世独立。
寒露来临时,草木萧瑟,日影南斜,白昼一日短似一日。
寒露这天,朋友相约去“信安阁”喝茶。喝茶是一件难得的雅事,也是得一时之闲暇。
茶为南方嘉木,古人称茶为茗,故喝茶,又谓品茗。茶生于天地之间,濯山野之泉,沐天地之露泽,虽寒而不凋,其色常绿常新,郁然如丁香瓜芦之树。陆羽《茶经》中说,“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
有一则轶事:北宋时,有一次,苏东坡从故乡四川眉山至重庆经长江回京,船至西陵峡时才忽然记起宰相王安石曾有一事相托:“回程时取巫峡江水一罐以供煮茶。”于是,苏东坡硬着头皮连忙取了一罐西陵峡之江水权当巫峡之水。心里想,同样是长江水王安石如何喝得出?回京时,苏东坡有些忐忑,亲自将水送到王安石府上。王安石大喜过望,遂邀苏东坡留下一起喝茶,水煮开后,泡上茶。王安石呷了一口,回味片刻,笑着对苏东坡说,此非巫峡之水,乃西陵峡之水也。苏东坡大惊失色,佩服至极,作揖赔罪,连忙说了原委。喝茶喝到王安石这份上,不只是高人而是天人了。
由此可见,喝茶需先煮水,好茶还需配好水。而用水之精者,喜山间之泉,杭州人泡龙井茶,常去取虎跑之泉。其次是江河溪流之水,再次是井窟之水,而现代人用所谓的桶装纯净水泡茶,实因无水可煮,也只能以此代之了。
喝茶,我本是不太讲究之人,好比抽烟,也无南北之分,好坏贵贱,曾与朋友戏言,能点着的即可。朋友用的是云南的普洱红茶,虽煮时工道繁复,但喝时味纯可口。
秋末之际,容易感伤,喝茶却能宽心,坐在信安阁内,静听秋风过耳,远观树木摇曳,更远处高层楼宇,车马流水,红尘滚滚,喧喧嚣嚣,秋天已经被逼仄到了一些不易为人注目的角落。信安阁西面,可观日之西薄,晚霞翩翩,横亘在远天,仿佛无数美炒玄烂之花。天空下远远的可以望见衢江,灰白一线,流向由南向北又转东,曲折逶迤,茫茫不知所终。
时近日暮,天空苍黄,天色为薄霾所翳,更见苍茫,内心似乎也徒增一片苍茫。
而眼前壶内的水声呯然跃起,似煮水知人生,又如饮茶,初极浓郁,终淡如水,此始于水而又终于水,饮茶即品人生也。
古人有喜收集雨雪寒露之水为煮茶之用的。《红楼梦》中的妙玉,喜欢用雪水煮茶,而且是梅枝上的雪。苏东坡被贬海南,叫人收集芭蕉叶上的露水煮茶,此等皆妙人文人雅事尔。而乡下乡野农夫用野茶叶,粗瓦罐泡茶,照样喝得痛快淋漓。唐朝的郁离子,喜欢用从天而降的露水煮茶。寒露过后,露气将结。每天清晨,路边草木上无数的露珠晶莹透彻,看的人满心欢喜!只是露水易逝,古人歌薤露以寄哀,人生如薤上之露,短暂易逝。
我想,仅为煮茶而收露水,实为暴殄天物。露水宜观,遍地晶莹之境,不说收之不易,收了于心何甘,实实在在糟蹋了眼前的这一番美景。
3
我刚到衢州这个城市的时候,是在春天,大约在三十年前。如果说,现在这个城市五颜六色,五光十色,是彩色的,那么,那个三十年前这个城市似乎是灰色的。那时的东门街,一切似乎是灰色的陈旧的,街道、商铺、房子、门窗、树木、电线杆、路灯,甚至连飞过东门街上空的麻雀,也是灰色的。
东门街的尽头,有一截老城墙,晚饭后,我常一个人去走走,有时也会爬上城墙看看。灰色的老城墙历经沧桑,破败不堪,城墙上草木萋萋杂草丛生野花朵朵,在风中晃动摇曳。沿破旧的城墙根长有一排樟树、榆树、梧桐、香椿、苦楝,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乌鸦或喜鹊在它们上面筑巢、跳跃或尖叫。城墙下,路边的草木我大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就像它们也叫不出我的名字,就像那一块块陈旧的城墙砖一样,我们都一样默默无闻,有一瞬,我差点泪流满面。
一切似乎都是默默无声的。
其实东门街还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声响的,但更多时候,带给我的是一种静静的感觉。并在不同的季节里,又有着极其细致的区别。
春天的东门街是宁静的,冰雪融化的声音,草木发芽的声音,轻寒和温煦产生着轻轻的碰撞和磨擦声。风声圆润,草木和大地有一种复苏时的慵懒、迟钝和清醒。清晨,太阳刚刚从古城墙上升起,雾岚从潮湿的地方、从低处升起,然后萦绕在枝节变软的树梢上。
鸟鸣清澈,满心欢悦。就是在夜晚,大地也有一种可感受的明亮,空气中弥漫着序幕拉开时的激动和不安,一切仿佛有一种没有终止的无限。
客居东门街的日子,像一卷老旧的黑白电影胶片,一格一格的胶片把我与东门街定影并紧紧相连。我认识了房东读外贸的女儿许婕,她志存高远,像东门街蓬发的草木,后来去了俄罗斯。开水产批发、戴一副黑框眼镜的绳建华,跑长途车给钢窗厂拉货的胖子司机李大木,后来和人打架,把人打残了,他自己也不知去了何处。民工诸暨人小魏,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腰椎,还有楼下小卖部我经常去买香烟时认识的瘦老头老尚。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吹牛,聊天,打牌,下棋,喝酒,抽烟,那是一阵风一样的日子,一切似乎是灰色的,但并不影响我对未来色彩斑阑的日子的向往,在寂静的无眠的夜晚我会写下一些文字。
三年后的春天,我离开了东门街,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在春天的时候搬到东门街,又在春天的时候搬离东门街,与我一起搬走的还有那些灰色的日子与这些恍惚的记忆。
春天来了,风细了,瘦了,圆了,长了。丝丝地吹着,若有若无,仿佛来自灵魂的缝隙。在清晨,沉默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花斑鸠突然叫了几声,是一只,或是两只,在这条路边的杂树林子里。从此,在以后的许多个早晨它都会不停地叫下去。阳光也出来了,阳光变暖时,便成了一种抚摸。在路边,我发现那株野海棠的枝条上爆出了芽粒,星星点点的,腥红。很红很红的颜色似乎有尖锐感,像针尖。好些年了,它一直没有开花。不知道今年它会不会开。我看了一会儿,感到很愉悦。感到春天正一针一线把我织进她的图案中去。还有一株野石榴树,枝条也变得柔韧了,树皮有些被风吹破了,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张力。去年,这株石榴树结了七颗野石榴,小小的,圆圆的,润润的红皮石榴,像北斗七星。毫无疑问,今年,它会结的更多。天空会在它纷披的枝桠间落下一个更加璀璨的星群。沉寂中又传来一阵花斑鸠的叫声,我没有到江对岸去,我在江这边停了下来。
从沙湾到徐家坞之间这条路,我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了。同一条路,我走得越多,越说明了我生活的单调。反过来说,为什么我就不能通过对简单有限事物的反复描述,来使自己抵达某种繁复呢。从沙湾到徐家坞之间的这条路,中间隔着一条衢江。衢江上架着一座新建的大桥。去年夏末,下午,阳光明晃晃的,当我经过大桥时,我看到一大堆雪白的云。映着深邃渊静的蓝天,映着波光粼粼的江面,映着地上郁郁葱葱的树梢,那堆白云显出极其强烈的亮度和质感。当然,那片白云早就消失了。云聚云散,缘起缘灭。如今,只剩下那一片空旷的天空。只有我知道,那一片天空,曾有过多么绚丽的景象。只有我,一直对那一片白云念念不忘。因此,每次走过那条路时,也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那片天空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荒凉。徐家坞北有一片橘树林,小小的白色的花骨朵刚刚从枝叶间脱颖而出,脆弱的美从虚无深处再次来到人间。我一直在某种极端的有限性中生活。是的,我要把同一条路,反复走,经常走,直到把它走成一种无限,直到用尽自己的这一生。
4
1992年我来到衢州这个城市,到如今屈指算来已27年了。27年,时间在流逝,江水也在流逝。我站在衢江边,看见树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倒映在江面上,仿佛它们都来自另一个世界。落日西沉,溅红了江面,江风吹来,树的影子,我的影子,随风晃动,之后一切都不见了,青春、岁月、容颜,留给我无限的惆怅。
27年前,那时衢江还没有防洪堤,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河床似乎比现在低,河滩上堆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江水紧贴着河床的底部,江水的骨架以及从前的跌宕起伏和野蛮放纵气势不知到哪里去了。江水像一个衰竭的老人,此刻它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只是努力地把自己拉长,拉得更细更长,像拉扯着拧在一起的一匹绸布,似乎永远也不会断掉。只有当你走近时,一直走到它的跟前才能听到它的动静,那有几分嘶哑的咕咕的响声仿佛是水里间或暴露的石头的棱角发出来的,就像一匹灰色的绸布在河的皱褶处被石头给挂住了,紧接着又被撕开,因为不是太用力,裂开的口子也不大,但老是挂住,又老是被撕开。
正是因为这样,向它走近的人才能走过一段踏实而又柔软的泥土与河沙交叉混合的地带,也才能继续走过时而隆起或时而凹陷的沙滩地段。这片沙滩地段,沙土丰腴而肥厚,成片成片的芦苇恣意疯长。我尤其偏爱雨后一尘不染的芦苇。如果正好有风,且是大风,吹过芦苇丛,风卷残云,苇浪滚滚,恍恍惚惚,将一种凝重的哲学无限张扬和扩展。
无数的野花在沙滩上面肆无忌惮的竞相开放,无数的有野心的水草在沙滩上面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竞走。它们妖绕而艳丽,它们水嫩而光鲜。它们的腿随时都会因为需要而从身体的某个部位里钻出来,它们的身子也在不断拉长,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细,这一点与嵩溪河的水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的队伍很快就庞大起来,沙滩地段也随处可见,只是竞走变成了攀爬,且它们的根茎要细小得多,柔软得多,它们想更快一点(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盲目),它们的足底却变得轻浮,甚至有点打滑,它们想把根须扎牢一点,或者想抓得紧一点,但往往事与愿违。它们经常被扯起来,像一条条细长的蜈蚣,它们的根须上细细密密地沾着黄褐色的沙子,只轻轻一甩,沙子就会细细密密地落下来,那些根须就像是刚从水里洗过一样被捞了上来,白生生的。一同被翻出来的还有滑溜的小石子,它们用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告诉我们水流的方向和时间的久远。当然还有一些鱼的骨头,间或还会有一只鸟的头盖骨,曾经还有人在这里找到过人的牙齿,它们混杂在石子中间,成为另外一些石子,被几只黑衣蚂蚁辨认出来,无论是鱼是鸟还是牙齿,也无论是空气还是水,它们都曾游过、飞过、浸泡过,现在它们安静下来,包括它们的回忆。而成片成片的芦苇,它们是我那个时候见到的唯一具有灵性的植物。若在早晨,它们的叶尖会像刺刀一样挑着晶亮的露水,让每一个经过芦苇丛的人脖子里都会感到一阵阵的沁凉。
在北门沙湾,衢江流到这里拐了个大弯,这里江面宽阔,著名的浮石潭就在这里,因而江流是无声的,舒缓的。它以它表面的平静,掩藏了深处的流动。我也是无声的,我以我的沉默,埋藏了内心的波涛。只有不远处江岸边的一丛丛芦苇,迎风摇曳,我爱这美丽的芦苇。它或许知道一个青涩青年的心事,知晓他心中的秘密,但它没有说。而我面对这一美丽的景致,内心的诗笺早已铺开,写下一阙绚丽的诗篇。看着远去的江流,我知道,水的流向,就是我心的流向。1998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城市的东门搬到北门,无形之中距离衢江又近了些, 到现在不知不觉又过去二十个年头了。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有时想离开这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这么多年来,我守住城北这一小片地方,守住生活中某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有时我也想,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拴住了我,让我无力离开。
一个人在某地停留下来,自然有不必说出的缘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多久才算熬到尽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似乎已厌倦!厌倦地不能了结,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疲惫的惯性。
久居一地,我已失去了早年的热情,在熟悉的环境中,我已找不到过去的足迹、气味、气息、梦境和青春时代的影子,我已被自己和他人遗忘。
我会慢慢地衰老,黑发生成了白发,我会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当作陌生人,把一朵凋谢的鲜花看作旧日的情人。年轻时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不让我再留恋,我已踏上遥遥无期的还乡之路,我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像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我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
慢慢地,我的梦想已不会比一条江走得更远了。我居住在这条江的附近,这样,我就不得不爱上它了。我不得不爱它枯水期的清瘦,不得不爱它丰水期的丰盈,甚至我不得不爱它的泛滥与污染。
我已说过,我已经在城北生活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还要在这儿再呆多少年。而衢江,一提起它,仿佛就像提到生活中一个熟人或朋友的名字,我越来越感到我无力离开它,就像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它和我的生活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
——以“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报道为例
——2017首届世界针灸康养大会在衢州市衢江区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