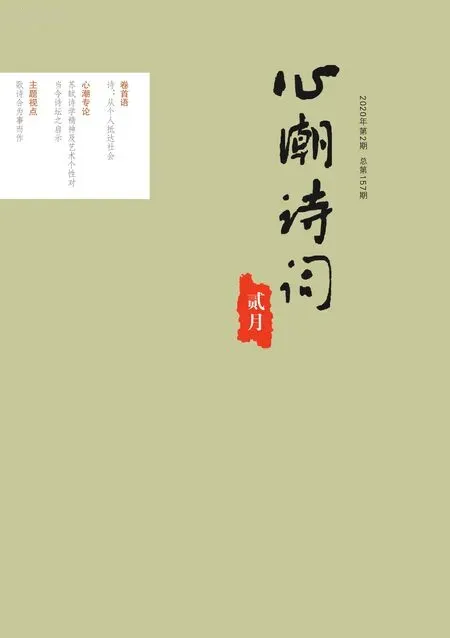俗而能趣,大俗亦可大雅
——《南广勋散曲集》序
赵义山
广勋先生散曲终于结集了,真是可喜可贺!
他来信说,是从自己3000多首曲作中选出的500首,而且希望我能“再帮把把关”,甚至说可以“痛下杀手”!其用意,当然是希望把最好的作品献给读者,这可见他对读者的尊重,当然也是一种十分聪明的自重。我固然很感谢广勋先生的信任,但我却觉得不必再多此一举了。一者,广勋先生自己由3000首而删汰至500首,这就已经割爱太多,我又何忍再“痛下杀手”!二者,作家别集,存多存少,也并不影响读者对其艺术成就的认知与评判,杜甫存1200余首,人不以为多,张若虚“以孤篇压倒全唐”,人不以为少,所以,我又何必再“痛下杀手”!三者,即便我真的从500首中再来挑选一番,那也不过是我个人的偏爱,我怎能以我之偏爱代替作者之爱好与读者之期待?因此,我又何能“痛下杀手”!这应该是能得到广勋先生和读者朋友理解的。
广勋先生邀我为他的曲集作序,一晃好几年了,直到今年暑假,才能来完整地阅读他的作品,也才可以说一点无愧于曲、无愧于广勋先生、也无愧于读者的感受。如果没有完整地读过作品,凭所谓“尝鼎一脔”便动笔来写,我是没这个胆量的,这便是直到今日才能来谈一点感想的缘故,也是这些年来不断谢绝一些朋友索序的主要原因,有负他们的热望,我自己很歉疚,也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谅解。
纵观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学的发展,其基本规律是,当旧体式微之时,便是新体诞生之日,新体既出,旧体不废,新旧互渗,又生新体,如此生生不息。诗经之后楚辞,而后乐府,而后五言,而后七言,而后律诗绝句,而后词,而后曲,莫不循此道而演进。唐人近体以前不论,仅就唐诗、宋词、元曲三体以观,可以说,每一新体,都是对旧体的“反动”。宋词之长短参差不齐,是对唐人近体诗句式整齐划一的反动,而元曲之自然通俗、活泼俏皮,又是对宋词婉丽修洁、文雅蕴藉的反动,但最后都卓然而成为“一代之文学”,这才真正是“造反有理”。不过,新体的“反动”并非与旧体“划清界限”,而是在逆反中有继承,在继承中有创新的。如果像现代一些新诗那样完全与旧体“划清界限”,也难以为大众接受。
曲的自然通俗、活泼俏皮,成为曲之为曲的当行本色,曲也正是借此而特立独行于元代文苑,并凸显于中国诗坛。王国维先生著《宋元戏曲考》,曾赞扬元曲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其着眼点便在曲之自然通俗,如舍此自然通俗、活泼俏皮之当行本色,而与词体之婉丽修洁、文雅蕴藉为近,那是会招来批评的。如元曲中关汉卿、马致远等豪放本色一派,向来被视为曲中正宗,而乔吉、张可久等清丽一流,则被视为别派,便是明证。明曲中梁辰鱼、沈璟等人曲作近于词体婉丽修洁、文雅蕴藉之风,即遭任中敏先生在《散曲概论》中的尖锐批评,谓其“词不成词,曲不成曲”,“臣妾宋词,宋词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耻”。总之,自王国维、吴梅、任中敏、卢前、冯沅君、郑振铎等先生以来,都对曲体自然通俗、活泼俏皮之本色特征给予很高的评价。冯沅君先生在《中国诗史》中写“近代诗史”时,写完唐诗、宋词之后即接写元散曲,在她的诗学观念中,只有散曲和小曲歌谣才是元明清三代坐正席的诗歌,她甚至充满深情地礼赞元代散曲“是轮方薄中天的太阳”。郑振铎先生亦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列专章来讲述“散曲作家们”,尔后又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以重要篇幅论述“元代散曲”,他对元散曲独具个性的审美特质,差不多是与冯沅君一样的大加褒赞。前辈们如此看重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如王国维、任中敏、冯沅君、郑振铎等人的卓识,也不能不令人赞叹!因为这些著名的词曲家、文学史家们的极力肯定和倡导,学界贵诗词而贱曲体的风气得到彻底改变,因而也就有了以陈栩、姚华、吴梅、卢前等为代表的民国散曲的繁荣。
遗憾的是,进入共和之后,因为时代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切传统的诗歌体式皆被自由白话体新诗取代,胆敢大张旗鼓地公开写旧体诗词的几乎只有毛润之先生,以及与他唱和或经其授意的少数几人偶一为之。尤其到“文革”时期,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年轻一代的旧体诗词读本,已经不是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马致远等历代伟大诗人的作品,而是毛主席诗词和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歌。所以,当时的年轻人如有写几首旧体诗词的冲动,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几乎都是以《毛主席诗词》作为范本,而毛本人只作诗词,不写散曲。所以,这就导致了国人对散曲的集体失忆和无知。尤其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现年在70岁左右的文人,在文革中20岁上下,如果那时学习写旧诗,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者外,大都是跟着《毛主席诗词》来学着写诗填词的,对于散曲一体,压根儿就不知为何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社会开始拨乱反正,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也全面复苏,于是,对旧体诗词,人们也敢于大胆写作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从民国进入共和、旧体诗词功底较深厚的遗老遗少们,与一些爱好旧体诗词创作的中青年一起,还组织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华旧体诗词的写作已经蔚为大观。相对于旧体诗词创作快速复苏的步伐,散曲则相对滞后,原因已如前述,即人们的集体失忆和无知。不要说一般弄笔旧体诗词者,就连一些有相当学术修养的教授,也曾在一些场合公开断言:别指望散曲能在现代复兴。但事实却是,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经过中国散曲研究会20多年来的倡导与组织,尤其是首任会长羊春秋先生和现任会长赵义山等人身体力行的创作引导,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华诗词学会全国散曲工委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中国散曲的创作,日渐欣欣向荣,也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并且方兴未艾,其发展前景,未可限量。笔者曾斗胆放言:散曲一体,继承传统,融合现代,书写当下,相对灵活自如,最接地气,故最有可能成为孕育未来新格律体诗歌的摇篮。
广勋先生的散曲创作,就是在上述新世纪散曲复兴的背景中展开的。他在来信中说:“您的《元散曲通论》对我影响至大,自从拜读过您的大作后,我学习散曲才慢慢走上正路。所以,曲稿从2009年选起。”这当然是他的谦虚,但拙著也可能确实对他有过一定帮助。拙著于1993年在巴蜀书社初版,因为印数太少,社会影响有限,直到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这才引起曲学界的广泛注意,但现在市面上又难觅踪影了。广勋先生所言受拙著影响,或许应是2004年之后的事了,这与他所言“曲稿从2009年选起”,也是吻合的。但广勋先生的散曲创作,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想来已经20多年了吧,应该算是曲坛老将了。他本人,既是北京散曲学会会长,又是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和全国散曲工委副主任,他既勤奋创作,又与曲友们一道,积极组织北京及全国的散曲活动,这就不仅是一位曲坛老将,而且更是一员大将了。写曲,已然成为他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内容。陆游当年是“无诗三日即堪忧”,我看广勋先生却是无曲一日即堪忧的。在网络上,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他的新作,他写得既快又好,几乎无事不可入曲,无意不可入曲。
凡读过广勋先生散曲的读者,都熟悉那扑面而来的满纸“俗”与“趣”,他是坚定不移地继承散曲尤其是北曲的本色当行作风,把散曲文学的“俗”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代散曲大家。他曲中的“俗”,并非庸俗、粗俗、鄙俗,而大多是自然通俗,是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所言“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之俗。其于人、于事、于景,皆出于自己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与心之所感,是自己眼熟、耳熟、心熟之平常人、平常事、平常景,故其曲一出,即给人熟悉亲切之感。
出现在广勋先生曲中的人,大多是身份地位卑下的老头、老太、大叔、大妈、大姐、村姑、街妹,不是引车卖浆者,便是挥汗劳作人,更多市井百态相,总之,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俗”人。由这些“俗”人连带而出的所作所为,也自然都是些“俗”事,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游观睡,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人人不可避免、个个必须经历之生活琐事俗事,只要活着,只要生存,就不可避免之平凡事、普通事。而由这些“俗”人经历着“俗”事,其活动的环境,也自然多为“俗”景,故其曲中所涉笔者,风花雪月、桃红柳绿、楼台亭阁、小桥流水等固然有之,但其大半是夏热秋凉、尘街雨巷、残荷落英、小院旧居,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过平常日子举目可见之平常俗景、小景。总之,广勋先生笔下所见者,大多“俗”人、“俗”事、“俗”景而已也。
此等“俗”人、“俗”事、“俗”景,广勋先生偏又以俗语写之,通篇家常语,满纸大白话,但却无一酸语、腐语,无一空话、套话。仿佛农家之南瓜粥、苦丁茶、干白菜,就得用陶碗、瓦盏、竹篓来盛,若换作金碗、玉盏、银盘,反到不伦不类了。随便举几首,看看作者是如何以“俗”语写“俗”人、“俗”事、“俗”景的吧:
豁牙露,老腰勾,脸似核桃皱。枣一兜,蛋一兜,哀言苦把客人留:“短秤折阳寿!”(【南吕·干荷叶】《路旁卖山货老太》)
是她!是她!眉眼新描画。五十一载一抹霞,常在心中挂。岁月犁铧,云水摩崖,温凉一碗茶。“看啥?看啥?没见过白头发?”(【中吕·朝天子】《同学会偶遇伊人》)
老乖乖,小乖乖,满脸菊花次第开。臭美归来疯未够,耳环偏要我来摘。(【正宫·双鸳鸯】《老妻》)
宽衣宽袖,长襟盘扣,穿行茶座人前后。铁勺抠,掸毛搜,掏完耳屎清尘垢。吉祥话儿不断口。钱,拿到手;人,马上走。(【中吕·山坡羊】《成都掏耳郎》)
秋风萧瑟,残红飘落,藕肥子满残荷破。日如梭,月如梭,眼睁眼闭浮云过。料是来年花更多。红,还似火;人,不是我。(【中吕·山坡羊】《秋日叹残荷》)
以上这些口头语、寻常话,有谁不懂?而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景,又谁没见过?但却很少有人会取之入诗的,因为不少人以为诗词是文人小圈子内的雅玩,惟恐沾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于是也有人真的以为“诗在远方”。近读莫砺锋教授《诗歌不在远方》,见他对一些当代诗人以为“诗歌真在远方”,“写诗尽量避开身边芸芸众生,惟恐沾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提出批评,并引金圣叹语:“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我很同意莫教授的批评,也很赞同金圣叹的观点,当然,我也就很肯定广勋先生以俗语写俗人、俗事、俗景的当行本色之曲作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俗,是不能成为艺术的,得俗中有趣。如上引【干荷叶】结句“短称折阳寿”,写老太以赌咒发誓来显示自己的诚实无欺,便极生动有趣,且极富表现力,把山里老太憨厚、急切之态表现得非常传神。【朝天子】写老同学相会,猛然见到“伊人”的喜出望外,谁知岁月催人老,“伊人”竟没有认出老同学:“看啥?看啥?没见过白头发?”结尾三句写出这种意想不到的误会,真是奇妙至极、奇趣至极。【双鸳鸯】结末“耳环便要我来摘”,仅此一句,就让发妻人老心不老,欲学年轻人黏糊糊撒娇的那股“疯”劲儿跃然纸上,可谓妙趣横生。【山坡羊】写成都掏耳郎,先是满口“吉祥话儿”讨人喜欢,其后是“钱,拿到手;人,马上走”,也是意趣盎然。【山坡羊】写秋日残荷,如此衰残之景,常用以抒发迟暮之感,此曲也不例外,但像“料是来年花更多,红,还似火;人,不是我”这样跌宕反转、俏皮风趣的则少见。这些曲子,因为构思巧妙,平起奇收,妙在结句出彩,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诗头曲尾”这一规律。因为有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可以上升为艺术的“趣”,于是,“俗”便转化为一种雅,所谓大俗大雅者,即此之谓也。
相对而言,作者关注国计民生、社会时事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比如对前些年社会上猖獗一时的腐败之风,作者也给予了揭露和批判,表现了自己的正义立场。如以下几首:
庙不大、钱多就行,水不深、鱼傻则灵。人不贪,生何用?位虽卑、怎奈人精。铁帚钢锨样样通,直刮得石头叫疼。(【双调·沉醉东风】《小赃官儿》)
好官家,贪官犯事便开铡。今天拉倒藤萝架,明儿又发芽。一茬又一茬,一挂接一挂,好像连环画。刨不完的红薯,打不净的芝麻。(【双调·殿前欢】《百姓的担心》)
权做钎,钱当铲,不信高墙捅不穿。囚服一甩“回头见”!酒照喝,花照拈,人不闲。(【南吕·四块玉】《“监外执行”》)
如此严肃的社会题材,作者却仍以诙谐之语道出,依旧给人妙趣横生之感!
领略了广勋先生曲作的俗趣诙谐之风,不由人想起元曲中杜仁杰、王和卿、刘庭信、明曲中陈铎、朱载堉、赵南星等人的曲作风格。此种以俗语写俗人、俗事,在曲体文学中把俗趣诙谐之风发挥到极致者,确实由来已久,但入清之后,随着散曲逐渐衰微,曲中俗趣诙谐之风便沦落不振。直到现当代,虽然不时可见此等曲风,但如此广泛地专注于芸芸众生和市井百态而卓然名家者,除去已故之著名散曲家萧自熙先生而外,现今仍活跃于曲坛者,殆广勋先生一人而已乎!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散曲一体只能关注平常人、平常事,也并不等于认为俗趣诙谐之风是散曲唯一值得称道的作风。事实上,那些密切关注世道人心、时代风尚、国家命运及前途,而又能表现出作者真知灼见的曲作,或许更值得我们期待;那些书写愤世嫉俗、嫉恶如仇而表现出的豪放爽辣、幽愤沉郁之风,也同样值得我们赞赏!艺术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从来都是多元的,艺术家们不必面面俱到,也无须刻意去追逐高、大、上,只要能本着正直善良的情怀,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内,写出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就好;读者和批评家们也不必厚此薄彼,能客观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好。
广勋先生虽年届古稀,但其创作精力却依旧十分旺盛,“老树着花无丑枝”,可以肯定,广勋先生笔下特有的诙谐风趣,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是会得到读者广泛喜爱和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