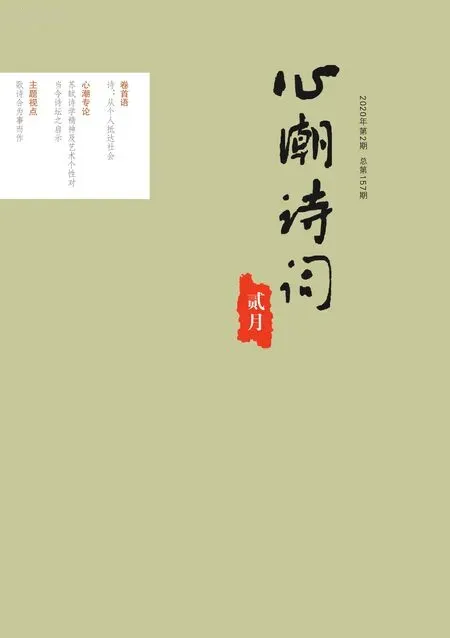歌诗合为事而作
——关于叙事诗创作的几点思考
文志之
叙事诗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动体现。白居易用一只诗笔践行了自己关于“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主张。他在创作《秦中吟》时提到,“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充分说明,诗者叙事是把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作为诗之使命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长于‘讲故事’和还原生活,能从审美、娱乐和认识世界诸方面满足读者需求的小说的兴盛,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所下降。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影电视等新兴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的出现,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式微的危机,有人甚至发出‘诗歌将死’的预言”。①杨守森、周波主编:《文学理论实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当代学者所说的这些现象客观存在,必须引起当代诗坛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叙事诗不但不能缺席,而且还应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显然,彰显时代性创作叙事诗,是传承与发展中华诗词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传统诗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代赋予当今诗坛的神圣使命。笔者结合自身创作叙事诗的初步实践,深感弘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倡导叙事诗创作,需要不断深化对以下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1.现实主义创作呼唤叙事诗。中华诗学史表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决定着历代诗人都具有直面人生、关注民生的叙事传统和审美意识,总是自觉地将自己的诗词曲创作融入宏大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之中,构成中国古代叙事诗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与主旨追求。从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到唐代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千百年来的中华诗学传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伟人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堪称是现代诗坛的“泰山北斗”。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史诗,为当代诗坛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叙事诗树立了光辉典范。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当代诗坛的广大诗人或诗词爱好者,要自觉地树立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主动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充分发挥传统诗词曲的文体优势,吟咏中国故事,努力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尽管有学者认为:“新诗多反映社会生活,旧体诗词则大多同个人经历相关。新诗的生命力似乎是外在的,旧体诗词则是内在的。这种内容上不期而然的分工,大约正是旧体诗词的一个比较特别的长处。”①张永芳:《当代诗词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曾大兴:《唐诗十二讲》,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但是,正是由于旧体诗“内在”的美学特质,用传统诗词曲这种特别文体写成的叙事诗,其不同于新诗的叙事特征,呈现出情感缘事而生而又逸出事外的特点,往往可能更有利于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
尤其是遵循“诗学三命题”(即“诗言志”与“诗缘政”“诗缘情”),“诗言志”决定了叙事诗的美学特质不在于单纯地表现客观现实,而是或者即事抒情、缘事感叹,或者即景会心、咏物寄意;“诗缘政”与“诗缘情”又决定了叙事诗创作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以“大我”为主题,言“大我”之志;一个是以“小我”为主题,言“小我”之情。这样,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就是要将“诗缘政”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充分发挥传统诗词曲的叙事功能,讲好我们身边的故事,为现代社会传递正能量,
2.科学界定与理解叙事诗。何谓叙事诗?按照词典或教科书上的定义,“是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诗歌,它一般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始终具有诗的节奏和韵律等一切外在形式”。②杨守森、周波主编,《文学理论实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21页。胡秀春:《唐代叙事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显然,遵照这种定义来判断叙事诗,必须要有两大要件:一是是否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是否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然而,这种定义并不符合自古以来的中国叙事诗史的实际,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辞海》所定义的‘叙事诗’是当代中国人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之后形成的一种观念,套用它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分类研究,不符合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特点,确立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史实际的界定标准必须借助中国古代的叙事理论。”③胡秀春:《唐代叙事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在中华诗学史上,真正具备这两大要件的诗歌犹如凤毛麟角,大概只有《长恨歌》等极少数作品。有学者甚至基于“真正的叙事诗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最起码的要求”,认为“汉族是一个叙事诗不发达的民族”①张永芳:《当代诗词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曾大兴:《唐诗十二讲》,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叙事往往是一种表现方式,诗者对所要表现的事件不做全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而是适当挑选那些具有强烈情感的情节为集中描绘。“中国古代叙事诗必定具有抒情意味,只要诗歌的主题以事件本身为主,人物形象被作为事件逻辑链条中的必要环节的,便可以成为一首叙事诗。”②杨守森、周波主编,《文学理论实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21页。胡秀春:《唐代叙事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要之,当代诗坛为了繁荣叙事诗创作,需要科学界定与理解叙事诗。
中国古代经典叙事诗的显著特征是既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又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朱光潜就提出过“抒情叙事诗”的概念,认为诗性叙事中的“事”,是“通过情感的放大镜的,它绝不叙完全客观的干枯的事”。③胡秀春:《唐代叙事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朱光潜的这一诗学观点,既符合我国古代诗歌史的实际,又有利于传承与发展我国叙事诗的优良传统,促进当代叙事诗的创作。当然,如何立足于古今叙事诗词曲的创作实践,科学合理地定义叙事诗,可能还需要诗学理论界形成共识。但是,为了繁荣当代叙事诗词曲的创作,笔者倒是主张不妨将“定义”与“理解”叙事诗相对分开来讲。从定义的角度讲,语言应当相对包容一些,比如说,可以将抒情融入叙事(即“情事交融”,与“情景交融”相对应)的诗作称之为叙事诗。从理解的层面讲,则可分狭义与广义两个视角:从狭义上讲,当是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者;从广义上讲,只要叙事因素是诗作感染力的最主要因素,即可认为是叙事诗。
3.适应叙事需要选择与创新诗体。“诗具史笔,史蕴诗心”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突出特点。当今,弘扬叙事传统,既需要学习与借鉴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叙事诗的创作技法,也需要认识不同诗歌体裁的特点,根据叙事内容来选择比较合适的诗体,甚至是在传统诗体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诗体创新。一般而言,乐府、古风等诗歌体式,其篇幅相对灵活,平仄对仗相对自由,比较适合于长篇叙事诗创作。这方面历代诗人的经典名篇很多。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等。与此同时,用篇幅相对较小的诗词来创作叙事诗,只要突出关键的叙事因素,同样能够实现情事交融的艺术效果。毛泽东诗词中的很多诗篇,如《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就是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描述了宏大的历史事件。当代诗人或诗词爱好者,大多是在《毛泽东诗词》的引领下热爱传统诗词的。同样,我们也应跟着《毛泽东诗词》学习与创作新时代叙事诗。
根据笔者的切身体会,认识散曲的叙事优势,有利于促进当代叙事诗的创作。其中,一方面是要充分认识到较之诗词,散曲自身有着独特的叙事功能,可多创作一些叙事曲。散曲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表明,由于散曲直白的语言风格,也包括杂剧对散曲的影响,使之形成长于叙事的特征,有时哪怕是三言五语的简短小令,亦可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传神细节,其叙事之妙惟妙惟肖,很多作品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精彩的小品。至于说,运用带过曲、联章体(或重头小令)、套曲来叙事,更可以提高叙事容量,以满足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表现的需要。可以说,直接用散曲来叙事,也许是推动当代叙事诗创作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叙事特点,借鉴散曲体裁的诸多特点,不断探索诗体创新的“增长点”。例如,借鉴散曲“重头”(包括“同调重头”或“异调间列”)之义,可重复填写同一词牌(甚至是不同词牌)来写叙事词;又如,可借鉴散曲“带过”之义,将诗词曲相互打通来创作叙事诗;还如,借鉴散曲“套数”之义,打破诗词曲三者之间的壁垒,更可为当代叙事诗创作闯出一条新路来。
4.赋含比兴是叙事诗创作需要重视的修辞手法。中华诗学中的“叙事”往往与乐府相联系,“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倒,且轶荡宜于节奏,而真率又易晓世”①(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仔细阅读与鉴赏乐府诗集,尽管以“赋”为主的修辞手法比较突出,但仍然不失“比兴”。作为史诗的杜甫诗歌,更是以“赋含比兴”见长。基于现实主义创作叙事诗,也不能像摄影机一样简单地记录故事是什么样的,而应该以某一现实事件为底色,通过诗者的切身体会,遵循现实应该是什么样来创作,进而将融入作者情感的诗作向社会传递人性的温暖。
就赋比兴而言,“‘赋’是直接的‘即物’‘即心’‘陈事’‘布义’之法,无论写物还是之与心,都直奔对象,不绕弯子。‘比’则是委婉、含蓄的比喻方法。‘兴’是委婉的开头、起兴方法。不过,当‘体物写志’,‘叙物言情’融为一体,通过‘即物’来就‘即心’时,‘赋’就与委婉的‘比’相交叉了。当‘赋’直接‘即物’时,‘赋’便成了文学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②祁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104页。。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引俞犀月语认为:“少陵咏物多用比、兴、赋。兴者,因物感人也;比者,以物喻人也;赋者,直赋其物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杜甫的叙事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关注叙事诗的修辞手法,需要厘清传统诗学中的一种观点:即只有“比兴”论才是形象思维理论,而“赋”论却与形象思维理论无缘。例如,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云:“……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兴比,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当代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赋’只有在单纯地‘即心’时才表现为抽象的议论、说理,当它‘即物’时,对事物的直接描写、叙述恰恰可以创造出形象来。而且照今人对文学形象的定义(艺术形象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赋’较之‘比’、‘兴’的修辞手法,乃是产生真正的文学形象的更为根本的途径。”①南京严羽:《沧浪诗话》上,张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3页。祁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这就表明,只要用以审美体验为特色的积极心理来引领以形象思维为特色的积极思维,运用以赋比兴为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来创作叙事诗,就体现为叙事诗创作的一种诗学理论自觉。与此同时,不断学习与借鉴历代叙事诗的创作经验,不断学习与借鉴新诗及其他叙事文学的创作经验,当代叙事诗就一定能够远离空洞无物的说教,超越苍白无力的说事,运用“赋含比兴”的修辞手法,将“即物”“陈事”“布义”与“即心”融会贯通,就一定能够在当代叙事文学之林中,绽放出传统诗词曲别具一格、绚丽多彩的风雅之花。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诗的艺术风格分为“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大类。所谓优游不迫,即温柔敦厚,其艺术表达的特点是含蓄蕴藉,艺术效果则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所谓沉着痛快,用《沧浪诗话》校笺者张健的话来说,其内涵有二:一是直截了当的表现;二是力度大。他认为严羽所谓的沉着痛快是直言,是明言,这种明目张胆的直言,往往能产生力度、痛快淋漓之感。这种特点与优游不迫的不直言,不明言正好相对。①南京严羽:《沧浪诗话》上,张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3页。祁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显然,“优游不迫”或“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对应着以比兴为主的修辞手法,而“沉着痛快”或“明白清楚”的艺术风格对应着以赋为主或赋含比兴的修辞手法。古往今来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表明,运用赋含比兴的修辞手法创作叙事诗,不尽是一唱三叹的纯粹抒情,而是寓抒情于叙事之中,呈现给接受者的或许是一种清新流利、具体明白、直接“不隔”的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