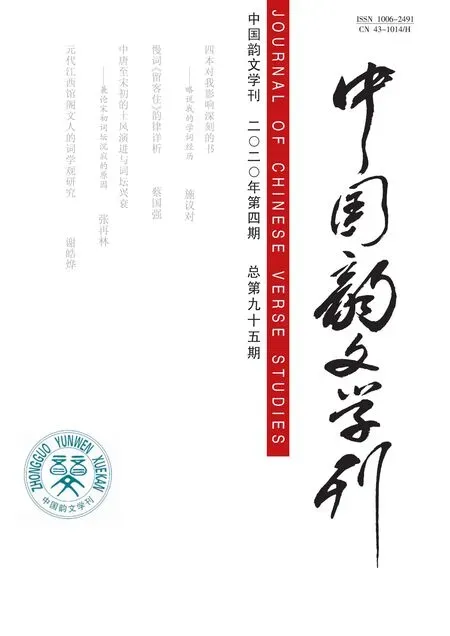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的发展及新变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由于广东所属岭南地区僻远闭塞,唐五代、宋元时期文献散佚,女性词作迄今未见有流传者。最早见于载籍的广东女性词人是明末岭南名妓张乔。张乔,字乔靖,号二乔,人称小乔或乔仙,其生平事略见于明末抗清名士黎遂球所作的《歌者张丽人墓志铭》:“乔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十六日,其母吴娼,入粤生乔,居番禺。乔卒于崇祯六年(1633)七月廿五日,年十九。”[1](P22)张乔死后,在彭孟阳等广东名士的努力下,其《莲香集》得以传世。《莲香集》收录诗作百余首,附诗余。《粤东词钞》收词四阕,《众香词·书集》收词三阕。此外,又有番禺人梁善娘,梁真祐之女,生卒年不详。有词四阕见《众香词·御集》,《全明词》及《全清词·顺康卷》所收均据《众香词》,应为明末清初人。清初及中期,广东女性词创作甚为寥落,鲜有传世者。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始蓬勃发展,蔚为大观。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出现了如下34位女词人:
麦英桂。柯愈春编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断其生年为1761—1765年之间。[2](P984)号醉醒道人,自号醉醒老人,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据《榄溪麦氏族谱》载,其为增贡生麦德沛第五女,何启图室。有《芸香阁诗草》一卷,道光二年留香堂刊行,《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
麦又桂。柯愈春编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断其生年为1766—1770年之间。[2](P1022)字芳兰,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据《榄溪麦氏族谱》载,其为增贡生德沛第七女,麦英桂妹,同里何怀向室。诗词音调清朗,音节和平,虽处困极,绝无哀痛之声。有《谢庭诗草》一卷,集前有何其英序,道光二年留香堂刊行,《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
吴尚熹。生卒年不详。别字禄卿,又字小荷,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其父吴荣光(1773—1843),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编修官擢御史,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尚熹擅书法绘画,兼善诗词,成年后嫁画家叶梦龙之子叶应祺,夫妇唱和,闺房翰墨,称一时韵事。她画的菊花扇面、《水仙卷》及《群仙拱寿卷》今藏于广州美术馆,有《写韵楼词》一卷。
张秀端,生卒年不详。字兰士,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其父张维屏(1780—1859),嘉庆九年(1804)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后隐居“听松园”,闭户著述。秀端嫁士子钱君彦。她擅画花卉,其兄群鉴以素绢索画,为绘墨梅帐檐,并题金缕曲一阕,为世称道。工诗词,有《香雪巢词钞》。《粤东词钞》收词十五阕。
潘丽娴。生卒年不详。别字励闲,又字素兰,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潘恕(1810—1865)女,施华封室,潘飞声姑母。善诗词,有《饮冰词稿》。《粤东词钞二编》收词五阕。
居庆,生卒年不详。字玉徵,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居巢(1811—1865)长女,嫁于中立,于晦若(1865—1915)之母。工花卉,仿恽寿平。能诗,有《宜春阁吟草》附词。《粤东词钞二编》收一阕。《清词综补续编》卷十五收另一阕。
居文。生卒年不详。字瑞徵,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居巢次女。《清词综补续编》卷十五收词一阕。
范荑香(1797—1884)。原名蒥淑,字茹香,又字荑卿,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人(今属广东省梅州市)人。范引颐之女,同邑邓耿光室。十二岁即能赋诗填词。嫁夫四岁而寡,守节终身。晚遁空门,年八十余始卒。其诗缠绵悱恻,凄婉哀伤;扣人心弦,不忍卒读。有《化碧集》,梅州管又新民国五年(1916)刊行。范荑香为近代岭东三大女诗人之一,与黎玉贞、叶璧华齐名 。
黎玉贞。生卒年不详。字宁淑,梅州(今广东省梅州市)人。著有《柏香楼》文集一卷,诗集二卷。其父是乾隆举人,她小的时候就受到良好教育,有家学渊源,博通经史,诗文高洁,书法亦秀劲,无闺阁气。遗憾的是婚后不到一年,她的丈夫就死去。她从此避不见人。著有《柏香楼》文集一卷,诗集二卷,可惜都已经散佚。
叶璧华(1844—1915)。字婉仙,号润生,嘉应白渡堡卢陵乡(今属广东省梅州市)人。嫁清末翰林李载熙之子李舫蓉。幼承家学,博览群书,以才学受聘为张之洞家庭教师。戊戌变法失败后创办懿德女校,竭力推行新学,为粤东地区兴办女校开了先河。有《古香阁词集》一卷,附于《古香阁全集》。
梁霭。生卒年不详,字佩琼,号飞素,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潘飞声室。其书斋号为飞素阁,故作品名为《飞素阁集》。《闺秀词续》收词一阕。
张宝云。柯愈春编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置其生年于1846—1850之间。[2](P1817)字缦如,香山人。张兆鼎女,何隶桥室。有《梅雪轩全集》四卷,分诗词、试帖、论说等类,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伦鸾。生年不详,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后。字灵飞,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师事名士邓尔雅,先后任桂林女学教习、北大词学教授。有《玉函词》,今不存。况周颐《玉栖述雅》收词五阕及断句若干。
康同璧(1889—1969),字文佩,号华鬘。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康有为次女,宝安罗昌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擅诗词、书画。康同璧作为中国最早女权领袖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官派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妇女代表,在国内女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有《华鬘诗》《华鬘词》,今全本已佚,仅存诗词三十余篇。
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新会(今广东省江门市)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启超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曾师事麦孟华。工诗词,有《艺蘅馆词选》五卷。
冼玉清(1895—1965)。以字行,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在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诗词书画创作、金石丛帖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为岭南文化研究献出毕生精力。有《词集》一卷、《张萱研究》二卷、《广东艺文志解题》。
张纫诗(1911—1972)。原名宜,后名转换,自署南海女子,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纫诗少年受业于叶士洪及翰林桂玷,以诗古文辞见称,尝为民国政要陈融掌书录,加盟广州的越社、棉社,寓居香港后又加入坚社、硕果社,有《文象庐诗集》《仪端馆词》《张纫诗诗词文集》等。
王德徵。生卒年不详,南澳(今广东省汕头市)人。揭阳陈毅斋室。工诗词,有《彤规素言》。(《潮州志·艺文志》)
文信。生卒年不详,俗名刘芳,广东人。某方伯侧室之女,道光间祝发广州檀度庵。工诗词、书画。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她的《山水册》。(《海珠旁璅》《艺林月刊》)
尹莲仙。生卒年不详,东莞人。何师臣室。工诗词,有《瑶亭集》。(《东莞诗录》卷六十四)
张八、袁九。粤妓,年代不详。《峭蛣杂记》所载张八、袁九各一阕为陈廷焯录入《别调集》,亦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徐叶英。生卒年不详,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山阴何纟冋文室,工诗词。有《徐叶英诗集》,见《柳絮集》《广东女子艺文考》。
刘嘉慎。生卒年不详。一字敏思,又字佩规,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况周颐弟子。有词一阕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近代女子词录》,另有四阕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近代女子词录》。
翟兆复。生卒年不详,惠阳(今广东省惠州市)人。有词二阕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近代女子词录》。
黄庆云。生卒年不详,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有词一阕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近代女子词录》。
程倩薇。生卒年不详,广东人。有词一阕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近代女子词录》。
杨晶华。生卒年不详,字明洲,广东人。北京文科学生。有词二阕见《词综补遗》卷五十。
王翔。生卒年不详,字蕴文,广东人。有词一阕见徐乃昌所编《闺秀词钞》,并见于《词综补遗》卷四十。
汪彦斌。生卒年不详,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汪兆铨之女。有词一阕载古直辑《诗词专刊》卷六,另有二阕见《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四号。
王兰馨(1907—1992)。号景逸,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父官至广东巡抚。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有诗词集《将离集》《晚晴集》,以及著作《景逸词论》等。
黄倩芬(1907— )。中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香港海声词社成员,香港汉文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嘉谟学校校长。有《淡明楼诗词稿》。
刘佩蕙,(1923— )。佛山(今广东省佛山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香港海声词社成员,任香港耀山小学校长。其《兰馆词草》存词百余篇。
潘思敏(1920— )。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适名士陈荆鸿。今门人代集之《茹香楼存稿》存词百三十首。
总体来说,清代以前的广东女性词家传世者不多,存词也较少。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始盛,并在岭南文学史上逐渐占有重要地位。其以女性视角传达不同的思想情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面貌,在承袭传统女性词的优势之外,又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及新变,对后世的岭南词坛影响较大。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的发展及新变
(一)创作主体的发展及新变
与前代广东女性词人的数量和分布格局相对照,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坛已经开始呈现出兴盛的势头。就创作主体而言,其发展和新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词人数量显著增长。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人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到34位之多,是唐宋以来近千年时间里产生的女词人数量总和的几十倍,从彼时的寥若晨星,到此时的群星璀璨,在数量上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蓬勃发展态势。
其二,创作主体身份趋向于多样化。纵观历代女性词人,身份无外乎后妃、闺秀、方外人士、歌妓这几大类。时至新旧更迭的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思想、新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不断涌现,女性词人的身份也趋向于多样化,总体上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征。
就上文所辑34位广东女词人的生平来看,生于十八、十九世纪者占三分之一强。这些女词人通常出身于诗书世家,是官宦人家的闺秀或者士人伴侣,大抵还囿于传统的闺阁身份。属于此类者如麦英桂、麦又桂姐妹,她们分别为香山增贡生麦德沛第五女和第七女,皆嫁同里士人为妻(见《榄溪麦氏族谱》);吴尚熹,其父吴荣光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成年后嫁画家叶梦龙之子叶应祺;张秀端,其父张维屏道光二年(1822)进士,秀端嫁士子钱君彦;潘丽娴,士人潘恕女,施华封室,潘飞声姑母;居庆、居文,分别为画家居巢之长女、次女;黎玉贞,其父为乾隆举人,夫死后避世,等等。亦有歌妓和遁入空门者,如张八、袁九,粤妓,有词录入陈廷焯《别调集》;又如范荑香,大埔士人范引颐之女,同邑邓耿光室,嫁夫四岁而寡,守节终身,晚遁空门;文信,俗名刘芳,道光间祝发广州檀度庵,工诗词、书画,等等。她们大部分生活于晚清,无论所受教育、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个体认知等都还难以跳脱传统窠臼,因此,与历代传统女词人并无明显的差异。
此外,上文所辑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广东女词人属于由清而入民国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走出闺阁,突破传统女词人闺秀、方外、歌妓等身份,成为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甚至留洋学生,进而成长为女教授、女教育家、女政治家等,较为明显地呈现出由传统女性向职业女性过渡的身份特征。比如杨晶华,北京文科学生;叶璧华,以才学受聘为张之洞家庭教师,后创办懿德女校,竭力推行新学,开粤东地区兴办女校之先河;伦鸾,师事名士邓尔雅,先后任桂林女学教习、北大词学教授;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最早女权领袖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官派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妇女代表;梁令娴,梁启超长女,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冼玉清,在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诗词书画创作、金石丛帖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为岭南文化研究献出毕生精力;王兰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张纫诗,曾为民国政要陈融掌书录,加盟广州的越社、棉社,寓居香港后又加入坚社、硕果社;黄倩芬,曾任嘉谟学校校长;刘佩蕙,任香港耀山小学教员、校长,等等。受新时代民主大潮的影响,加之对职业化的追求与探索,以及社交平等和自由的实现,使得女词人具有了与男性平等受教育和走进广阔社会的机会,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词学创作的面貌也因之焕然一新。
其三,创作主体的词学渊源与词学活动也与前代有着本质的不同。
传统女词人学词大抵不外乎两种途径:家学渊源和名师指点。这两种方式在晚清民国的广东女词人中依然存在。比如麦英桂、麦又桂姐妹,居庆、居文姐妹,吴尚熹、张秀端、潘丽娴、黎玉贞、张宝云等人,皆出于书香世家,大多因家庭熏陶而喜好填词;又如伦鸾曾师事名士邓尔雅,刘嘉慎乃况周颐女弟子,张纫诗少年受业于叶士洪及翰林桂玷,梁思顺曾师事麦孟华,等等。
然而,受“新思想”和西学的影响,民国时期更有一大批女词人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学成以后,一部分人又在新式学堂以教授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为职业,这不仅让女性词人的学词方式更加开放和多元化,也为其在词学领域继续深造和持续钻研提供了更多机会,使得一些女词人在从事词学创作的同时,又参与词学研究,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比如王兰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有诗词集《将离集》《晚晴集》,以及学术著作《景逸词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民国女词人的立言意识也逐渐增强。她们不再满足于自娱自乐式的闺阁吟诵,而是热衷于公开发表词作以展示才学,或参与词社等互动性较强的团体,彼此切磋,应和酬答。比如,刘嘉慎、翟兆复、黄庆云、程倩薇等人,皆有词作发表于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中“近(现)代女子词录”;汪彦斌,有词二阕发表于《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四号;杨晶华,有词二阕见《词综补遗》卷五十;王翔,有词一阕见《闺秀词钞》,等等。各种刊物和词选对女性词作的公开发表和选录,极大地提升了她们创作的热情。同时,近世也有一些广东女词人,如黄倩芬、刘佩蕙等,寓居或游学香港,成为香港海声词社成员。
(二)创作内容的新变
不可否认,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广东女性词作,其闺情、咏物、节令等自娱娱人的内容仍然是主流,描写内心苦闷愁怨,抒发自怜自艾之情也依旧是女性词最普遍的表达。然而面临国事动荡和时代巨变,加之大批女性走出闺房进入社会,其身份、地位和学识较之传统女性有了质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女性词作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质变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国时期,新思潮带给广东女词人群最大的改变即是对狭隘生存环境和单调生活体验的突破。反映到创作上,女性词作不再拘囿于闺阁而转为书写新生活、新见闻、新体验,这就大幅度拓展了词作的表现范围,使其能够牢笼万象、吟咏百端。如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病卧印度槟榔屿。时年十九岁的康同璧“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3](P3),只身寻父,随父游历十余国。她的外邦纪游之作,设色鲜明,波澜壮阔,为广东女性词的题材辟开了新境。如其《鹧鸪天·咏士多噉岛景物》:
海气凉生夏亦秋,汐烟吹绿水悠悠。万山灯灿繁星列,千岛桥衔接水流。 停画舸,驻琼楼,如云士女载歌游。欢呼漫舞嬉潮月,夜夜随人上钓舟。[4](P285)
奇丽多彩的外邦风物、载歌漫舞的异域士女,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一幅印度士多噉岛的旖旎风情画卷。
又如《南歌子·大吉岭秋晚试马》:
马跃天风上,崖横雪岭前。风峦层叠翠环偏。金碧山川灿晓,艳阳天。 宿雾收云脚,朝云浴涧边。望迷一片绿芊绵。须趁秋深茶熟,踏花田。[4](P284-285)
其序曰:“大吉岭沿山皆为茶田,当晓日方升,极目葱茏,香风送爽,驰骋其间,令人神怡。”全词色彩明艳,境界开阔,可想见其纵马驰骋于异域山水间的心旷神怡和飒爽英姿。
由此可见,社会的动荡、个人身世的离乱漂泊,使得女词人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将日常生活艺术化,以及将栖居之地诗意化,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传统身份的新变,社会地位的提升,生活阅历的丰富和知识技能的增加,其所能取材的内容既日渐丰富,洞察力也愈加深邃。
其次,在晚清民国遍地狼烟的时代背景之下,亲历时世危难与家国衰亡,广东女词人群体忧时忧世情怀日益深重。传统女性词中最常见的顾影自怜的“忧生”主题,在一部分襟怀朗彻的女词人笔下,转而为对国家民族苦难的真切悲悯与无限忧思。如程倩薇《扬州慢·闻平津警报》:
金寸山河,铁围区脱。从教虏骑凭陵,貔貅坐拥,甚面目谈兵。叹神州,微茫禹迹,膻腥染遍,谁误苍生?悄危栏闲凭,愁闻哀角声声。 杞忧莫诉,便痴顽,也自心惊。怅虎豹当关,荆榛塞路,难请长缨。抚剑雄心犹在,浇清醑块垒宁平。更伤情长望,龙沙凄黯征程。[5](P167)
以朗朗硬语、耿耿英气,将身世家国之感打并于一处,表达对锦绣山河破碎的幽忧悲懑,以及期盼中华民族崛起,表达虽女子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又比如广东近代教育改革家、妇女教育先驱冼玉清,其作于抗战时期的《高阳台》词,更是真实地再现了烽火连天的背景下,故园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的凄凉和怅惘。其词如下:
锦水魂飞,巴山泪冷,断魂愁绕珍丛。海角逢春,鹧鸪啼碎羁悰。故园花事凭谁主,怕尘香、都逐东风。望中原,一发依稀,烟雨冥濛。 万方多难登临苦,览沧江危涕,洒向长空。阅尽芳菲,幽情难诉归鸿。青山忍道非吾土,也凄然、一片啼红。更销凝,度劫文章,徒悔雕虫。[6](P124)
词序曰:“羊城沦陷,客殢香江,杜宇声中,一山如锦。因写《海天踯躅图》以志羁旅,宁作寻常丹粉看耶?”女词人以真实切肤之痛,以沧桑之语与衰残之景,书写国家危亡之感与流人幽恨之思,忠爱悲慨之情郁勃而出,其襟怀恢廓确非“寻常丹粉”能堪比拟。
当然,这种充满时代感和使命感的“壮词”,往往是时代、世道、词人个性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女性词中并不多见。然而,尽管这种慨时忧世的激越刚健之音是个别的、间歇的,并未形成群唱,但这异响已足以引人注目,成为当时广东女性词作中的最高调和最强音。
第三,晚清民国时期,受到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思潮的影响,许多广东女词人自觉突破性别的圈囿局限,有意跳脱出前代一脉相承的“思妇”“怨妇”之苦闷渊薮,以蹈扬性情、雄姿英发的女主人姿态示人,词中的“自我形象”大为改观。
传统曲子词中“男子而作闺音”[7](P1449)的代言模式,大抵无外乎乞怜依附于男性的奴妾或曲意逢迎的歌妓身份;而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词人的作品中则出现了与男性平分秋色、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形象。如生于清道光年间的岭南才女吴尚熹,其《满江红·秋夜有感》云:“乡梦远,浑难托。琴书案,全抛却。但消磨羁旅,壮怀牢落。百岁韶华弹指事,鸿回燕去空漂泊。问襟期、原不让男儿,天生错。”表达了要求与男性一样拥有广阔天地的强烈渴望和不凡襟抱。又如潘思敏《摸鱼儿·九日登太平山》:“齐烟外、信有尧封可睹。登临知甚情绪?纷纷蛮触争蜗角,多难愁闻金鼓。夸武库。君不见,星津月地浮槎渡。何堪再语。叹度曲楼荒,思悲响歇,高会未能赋。”被何乃文赞为“有序有物,尤觉有气势,类丈夫之言”[8](P2),此评不虚也。再如师出于叶士洪及翰林桂玷门下的南海女子张纫诗,早岁即与詹安泰、朱庸斋、叶恭绰、冒广生等诸公唱和交游,寓港时又同廖恩烹、饶宗颐、潘小磐、黄松鹤等名家往来酬唱,其风神气度与雅性高情自然非同凡响。友人卢鼎公为《仪端馆词》作跋,特举其词中俊句以摹状其人:“《玉楼春》之‘江山千古在诗中,不放天涯三月去’,其抱负也;《小重山》之‘知君不肯嫁东风。天作主,休问为谁红’,其操守也;《双调天仙子》之‘天阔莫嫌今夜短,人生百年如露电’,其人生观也……《唐多令》之‘怅醒时不是前身’,《玉楼春》之‘试从天上念人间,人爱春晴人爱雨’,殆人而仙者乎?而《画堂春》之‘有酒有诗换日,栖心人境何妨’,《换巢鸳凤》之‘修到神仙也相思,分沉人海悲天老’,则仙而佛矣。”[9](P32)由此可见,其高风雅契非但于女性词人中所罕见,即或与当时男性中之贤才高士相比较,也不遑多让。
此外,广东女词人笔下还出现了诸如“啼破霜天,摇鞭古道西”“独抱征鞍,霜痕认马蹄”(叶璧华《梅花引·旅行》)的旅者形象,“家国两凄惶,高堂生白发,结中肠,羞看珠泪灿寒光,儿女态负我志轩昂”(翟兆复《小重山》)的忧国忧民者形象,“满眼西风黄叶地,当年谁会幽栖意?亿万黄魂呼欲起。嗟已矣。尊前慷慨空余泪”(潘思敏《渔家傲》)的仁人志士形象等等。
由于处在时代变革、文化转型的重要节点,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女性词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与前代既同且异的特征。虽然无论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内容而言,其发展和新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纤微的或局部的,但仅此也可见这一时期广东女性词较之于前代的开拓和创新。
三 广东女性词发展新变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广东女性词的发展和新变,不仅在岭南地区词学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女性词是中国女性词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其在提供丰富词学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近代女性词的发展趋势。
如上所述,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的发展与新变,一方面缘于当时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思潮的推动,使其能够对千年来已成定式的闺阁文学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动荡的时局、危颓的国势,也为广东女性词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一时期的词作既是千百年来传统女性词的“收官”和总结,也为中国现当代女性词“导夫先路”,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女性运用词体、革新词体的产物,其词史意义、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女性词人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词史的书写,而且一些人较早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词学观念,比如梁启超长女梁令娴,曾仿周济《宋四家词选》体例编《艺衡馆词选》,录历代名家词作计676首。其自序云:
顾词之为道,自唐迄今千余年,在本国文学界中,几于以附庸蔚为大国。作家无虑数千家,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词》《乐府稚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未由尽正变之轨。近世朱竹垞氏网罗百氏,泐为《词综》,王德甫氏继之,可谓极兹事之伟观,然苦于浩瀚,使学子有望洋之叹。若张皋文氏之《词选》,周止庵氏之《宋四家词选》,精粹盖前无古人。然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10](P2)
对历代词集编选之得失予以评骘,对曲子词的发展变迁也有所述及,展现出了较为精严的选词宗旨和选词理念。这表明,晚清民国时期一部分广东女词人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词学观点和创作主张,并在创作中以此为导向,为推动近代女性词朝着多元化和深刻化方向发展打下理论基础。
其次,从地域观照维度而言,广东女性词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板块,也是岭南词史的重要支流,其发展及新变既有女性词的共性特征,也具有因地域相近、声气相通而一脉相承的、独特的岭南文化色彩。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广州等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和经济日渐繁荣,岭南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粤词创作也一改往日颓势,呈现出作家人数攀升、作品数量激增、佳作层出等良好发展态势。相当一部分粤词通过展示粤地自然风物和人文精神等内容,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岭南词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同时期的广东女性词也在词境、词艺、词风等方面为粤词的不断丰富和发扬光大做出贡献。
不仅如此,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虽然看似零散,不成体系,既没有出现诸如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这样的“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没有形成如“南社”“兰社”“梅社”“寿香社”等有众多女词人参与的著名词社,然而,在粤词的发展过程中,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进入共和国以后,出自著名词人、词论家朱庸斋分春馆门墙的女弟子,如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等人,继续活跃于广东词坛,为现当代女性词传灯续火、开枝散叶,成为粤词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综上所论,广东女性词作为粤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其发展趋势与粤词的整体走势相一致,呈现出清中叶以前寥落而近代兴盛的局面;另一方面,女性书写作为独立领域,又因其特殊性而分立于男性话语之外。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女性词的发展和新变等问题的考索和探究,无论在近代词史研究和岭南词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中国女性心灵发展史研究方面,都有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