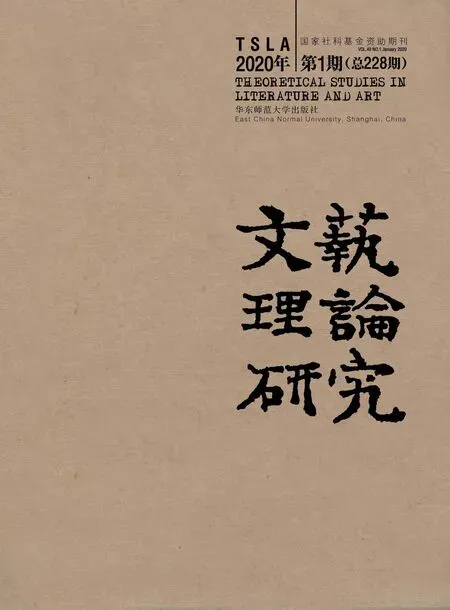“五四”与传统: 激烈反叛背后的承担
高旭东 石统文
2019年是“五四运动”(即“政治五四”)爆发100周年。李泽厚将“文化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政治五四”分开,认为前者是“启蒙”,后者是“救亡”,后来“救亡”压倒“启蒙”,从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丧失(7—49)。这种对“五四”的二分法是不符合史实的。陈独秀办《新青年》就是以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铺路,鲁迅张扬个性自由的目的,就是希冀中国走出困境而成为雄励无前的“人国”。可以说,启蒙的目的就是救亡,这是《新青年》同仁的共同思路。当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与罗家伦等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走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当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时候,人们感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是一体的。因此,当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时,这里的“五四”既指“文化五四”,也指“政治五四”。一方面,作为青年学生援助外交的五四运动,因为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成为东方睡狮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借助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得以广泛传播,白话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乃至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为什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因所在。
虽然文化上的西化与反传统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然而将此推向极端,并以其激进性划出一个新时代的却是“五四”。马列主义正是在“五四”西化的高潮中,以西方最新思潮的面目进入中国,并得以广泛传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的直接结果,是符合史实的。改革开放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学热,使“五四”与传统再一次成为学术思考的热点。
就表面上看,“五四”反传统的确是整体性的、激烈的、彻底的,而且对于“五四”反传统发生的原因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就是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毅然抛弃传统并且全盘西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列国是不是遇到民族危机的时候都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而拿来强势一方的文化呢?换句话说,在民族危机的语境下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呢?如果不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激进的抛弃传统的文化运动呢?在当下强调中国主体性与弘扬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应该怎样评估五四及其激烈的反传统呢?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出路何在?
一、 “五四”激烈的反传统
回望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战胜国能在文化上超过中国,因而最终免不了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命运。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一败再败,但是中国的西化仅限于科技工艺的引进,并且,为了抚慰因引进西方科技工艺而损伤的民族自尊心,中国在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上甚至比明代中叶与清代中叶还保守,这正是在鸦片战争后长达50多年时间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选择方案得以盛行的原因所在。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选择方案的破产,中国在文化与文学上扬起了西化的风帆,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革命派”的作品在排满与光复旧物的拟古包装中表现出现代性。①随着袁世凯尊孔、复辟帝制以及辛亥革命失败后民族危机的有增无减,一场前所未有的、以激烈反传统与西化为特征的文化运动暗流涌动,悄然兴起!
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首领是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与主撰人,他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以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不久又接受了李大钊传播的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认识到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因而《新青年》就以西方的伦理道德对中国传统的孔学礼教施以猛烈炮火。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将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与审美的文学革命结合在一起。陈独秀说:
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以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95)
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迅速涌向全国。陈独秀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事物是永恒地运动、发展、变化的,一切都处于竞争状态,动物界如此,人类社会如此,国家之间亦如此。他在《敬告青年》中指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独秀》3)依据这种优胜劣汰规律,如果中国这样一直贫弱落后下去,就会被动挨打,被列强侵略而沦为其殖民地,被世界淘汰,而要改变中国这一厄运,他认为首先须废掉孔孟之道,“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5—6)。于是,陈独秀想在中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如果说康有为还想在孔学的大框子里装进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么,陈独秀则为了张扬个性的自由独立而横扫孔子的礼教道德。他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多篇文章中,将反传统的矛头直指孔孟之道以及传统伦常的核心——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反叛。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说:“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独秀》89—90)为了巩固共和国体而走向伦理革命,是当时陈独秀的思想逻辑。于是陈独秀更进一步地将伦理道德上的觉悟,看成是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的和最后的解决方式。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说:“此(伦理道德)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独秀》41)而伦理道德革命的核心就是以西方独立自由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反叛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合群主义,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认为西方“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方“以家族为本位”,因而中国欲振兴就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独秀》28—2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独秀在反叛传统等各方面都比胡适激进,然而“全盘西化”的口号却是胡适而非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一方面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他美国导师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文学进化为根据的白话文革命的发难者以及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白话新诗的尝试者。他指出文字改革虽然是形式,但与内容有莫大的关系,为自由精神的发展解除了枷锁,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改革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做一种活的文学,必须要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胡适文存》第一卷283)
尽管黄遵宪、裘廷梁等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倡导白话文,但像胡适那样执着地以白话文作为文学价值唯一的衡量标准者,并且终于使白话文成为文学的正宗,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将自己的白话文革命与但丁倡导俗语,并在《神曲》中不用拉丁文而用意大利俗语进行比较。胡适说:“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通译《神曲》——引者),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79)但丁在文学经典中开风气之先,很多人开始用俗语创作。“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80)胡适认为,其他像德、法、英等国虽然也有以各自民族语言写作而摆脱拉丁文的过程,但是,这些国家的民族语言与拉丁文差异太大,因此:
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替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81—82)。
比起五四时期鲁迅蔑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读中国书”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似乎表现出一丝对传统的温情,然而他却赋予了“整理国故”一种反传统精神。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文集》第二卷551)。他将自己这种“评判的态度”与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画等号,表明了他以西方的学理批判传统国故的文化立场。特别是当人们肯定中国文化传统时,胡适会寻找一系列满含贬义的词汇来形容传统,就像他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就指责的,中国独特的“宝贝”就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牢,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胡适文集》第五卷388)。192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的浪潮回落之时,应《中国基督教年鉴》的约稿,胡适在英文论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提出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wholesale acceptance)(Hu Shih132),后来此文被看作“全盘西化”说的源头。②从词义上看,必须是100%,而99%就不是“全盘”,所以1935年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在没有否定其全盘西化主张的同时,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充分世界化”(543)。可以说,将全盘西化等同于“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或“充分世界化”,倒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选择之恰如其分的概括。
尽管在英美派文人中最激进的胡适与留日派文人相比仍显得谨小慎微,但是他以鲜明的西化立场与传统对着干却是毫不含糊的。中国文学传统可以分为文人文学传统与民间文学传统。文人文学传统作为正宗,以诗歌散文为主导文体,偏重于表现家国的忧患与个人的悲愁。从屈原的“发愤抒情”,辛弃疾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以及诗词中普遍的伤春悲秋,到中国文论与诗论中的“蚌病成珠”,“不愤不作”,“欢愉之词难工,穷愁之言易好”(《古文》88),“诗必穷而后工”(张潮226),形成了一种崇尚悲剧精神的文学传统。民间文学传统以小说、戏剧为主导文体,明显以乐观为基调,并且普遍以大团圆为结局。于是胡适就在诗歌与小说、戏剧两条战线上悖谬式地反传统。他一方面在诗歌等文体上提倡乐观主义精神,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中国文人正统文学的悲剧精神:“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胡适文集》第二卷9—10)因此,胡适的白话诗就以乐观为基调,一反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传统,在《誓诗》中说“更不伤春,更不悲秋[……]月圆固好,日落何悲”(《胡适文集》第九卷223)!另一方面,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又以西方的悲剧观念批判中国民间文学以乐观为基调的大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胡适文集》第二卷122)不难看出,中国文学传统的两重性将胡适的反传统逼进了一个尴尬的语境中,即一方面在诗歌中倡导乐观精神批判悲剧精神,一方面又在戏剧中倡导悲剧精神批判大团圆,这使其批评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声援胡适发起文学革命的还有钱玄同,他在反传统方面比胡适更激进。在给胡适的信中钱玄同写道:“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25)因为“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彀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26)。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钱玄同则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家园: 要扫荡中国文化传统,就要摧毁其赖以存在的汉字而实行罗马拼音文字,或者废除汉文而代之以世界语。他与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影响最大的三大将,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在小说《荆生》中以金心异与田其美、狄莫对三人分别影射攻击。而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则将白话文革命的成功归功于激进的钱玄同: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鲁迅,第4卷13—14)
鲁迅介入新文化运动,就与钱玄同的拉稿有关。当时,鲁迅因不急于介入而表现出来的踟蹰基于多重考虑,一方面陈独秀的《新青年》让他联想到自己当年想以《新生》发起一场文艺运动,他不想重复咀嚼失败的苦味;另一方面他也在进行思想调整,尽管陈独秀以“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独秀》27)的伦理革命与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第1卷48)是完全一致的,鲁迅留日时期所推崇的拜伦、尼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先驱,但是,鲁迅留日时期的“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58)的“取今复古”与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不同,同时,他那将现代性包裹在古奥典雅的文言文中的“拟古的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抛弃文言文推崇并使用白话文,却是迥然相异的。而经过思想调整的鲁迅一出山,就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他抛弃了从《文化偏执论》到《〈越铎〉出世辞》那种“取今复古”的文化选择方案,完全认同了“五四”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激烈反传统,甚至表现出一种近乎决绝的激进性与叛逆姿态,进而使得毛泽东将他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新文化“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毛泽东698)。
我们且看五四时期鲁迅激进反传统的文化表现。当时中国的固有文化被有些人推崇为“国粹”,而鲁迅却将“国粹”视为应该割掉的瘤子与脓疮。他在《热风·三十五》中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鲁迅,第1卷305)他甚至将“国粹”比做“梅毒”,正如用六百零六可以医治肉体上的“梅毒”,用科学也可以医治精神上的“梅毒”——“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鲁迅,第1卷313)。儒家所设计的政治秩序,就是让人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而苦下去,所以“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鲁迅,第7卷312)。鲁迅的激烈反传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表现得更充分,他认为由“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构成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一级一级的制驭着”的等级秩序(鲁迅,第1卷215),其实质就是一级一级地“吃人”与“被吃”的关系。于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第1卷216)。而中国的历史也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离乱之世)和“暂时做稳了奴隶”(太平盛世)两个时代的恶性循环(鲁迅,第1卷213)。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又剖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然后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那种画圆圈式的循环。当有人倡导“尊孔读经”的时候,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说:“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鲁迅,第3卷127—29)。鲁迅甚至让人“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鲁迅,第3卷96)。而且外国人也不能赞美中国文化: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鲁迅,第1卷216)
鲁迅甚至认为外国人赞美中国文化就是想加入“吃人”的队伍。鲁迅是文学家,其激烈反传统的矛头不能不指向中国文学传统。在《论睁了眼看》《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文中,鲁迅认为中国文学是不能直面人生血泪的“瞒和骗”的文学,是没有人格平等观念的“官僚文学”——“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而鲁迅以小说、杂文等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不但具有反传统的激进性,而且使得对传统罪恶与黑暗的表现达到了令人恐惧的深度。尼采是基督教文化中反传统最激烈的人,并以“重估一切价值”著称;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中国小说“重估一切价值”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导言》中,明确指出了二者的精神联系。如果说《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是尼采颠覆西方传统实行价值翻转的代表作,那么在《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狂人敢于将象征中国文明史的“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踩在脚下,几千年的“仁义道德”也变成了“吃人”,面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传统狂人发出了最具有颠覆性的呐喊:“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第1卷429)不仅如此,好与坏、善与恶,在《狂人日记》中完全颠倒了。用鲁迅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的话说,天地都在叛逆的猛士眼中“变色”。这种反传统的激进性也表现在《阿Q正传》中。中国的文化传统被鲁迅浓缩在阿Q这一形象中,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文化传统希求圆满的一种凸显,中国传统的造反(革命)也是一种没有理想之光的旧秩序的重建,一个循环性的圆圈。小说写到后面,阿Q抓进监牢不烦恼而圆圈画不圆就异常烦恼,表明杀死阿Q的圆圈(死刑犯的画押符号)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可以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仍然弹奏着《狂人日记》传统文化吃人的主旋律。《阿Q正传》对传统文化的控诉一点不亚于《狂人日记》,只是由于象征技巧的运用需经深入分析才能看出来。
鲁迅介入新文化运动并不很早,但就反传统之激烈深刻而论,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积淀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揭露与剖析,赋予了“五四”反传统以实质性的内容,成为中国文化传统最激烈的解构者。鲁迅与解构主义的精神联系,可以从他深受尼采的影响看出来。尼采是颠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文化大师,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德里达就说过他的精神先驱就是尼采。那么,鲁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的解构主义者,也就毫不奇怪。
二、 激烈反传统的根源来自传统
为什么说“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根源于传统呢?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观察和思考,把“五四”爆发的境遇和世界其他民族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时作出何种不同的文化选择,那么我们对“五四”反传统的动因与实质就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五四”反传统是因为中国当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军事失败,外交屈辱,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不但沦为半殖民地,而且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中国要想强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抛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问题是: 一个民族受到列强的压迫导致民族危机,就都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而拿来强势一方的文化吗?在民族危机的语境下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呢?
我们考察的结果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当民族发生危机时就抛弃固有的文化、信仰与传统,并不是普遍的文化现象。我们先看犹太教文明。在历史上,这个以亚伯拉罕为始祖而创造了一部圣史的犹太民族,的的确确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罗门逝世后出现一个以撒马利亚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与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太王国。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入侵并毁灭了以色列王国,除了将两万七千多人掳走,其余被迫流散,史称“失掉的十个部落”。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国三度入侵犹太王国。尤其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犹太圣殿被毁,犹太国王被挖去双眼,与其族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然而,犹太人并没有因为国家被毁、民族危亡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传统,而改宗巴比伦文化,而是坚定地信仰他们的上帝。随着巴比伦为波斯所灭,犹太人不久又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了圣殿。从公元前332年开始,犹太王国先后被马其顿王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所征服和奴役,直到公元前168年,犹太人推翻了塞琉古王国的统治才重获自由,然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犹太民族。公元前63年罗马大军横扫巴勒斯坦,犹太沦陷为罗马的一个省,并且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罗马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算得上是“先进文明的代表”,然而,被奴役的犹太人却没有因为家国沦陷、圣殿被毁就反叛犹太教文化传统而“全盘罗马化”,他们甚至根本不买这个军事上异常强大的“先进文明”的账,为了信仰自由与民族独立奋起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在公元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被罗马人屠杀者就达百万之众!结果是: 犹太人的反抗使得罗马人将其从故土驱离,犹太人此后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地区而在世界各国流散。然而另一方面,当时作为犹太教一个教派的基督教却逐渐征服了罗马,使得西方人接受了犹太人的上帝,并且以犹太人的历史作为圣史。从理论上说,犹太教与基督教是非常接近的宗教(《旧约》是两教共同的经典),然而流散在基督教各国的犹太人虽然也有个别人信仰基督教,但主流倾向却是排斥基督教而坚信犹太教。为此他们要忍受世界各国的排犹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歧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甚至被希特勒视为一切邪恶事物之源而被屠杀600万之众。然而直到今天,犹太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并且以其对知识与财富的高比例拥有,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我们再看伊斯兰教文明。在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仇视其母体犹太教,他们尤其痛恨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并且不相信耶稣复活,也曾经发动过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在中世纪中后期,当时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在罗马天主教皇准许下,以收复阿拉伯穆斯林占领土地的名义对地中海东海岸国家发动战争,前后共计九次。十字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文明尽毁,阿拉伯世界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但穆斯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并且依靠信仰的力量团结了信众,抗击十字军东征,甚至伊斯兰教信徒比以前更多,影响范围更广。有趣的是,由于犹太教是一神教,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源出于犹太教,这就使一些基督徒产生错觉,以为都是一神教,改宗很容易,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信仰基督教,然而,尽管十字军东征使穆斯林流血牺牲,后来基督徒又千方百计对穆斯林进行归化,但是正如戈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中所说:“基督教徒的归化徒劳无功,穆斯林根本不可能改宗。”(247—48)事实上,当代美国不断对伊斯兰国家施压,并以最先进的武器攻打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却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因为战败而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抛弃其传统文化,进而西化或美国化。
不难看出,在民族危难之际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吸取侵略者一方强者的文化,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主要是儒家文明的特例。先是儒家文明接受国日本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后是儒家文明的故乡中国的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而在中东,即使是后来接受伊斯兰教的国家,也没有抛弃伊斯兰教转而西化的迹象。因此,日本与中国在民族危机之时先后抛弃传统的最终根源,还是因为两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当然日本的神道教具有扩张与侵略的文化倾向,而贵柔守雌的道家文化更加爱好和平,从而使中日两国迥然相异)。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位儒学信徒,他本人年轻时代也熟读儒家经典,但后来他转而反儒反传统,发表《脱亚论》,成为开启明治维新的功臣。下文深入分析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培植激烈反传统的仁人志士。
自从汉代的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后来即使有儒道释三教“同源”共存的文化格局,儒家的正统地位仍然是不能动摇的。儒家不看重信仰,也不相信鬼神,孔子不说鬼神,还让人远鬼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朱熹121)。而孔子更明确表示不相信鬼神的是《论语·八佾》中的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朱熹61),像人就一定不是人,好像神在就表明了孔子压根儿就不信神。儒家另一部经典《左传》也是不信神的。《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杨伯峻1549)《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载:“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杨伯峻275)儒家非但不信鬼神,而且不以信仰为重,而是以家国社稷的振兴为第一要务。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上尤其表明这一点:“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朱熹64)在这里,孔子从道德品质的几个方面抨击了管仲,其他的缺点可以不计,然而管仲的“不知礼”甚至非礼,对于儒学却是致命的,因为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甚至后来有人将儒教称为“礼教”,那么,孔子为什么又与非议管仲的弟子子贡、子路大唱反调,认为管仲达到儒门最高的“仁”的标准了呢?唯一的理由就是管仲振兴了家国社稷,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且看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对管仲的赞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而且“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朱熹149)!
既然孔子把“仁”送给了“非礼”却给家国社稷带来巨大利益的管仲,那么以振兴中华为目的而反叛“礼教”的五四文人,不就是现代管仲吗?可以说,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家国振兴为要务,加上传统士大夫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就是“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传统动因。五四时期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一些专业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反传统并不激烈,而反传统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兴国振邦的使命感最强烈的文人。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儒家对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对于士大夫的要求却很高,要求他们在像一般百姓那样崇拜祖宗、孝顺父母、生儿育女的基础上,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家庭之祖宗香火的兴旺,而要关心家国社稷,为万民谋福。这就是“仁者,天心也”,仅仅关心小家庭与个人的宗族是不能成仁的,要想成仁成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就要强烈地忧患家国社稷与天下苍生!日本在文化上原来是中国的学生,然而在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之后,甲午战争一役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家门口打败了曾经的老师,并使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这就使得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比日本更加激烈地反传统而全盘西化,才能振兴家国社稷,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真正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以家国社稷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苗裔,只不过他们的“非礼”——反传统,表明了他们是管仲式的家国拯救者。鲁迅在《热风·三十五》中的话作为五四时代流行的观念,就表明了民族的生存比“国粹”更重要:“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第1卷306)
在现代中国,留日文人比留学英美的文人在反传统上更激进。在英美派文人中,与“昌明国粹”的学衡派相比,胡适反传统是比较激烈的,然而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留日文人相比,胡适还是显得谨小慎微。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陈独秀在响应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中则将其改正为“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本意是要提出建议而与全国学究商讨,而陈独秀则说绝无商讨之余地,并以三个“推倒”表明了反传统的决绝。后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青年进研究室,提倡整理国故,在《论国故学》中又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文集》,第2卷327)。他的这些主张都遭到了比他更为激进的留日文人李大钊和鲁迅等人的抵制。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是由留日文人主导的,后来留日文人与瞿秋白等留俄文人联手,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激进主流。
为什么留日文人要比英美派文人的反传统更激进更强烈呢?因为留日文人在内忧外患的激发下,与传统士大夫血脉相连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当中国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以西方为师法对象的时候,也正是马克思、尼采等西方哲人反叛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时候;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与西化的号角刚刚吹响,斯宾格勒已著书揭示了“西方的没落”。就在胡适、吴宓等留美前后,美国哈佛大学的白璧德立足现代的废墟,将重建西方文化的视野转向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与印度的释迦牟尼。而在胡适师法西方提倡文学改良之前,庞德(Ezra Pound)已经在师法中国倡导意象派诗歌。因此,英美派文人在英美的日子不像留日文人那样困窘,胡适就经常被请去讲演。这就是为什么英美派文人,除了胡适等个别例外,试图调和“国粹”与“西化”的原因。而当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刚刚“脱亚入欧”,一副“西方等于文明,中国就是野蛮”的傲慢姿态,他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瞧不起中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东亚病夫”。留日文人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鲁迅的《藤野先生》、郁达夫的《沉沦》、郑伯奇的《最初之课》等作品都表现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所遭受的屈辱。鲁迅在仙台的医学专业课考了及格的分数,日本学生就不依不饶,认为藤野先生漏题给鲁迅,以致鲁迅愤而离开仙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留学生在精神上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这种民族屈辱感激起了留日文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振兴中华的雄心。留日文人在深层意识中是瞧不起日本的,他们仅仅把日本看成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桥梁和窗口。日本人过去是中国的学生,现在的发达则因其全面西化与脱亚入欧而成为西方的学生,那么对于留日的中国文人现成的逻辑是: 要想超越日本,就要在西化与反传统的路上更加激进。
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五四一代文人激烈反传统的深层动因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家国社稷的振兴为第一要务的传统,以及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与忧患意识。这甚至潜在地制约着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个性解放的伦理革命为本,然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联的成功建立又使得集体主义的救国方案成为五四一代文人的文化选择。后来随着苏联建设的成功与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追求个性解放的一代文人又放弃了个性自由,投身于集体主义的救国洪流中。这都是传统的深层语法规则对新文化发生的制约与变异。因此,那些真的以为“五四”彻底抛弃了传统而全盘西化的学者,仅仅是看到了表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五四”造就的新文化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新文学虽然比起传统文学来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在语言上也更加精密化,但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世俗传统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事实上,即使在海外学者当中,也有不同意五四一代文人断裂传统造成“失语症”的人,夏志清甚至发问:“我们不禁怀疑,西方文学的研究,究竟已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了多少?”(夏志清432)
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的安定团结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从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到实现“中国梦”,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当代是越来越显著的。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文化立场批判“五四”,就像我们不能用宋代理学的立场去否定六朝对佛教的吸取,因为没有六朝对佛教的吸取就没有理学,作为新儒学的理学正是在迎接佛教挑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强调弘扬中国文化,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建构起包容西学的中国哲学—文化图式。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在西方文化没落之时,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文化又焕发出青春活力。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注释[Notes]
① 详见高旭东:“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江汉论坛》11(2016): 81—85。
② 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三种可能方案: 一是抵制(resistance);二是全盘接受(wholesale acceptance),即全盘西化;三是选择性接受(selective adoption)。对于第一种方案,胡适明确表示拒绝。对于第三种方案他在后文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这种选择性接受方案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而且是相当没必要的(quite unnecessary)。文中他还提到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On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并在1928年对这篇文章的主旨重写并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的观点是:“中国必须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和民主。”所以,胡适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是第二种方案,即全盘接受或全盘西化。见Hu Shih. “Conflict of Cultures”.《中国基督教年鉴》(第19册)(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32、134、138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独秀: 《独秀文存》。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Chen, Duxiu.CollectedWorksofChenDuxiu. Hefei: Anhui Renmin Press, 1987.]
赫伯特·戈特沙尔克: 《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阎瑞松译。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Gottschalk, Herbert.TheWorld-ShakingIslam. Trans. Yan Ruisong.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 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
[Hsia, Chih-tsing.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 Hongkong: Union Press, 1979.]
胡适: 《胡适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Hu, Shi.SelectedWorksofHu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胡适文存》。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 - -.CollectedWorksofHu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Hu Shih. “Conflict of Cultures.”《中国基督教年鉴》(第19册)。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32—41。
[- - -. “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ChristianYearBook. Vol.19.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132-41.]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7年。
[Li, Zehou.OntheHistoryofModernChineseThoughts. Beijing: Oriental Press, 1987.]
鲁迅: 《鲁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uxun.TheCompleteWorksofLu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
[Mao, Zedong.SelectedWorksofMaoZedong.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玄同卷》,张荣华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5—45。
[Qian, Xuantong. “The Issu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uture.”LibraryofModernChineseThinkers:QianXuantong. Ed. Zhang Ronghu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25-4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
[Yang, Bojun.AnnotatedZuo’s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姚鼐纂集: 《古文辞类纂》。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Yao, Nai, ed.AnthologyofClassicalPros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6.]
张潮: 《幽梦影》。青岛: 青岛出版社,2010年。
[Zhang, Chao.TheShadowofDreams. Qingdao: Qingdao Press, 2010.]
朱熹: 《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6年。
[Zhu, Xi.AnnotationstoThe Four Books. Ed. Wang Huabao.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