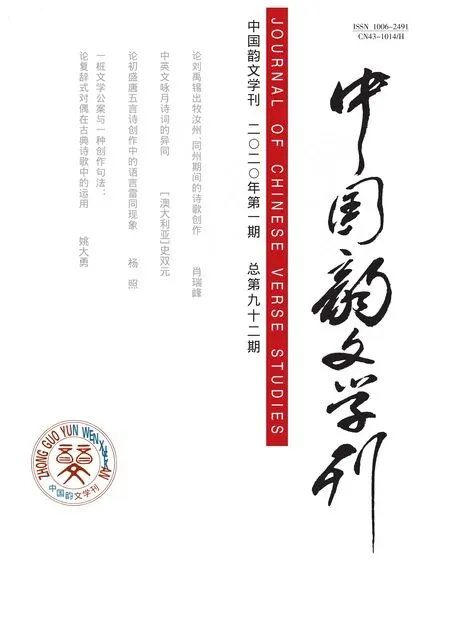论刘禹锡出牧汝州、同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2)
刘禹锡一生先后主政六个州郡,即连州、夔州、和州及苏州、汝州、同州。就中,苏州、汝州、同州在唐代均属地位相对重要、条件相对优越的“上州”,与诗人视为“谪居”之地的连州、夔州、和州不可同日而语。但诗人在汝、同二州生活的时间很短:汝州只有一年多,同州还不到一年。在血流成河的“甘露之变”使得政局更加险恶的背景下,因对国家及个人前途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终于痛下决心辞去实职,返回洛阳闲居。作为其仕途的最后两个驿站,出牧汝州、同州期间,他的心态与诗风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创作形式也不无遗憾地自囿于酬唱赠答。
一 人情冷暖:赴任途中的遭际与咏叹
大和八年(834)七月,刘禹锡自苏州奉调移任汝州(今属河南)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史。他对苏州这所自己生活了将近三年的历史名城充满了依恋之情。《别苏州二首》写道:
三载为吴郡,临岐祖帐开。
虽非谢桀黠,且为一裴回。
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
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1](P607)
碧水潺湲,翠柳飘拂,这是典型的送别环境;郡人祖饯,临岐徘徊,这也是典型的惜别场面。诗人寥寥几笔,就传达出自己与这座城市彼此间的深深眷恋。而“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这直抒胸臆的结句更将诗人的离愁别恨和盘托出。“魂销”,暗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此前曾多次来到阊门外送别,却只有今日才真的产生了“魂销”之感。这就将其对苏州的缱绻深情表现得格外真切。
不过,汝州的地理位置靠近东都洛阳和故里荥阳,这又让刘禹锡不无欣慰。在《汝州谢上表》中,他就直陈此番移任之乐:“忽降新恩,近乡为贵。”所以,离开他三载相依的苏州,他固然心有慊慊,不忍遽去,但与此同时,对履新后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生活形态他却又满怀期待。这样,赴任途中,他的心情总体上是明朗的。《罢郡姑苏北归度扬子津》其一说:
几岁悲南国,今朝赋北征。
归心渡江勇,病体得秋轻。
海阔石门小,城高粉堞明。
金山旧游寺,过岸听钟声。[1](P608)
“北征”,既是实写北归的行程,亦有以杜甫的《北征》隐然自况之意。《北征》是杜甫五言古诗中篇幅最长、享誉最盛的作品,它以忧愤国事为主旨,不仅描绘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图景,而且陈述了诗人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对复国之策的建议,表达了平乱在即、中兴在望的热情期盼。“今朝赋北征”,说明刘禹锡认为自己对国事的关切差可比肩老杜。正因为内心的希望之火再度燃起,所以“归心渡江勇,病体得秋轻”的愉悦之感才会油然而生。
途经扬州时,诗人受到了时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接待。但接待过程中,牛僧孺自负权高威重,咳唾成珠,表现出酒后的极度轻狂。他即兴赋《席上赠汝州刘中丞》一诗,重提自己当年被刘禹锡“飞笔涂窜其文”的不快往事,妄称“曾把文章谒后尘”,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度尽劫波的刘禹锡无意反唇相讥,在《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一诗中,他刻意放低身段,以平淡的语调强化他与对方今日的尊卑之分。诗的尾联说:“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1](P609)貌似卑躬屈膝,实则深蕴气骨:旧日之冠剑虽在,今日之颜面尽失,唯有静待牛氏入相后像拂去尘埃一样将自己罢免。其言外之意是,如果你想挟公权以报私怨的话,尽可以将我罢免,我自岿然不动,静观其变!在故意呈现的弱者之姿中潜匿着真正的强者之风。[2](P107-108)
关于刘禹锡的这次扬州之行,《全唐诗》卷868 另有一则荒诞不经的记载:大司马杜鸿渐命“二乐妓侑觞”,禹锡醉吟一绝,即所谓“司空见惯”诗也。时隔二年,禹锡携二妓赴京,夜宿邸中,“二妓和其诗”,且执板唱道:“花作婵娟玉作妆,风流争似旧徐娘。夜深曲曲弯弯月,万里随君一寸肠。”这是援《云溪友议》之余绪而加以发挥,虚构出一段更见曲折浪漫的风流佳话。非唯时间不合,人物与情节也多有乖戾之处,只能作为茶余饭后聊以消闲的谈资。
如果说扬州的刘、牛之会让刘禹锡颇为不快的话,那么经由汴州时他与李程的相聚则要融洽欢乐得多了。李程时任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是刘禹锡多年心契的知交之一。巧合的是,刘禹锡几次转任,都行经他驻跸之地,两人得以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畅叙契阔。刘禹锡这次创作的诗篇是《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
长安旧游四十载,鄂渚一别十四年。
后来富贵已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
初逢贞元尚文主,云阙天池共翔舞。
相看却数六朝臣,屈指如今无四五。
夷门天下之咽喉,昔时往往生疮疣。
联翩旧相来镇压,四海吐纳皆通流。
久别凡经几多事,何由说得平生意。
千思万虑尽如空,一笑一言真可贵。
世间何事最殷勤,白头将相逢故人。
功成名遂会归老,请向东山为近邻。[1](611)
同样是“追思前事”,感怀旧游,却既无虚情假意的客套,更无唇枪舌剑的揶揄,有的是仕历六朝而幸存至今的惺惺相惜之意和久别重逢、把酒言欢的心心相印之感。此外,还有对自身节操的肯定和对李程政声的赞扬。“后来富贵已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意谓后来居上而享有荣华富贵者纷纷零落成泥,只有自己等少数贞刚忠直之士犹如岁寒而不凋的松柏一样依旧卓然独立。这与其说是庆幸屡遭劫难而犹健在,不如说是借以写照自己不畏风霜雨雪的节操。“夷门”以下四句转为称美李程。“夷门”,本为战国时魏都城的东门,其故址在汴州城内东北隅的夷山之上,故名。后代常以夷门作为汴州(今河南开封)的代称。夷门既是扼天下咽喉之战略要冲,又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闻名,但以往却因施政不善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幸赖李程等贤臣相继前来镇守,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才形成今日“四海吐纳皆通流”的欣欣向荣局面。“久别”以下八句抚今思昔,无任感慨。阔别以来,又经历几多坎坷?但个中滋味却无从说起;万千心事尽付劫灰,唯有眼前的老友最堪珍惜!于是,诗人在篇末倾吐了归老后卜邻于东山的热切愿望。
二 寄意酬唱:萧散闲适之际的无奈与不甘
汝州,西临古都洛阳,东望黄淮平原,历史悠久,物产丰饶,民生富足,公务亦不及苏州烦冗,所以刘禹锡在汝州的生活相对比较清闲和安逸。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以酬唱赠答为主,而酬唱的主要对象则是获任东都留守不久的裴度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白居易。《酬乐天闲卧见寄》一诗写道:
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
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
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1](P627)
诗人先用“散诞”二字形容自己眼下的生活状态,又以一个“闲”字对其加以强化与固化,至于身处这种生活状态,是幸抑或非幸?诗人并未点明。揆以常情,应当是在萧散闲适中又糅合着几分无所作为的不甘与无奈。“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看似自得其乐,其实不过聊以自遣。“风碎”一联,造语奇拗,铸境健峭,颇堪玩赏,而诗人自身玩赏“竹间日”与“池底天”的悠然情态也宛然在目。“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改用谐谑口吻,自嘲之所以尚未归隐,是因为囊中羞涩,缺乏购置山林的资金。全诗笔法多变,摇曳生情。
在写于汝州的酬唱赠答之作中,最耐人讽咏的是《答杨八敬之绝句》:
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
今日知音一留听,是君心事不平时。[1](223)
题下自注:“杨时亦谪居。”杨敬之,字茂孝,元和初登进士第。据《旧唐书·文宗纪》下:大和九年七月,时任户部侍郎杨敬之受牛李党争之累被贬为连州刺史。连州为刘禹锡谪居旧地,当杨敬之将蹈袭他当年之足迹,去岭南烟云深处体验罪臣生涯时,种种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浪涌潮奔般俱上心头,迫使他重新审视当年的生活与创作。“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这与其说是对杨敬之原唱的形象概括,不如说是对自己流徙巴山楚水期间的创作的艺术写照。换言之,这实际上是“夫子自道”,是借友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杨敬之的原唱已佚,今日无从把玩,但想来当也是情辞激愤,于是引发了刘禹锡的强烈共鸣,使其从语言和思想仓廪中攫取合适的材料,熔铸成“饱霜孤竹”和“带火焦桐”这两个深蕴气骨的意象,寄托自己顾思前尘往事时的耿耿怀抱,充满不平之鸣。“今日知音一留听,是君心事不平时。”诗人自托为知音,甫一倾听,便察见了杨氏原唱中包孕的无限心事,而所有的心事汇聚到一起,只有蔽之以“不平”二字。这固然是为杨氏鸣冤,又何尝不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曾经蒙冤受屈的志士仁人发出如“饱霜孤竹”“带火焦桐”般悲怆入骨的不平之鸣?
《送廖参谋东游二首》则是这一时期的送别诗中较值得注意的作品:
九陌逢君又别离,行云别鹤本无期。
望嵩楼上忽相见,看过花开花落时。
繁花落尽君辞去,绿草垂杨引征路。
东道诸侯皆故人,留连必是多情处。[1](617)
前一首以“行云别鹤”比喻各自的宦游生涯,已漾出聚散无定的悲慨。而“看过花开花落时”,既是嗟叹阔别时间之长,也是感慨几经沧桑,看够了人间衰荣。后一首开篇即云“繁华落尽”,一方面是点明时值众芳摇落的暮春季节,另一方面亦暗寓盛世已去、中兴无望的隐忧。和诗人早年的同类作品相比,少了一些豪雄之风,而多了几分沉郁之气。
三 甘露之变:最后一丝政治幻想归于破灭
大和九年(835)十月,在汝州度过了一年多相对安定的生活后,刘禹锡奉敕改官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岛防御、长春宫等使。本来,这个职位是授予白居易的,但此时的白居易已决意远离政务、闲逸终老,所以托病固辞不拜。朝廷只好另觅替代人选,于是刘禹锡便进入视野,“李代桃僵”。
刘禹锡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一任命,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依然留守东都的裴度新加中书令衔,让刘禹锡产生了他有可能东山再起、重掌政柄的误判。在去同州赴任途中,他经由洛阳,与白居易、裴度、李绅相聚。此时,他犹心存幻想,《两如何诗谢裴令公赠别二首》泄露了其中消息:
一言一顾重,重何如。今日陪游清洛苑,昔年别入承明庐。
一东一西别,别何如。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1](P624)
第一首以“昔年别入承明庐”作结,颇有深意。“承明庐”,本为汉代承明殿之旁屋,乃侍臣值宿时的居所。后代便以“入承明庐”作为入朝为官的典故。这里,诗人在“陪游清洛苑”之际,刻意提及“别入承明庐”之往事,显然意在勾起裴度对当年叱咤风云的显宦生涯的回忆,而萌生卷土重来的愿望。如果说这层意思在第一首中还表达得非常含蓄的话,那么,在第二首中它则几乎演变为不加掩饰的直白了:“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他多么希望能借助裴度出山掀起的政治旋风,扶摇直上,翱翔于九霄之中。
政治经验远比刘禹锡丰富的裴度却早已心如灰烬。如果说刘禹锡尚处在“死火余温”“死水微澜”的半明半灭状态的话,那么,裴度内心深处则已燃尽最后一点火花,再也产生不了热能了。他预感到朝廷中有可能爆发更严重的祸乱,所以不得不用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独有的方式给刘禹锡降温,使刘禹锡在瞬间上升到沸点的政治热情转瞬又骤降到冰点。在《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联句》中,他明确表态说:“不归丹掖去,铜竹漫云云。唯喜因过我,须知未贺君。”[1](P622)这等于告知刘禹锡,无论是限于客观条件还是本于主观愿望,他都绝不可能重回朝廷、重振纲纪了。他希望刘禹锡明白他的态度后能变得更加清醒,早日全身而退,加入“洛阳之会”的行列。果然,如同裴度所预见的那样,裹挟着血雨腥风的“甘露之变”就发生在刘禹锡离开洛阳赴同州就任的途中。
此时君临天下的唐文宗李昂倒是个见贤思齐、崇尚节俭的仁君。即位之初,他便致力革除奢靡之风,敕令放还部分宫女和教坊乐工,停废“五坊小儿”,禁止各地的额外进献。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饮食从不铺张,当各地发生灾荒时,他更是主动减膳。就个人兴趣而言,文宗不喜欢声色犬马,听政之暇,唯以读书为乐。他精熟古典,对当代诗文名家名篇也饶有兴趣。这样一位被史书誉为“恭俭儒雅,出于自然”的仁君却有着先天的严重不足:他是由宦官所拥立,登基时即已大权旁落,以后也就处处为宦官所掣肘,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政。早在大和二年(828)三月,文宗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进士刘蕡在对策中直陈宦官专权之弊,将天下倾覆、国家动乱、生灵涂炭尽皆归因于宦官专权的结果。同时,对藩镇割据、朋党倾轧所造成的危害,他也放言无忌。一时朝野震惊,群小侧目,掀起轩然大波。文宗颇以刘蕡所论为是,但迫于来自以宦官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只得弃用鹤立鸡群的刘蕡,违心地让他落选,但刘蕡向他灌输的治国理念却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田。他试图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寻找合适的时机,给擅权已久的宦官势力以致命一击。
大和四年(830),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合议秘密铲除宦官势力,但因时机尚不成熟,计划胎死腹中。其后,文宗又反复物色可以共谋大计的股肱之臣,终于选定郑注、李训。他们分别以精通医术和熟知《周易》而得以进用,都善于窥测运势,把握机遇,揣度人心,又兼才思敏捷,口齿伶俐,所以深得文宗欢心。大和九年(835),误判形势的文宗及郑注、李训以为羽翼已丰、时机已到,便果断地向宦官势力“亮剑”。血流漂杵的“甘露之变”由此引发。事情的结局是,草率行事的李训的“阴谋”完全败露。掌管神策军的宦官头目仇士良等迅即调兵遣将,对宰相和朝官痛下杀手。李训、郑注及王涯、王璠、贾餗等重要朝官全遭诛杀,罹祸者达几千人以上。这就是唐王朝历史上令文武百官闻风丧胆的“甘露之变”。它以伏诛宦官为初衷,却以屠戮朝官为结局。朝官与宦官的又一次较量,依然以朝官的惨败谢幕。
“甘露之变”的发生,使刘禹锡对政局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他一方面钦佩裴度不愿重新出山的先见之明,一方面则庆幸自己因离京外任而免遭无妄之灾。政坛机弩四伏,仕途风险丛生,这时他才意识到白居易托疾辞任同州是明智的选择。他真想卸却簪缨,折返洛阳,与早已赋闲的裴度、白居易一同,在兴味无穷的“文酒之会”中了此余生。然而,君命岂同儿戏,既已衔命赴任,又怎能中道变卦?刘禹锡只得继续已被他视为畏途的同州之旅。但内心已暗自决定,一旦时机合适,就告病归隐,绝不恋栈。
这时,他的诗歌创作也悄然开始发生变化,有意无意地回避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当实在无法回避时,则竭力遮蔽自己的真实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就以他对“甘露之变”的反映而言即如此。这一举国震惊的恶性事件,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留下了历史记录,如杜牧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李甘诗》,李商隐的《有感》《重有感》,白居易的《咏史》《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等等。刘禹锡自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回避这一事件。一般认为,他的《有感》一诗即为悼念在“甘露之变”中遇难的朝官王涯、贾餗等人而作,但诗意之隐晦、措辞之轻淡,与他惯常的风格做派形成较大的反差: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
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
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
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1](802)
王、贾都是因“城门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鱼”。起句“死且不自觉”,意谓王、贾等人对突然降临的杀身之祸毫无预感,依稀有惜其无辜遇害之意,却不敢公开为其鸣冤叫屈。“骑吏”二句写宦官统帅的禁军在京城中纵横隳突,尘埃未息,以致出殡的灵幡随处可见。这似乎是谴责,但若非深究细察,其意亦不明显。“平生”二句写王、贾宠妾泣于黄昏时分,若含怜悯,但如果想到他在讽刺武元衡之死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中有“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的类似描写,其情感指向如何,也难辨别。诗人对“甘露之变”的态度本来是并不暧昧的,但形之于诗,却有些暧昧莫名了。这恰好昭示了其创作倾向开始转变的信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年二十四岁的李商隐的同题之作倒是显得态度明朗,直言不讳: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队,兵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3](108)
不仅将滥杀无辜的宦官指斥为“凶徒”,而且在余波未平之际重提“清君侧”这一令人闻声色变的话题,显示出初生牛犊的虎虎生气。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确实如此。而李商隐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岂不反衬出禹锡转型之际的暧昧其词、明哲保身?
不过,早年同样“激切言事”的白居易此时的态度也与刘禹锡相仿佛。他的《咏史》一诗写道: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
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
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4](P2333)
将执着用世而惨遭“刀斩”和“鼎烹”的李斯、郦食其与隐居深山、闲卧白云的商山四皓相比照,揭示出两种人生态度与人生结局的巨大差异:一为“菹醢机上尽”,死于非命;一为“鸾凰天外飞”,畅享自由。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显然是:与其用世而遭祸殃,不如避世而得逍遥。诗题下作者自注“九年十一月作”,分明是借咏史之名,抒发因退居洛阳而免遭“甘露之变”殃及的庆幸之情。诗中略无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评价,既不是此,亦不非彼,全然置身局外,政治态度显得十分模糊,与刘禹锡的《有感》如出一辙。两相参照,有理由认为,这群历尽坎坷的老臣在面对又一次政治风波时相约集体噤声,以求全身远祸。
四 去意已决:与残酷的现实政治彻底疏离
刘禹锡于十二月初抵达同州(今陕西大荔)。同州居晋、陕要冲,境内三水环流,土地肥沃。但天公作祟,连续四年遭遇旱灾,抗灾救灾成为刘禹锡到任后的当务之急。他从朝廷申请到六万石救济粮及适度减免赋税等其他优惠政策,去其旧弊,立其新规,使民众安于畎亩,免于流离。他在《谢恩赐粟麦表》中说:
伏奉今月一日制书,以臣当州连年歉旱,特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并赐斛斗六万石,仰长吏逐急济用,不得非时量有抽敛于百姓者。[1](1211)
可知他在争取资源与政策支持及后续的生产自救方面是竭尽全力的。这与以往治郡时无异。不同的是,对仕宦生涯越来越心灰意冷,越来越怀疑自己固守理想究竟有何意义?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中。而当他走出迷惘时,他已经以决绝的姿态与官场揖别:在同州未曾任满一年,刘禹锡便于开成元年(836)秋,以足疾发作为理由向朝廷递交了辞呈。
主政同州期间,刘禹锡的诗歌创作虽未间断,但为时既短,又笼罩在“甘露之变”的阴影中,还因赈灾而牵制精力,所以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不能尽如人意。而且,几乎都是为酬唱赠答而作——事实上,当酬唱赠答成为唯一的创作动因时,作品的思想饱和度及艺术生命力就必然要打折了。
就中,《酬郑州权舍人见寄十二韵》要算是相对出挑的作品了:
朱户凌晨启,碧梧含早凉。
人从桔柣至,书到漆沮傍。
抃会因佳句,情深取断章。
惬心同笑语,入耳胜笙簧。
忆昔三条路,居邻数仞墙。
学堂青玉案,彩服紫罗囊。
麟角看成就,龙驹见抑扬。
彀中飞一箭,云际落双鸧。
甸邑叨前列,天台愧后行。
鲤庭传事业,鸡树遂翱翔。
书殿连鳷鹊,神池接凤凰。
追游蒙尚齿,惠好结中肠。
铩翮方抬举,危根易损伤。
一麾怜弃置,五字借恩光。
汝海崆峒秀,溱流芍药芳。
风行能偃草,境静不争桑。
转旆趋关右,颁条匝渭阳。
病吟犹有思,老醉已无狂。
尘满鸿沟道,沙惊白狄乡。
伫闻黄纸诏,促召紫微郎。[1](P629)
诗的主要篇幅用于忆旧,但在对旧日情谊的追述中,时时可以察见诗人不经意流露的身世之感和屈从于残酷现实的无奈喟叹。“铩翮方抬举,危根易损伤”,诗人已有过多次“铩翮”的惨痛经历,而今又处于“势偏根危”的险恶境地,极易受到伤害。融入其中的分明是对随时有可能到来的不测之祸的隐忧。“风行能偃草,境静不争桑”,看似纯属景物描写,实际上讽兼比兴,糅合着诗人从自身遭际中领悟到的人生哲思:劲风吹处,必有草木偃伏;与世无争,才能心境平和。“病吟犹有思,老醉已无狂”,尽管病中吟哦,诗思不减当年,但身入老境,即便醉后也已不会呈现狂态、倾吐狂言。这是自解、自嘲,还是自叹?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从中感触到的是诗人准备随俗俯仰的不甘与无奈。
《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盐铁使院中作》一诗风格较为清新,不像前诗那般沉重:
柳动御沟清,威迟堤上行。
城隅日未过,山色雨初晴。
莺避传呼起,花临府署明。
簿书盈几案,要自有高情。[1](P633)
但即使在酬唱赠答之作中,它也绝非上品。诗题中的几个关键词“春”“早朝”“回盐铁使院”倒是逐一通过景色描写得以示现,而景色描写与人物的特定身份、特定境况、特定做派也相当吻合。“莺避传呼起,花临府署明”,既点染出花鸟之精神,又暗示了其衙署之气势和其人回衙时之威仪,不乏可玩味之处。结句称赞令狐氏虽不免案牍劳形,却高情未减,依旧醉心于吟章弄句一类雅事。
《奉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书》一诗以工稳的对句和严密的章法表现裴度的闲适情怀和自己的退隐意向,是这一时期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蔼蔼鼎门外,澄澄洛水湾。
堂皇临绿野,坐卧看青山。
位极却忘贵,功成欲爱闲。
官名司管钥,心术去机关。
禁苑凌晨出,园花及露攀。
池塘鱼拨剌,竹径鸟绵蛮。
志在安潇洒,尝经历险艰。
高情方造适,众意望征还。
好客交珠履,华筵舞玉颜。
无因随贺燕,翔集画梁间。[1](P628)
“绿野堂”,是裴度耗费一生积蓄构筑于洛阳午桥的别墅。据《新唐书·裴度传》载,裴度因宦官专权,“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5](5218)。裴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等为文酒之会,“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绿野堂初成规模时,裴度欣然赋诗,众人奉和,身在同州、暂时不能躬逢盛会的禹锡也以此诗致贺。除尾联外,其余九联均以对偶句构成,“两两相形,以整见劲”。在诗人的想象中,绿野堂应是碧草盈畴,青山弥望,鱼跃池塘,鸟语竹径。因为没有亲历亲见,他只能对绿野堂的布局与设施做粗略的勾勒和浮泛的描摹,诗的大半篇幅用于刻画裴度“位极却忘贵,功成欲爱闲”的高士风范。但与此同时,诗人也有意点出,裴度这种心无机关的极度“潇洒”,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历尽“险艰”后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明智选择。这就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其“高情”后的隐曲。“无因随贺燕,翔集画梁间”,结尾处憾恨自己不能与春燕一同前往祝贺,在雕廊画栋间一窥其文采风流,将不可抑制的欣羡之情与追随之意一并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