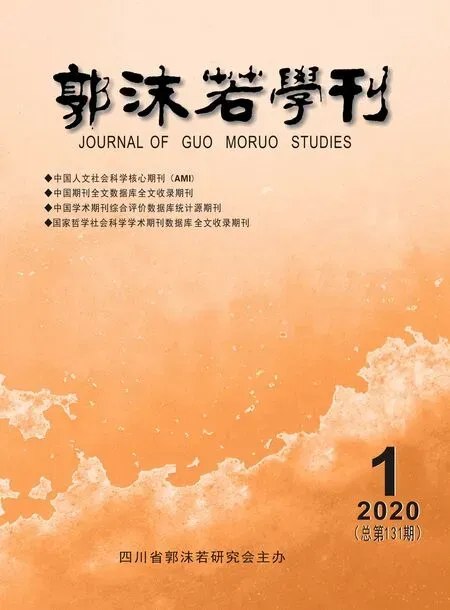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的版本与修改
乔世华 乔雨书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1)
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最早对“儿童文学”做出界说并明确提出“儿童本位”,同时阐述了儿童文学本质及建设路径。该文最初发表在1921年上海《民铎》杂志第二卷第四号上,后又收录在郭沫若第一部文艺批评论著《文艺论集》中。《文艺论集》在不同时期出版单行本或并入合集时,郭沫若均对书中具体篇目和文章内容做过程度不同的增删修改,因此该书先后有过多个版本,如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初版本、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订正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沫若文集》第十卷等。以不足五千字的《儿童文学之管见》来说,也因多次修改而实际上先后形成了《民铎》版、光华初版本、光华订正本和《沫若文集》本这样四个文字表述不尽相同的版本。我们恰可以透过这篇文章历次修改而形成的诸种“异文”,发现郭沫若三十多年间在诸种人事尤其是文艺相关问题认识上的历时性变化。
一
《儿童文学之管见》在《民铎》杂志最初发表时,文章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国内对于儿童文学,最近有周作人先生讲演录一篇出现,这要算是个绝好的消息了!”①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显见此文的写作是对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平孔德学校的演讲《儿童的文学》的一种积极回应。但在1925年光华初版本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中,这一句话均被删掉。个中缘由值得细细推敲。
据咸立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可知,郭沫若在翻译问题的认知上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发生龃龉正是在写作《儿童文学之管见》前后。《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0月10日在刊发周作人译作《世界的霉》、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郑振铎译作《神人》等几篇作品时是依照周作人、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的顺序排列先后的,这引起了郭沫若的不平,遂在1921年1月上旬(略早于1921年1月11日《儿童文学之管见》的写作时间)致编者李石岑的信件中有“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感慨,并主张“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①郭沫若:《通讯》,《民铎》1921年2月15日第2卷第5号。。可见,写作《儿童文学之管见》时,郭沫若已经因翻译问题对周作人等心存芥蒂了。当1921年6月10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认为郭沫若的这一说法“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郭沫若即迅速反应,在致郑振铎的信件中表态:“有的说创作不容易,不如翻译(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有的说中国人还说不到创作,与其嚣嚣焉空谈创作,不如翻译(耿济之《甲必丹之女》序文中有这么意思的话);像这样放言,我实在不敢赞可。”②“郭沫若致郑振铎信”,《文学旬刊》1921年第6期,转引自咸立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1925年前后正是郭沫若思想发生巨变时期,正如其在《〈文艺论集〉序》中所表示的那样:“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罢。”③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第1页。1924年,郭沫若翻译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是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是非常感谢。”郭沫若由是“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④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1926年1卷2期。。职是之故,获得思想新生的郭沫若不愿意再在自己文章中提到周作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此可相印证的是郭沫若对《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的修改。该文最初在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篇末曾有一段长文字介绍了写作缘起,其中特别点明此文与沈雁冰之间的精神联系并对沈雁冰表示出相当敬意:“我这篇文字的动机,是读了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而感发的。雁冰君答复我的这篇评论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很钦佩”,“雁冰君的答辩,本来再想从事设论,不过我在短促的暑假期内,还想做些创作出来,我就暂且认定我们的意见的相违,不再事枝叶的争执了。我们彼此在尊重他人的人格的范围以内,各守各的自由。”⑤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见黄淳浩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但在《文艺论集》1925年光华初版本以及后来的各版本中,这段说明文字也同样被删掉。再联系稍后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对被他们视为落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沈雁冰等人的批评和攻击这一事实来看,郭沫若自从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就已经不愿意再在文中和周作人、沈雁冰等落伍的新文学权威出现思想互动了。
不过,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实际上所发生着的密切精神联系,是无可否认的。比如,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中有如是表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⑥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8卷第4号。。郭沫若在文中也有类似说法:“儿童与成人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状态,相差甚远。儿童身体决不是成人之缩形,成人心理亦决不是儿童之放大。”⑦郭沫若:《通讯》,《民铎》1921年2月15日第2卷第5号。再者,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实际上为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开出了创作、收集和翻译这三种方法,比较而言,他更看好收集和翻译这两种方法,并用大量篇幅论及此,如:“童话也最好利用原有的材料,但现在的尚未有人收集,古书里的须待修订,没有恰好的童话集可用。翻译别国的东西,也是一法,只须稍加审择便好。”①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8卷第4号。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同样依次提到了“收集”、“创造”和“翻译”这三种方法,只是他并不像周作人那样看好翻译:“太偏重翻译,启迪少年崇拜偶像底劣根性,而减杀作家自由创造底真精神。翻译亦不可太滥。欧人底儿童文学不能说篇篇都好,部部都好,总宜加以慎重的选择。并且举凡儿童文学中地方色彩大抵浓厚。译品之于儿童,能否生出良好的结果,未经实验,总难断言。所以我的主张还是趋重于前的两种。”②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
二
《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提到了华兹华斯、泰戈尔、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一些外国作家或其作品,如举说华兹华斯《童年回忆中不朽性之暗示》、泰戈尔《婴儿的世界》等以说明“儿童文学不是些鬼话桃符的妖怪文字”,“儿童文学底世界总带神秘的色彩”③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等。《沫若文集》本全部删去原来所引的华兹华斯的诗歌和泰戈尔诗歌的外文部分而只保留中文译文,这应该是考虑到方便读者阅读的因素。至于《民铎》版译文中“位置”、“束缚”等词语在《沫若文集》本译文中改作了“地位”、“羁缚”等,或可显示出郭沫若在翻译时措辞上的用心。
当然,在涉及到对华兹华斯、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外国作家作品的“评价”时,《沫若文集》本做出的些许改动,是可以显示出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对上述作家的新认识的。
比如在谈到收集童话童谣的必要性的同时,郭沫若提到了两首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谣曲:
大家必吟诵起这两首谣曲起来,那时底幸福,真是天国了!如今呢,回忆起来,不容不与瓦池渥斯起同样的哀感!(《民铎》版)
有时会顺口唱出这些儿歌来,那时候的快乐,真是天国了!(《沫若文集》本)
郭沫若早期对华兹华斯是甚为欣赏的,譬如其在《三叶集》中对诗歌有这样的看法:“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④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7页。。这与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的认知正相吻合:“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⑤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2页。删掉与华兹华斯有相同感受的文字,保持和他的情感距离,这应该与华兹华斯等诗人在社会主义国家被贴上“消极浪漫派”的标签有关。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中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有严格的区分:“在浪漫主义里面,我们必须分别清楚两个极端不同的倾向:一个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相妥协;或者就使人逃避现实,堕入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无益的深渊中去,堕入到‘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堕入到不能用‘思辩’,直观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由科学来解决的谜之中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⑥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戈宝权译,上海:读书出版社,1946年,第7-8页。1949年以后,国内学界也都紧紧跟随这种说法,如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文艺报》1949年1卷4期)、晴空《我们需要浪漫主义》(《诗刊》1958年6期)、朱光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3期)等,都普遍认为作为消极浪漫派的华兹华斯站在与历史相抗衡的立场上迷恋过去生活,“厌恶革命”⑦朱光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是他的标签。在革命浪漫主义被肯定和提倡的1958年,郭沫若虽说敢于坦白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了⑧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中表示:“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但是不愿意再和华兹华斯这样的消极浪漫主义者保持声气相通,也是情理中事。
同样的,梅特林克的《青鸟》、霍普特曼的《沉钟》等象征派戏剧在1949年之后声名不佳,郭沫若也要避免和他们发生关系。在《民铎》杂志版、光华初版本、光华订正本等20年代几个版本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中,郭沫若还对他们有这样不加掩饰的赞赏:“梅特林底《青鸟》、浩普特曼的《沉钟》最称杰作”①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其1920年与宗白华、田汉三人之间通信集成的《三叶集》中就多次提及带有典范色彩的梅特林克《青鸟》、霍普特曼的《沉钟》,表现出明显的称赏态度来:“你若果能把我们做个Model,写出部《沉钟》一样的戏剧来,那你是替我减省了莫大的负担的呀!”②郭沫若:《郭沫若致田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6页。而在《沫若文集》本中,郭沫若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正面评价换成不动声色的客观事实的描述:“我看过梅特林克的《青鸟》、浩普特曼的《沉钟》”③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4页。,以此与这些不入时人眼的作家及作品保持着谨慎的距离。
三
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效用时,《民铎》版如是说:
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非常宏伟之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入于醇美的地域;更能启发其良知良能——此借罗素语表示时,即所谓“创造的冲动”,——达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之境。是故儿童文学底提倡对于我国彻底腐败的社会,无创造能力的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
光华初版本、光华订正本都与《民铎》版保持一致。《沫若文集》本则将原先对社会和国民显示着强烈绝望和批判色彩的词语如“彻底腐败的”、“无创造能力的”等尽数删除:
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借罗素的话表示时,即所谓“创造的冲动”,敢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
虽说这种改动可能会令后面的“起死回春”显得突兀和失去依据,但整体表达在语气上和缓了许多,不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这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许还意味着郭沫若在解放后文化精英立场的某种退隐。
而与此相关联的是,郭沫若也一并矫正了早期对民间文艺的轻视态度。《民铎》版在谈到儿童文学的“创造”这一路径时,对在民间流传的童话、童谣等的艺术价值和收集者所能取得的成效是抱持怀疑态度的:
此种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学家之创造自无待言,如童话、童谣等体裁,我国旧有的究竟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尚是疑问,采集的人更要具有犀利的批评眼才行。将来的成果如何,究竟不能预料;那么还是有待于新人底创造了!不过创造的人总不要轻于尝试,总要出诸郑重,至少儿童心理学是所当研究的。
光华初版本和订正本的有关表述除了个别文字有变动外,也都和《民铎》杂志版相同。郭沫若彼时之所以期待新人创造,实在缘于其对民间文艺的信心不足。《沫若文集》本则删除掉此类表态:
此种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学家的创造。童话、童谣,除旧有的须迅速采集而严加选择外,还是有待于新人的创造。创造的人希望出诸郑重,至少儿童心理学是所当研究的。(《沫若文集》本)
《民铎》版中,郭沫若在提到自己印象深刻的两首谣曲时,毫不留情地对其他谣曲给出了负面评价,《沫若文集》本则力避感情用事般的评价:
我所能记忆的谣曲,有价值的只上两首,此外虽还记得些,但都鄙陋无可言。(《民铎》版)
我所能记忆的儿歌,比较有价值、留在记忆里的只这两首。(《沫若文集》本)
郭沫若对《儿童文学之管见》做修改的1958年,正值这样一个大背景:“全面搜集民歌及其他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件必须全党、全民动手的工作,同时必须动员和吸引全体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工作”,“我们的诗人一定要深入工农群众,和群众一同劳动,一同创作,向民歌学习,向优良传统学习”①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艺报编辑部编:《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3页。。更何况,郭沫若对民间文艺的态度早在这之前就已有变化。1950年,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意识到了“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②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页。,所以郭沫若在修改涉及到民间文艺话题的旧作时,就竭力消除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而对事实进行客观陈述。
四
在正式进入对儿童文学的论述之前,《民铎》版首先谈到了对文艺上功利主义和唯美主义之争的看法:
文学上近来虽有功利主义与唯美主义——即“社会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论争,然此要不过立脚点之差异而已。文学自身本具有功利的性质,即彼非社会的Antisocial或厌人的Misanthropic作品,其于社会改革上,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就此效果而言,不能谓为不是“社会的艺术”。他方面,创作家于其创作时,苟兢兢焉为功利之见所拘,其所成之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艺术且不成,不能更进其为是否“社会”的或“非社会的”了。要之就创作方面主张时,当持唯美主义;就鉴赏方面言时,当持功利主义:此为最持平而合理的主张。
光华初版本和光华订正本也都对此没有做什么大的改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其后更长一段时间里,郭沫若都声明“我更是不承认艺术中会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③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第267页。。在他看来,文学本身是兼有功利性与唯美性的,即使是包括“非社会的”和“厌人的”作品等在内的那些唯美主义作品,也都会因为有益于社会改革或人性提高而具有功利性。显然,郭沫若有要调和融通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文艺观念的意图。因此,20年代的郭沫若主张就作者一面而言,创作时要以唯美为追求,这样才能创作出“深刻动人”的作品;主张就读者一面而言,鉴赏时要持功利主义态度,如是方能受益。
《沫若文集》本中,郭沫若对此段文字做了较大程度的修订,将“社会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争置换为了更为明确的“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争:
文学上近来虽有“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之争,这是强加分别的,究竟谁是人生派,谁是艺术派?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味的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创作家于其创作时,苟兢兢焉为个人的名利之见所囿,其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艺术且不成,不能更进论其为是否“人生”的或“艺术的”了。要之,创作无一不表现人生,问题是在它是不是艺术,是不是于人生有益。
显见,郭沫若修正了自己早先关于艺术和人生关系的认知,他更愿意强调文学的“人生”性,强调艺术之于人生的意义,而不愿意再像早年那样做一个艺术观念的调和派。
五
比较而言,光华初版本、光华订正本和光华改版本对《民铎》杂志原刊文章的修改都不太大,这可能同《文艺论集》出书时间与文章发表时间相去不是太远、郭沫若思想变化还不是很大有一定关系;而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世事的变化之后,已是花甲之年的郭沫若在修订编辑《沫若文集》时对于文学艺术的认知和表达更加趋于沉稳。更何况,1950年代以后的郭沫若是身兼数职的重要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身份的变化,使得其在对文学艺术的言说上必须要更加慎重,不可能太随心所欲了,因此《沫若文集》本在措辞上所发生的变化,有不少都是为了表达的圆满稳妥。
早先《儿童文学之管见》成文时确实有不够缜密的地方,如对宗教画中耶稣肖像的描述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沫若文集》本遂有了更精准的表达:
欧洲古代画家未解解剖学之重要,宗教画中之耶稣肖像大抵皆为成人之缩形,吾希望我国将来的儿童文学家,勿更蹈此覆辙。(《民铎》版,光华初版本)
欧洲古代画家未解解剖学之重要,宗教画中之幼年耶稣肖像大抵皆为成人之缩形,吾希望我国将来的儿童文学家,勿更蹈此覆辙。(光华订正本)
欧洲古代画家未解解剖学之重要,宗教画中的婴儿耶稣大抵是成人之缩影,我国画家和雕塑家也有这样的毛病。(《沫若文集》本)
而且,郭沫若早先并未对我国画家雕塑家有所批评,《沫若文集》本中则指出中国画家和雕塑家也都存在这种艺术上的通病,这可能意味着此时郭沫若对本土精英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有了更多了解,产生了新的认识,才会下此断言。
又如《民铎》版认为“儿童文学中采取剧曲形式底表示者,在欧洲亦为最近的创举,我国固素所无有也”①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沫若文集》本则改为“儿童文学采取剧曲形式,恐怕是近代欧洲的创举”②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页。,不再就我国是否有剧曲进行判断,如是避免了无谓延伸有可能带来的表达上的疏漏。再如在谈到人的改造要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时,《民铎》版最初是这样申说的:“所以改造事业底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这决不是故意夸张,借以欺人弄世之语。”③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光华初版本、光华订正本也都没有变化,《沫若文集》本则删削了一些冗赘文字,直接将这段话改作:“因而改造事业的组成部分,应当重视文艺艺术。”④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页。《民铎》版中,郭沫若对儿童文学翻译这条路径显得不是特别看好,因而说“译品之于儿童,能否生出良好的结果,未经实验,总难断言”⑤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在《沫若文集》本中则改为“尚难断言”⑥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4、148、155页。,虽只是一字之易,但在表达上更无懈可击,至少对翻译并非毫无信心。
事实上,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对《儿童文学之管见》的修改,不但反映着他一个人思想或性情上的变化,更是有代表性地反映着“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中左突右进时的心灵挣扎。值得提及的是,历经世事沧桑的郭沫若对诸种文艺事项在认知上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但其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几个版本只是在个别字词上略有差异):“儿童文学无论其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溯于其精神堂奥者,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像与感情之艺术。”⑦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赤子之心的诗人也许唯有在面对至为质朴本真的儿童文学时,才心无挂碍、没有那么浓重的人间烟火气,而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遂成为郭沫若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莫大贡献,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