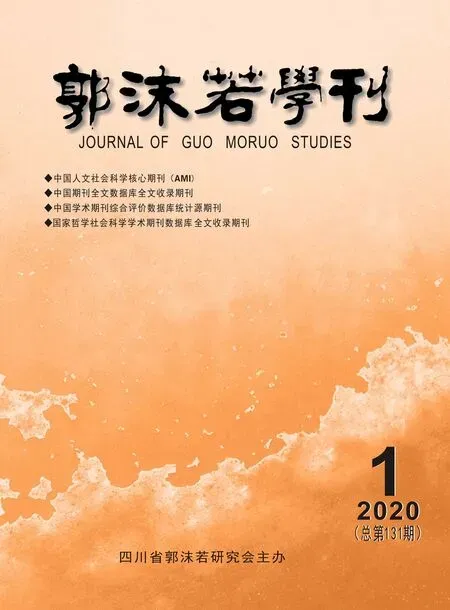从自叙传到自传:论1928年前后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与自我建构
吴 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在郭沫若一生所创作的文字里,自传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为例,在全部20卷“文学编”中,第11到第14这四卷全部是自传,占到了其全集所收录文学作品总量的近五分之一。
以1922年刊登在《创造》季刊上的《今津记游》为开端,到1948年的《洪波曲》,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如果将这些自传作品在时间轴上依次排列,就会发现,其自传创作多集中于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时间里。在这十年中,郭沫若因为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故此通常又被称为是郭沫若的“海外十年”,这段时间,郭沫若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于历史学和金石学的研究上,一切文学创作活动几近停滞,考虑到这种背景,其自传写作的大量出现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上述两个时间点的重合并非是偶然,之于作家而言,对文体的选择显然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①(英)克莱夫·贝尔著,薛华译:《艺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而一种文体以替代另一种文体的方式出现在作家的创作年表中,其背后的原因则更为复杂。有研究者称,传记文学的本质在于“吾丧我”,而自传文学则更是如此,自传文学是“我与我周旋”出来的文学,而其内容,即“自传事实”则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②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也就是说,在郭沫若放弃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而选择自传创作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与其自我认知建构相关的重要内容。通过书写自传,郭沫若得以对自己之前的思想脉络做出分析和整理,而这一分析整理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则通过自传的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事实上,郭沫若在很早之前就有着自传写作的冲动,在郭沫若开始大量创作自传之前,在其于1920年代初期所创作的一系列“自叙传”小说中,就可以看到他想要进行自传书写的意图。而正如郭沫若在《水平线下》结集时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1928年之前,郭沫若所创作的那些后来被冠之以“自传”的文字“内容是很驳杂的”,在其中“有小说,有随笔,有游记,也有论文”,①郭沫若:《原版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页。其“自叙传”小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其自传写作的一部分。这样看来,郭沫若在192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大量进行的自传写作实践则可以被认为是其长期以来自传书写在形式上的转型。显然,这个转型与当时郭沫若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其自身的境遇有关,其背后是郭沫若在这一时间点前后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对其自身进行的发现与重构。
一、大革命及“自叙传”的限度
有研究者指出,在“自叙传”小说中“不追求曲折的情节和精致的构思,却努力写出自己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的变化,仿佛是靠激情、才气信笔写去,松散、粗糙在所不顾,只求抒情的真切以成情感的结构”,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可见,如果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自叙传”小说远称不上成熟。但是,正是这种不成熟的文学观念,却能在1920年代中叶之前风靡一时,其原因则在于“自叙传”的背后隐藏着那个时代的秘辛。
“自叙传”小说虽然其名为“叙”,但是,其本质却并非叙事,而是抒情。1925年,郭沫若曾经这样概括过文学的本质,即“(1)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2)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3)诗是情绪的直写,小说和戏剧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①郭沫若:《文学的本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不难看出,此时的郭沫若对文学的看法主要还是集中于情感的抒发,即使是那些“叙事”的部分,也只不过是“构成情绪的素材”而已,有研究者认为“自叙传”小说的作者们“很少关注外部现实,他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并极其真诚地将这些感受描写出来。”②(捷克)亚罗斯拉夫·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0-61页。“自叙传”小说的这一特点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了其内部存在着的局限,由于“自叙传”小说以作者本人为中心,进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里,作者是可以描绘出其情感的基本面貌的,因为这种情感并不与外界世界直接相关;但是,一旦外界因素打破了这种由作家建构出的、自给自足的文学世界的边界,也就是说,当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文学主人公不得不走出“隔膜”,进而必须与他人产生关联的时候,“自叙传”小说就面临着被自我瓦解的危险。
1920年代中叶之后,随着革命政治的兴起,“大革命”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基本社会氛围,有人在1928年前后对这个时代进行了概括,称:“这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而“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③朱自清:《那里走》,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1页。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诸如“自叙传”小说一类只聚焦于自我情感的文学样式自然是举步维艰的,对于这种局面,“自叙传”小说的作者是有所察觉的。1923年,郭沫若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破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时,仍然能够充满希望地说:“让自然做我们的先生吧!在霜雪的严威之下新的生命酦酵,一切草木、一切飞潜蠕匍,不久便将齐唱凯歌,欢迎阳春归来。”“让历史做我们的先生吧!凡受着物质苦厄的民族必见惠于精神的富裕,产生但丁的意大利,产生歌德、许雷的日耳曼,在当时都未收到物质的恩惠。”④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然而,到了1926年,就连郭沫若也不得不改口,称“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两杯酒便是什么浪漫精神,多做得几句歪诗便是什么天才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⑤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43页。从郭沫若前后的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在这三年内,郭沫若对自己的文学观念是做了全面更新的,这种更新是建立在对之前所持有的那种抒情式的文学创作观念的否定,按照郭沫若等“自叙传”文学倡导者的设想,他们从事写作的目的就在于“把艺术救回,交还民众”、“使艺术感染民众的生息”、“把民众提高到艺术的水平”,⑥郭沫若:《一个宣言——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作》,《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23页。这种设想也许在1920年代中叶之前是可行的,然而,伴随着1920年代中叶之后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日益凋敝与“大革命”语境之下社会气氛的日渐紧张,人民求生存尚且不能,更遑论接受艺术的熏陶了。而作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中的一员,这些立志要以艺术去改造民众精神的作家们也同样饱受煎熬,正如郭沫若所记录下的那样,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吴佩孚倒了,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这一系列变化使曾经坚信艺术能够改造国民的郭沫若的“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⑦郭沫若:《到宜兴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323页。时局的剧变不但早已容不得郭沫若等人按照自己原先的设想去改变民众的精神,而且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去重新认真的去面对这自民元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思考下一步将何去何从。1926年郭沫若同郁达夫、王独清等人一起离开上海远走广州,紧接着穆木天、郑伯奇等人也陆续南下,这样一来,曾经倡导“自叙传”写作的创造社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整体的位移。而由于广州又是当时革命政治的一个中心城市,郭沫若等人的南下并非仅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迁徙,还意味着他们走出了曾经以“情感”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建构的围墙,开始和外界进行深度的接触。这样一来,“自叙传”这种文学主张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自然也就无以为继了。
可见,对于“自叙传”小说而言,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带有革命意味的社会实践正是存在其内部的限度,对于1920年代中叶之后的宏大时代语境,个人性的抒情不但其声音是微小的,而且也很难再与同时代的其他青年朋友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在这种情况下,这群曾经想要“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的年轻作家们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去完成文学目前所不能完成的社会理想。而通过“自叙传”小说的写作实践,作者们也逐渐开始反思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具体到郭沫若而言,大革命则成为了他由“自叙传”小说写作向自传写作转型的重要契机。
二、作为时间节点的1928年
既然郭沫若从上海前往广州的时间是在1926年3月间,那么,为什么直到1928年《我的童年》出版,郭沫若才算是有了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呢;又是为什么在此后的十年间,郭沫若开始大量的书写自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将192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并加以倒推,来对郭沫若在这两年内的行动与著述进行一番考察。
郭沫若本人称这两年的时间为自己的“石女时代”,并认为“我自从从事实际工作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惟文艺上的作品少有,便是理论斗争的工作也差不多中断了”,①郭沫若:《原版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03页。可见,郭沫若将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绝少写作的原因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与文艺工作的冲突,这所谓的“实际工作”一方面是指北伐,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其在广州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期间为学校所作出贡献,而实际上,在这两件事情内部,是有着一种承续的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郭沫若声称“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是“蝉联”着的。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9页。
在郭沫若南下之时,广州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其对于当时作为主要革命力量的国民党而言,是一块“风水宝地”,而广州大学作为广州城内知识分子主要的聚集之所,自然也就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竞技场,不但国民党试图将其“党化”,就连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两派也对这所大学的控制权争得不可开交。而广州大学此次聘请郭沫若等人,正是让其出任文科学长,在广州大学,这一职位并非仅仅像字面上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统筹各大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并且能够作为校务会议的核心成员来对学校内部的种种事宜进行最高决策的实权职务。③周文:《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而在当时,广州大学方面引进郭沫若等人,也正是看上了他们身上的革命精神,时任广州大学代理校长的陈公博就宣称:“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作革命青年的领导”。④E:《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而此时的郭沫若,由于在上海滩的文场上与《孤军》杂志同人及以赵南公为代表的泰东图书馆方面的交往过程中,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对“无产”有着切肤之痛,⑤吴辰:《双重"无产"的体验:论1923-1925年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再加上此前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在1926年南下革命圣地广州的时候,郭沫若已经“正式完成了从思考到行动的转变”,⑥刘奎:《郭沫若的翻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24-192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有了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生活中问题的自觉。也就是说,郭沫若这次的南下广州无论其促成者为共产党方面的瞿秋白⑦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78页。还是国民党方面的陈公博⑧周文:《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其目的都是在于以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在广州大学内部掀起一场改革。事实上,郭沫若也确实做到了这点,据当时在广州大学学习的徐彬如回忆,“郭沫若来后,文学院进行了大整顿,腐败的老文人都给清理了出去”,①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6期。这些被清理出广州大学教授队伍的旧派文人甚至还在文科学院内部掀起了一次旨在驱除郭沫若的罢课风潮。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立志改革广州大学的郭沫若在学校的生涯并没有过久,四个月后,他便离开校园,响应革命的号召去参加北伐了。
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其在广州大学主持改革工作的延续,当初广州方面之所以能够注意到郭沫若,正是因为其对革命的激进态度,而郭沫若之所以能够来广州,也是由于广州革命气氛的浓厚。郭沫若曾经在由上海远赴广州之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里边说道:“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何以故?以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在革命的时期中永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故”,②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37页。而在广州大学任文科学长期间,郭沫若经由毕磊向陈延年反映要求入党③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的行动也证明了郭沫若此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倾慕与在马克思主义事业实践上的激进。
然而,革命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1927年4月12号之后,曾经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成为了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逃犯,这是当初幻想能以革命之力一举改变中国的郭沫若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在郭沫若创作于北伐之后、远遁日本之前的《恢复》诗集中,郭沫若写到:
中小学体育课要把握好运动的“度”,不能让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效的运动才是保障学生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能的目的,运动负荷过小,则体育课就变成“闲聊课”和“游戏课”了,失去了体育运动的意义;运动负荷过大,则学生身心难于承受,遇难而退的学生比比皆是,运动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因此,体育老师要为学生设计合理的运动项目,给予学生适当的运动负荷,把握好体育教学的大方向,在完成运动负荷的前提下再让学生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笑脸开颜,/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为我们喜欢;/但不幸我们的革命在中途生了危险,/我们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那时候从后方逃到前方,你想直趋武汉,/但不料就在这春申江上你便遭了摧残。/你的生命不消说会长留天地之间,/但我们的革命势力呀已经是五零四散。④郭沫若:《怀亡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第365页。
鲁迅曾经在大革命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说到:“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⑤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而他在后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说的一番话更是语重心长:“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⑥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虽然鲁迅在演讲中将这番话的所指设定为辛亥革命,但是“左联”内部那些由大革命走出的人们不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
事实上,在1927年的大革命之后,在参加过北伐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严重而急剧的分化,对革命的消极情绪弥漫在整个知识界的上空,就连在大革命后期肩负共产党方面宣传工作的茅盾也经历了“幻灭”的感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⑦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由于被大革命甩出,在此时的郭沫若身上,那个致力于“实际工作”的政治家的色彩又慢慢地退却,而文学家的本色又显露了出来,他重新操起了纸和笔,写下了《英雄树》《桌子的舞蹈》《留声机器的回音》等文章,这意味着郭沫若重新从“实际工作”又开始回归到了文学上。这次回归使郭沫若看到了文学对于革命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人说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出现。这犹如说要饭煮熟了,才有真正的米谷出现。”。①郭沫若:《英雄树》,《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郭沫若在由广东逃亡上海之后,一度重病不起,在病愈恢复期间,“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在郭沫若平生里,“诗意的袭来”并不止这一次,但是,此次,郭沫若却分明地感觉到“这写《恢复》时比前两次是更加清醒的”。②郭沫若:《跨着东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与茅盾等人在大革命之后开始暂停革命的步伐转而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做法不同,曾经被革命同志称之为“情感家”③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的郭沫若却将反思的触手伸向了自己的内部。在进行《恢复》集中各篇什写作的同时,郭沫若还在翻阅《资本论》以及一些苏联方面的社会主义著作,正是由于对这些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吸收,才使得这次在诗意来袭的时候,郭沫若没有再如写作《女神》之时被诗意所绑架,而是将其诗意统御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下。在《恢复》诗集里,郭沫若将《战取》一诗作为全集的收束,这是颇有意味的,诗中说: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阵痛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高潮,/母体已经不能支撑横陈着了。/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喜酒,/但这决不是莱茵河畔的葡萄。/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④郭沫若:《战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有研究者早已指出在“莱茵河畔的葡萄”背后隐藏着的革命“顿挫”中的修辞症候,⑤王璞:《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但同时,郭沫若在诗中宣称这鲜红的酒实际上就是他心中的热血,也就是说,此时的郭沫若虽然已经被大革命甩出,但是其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激烈的“革命”,在日记中,郭沫若说:“中国的现势很象一八四八年的欧洲。法兰西二月革命影响及于全欧,但德、奥、比、法均相继失败,白色恐怖弥漫,马、恩都只得向海外亡命。”⑥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显然,在此时已经准备好流亡海外的郭沫若并没有对革命失望,也并没有和茅盾一样,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疑问,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种种的疑虑都在历史和文学中找到了回响,并将流亡看做是革命的一部分。
1926年到1928年这两年间,郭沫若通过对革命的参与,亲身经历了革命的高涨与低落,进一步明确了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化。在与李初梨辨析“留声机”概念的一篇文章中,郭沫若就明显地流露出要重新认识“知识青年”的意图,他希望这些知识青年能够“翻然豹变,而获得一个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成为未来社会的斗士”,⑦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而此时的郭沫若也同样有着对自己的过往进行重新梳理的需要,但是自叙传的形式显然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已经不能满足郭沫若的要求,这样,自传就成为了他对自己进行反思的最佳途径。
三、参与自我建构的自传写作
在郭沫若流亡海外的这段时间,他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上,有研究者认为:“流亡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不仅因为他成就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辉煌,更因为他所走过的心理历程,铸成了他此后人生的一种生存方式”,⑧蔡震:《“去国十年余泪血”——郭沫若流亡日本的心理历程》,《郭沫若学刊》,2006年第3期。而除此之外,其自传写作也达到一个鼎盛时期。自从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就开始其自传写作,先后诞生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等自传作品,事实上,在其自传写作和历史研究内部,是有着相同的逻辑理路的。
在历史研究领域,郭沫若称其所要进行的历史研究并非如前人一般的“整理”,而是要进行“批判”,他认为“‘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而其在自传中也说到:“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阬底挖出土来。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②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0页。也就是说,此时的郭沫若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征进行抒情性质的记录,而是需要一种能探知其内在原因的方法将其加以整合并进行叙述。但是,正如一名友人写信给郭沫若所说的那样,“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的童年时代其实并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在欧战前后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进展,余波一直到现在。”③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1卷,第 163、164、182、163页。由于郭沫若的创作意图与实际材料之间的不兼容,在《我的童年》中,常常能够觉察出作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用上的僵硬。例如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描写:“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④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0页。不难看出,在这类描写背后,作者并没有立足于事件发生的年代,以阶级的立场去分析事件,而是站在现在的立场,用阶级的态度去感叹当年。说到底,这种对于阶级观念的移用并没有超出“自叙传”小说抒情的本质,而郭沫若本人对这一问题也是有着认知的:“我的这部自叙传的工作自从去年四五月间把幼年时代写完之后便把它丢下了,丢了已经一年。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⑤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1卷,第 163、164、182、163页。而得到了这位友人来信的支持和建议,也使郭沫若意识到自己的自传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仍是有写下去的意义。
事实上,郭沫若在其自传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将自传与“自叙传”分别看来,直到1932年创作《创造十年》的时候,他仍称自己的作品为“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⑥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36页。但是,诸如《我的童年》中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硬使用却已经被一种理论性的分析所代替。郭沫若在反思曾经在少年时期受过的教育时说:“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⑦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1卷,第 163、164、182、163页。不难看出,郭沫若已经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洞察封建社会下教育的根本问题,并对其进行批判。此时的郭沫若已经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以其文学天赋加以整合,最后形成一套叙述,而从郭沫若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这种叙述姿态进行自传创作便可以看出,其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大的,毕竟,流亡海外的十年中,郭沫若的经济状况不能说是十分的宽裕,他自己也承认“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⑧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1卷,第 163、164、182、163页。从《反正前后》的写作开始,郭沫若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兼顾思想和经济的路子去进行自传写作。
在大革命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们认识到自己所欠缺的并不是来自于书本和理念上的种种“主义”,而是缺乏一种对这些主义的操纵能力,换句话说,对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的知识青年们而言,他们缺乏的不是世界观,而是能够使用这一世界观的方法论,毕竟世界观的能指还是过于宽泛,它在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带进革命队伍中之后,却未能为他们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胡适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思考:“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①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出于对“主义”本身的浪漫理想,这些“主义”在运作层面上也大多数脱离了社会语境,在1920年代后期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动的社会变革面前,缺乏方法论明确指向的“主义”根本经不住现实的一击。这也无怪乎在大革命之后,“主义”与实践的脱节将许多青年引领向了歧途。而在1928年之后,郭沫若的自传写作将自身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夹叙夹议地历数自己走过的道路,无异于一种现身说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活化,以一种贴近日常生活表面的叙述来引领着同时代的读者们走出思想的迷障。
而之于郭沫若本人而言,自传写作不但是其改造读者思想的一种方式,更是流亡日本期间其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郭沫若在大革命之后就意识到了自身需要克服的问题,即其大革命之前所依仗的生活经验中的能动性已经在时代的转换中消耗殆尽,而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又被其自己所否定,郭沫若此时其实已经几乎陷入枯竭的地步,他以“章鱼吃脚”作为类比,说:“章鱼的脚断了一两只,并不介意,有时养料缺乏的时候,自己吃自己的脚。往往没有脚的章鱼,脚失后可以再生,大概经过一年便可以复元。文艺家在做社会人的经验缺乏的时候,只好写自己的极狭隘的生活,这正和章鱼吃脚相类。”②郭沫若:《离沪之前》,《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与此同时,大革命之后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时尚未能够及时的沉淀和被吸收,于是,郭沫若急需对这一资源加以整合,使其镶嵌进自己的创作和思想之中。正如郭沫若此时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郭沫若想要重新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寻求变革的资源,则需要跳出自己原有的生活语境。然而,从郭沫若在大革命之后滞留上海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国内的政治文化语境不断地催促着这位习惯以情绪驱动自己行为的文学家不得不继续用自己的既有思想资源写作下去,面对着被缉捕的境遇,他不惜化身为“麦克昂”,也要在上海文坛发出声音。这样一来,流亡海外的十年则成为了郭沫若整合自己思想的最佳时机。
对郭沫若而言,历史研究和自传写作实际上是同质而异构的,其历史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和批判中华民族的历史,而其自传写作其实使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和批判自己的历史,而其在自传写作中又有意识的将自己置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之内,这就使其自传写作超越了以感情宣泄为主的“自叙传”写作,成为了可以与千万在大革命之后陷入困顿迷茫的年轻灵魂互相沟通、互相扶植的文学形式。在郭沫若流亡海外期间写下的自传里,克服了之前《水平线下》所存在的“驳杂”的问题,转而将整个自传的叙述都置于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译过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现象的描述,而是聚焦于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因素。在通过历史研究和自传书写对自己以及整个民族的过往进行了批判和整合以后,从流亡海外的后期开始,郭沫若开始从历史故事中开发出新的资源,先是有了集结成《豕蹄》集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之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苦》等六篇历史小说,后来在归国后又创作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在其中,郭沫若贯彻了一种被称作是“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而这种原则背后,其对理论资源的运用与1928年前后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也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在1928年前后,郭沫若通过具有理论自觉色彩的自传书写重新批判和整理了自己的思想资源,他在建构自己的同时,也重新以纸和笔加入到了革命工作之中,以自身经历向那些被大革命甩出的青年人们讲述革命的道路具体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