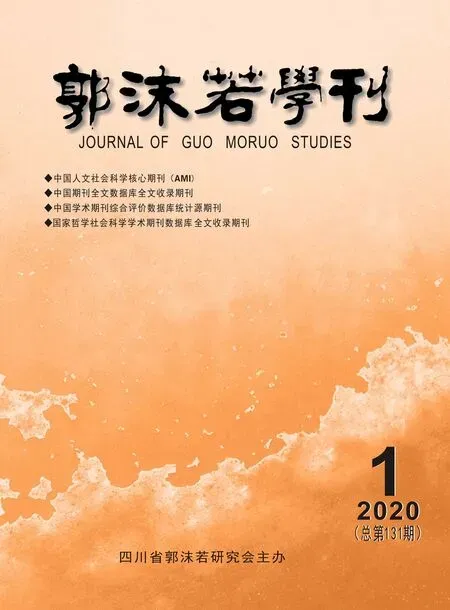《孔雀胆》的版本变迁
段 煜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1617)
《孔雀胆》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之一。这部剧只“写了五天半”并“差不多改了二十天”①郭沫若:《〈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第四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 161页。。这部在创作时只用了二十五天的戏剧,从初刊到最终定本却先后四易其稿,绵延十五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版本问题。
一、《孔雀胆》的版本概况
郭沫若对《孔雀胆》的构思始于1942年夏天。郭沫若本打算将宋末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钓鱼城之战戏剧化,却在整理资料时对阿盖公主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加之在少年时即曾为阿盖公主的辞世诗所感动(见《孔雀胆的故事》),遂在收集了“比正文多五倍”的资料后,于1942年9月3日起,用五天半的时间写出了《孔雀胆》。剧本先后在成都、乐山、昆明等地上演,大获成功,很多观众被故事所感动,慷慨地流出了眼泪(见《孔雀胆归宁》),周恩来亦曾观看此剧的剧本,并给出了“剧本写的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的评价。②张颖:《挚友·知音——周恩来与郭沫若》,《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在经过多次演出和调整之后,《孔雀胆》的剧本在1943年4月刊发于《文学创作》第1卷第6期,是为初刊本。
194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帮助郭沫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在重庆成立了群益出版社,郭沫若为创始人之一。群益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郭沫若的著作,《孔雀胆》自1943年12月出版开始,先后印刷四版,并于1948年2月出新版群益修改本,共印三版。
群益本是《孔雀胆》的第一个单行本,与初刊本相比,群益本在正文后增加了《〈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的故事》《〈孔雀胆〉故事补遗》《昆明景物》五篇文章作为附录。正文部分则有大小修改479处。③关于修改次数的统计方式,在字词和标点的修改上,本文以每一个断句为一个分割点,如果两版在同一断句中有所区别,则记为一处修改;涉及剧情的大段修改则从修改开始到结束无论篇幅长短均记为一处。而群益修改本则是群益本基础上的修订版,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孔雀胆归宁》《孔雀胆二三事》《孔雀胆资料汇编(杨亚宁来函四件)》三篇文章。正文部分则有大小修改486处。群益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海燕书店、大孚出版公司合并为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又依群益修改本于1951年8月重新出版《孔雀胆》,是为新文艺本。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沫若文集》,郭沫若借此机会,于7月“在北戴河海岸把这个剧本又作了一次修订”①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四卷),1958年,第244页。。文集于1957年3月出版,《孔雀胆》收录于第四卷,附录部分删去了《孔雀胆归宁》一文,正文部分则有752处改动,是历次修改中幅度最大的。
此后,《孔雀胆》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的单行本,以及《郭沫若全集》第七卷收录的全集本。但只是增加了一些注释,正文部分没有改动。
可以看出,从最初创作到最终定本的过程中,《孔雀胆》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故事情节的修改,也体现在遣词用字的调整。
二、故事情节的修改
对于故事情节的修改主要体现在群益本和文集本之中,经过修改,《孔雀胆》的剧情内容和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变化。
群益本中,剧情内容和人物形象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调整,剧情内容方面,首先是在原来的第三幕前增加了一场。在初刊本中,杨渊海是段功被刺身亡后才回到云南;群益本将杨渊海返回的时间提前了一天,段功得以提前知晓车力特穆尔有阴谋。段功反复强调“小不忍则乱大谋”“欲速则不达”,杨渊海则认为“你那过分的宽大我实在是感觉着不是个办法”,“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同流合污的”。段功从初刊本的一味妥协变为“明白地表示要以和亲的手段,避免流血的痛苦,以求得到人民的福利”;杨渊海则更加“反对同流合污”②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第四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 178页。。段功的妥协和杨渊海的抗争形象都得到了强化,他们代表的两条道路的冲突也变得更加明显和激烈。
另一组关于剧情的修改是精减支线情节。第一幕是阿盖公主与侍女施继宗、施继秀在通济桥迎候段功时给侍女讲的介绍沙漠骆驼的习性和元军征伐金齿国时元军将领纳速辣丁智破象兵阵的故事。第二幕是梁王妃忽的斤介绍汉人喝茶时对炭火、水源和泡数的讲究和梁王与向段功介绍蒙古人喝茶时喜欢在茶中放一点盐的习惯。第三幕则是阿盖公主为段功之子段宝讲解的《正气歌》中“在晋董狐笔”的典故,只保留了“在齐太史简”。
在初刊本发表之前,郭沫若就已经删去了剧中有关赵盾的历史故事,并曾谈到:
有的劝我把第一幕的谈骆驼与象的那两段也最好删掉,我却踌躇了。在进言者是以为这些故事与剧情无关,但在我的作意是正为取其与剧情好像没有多么大的关系。因为那样才显得自然,才显得不是完全在作戏。……有些朋友说,这样表现正好,所以我也就不愿意割爱了。③郭沫若:《〈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第四版),第 168-169页。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郭沫若设置这些支线剧情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情节更加自然,因此在初刊本中仍整体保留了这些较为突兀的剧情。而群益本中则将“这一节后来依然删掉了”④郭沫若:《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第二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年,第167页。,只留“在齐太史简”一处。对戏剧整体情节紧凑性的把握最终战胜了“显得自然”的考虑,全剧情节更加紧凑,冲突更加密集,艺术性得到了提升。
对于段功的调整也是从群益本开始的,较大幅度两处的修改在第三幕。第一处是阿盖公主向段功证明车力特穆尔送来的蜜枣有毒后:
初刊本:
盖(在沉默一会之后)摩诃罗嵯,你现在可相信了罢?半年前继宗继秀的父亲们也是被他们毒死了的。
段 我还是有点不大了解,他为什么要来这一套呢?
盖 唉,你这个人是太忠厚了!
段 我实在想不出他这个理由。我在这里想,说不定那蜜枣原来就是因为什么原故放了毒的,辗转流传,流到车丞相的手里,有毒没有毒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盖 唉,你忠厚得就像大佛菩萨一样了!他同晚母串通着在深宫后院里也下过毒的呀!
段 我始终不大相信。
群益本:
盖(在沉默一会之后)摩诃罗嵯,你现在可相信了罢?
段(微笑)我早就相信了的,不过我怕建昌阿黎和继宗继秀们到外边去传播,所以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哈哈哈……
第二处修改在第三幕结尾处,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详细列举。在初刊本中,段功在生死之际仍抱有幻想,希望用自己的“至诚”来使国王感悟,并且因为“国王叫他来杀我的时候,我去杀他,那我就是成为叛变了”而不愿除掉车力特穆尔。在群益本中,这种幻想和瞻前顾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减弱,段功只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才暂时不除掉车力特穆尔,对局面和车力特穆尔的认识也都变得更加清晰。
经过修改,群益本中的段功“减弱了愚直”①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第四版),第 178、177页。,更富有内涵和立体化。由对敌人抱有幻想而盲目陷入死地变为希望避免无谓牺牲而甘冒生命危险。段功的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思想更加得到了强化——即使认清了局面和后果也不愿武力反抗。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妥协主义者必然是有所企图的,而且必然是相当聪明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原因是梁王的恩和阿盖的爱”②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第四版),第 178、177页。。
与群益本不同,文集本在涉及故事情节的修改时,明显更加以对人物形象的修改为核心,剧情内容的修改更加侧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是在史实层面上对段功人物设定的修改。郭沫若曾提到他在创作《孔雀胆》时,并不清楚段功到底是何民族:
段功究竟是不是汉人,在事实上也还有些问题。……现在的大理人有好些都还是民家人。段功可能是民家人和汉人的混血。但我因为他有汉式的姓名,又因为大理已成国土,所以我率性把他定为汉人去了。③郭沫若:《〈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第四版),第 178、177页。
可以看出,将段功定为汉人,即使郭沫若本人都认为较为勉强。事实上,大理段氏在太祖段思平建国(947年)时是纯血统的白族政权,元灭大理后,原大理国主段兴智仍世袭大理总管,(见《元史·列传第五十三》)并延续至第九代总管段功。可见段氏的血统并未中断。文集本将段功由汉人改为了民家人,并在收录《〈孔雀胆〉的润色》时删去了“段功究竟是不是汉人,在事实上还有些问题”和“所以我率性把他定为汉人去了”。④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四卷),1958年,第267页。
其它的修改集中于结尾部分。首先是对杨渊海的修改。之前的版本中,杨渊海留下绝命诗给建昌阿黎后伏杀车力特穆尔,随后自尽。文集本去掉了这个情节,并增加了两段剧情。第一段在梁王见到车力特穆尔的尸体后:
梁 王 很好。我正想除掉他(指车力特穆尔,笔者注)!杨渊海,我感谢你。
杨渊海 你这昏庸老朽,我和你不能两立。(挺剑欲刺,被卫士们抗拒,呈紧急状。)
阿 盖(急止之)杨渊海,你不要怪我父亲。(向梁王)你现在可明白了吧?父亲!
杨渊海收回剑
第二段在覆面僧铁知院向梁王揭示车力特穆尔阴谋的始末后:
杨渊海(挺剑欲刺僧)我要把你这些魔鬼除尽!
阿 盖(极端苦闷中)杨渊海,你也容束了他。……
对于杨渊海,郭沫若曾谈到:“非妥协主义者的杨渊海,则以对于段功的忠诚和友谊,不能自行拯拔,终竟同陷于悲剧的境遇。”⑤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四卷),1958年,第267页。调整之后,杨渊海不仅能够“自行拯拔”,且反抗精神更加彻底,在为旧势力掘墓的同时也代表了“第二期的新生代”,也给悲剧气氛弥漫的全剧增添了一丝通向希望的光芒。
结尾部分的第二个主要修改则围绕阿盖公主展开。阿盖与段功之女羌奴诀别时送给羌奴载有阿盖绝命诗的诗笺一张,文集本将诗笺改为短刀,并告诉羌奴:“对于你会有用处的。”由象征哀怨的辞世诗到象征抗争的短刀,彰显了更强的反抗精神,这也与文集本的整体修改倾向相符。在之前的版本中,阿盖公主在说完“我要到那更幸福的世界里去了”之后便“气绝”,在文集本中,“气绝”被改为了“苦闷加剧”,随后便是全剧结尾处的修改:
群益修改本:
僧(合掌):死去了的我们应该收尸,让明天清早呈出一片干净的世界。
在钟声中闭幕。
文集本:
阿 盖:(作最大的努力,勉强支持起来)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倒下,气绝。)
余人均俯首沉默。
——在钟声中幕下
“一切都过去了”显然比“死去了的我们应该收尸”更加积极和富有诗意,而由阿盖来收束全剧也比铁知院更加有意味。总的来说,通过结尾部分的修改,整部剧的悲剧性有所减弱,在悲剧之中透露出了更多的光明与希望,整部剧的气氛更加“哀而不伤”了。
文集本中,还涉及民族问题的叙事做了调整。将“蒙汉不通婚”改为“蒙古人不同族外通婚”,“蒙汉本来是一家”改为“天下本来是一家”,“蒙汉一统”改为“天下一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页。。1954年宪法也基本沿用了这种提法。经过改动,作品超越了“狭隘”的蒙汉之分,强调全民族的大团结,更加契合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三、遣词用字的调整
遣词用字的调整贯穿了《孔雀胆》的三次修改,这些修改既有对词句的进一步修饰,也有对语言精确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并对之前版本出版过程中的失误进行了修正。
第一,指示性语言更加细化和准确化。这主要体现在群益修改本和文集本中。群益修改本中,第一幕梁王按段功的请求封赏施宗、施秀时,在“侍臣等均不乐”后增加了“面面相觑,表示嫉妒”,在梁王又封赏杨渊海时,增加了“车力特穆尔及侍臣等均呈不悦状”,杨渊海辞谢不受时“车等闻此,不觉喜形于色”,梁王不准杨渊海辞谢时,“车等一喜一忧,至此均不觉愕然”;第二幕车力特穆尔醉酒时由“俯身其上而大呕吐”细化为“俯身其上以手指而指喉大呕吐”;第三幕第一场段功与杨渊海登场时也由简单的“段功与杨渊海并肩而行”修改为“段功已改换戎装,身着披风,头戴蒙古盔,与杨渊海并肩而行”。经过修改,剧本对演员塑造角色有了更加具体的指导,更加便于演员通过阅读剧本理解人物和进行表演。
文集本则进一步贯彻了细化和准确化的调整。首先是对人名用法的修改,将对话前的人名由简称改为全名;其次是指示性语言更加准确,减少了随意性,如“二施”统一改为“施继宗、施继秀”,“二人就坐”具体化为“梁王、王妃就坐”,指示动作的“如前”被具体化为“十分镇定地”“语调放重”等;最后是对人物动作描述的规范化,在台词中穿插的动作用括号表示,不涉及台词的动作则另起一段直接叙述。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调整实际上反映了郭沫若的定本意识,这些辅助性文字的调整减少了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歧义,作品的格式也变得更加整齐了。
第二,对冗余语句做了精简。这主要体现在文集本中。首先,删除了第三幕第一场审讯杨渊海带回的日耳曼人刺客的剧情,为表现语言不通,之前的版本均使用了大段用汉字模拟的德语发音,并进行了翻译。文集本直接删去了这长达529字的一段。而语言的精简则随处可见,试举一例:
群益修改本:
我要尽我的力量做,我一定要报仇,仇报不了,我是不想活的。
文集本:
我一定要报仇,仇报不了,我也不想活。
经过修改,大量多句表现同一意义的台词被缩减为一句,剧本的语言更加简练了。
第三,具体字词的用法更加规范化。如群益本中将“犭累犭累”改为“倮罗”,“曲蟮子”改为“蚯蚓”,“蝮虫”改为“蝮蛇”,“腆怯”改为“羞怯”等;在群益修改本中,这类修改更多一些。其中一部分反映了汉语用语习惯的发展与变化,如:
事体→事情 吃茶→喝茶 原座→原位 刑爵→刑罚 糖食→糖点
粗浮→浮躁 泥酱→肉酱 天从人意→天从人愿 为非作恶→为非作歹
另一部分则体现出郭沫若对语言精确性的追求,如:
热的→暖的 蜜蜂水→蜂蜜水 山门一座→山门一道
步至桥头→步出桥头 和我叩头→向我叩头
一时气厥→顿时气厥 送来的东西→送来的礼物
文集本在贯彻群益修改本这种倾向的同时,也兼有字词和标点的调整,前者如将“那吗”改为“那么”,“摩诃罗嵯”与“摩诃罗磋”统一为“摩呵罗嵯”;后者则包括句尾的破折号统一改为省略号,并开始使用引号等。
最后,各个版本都对误植和误排进行了更正。如群益本中“七星关”误为“七里关”,“乳饼”误为“乳骈”,“草菅人命”误为“草管人命”,第三幕中将“段”误为字形相近的“叚”等错误在群益修改本中均得到了更正。
四、版本变迁之动因
《孔雀胆》的初刊本整体来说尚显稚嫩,经过修改,群益本在剧情上更加整齐、紧凑,遣词造句也更加顺畅,使剧本由草创到初步成型;群益修改本的修改是一次规模不大但较为全面的修改,经过修改,情节、文字和编校质量都变得更加严谨;文集本则在感情色彩上更加积极,情节上更加紧凑,格式上更加整齐,史实的考订也更加详实,文集本也最终成为了《孔雀胆》此后通行的定本。
从1942年的草创到1956年的最终定稿,《孔雀胆》经过了四次大规模的修改,其中,除从初稿本到初刊本的修改只能通过《〈孔雀胆〉后记》略作观照外,后三次修改清晰可见。虽然各个版本面貌差异颇大,历次修改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但是从这些差异中仍能窥见到一些贯穿全局的修改动因。
第一是对“事”与“似”的关系的处理。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时依照的是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处理艺术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时主张“失事求似”,同时也认为“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①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具体来说,就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可以为故事化的史剧情节“让路”,而在涉及“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时代的风俗、制度、精神”时,则要“尽可能的收集材料,务求其无瑕可击”。②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这种倾向在《孔雀胆》的版本变化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情节上的修改基本没有囿于史实的改动,反而让史实中为段功自杀殉葬的杨渊海活着继续抵抗下去;曾在群益本中增加的“龙套”史实人物施宗、施秀在文集本中也被删去。而在段功的民族、剧中的景物和用具等问题则一旦发现有误便加以订正。经过修改,“事”与“似”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恰当的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美学的统一。
第二是对社会政治环境变迁的调整与适应。郭沫若不仅是文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因此郭沫若十分注意作品与社会现实的适应。《孔雀胆》的主题思想便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反对妥协中和,主张坚决抵抗。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文学的范式发生了变化,旧作中的某些内容不再符合新范式的要求,因此也就有了文集本中依据新中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对民族叙事进行的调整;全剧的悲剧色彩有所减弱,情绪更加积极,善与恶、正与邪的对立更加分明,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杨渊海形象的改变。
第三是郭沫若本人对艺术的完善和定本意识的增强。初刊本由于写作时间较短,带有明显的“急就章”色彩,艺术上不够成熟,语言上也不够准确和精炼。经过三次修改后,段功、阿盖公主、杨渊海等主要人物的形象不再扁平而更加立体化,故事情节也更加精炼,戏剧冲突更加凸显和集中。文字上也更加正规化,体例更加整齐划一,描述性文字的使用更加严谨、规范,错别字等讹误也基本消失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对《孔雀胆》的版本与文本变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郭沫若是一个很注意修改旧作的作家,通过对《孔雀胆》版本的梳理,既有利于理清《孔雀胆》本身的创作历程,也有助于回到文学作品产生和变迁的历史现场,从一个侧面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和郭沫若本人创作思想的变迁有更加深入和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