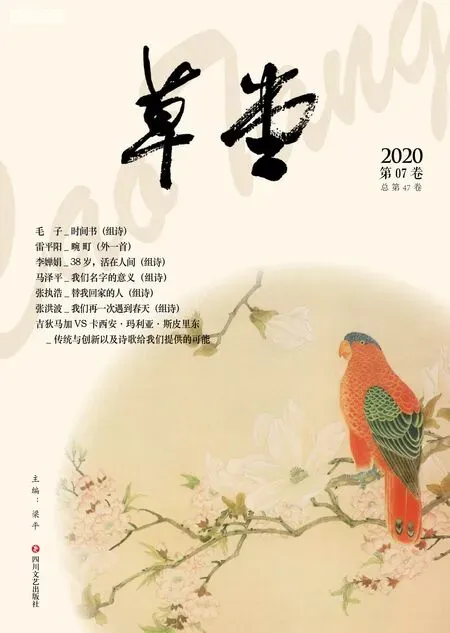传统与创新以及诗歌给我们提供的可能
◎ 吉狄马加 VS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亲爱的朋友和诗人吉狄马加,我很高兴地回忆起我们在天水“李杜国际诗歌节”期间多次会面的场景,特别是那些天举行的“东柯杜甫草堂”的落成仪式让人兴奋难忘。中国几千年的诗歌以其达到的抒情高度处于最富感染力的诗歌之列,它是一种历久弥新、永远都有现实意义的诗歌。 在这种超越一切的传统辉映下,你的诗歌、颇具敏锐性的诗歌的位置又在哪里?
吉狄马加:我同样怀念我们在天水相处的那些日子,正如你所言,中国有几千年的诗歌传统,而杜甫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诗人之一,我以为我们在天水对杜甫的缅怀,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伟大的诗歌传统的追寻。就其来源来讲,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是迥然不同的,它们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质,中国古典诗歌与其所承载的文字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字的特殊意蕴和内涵,旁观者要真正进入中国诗歌的内核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所构成的美学精神除了其东方哲学的背景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承载基础,那就是具有象形以及复合意义的中国文字。毫无疑义,中国古典抒情诗不仅从一个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就是与同时代的西方诗歌相比较,无论就其诗人的数量,还是所留下的浩如烟海的作品,同样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不可比拟的。当然那个时候的东西方世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交流,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和翻译已经到了十八世纪以后,与我们所说的唐朝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要晚了几百年。中国诗歌的传统一直保持了其连续性,除了其语言和文字的稳定性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其贯穿至今的一种传统,杜甫的诗歌被后人尊崇为“史诗”,那是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见证历史的罕见力量,其实杜甫一直存活在诗歌的“现场”中,他没有一天远离过我们,在当下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中国诗人都还会经常阅读杜甫,这并非一种时尚,而是因为杜甫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毫无疑问,我所承继的诗歌传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彝族的史诗和民间诗歌,第二个就是汉语的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另一个当然就是被翻译成中文的世界不同国家的诗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诗人,毋庸置疑,我的全部写作以及用这种语言所进行的创造,都是悠久而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与那些已经仙逝了的古典诗人不同的是,我们依然还在为这一诗歌传统续写着新的篇章,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这一肩负的责任既是神圣的,当然也是不可推卸的。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你来自少数民族,彝族拥有很强的文化传统,它通过自身的创造,尤其是今天的创造者们,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展现于汉族的巨大空间。你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通过什么在当今中国的文化整体中体现其代表性的?
吉狄马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多元共体既是一个文化特征,同样也是一种现实存在,这里所说的多元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共体指的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诗人在不同时代都被认为是民族的精神符号,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他们还承担着精神和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在我们彝族的文化传统中,诗人更接近于精神上的祭司,他通过语言和文字所进行的创造,既构建了一个属于其个人的精神疆域,同时又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诗性地呈现给了这个世界。所谓文化身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形成的对文化归属的一种诠释,当代阿拉伯重要的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就对个体文化身份的存在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当然所谓的文化身份常常并不是单一的,反映在个体身上很多时候甚至是多重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正因为这种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彝族诗人,同时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诗人。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是丰富的、多元的、极具包容性的,最令人欣喜的是许多民族都有着其代表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当下中国诗歌写作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我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你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我也可以大胆直言,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我们的人民之间就存在过一种兄弟缘分,证明这个现象的是属于(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的彩陶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两者有着强烈的相似特征,他们都出现在六七千年前。这种神奇的同一性是否连续不断,目前,我们又可以通过哪些元素来肯定这一点?
吉狄马加:我在罗马尼亚驻北京的文化中心看见过属于新石器时代库库特尼文化彩陶的图片,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极为相似,尤其是在今天不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了解在远古时期不同文明和文化是如何进行交流并相互影响的,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有许多文化之谜都不断地被解开,我相信总有一天库库特尼文化彩陶与仰韶文化彩陶之间的隐秘关系也会被我们所破译。在古代原始艺术中,这种具有相似性的情况并不是个案,我们彝族的原始木器,不论是造型还是木器上的色彩和纹路,都与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以及秘鲁的克丘亚人的原始器皿非常相像,过去有考古人类学家做过这样的推论,认为美洲的土著都是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过去的,我在玻利维亚就听当地的一个土著首领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就来自于东方。当然,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也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相同纬度的不同地域的人类,如果其居住的地貌和海拔相同,同时其感官吸收宇宙及外部信息比较接近,也可能创造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为相似的原始艺术品,不过这同样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和推论。人类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还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人类文化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它的差异性,也正因为这样,建立一种更为包容、相互理解、人道的文明与文化的对话机制就更为重要,同时我们也要对差异性有更足够的尊重,特别是在今天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并存的这个时代,对弱小文化的延续和保护更应该上升到道德层面来形成共识。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必须对现实产生作用,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正在激烈博弈的这个当下,作为诗人,我们必须站在促进人类和平和人民友爱的一边。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伟大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写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现诗歌的“支撑”和“用处”?
吉狄马加:老子的《道德经》都是通过认识天地、山谷、容器、车轮、房屋等具体存在之物去发现抽象的道理,他深刻地揭示了 “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关系,认为“无”常常被一般人所忽视,正因为“有”和“无”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那些无形的东西才可能产生不可被忽视的作用。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诗歌的教化和审美作用已经伴随了我们数千年,诗歌被视为人类精神遗产中那个“最柔软”,同时也“最动人”的部分,恐怕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生命经验,如果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灵史的话,那这一部又一部的心灵史,可以肯定都是用诗歌写成的。诗歌不可能摧毁坚实的堡垒和城墙,但诗歌却能抵达人类的灵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美好的诗歌,而不是花样翻新的杀人的武器。诗歌始终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我们只有高扬起这面光辉的旗帜,人类才可能通向一个令我们所有的人期待的那样美好的明天。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你在一篇访谈中称,在一流的外国诗人中对你产生影响的当数亚历山大·普希金,以及其他一些伟大的世界级诗人。
如果与当今世界诗歌镜照,你认为当代中国诗歌处在什么位置?
吉狄马加:无可争议,今天的中国诗歌是当下世界诗歌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也可以说它同样是开展国际诗歌交流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开展广泛的国际诗歌交流主要是在近二十年,我想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分不开的,随着中国深度地融入国际社会,这也给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进入一个更为国际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现在中国每年都要举办不同层级的国际诗歌活动,其中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都国际诗歌周、泸州国际诗酒大会以及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等,都已经在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现在中国每年出版的诗集的数量估计在世界上一定名列前茅,当然这和总的人口基数有关,同样也说明我们有一支庞大的诗人队伍,特别是近十年我们翻译外国诗人作品的数量也是令人惊叹的,可以说世界不同语种中重要诗人的作品,现在在中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译本。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正是因为这种交流和诗人作品的相互翻译,过去由于没有正常交流所形成的误解与误读,都在更为直接的对话和访问中得到了消除,也正因为加深了对彼此诗歌的深度理解,中国诗人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加重视自身的诗歌传统,开始了更为广泛的对自身诗歌传统、语言以及诗歌艺术形式的再认识,同时对外来诗歌的借鉴也进入了一个更为理性的阶段。这一切都是在交流和比较中得来的,说到底诗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背离它是民族语言所创造的结晶这一根本原则。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 :在一首题为《巨子》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所有呈现的一切都朴素如初。”我们从这句诗说开来,布朗库西如何反映在了你的抒情世界里?
吉狄马加:在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中,我最看重的是艺术家的原创力,其实回望已经走过的路程,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而又具有原创力的艺术家是少而又少的,从我的角度看,马蒂斯、毕加索、康定斯基、彼埃·蒙德里安、马列维奇以及布朗库西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在原创上布朗库西最重要的是回到了精神和形式的原点,它的朴实是建立在视觉的简洁上的,这是让创造返回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或者说是让原始成为一种极致的简洁,这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是很难做到的,但天才的布朗库西做到了。我以为在艺术创新上始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朝着有序的复杂向外走,另一个当然就是朝着原始的极简向内行,毫无疑问,布朗库西属于后者。我以布朗库西的创作为主题写的这首诗歌,除了向他表达一种敬意之外,更重要的是布朗库西给我带来了一种思考,那就是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和文字的艺术,同样需要我们在形式的探索上有更多的创新,在语言和形式上如何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具有原始品质的极简,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和法国诗人吉尔维克都在这方面进行过可贵的试验和探索。在很多时候,绘画艺术的创新与诗歌的创新都会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 :詹巴蒂斯塔·维科在《新科学》中认为,“诗歌,即此而非其他”是“所有艺术的源泉”;这一点得到古希腊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康德,甚至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所认同。
在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设备”走到了“人类”前面的当下,诗歌还能如何作为?
吉狄马加 :说诗歌是“所有艺术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哲学家与西方的哲学家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但东方的哲学家更强调诗歌所隐含的“阴”与“阳”的关系,这是东方哲学的基础,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东方哲学家还把诗歌看成是与心灵和自然对话的一种超先验的方式,我们从古代东方的禅诗中就能感受到这种意境,诗歌在人类漫长的生活中,它一直扮演着一种角色,那就是它既充当了联系天地和万物幽秘关系的媒介,同时它也给其他所有的艺术提供了形而上的源泉,也正因为此,我们才相信并肯定了诗歌是其他艺术的来源和根本。对诗歌本身所给出的这个定义,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被改变,哪怕就是到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个定义本身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同样也不可能被改变,有人曾经问我机器人最终能替代人类来写诗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基于我对人与诗歌本身的判断,因为机器人永远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最大的差别是真正的人有灵魂和感情,而机器人永远不具备这两样东西。也因为正如你所说的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设备”走到了“人类”前面的当下,我们反而要重新思考诗歌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诗歌离我们的心灵和灵魂越来越远,它们只注重修辞和语言的试验,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形式和技艺上的探索,那么所谓“新的技术设备”,就完全有可能替代今天的诗歌,并让传统的诗歌寿终正寝。但我相信真正的诗歌还会存在下去,那是因为还有许多具有“灵魂”和“感情”的诗人还会执着地写下去,人类也会因为有这样的诗歌对明天和未来充满了期待。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诗歌始终是自由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或有何人能够停息这种崇高的声音吗?
吉狄马加: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诗歌始终是人类自由的声音,因为这是诗歌所代表的自由与正义的精神所决定的,高扬这种精神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就有无数的诗人为了捍卫这种精神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远的不用说,二十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就是一位发出过正义和自由声音的战士,他就被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支持的长枪党杀害于自己的故土格拉拉达,也因为法西斯政权的这一暴行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行动,洛尔加虽然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但他所发出的正义与自由的声音却传遍了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没有任何人和力量能够停息这种崇高的声音。是的,正义和自由的声音是不可能被压制下去的,即便遭遇了曲折和磨难,它也会等到最终伸张正义的那一天。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你怎么看诗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
吉狄马加 :有关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因为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在写作实践中都会与它相遇,我不想简单地用抽象的语言来对它进行阐释。诗歌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更重要的它还是历史和精神的产物,现代主义运动在诗歌中带来的首先是对过去业已形成的崇高文学正典的背离,当然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对其精神价值取向的割裂,这似乎是现代诗歌的一种必然的归宿,毋庸讳言,形成这种精神和现实的迷茫,这与人类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工业和后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爱尔兰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反映出了人类面临的这种特殊处境,不仅仅是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背后的那束精神之光在渐渐熄灭,我们回过头已经很难看见人类精神源头涌动着的光芒,也正因为此,在大多数现代诗人的作品里就很难读到荷尔德林以及像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所投射给我们的那样一种崇高庄严的思想,今天的诗歌变得更加碎片化,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的精神的指引,我们甚至很难再产生一位像卡瓦菲斯那样能从容穿行于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诗人,这或许就是今天最真实的一个诗歌现实,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一切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说诗人是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但他的精神却必须要立于群山之巅,还应该更加自由地飞翔于无限的天际,从某种角度来讲,诗歌是需要精神高度的,也可以说,一个没有在诗歌中呈现形而上的诗人,他肯定也是一个注定了没有精神高度的诗人。诗歌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最直接的反映,如果是那样,诗歌就不可能翱翔于心灵、大地和天空之间,真正的诗人只能攀爬上那条形而上的楼梯,也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置身于那个光辉的顶点。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你在一首诗里提出“让我们回去吧,回到梦中的故乡”。我以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里是先辈带着他们继承的信仰和传统世代存续、又将它们传递给后来者的家园。今天的诗人们还有家园吗?
吉狄马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我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诗人的作品被谱写成曲广泛传唱,在二十世纪中叶这样的情况还比较普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希腊诗人扬尼斯·里佐斯等,就有许多诗歌被传唱,里佐斯的长诗《希腊人魂》被希腊现代卓越的作曲家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谱成曲后,不仅在希腊民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世界上也获得了许多诗歌和音乐爱好者的高度评价。我的诗歌《让我们回去吧》是彝族著名的歌手奥杰阿格谱曲的,现在是我们这个人口近千万的彝民族中传唱最广泛的歌曲之一。我以为人类既有现实的家园,同时还有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两个家园并非都是重合在一起的,要回到精神的家园无疑是人类每时每刻的渴望,我在长诗《不朽者》中有这样的诗句“我要回去,但我回不去,正因为回不去,才要回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或许说,这也是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诗人的处境,今天诗人的家园在哪里?我们只能永远在这种精神与现实的悖论中去做出自己的回答。
卡西安·玛利亚·斯皮里东:我知道你熟悉罗马尼亚诗歌,熟悉爱明内斯库,而且也熟悉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他有一部诗集,标题是《哀歌十一首》,我也就大胆跨过十问的门槛了,请你在最后向我们谈谈,对中国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抒情世界的看法,我们是否还可以唤起七千年前库库特尼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那种惊人的巧合?
吉狄马加:我喜爱罗马尼亚诗歌,是因为罗马尼亚诗歌中始终保有着一种适度的哲学性和优雅的抒情特质,我以为这是精神传统和血液中带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但体现在诗歌中,还在你们的音乐、绘画、雕塑和其他的艺术中。罗马尼亚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图多尔·阿尔盖齐、卢齐安·布拉加、马林·索雷斯库以及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等等,在今天已被这个世界上热爱诗歌的人们所熟知,我就曾专门为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和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写过致敬诗,在献给斯特内斯库一首名叫《在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墓地》的诗中我这样写道:“如果再晚一分钟,/你居住的墓园就要关闭/夜色降临前的门。/用一种姿势睡在泥土里,/时间的板斧终于成了盾牌。/此刻,手臂是骨头的笛子,/词语将被另一个影子吹响。/凝视的眼睛,穿过黑暗的石头,/思想的目光爬满永恒的脊柱。/一个过客,吞食语言的钢轨,/吞食饥渴的星球,吞食虚无的圆柱。/当死亡成为你的线条的时候,/当生命变成四轮马车发黑的时候,/当发硬的颅骨高过星辰的时候:/唯有你真实的诗歌犹如一只大鸟,/静静地漂浮在罗马尼亚的天空。”最令我感到欣喜和满意的是当下的罗马尼亚与中国诗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交流最可贵的是除了对彼此诗歌的翻译之外,还有更多的诗人开始进行了深度的互访,这种诗人之间相互置身于对方国度的“在场”,无疑为我们更广泛更具有针对性的了解对方提供了可能,我相信因为诗歌所搭建起来的中国和罗马尼亚的文化交流会被不断地延续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样也是你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