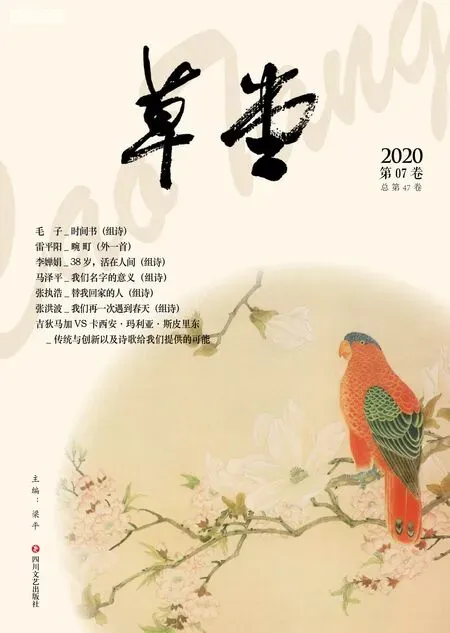时间书(组诗)
◎ 毛 子
[依赖之诗]
元素并不在元素周期表里
钟表和时间也毫无关系
但我们需要世界的表象,那过于真实的客观
会让人无处躲藏。
就像月亮反复来到人间,我们难于接受
它是一个不发光的天体。
减震之必要啊,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减震之必要啊,因为我们困宥在物种的属性之中
你看战争,历史,爱,神话和外星人
它们来过同一块银幕
但灯亮了,银幕只是一块银幕
它上面
什么也没有
[论 爱]
遥远,并不能穷尽星空
但我还是脱离自己,和它的安静
待了一会儿。
回来时,我并没有强大
你依然是要害,是迷信
是我的所剩无几
就像那一年,我们仓皇地出逃
拖曳着大雁塔、华清池和兵马俑
一路上,你紧紧抓着我的手
你说,面对那些无限的东西
请给我的短暂
施予援手……
[星 空]
眺望星空,看到更远的自己
更大的
更过去的自己。
放下家谱,我不再想
江西填两湖。
我要去原始社会
找我的父亲……
[矛盾律]
一只碗破了
我们占据它的破碎性。
一条小河枯竭了
我们占据它的干渴和焦虑。
一个人走了
我们占据他的疼痛和伤悲。
占据太多了。是不是该撤回来
让事物各归其位。
可倘若人类消亡了
谁又替我们,思考这个世界。
——尽管世界不需要思考,尽管
宇宙
不需要任何的意义。
[翁牛特旗沙地,给德东]
沙漠并不渴望了解,它只
保持它自己。
我们从千里之外赶来,就想看看
拒人千里的东西。
拒绝越来越稀有啊。想想这世界
人们总需要太多,唯独缺少
不需要的能力。
可以没有吗
可以不要吗
可以在他们的正确中
完成不正确吗
如果有一种
和盘托出而又守口如瓶的事物。
眼前的沙漠算一种,我们的寡言
是另外的一种。
[故 事]
每一个城市里
都有一个最晚回家的人
最晚就寝的人。
这是白天
形成的因素
[沙漠课]
我见到的
最大的
软体动物。
不是陆地上的蛇
也不是海洋里的巨型鱿
而是内蒙古高原西部
库布齐沙漠。
就像亚马孙流域
蛰伏的鳄鱼
用全部的软组织
集聚爆发力。
库布齐,用它的光天化日
告诉你
—— 一览无余,是另一种白内障
毫无遮拦,是另一种强迫症
而过于炫目的光明,则是
另一种黑暗。
现在,我写作
想让每一个词,像变压器
有着强大的电阻和电流
但我知道,有一根无形的高压线
在高高的头上,随时掉落。
[好 像]
无人的白天,好像不是白天。
空气里也好像
没有空气。
这是封城的第几日,时间
也好像忘记了时间。
透过玻璃窗,世界
还是原来的世界,但它
好像用尽了自己。
阳光依旧照在
它照过的地方,但我们好像
脱离了这一切。
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生的
怎么
发生的
问题好像
一个疑似病人
它等待最后的确诊……
[体恤之诗]
原谅地图的误差
特别是古代的地图。
原谅大西洋
一直待在西半球。
我那没有见过世面的母亲
不知道时差为何物。
原谅分子和分母
一辈子都不能平起平坐。
卡在圆周率的小数
永远没有透气的时候。
原谅白天,原谅夜晚。
原谅岁月仅剩下这两个
陪伴我们的
濒危物种……
[时间书]
天空留下来,已经
很多年了。
天空下的山川和流水
也留下来
很多年了。
很多年,一个鲁国的书生
面朝大河,不能自已
很多年,有人走下了幽州台
有人完成了《剩山图》
很多年,只是一瓢、一念、一须
一片汪洋都不见。
很多年,软体生物
遇见了造山运动。
我那类人猿的父亲
开始了直立的行走……
[束缚:答扎西]
兄弟,我们都被束缚了
这是生物的法则。
空气多自由啊,可从飞机上
我摸到了它的边。它也束缚在
薄薄的大气圈里。
有不被束缚的。也许
死亡算一种吧,但至今没有人
从那边返回来。所以
死亡也束缚在死里,就像爱
束缚在爱中。
尊重我们的局限吧。
但要像加缪一样给它迎头一击
只有伟大的音速,才能遇到
伟大的音障。
[瞧,那个人]
我活得越来越软,像犹大
遗弃的那截绳子。
我知道,凡是人都会犯那样的错。
可如果有人问:有通向圣十字的路吗?
我会指着那棵树,那个人说
——那挂着的羞耻和重量
我们至今还没有
领回去……
[造 就]
植物们从不挪动半步,它们是怎样
遍及了世界。
七大洲抛出的问题,能不能
让四大洋去解答。
太大的问题,穿在每一件事物上
都那么得体。
想想从前的海藻,后来的森林
想想花粉在风中受孕
你我在人山人海中相遇。
这样的造就,这样的奇迹
它们说不清,道不明
却既成事实。
[论距离]
你第一次离家出走
隔着几个乡镇,望着它
觉得走回去
很远。
你继续迁徙,隔着几个省
你远渡重洋,隔着几个国家。
你望着它,觉得走回去
很远。
落日在任何地方,有一样的表情
这里面,有你想表达的东西。
而宇航员透过太空罩,在月球上
打量蔚蓝色的星球。
他登上返回舱,进入大气层。
他感到人类的家园
扑面而来。
假如一个天文学家
读到这首诗,会怎么说。
一个心理学家或地理测量员
又会怎样。
[读荷马,并遥想东方]
驶向一座失明的眼睛
一艘航海的心。
他用历程、英雄和史诗
供养后世。
这是人类的拂晓,一切准备就绪
——西半球醒来,而东半球
也有了动静。隐身的老子
走出函谷关,孔子游说列国,走神的庄子
也在天地间入神。
世界被提前了。
而我通过一个盲者的瞳仁
看到地球
开始了转动……
[论古老]
在博物馆或地质公园
人们惊叹于青铜器、木乃伊和恐龙化石
但在我们身边,捡起的任何一块石头和土壤
都可能比它们古老
我们修建通天塔,我们登上
珠穆朗玛峰。
记住这一点,不管在峰顶,在峡谷,在深渊……
你在地表上的任何一个点
都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高压线]
我对高压线充满恐惧,每次
从它下面经过
总是胆战心惊。
这源自少年的阴影,一个叫王二荣的基干民兵,生产队的种田能手
在农忙歇息时,爬上田头的高压塔
那时刚刚放过《英雄儿女》,他在
高高的铁塔上,呼唤着: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向我开炮。
他掏出腰间的牛鞭,像王成拔出爆破筒。
可他高高举起的双手,被电线牢牢吸附。
他痉挛的身体,在抽搐中冒烟
在火花中,慢慢地蜷曲
村民用竹竿取下,已是一团
黑乎乎的碳化物……
现在,我写作
想让每一个词,像变压器
有着强大的电阻和电流
但我知道,有一根无形的高压线
在高高的头上,随时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