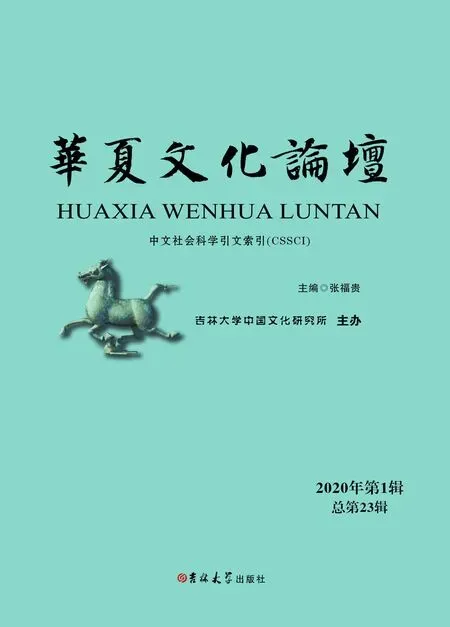在生活中的牢笼中寻求自由
——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野》
高祎博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大野》以双线叙事方式讲述了两位“70后”女性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坚韧是李凤群笔下女性成长中最为可贵的品质。李凤群以细密平缓的语言,借“今宝”和“在桃”的人生经历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间小城镇的社会变迁。通过对繁复的现实生活的思考,试图整体性把握个人遭际与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大野”暗喻在广阔而喧嚣的时代背景中,每一个人都在旷野中寻找着自己的来去与归途。
2018年10月,《人民文学》节选了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野》中的最后一章,并在当期的发刊词中评价说:“给这个年代的长篇小说提供诸种新的特质,是非常困难的,但本期发出的《大野》,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一部。”①《人民文学》2018年10期,卷首语。同时《大野》还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王德威先生评价说:“两个女子以生命演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在。”如果《大野》仅以双生花的结构模式去书写今宝和在桃两位现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人生际遇,这种题材并不鲜见,李凤群通过平缓却绵密的语言在个体命运的际遇流转之中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别、财富等诸多命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大野》无疑是个体生活经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次超越的表达。两位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不仅是女性寻求自我的精神成长史诗,同时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在记录4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与人的变迁与流动。
一、“坚韧”女性成长的核心
在阅读《大野》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萧红的《生死场》、王安忆的《富萍》、毕飞宇的《玉米》和《青衣》,盛可以的《北妹》、《野蛮生长》和近作《息壤》、付秀莹的《他乡》等,无疑我们可以将《大野》中的今宝和在桃归入中国当代女性困惑和成长的人物形象谱系中。
从创作的内容上来看,李凤群早期的作品《边缘女人》(2002年)、《非城市爱情》(2003年)、《背道而驰》(2006年)、《颤抖》(2013年)书写的也多是那些漂泊在都市中的外乡人的内心与情感纠葛。尽管她们在空间上逃离了乡土,但从根本上却无法斩断她们深埋在血脉之中的乡土情结,在环境的变换与精神根系的不变之间所形成的拉锯、对立、撕扯,进而沉积为主人公的心理暗疾。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李凤群和不少同一代际的“70后”作家如魏微、盛可以、朱文颖等人有着相近的创作倾向。而从2014年的《良霞》开始,李凤群似乎进行了转向性尝试,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这些心怀悲怨在城市和故土之间拉锯的女性,转为一种守家在地,更为沉静却坚韧的女性。
《良霞》的主人公徐良霞从骄傲美丽的如花少女因疾病而遁入困厄,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的身体,同时还有爱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整个家庭也因为她的疾病而堕入困厄之中。良霞的美丽不在于年轻的时候,反倒在于因为疾病她被禁锢在一隅,无力反抗时不怨愤地去承受,看透前路,仰面接纳。良霞宽厚淡泊,安静地承受疾病的纠缠,而《大野》中今宝除了一次未见成效的出走和跟着丈夫的一次上海之行外,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县城,与良霞的被迫相比,今宝则是一种自主的、静默的坚守。正如作者所言:“静默的生命获得了强度,她终究脱离了我,成为她自己。”①李凤群:《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后记)》//《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03页。而从“良霞”到“今宝”,那种沉静的坚韧成为人物的核心力量所在,在良霞和今宝身上,在她们静谧的内里,真正使人震撼的力量在于人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或者说在无可失去之时,明知到不了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之后该如何应对。她们的魅力就源自看透自己的内里,平和地接纳他人,即便众生奔跑也能够独自驻足。
《大野》的人物塑造与这种“双生花”的双线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单数章节以叙述者的视角俯瞰着今宝的一生,双数章节则是以在桃写信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在絮语着自己的过去与现在。阴阳互嵌的叙事使得明烈与静穆得以糅合,双线叙事互为衬托。如果没有了今宝,那么在桃也只是众多青春叛逆少女中的一个,在寻求自由的路上横冲直撞、遍体鳞伤。同样,缺少了在桃,今宝也就变成了镶嵌在土地上沉默顺从的少妇,存在感被日渐磨蚀消解,最后老去消亡。
今宝与在桃之间互为理想。“每一个狂放不羁的在桃的心里都有一个今宝,每一个今宝的心里都依偎着一个在桃。像对立在镜子正反两面的姊妹花,互相映照,互相取暖,却永不重合。”②李凤群:《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后记)》//《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03页。而如果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合二为一,她们所构成的则是面向于现实、面向于生活的“理想的女英雄”,又或是现代女性人格中的两个侧面。在《大野》中李凤群所创作的今宝和在桃是深住在她记忆深处,与作者同一时代走来的少女的缩影,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生活在小城市与乡村的女性成长历程的缩影。
许多人年轻的时候是在桃,向往自由,努力摆脱所有来自生活的既定的可能,永远不被现实招安,也不可能被安稳的现世所驯服。来自生命本身的原始的动力,支配着年轻的她与她们在人生的旷野上横冲直撞,笨拙却肆意。在桃身上总是散发着对于自由的本能的向往,11岁就会追着那支蹩脚的乐队,因为在那些旋律与歌词中她可以本能地去追寻自由的味道,那是与她此前认知的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桃的“桃”与“逃”同音,名字暗喻出她势必会想方设法逃离陈志高为她所铺设的安稳生活。在卑微地爱过之后,她认清了南之翔的虚伪与自私,她再一次选择忍痛离去。在桃周身散发着一种勇力,即使遍体鳞伤也要遵从内心的勇气。
但作者李凤群并没有止步于此。现实生活最大的磨难其实大多并不来自少数的极端事件造成的转折,而在于缓慢而无声的损耗,这种磨损无所不在,却又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更糟糕的在于这样的生活磨难无可避免。今宝的价值正在于她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这个出生于小县城的姑娘,“她的个人生活与庞大的历史之间无限接近,却又无法汇合”。①李凤群:《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后记)》//《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98页。她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获得成功的机会,即便是痛下决心离家出走,最终也在弟弟的三言两语中被糊弄过去。甚至多年之后丈夫根本不知道她还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以为她是回娘家小住。但也正是这次静默无声的出走才让她邂逅了在桃,在往后的人生中两人互为精神上的支撑。
今宝是一个真正的“女英雄”,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故与不幸之后,依旧能对生活保持敬意,既不无望,也不再对自身和生活抱有过度的期待。她依旧能身处瓦砾之间却心怀世界,她明晰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并以此捍卫着“成为自己”的权利。在丈夫老三被自己的弟弟架空公司、骗光积蓄以后,她也没有离去,即便这个男人在木然无趣之外还变得更加冷漠敏感,这时候今宝的内心已经变得平静而坚定。正如她在回答母亲为何不出去的询问时所说的那样:“我觉得那些从家里出去的人才应该被问为什么出去,留下来本身不需要理由的……”②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61页。在这个家庭关系内外焦灼的时刻,今宝不但没有逃离,反而选择留下,是因为她的内心早已知晓“逃别人特别容易,逃自己是困难的”。③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61页。此时她早已能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进而平和地对待周遭的一切,既不过分艳羡,也不会颓然萎靡。
“只有当他们将来回忆的时候,才能看清这是什么地方,而自己又是什么一副模样。”④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2页。人如何认识自己、成为自己是现代文学反复书写的核心命题之一。在面对自我时认清自身的平凡乃至平庸,永远未曾被注视、被听见,甚至不会被挽留,真正做到与生活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宝的力量就在于即便认清了庸常的生活的本质,但依旧愿意做那一朵在荒漠深处开放的小花,在一片静穆中她获得了生命的强度。
二、城乡过渡带的日常人生
如果李凤群仅仅将小说的笔触停留在今宝和在桃两位女主人公的情感与人生经历上,那作品的叙事格局难免会显得逼仄。《大野》的成功之处更在于李凤群以平缓细腻的笔触叙述出了改革开放的40年间,在都市之外的地方的社会变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变迁。
除了早期的以都市外乡人的内心情感暗疾为主的小说以外,在李凤群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以《大江边》(2011年)、《大风》(2016年)为代表,描写在代际的更迭中家族命运遭际、农村家庭变迁的历史的另一个系列。而不论是都市漂泊者的情感叙事还是农村家族的变迁史,李凤群小说中一系列人物都以“江心洲”这一独特的乡土空间为起点所展开。而在《大野》的创作中,李凤群的角度从以往的“江心洲”叙事上有所转移,她敏锐地捕捉到城乡过渡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叙述个人与社会以及40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个人的生活充满着可言说性的话语空间。县城边缘与国营农场——这两个既保留了一定的乡土特质,又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向城市化靠拢的中间地带,为她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视角。
王安忆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①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大野》作为一部气质独特的文学作品,其魅力除了来自作者对于两位互为镜像的女主人的塑造外,更来自其面向现实的创作。整部小说的叙事以绵密的语言针脚还原着生活的真实,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多是最底层的平民百姓,而他们断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能是被大的历史和时代所裹挟的跟随者,或者说他们也未曾刻意地跟随潮流而去,只是生活在某种氛围之下,被这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牵引着。
小说中作者从不直接去评论或描述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时间节点,而是在细节中去展现大的时代与历史背景延伸下最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心态的变化。读者对一部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语言所描绘的细节同生活经验的贴近,使得在阅读中个人的经历被带入情节。小说中描写的今宝与老三的母亲两个女人之间日常琐屑中的种种矛盾,不单是来自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廉价的生活装饰物所显示出的今宝作为一个少妇对于生活情趣的追求,与婆婆极度节俭、省电,甚至于宁愿忍受病痛也要节省药物等等小的生活细节上的冲突。这对婆媳之间的矛盾,更深一层则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下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观念上的冲突。尽管今宝因为种种原因仅在下城区的鱼馆做过服务员,但近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幻想着大城市的种种,包括今宝在内,都怀揣着到外面去,到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的冲动。这样的想法来自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外界信息,使得整个的社会环境都散发着一种躁动与不安,充满探知的热情。那些生活在村镇的中青年一代在社会变革期中正急于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人的流动性的束缚。而丁建新的母亲、今宝的婆婆周身所散发的则是对于农业耕种和养殖近乎迷恋的执着。老三积累下的财富并没能给母亲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她让儿媳接手了之前她打理的一切,前院的韭菜、圈养的猪仔、栅栏边的丝瓜架,后院菜地里的茄子、长豆、西红柿,两个月中今宝学会了喂猪、养鸡、种菜和除草。显然这位来自空心洲的老人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她骨血中根深蒂固的农业属性,乃至于她的骄傲和快乐更多来自对于别墅周边荒地的圈占,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位婆婆都从未向城市靠拢。这也影响到了儿子生活情趣的匮乏,事实是财富并没能改变丁建新从母亲那里承袭来的节俭,别墅不过是一个扩大升级的乡村院落。
今宝和那些生活在她周围的人们所经历的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社会变化与发展的细微之处,这些在平常百姓的不经意间流淌过的岁月已经成为小说最为有力的推动力。李凤群用最为平实的笔触记录与描绘着以河沟镇为缩影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小县城的进化历程与其中的得与失。就如同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在小说《王城如海》中总结说:“一首歌在首都流行一个月以后到他们省城,省城流行两个月后到他们的地级市;地级市唱完了三个月,才能到他们的县城;县城唱过四个月,镇上的年轻人开始唱了……”①徐则臣:《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形象地道出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距离,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也在一片喧嚣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摇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越来越多的小城镇正在褪去它们的乡土面貌,成为当代消费社会中城市流行文化的承袭者,然而向城市靠拢的进程中,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也如影随形,不论是大众流行文化还是物质上的承袭和效仿都很简单,但人从土地中脱离,转换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却有更长的路要走。
小说中今宝和老三所居住的坐落在城乡交界处的一栋别墅,也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最初它是一个门面,是老三丁建新财富的最为具象化的表现,进而成为了一个空间上的牢笼,将今宝圈缚其中不得脱身。而在平缓流淌过的岁月中,它是一个坐标和见证,见证着这座小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摇摆。最初所谓的小区仅仅是由三幢萧索的孤立的房子以及狭窄的人工湖构成,此外更为广阔的地区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别墅区外的农民将居住在其中的人看作是有钱的富人,然而实际上围栏内外的人无异,他们都延续着旧有的生活。此后今宝发现原本只有操场那么大的垃圾场在不知不觉之间扩大着面积,自己工作过的饭店已经变得宽大敞亮。经济的发展使县城在喧嚣间悄然发生着巨大改变。小说将近结尾时别墅已经有点过时了,在重新被利用起来的院落中,今宝种上了郁金香,花卉取代了蔬菜瓜果,生活的情致取代了生存温饱的迫切,今宝在成为她自己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同时这也昭示,含混着城市与乡村边界特质的下城区朝着城市又迈进了一步。
三、到“外面去”、到“世界去”的自由向往
电视的普及带来了大众通俗艺术的繁荣,自港台而来的琼瑶、三毛、金庸、古龙为这一代际的人的成长引入了一种沉湎自我的哀伤感和对英雄传奇的向往精神氛围。另一方面,在“70后”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影响力巨大的社会政治因素已经退出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系统地接受教育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活跃成为“70后”成长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读书与致富成为影响和改变命运的两大途径。到外面去闯一闯,到世界去看一看,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成为“70后”作家在关涉到县城、乡村的叙事中一个较为集中的表述。
小说中在桃出走,以及与给她带来伤痛的南之翔的相遇,就来自她对于这只浪迹在村镇之间的乐队的痴迷和追随。笔者认为作者李凤群对于在桃的出走以对乐队的追逐为节点显然有着一种隐喻,尤其是乐队所演唱的歌曲不是一般的通俗的流行歌,而是窦唯的《哦,乖》以及黑豹的《无地自容》。小说中引入这些歌的歌词正暗示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年轻人的内心渴望与精神状态,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更多被杂糅进了一种浪漫性的幻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同时这种浪漫性则催生出一种躁动。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她的两位好友离开不久,她渐渐意识到周围所投射过来的躁动的气息。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变成了这样:成长,读书,考上大学,考不上的去南方。所有人喜欢谈论的话题,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出去闯世界’这样的主题中。关于邻里朋友闯世界的传奇故事开始慢慢传了回来,某某发了大财,某某成了高官,某某嫁了富豪,在这个到处盛开着富裕之花的地方,贫穷已经成了错误。”①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93页.不论是今宝还是在桃所生活的小城镇与农场,甚至于在整个刚刚迈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中,对于财富的渴望不再是一种羞耻,财富的多寡成为自身价值最有力也最显而易见的证明。比如小说开篇不久今宝因为意外事件而死去的表弟吴波,一个电缆厂的保安因为经常被总经理指派而倍感骄傲,也会将“扩大经营”“企业前景”等当时时髦的词语挂在嘴边。这个莽撞的年轻人身上所带有的特质正是当时的村镇青年急于通过高考之外的途径去摆脱乡土的束缚,摆脱祖辈旧有的农民身份,在不断膨胀的自我中急于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
曾经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反而促生出对于外部世界的躁动和对浪漫传奇的向往,这也成为一种情感氛围弥散在那些“70后”作家关涉到自身成长经历的叙述中。相比较于那些叙述向城求生的故事中的灰暗与无奈,掺杂了与自身成长经验的回溯的“到外面去,到世界去”是很多出生于小城镇的70后作家的共同性。小说中多次描写今宝会将那些从书籍、报纸、杂志、电视中看到的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介绍性内容刻板地背诵下来。从少女到少妇,今宝的心里其实一直潜藏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否则不会促成她与在桃的相遇,致使在桃成为了那个替她去感知世界的另一个自己。身在一地却心怀世界。同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同样将“必须到世界去”当作一种精神符号,让作品中的人物反复提起,那些从花街走出去的孩子们在追寻世界的旅途上有人成长,有人狼狈。而路内的“追忆三部曲”用略带戏谑的口吻勾勒着“戴城”这座由化工厂、技校、新村构成的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颓废的工业小城,路小路躁动不安的青春岁月里因为白兰的出现与离去唤醒了他对世界的追寻,因为白兰不属于逼仄的工厂空间,她是外面世界的化身。而在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中,这种到世界去的情绪则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安小男身在北京却时时刻刻地监控着另一个半球的美国仓库,世界已然随时随地能被看见。然而那些盘踞在心中的疑问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呢?到外面去、到世界去的想法所隐含的是“70后”整体的一代人的一种精神向度。表面上看是急于摆脱地缘,甚至于是摆脱血缘的束缚,对财富的迫切渴求,而实际上则是这一代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和自我构建的精神之旅。
世界究竟是什么?今宝在和丈夫蹩脚而尴尬的上海之行后清醒地认识到:“人跟物的关系,不是距离决定的,人和世界关系早就发生了。人在世界里头,对人来说,他只在这里;对于世界来说,所有人都在里面。”①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正如徐则臣说:“年轻时,觉得更广阔、空间更大的地方就是世界。多年以后,你想追求内心最为安妥的地方时,那个世界可能是故乡。故乡和世界的关系是不断置换的。也许找了一圈,世界就在家门口。”②徐则臣:《70后“要到世界去”》,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9日,第10版。当在桃发现自己叛逃的起点竟是如此的荒唐,自己与母亲之间根本不存在血缘关系,她终于结束了漂泊,回到了那个她所逃离的农场,开始安稳的人生。出走与回归,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更容易看到一种与生活的和解,最终“世界”与“故乡”,去处与归途重合,在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里,在那些兜兜转转、分分合合的际遇中,这些细致的人生体味充满着真实的温暖与疼痛。
小说题目《大野》似是在暗喻着生活本身就是一片旷野,同时生活又是一座最大的牢笼,每个人都身处其间。故乡可以从空间上被逃离,但人终究逃不出自己。每个人都在其中回忆着来路,寻找着归途。在繁华而喧嚣的时代中、在生活的旷野里,能否做到即便是无所收获却依旧觉得不虚此行?随波逐流易,真正难的在于能够在内心中与平庸的自己和解,能平和地对待接踵而至的失望,在自我肯定与否定的循环往复中,理解自己,宽宥他人。作者李凤群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她所关注到的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像今宝与在桃一样跟作者同时代走来的人们,他们的苦难不仅仅来自经济上生存的压力,当生存境遇已经改善时,艰难来自内心,精神的困境像是一张漫天撒下的大网。真正的自由来自内心的自适,我们身在世界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心怀世界。
四、结语
李凤群的《大野》不仅是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的交错编织,更是她对于4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思考的凝聚。小说从最细微之处去切入生活,用文学的表达回答着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家发展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小说中的精神向度也显露出作者和那些与她同一代际成长起来的人们内心中持久的、对于更为开阔的新生活的不懈向往。这种向往,推动着那些曾经青春年少的人们向着他们想象中的世界走去。广阔的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旷野之旅,最终他们也都发现那些根植在血脉中的惯性是无法连根拔起的,与生活和解不是绵软无力的表现,用更为包容和坚韧的内核去面对无声的磨损,方能从自我走向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