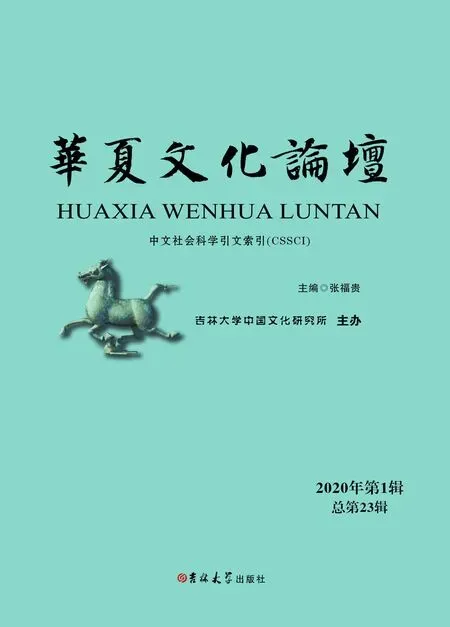双雪涛小说中的“失落者”群像
胡 哲 罗秋红
【内容提要】新世纪文学发展至今,文学现象层出不穷,“80后”批评家杨庆祥在“旧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为书写对象的“新伤痕文学”,其主要内容则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给中国人造成的物质创伤和精神创伤。①杨庆祥:《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双雪涛的小说集《飞行家》《平原上的摩西》以及中篇小说《聋哑时代》和《天吾手记》均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塑造了90年代东北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失落者”群像。作者用悲悯的情感和人文关怀向我们诉说了父子两代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女性个体等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生。这类群像既是对“新伤痕文学”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底层人物精神困境的回应,使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新伤痕文学”概念由“80后”评论家杨庆祥提出,它的书写对象是“改革开放史”,延续了80年代“伤痕书写”的人道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对话式的倾向,看到阴暗和伤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②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童年时期生活在铁西区艳粉街的双雪涛,采用回忆的方式记叙了20世纪90年代,受下岗潮影响的工人群体被迫走出衰败的工厂,走向社会底层的故事。他们在面对身份地位的急剧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时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这群人深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双重矛盾下,他们被打上“失落者”的标签,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是被损害、被欺压的对象。对于“失落者”形象的研究,最早是1987年韦湘秋和黄强琪在《科场上的幸运儿,官场上的失落者——赵文关》中对广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赵文关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其官场失落的原因,揭开了“失落者”形象研究的序幕。此后,学者对文学作品中“失落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张爱玲及其笔下人物作为苍凉的时代失落者的研究,如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和朱立新《心灵归宿的无望追寻——探寻张爱玲小说中失落者形象》等;第二类是对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失落者形象的研究,例如许晖《不自知的失落者——〈肥皂〉中四铭形象分析》;第三类是对梦想失落者形象的研究,如朱飞英《刘震云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变迁之旅——从梦想失落者到精神异化者再到孤独逃避者》和游澜《迷失主体、世俗慰藉与沉默言说——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研究》。其他如研究“无根一代”留学生失落者的曲树坤,研究《呼啸山庄》权力失落者希斯克利夫的刀喊英,研究灵魂家园失落者王建业的汤达成,研究文化身份失落者的金延英,研究《梦之谷》爱情幻象失落者的余凌,等等。通过研究者对失落者“失落”原因的分析,他们无非受权力、制度、物质、精神及情感因素影响。再观双雪涛笔下的人物,他们与张爱玲或鲁迅笔下的“失落者”不同的是,他们失落于时代变革,相同的是对精神和物质的失落。堆积的情绪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渐渐形成一种天鹅绒式的创伤。随着下岗规模的持续扩大,失落的情绪弥漫到各行各业,渐渐形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创伤。隐形的伤害正是来源于杨庆祥所说的中国“改革”之阵痛。这种伤痛情绪是抽象的,而双雪涛却将抽象的情绪安置在不同的人物命运之中。
所谓“失落者”,是指在精神或感情上没有着落、失去依托的人。①朱立新:《心灵归宿的无望追寻——探寻张爱玲小说中失落者形象》,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在双雪涛的文字表述里,清晰可见散落在小说各章节之中的“失落者”形象,他们生活在中国东北最著名的工业区(因位于长大铁路西侧而被命名为“铁西区”②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居住在工人村或棚户区。作者在《走出格勒》中写道:“那时的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它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每当市里发生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此处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随处可见的垃圾和脏水,即使是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整条街。”③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87页。“失落者”因其失落而追寻,追寻的结果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人因追寻无果而陷入无望,在无望中更加失落,另一类人在追寻中迷茫,在迷茫中期盼,在行动中重寻希望。他们在“失落——追寻——无望——再失落”和“失落——追寻——迷茫——期盼——重建希望”中徘徊挣扎,经历人生沉浮。他们不仅展现出人性的敏感多疑、自私卑劣、虚伪扭曲、软弱无能的一面,还展现出人性的坚韧和不屈的一面。通过对“失落者”生存状态的描摹,双雪涛的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冷峻苍凉的文风,给人以无法言说的感伤和沉重。
一、“父”辈的记忆与重塑
双雪涛小说的精神家园中必然有一处来自对父辈的讲述,细数父辈独特的生命历程,在塑造“子一代”和“父一辈”的形象中重新思考历史的发展与变化,通过对父辈的回忆与想象,从中找寻被遮蔽的父爱和遗留下的父辈精神。本文接下来对双雪涛小说中父与子的形象分别做三种类型研究,“子一代”分为精神异变成疾的失落者、迷途知返的失落者和迷茫堕落的“失落者”,“父一辈”分为落寞时代的担当者、隐士和追梦人。通过分析父子形象,掌握他们“失落”的深层次原因,感受父辈给予“子一代”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能量。
双雪涛在小说中运用传统的叙事策略,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向我们塑造了“失落”的青年群体。精神异变成疾的代表性人物是霍家麟和安德烈,由于两个人极具相似性,所以选取霍家麟作为分析重点。在他者视角下,他是一个天才,初一即可熟练运用物理和数学知识总结出“镜子理论”,涉猎广泛,善于思考和纯粹的兴趣研究。性格孤僻,喜欢和学校不成文的制度作对,喜欢维护正义和友谊,但是最后却沦为精神病患者。“失落”的开始是对教书育人的老师的失落,不尊重学生的尊严和个性发展,任意处罚,是失德;政治课和历史课不讲知识专门讲野史、稗史,是失职;升旗演讲限制题材,搞虚假情感,是失真,使得霍家麟不得不成为他者眼中的另类。在躲避“失落”的足球场里,他意外收获了与李默的友谊,当得知有人顶替了李默去新加坡留学的名额,他大胆地向校长写大字报揭发孙老师,自己却被告知退学回家。父母对他的期望,反而加剧了他的悲剧人生,由于家里靠卖肉为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供他求学,然而他的不学无术让父母陷入失望,逐渐转变为怨气,这使父子矛盾升级。辍学后,他无心工作,祈求书籍能够宽慰自己的灵魂,却无法直视卧病在床的父亲,最终他在迷茫中求索无望,陷入深深的失落,并患上精神疾病。当李默从医院离去,家麟对他最后的嘱咐语标志着这份“失落”走向最终的悲剧。李默,是迷途知返的“失落者”代表。在第一人称视角下,读者找到了李默“失落”的源头:下岗潮带来了家庭经济危机,父母的期望与学校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李默的精神出现张裂。现实的反差使这份“失落”进一步深化到内心,形成自卑的心理,这源于他去许可家里的一次经历:当头顶上硕大的吊灯发出柔和的光时,他的脑子曾一度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与自己家里暗黄的灯泡比起来,眼前的一切似乎是不真实的,他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他一直所熟悉和痛恨的世界,这种赤裸裸的体验和对比后,因物质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他内心扎下了深根。升学考试的失利笼罩了他全部的高中生涯,失眠症的好转让他“准备选择像大多数人一样,无赖一般地活着”①双雪涛:《聋哑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逐渐地自我放逐,而青春的孤独只有当他在厕所抽烟时才有种被释放的错觉。高考的失利使这种颓废、自暴自弃的情绪又延伸至大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原本在这条迷途中准备荒废一生的他,却在爱情中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机。年少时的爱人在十年后出现,因一本日记而发掘出他的写作天赋,并鼓励他创作,当《一生所爱》被发表到某著名刊物时,李默的内心有了觉醒的声音,这种失落后孤独、孤独中迷茫、迷茫后自暴自弃的人生下线中断了,他开始尝试进入新的领域,而此时爱人的离开又将他打回原形。正是她的离去完成了他的青春成长。在与母亲的相处中,得知父亲离去的故事,他顿悟了,他终于在迷途中发现真正的自己,开始有意义的人生,正如他所说:“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①双雪涛:《聋哑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迷途知返、重寻希望的失落者还有他们:《跛人》中的“我”失落于高考压力而离家出走,最后重新回来复读;《大路》中的“我”失落于学校、亲人、社会,得一“小女孩”的温暖帮助而告别盗窃选择铺路的职业,并坚持积极读书;《走出格勒》中的“我”也是选择学习作为逃离恶劣环境的出路。柳丁,迷茫堕落的“失落者”。柳丁的悲剧在于母亲的离去,父爱的缺席。在自我与他人的叙事线索贯穿中能够判断,从小与姥姥一起生活的他,一直在苦苦寻找母亲,对于母亲的想象均是在他人的回忆性语言中建构而成:“母亲大概一米六五,长头发,方脸,有点兜齿,走路有点内八,细腰,抽红梅,在春风歌舞厅当收银员,慢三跳最好,一只耳朵有点萎缩。”赵戈新的出场则填补了他对于友谊和父爱的缺失,被老师当作差生的他在老赵这里找到了平等。此外,赵用力刷牙的行为让柳丁误认为他当过兵,而当兵曾是柳丁的梦想。再者,赵愿意充当故事的倾听者,教他吹口琴,带他去影子湖钓鱼,等等,这种父爱般的陪伴正是柳丁所缺少的。当柳丁计划与赵一起去北京找母亲时,赵充当了他行为的支持者和精神上的共鸣人,所以当出水痘的赵向柳丁道出杀林牧师可以得到路费时,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并在赵的指导下完成一次完美的刺杀,虚假的父爱成为了“失落”的助推器,柳丁堕落进犯罪的深渊。这三位典型的子一代失落者“失落”的原因都涉及家庭因素,与父亲对立的高家麟、受父爱压抑的李默以及父爱缺席的柳丁共同构成了双雪涛笔下“失落者”的子一代形象。
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父与子关系的绝对性和不可选择性是中国“忠孝”文化的伦理前提。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父亲”的角色,学者郑家栋总结出父与子关系的三种诠释面向:一是着眼于终极超越者的关系,二是着眼于身份伦理和社会契约的关系,三是着眼于文化类型。②郑家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及诠释的面向——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起》,《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父辈的品格和行为作为影响子一代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重返20世纪90年代下岗经验叙事中,双雪涛对父辈们失业的伤痛进行再度体验,挖掘出父辈们对于社会的“忠”,对于家庭的“孝”,在子对父的依附中,讲述父辈对自主、公正、法律的社会契约精神的追求,用自身经验来完成“父权”的重新建构。《北方化为乌有》中的老刘是落寞时代的担当者,作者从小说家刘泳的角度布局了一场亲身经历的无头凶杀案,在饶玲玲的反问下和陌生女孩米粒的年夜来访中逐渐拼凑出案子的原貌,老刘的形象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工厂即将倒闭时,老刘为了救工厂和工人,不满车间领导的“小舢板突围”策略和大批裁员行为,决定写材料寄给五个部门,举报厂长副厂长四人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工人养老保险在农村买地给自己盖房等行为,却不料被人暗算,凶手从排风口进入办公室将伏案的老刘一刀杀死,而这一切被身处于衣柜内的米粒的姐姐所目睹。工厂倒闭,则意味着工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家园,以工厂为象征的“北方”则化为乌有,老刘用生命作为砝码,不畏强权,担当起守护家园的责任。虽然他失败了,但这种精神永不泯灭。《大师》中“黑毛”的父亲,是下岗界的一股清流,嗜酒与棋,却从来不赌,以棋交友,棋外家庭,棋内温情,让无腿老和尚心服口服。在那段“失落”的岁月中,父亲不追求棋艺输赢,只追求精神富足,正如李振所说:“在一盘有输赢的棋里,双雪涛写出了没有输赢的人生:落寞也好,坎坷也罢,从地上捡烟头抽的父亲在他的棋里获得了心灵的超脱,而没了腿的和尚却在世俗的情义里了却凡尘。”①李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冒险——双雪涛论》,《百家评论》,2015年第6期。当父亲处于人生低谷时,棋局的博弈成为了自我疗愈的途径,在与他人共情中领悟人生。《棋王》王一生是知青下乡时代的隐士,黑毛则是20世纪90年代工人下岗的隐士。《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是时代的追梦人,他的梦来自父辈李正道的“爱折腾”,信奉知识就是力量,劳动创造自由。下岗的“失落”、生意的失败、婚姻的不幸让他萌生出逃离的意识,于是他改造飞行器,带着抑郁的儿子和小儿麻痹的弟弟乘坐热气球飞向南美洲。“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最后让人关在岛上,这辈子也算有可说的东西了。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②双雪涛:《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5页。这是父亲李正道传给李明奇,李明奇又传给小峰的话语,这种对梦想不懈的追求和迎难而上的精神是子一代身上所欠缺的。
双雪涛运用魔幻的手法讲述父与子的故事,结尾的开放性处理方式,使读者走进历史现场,并从中体悟时代人物的艰辛与苍凉。此外,双雪涛的小说语言善用短句,字里行间带有独特的东北方言特色,营造出黑色幽默的氛围,在叙述“子一代”的青春孱弱与孤独中,注入了一股悲伤和忧郁的气息。作者对父辈失败的体验叙述中,寻觅精神遗产,发现了失落的阶级光芒,重寻属于父辈的时代精神,工人尊严和荣誉,给当下青年以抵抗沉沦、重塑人生价值和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正如黄平所说:“‘父亲’净化了这类小说中软弱的悲悯,以不屈不挠的承担,肩住闸门,赋予‘子一代’以力量。”③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双雪涛骨子里缺少不了父亲的影响,他在与张悦然的对话中也曾谈及:“父亲当了一辈子工人,却极爱阅读,喜欢下棋。”双雪涛的小说中确实创建了相似的人物,如《大师》中的黑毛、《飞行家》中的高旭光等。中国作家需要从父辈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和灵魂向导,从而摆脱青年的迷茫和空虚的日常,实现向内心灵的超越,谱写“我们”的当代史。
二、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裂痕
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光芒,工人的身份则带有国家共同体的光环,他们同样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国有企业转型,大批工厂倒闭,“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拉开贫富之间的差距,知识分子大多走上了经商之路,反观工人群体在遭遇“下岗”后只能选择廉价的生计过活,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种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此时的失衡也正是改革之后的“阵痛”。“互相区隔甚至是相互仇视的精神状态导致了一种巨大的分裂——不平衡总是与分裂密切相关——一种可望的共同体形态彻底破裂了。”①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任何一种故事的结构模式一旦被确立,便会逐渐给阅读带来思维的惰性和走势,从而减弱甚至取消读者的想象和沉思。这种状况导致了故事叙述规则和叙事技巧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②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双雪涛用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叙事策略来讲述“失落者”们的故事,在线索的不断展开和视角的多重变换中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平原上的摩西》通过7个人的视角勾勒出一条时间线,但是唯独没有李守廉的第一视角,在傅东心、庄树、庄德增、李斐、赵小东、蒋不凡的讲述中建构起他的整个人物形象。作为下岗工人,他失去了发言权,而晋升到新阶级的庄德增则拥有了新的社会身份和话语权。作者运用巧妙的行文方式暗示了知识分子与下岗工人在时代伤痕下的不同命运。
经商之路上的典型知识分子是《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庄德增,1995年,他脱离卷烟厂,南下做生意,给人画烟标,拿技术入股,赚得第一笔资金后回老家承包了印刷车间,接管了以前的工厂和工人,敏感的商业头脑和非凡的远见,使他走向了财富积累的道路,渐渐进入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等行业。反观工人群体,自谋出路的状况充满无奈和辛酸,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低成本的行业谋生,例如卖苞米和茶鸡蛋,有技术的工人会开诊所或者当出租车司机等,这些职业都是社会底层中较好的,不好的则是成为了犯罪分子、无业游民、醉汉等。双雪涛笔下的李守廉正是“失落者群像”中的代表,从普通下岗职工不慎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下岗前,他是小型拖拉机厂的钳工,技术被人敬佩的李师傅,人缘好,从小便与庄德增相识,妻子在生小斐时离世,后来厂子里经常有人给他织围脖和毛衣,傅东心也收了小斐做学生,并传授文化知识,女儿也乖巧懂事。生活的平静被下岗所打碎,先是好友孙育新向他借钱开诊所,后又将多年珍藏的“文革”邮票卖掉为女儿筹集9000元学费。1995年的平安夜,为了给女儿看病,被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警察蒋不凡怀疑为近来杀害出租车司机的犯罪分子,意外中,女儿出了车祸,半身瘫痪,愤怒的他将警察打成了植物人,父女二人靠着孙育新的接济,过着逃亡的生活。这一场变故迅速将他推向物质贫困的深渊,女儿身体上的残缺给父亲带来巨大的打击,精神创伤就此形成。十二年的时光带走了李守廉对于现实世界最后的期望,他的内心之中布满伤痕与厌恶之感。当他看到卖苞米的女人被城管欺负,女孩的脸被烫伤,城管却逍遥法外时,隐藏于心的精神创伤再次被放大,面对如此残酷的场景,他无法选择沉默,拼上一切只为维护内心之中最后的“道义”,他将两个城管杀害,真正成为了杀人犯。
双雪涛在小说中安排庄德增与李守廉这两个人物,巧妙地安排二者相逢的冲突场景,从而呈现出文本的多样性,西装革履的庄德增在返乡时乘上李守廉的出租车。冲突一:堵车钱的支付。庄认为将耽误司机的时间折合成现金,是对劳动者劳动的尊重和补偿;李则认为,给多余的钱是侮辱了他,把他当作奴才看待,并赶庄下车。冲突二:讨论主席像下静坐的老人。庄认为老人念旧,借这事泄私愤,忍着就有希望;李认为老人是不如意,将其比喻成海豚,海水污染了,它们就上岸集体自杀,懦弱的人才这样。冲突三:主席座下的保卫战士的数量。庄忘了,而李能清楚地说出:“三十六个,二十八个男的,八个女的,带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持冲锋枪的三个,背着大刀的两个。”①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4页。通过以上分析,从中能够发现庄已经由知识分子变成资本家,站在资本的逻辑立场上思考问题,淡化了情感,遵从金钱至上的思维原则;李站在底层人的立场回答问题,充满真情实感。关于对共同体的想象和故乡的情感,搬家后的庄对于故乡的记忆和情感逐渐淡漠,他脱离了共同体,走向资本的市场;而李则一直保持对共同体的想象,用共同体时期的原则对抗世风日下的现实。
三、女性的救赎
“失落者”群像之中一定不能缺席的即是女性形象,双雪涛笔下的女性形象被其注入了“救赎”的元素,这一元素的功效便是女性情感意识的显现。小说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主要按年龄阶段划分:女青年失落于友情、学业、亲情和爱情;母亲失落于家庭;老妇则失落于苦命的人生。女性的多愁善感体质一方面将伤痛向内转向自残,向外仇视社会,另一方面则会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力量,借助宗教的方式实现自我救赎,释放自我的情感意识。针对人性中的缺陷和顽疾,女性怜悯与温柔的天性,给予“新伤痕时代”中的人们以爱的呵护和疗愈。
失落于友情的李斐,她的悲剧源于友谊中爱的不对等,一方拼命在乎,一方熟视无睹。李斐出生时母亲离世,母爱的缺失让她对傅东心有着天然的依恋感,她十分珍惜和小树的友谊。开始的失落是傅东心对待小斐和小树的态度造成的。傅老师对她的教育和关心让她感觉到母爱的温暖,却让他感觉到母亲的陌生。由于傅老师的原因,小斐对小树是一味地容忍和关爱。在情感的天平上,小斐的爱在下沉,悲剧在悄然酝酿。小斐为了在平安夜给小树一个惊喜,她带着汽油向父亲撒谎说肚子痛,想去孙育新的诊所看病,其实诊所附近的高粱地才是她的目的地。这一晚,李守廉被怀疑成杀害出租车司机的嫌疑犯,她遭遇车祸,半身瘫痪。这一晚,小树忘记了赴约。时隔多年两人在湖上相遇,小树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案子查到李守廉,永远不会找她,她的内心陷入更大的失落。在这场友谊里,她是牺牲品。尽管如此,她还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②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3页。情感的天平在这一瞬间平衡,他们又回到儿时的“平原”,它铭刻了作为生命本质的爱与美。③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失落”于老师的教育方式而向外攻击他人的陈书梦,因老师的宠爱和私心而精神成疾。当她因管理纪律而收到很多纸条时,金老师为了免遭学生的报复,将写满错别字和朦胧爱意的纸条归罪于她的不检点,这一标志性事件从此开启了她“失落”的旅程,她变得沉默寡言,专心学业。面对即将来临的升学考试,巨大的压力使她出现了心理问题,一次模拟考试的失利则将她推向了挫败的深渊。金老师嘲讽她“越到关键时刻越不争气,到底是个女孩子,一见压力就没用了”,而她脸上温存的笑意惹恼了老师,进而遭受到更大的侮辱:她被她扯住红领巾,像牵狗一样把她从座位里拽出来,重复刚才的话。①双雪涛:《聋哑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3页。积攒已久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她将手中的铅笔戳进老师的腮帮子,最终酿成悲剧。“失落”于亲情而导致心理抑郁并企图自杀的安娜,四岁开始学习书法、钢琴、舞蹈,拿过书法全国赛的奖状,这种优秀却是在母亲长期的打骂和虐待中形成的。当她唯一的“朋友”——钢琴被母亲卖掉后,她迈向了“失落”的边缘,从此与她相伴的便只剩孤独。母亲是家里经济的来源,她的强势放大了父亲的软弱,她长期的外遇令他尊严扫地,他又因依附她的钱财而自欺欺人。父母的相处方式使她对爱情失去了期盼,终日游走在男性中间,她将爱情最后的希望赌在了李默身上,却没想到他也只是贪图她的美貌和肉体。安娜最终明白这个世界不曾有人给予她真正的关心和爱护,自此陷入更深的绝望,不断地伤害自身,一心寻死。除此之外,小说《天吾手记》中的“安歌”、《大路》中施舍给“我”钱和衣物的“小女孩”皆是因对亲情的“失落”而消失或自杀。“失落”于爱情的张可,被男朋友逼迫做皮肉交易,供养两个人的生活,而他自己却沉迷于网吧,她坐一块钱公交去向下一站的终点,可笑的现实将她打醒,没有灵魂只有物质的爱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小说《宽吻》中,双雪涛还塑造了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形象——海豚训练师阮灵,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使读者体悟到了生命之间的相惜,同时也能感受到生命陨落的伤痛。
根据波伏娃的观点,婚姻家庭在人的意义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是幸福家庭的维系者。知识型女性的代表——傅东心,当得知庄德增在“文革”时期打死了其父亲的同事,于是便对这段婚姻抱有戒心,李守廉在1968年救下了她被打的父亲,出于感恩,她对小斐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却忽略了儿子的成长,即使后来李家搬走,她仍到处找寻女孩下落,并给儿子留下了一张二人童年时期踢球的画。因画“平原”烟盒,她喜欢上了小斐,用母亲的温暖关照着女孩的成长,也正是这种爱为日后小树与小斐的重逢蒙上了亲情色彩,让迷失的二人重返儿时的“平原”时光。传统型母亲在双雪涛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小说《无赖》中的“我”母亲,每次搬家都带着一只红色的大皮箱,却从来没有打开过,“我”在情急之下撬开了锁,却发现里面全是土,“我”陷入认知的困境。在双雪涛看来,设置这样一个环节,母亲是为了给家庭留下希望而不是放大绝望,红色木箱子是母亲对家庭的爱,是为了激励“我”走出困境。这就好比如沙漠里最后的空水袋,只要它存在,希望就存在,人就会绝境逢生。《走出格勒》中的“我”母亲,丈夫进了监狱,自己下岗后从事卖毛嗑的小生意。生活的艰辛没有摧垮她的身躯,在穷困的环境下,她让“我”想象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正常的孩子,他们每天读书写字,长大后就可以坐在有电扇的办公室上班,惟有超越他们,才能跳出贫困的圈子,不畏艰辛的母亲最终还是为“子一代”注入了向上的精神念力。追梦型女性——张雅凤,独自承担失业的痛苦和抚育孩子的艰辛,她将希望寄托在光明堂的林牧师身上,虔诚地侍奉上帝并期待得到救赎,当所依赖的人倒在血泊里时,她拾起《圣经》,系上带血的丝巾,带着林牧师的爱和主的旨意走向南方,以博爱来宽恕和她一样挣扎于边缘的底层人,光明堂的倒塌深固了张雅凤的信仰力量。老妇形象的代表——柳姥姥,身体饱受冻伤的疼痛,心灵饱受情感的伤痛——丈夫死于矿难、儿媳扔下孩子柳丁,她将改变现状的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对主的侍奉中,渴望得到主的救赎。双雪涛小说中宗教常常被提及,却没有准确的定位,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似乎找到了神奇之门的钥匙,那就是底层人物无法言说的精神诉求,最终寻求宗教解答内心的困惑。
女性在文学的世界里大多充当着怜悯与温柔的角色,当“父一辈”面对现代化改革中身份的失位,难免会陷入情感、尊严与经济的两难,“子一代”在家庭的变故中势必将这种伤痕累加。反映在双雪涛一代的工人子弟身上,父辈所遭受的屈辱,给他们的童年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难忘的是父辈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母亲在困境中对家庭的守护,这是属于“下岗”职工家庭最后的慰藉与精神财富。“新伤痕时代”一定会留下新的创伤与疤痕,如果没有一种人文主义的关照,只会积久成疾。历史的真实性和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所忽略,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双雪涛把这段历史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用不可回避的方式正视这段历史,符号化艳粉街不是目的,疗愈时代所给予这群“失落者”的伤痛才是目的,激励当下青年摆脱父辈的影子,继承父辈的精神和母性的温暖,在时代的巨变中站稳脚跟,探寻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
结语
双雪涛笔下的“失落者”是对“新伤痕文学”的回应,从杨庆祥所提炼出的抽象的时代情绪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时代人物形象上,有助于我们对“新伤痕时代”的理解。正如黄平所认为的:重返历史,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向度,它从“地方”开始,但要始终对抗地方性,严重一点讲,也可以说对抗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以来将地方“地方化”的趋势,重新从“地方”回到“国家”,从“特征”回到“结构”,从“怪诞的人”回到“普通的人”。①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双雪涛所塑造的失落者凸显了父与子、知识分子与工人、母与女的形象关系。他们在家庭、社会、婚姻爱情、学校友谊中体会不同的失落感,他们中有梦想的追寻者、时代的堕落者、道义信仰的守护者、清醒的行动者、醉心的隐士等。“失落者”是“新伤痕文学”中的主力军,在继承“五四”人文主义精神的过程中,双雪涛以独到的笔触刻画出了新时代的人物群像。
“失落者”形象进一步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变革之中的历史,对底层人物怀有同情和悲悯之心。从双雪涛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之情,他呼吁尊重人的价值和社会权利,直面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特殊的历史阶段,给底层人民以人文主义关怀,继承了左翼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写作手法,坚持对现实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文学的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相互滋生的。只有当这种创伤被表达出来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所在、问题的根源所在。”①杨庆祥、魏冰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和“爱”了——“新伤痕文学”对话》,《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双雪涛通过写“失落者”,进一步揭露出形成社会创伤的根源,给予失落者一份跨时空的理解和爱。从第一代东北作家群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到“新东北作家群”的双雪涛、班宇、郑执,其共同之处在于对困境中底层人物的书写,揭露传统文化遗留在人思想中的痼疾,同时表达对故乡故土故人的生命共情。双雪涛与东北大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一道,歌颂东北大地上人们骨子里怒放的生命力和不息的抗争精神,以人文关怀表达了“爱”的哲学,呈现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一个充分包含了文学如何在‘地方生产’的故事才最后形成了值得期待的‘中国文学史’。”②李怡:《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双雪涛的“地方”文学生产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失落者”群像的构建正是双雪涛对于自我成长经历的回顾,为那些无法言说、不被关注的底层民众代言,重返历史中加深对人与社会、人与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随着“铁西三剑客”“工人村”“东北文艺复兴”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关于“新东北作家群”“新的美学崛起”“东北地域文化”等问题也迅速升温,可以说双雪涛、班宇、郑执重新开启了阅读者对于东北地域文学的想象与认识,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条研究“地方”文学的路径,重新审视“共和国长子”成长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