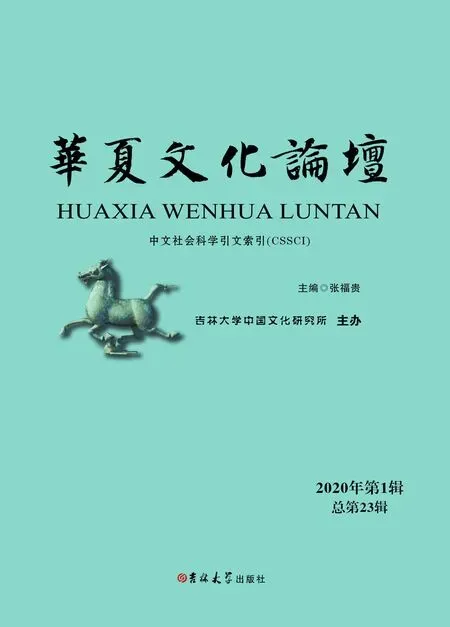租界体验与都市上海的“逆向”书写
——以20世纪30年代鲁迅杂文创作为中心
丁 颖
“上海,因着它的中心地位,在国内成为南北关系的焦点,在洲际成为东西关系焦点……文化是一个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而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整体接触,最多的地方恰巧在上海,在租界。”①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在上海的地理文化场域中,“半租界”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的区域,是“越界筑路”的产物。作为西方殖民势力的延长线,发挥着为租界“开疆拓土”的现实作用。无论是租界制度、文化风俗还是政治伦理,华洋两界包括租界内部不同文化归宿的租界人都存在着“短兵相接”式的文化接触。这种表现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的“去中国化”自然强化了租界人的生存体验,并赋予华人世界中国现代性“被动嵌入”的文化屈辱感,形成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性生成过程与“中国殖民境遇”因果关系的探求:“后来者的上海,现代化最初是被强加的外来之物。上海的崛起,本身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后的产物,是以服从列强——先行者自身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殖民侵略、商品与资本的输出等为前提的。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半殖民地的缩影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的被强加程度也最高,无论是租界、法律、市政、社会组织、工厂企业、生活内容与方式等各个方面,无不由被强加而来。”②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一、都市人与租界人的生命体验
伴随近百年殖民历史的演变和型构,中国近现代以来包括广州、天津、上海等主要区域都典型地经历着“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上海因租界史中的特殊地位而在殖民症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里,“租界”和“半租界”不仅具有空间地理学的意义,同时也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将指涉功能反作用于人,参与到人的社会活动和心灵活动的建构过程,形成了城市空间形式文本意义上的建构与表达,鲁迅上海时期带有殖民体验气质的都市创作即是其中的经典文本。
早在厦门时期,鲁迅在与景宋通信集中提到了“穿湿布衫”的生存体验。几年后,鲁迅致信给郑振铎也提到了这种“穿湿布衫”的感觉:“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Grotesque(英语:古怪的,荒诞的),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而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①鲁迅:《书信·331202·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在这里,除了对上海文坛由历史“合力”所形成的极其浅薄的文化形态发出自己的感慨外,同时也可以作为鲁迅生存状态的通约性理解:第一,它本身即是鲁迅的生存寓言。这种不适感和异己感是没有时间和场所限制的,是一种永远无法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交融到一起的“在而不属于”;第二,它可以更确定地指称鲁迅在都市上海的殖民体验。一种由殖民都市所拥有的文化景观和城市景观的“陌生化”所带来的文化心理上的差异感和疏离感,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审慎的怀疑精神,拒绝一种“和而不同”的“兼容”。
鳞次栉比、拥挤不堪的都市空间挤兑、压抑着人们的心灵空间,不绝于耳的永远是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市声”,还有由城市环境熏陶形塑的“都市人”和“租界人”所构成的生活常态:“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风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②鲁迅:《华盖集续集·上海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20世纪30年代,屡遭革命之梦放逐的鲁迅,最终选择上海作为生命十年最后的壕战之所。生存空间的狭小和逼仄使其思想的翅膀,从“荒原”和“旷野”形而上的精神领域旋起旋降于现实的人间,在“租界”“弄堂”里认定“这也是生活”,其艺术的想象和哲学的沉思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中找到一种落实,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使作家以“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作为“释愤抒情”的工具,以杂文创作作为都市写作的主要文体和形式。这里不仅有着“时代的眉目”,“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并且“实质上潜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灵魂,把握了这个事件和物象所构成的世界的矛盾和张力,表现了现代生活不连续性和断裂的特点”。③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85页。
二、“亭子间”的文化质询
1934年,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中写道:“入民国后,(日本人)忽而唆使袁世凯为皇帝,忽而协助蔡锷以抗袁,忽而挑拨南北感情,忽而助奉入关,忽而出兵阻拦北伐,实皆彼多年阴谋计划,至此实现。中国上下皆堕其术中,而不知其悟。”①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3-54页,第184页。而鲁迅,正是以其大胆怀疑、深度质询的思维模式,深刻透析异族人的“文化阴谋”。这既是鲁迅生命意识释放的需要,也是鲁迅社会感知的理性选择。“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②鲁迅:《两地书·北京》//《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以一种反常规的叙事策略和政治敏感,“从表面的繁荣底下,看出持续的荒芜和破产,从‘现代’里面,发现明季和宋末的幽灵;从每每遭人轻蔑的底层民众的被动状态中,他看到了深藏的清醒和透彻;从若干新颖的旗帜、姿态和运动当中,他更觉察出向来深恶的专横和奴性”。③王晓明:《鲁迅式的眼光》//一士:《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对西方文化观和艺术观秉行“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借用语言“反方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外国人从异域来到中国,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描写。在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的笔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文章里以及法国学者保罗·巴迪的谈话中均有对“北京魅力”的痴迷。其实在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中也有一篇命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文章:“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沉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④[日]鹤见佑辅:《北京的魅力》//《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这篇文章引起鲁迅的注意,也激起鲁迅的震悚和对殖民文化“异位”介入的预知。作为鹤见佑辅随笔集的中国翻译者和介绍者,鲁迅出于对殖民文化的警惕和预见性的忧虑,并没有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和痴迷那里获得自豪感和欣喜感,而从问题的反面,以迥别于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出于对异族人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所包含的“文化阴谋”的洞悉和谙熟,发出了显然不同于他人但又发人深省的质询和诘问: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的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加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这当然不仅决定于“尖刻”“多疑”的思维特点,与“黑暗捣乱”的故意玩玩,在谩骂和蔑视面前乐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两个字”,而是身外和身内挫败后的经验总结,是“反抗绝望”的斗争哲学。正如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中所阐述的“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记忆、非凡的经历”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页。一样,东方是西方的目的物,是“一种谋生之道”。“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推论东方是低于西方的‘他者’,并主动强化——当然甚至部分是建构——西方作为一种优越文明的自身形象。”②[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在由异族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上升到殖民侵略隐秘心理的分析中,显现出“鲁迅式”的思维特点:“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③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十年后,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行为的现实教科书,鲁迅对外国人的某些做法有了具体而明确的理解:“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够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是嫖赌的天国。”④鲁迅:《书信·340306·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350页。
三、上海镜像描写与反思
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做出了犀利的判断:“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⑤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7页。以此反观上海的殖民世界,就会找到一种对应关系。在增田涉的观察中:“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接触到内心’的现实,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⑥[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页。在这个有幸师从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人眼里,鲁迅对于“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⑦[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页。既防止做本国人的奴隶,更警惕做异国人的奴隶。即在民族内部植根于历史纵深处的“主—奴”精神结构和封建传统文化的“食人性”之外,截取“交通传来之新疫”极富病态的部分:东方主义在上海租界现实性的落实。熊月之亦认为,“在对上海城市的认知描述中,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上海形象开始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⑧张鸿声:《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24页。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鲁迅难以享受“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幻象之外,敏感地触及了西方社会形态的变异: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是“帝国主义”,从对东方主义理解的现实深入性角度看来,鲁迅并不比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逊色多少。
带着这样的文化感知和预见性的智性敏感,在鲁迅的视阈里,上海社会泾渭分明地被区隔为这样一个世界:“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①鲁迅:《集外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10-311页。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鲁迅接着对上海的租界进行类型上的划分和概括:“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②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这种殖民社会形态构造,在西方人哈洛德·伊萨克那里也有过类似的说明:“代表殖民势力的外国人,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上层华人买办,及有限的华人竞争者;大批在外资和中资受雇的中方白领,以及从赤贫的乡村涌入的贫困潦倒大众,他们成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搬运夫、乞丐、妓女、罪犯和一群无助的人,这些人每年在城市街道上留下50,000个死婴。”③[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在这里,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外国人,接着则是那些粗懂洋文、发挥桥梁媒介作用的读书人、华人买办。其次则是奴才和遥距于权门之外的社会底层人物。有别于鲁迅上海创作所塑造的形象系列,外国殖民者形象作为新的艺术典型,在“半租界”近距离的审视中得到了阐发,并且通过“推”“踢”“冲”等极富动作意义的行为表现出来,在杂文《推》《踢》《冲》《抄靶子》中有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接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板,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在黑格尔的线性历史哲学里,曾提及“民族精神”只有符合“精神”通向“真理和自觉”的形态,一个民族的历史才能步入“世界历史的行程”,因而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实在太古老,但由于中国缺少“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的对峙,它无从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黑格尔的警言暗合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他者化”的隐秘心理,也震悚着中国知识阶层本不平静的内心。临去上海前,鲁迅曾创作《略谈香港》,在那个为英国人全面殖民的都市里,作者的那场自己视为“老生常谈”的讲演就颇多受到“干涉”,点滴的细节宣告着中国人没有言论的自由。不仅如此,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更是饱受殖民奴役的痛苦和屈辱。不是“被抽藤条”,就是为英警“执行搜身”,并且领受英国人横暴的训斥:“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相比较而言,殖民主义在上海也不是“幽灵”的存在,而是现行的具体的存在。不仅动作密度大,而且极其穷凶极恶,“踢”“推”“冲”以及“抄靶子”等动作中,张扬着殖民主义者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充满对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中国生命的贱视。作为殖民主义者文化行为的直接表述方式,“洋大人”粗鄙化的行为蕴涵着西方历史和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来自异族并施于异族的种族歧视和殖民同化。并且,更有深意的是,同样粗鄙化的言辞也深刻地透露着萨义德所言的权力与话语、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在无主权的生存境遇中,只能接受着被代言、被强加的命运。不仅要接受损失,而且还要蒙受羞耻。
四、文化殖民批判与世界人意识
不仅如此,鲁迅还在电影中看到西方人的“文化阴谋”,看到他们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人的驯化和奴役:“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糊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糊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①鲁迅:《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军事上的统治和征服可能是暂时的,相反可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抗压的决心和“复仇”的斗志。而文化的奴役和教化则是危险的,更何况这民族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善于向异族人宣扬“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三年后,鲁迅则以孺牛为笔名,撰写了《电影的教训》一文,发表在1933年9月11日的《申报·自由谈》中。
但等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到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预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想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在电影院这个原本可以获得休闲和娱乐的场所里,鲁迅却将电影内和电影外的世界连接起来,在浑然一体的结构中,剖析电影作为一种以画面和声像为媒介的现代艺术所具有的或悄无声息或惊心动魄的文化殖民能力,在浓郁的文化消费气氛中显现其独有的冷静和深刻。既揭露了文化殖民主义者的险恶用心,也更为痛惜地批判了国人毫无痛觉、毫无判断力的昏迷、愚蠢,而这只能造就奴隶和奴才的命运。借此更充分地彰显了鲁迅“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和“更为清醒的现实精神”:“我知道了鲁迅所说的‘奴隶’‘奴隶’,是包藏着中国本身从异族的专制社会求解放在内的诅咒,同时又包藏着从半殖民地的强大外国势力压迫下来求解放在内的二重三重的诅咒。……必须理解到,他的愤怒、悲哀、热骂、冷嘲、讽刺、讥笑,或者他常说的‘寂寞’,是他肉体的呼吸,是他根涤的意志。”①[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页。
细腻的近距离的观察洞见,恰是对鲁迅精神世界中重要关键词“奴隶”的提取和发现。对“奴隶”一词的切实敏感可以说是伴随着鲁迅的生命全程,在言词间也多有流露:“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③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还有“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后成奴隶的奴隶”及“奴隶总管”等对革命的警惕和总结。而尤其让鲁迅痛惜的是,不仅是要做直属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的、现存制度的奴隶,而且因民族性格的不振拔而再度沦为异族的奴隶,所以是谓“二重三重的诅咒”。对西方殖民行为进行直接的文化批判无意识地消解了那些主导叙事:“仅仅将上海看成是‘黑暗的城市’,看成是‘必将蔓延到中国其他部分去的罪恶的化身’,而‘不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反殖民根据地’。”④[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在现代性批判的缺席和黑格尔线性历史观输入的推波助澜下,‘五四’世界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日益获得霸权,而真正的反殖民话语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出现了。”⑤[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确立的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二患并伐”黑暗现实的双重疑惧和控诉,也凸现了鲁迅精神世界中追求平等、追求民主的“世界人”意识。
——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