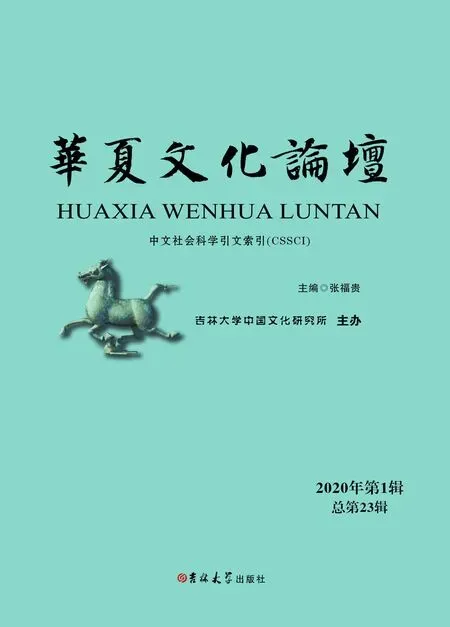姚莹入藏诗的志士形象塑造及诗史意义
温世亮
【内容提要】姚莹是嘉道时期著名的经世文士,他以负罪之身两度奉使康藏。此间创作的诗歌,情思复杂而丰富,不平之鸣、现实喟叹与志士胸怀交会,既表现出强烈的生命体验,又洋溢着积极的事功意识。结合姚莹的仕宦经历及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背景考察其入藏诗,不仅有助于认识诗人当时的人生心态,而且有益于体会其诗所塑造的志士形象。姚莹入藏诗所塑造的志士形象,在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不乏典型意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均见突出。
姚莹(1785—1853年)既是鸦片战争前后极具影响力的政界人物,以学问经济名于时,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又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诗人,“姚门四杰”之一,在道咸诗坛不乏声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姚莹于台湾击退英夷侵犯,却于二十三年(1843年)以“贪杀冒功”罪革职下刑部狱,明年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调至四川补用。自此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间,姚莹曾两度奉使康藏乍雅、察木多,以抚谕两呼图克图之争,历时凡一年零三月,并据沿途见闻而成《康輶纪行》一书。查检《康輶纪行》,沿途所为诗89首①本文所引姚莹诗,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均录入《后湘续集》。就实而言,这些作品都具有纪行性质;但更重要的是,姚莹乃以负罪之身发配至四川补用,境况特殊,他的入藏诗,因此亦难免要被涂抹上一层悲苦的色彩。不过,姚莹一生以经世为怀,其入藏诗,情思复杂而丰富,既表现出强烈的生命体验,又洋溢着积极的事功意识,诗史意义又是显在的。
一、“不能恝然无恨”:激愤凄厉的不平之鸣
奉使入藏是姚莹生命中一次颇具政治意味的遭遇,也是其经历刑部狱后的又一次人生历练。讨论姚莹入藏诗,自应结合其政治遭遇及因此而产生的人生心态来展开。
至道光一朝,“至明代而始大且久”的“海盗之患”此起彼伏,东南沿海的鸦片贸易亦日益剧增。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无视外交的重要性,忽略英美等夷蕃之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终究发展为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①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0年,第292-317页。。入藏前亦即“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曾为台湾道五年(1839—1843年),在与英夷的军事对抗中屡建战功,为英夷和议和派所忌恨。正是受英夷之蛊惑威慑,在穆彰阿、耆英等朝廷议和派的助力下,姚莹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贪杀冒功”罪革职下刑部狱,这就是方东树《寄饯石甫》小引所谓“石甫任台澎道四年,召募义勇三万余人,挫败英夷。英夷惮之不敢近,故连年浙粤、江南皆丧地失守,而台湾独完。英夷忌恶之,诬讦致抵罪,被逮入狱”②[清]方东树:《方东树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59页。。对此遭遇,姚莹能豁达以对,称“莹现所处,人皆以为患难。莹曰,非也。……为人臣子,仰体圣怀以全大局,非一身之利害得失,亦非一身之困穷阸塞也。……人情耽耽不能已者,徒以一官耳,莹之得失岂在一官耶”(《又与方植之书》)。不过毕竟是蒙冤受屈,终难坦然,故其亦有“此心有不能恝然无恨者,则天下之忧,此即翁不忧一身而悲愤时事之意云尔”③[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7页。的不平之鸣。对议和派、英夷,姚莹多有声讨,《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台湾镇、道冒功,上干天听。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己美,未有称举众善,而谓之冒功者也”④[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与余小颇书》“英夷之狱,议和诸帅皆欲甘心镇、道以谢夷人”⑤[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70页。,等等,无不是对台湾事件所给予的正面回应。
梳理以上文字,不难发现在姚莹的意识中,“杀俘冒功”既使自己蒙上了欺上瞒下的污名,又让自己无法再像既往一样投身热衷的功业,言辞中不时传达出郁愤凄苦之情。在《再与方植之书》中,他将在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却流放伊犁的林则徐、邓廷桢等引为同道,故作“相聚西域”的和乐之想。然而,姚莹乃以天下为怀的志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避居一方“乘暇读书”⑥[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非其愿,文章读来并不难体察那达观中见凄楚的心境。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姚莹出狱后发配至四川补用,又以“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莹徒以不能善事贵公而得是役,且一再罚之不已”(《复光律原书》)⑦[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两度奉使康藏抚谕番僧。入藏之行,一如《复光律原书》所谓“沈困阸塞之中,鸮不变音,老而弥笃,作为是书,皆中正平实为归,初非有怨愤不平如司马氏之意存诽谤,而斤斤以人心世道为忧,皦如白日,自谓宜无恶于君子”⑧[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怨愤不平”自是姚莹下笔时的特有心境,他的入藏书写当然与之相关。
出使乍雅前,姚莹有系列赠答诗。这些作品固然有临歧一别以示情谊的目的,但又非止于此。相反,它们恰恰构成了一组重章叠句、后先连缀的抒情篇什,往往能于诗人凄迷低回的反复咏叹中体会其悒闷难言的心绪。如《息凡见和奉赠之作且送余西征依韵为别》是入藏前第一首:
怪底瑶华惊老眼,相逢鹦鹉托深杯。文章有道宁憎命,山水多情未尽才。万里星轺
邛笮近,五更边月帐牙开。康居秃发君休问,雪岭冰天一骑来。
无论“文章憎命”,抑或“未尽才”,难免都带有自怨自艾的意味,而究其根源,与其此前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自脱不了干系;只是身不由己的孤愤哀怨已化作“相逢鹦鹉托深杯”时的知遇感慨。而《翼日达庵亦有和诗二章三疉前韵酬之》其一“别史恨长千载近,奇文境险五丁开”、其二“长沙不用嗟迁客,赢得支机天半来”,或曲写身临之困厄情境,或以贾谊自况,悲苦的遭遇,伤感的情怀,委婉的批判,均不期然地显现。
随着入藏行程的深入,其诗所蕴含的怨愤的情绪亦越发清晰。总体看来,沿途所作,融情入景,多见凄寒的色彩。如《瓦斯沟》首颔联所写景——“荆榛蔽石杂芳椒,击柝传呼斥堠劳。斜日破云穿屋漏,远山横路束群腰”,实乃黑暗世路的返照;而结尾之情——“序逢小雪惊时晚,人耐卑官任客嘲。此去鱼通无百里,渡泸谁见水源高”——与景谐和,苦闷无奈中所折射的正是诗人身遭冤屈后的自我伸张。
又《出炉城寄示浚昌》一首:
濯龙锦水渺如烟,杜宇蚕丛又一天。夺色岂无人恶紫,着经犹望汝通玄。萧条门户
寒儒分,桀骜蕃僧下吏权。终是出关乘使传,得平蛮触即安边。
看似兴叹家族门第的衰落,结末云云亦蕴含着宽慰激励,似乎让诗人看到了生命的曙光。不过,仔细揣摩开首的描写议论,由霞光灿烂的通途走向逼仄的险境,由“恶紫夺朱”的兴味到“著经通玄”的期许,化典为实,冤屈与希冀同在,饱含诗人于崎岖生命的体验,呈现诗人对正义的呼唤,从中我们又不难感触诗人的一腔抑郁和激愤,而这样的情感原点,又与其入藏前的遭遇相呼应。毕竟,在靠读书仕宦以耀门楣的时代,姚莹的冤屈难免会成为其家族走向没落的重要节点。他如《折多山雪》“怪底舆中寒起栗,无端风雨却横经”、《里塘乌鸦》“生憎窗外乌声恶,莫作长沙鵩鸟魂”、《头塘晓起冒雪登山》“怪石欺人立,重山让荆肥”、《将至巴塘》“遐荒怜汝苦寂寞,野鸽朝暮空飞呼” 等浓情笔调,无不是以藏地奇异的自然景象为底色而生发,或托物抒怀,或直抒胸臆,反映的不平意气却是一致的,亦是清晰的。
二度入藏,因两呼图克图之争一时难以调停,姚莹久寓佛寺,尝为《秋寺》一首:
年来况味是行僧,踏遍千山雪里冰。尘榻鼠跳闻夜雨,佛龛香冷坐秋灯。江湖鸥鹭
原无竞,吴越莺花谢未能。袅袅西风吹落叶,祗陀园畔听呼鹰。
姚莹称此诗乃“秋日无聊”而作,不过笔者以为这样的“无聊”之作恰恰反映了诗人的胸中真意。综观全诗,行程之苦辛,身世之艰难,边事之复杂,闪烁其间,内涵丰富深刻。诗人以“行僧”自居,笔触跨越空间的鸿沟,由佛寺而江湖,由康藏而吴越,显现的正是一个“鼠跳”嘈杂的现实世界,其愤激不平的情感又借诗性的语言得以呈示。
二、“忧时绠短肱空折”:沉郁悲楚的现实喟叹
如上所述,不平之鸣是姚莹入藏诗的重要题旨。不过,作为嘉道经世士人代表的姚莹不可能为自己的遭遇所折服而沉浸于凄苦世路的惋叹;相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亦是其入藏书写的内容。
姚莹敦崇实学,他强调士人应有胸怀天下、匡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复李按察书》)①[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9页。。这一理念也深入贯彻到他的政事治理中,故为官一方,总能悉心世务而不乏政声。即使在人生最困厄的入藏时,姚莹亦未曾凄迷沉沦,依然强调“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②[清]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3页。,不忘关切风物民情、国家兴衰、外夷形势,这在《康輶纪行》中不无体现,若《西域闻见录》《西藏疆理二条》《外夷形势当考地图》,触及藏地风土、边疆事务、中外形势等,都是这样的作品。正因此,林则徐对其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③按:姚莹《十幸斋记》引林则徐语,参见《姚莹集》,第303页。。其实,作为一个恪守经世理念的诗人,姚莹论诗求道与艺合,以教化功用为追求。《谣变并序》称少即喜言“兴观群怨”④[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10页。大意,《孔蘅浦诗序》强调“古诗所以可贵”正在于呼应了“兴观群怨”⑤[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页。的旨趣,《黄香石诗序》更是发出诗当“发明道义,陈列事情”“讲求世务,隐然有人心世教之忧”⑥[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2-123页。的呼吁。入藏后他又重申这一观念,如《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一文,在推扬考察异域风土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提出“文人词客”亦当“留心世务”的要求⑦[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7-178页。,以如此意识行为咏叹,读姚莹的入藏诗,自能见其于社会现实的关注。
其一是对边地民众苦寒生活的注目。作为边地的康藏,不惟习俗风景迥异于内地,其苦寒的程度亦远甚于内地,对此境况,胸怀天下的姚莹自不会熟视无睹。如进入大相岭,姚莹有《小关山》一首:
严霜草冻石棱顽,峻岭云横雪树斑。板屋数家鸡唱晓,岁寒人渡小关山。
乃以“时已冬令,冰雪交凝,山石荦确,偪仄险滑异常,偶见民居村店,屋皆覆板,无复以瓦,可知其艰矣”⑧[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页。为背景,描写藏地百姓生活环境,曲写他们的“休戚痛痒”,怜恤之情隐然可见。
又《高日寺》一首:
山中夜添雪数尺,天上寒云带愁积。肩舆破晓惊山灵,万柏千杉森玉立。西来冈岭多不毛,惟闻石礀水怒号。到此始觉林泉胜,何来怪鸟鸣鸱鸮。山高径仄苦难上,蕃儿曳舆不可仰。更驾双牛汗喘登,人牛喧杂行踉跄。去年经过前山沟,牦牛跌死猿猱愁。蕃儿言之泪交流,问我于役何时休。往来时序殊春秋,相对忽忘人白头。
高日寺为山名,“在东俄落西十数里”,入乍雅必经之所。内中固有“林泉胜”的兴致,但可肯定的是,描写“山径峻陡峭曲,肩舆皆蕃人牵曳而上,复驾二牛助之,上下者再人牛数易,雪光晃耀,深涧俯临,不能无恐”①[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4页。的艰危情景,叙述蕃儿为生存年复一年从事危及生命的“曳舆”业才是诗人的意图所在,虽纯用白描,却将蕃儿的满腹辛酸融含其中,既反映藏地黎庶的苦难,又展露诗人“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的怀抱。
其二是对清廷官吏的荼毒生灵及不作为的批判。于此,《乌拉行》具有代表性。诗因“目睹夫马长征之困,慨然有感作”②[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页。,既描述了藏地百姓生活的艰辛,又对地方官吏、朝廷使者的巧取豪夺进行无情的披露:
蕃儿蛮户畜牛马,刍豆无须惟放野。冬十一月草根枯,牛瘦马羸脊如瓦。土官连日下令符,十头百头供使者。使者行程逾数千,揝粑难厌盘蔬寡。备载糇粮赢半岁,槁装毡裹谁能舍。天寒山高冰雪坚,百步十蹶蹄踠扯。鞭棰横乱噤无声,谁怜倒毙阴崖下。我谓蕃儿行且休,停车三日吾宽假。艰难聊作乌拉行,牛乎马乎泪盈把。
诗紧扣“艰难”二字生发感慨,同样关乎嘉道时藏地的民生利弊,但诗人想要表现的又不止于此。孟森指出,以“十全武功”标榜的乾隆朝,虽国威远震,但“视边裔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③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0年,第270页。,情况至嘉道更显深重,此间边疆战事频起与此即不无干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诗反映的正是当时边地百姓深罹官府鱼肉的佐证,诗人的警策意图由此亦可窥一斑。
至于《西行所见剌麻寺多矣,僧既秽浊,其诵经皆在喉间,初无音节,钲鼓喧振,杂以铙铃,使人厌听》一首,虽涉“蕃人礼佛”④[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有讽刺僧之秽浊意。不过,从结尾“经过三百八十寺,何处一闻清磬声”的咏叹来看,其关涉范围又不是“僧”这一概念所能涵括,这倒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当时那些尸位素餐的清廷官吏。推想若成立,诗具有的现实意义就更显深刻了。
其三是对中外形势的密切关注。由前文可知,入藏后姚莹对现实的关注并未局限于康藏的民生利弊,其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⑤[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的古训亦三致意。因此,于中外形势的体察也是其入藏书写的面向,如《再叠前韵》《阿娘坝晓发》《四月十四日读卫藏图识》等都包含着相关的内容。大致而言,《再叠前韵》以“西夷米利坚国遣使顾盛有所要求,欲朝京师,粤帅却之而许其求”⑥[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页。为背景,《阿娘坝晓发》以“西方金天气肃杀,淫凶残狠人偏诐”为情感生发点,《读卫藏图识》则是“外夷形势当考地图”①[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67页。意识支配下的反映,从不同侧面显现作者于中外形势的用心。
在关注中外形势的同时,姚莹对造成国家忧患的原委亦有思考。而要求统治者密切关注外夷形势恰是“鸦片战争”后他为深受外夷欺凌的清王朝所开出的一剂方药,这在《康輶纪行》中多有体现,对“外蕃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儌外事”②[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的现实“深以为恨”(《自叙》)③[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便是明证。至于因“自感失职无权,坐视两呼图克图桀骜,莫能禁服也”④[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4页。而愤然书写的《自题康輶纪行卷后》,则是这一理念作用下的产物。此诗不仅描述了清王朝忧患重重的景象,且以激愤的态度告诫统治者要警钟长鸣,当时刻关注中外形势,否则便有被天下承平假象所迷误的危险:
万方櫜甲庆承平,小吏严符敢惮行。冰雪未消千里冻,触蛮难罢十年争。忧时绠短肱空折,怀古心长泪欲倾。佛火一龛忘异域,宵来犹待晓钟鸣。
总而言之,或注目于边地民生,或关注官吏腐朽,或用心中外形势,现实之书写确又是姚莹入藏诗中的重要内容。借此,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之学”⑤[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21页。毕现,“身历困穷险阻之境”,其于家国的苦心孤诣每见于沉郁顿挫的文字中,读来难免有柔肠百结的负重感。
三、“有为天下”:慷慨昂扬的志士胸怀
不可否认,不平之鸣与现实感喟都是姚莹入藏书写的应有之义。但要注意的是,姚莹的入藏诗,同样蕴涵着昂扬激越的志士胸怀。
姚莹成长于恪守程朱的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自小即受儒家道义精神的濡染,对于家国之义尤为看重,年未及弱冠便开始探究为人之道,经世之志已然萌发⑥施立业:《姚莹年谱》,黄山书社,2004年,第19-20页。。而有感嘉道以还清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在“道光己丑”《复管异之书》中,他区分“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并强调在“元气大亏,杂症并出”的“艰难天下”更应高扬胸怀天下的士人情怀,呼吁“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⑦[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展露为天下所用的雄心。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身历刑部狱后,如前所述,姚莹虽“不能恝然无恨”,但家国之念仍是其执守的重心所在。在《十幸宅记》中甚至还将这一经历及奉使康藏视为一生十大幸事之二,称“台湾之狱”“其幸六也”“一再出关,西至喀木”“其幸七也”⑧[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03页。。当然,这在他与上司友人的书信中亦有体现。如《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写于道光癸卯(1843年)受“贪杀冒功”诬陷而下刑部狱时。在文中,姚莹一方面向巡抚刘鸿皋陈述台湾事件的经过本原,另一方面则表达于“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台湾镇、道冒功,上干天听”的不满,同时借此表明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心系家国——“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的胸怀①[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前文所及《再与方植之书》亦作于此年,所谓“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同样是其用心家国旨趣的反映。尤为可贵的是,入藏后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姚莹为国效命的心志依然坚挺。如完成于此间的《进退存亡当不失其正》,强调士人在“国家多难”时不当“私计自全”“避位远害”②[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5页。,而应有“赴难蹈死,何计利害”的操守;而《一腔热血须真》一文,则再次展示其“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③[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3页的胸襟。一如《复管异之书》所谓“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惟孔孟之徒,道能一贯,其他盖不能同趋也”④[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姚莹都能坚守“有为天下”的信念。
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有了如此信念,姚莹论诗亦显现浓厚的人文关怀。他恪守儒家诗教,重视“道与艺合”,主张个人思想与创作的会通,讲求创作的道德价值,强调诗文当有经济天下的功用,“由‘道义’的宣扬深入到‘世务’的省察,将诗以载道的理念明确落实到经世致用的深度”⑤温世亮:《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意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其实,受“有为天下”“经济天下”理念的影响,姚莹入藏时虽已届耳顺之年,且正遭遇不公正的政治打压,但他能正视自己的不幸,每以世务为重,用坚韧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波折不平。第二次入藏回成都后,他曾作《还成都寓舍》一首,借以表明自己一直以“我似东坡在南海,朝云曾不厌清贫”⑥[清]姚莹:《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51页。的心态对待辛酸不测,故他的入藏诗,亦不缺少“有为天下”的情怀。如《渡平羌江至雅州晤余小坡太守》两绝句:
锦江西去接平羌,青海遥通古塞长。谁信白头犹奉使,笑他年少戍敦煌。
使君仗节古诸侯,骢马还临大渡头。政好不嫌边郡恶,黎风雅雨足吟讴。
诗写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入康藏至雅州府时,虽有酬酢之意,但若将前后两首当作一个整体并置于特定的背景下考察,则不难体悟其中之深衷。诗人以欲扬先抑之法生发情感,前者用隋朝名将史万岁戍因大将军尒朱谋反事受牵连而贬为敦煌郡戍卒之典,联系诗人因刑部狱而奉使康藏的经历,并不难于诗人勃发张扬的咏叹中体会那份淡淡的感伤。至于后者,则以东汉骢马使桓典触犯专权宦官,虽遭严厉的政治打压,但终以忠义感动献帝事,既委婉表达不畏强权、以正祛邪的心志,又借“黎风雅雨”⑦[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的民谚将自己虽身处边陲逆境,但终会有所作为的豁达之情体现出来。在此,感伤的情绪已被积极向上的气度所替代,这又是姚莹真正想要表现的。
又《题丞相岭庙壁》一首,为初入藏经大相岭时所作,丞相岭又称武侯岭,因“昔日武侯屯兵于此”得名,后又以“五代蜀王建时,南诏寇黎州,王宗播等败之于山口,破其武侯岭十三寨”①[清]姚莹、刘建丽:《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名史:
参差林涧挂冰条,岭日晴烘积雪消。千载英灵丞相节,一官落拓野田匏。重承明诏来荒服,敢惜微躯使不毛。天步艰难时事异,古来惟有中兴朝。
总的看来,诗宣示的情感颇为复杂。一方面,诸葛亮的忠义大节和王宗播败南诏之事,自是诗人礼赞的对象,故中有“千载英灵丞相节”“古来惟有中兴朝”的咏叹;另一方面,“一官落拓野田匏”之谓,则是以比兴法就自我偃蹇的境遇予以渲染。此外,诗人的旨意并不局限于咏史怀古,亦不在于感事伤怀,舍身为国的斗志的抒发方是其本根,其中“重承明诏来荒服,敢惜微躯使不毛”云云,恰又在一定程度上将那昂扬激越的情怀展露出来。
除上所举之外,《飞越岭示汛卒》“霁雪冻含云黯黯,阴崖愁见日闲闲。健儿莫叹书生老,一饮能朱镜里颜”、《出炉关答送行诸君》“重臣持节多边计,上相陈辞悦圣颜。奉使但期无辱命,白头敢望玷朝班”、《江卡道中》“万里关山度险巇,衰年未肯负须眉。平原浅草驰新马,一片愁心付健儿”、《察木多西北博窝野蕃多出良马》“书生万里走西陲,便欲穷寻阿母池。騕里不须怜一蹶,追风善堕是男儿”等,均作于入藏期间,又无不是诗人经历政治打压和康藏苦寒后的心理呈现。一言蔽之,这些作品恰从不同的侧面昭示诗人不屈于困厄人生而经世泽民的志向,有为天下则又成为它们共同的关键词。
四、余论:姚莹入藏书写之诗史意义
毋庸置疑,姚莹的入藏诗是清王朝趋于颓废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姚莹自身的仕宦沉浮有着内在关联。结合当时语境,我们并不难挖掘创作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如所周知,姚莹是以抗英志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以此形象载入清代史册的。在对英战斗中战功卓著的名臣却因“贪杀冒功”之罪而革职下狱,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台湾之狱”才使姚莹名声大噪,姚元之《送石甫弟南归兼柬正行刺史小眉通守献生水部律原方伯》“海上归来一个臣,男儿姓字觉重新(一时向余觅《后湘集》者甚多)。书生争读后湘集,异域都惊大将神”②[清]姚元之:《廌青集》卷二,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颇能反映这一实际。而如前文所论,入藏诗饱含姚莹经历“台湾之狱”后的人生况味,不平之鸣、现实喟叹与志士胸怀交会,愤激与慷慨并存,个人情趣与家国信念交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诗人经历仕宦浮沉后的复杂心态,这当然是它的价值所在,但又不限于此。
需要注意的是,姚莹毕竟是恪守“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的襟怀和心态来对待人生得失的,实际上,他亦从未因自身的遭遇而弱化对国家前途的关注,这样的襟怀同样在他的诗笔中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入藏诗中那些带有怨愤意味的宣泄,也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既合乎道德伦常,有其发抒的内在合理性,又是诗人处于人生最为困厄时对当下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所给予的一种带有批判性质的正义表达,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意味,与那些反映现实、表现家国的作品一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时代价值。由此看来,姚莹的入藏诗,实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有为天下”志士形象的塑造。
不惟如此,这样的形象塑造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诗坛同样有典型意义。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实际形成了主战和议和两个派系,又以后者占尽上风。此间因政绩卓著反遭贬黜的文士并不在少数,重者处死,轻则革职戍边,其著者如邓廷桢、林则徐、王鼎、龚自珍等,都有过因功见逐的经历,姚莹并非孤立的个案。这样一群文士,以经世为重,劳苦功高,本应受封进赏,却遭不公正的打压,对他们而言,心有戚戚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国家趋于败亡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生错迕对他们来讲又算不了什么,救亡图存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仕宦的不平不但未使他们消沉,反而历练、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强化了他们于国家前途的关注,这表现在诗歌领域,那便是严迪昌所说“鸦片战争起始的一系列外侮的刺激,诗的生命力也随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潮得到一次新的张扬”①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85页。。具体而言,借志士形象塑造以激发、推扬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确又是此间经世文士诗歌创作的重要面向。以林则徐为例,其禁烟本以保家卫国为目的,但终因触犯英夷、议和派而以贪功启衅、废弛营务、误国祸民等罪名流放伊犁②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1年,第335页。。因流放而致的愤懑、失落和苦闷,在他的伊犁诗创作中固然存在,若《次韵答陈子茂德培》“忆昔逢君怜宦薄,而今依旧患才多”“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沈吟拟北征”③[清]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7,清光绪十二年刻本。便是此类情感的映照。但总的看来,像《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④[清]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7,清光绪十二年刻本。这样的志意,才是诗人真正要表现的。至于与林则徐同时谪戍伊犁的经世名士邓廷桢,其流寓伊犁的诗歌创作表现,正所谓“(林则徐)谪戍后诸作,尤悱恻深厚,有忧国之心而无怨诽之迹。当时好事者,合公与邓嶰筠制军之诗,辑为《林邓唱和集》,工力相敌,并称传作”⑤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第5341页。,与林诗又如出一辙。再如光绪年间,因得罪两广总督岑春煊而以贪腐之名谪戍新疆的经世士人裴景福,并未因命运的折磨而沉沦于怨恨苦痛,“夷险一致,行更寒暑,虽极人世难堪之境,而处之泰然”(金宝权《河海昆仑录重印序》),他表现出倏然物外的自若,以至流放“途中山川道路风俗政教,凡所见闻,辄上下其议论,间或发为咏歌,声满天地,匪惟绝无怨尤,且能于患难流离之际,不乏省察克治之功”⑥[清]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1页。。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亦能感触那份宠辱不惊、昂扬向上的精神斗志和以家国为重的时代气息,可以说,他们与姚莹一道为当时乃至后世塑造志士形象提供了范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回溯中国文化发展史,“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以天下为己任乃中国古代士人所恪守的文化信念。因受这一思想的浸染,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艰难时,文士们所显示出的民族气魄从未消歇,反而每见激越,愈显坚韧。而无论《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还是孟棨《本事诗》所透露的诗史观,范仲淹所推阐的忧乐心,抑或后来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①[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0页。,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史亡而后诗作”②[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页。,前后递嬗中明显带有某种精神志意的赓续。概而言之,这就是一种深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昭示,一种强大的文化精神之生命力的彰显。顺着这一思想进路,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出,借文学以塑志士之形以表现家国情怀,实在是中国古代文士最为惯常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梳理这一进路,我们同样不难发现,自《诗经》所显示的忧患意识到杜甫创作的“诗史”价值,再至宋遗民、明遗民乃至晚清经世士人创作所流露的家国情怀和抗争精神,其实均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以天下为己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印痕,历久弥新。当然,姚莹入藏诗所塑造的志士形象,内中固然少不了因现实不公而形成的不平,不无私人化的表征,但交织其中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又最为浓烈,无疑是它的精神本根所在,若追究它的文化根脉,我们是无法绕开中华文化精神而作片面论。换言之,姚莹诗塑造的“有为天下”的志士形象,实亦“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文化精脉作用下的产物,它的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均见突出。
要之,以鸦片战争前后动荡不安的时代为背景,结合姚莹仕宦经历探视其入藏诗,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姚莹当时复杂的个体情怀,而且有助于我们体会其所塑造的志士形象所包孕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于此间不计个人荣辱而以家国利益为重的经世士人诗歌研究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