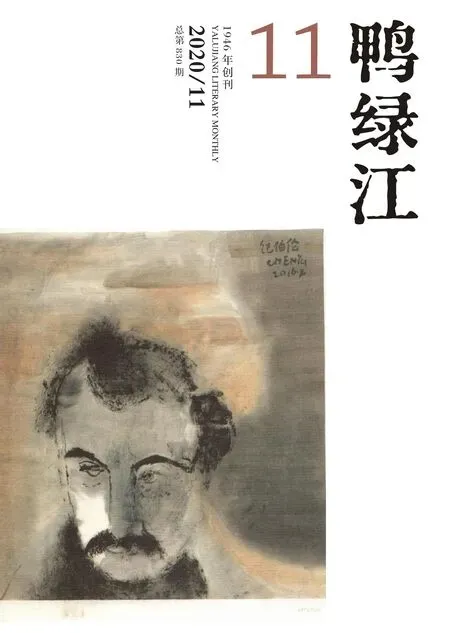篱笆
赵冬妮
1
塔柏单独看,会有一种落落寡合的气质,哪怕三五成群,立在一片开阔地,也没法改变我的这一印象。是针叶树种都这样吗,还是树本身尖塔的形状容易让我想入非非?高耸着向上伸展,似乎在向天空传递着什么。传递什么呢?在想也想不明白的时候,人早就走神了。偏偏D要把它们聚集在一起,他在美国时常见有邻居以柏作庭院篱笆,就喜欢上了。好家伙,绿篱笆密实厚重,人在外头走,别想看见里边;而里边的人,哪怕冬季,也被绿深深包围,既然一定要有篱笆的话,那就要这种篱笆。D从不忽视自己的决心,当我们的房前有了个小园后,他明确地说,种绿篱。于是从山上拉来了满车塔柏,回来跟工人一口气栽种上,转眼间我家就有了一道绿篱笆。
沿着低矮园墙排列,三十几株塔柏密集簇拥挤作一列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塔肯定是不见了,上尖下阔的树形很快就被修正,从圆锥体变成了直筒筒的圆柱体,结构服从于人的意愿,新的使命要求它们要联合起来,要成为一体,彼此难解难分。要成为篱笆墙,谁也不能孤傲,不能拔尖,不能不保持队形。给水充足的话,不过半年光景,一道塔柏已横平竖直,绿茸茸地成为篱笆墙了。塔柏生长缓慢,也并没长很高,但已看不出谁是谁了,它们也要削足适履,或许比人还不容易。篱笆外边是铁栅,铁栅外边是街巷,之前责权利约定好的,房地产商将铁栅立起来,街道铺平坦,现在全被挡在篱笆后边,都虚化了一样,确实存在,又不那么真切。街巷对面的房子只露出上半截,红墙壁灰屋瓦;日间汽车从街道无声滑过,很清楚那是汽车,甚至辨得出它是白色的,或是黑色,那是塔柏与塔柏间的缝隙透露出来的;人影绰约而过,我坐在书房,隔过窗玻璃也能看得清楚,行人,红色衣裳。生长需要时间,人脑海里给塔柏绘了个长方形框子,但塔柏并不是小孩子手中的蜡笔,不是汪洋大海,说涂立刻就能把那框里边的空白涂满的。一棵塔柏就像被装进了一个长方形大纸盒里,它要用枝条和针叶去填满盒子。它天生枝条疏松,小枝生满鳞片似的细叶,细叶针尖大小,它得怎样去填满你的那个大纸盒子呢?它还需要日照,需要水,害怕病虫害,塔柏也不是它自己。
2
塔柏移栽刚过两天,邻居电话打了过来。号码陌生,我不接,不接就一直打,直到我接了她赶紧说,别放电话,我是你家邻居。
我们这趟房有九户,小区一共多少趟房我不清楚,每家西山墙上钉着的房牌号都很大,但我想这不应是实数。我家把西头,靠大道边,东侧隔壁房子距离我家最近,自然是邻居了。我们还谈不上熟悉,可也不是路人,她到过我家两次,那时房子刚装修完,两家都还没正式入住。第一次她忘了带钥匙,她站在自家院门口,等着人来送钥匙,正当晌午,她手遮额上,太阳光直射下来,一小团黑影堆在她脚下。
没有阴凉地。当初家家门口有树,山钉子树或槐树,树种不起眼也不名贵,深秋时有几天它们会异常美丽,山钉子绿叶丛中挂满小红果子,熟透时鸟就来啄食;而槐树似乎一夜之间,叶子就全部黄艳艳的,比金色浅,比金色明亮,其间没一丝杂色,不禁让人想象树内在又隐秘的话语,是否有着一个约定,大家说黄就黄,而且黄得那么一致、彻底。这树她家装修过程中给起走了,她站在太阳地里,正赶上我出来进去里外忙活,我叫她进屋来坐。还没有家具,空荡荡的客厅显得很大,说话都带回声,像在山谷里,两壁书柜同样空着,没可看之处。地板刚擦出来不久,泛出木本身柔和的光泽。她对我地面不铺大理石感到不解,我说我们喜欢地板,我喜欢木头的。木头的?那厨房、卫生间呢?就用地砖,我说,至少不那么亮。房子装修大半年,除了偶尔照面道声“嗨”,我们第一次这样近距离接触,我知道她是坐办公室的,也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机关事业单位里有这样一些“坐办公室的”,在这样人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职业特征,什么文员财会接待,好像一样都挨不上,好像她们都是风,没法细究她们碰触过什么,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供你辨认。她的脸有点木木的,我猜这是连她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她想去看看那些不亮的地砖,她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很难看出她目光里有什么。这一点也不意外,我熟悉这种目光,没有色彩,也没有细小之物。转了一圈,地砖显然让她觉得档次不够,她说,她这里,这里,全铺大理石。同样她说什么时也并不看着我,我知道她的心在忙着做各种比较,就好像在两个房之间来来回回地跑,根本顾不上我。我说大理石也好,可她把视线转到浴缸上去了,她说这次她没安浴缸,我问为什么不装?以前装了浴缸都不用,只用淋浴。嗯,我说我每天都要用浴缸。每天吗?每天。她心里的比较停住了脚步,不再奔跑了。
过几天她又来我家,那次我没在,只装修监管小鱼一个人在,他里里外外领她又转过一遍。几天后小鱼告诉我,邻居家把浴室全刨了,她要装浴缸,墙面地面,连同玄关,所有大理石也都刨掉了,另换一种花色金贵的,重新贴,重新铺。我吓了一跳,我说前些日子她家窗户不是拆了新换,过后嫌颜色不好,刚刚又拆了又换吗?之前小鱼告诉我时,曾把他心疼得不行,这次我好像后返劲儿,也跟着心疼起来,这砸进去多少钱才算完啊,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吗?
没想到邻居开始跟我通电话了。也没有想到是冲着塔柏来的。她在电话里说:“昨天我去了新房,看你家院里栽了树。我就觉得要跟你说一下,这在我们农村,额,你们是在城里长大的吧,我对象就说,你们不懂,这在我们那里,栽这种树不好。有什么不好?你看这不清明刚过吗,前两天我们还回乡下去了,我和我对象刚回来,给他家扫墓,我就想告诉你一下,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说,但我还是想说,也不知我说明白没有。”“说明白了。”我答道,把她从艰难的吞吞吐吐中解放了出来。那一大堆话里,不需要什么逻辑链接,只抓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她不是交谈。她不知道我天生的敏感永远是一触即发,哪怕隔着距离,见不着面,哪怕只是呼吸,我也一下能嗅出味道来,我说谢谢你,我知道了。我在那儿买房子住,我本来是想做个乡下人的,现在看,好像哪里出了点毛病。
3
轶林站在园子里,脸仰向天空,一只手紧扣着太阳穴,努力在记忆里追索着什么。他叫着妻子的名字,好像这时候特别需要她,需要她来帮他,与他一起共同打捞一个深不见底的东西。还没等她明白过来,他终于想了起来,想起了老韩家,和老韩家的一口井,对呀,这地儿是老韩家的,他家就在这儿,在这儿,是他家的井。他用脚尖来回踩踏着,要找回一个更准确的位置。我们在说井。我一直想打一口井,又担心地下不是水脉,花冤枉钱又白辛苦一场。轶林在山上有自己的苗圃,我家大部分树是从他那里买来的,后来常来常往,大家就成了朋友,园子里的活儿,不懂就电话请教他,做不动的他就和妻子过来帮忙,之后我们支付工钱。时间久了,他知道我最大的弱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抹不开脸儿——他常用这话来笑话我,同时也很会利用我的这一弱点谋点小利。D和我心知肚明,我们相视一笑,之后各干各的。
老韩家的旧宅地和井。这不啻于深夜里的一声叫喊,我醒过来睁大双眼,久久停留在震惊当中。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家园子这儿,曾经是老韩家的。轶林穿着走样了的黄胶鞋就好像一直在动一直在说,在这儿,在这儿!整日山上山下跑,黄胶鞋从来都肥得像两只灰青蛙,脚心窝的地方凸鼓出来。轶林是当地人,他向着天空追索着老韩家和一口井的样子打动了我,我觉得他那时是在追索一个村庄。我一直以为这里原本只是个溪谷,我看到过溪水怎样从山岩石缝里涌出来,最终流入一小片水库里,小区开盘那天,水库闸门打开了,水流顺着垒石河道淙淙而过。河道再没放过水之后,巨大的茅草开始一簇簇生长,秋天时随风摇曳充满着乡野气息,我从没想到过,这里曾有过人家。我看到的也是山脉间的一窝凹地,后来我常在那里走路,我和D沿着山路往山上走,大雪天我们走到山谷最深处,蹚着新雪听积年的腐叶在雪下沙沙作响,再原路折返。我来了。如果说进入,我是从开发商起的名字起步的,纳帕溪谷。有一阶段我们的楼盘几乎都是洋名,纳帕溪谷这个名字我能接受,弗罗斯特的童年就是在旧金山Napa Valley度过的,看房子时我就在想诗人弗罗斯特,甚至想这种巧合不期而遇。当然弗罗斯特的纳帕溪谷是在大都市,空气中散发着鲁莽和愚蠢——他曾这样说过,可是由此,他才可能让生命和诗深入进田园,才悲悯一簇花一棵树。
Valley,英文里是这样解释的:a long depression in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that usually contains a river。溪谷,中文里更趋向于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谷,单独又指两山之间的空地。中文里另有一层意思却完全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溪谷与人的肉体有关,它藏在人身体里,是肢体肌肉之间相互接触的缝隙或凹陷部位,大的缝处称谷或大谷,小的凹陷处称溪或小溪,“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古人就这样命名溪谷,解释肉身。从小我就熟悉合谷,展平手掌,在手背拇指与食指的掌骨之间,你看不到它的深,父亲告诉我,但它是深的,是手指可以按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合谷。每次晕车,我就按父亲告诉我的,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紧紧掐住合谷,用两指掐住,它非常薄,可以从里外两方面进入,酸痛和鼓胀就会在那升起,并渐渐涌入痛苦的身体,直至侵入太阳穴,于是,似乎那里有两面鼓开始砰砰作响,血液下沉,慢慢止住胃里边翻腾不止的呕吐,痛苦缓解了,余下的血肉间的疼痛变得容易忍受。合谷夹在两根细瘦的掌骨之间,它空旷、平坦,因此可说是裸露的,易于接近,它是我接触最多的身体穴位。
在园子里干活儿,我常忘记戴上手套,等我想起时,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我还没养成戴手套的习惯。有时我举起手,放在眼前,想到轶林和老韩家,和那口消失的井,和他家邻居那些消失的井,我举着两手,上面不仅满是泥土,而且被晒成深棕色,早已不再白皙,但在我这里,也已变得容易忍受。
我是心甘情愿的,栖息于山林之下。从没有人懂得,或许就连我自己也没法说清,我为什么喜欢过田园生活,而且完全是种男人式的喜欢。似乎有个隐秘的根源藏匿在某处,无从回溯,却始终就在那里。我喜欢土地,喜欢无尽的乡野和缓慢的时光,我擅长走路。这不是一种浪漫,也不是乌托邦,其间蕴含着劳作,不乏身体上的辛劳付出。山脚下。我时常会用这个词替代溪谷。我住在山脚下。这样的话是可以口头表达的。这转换过程是一种下沉,甚至是从诗歌沉入泥土,就像弗罗斯特从旧金山纳帕溪谷转身让身体沉入新英格兰乡间,这远不仅是命运,更是种必然。来过的朋友都说好,园子有山林之风,就是都嫌远,觉得这里不城不乡。我太不在乎城还是乡这些概念了,而且远,“什么样的近可以抵达?”这是谁的诗句?我忘记了。房子还在装修期间,每次开车驶出闹市区,就觉得耳边被清水洗过了一般,世间完全寂静下来,我们开车向前跑,直至群山出现在视线里,每当看到不远处群山连绵不绝,而我正在向它接近,一直向它接近,渐渐进入群山之中,我内心就充满了感动,山峦低矮起伏,山际线舒缓绵长,山气青缥虚静,我在时间中逆行,重返或者获得我从不曾有过的——如诗人吕德安所说——某种创世般的寂静。
最初一段时间内,D和我常要返回到市区去,去取快递,去理发店和洗浴中心,还去看电影,到超市购物。开车驶出小区门楼时,就像越过一道闪亮的关卡,照见我自己已被放野了,我就会说,进城了。似乎城是一次收敛,它能从头到脚修理你,一直修理到指甲缝,保证那里不藏泥土。整个小区被大篱笆墙圈在里边,大篱笆里有小篱笆,小篱笆才界定或者说表达了背后的那个个人。我家篱笆墙内有我干不完的杂活儿,有各种劳作,脚上是43码的男人的大雨靴,一趟趟来来回回走过,树要照顾,草要照顾,菜地要照顾,我进城了,确实在承认自己是乡野之人。我在乡野。不过很快,没用上一年,也就没什么远不远的了,顺丰车开始出现在小区里,不费劲儿我一眼就会认出,黑色车身,永远像异域黑鹰,上面白色logo,白色英文字头SF里有一颗凝重的红点。取件箱也立在了物业门口,同样是黄色的,凡·高向日葵那种明黄,老远就看得到,不过不是“丰巢”,也不是“日日新”,而是家更新的:“速易递”。许是太快了,取件窗页面有两个一直在反复地换,黄页面熟悉了,不久换成了红的,等我准备好对付红的了,黄页面的笑脸又跳出来,像个女人在选衣服,试了这件试那件,在身上两件来回穿,拿不准主意要哪件。亚马逊取消了售书业务,购书也不得不转移阵地,我重返当当网,继而新认识了“品俊快递”和劲头正足停不住脚的快递员,他从不进院子,只隔着矮栅门与我完成书的递交仪式,我们默契地相互关照,我多跑几步出门,省他下车,我光着脚跑出去,他也不会笑,碰上我不在家,他就把书投取件箱里,再电话告诉我别忘了取。不出多久,彼此像是成了朋友,每次我谢谢他时,他就说我谢谢你。
我几乎忘记了邻居的那通电话,最开始,塔柏令我烦恼多日,总是陷在说不出话来的虚空中。她在我头脑里挖出了个大坑,它空旷不见边际,无数碎片在其中飘浮,有些是词语,有些不是,我看不清那都是些什么,也根本捕捉不到,更别想把它们连缀成片。最主要的,我没有了确切的方向来说服自己,要这样,或者要那样。根本没法谈论。她半吞半吐的话语并没有很快消失,在一段时间内它们窸窸窣窣,四下里爬动,要么就非常黏稠,不知从哪里流淌下来,然后停在眼前再不动弹。好在我有收拾起自己的力气,所谓乡野生活也调服着我的内心,内心里一向所具有的坚定又重新回复,重新往胸腔左部那个怦怦跳动之处慢慢聚拢,篱笆墙内生活的单纯呈现出事物原本的质地和方向,塔柏长列一排,尽管生长缓慢,却从未停止生长,进入冬季后仍旧绿油油的,岁寒,一切草木凋零,只有它们饱含深沉的香气,隐秘地、幽幽地向外释放,以至于使我爱上了冬天。没有冬天,没有冬天的静谧和寒冽,还有,没有这园子,我不会真正地认识到塔柏的高贵。有时候我并不干什么,只是坐在书房里,长时间地看着窗外那排安静的生物,园子里树木花叶尽落,露出光秃秃的枝干,唯塔柏显露出来,几乎不见树干,从上到下披满幽绿色针叶,难以历数的鳞片针叶,在寒冷中锁住了水和养分,锁住生命之本。我见证过它们四季生长的过程,知道它们所需求的极其简单,只要浇水,初春和初秋各打一次药,它们就连病虫害也不生,它们只要求我们真诚。我有时间了,有时间用我的脚去踩泥土,用手去触摸它们密集的鳞叶,体会它们带给肉体的针尖一样细小而尖锐的刺痛感,我想到麻木不异于一种死亡,为什么要那种腐朽的呼吸来包围我的生命呢?我没有跟D探讨过电话事件,在他的决心里面,耸立的唯有事物本身。我不能跟他谈意象。而且,邻居跟我电话里谈的,也绝非意象。我要是把这些跟D说了,他就会说,哪有工夫管它呢。就算我给他背诵“青青陵上柏”,他也准会朗声大笑,准会取下句“磊磊涧中石”,他这个人就是涧中石,不絜尘羁,再如果参透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就自己都会羞于启齿了,是的,我俩都爱树,只单纯地爱树,不用去管篱笆墙的影子咋就那么长。
4
小区里从未停止过大兴土木。要是在闹市区里买房子,涉及到的装修只在自家房门以内;要是在城郊,要是房子周围还附带有一小片地,那片地也能在产权内允许使用,成为自家的园子,装修就会四处蔓延,不仅是向周围蔓延,还会上下蔓延。蔓延改变了房子原有的样貌,甚至改变了小区的风格。尤其有了土地这一点点余裕,房子就更嫌小了,房子是不大,面积大都160平方米,开发商出售的就是这个价,160平方米加个小园,都是奔着这个价来的,这价跟田园梦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小区自然就翻江倒海,不得消停了。房子扩建楔进了土地,园中土被扒开了,挖掘机把园子挖出了个天大的坑,从房子一直挖到院墙根,房子底部的回填土也被掏空,地基裸露出来,房子凌空而立,我第一次看到一座大房子是被几根细瘦的水泥柱支撑着的。也许就在那一刻,我迷信起泥土,迷信泥土深厚的力量,我觉得那几根支撑好脆弱啊,心里真怕房子瞬间倒塌。但是没有,大坑里到处浇筑了水泥,竖起钢筋,其后还是水泥,很快,地下室就冒出来了。院墙也没有因大坑的出现而倒掉,下半部分反而额外多出了几扇半截窗,阳光斜照进去,不那么明亮,地下室似乎也正常,也不需要有多么亮。窗框材质全是铝合金的,别扭地浮在欧式建筑的背景前,像容易让观众出戏的蹩脚演员。三年时间里,每条街巷都诞生出了这样的演员,它们卧在街巷一侧,只把玻璃眼露出来,冲着街道,其余全部身体包括头部都趴进泥土里,有两次我从它们面前经过,它们半睁半闭的眼睛看着我,看我的脚和小腿,不明物体似的慌张走过,它们头顶上的院墙,竟让我想起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鬓边青草,颌下绿莎,要么就是头上有草,脸上有泥,总之我就再也没深入街巷里走过。院墙、篱笆墙、木篱、绿篱、竹篱,所指都是一回事,是对家的保护,无论怎样扩建,怎样让地下室棚顶冒出来,替代了园子里泥土,用石砖等各种硬覆盖铺地,院墙们或篱笆们都保留了下来,哪怕改头换面,哪怕面目皆非,它们存在着,把房子像心脏一样围在中央。
篱笆,名词;站立,动词。如果有很多名词都指向同一件事物的话,我就得关心动词。事物本身就在那里,是动词回过头来,对它发生了改变,是的,是对它发生了改变,然后才是使它发生了改变。动词有冲击性,也有抚慰,最终形成状态。不是像撇奶皮,动词没有撇去意义,事物仍立于事物本身,面容却更加清晰,更加单纯、透明。动词才是对事物的最终说明。这样想的话,关于塔柏或者篱笆的事,会不会就变得简单,而不那么复杂了呢?我不愿意走那么远,我在城市里长大,我父母也在只有十几岁时就离开乡村,他们早早进入城市,求学工作,直至把我放在一个光秃秃的大院里独自长大。院子处在几幢三层红砖楼之间,红砖楼就是围墙,特别高的围墙,无数人躲在其中的围墙,楼与楼之间是仓房,仓房里面是煤碎木材酸菜缸咸菜缸工具和各种破烂无用的东西。两排仓房之间是个垃圾堆,夏天苍蝇们打着转在它上面缭绕,发出嗡嗡嗡的轰鸣。在没有仓房的一块空地,有三棵大杨树,那是几个楼的大院里唯有的树。夏日午后,我们女孩子抢着躲在树荫下,跳绳,把皮筋系在两棵树上,或坐在石头上,摘豆角削土豆皮。树有阴凉。我们并不懂树,甚至不是喜欢那树,我们是喜欢那庇护。树就是庇护。我们要绕很大一圈,才会去爱上事物本身,爱上它原本的状态,在我经历过无数崎岖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样是不是太晚了?所以即便动词,我要那些平坦的动词,优雅的动词,它们可以很旧,很老,可以发生在古代,就是不要有伤害,有恐惧。
但动词一旦发生巨变,我对动词的信任就站不住脚了,就不能不随即坍塌。比如说,篱笆,名词;倒,动词。名词仍然在那里,但事物不再是站立的样子了,意义变了,事物同样清晰单纯,只是换作了另外一样,它有了一个你不能接受的状态,你还能继续信任动词吗?这已不是词语问题,你躲不进去,这时,你就要从词语当中走出来,切实面对那倒掉了的篱笆。
是的,篱笆倒了。我这样对D说。我们在外地的时候,挨她家围墙的几棵塔柏被邻居挖掉了。先是扒掉我们两家共用的围墙,然后是塔柏。还是要扩建地下室,殃及池鱼,电缆挖断了,一根电缆上的几家都跟着停电。物业瞒了又瞒,终于想到我家冰箱,冰箱里的冷冻冷藏,不得不电话通报我了。我问物业,可是她家不早就建地下室了吗?想再建大一点。我问:要多大呢?物业一阵不语,然后说,好像在院子里再扩扩吧,院子里都做地下室。我问物业:那么为什么要扒院墙,然后再过来挖树?她建地下室,和这院墙树都有关系吗?物业迟疑着回答:是不需要扒院墙,是想用院墙下的那块地基吧?我们也不清楚。我继续问:你们物业有规定,装修要有左邻右舍邻居签字同意,事先你们问过我们吗?经过了我们签字同意吗?物业说,是没有,她来这里签字时说你们同意了呀。这是扯谎!她们家从来没问过我,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们从不知道有这回事,而且你物业也不来问问我们吗?你们拿到我们的签字了吗?你们凭什么?到了现在,断电了你们觉得不能不告诉我了,才打来电话,如果电不断的话,你们就会一直瞒下去,直到她做完了神不知鬼不觉,让我不知道墙曾经被扒掉树是怎么死的,是吗?是这样吗?你不觉得这已过界了吗?这太过分了吗……
我被自己的愤怒气哭了,却努力忍住哭腔,想起了秋天时朋友曾来电话,跟我说邻居家想要朋友帮忙,把我园里的银杏树起走,他来征求我意见,需要不需要他把树起走?银杏树,离她家远着呢,我问朋友为啥要起走?朋友也一时回答不出,于是我明白了,她只是恨树。可她为什么要恨树?她把院子弄得光秃秃的,地上全铺上灰色石砖,一棵树也没有。只是在门口,在起走山钉子和槐树那小块地方,后来种上两棵枣树,以我的理解,她只是想要枣子而已。要是能越过树,直接够到枣子,她定不会要树,她和枣树之间只是三角关系,甚至没有关系,但肯定不是直线关系。不在肌肤之间,更不在溪谷。她不喜欢泥土,买园子干吗?她不爱树,回去住高楼大厦好了。可是翻腾出这些,都无聊啊,还是我率先偃旗息鼓,我只对物业说:哪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只要马上要连上临时用电,树怎么挖的怎么种回去,要保证树不能死,否则我就起诉她……我放下电话后,一阵惊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起诉,这两个字会在我口中说出,会在我与邻居的关系中产生。我从来不曾跟人红过脸,不曾发生过冲突,遇到问题就往后退,不去伤到别人,打掉牙就咽到肚子里,现在竟然脱口说出起诉,怎么会是这样?
除了新增几只玻璃眼外,她家地下室也拉长了,形状不再是原来的一窄条,而是扩展到大半个院子,泥土终于瘦成一窄条,身单力薄地躺在园东边。五棵塔柏被挖掉,被扔在院子里,树根裸露在外,暴晒三日,半年过去,连同跟它们相邻的三棵塔柏,全部死去。塔柏种回去了,一棵也没活。就在一年前刚刚从山上把它们拉回来栽下时,轶林要求我们天天浇水,他也跑来浇水,怕它们不活,大家总是去看它们,观察针叶是变黄还是绿着,每次浇水我脑海里就冒起我妈,我妈整天节约用水,我们看不下去了说她不用太过于节俭,她就说,水,人类资源越来越少了,你们不知道吗?我哪是差那一点钱。诸如此类的话,没挂在她嘴边上,被惹恼了她就会说出来,我拖着长水管,或看着D拖长水管,耳边响起她的声音,心里便觉得对不住她,直到后来我才想,在塔柏被连根挖起又重栽回之后,每次浇水时我才想,她才该起诉,起诉我,起诉D,起诉我们大家。可是我爱树,D也爱树,他给树浇水,见到树就停住脚步给它们拍照,我们会一同坐着观看树,就这样两头绞杀,往哪头走都不是,要么是忤逆我妈,要么就抛开自己。可是现在终于,塔柏还是死了,我再把手伸进那针尖密布的叶片丛中时,仍旧是细小的尖锐的疼痛刺着我,像没死一样。这些种回去的塔柏站在篱笆中,站立有五个月之久,其实在它们的内部,在根系,已经倒掉了。
不,肯定不是词语的问题,尽管词语会在你这里发生作用,会让你心烦意乱,会让你痛不欲生,尽管你也会用词语回击别人,尤其是发现自己掉入陈腐的烂臭的词语雷区,自己被炸得血肉横飞,头脑空荡暗黑如同无尽宇宙,除了词语,你还有什么依靠呢?还有什么护卫?你能够想到自己是一堆碎片么?你肯定不愿意。尽管……可肯定不是词语问题,其实你已走出词语,进入了现实。在现实中挣扎,跟完全不明来路的人为邻,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什么星球来的,却要从中扒开一条路来走,这才是困住我的真正篱笆。已经没有退路。你要进入一棵树,进入它单纯的生长与死亡,进入它带给你的疼痛感。即便住得再近,即便在篱笆间,你也没有邻居。
5
朋友没有起掉我园里的银杏树。他说其实她对象那人并不坏,他就是在官场混久了养成了那种……我笑笑,没有接过话。我想说所以他才那么跋扈,我想说他最该懂得什么叫公民,懂得公民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我觉得那些事一说出口,就会变成一地鸡毛。这是我回避麻烦的方法之一,我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保全自己。我在逃难。沉默就成了我的篱笆,它不仅使我觉着安全,还能保障我不轻易越到外边去,不随便与他人为伍,它给了我时间,让我去看,去观察,去蹚过那深不见底的心脏。心脏,我爱它们是肉做的,所以我温和。我不出手,不是我弱智,只是不善于也不屑于家长里短。轶林要我让她家赔偿,他会开出发票,要让她把交在物业的五千元押金一分也拿不回去。我拒绝了,在轶林那里重新买了塔柏,补上篱笆。
我要简单。只图简单。有一段时间,我越来越想住回到高楼大厦里去,钢筋水泥,天然壁垒,比篱笆墙牢固结实,不必担心它倒掉,不必担心它烟消云散。也不必管别人的爱憎。关起门来,什么都侵犯不到我,楼上要是不装修,永远都是安静的,不发出声音,也闻不到谁家厨房烧了什么菜,是不是酸甜苦辣。在一幢楼里住了十年,我没见过对门邻居,不知道他们是谁,做什么的,偶尔听到他们家开门声、关门声和狗因为我们出入的动静而发出的激动的吠叫,我才记起邻居的存在。那才是邻居的距离。这是一种省略,一种空白,我早就习惯了。不用像小时候那样去邻居家写作业,去串门;炒菜时发现酱油没了,跑到隔壁借一小碟端回,第二天再还回一小碟,附带捎上一碗饺子;不用大年初一挨家挨户拜年,不去的话父母嫌你不懂事,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早来过拜完年了。冬天晚饭后,我时常去邻居孙婶家,她家女孩比我大好几岁,男孩比我小,孩子们玩不到一块儿,也就不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往她家跑,孙婶很少说话,她丈夫坐在床上卷旱烟,同样不说话,我就坐在那儿看一个黑瘦中年男人卷烟卷,我不明白为什么就那么坐着,看他从一个小烟纸本上撕下一张,纸很薄,不发出声响,在灯光下泛出冷冷的荧光。他把烟丝放进纸芯,拇指手指对齐划过,烟丝立即直成一线,变得十分整齐,像猫毛在手指下滑过,瞬间从头到尾地平伏了。他再将它们卷起,手指间拈着滚过一圈,再放到唇边舔湿纸边封口,两头拧劲捏实,一支烟就成了。有时候他会一气卷出好多烟,一根根码进纸盒里;有时只卷一支,卷完后衔在唇间,他划着火柴,点着后开始吸烟,仍旧不说话。一间房子不大,静悄悄的,除了能听到隔壁家孩子在哭偶尔传过哭声来,轻烟在昏黄的灯光下晃动之后,慢慢向上爬,未到半空中就消散不见了。
格局是这样的:我家住在二楼。上完楼梯有三扇大门,正对着中间的就是我家大门,左手大门就是孙婶家,右臂同样有扇大门。我们叫它大门,因为每扇大门背后都住有两家,大门是区别于自己家的小门而言,站在大门里边看,确实又有两扇小门。晚上睡觉前我们都会站在大门口,高声问一下:都回来了吗?另一扇小门就会传出回答,都回来了,于是就插好大门,听到还有没回来的,就回一嘴:那就留门了。然后回屋睡觉。我们跟对门,叫对家。用的是家的概念。D他们那片区域叫“同居的”,正在进行时,用的是居的概念。大门里边最会吵架了,很多对家或同居的吵架,但我们和对家不吵,我妈严格控制我们与门外邻里间的关系,她总是严肃地训诫我们:不许跟人红脸。十一岁,在我十一岁那年夏日,我在家烧晚饭,黑铁锅里加水蒸萝卜块,是蘸酱吃的。铝盆当锅盖,大小合适,但没有把,我站在板凳上,想要确认萝卜块熟还是没熟,在捅开盆盖的同时热蒸汽猛烈冲出来,一口吞噬了我来不及抽回的左手。我放声大哭,孙婶吓疯了,拖鞋也没换拉着我就往医院跑。她是可怜我,我父母每天下班回家,晚饭只有半个小时,吃过晚饭扔下饭碗就匆匆返回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这些她都知道,可事后她还跟别的邻居们说我父母心可真狠。跟手背一样大的水疱盖住了手背,而且还在扩展。她个子高,我还很矮,她举着我的手往医院跑,我半个身体被提了起来,斜吊在空中,另半个身子趔趔趄趄,我只能用到一只脚脚尖着地。部队医院正准备下班,通常他们绝不给地方看病,但是那天——孙婶后来说是我命好,医生从一个塑料圆盒里挖出了一坨黄乎乎的油膏,敷满了整个大水疱。怕我手背上落疤,那可就破相了,孙婶说,每天她都检查,不出冬天,受伤的手竟好利索了,完好如初,她里外翻看了一遍,连手心都没放过。最后她说,小东西,真倔!我二十多岁以后就再没见过孙婶,没去给她拜年,没从她家厨房端回过一碟酱油再还回一碗饺子,我们搬家了,她早早死去了,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
这些早都省略了,我早已习惯了,这空白。这空荡荡。回不去了,不过就算如此,高楼大厦要回还是回得去的,这并不难。我独自踟蹰。我住得高,可以望到海湾,看到船从码头进进出出,无声地划破缎子般的海面。我就对D再三说,把这房子卖掉吧。带园子的房子,在篱笆的心脏,有一段时间我只围着一个心事打转,只想把它卖掉。现实问题是,我觉得我病了。就算朋友,他一边被人家请求帮助挖银杏树,一边被人家拒绝挖银杏树,我能看到他站在篱笆中间正一只手托两家,他更需要解救。我不敢伸出手去碰那份沉重,尽管我还确定不了那手是不是沉重,我希望它不是。所以当我们碰面,他想重提塔柏时,我只是轻轻一笑,并不把旧话提起。轻轻松松走到一起,不能彼此解救,至少谁也不要压着谁。在所有的篱笆当中,阻碍最不应该出现。如同篱笆原本就留有门一样。我在适当的时候,轻轻止步。
她家也看出了塔柏针叶不仅黄而且日渐枯萎了,最终认定它们死了,我们也曾一度以为它们还能活着,不会就那么死掉,可是不然。在我们意识的盲区中,它们死了。塔柏站立,且是并排死去的。物业打来了电话。夏季过去,马上就要到秋天了。物业在电话里说,邻居想问问你们,那些树,是作价赔偿呢,还是买些树给补种上?那时我正在园里走来走去,我看看那排塔柏,死去,就等于一切都没法挽回。而我还在这里走来走去。突然想起一个朋友发过的一张照片,一个男人独坐在野外长椅上看书,他正低着头,只见满头白发如雪,那成为黑白照上唯一的耀眼之处,朋友写道:白发丛生,顿觉天地悠悠。喉咙一下被哽住了,对电话里等待回答的物业,我说,不用了,什么都不用,到此为止。
“三个有雾的早晨加上一个雨天,就会烂掉/一个人建造得最好的桦木栅栏。”弗罗斯特。他写丧事,一个人濒临死亡,最亲近的朋友远道而来了,陪伴去死的人,但在人入土之前,他们的心思就变了,就想方设法要回去,回到生活和活人之间,做他们熟悉的事情。因为翻译,我无法体味弗罗斯特诗歌的音律之美,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孤独。在陪伴中的孤独。速朽,随时随地发生。这没有界限。缺少阻隔。
“有某种东西不喜欢墙。”我一直在想这诗句。来自弗罗斯特另一首诗《补墙》。“我”肯定不喜欢墙,但“我”也在应邻居之邀与其一同补墙,“在砌墙之处我们不需要墙/他全是松树,我是苹果园/我的苹果园绝不会越界,/吃他的松果,我告诉他/他只是说:好篱笆出好邻居。”“我”充满怀疑,为什么好篱笆出好邻居?“砌墙之前,我得弄明白/把什么围进来,把什么隔出去。/而我好像是冒犯了谁。/有某种东西不喜欢墙,/想要它垮掉。”我也摸索在黑暗里。死死思索着这想不明白的篱笆墙。这首简单的诗更像丛丛密林,我看到弗罗斯特在不断疑问不断拆解,不断在其中行走,不断弯腰搬起石头补墙。
6
重新买八棵塔柏补种上,又得开始重新养护。塔柏只挨院墙南边和东边各立一排,要是从空中看,就是个字母L。阳光洒落下来,照在每一棵塔柏身上。塔柏只遮挡铁栅那部分,其余砖垒院墙老样子留着。一个篱笆三个桩,塔柏是活的树木,一个桩也不用。但活的另一面就是死。任何事物都无法抵挡它的另外一面。我在园中干活儿或走动,尽量不出声,我知道篱笆的空隙,有多么地不牢靠。刚移栽塔柏那天,几个工人一边给立在土坑里的塔柏填土,用锹做出水坑,一边聊天。他们聊到一个有钱的熟人,他家里养了两个女人,老婆和后到的女人,她们住在同一幢别墅里,楼上楼下,不仅不吵架,还好成一团,常常设计联手对付男人。说得热火朝天,不知道我正好站在篱笆外,我被他们给引笑了,忍不住说还会有这样的事。听到我的声音在篱笆外响起,他们顿了一下,很快也笑着说有,这可不稀罕,于是,篱笆里和篱笆外就说起话来。补种塔柏的同时也新栽了草,是麦冬。不知道哪块心区在隐隐作痛,我不断地想,这又得浇多少水啊,就在那时我想起了我妈,想到该是她来起诉,起诉我和我们大家。可当天不到傍晚天突然间黑了,很快开始落雨,雨断断续续接连下了三天,塔柏和麦冬全活过来了。
园子西墙外边有片白桦林——特别年轻的白桦林,每当朋友来做客找不到房子时,我们电话里就告诉说,就找白桦林。小区里有几片白桦树,我们觉得白桦树最多处是在我家园外,D又叫它们为西林。三十多棵。其实与其毗邻的水杉数量也不少,也三十多棵,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叫白桦林。其实是杂木林,好几棵松树、白蜡,还不算外围一圈矮灌木林,温暖季节树木葱茏,这些树木跟篱笆内的树木连成一片,浑然一体,难以看出有什么分别,哪是我们私人的,哪是公共区域的。我们喜欢那片白桦林,同样清楚白桦林不是我们的,这之间是有界限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喜欢。必须划出地界。这是契约,是约定。要有地界,且地界必须垒高,已经不能用一块界碑来标明了,不能用一块木头或石头,我们这辈子就没见过,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是各种各样的篱笆墙。下午茶时,D我们俩更喜欢坐在餐厅,正对着西窗,看窗外的一小片树林和不远处的青山。鸟不时地飞过来,从白桦林的哪一棵树的枝丫上起飞,直接落到窗下紫苏棵里,或者从窗外急速兜个小弧线,然后向上拔起直接出镜,飞到窗框外边去,让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踪影。空中畅通无阻,要是两只鸟追逐而飞,更见出鸟们的飞行惊人地神速,两只鸟形同一只鸟,两只鸟之间没有一只鸟的距离,相隔极近,动作飞行线路和弧度却严丝合缝,高度一致。你看着它们,没法想象它们的小脑袋里到底装着什么神奇密码,眼看着它们打着旋冲你来了,却又同时遽转飞越过你,在你的上方远去或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