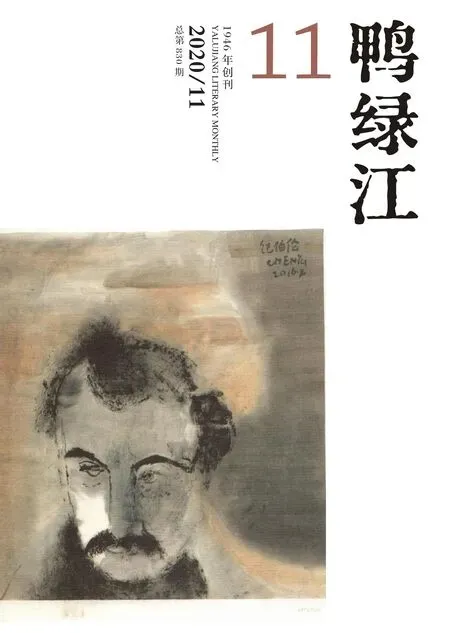郭小川的诗(二首)
郭小川
别煤都
煤都已经远了,远了,
这车子还在猛进急驰。
来路上的烟云
却紧紧地追踪着你这来去不定的战士;
铁道如同一条绵长的、有弹性的血管
连接着你的心胸和你的形迹。
无论你走到哪里,
煤都也要追到哪里;
别处纵有千好万好,
煤都究竟无法代替。
据说,最深的印象
将会反复地闪现在睡梦里。
那可就太好了,
飞来吧,煤都的色彩的翼翅!
那幻丽的夜景,
那丘陵中的城市,
那龙凤矿井上的红星,
那露天矿中的虹霓,
那千台山上的晓雾,
那浑河桥头的春意……
这一切呀,
无疑会给战士的生活带来情趣。
谁能否认哪?——
梦想也常常是一种生机。
多少英雄由于梦想着美好的未来,
无畏地把生命投入枪林弹雨;
多少英雄仅仅为了梦想,
将自己的鲜血洒上开花的土地;
而在我们的无边的国境内,
科学的梦想简直就是高大的旗帜。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说:
最深的理解将贯注于沸腾的白日。
最好的梦和最大的理解
常常是如此地不可分离。
那么,在这暂短的逗留中
你理解了什么呢?
你那窄狭的胸襟,
能够包容几块发光的矿石?
所幸呵,这开朗又狂放的煤都,
只使人陶醉,却不使人沉迷!
姑且这样放胆地说吧:
煤都是矛盾的!
它是那样老成,
却又那样富于青春的朝气;
它是那样安详,
却又那样满怀英雄的大志;
它是那样寒冷,
却又那样充满热力;
它是那样和善,
却又是那样无所畏惧。
是的,这样的种种矛盾,
曾使你在初来时感到惊异。
当太阳放出万丈光芒,
矿井下黑得比夜还浓郁;
当街道上已经亮开万家灯火,
煤井下却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日;
当城市沉沉入睡的时候,
矿工们还万炮齐发、千锤并举;
当纷纷纭纭的人群涌上街头,
升井的矿工却刚刚进入柔和的梦里。
然而,正是这样
生动的矛盾才达到奇妙的统一。
在这里,英雄的内心和美丽的外衣
是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老年的干练和青年的勇敢
是如此完整地凝结于一体;
这里,冷静和热情
在同一心灵的土壤中放出丫枝;
这里,寒流与热火
在最猛烈的斗争中迎来了花红柳绿。
就这一点点吗?
多么平凡无奇的哲理!
然而,这一点点也许水久刻入你的心头,
无论在梦中,还是在白日。
这一点点,将带着煤都的夜景,
进入你的亲切的回忆;
这一点点,将伴着煤都的春天,
装点长长的金色的日子,
这一点点呵,将在你的无定的往来中,
增添了说不尽的诗情画意。
现在,在这重要的时刻,
你还必须郑重深思:
从这热和力的源泉里,
你究竞带走了多少热和力?
为了煤都——也就是为全国,
你将能付出多少心血和勇气?
你将用什么来确凿地证明
曾经是来过煤都的战士?
呵,煤都已经更远了,更远了
这车子还在猛进急驰……
1961年3月10日于沈阳
鞍钢一瞥
在这里,
黑夜总是衰弱而又短寿;
在这里,
星星月亮总是满面含羞;
在这里,
腾腾的热气总是最早截断春夜的寒流;
在这里,
火红的云霞总是最先突破黑天的缺口;
在这里,
团团的炉火如同一群太阳在夜间停留;
在这里,
太阳好像从炉火中诞生而不是升自那高耸的千山背后。
——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呀
为了把答案寻求,
请你登上对炉山
从黎明了望到太阳出山的时候:
你看那——
星星和月亮唱着无声的哀歌宣告退休;
你看那——
云霞和热气以火焰般的激情托出大厦高楼;
你看那——
森林般的烟囱从炉火的红光中一齐举起有力的长手;
你看那——
山般的炉群
在太阳的召唤下同一刹那抬起了头。
于是在你的面前,
就有两个伟大的事物一同出世;
一个是太阳——这宇宙的骄子;
一个是鞍钢——中国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太阳用母亲般的温柔的手,抚慰你的脸庞和躯体;
鞍钢则以钢铁的铿锵的音响,鼓舞你的豪情壮志;
你成为最幸福的人了,
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地明亮而又壮丽;
你会不由地迈开三尺阔步,
满载着太阳的光辉向鞍钢的中心急急走去……
你大概无心观赏市容,也不会去留意街头的喧器的声浪;
这时节呵,
你的心中也许充满了新奇的设想。
你仿佛看见:
那些炼钢化铁的英雄们都在谈笑风生地欣赏着美丽的炉膛;
你仿佛看见:
那些身高万仞的炉群都像挺拔俊秀的山峰一样;
你仿佛看见:
从炉口滚出的钢河铁水都像山谷里的小溪似地丁当流淌
你仿佛看见:
进度表上的红色箭头都像风筝般地随风飘然直上。
能说你没有可靠的根据呢?无数确凿的事实书写在史册上;
年年增产的数字啊有着诗一般的动人的力量。
所有的来访者都可以证明: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如今确是成千上万个英雄的故乡;
所有的摄影家都敢于断定:
这个工业基地的景物时时都能够提供美妙而迷人的影象;
所有的冶金专家都可以宣布:
这个曾是破旧不堪的企业于今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技术武装;
所有的人都不能不相信:
这个企业的钢铁产量已经成倍、成十倍增长。
可是当你越过白楼、穿过洞门,
你或许要发出这样的惊呼:
——这是鞍钢吗?
——简直是一簇簇庞大而纷杂的怪物!
那平炉并不平坦,而高炉则过于突出,
它们仿佛有意把高高在上的天公羞辱;
那厂房大于海上舰船,梯道又险过山中栈路,
今日似乎决心在这块平地上安家落户;
那电缆有如万丈长鞭,烟囱好似擎天大柱,
它们正跃跃欲试地要在这里打插比武;
那煤气管恰像黑色巨龙,火车赛过成群结队的猛虎,
今天在这迷茫的云雾里狂奔漫舞。
而你呀,
且不要过早地惊骇,
那厂房的奇异场景,甚至会使你目瞪口呆。
什么暴风骤雨!
在那轰隆轰隆的音响中间,早已失去它那英雄的气概;
什么飞虹闪电!
在那喷薄而出的钢花铁水之前,早已变得暗淡而没有光彩;
什么雄狮巨象!
与那大型的机械相比,简直像猫狗一样纤弱而低矮;
什么山鹰海鸥!
只要看看飞行在空中的吊车,就会吓得连翅膀都不敢张开。
此刻呵,
你千万不要停歇!
你应当尽力保持镇定的心情,
进一步把这新奇的事物理解。
看,运载矿石的火车到达了,
原料车间的装卸工人竟分秒不误地前去抢卸;
看,白热的钢水喷出来了,
它真像爆发的山洪一般凶猛,却驯服地对准大罐口倾泻;
看,淡红色的钢坯跳出炉了,
它只顾沿着预设的轨道乖乖地缩小、轧平直到冷却;
看,各种型号的钢材轧成了,
汽笛欢叫的一列列火车又像摇篮似地来把新生的产品迎接。
也许是从此开始
你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你面前所有的纷杂的事物
仿佛一下子都被安排得妥妥贴。
那高低起伏的声响呀,
并不是狂呼乱吼的噪音而是像交响乐般地和谐;
那飞速转动的机轮呀,
呼吸得这样地匀称,神态又这样稳重和亲切;
那庞然杂陈的建筑物呀,
并不是没有章法的棋局,而是有组织的群体和有秩序的行列;
那千头万绪的联合企业呀,
一个工段紧接一个工段,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
现在你一定不像刚才那样惊骇了,
生活的芳香的酒使你陶醉;
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你已不能不大为赞佩。
多么巨大的组织才能呵,
使这一簇簇怪物
都服服贴贴地蹈矩循规;
多么神奇的力量呵,
教这笔半殖民地的遗产放出如此强烈的战斗的光辉;
你不能不深深地爱上鞍钢了,
似乎不再想着北去,
也不再想着南归;
你的灵感的翼翅又飞翔啦,
你在追寻着最好的诗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钢铁基地赞美。
但是,你必须承认:
你原来的设想并不完全符合实情;
这里是欢乐的、胜利的,却一点也不平静和轻松。
你看那炉长和炉前工
时而庄严地守候着巨炉,时而又像兵士那样勇猛地陷阵冲锋;
你看那在高空作业的工匠,
一会儿像飞鸟般在钢架上疾走,一会儿又像猿猴般攀援在房顶;
你看那在炉顶上操作的维修工人,
在近百度的高热中挥舞风管,就像神话里的仙人驾驭着飞龙;
你看那维护生产动脉的电工,
在无形的可惊的险境里工作,就像在怒海狂涛中破浪乘风。
在这里,不仅需要勇敢和敏捷,
而且需要高度的智慧、坚韧和镇定。
这里的十万建设者呵,都是那样高高兴兴又战战兢兢!
你看那厂长和党委书记
时时都在思考着、警惕着,又致密地指挥着持续不断的斗争;
你看那年轻的广播员
时时都在吃力地、精心地选择词句,发出钢铁厂特有的急促的高声;
你看那干练的调度员,
时时都在计算着、奔走着又调动着车辆和机械合理地运行;
你看那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时时都在刻苦地、谨慎地从事筹划,以保证生产正常和线路畅通。
从此你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了,
事实和想象常常是这样不同。
而生活的真理呵,多么巍巍然不可摇动!
这里的成千上万的英雄,
和这里的钢铁一样,是在洪炉里千锤百炼而成;
这里的光亮的钢花铁水,
不是山谷里的流泉,而是千万建设者的汗水的结晶;
这里的强大的技术武装,
和我们的军事武装一样,是在战斗的烈火里诞生;
这里的进度表上的箭头,
不是随风飘荡的风筝,而是无穷的勇敢和智慧的缩影。
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
你所见的风光比刚才还要明媚,
你平素所熟知的那些数字,此时更像大山一般地雄伟。
你的面前已不止是一座座巨炉、一垛垛钢轨,
而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一座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堡垒;
你的身旁已不止是十几万兵士和众多的指挥,
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支智勇双全的突出队;
听,鞍钢的机器的轰响,成了震动天地的洪雷;
看,一杆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红旗,在阳光四射的早晨骄傲地翻飞!
1961年2月草于鞍山
4月改于北京
《别煤都》首刊于《文艺红旗》(本刊曾用名)1961年第4期。
《鞍钢一瞥》首刊于《文艺红旗》(本刊曾用名)1961年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