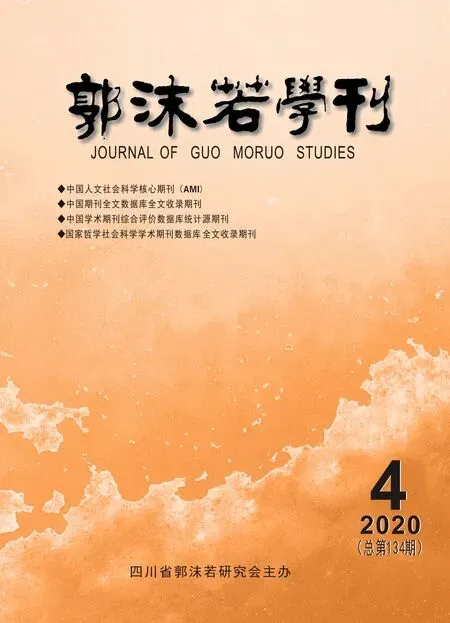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有关张恩和先生的记忆
魏 建
我认识张恩和先生很早——1983年,那时我在泰安师专任教。他和黄侯兴先生来山东出席郭沫若的学术会议,领导安排我陪他们两人游览了岱庙。张恩和先生穿了一件呢子大衣,很有派,像一位外国元首。可惜那天我们二人没怎么交谈,恩和先生的兴趣全在欣赏岱庙里的碑刻。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1986年9月。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全国性的郭沫若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益阳开的,会议主题是“郭沫若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此前我给《郭沫若研究》投稿的论文与会议主题一致,所以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到了会上才知道,像我等无名小辈只有三个,其他与会者大都是郭沫若研究的名家,可除了黄侯兴、张恩和两位,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黄侯兴先生是会议主办者,一直忙会上的事。恩和先生便成了我唯一的熟人,会下我总在他身边。他也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学术前辈:卜庆华、邓牛顿、傅正乾、高国平、龚济民、黄淳浩、李福田、邱文治、孙党伯、孙玉石、吴中杰等(以姓名音序排列)。会上所有人的发言都很认真,有几人讲得特别好,其中就有张恩和先生。当时学界对郭沫若的评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评价”。与那些人的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不同,恩和先生的发言别开生面。他既不认为肯定郭沫若就是保守,也不认为批评郭沫若就是“砍旗”。他说:对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大家敢于“说长道短”,是社会的进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思想解放还不够。他发言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震惊:尖锐批评了一位在场的学者,完全不顾人家的面子,就像与那人有仇而借机发泄。此后,经若干年观察,我才确定:这就是张恩和,敢批评,不管对谁。他与那天的被批评者关系不错,之所以无情批评,不过是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但只有他敢说。
第三次见面是1988年在北京召开的“郭沫若在日本”学术研讨会,第四次是在1991年的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再往后,就记不准是第几次了,反正见面越来越频繁。我发现:同龄学人对他都很客气,只是他对一些人爱答不理,时而露出不屑的微表情,或是歪头看人家一眼,低声嘟囔:“哼!风派人物!”遇到一些大家都看不惯的事,他肯定要指责的,不管场合,也不顾及情面,使得我原以为,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可是,多年来我参加一些张先生缺席的学术活动,许多前辈常提到:“张恩和怎么没来?”言语间流露出或偏爱或敬重的神色。后来我才明白,同辈人敬重恩和先生,因为他的正直,还因为他的资历。
张恩和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中是老资格的。这一代学人大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虽然年龄相仿但学术经历差异很大,大致可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类学术起步早,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学术成果在“文革”以前就产生了影响;乙类学术起步早,出成果较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少有学术成果发表;丙类学术起步稍晚,“文革”前没有涉足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从鲁迅研究起步;丁类学术起步最晚,此前从未涉足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才开始学术生涯。甲类与“第一代”学人关系密切,其佼佼者不仅有过与“第一代”的学术合作,还共同指导过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丁类与“第三代”的学术起步几乎同时。显然,“第二代”的这四类人中,学术辈分最高的是甲类的佼佼者,张恩和先生就在其中。
张恩和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就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1960年代前期在《文学评论》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1961年他被选入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会,直到1979年,他参加了这部文学史编写的全过程,负责该书鲁迅(上)(下)两章和《暴风骤雨》等章节的撰稿。这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影响最大、权威性最高的文学史著作,不仅因为它最早冠以“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还在于它是众多一流专家集体智慧的产物。这部文学史的作者也随之名扬天下。这部书的编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64年,张恩和先生与编委会成员一起完成了全书的讨论稿。这期间,他还与“第一代”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等人一起研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文学史书写的学术问题。第二阶段1978—1980年,除了主编唐弢和严家炎,他与樊骏等“第二代”学者形成编写组的核心成员(见该书《前言》),为这部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问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恩和先生还深得李何林、唐弢、王瑶、刘绶松、田仲济等“第一代”学人的赏识,使他较早进入“第三代”学人的师长行列。例如,1981年李何林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另外两位导师中就有恩和先生。1983年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又协助唐弢先生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当然,一个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主要是靠学术水平奠定的。学术水平又如何体现呢?有的人看重学术生产的“量”,更多学人看重的是“质”。我以为,衡量学术质量的主要标尺有两个:一个是开创性,二是生命力。先说前者,恩和先生的鲁迅旧体诗研究、鲁迅与郭沫若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化学研究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创性贡献。再说后者,最近我重新阅读恩和先生很多年前的一些成果,几乎看不到时代的印记。因为他不跟风,也因为做得扎实,所以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关注和敬重。如,重读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其站位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论证的水平,令我佩服之至。
我对恩和先生印象最深的一幕,是2000年8月,在长白山北麓的飞狐山庄。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那天下午,我正在孙玉石、张恩和两位先生的房间里聊天。会议筹备组的领导(一位地位很高的专家)来访,就下一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的建议人选,征求意见。听到新会长候选人的名字,孙、张两人立即表示反对,理由是此人对郭沫若毫无研究,当然还有另外原因。来访者继续做工作,孙、张二先生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做起来访者的工作了。几个回合下来,双方都没有妥协的意思,一段沉默过后,张恩和先生大喊一声:“他当会长,我就退会!”孙玉石先生立即响应:“我也退会!”来访者先是一惊,然后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走了。
第二天召开的学会理事会会议上,会议筹备组的领导说:这次到会的理事没有达到法定人数,不能换届。有些理事不明就里,与邻座窃窃私语“不到法定人数,干嘛昨天还做工作让ΧΧΧ当会长?”这次会议没换届,那位“会长”没当成。
每个人都有良知,都想讲真话。可事实上,大多数人经常说假话,或不敢讲真话。当现实挑战良知的时候,多数人选择了沉默,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敢于发声者永远是极少数。沉默的人越多,沉默的时间越久,正义越难伸张,悲剧必然产生,于是“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
有一种说法叫“好人的沉默”,其实沉默者并非都是人,不乏怂人。张恩和先生是难得的好人,在恶劣压力面前,他从不认怂。他一生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深知讲真话有可能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每当集体沉默需要有人发声时,他绝不认怂!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我们都混迹于诺诺千夫之中,逃避了责任也稀释了良知的责问。随着诺诺之风的猖獗,我们更加敬仰张恩和先生那样的谔谔之士。
2019年11月10日张恩和先生在北京病世,他再也不说话了!
在学人中,有真才实学的并不多,恩和先生是;少数有真才实学的人中,有公心有正义感的很少,恩和先生是;这极少的人中,敢在别人沉默时爆发的硬骨头更为罕见,恩和先生是;在这罕见的人中,硬骨头能几十年如一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恩和先生是。
可惜,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