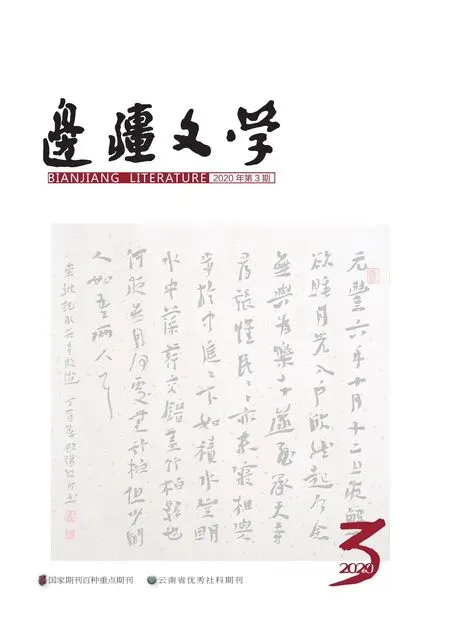没有神笔的马良[短篇小说]
梅妆
一
我缓缓从地上爬起时,黑色越野已绝尘而去。
腰杆子火辣辣的,腿也痛,不晓得是那狗日的光头功夫厉害,还是我自个儿身子骨太单薄,反正那熊玩意两脚就把我放倒了。牛皮筋底,死硬死硬的,一脚踹腰眼上,我两眼一黑天旋地转;一脚踢腿干上,我额头登时放了汗。三人扔死猪一样把我撂到这荒郊野外,跳上越野扬长而去。
十七十八月黑头,夜伸手不见五指,天公地母混沌一体,远处灯火缥缈,恍如鬼火萤萤。我估摸自个儿被那伙王八蛋扔出城不下六十公里。这个点儿,公交车早没了,过路的的士倒有,可借俩胆儿,哥哥们也不敢停。黑漆漆的野外,除了劫道歹人,还有孤魂野鬼。
路边这片芦苇荡是先前处决犯人的地方,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九世年代中期,数以千计的死刑犯在这被结束罪恶的生命,后来不知是换了地方,还是社会治安好以身试法的人少了,这里再也听不到沉闷的枪声。刑场废弃后,怕招晦气,早起的老汉不来这拾荒,拔兔草的孩子更是远远绕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他爸是李刚”的人为因素,个别冤死鬼在所难免。这里常会出现一些诡异,譬如早上周边清朗,芦苇荡却大雾弥漫;雨天周遭无风,这里却会旋风骤起劈断道边参天白杨。即使红天大日头,走这疙瘩都会心惊胆颤,何况这黑漆漆的夜。
如果不能叫停一辆过路车,我就得启动11号走回拖蓝城。凭我这脚力,估计得走到天明。今个儿是蒲兰生日,我就是爬也要爬回城里去。爱情是针强心剂,我爬起来活动了下腿脚,一瘸一拐地奔到路边,祈祷过路的神仙让我遇个好心人。
我掏出手机亮屏,一次次朝驶来的大车晃。大车在黑夜里隐却真身,只留俩大眼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扬起的尘土扑头盖脸,我不得不夹起眼来。几次三番后,我就放弃了。手机屏这点萤光,着实可怜,就像沙子落入沙漠,水滴汇入大海,被货车的大灯强光完全吞没。抑或司机明明看见也不会停下——一寸光阴一寸金,疲于奔命的我最是能够理解疲于奔命的他们。
对,今夜爬也要爬回拖蓝城,否则我给蒲兰没个交待。当然我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我怕冯涛那小子借蒲兰生日,进一步掳获芳心。蒲兰在单位与这小子走得近乎,早就成了我心头大患,害我寝食不安,害我频做恶梦。
这节气上,水泛冰凌子了,风能割掉耳朵,可怜我身上棉衣单薄。一入冬,蒲兰倒是给我买了件新的,我没穿。身上这件虽破,却是遗留下的母爱。母亲在我十六岁那年病故,在去之前,她拼尽余力给我和姐各缝了一件棉袄。姐那件是碎花的,我这件是深蓝的。那时候我的身量基本长足,也就一直穿到这。在这千里之外的拖蓝城,到处冷硬,只有这件棉袄能让我触摸到母亲温润的气息,一年年帮我抵抗着季节的冷,人世的冷。
我咬牙忍着身体之痛心灵之殇,朝着灯火阑珊处一步步挪动。
贪小便宜吃大亏,我感觉自个儿脑袋被猪拱了。就在四个小时前,我打小广告一个联系电话,喂,你好,请问代扣驾驶证一分多少钱?两百啦。手机里传来个当地口音。我心情一下子澎湃,两百?反正我没车开,留一分就行,也就是说可以拿出十一分,换成两千二百块钱。两千二百块呀,都赶上我一月薪水啦。有了这份外快,我可以买件像样的生日礼物搏女友一笑啦。呀,谁让你乱花钱?蒲兰一准会口是心非,一准会两颊通红像熟透的苹果,极为娇嗔地捶打我并不宽阔的胸脯。我呢,借机揽美女入怀,然后,嘿嘿,你懂。
我嘿嘿笑出声,对方不耐烦地说,扣不扣?我收回心猿意马,连忙说成交。
我和蒲兰都是大西北野象坡出来的,我们中学就相恋了。那时候蒲兰父亲倒卖山货母亲在家喂猪,家境好一些。我家却是个烂摊子,母亲有胃病,家里常年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元胡、砂仁、藿香、山楂、鸡内金,诸多药味混在一起,透过衣服渗透进我的肉身,从小学到中学,女生都不愿和我同桌,以至于初二之前,我的词典里就没有“同桌的她”。而那些男生,干脆给我起了个诨号“中药铺”。我是自卑的,为渗入肌体的中药味,更为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困。直到初二那年遇到蒲兰。蒲兰以前跟着她姨在另一乡镇上学,后来她姨调到县城,她转回本镇。老师安排她与我同桌,这个大眼睛女生非但没嫌弃我,还说喜欢我身上的中药味。感动无以复加,爱情风起云涌。
母亲像棵细脚伶仃的芦苇,风一吹就会倒,家里拾掇拾掇缝缝补补尚能应付,耕种耙犁全拎不起,几亩口粮田全是父亲的事儿。打我记事起,父亲像头老黄牛,拉着生活这辆沉重的破车,农忙了在家务农,农闲了就跑城里打工。我初二那年母亲撒手走后,这个铁打的汉子承受不住,夜以继日地喝酒,没出两年喝出个肝硬化来。父亲死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读书了——既然是家里的男子汉,就得挣钱养家让姐把书读下去。在一个火烧云霞的傍晚,一起坐学校西边的小山上,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蒲兰。蒲兰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汪了泪,却笑着对我说,放心吧,马良,你就是回家种地,我也和你好。
那个傍晚,我们第一次拥抱。
我姐马小竹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杠杠的,学校里就指望拿她放卫星。马小竹这年上高二,再熬一年就有出头之日了。把父亲埋到大洼与母亲合葬后的次日,马小竹留下一封信远走他乡,我这才晓得她早就背着我把学退了。姐在信里说,马良,我亲爱的弟弟,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是男丁,你是咱老马家的希望。居然和母亲在世时一个腔调。
那一刻,我感觉母亲的灵魂一定附在了马小竹身上。
马小竹去了鱼龙混杂的南方,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月月寄钱来,开始三五百,后来一两千。也打电话,电话都是打到学校的传达室,我一接就想哭。我哽咽着央求,姐,你回来吧!这学我不上了,咱一块种那几亩地吧。马小竹每次都训斥我,屁话!野象坡穷得兔子不拉屎,你回去耪四茏能有啥出息?!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马小竹过年也不回,春运千军万马,年年没她的踪影。或许因为快过年节了,马小竹这时候打电话从来极尽温柔,弟啊,姐在这加班,一天能拿三天的钱哩,就不回啦,啊?你去上坟时替我祭奠一下爸妈,再买点年货添身新衣。我困惑地说,姐,年都不回,钱挣多少才是多啊?姐不吭声,半晌后说,你要上大学了,总得做点筹备。
马小竹一直跟我说自个儿在深圳万莱坞电子管厂上班。后来我一堂叔说,老膏药的儿子大柱子就那干流水线,他打听过厂里压根就没马小竹。不光没有马小竹,张小竹李小竹王小竹,名字带竹的一概没有。我一下子急啦,我最怕马小竹不走正道,她瞒三骗四地到底想掩盖什么?高二那年一放暑假,我买了张火车票,一声不吭抵达深圳,在万莱坞居然真没找到马小竹。大柱子把我送到火车站,叹口气说,你姐为你肯定吃不少苦,你好好上学才对得起她。
那时候马小竹已经买了诺基亚手机,我却没勇气去求证什么。我气冲斗牛跑到深圳,灰溜溜地跑了回来。我不问马小竹,我怕自己心里那座山轰然倒塌。我想,我已晓得马小竹过年不回的原因,但不能戳破。这像一个打破了壳的蛋,那层膜戳破就要淌黄了。不戳破那层膜,我们就能保存那份已经不存在的体面,掩耳盗铃地活着。
我作为男人的那点血性,化成一夜哭嚎,撒在野象坡的夜风里。那一夜,也是这么黑,我哭得化摊泥软在山石上。
第二天回到课堂,我拼了命地学。离高考还有四个月,我从班里的三四十名一下子爬到前几名。高考成绩出来,我被南京一所211 高校录取,蒲兰则考了个二本。蒲兰父亲在山里收了两车核桃,没想到被收山货的老板骗个精光,家底子全砸进去。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蒲兰母亲喂了二三十头猪,因为猪肉价格史无前例的低,也赔了个底朝天。两下一挤,蒲家一下子由富裕户变困难户,蒲兰的学费拿不出,我不能眼瞅着她失学,便拿出些钱来帮她。
我咬牙忍着身体之痛,朝着灯火阑珊的拖蓝城一步步挪动,走了两三里路,就难以为继了,前胸贴后背的感觉真让人难受,我这才记起自己除了早上吃过两个素包子,这一天都没顾上喂肚子。两条腿直打晃,我抱着脑袋蹲下,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刻我分外想我妈,想我妈做的手擀面。那一碗热气氤氲的面啊!在手擀面的诱惑下,肠子蠕动更快了,我不得不裹紧我的棉袄。
二
想罢我妈的手擀面,又开始想马小竹的葱油饼。马小竹继承了我妈的心灵手巧,烙的葱油饼香到无以复加。
马小竹莫名其妙从这个世界消失了。那年,马小竹看万莱坞的谎言编不下去,便告诉我她在西塬一服装城上班。马小竹失踪后,我去西塬市公安局报警,警察叔叔说每年这种流动人口失踪全国数以万记,找起来大海捞针。马小竹!马小竹!马小竹!我蓬头垢面在西塬的大街小巷乱跑乱嚷,跑到香街芳春苑门前,一个染黄毛打扮妖冶眼袋有点浮肿的女人一把拽住了我,你是马良?我说我是,你咋知道我?女人叹口气说,你姐以前跟我一起干,我俩挺处得来。我姐呢?一提马小竹,我急不可耐。你姐喜欢上一个叫江海的快递员,前年跟他去了裴里翠。裴里翠在哪?我要去找我姐!我激动起来。
女人眼睛里泛里泪光,傻小弟,你找不到她了。
路上的大车多起来,灯光熙熙攘攘,耀得我睁不开眼。泪水爬出,沿着腮帮子流进嘴里,我很惊讶我的舌头居然还能辨别这份咸涩。此时此刻,要不是人世间还有个蒲兰,我真想一头钻进车底,让自己化为一滩血水,永远结束这让人摸不着北的人生。
黄毛叫蒋千帆。一听这名字,总令人想起温庭筠的《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幽幽。蒋千帆有自己的心伤。我和万山水是在一个小餐厅认识的。蒋千帆说。当时,我要了一碗米粉两个茶叶蛋,付费时前面有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身上忘带钱。收银员说你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眼镜脸红。我看不下去了,说我一块买了。我们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后来一起吃过几顿饭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原来,那时候的蒋千帆年轻、打扮得也清纯,万山水并不晓得蒋千帆的真实身份,一直以为蒋千帆是公司职员。晓得蒋千帆干那个,是五年之后。两人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万山水医科大学毕业,决绝地离开了西塬,跑回老家所在的城市。我堂堂大学生,决不可能娶个妓女!万山水对蒋千帆说。蒋千帆的心被剜了,整个人软成一沱面条。天蹋地陷一番挣扎,蒋千帆终于明白这个白眼狼其实早就知道她从事的行当,捂耳朵偷铃铛自欺欺人罢了,掏干她腰包罢了。就这样,蒋千帆的钱、青春与爱情,一起离开了她。也就从那天起,她开始自暴自弃。
兄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有时候回头也无岸。
如果此话出自一个道法高深的僧人之口,我决不会惊诧。可对面是蒋千帆。蒋千帆跟我说这话时,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口,缓缓吐了个烟圈,满脸颓废。
那一刻,我想教授说的那些都是狗屁,生活才是最好的哲学老师。
马小竹也是这样子?刚才那不恭的念头一闪而过,随之这个问号差点让我崩溃。
离开西塬,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毅然去了地处南鲁的裴里翠。一个快递公司一个快递公司地找,找了三天终于找到江海。
江海个头不高,头发有日子没理了,胡子拉碴全没半点青年人朝气。他那张脸出奇的瘦,眼睛出奇的大,别人双颊圆润的地方,他却是两坑深陷,如果脸上能盖楼,他肯定不用挖地基。江海那双大眼睛漠然地望了我一眼,说马良,我早该去找你的,可我老妈瘫床上离不开,打你电话也不通。
江海请了半天假,将我领进一家小酒馆。老板,四菜一汤!他说。白皙的胖老板娘,鸭子一样跩过来,今儿个倒大方啊,发财了?呸,发啥财,咱想钱钱不想咱。江海说完,捏起吧台上一根牙签剔起牙来,一口黄牙肆意张扬。对于这种资深烟民,打小讨厌得紧,我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全然不晓得马小竹咋会喜欢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男人。想当年,马小竹上中学就会写诗,还参加了学校文学社,上高中后又参与了校报《红叶》的编辑工作。她发《红叶》一首名曰《乡情》的诗,其中有两句被引为校园经典——故乡离我很近,故乡离我很远,我赤脚走过的田埂瘦成草蛇灰线,我濯足荡起水花的小溪涨成桃花深潭。
菜上来了,我没半点食欲,那些悲伤抵达了我的胃,又穿肠而过。我想吐,想翻江倒海地吐。可两天没吃饭,除了酸水胆汁,也没啥可吐的。江海顾自喝着白酒,大口大口的。胖老板娘上茶,亲昵地拍了拍他肩头,兄弟,再找个呗,何必苦了自己。又对我说,这个傻瓜,自从老婆死了,就一直放单飞。想的开也好啊,三天两头跑来喝酒,回回烂醉如泥,说也不听。既然是朋友就劝劝他吧,啊?老板娘的话让我豁然开朗——马小竹死心踏地跟江海来南鲁,来这个叫裴里翠的小城,完全因为这男人这份痴情吧?人在寒冷的时候,但凡有点火星都想偎过去,何况江海是个燃着的火球。一念至此,我原谅了马小竹精神上的这种沦陷。
我姐怎么死的?我眼圈一红,差点管不住眼泪。是的,这就是我此行目的之一,之二是想把马小竹骸骨带回野象坡,叶落归根,还是离爹妈近一些好。
江海大着舌头,马,马小竹有话,说自个儿活着时没脸回家,死了就更没必要回了,她怕把家乡的土污了。
至此,我才知道马小竹死于那种病。
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啊,就是一江清水也给染黑了。我狠命撕扯着头发,心痛到寸寸成灰。
江海人醉心不醉,仿佛看穿了我。他抬起头,两眼猩红,你姐在西塬并没染上。我认得她大半年,她都不让我碰她身子,直到我决意带她来裴里翠,她去医院做了检查。一查阴性,欢天喜地,似乎重生。
那她?莫非是你不检点害了她?我如同发现了猎物的鹰,凶狠地盯着江海。
江海仰脖透了杯中酒,又拿酒瓶给自己满上,你错了,兄弟!你哥我压跟就不是那种人。在西塬那么多年,我没找过一次小姐。有次傍黑,我一人出来溜达,有个半掩门子拉住我说不要钱我都没上。不是咱洁身自好,是一看她我就想起村里的姐妹。我疼惜钱,也疼惜我娘。我是遗腹子,娘独力把我拉扯大不易,我就想攒钱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两人一起好好侍奉我娘。
我想起那病的传播不止一条道,又问,卖过血?江海摇头,不,不是。来裴里翠后,我和你姐简单举行了个仪式,请亲朋好友喝了杯喜酒就算把婚结了。我干快递多跑几单钱就出来了,让你姐在家歇着,趁早怀个一男半女的,我们这小日子就红火了。你姐呆不住,非要去一家叫万春来的大酒店干收银,说挣了钱给你寄些,剩下的攒首付买商品房。到大酒店干收银,也算体面活,我拗不过她,就由了她,哪承想就害她丢了性命。
江海眸子里那点火苗熄灭了,他又端起了酒杯。
我这才晓得,万春来的老板娘,为了酒店效益,组织漂亮职员搞性贿赂,往这拉一些高规格的招待项目。马小竹原先打死不干,却驾不住威胁利诱。陪一次酒,老板娘给一万元红包。干收银巴死巴活一个月累得静脉曲张也不过千把,江海兔子一样窜上一个月不过三千,马小竹算过这笔帐决定背着江海挣些外快。谁晓得半年后马小竹出现发热、盗汗、腹泻等症状,体重减得很快。她没当回事,江海也没当回事,只以为她是感冒。直到全身出现淋巴结肿大,舌尖出现毛状白斑,江海这才急了,请了一天假,专门陪马小竹去了医院。结果一出来,马小竹受不了,直接跳进了裴河。
江海一说,我第一时间想起韩国因陪睡自杀的明星张紫妍来。张紫妍自杀九年后,案件被重新调查,沉冤得雪,也算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姐呢,我姐的仇谁来报?
万春来的老板娘在哪?我要杀了她!我拿拳头咚咚捶着桌子,咬牙切齿。放心吧,老天已经报应她了。江海淡淡地说,小竹死后不久,她也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
你姐死了,我也死了好几个死。可我还得活着,还有八十老母在堂,我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好歹我还能喝酒,有喝醉的自由。江海笑了,比哭还难看,让人毛骨悚然。
马小竹埋在翡翠山脚,我买了几刀火纸烧给她就回了,在回来的火车上,我感觉自己被抽掉了筋骨,只剩一摊臭皮囊。当然,我尊重马小竹,把她留在了裴里翠这个山青水秀的小城。有江海陪着,我想她不会太寂寞。
三
腰痛得厉害,腿痛得厉害,我这蜗牛爬式的行进,什么时候能到拖蓝城?我跺跺冻得发麻的脚,拢起双手朝手心呵气。焦急回望。有辆中巴滑过,停前边不远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肯定是司机动了恻隐之心。感谢上苍!感谢如来!感谢观世音菩萨!我一边在心里胡乱地喊,一边慌慌地跑,眼看就要够着车尾巴,中巴发动了。等——等——我!我大喊,声音在空中打了个旋,跌落地上摔得粉碎,像一件瓷器。中巴绝尘而去,车尾气与蹈起的尘土钻进我的嘴我的眼我的鼻我的耳朵。我无力地倒在路边,大放悲声。然而,谁又能听见我的哭声呢?一辆辆大车小车疾驶而去,只有风,风听见了一个男人的鬼哭狼嚎。然而,我算一个男人吗?一想这个问题,我就茫然。
勿庸质疑,我姐的死与我不无关系,纯粹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要从我姐这个角度说,我真算不上一个男人。一次我喝了酒,耍酒疯,又哭又笑。蒲兰搂我肩安慰,说马良你别这么说,要不是你,这学我能上到今天?
马小竹失踪后,我和蒲兰的日子一下子跌下水平线。我们在学校申请的助学金,相比于庞大的学费生活费,实在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我在学校打工,可学校那么几个商店,僧多粥少。我只好批发一些日常用品到学校出售,卖过水果,卖过手机卡,也卖过卫生纸、卫生巾。一个男生卖妇女用品,有时难以启口,有些文静女生也羞于过来。我只好置办了一身粉色裙装,买了个假发套,把自个儿男扮女装。把脸抹白,把唇抹红,把胸罩塞满丝棉紧勒胸前,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再加上一头披肩长发,居然颇有淑女范。最搞笑的是,有大一高个子男生迷上了我,天天跑来与我啦呱。尖着嗓子说话,本来就累,又怕他识破,只好跟他大谈我的男朋友。
最悲哀的是,某个周末蒲兰一声不吭来了,蒲兰拿起一包安尔乐卫生巾问价,又指一包猫王卫生纸问价,问就问吧,却偏偏掏出手机开始联系男朋友。手机在我身上叮呤作响,蒲兰兰眼睛一下瞪得溜圆,既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苦笑,说实是无奈之举。
大学毕业后,我去一家瓷器生产厂家应聘,结果让去烧浴盆。那温度,我全身的皮肤被烤得嗞嗞叫,虽然有防护,我也清楚地感觉再烧两天自己就要给废了。如果老马家的命脉断在我手里,到了那边,有何面目见爹妈?一念及此,第二天我就辞工。当家教、当代课教师、去干流水线,此后经年,我的日子颠沛流离。蒲兰比我好过不到哪里。我们决定考公务员。走这条光明大道的暂且只能一人,困顿的生活容不得两人一同任性。我盯着蒲兰说,砸锅卖铁我也支持你!蒲兰含泪,说马良,你真好!嗯,我考出去就返来供你。蒲兰走进一家收费高昂的培训学校,全天候应考培训,一年两万八千块的学费,差点把我的腰杆子压弯。幸好蒲兰争气,第一年败北,却在第二年考上市级公务员,进了市税务局干文秘。我在一家机械厂三班倒,公务员之梦搁浅在黄沙滩。蒲兰吃了行政饭后,开始跟我谈房子谈车子谈化妆谈首饰,独独忘了我们的相约。
我这才晓得爱情对于一个穷小子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基础,尽管我们拥抱接吻上床,把该干的事都干了个遍。
车子房子首饰化妆品,都是禁区,那两毛钱工资不允许我去染指。我成天给蒲兰打哈哈,要么转移话题,要么柔情以待。时间久了,蒲兰见我的愿望就没那么强烈了,就说上个礼拜,明明说好一起去周老大饺子馆吃饭,我都到地头了,她却微信,说他们副局长请客,她来不了。操他妈的小白脸,动不动拉着蒲兰加班,加班就罢了,还动辄一起出差。蒲兰说他们副局叫冯涛,这个冯涛让我寝食难安。房我不敢想,车我不敢想,贵重首饰我不敢想,卖了驾驶证上的分我可以给心上人买套化妆品做生日礼物。再不修葺,我担心多年辛劳是为他人做嫁衣。驾校是去年蒲兰拿第一个月工资后替我报的,说是送我的生日大礼包,现在我卖了分给她买生日礼物,也算投桃报李。对,十一月初六,她的生日就在今天。此时,蒲兰在干吗?会不会与那个小白脸相约红房子西餐馆,冯涛手捧玫瑰,拥她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念及此,我感觉脊梁骨又被人猛击了下,全身瘫软。夜,依旧很冷,很黑,好半天我才抹抹眼睛,继续一瘸一拐前行。
我和小广告上的老黄牛,约在城东一家交警队。接上头,光头一见我就说,你是马良?我说我是。光头嘎嘎地笑起来,你的神笔呢,拿出来给咱爷们画座金山呗?我一愣,这才记起小时候学过神笔马良的故事。我苦笑着摊开两手,说要有神笔哪还会计较这两毛钱。光头伸手,我把驾驶证和身份证一并递了过去。光头返手递给一个年轻小伙,小伙上机操作。处理完毕,我们一起走出大厅。小伙子把驾驶证和身份证扔给我。我拾起两证,嗫嚅着问光头,大哥,钱呢?光头头也不回,说跟我们去银行。
我跟着光头上车,车一路疾驶,把天跑黑了,就来到了这遥远的郊外,来到先前的刑场。光头把我扯下车,扔给我二百块钱。我刚一抗议,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夜很黑,夜真的很黑,又累又饿的我倒在路边。仰望着黑漆漆的苍穹,心中蓦然出现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我命令自己,跳,你给我跳!我看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风筝,牵着断线,以优美的姿态朝谷底飘去……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手机铃声在这样的夜晚,清脆又惊悚。是蒲兰。蒲兰带着哭腔说,傻子,大半夜的,你跑哪了?我还等着你给我过生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