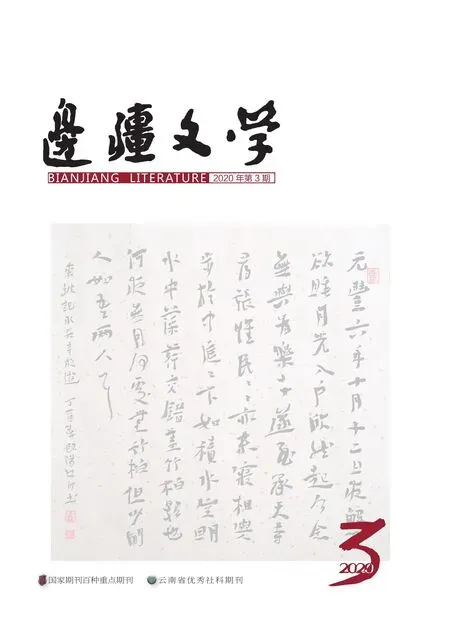河在梦中流[散文]
张乃光 白族
梦中,忽又听到儿时的声音:“到大河边洗菜。到大河边洗衣裳。”
所谓大河,是从高原湖泊洱海向西流出,穿城而过的一条河。它把我栖身的小城一分为二。河之北,是龙尾古城,居住着本地土著居民,本地人称“关迤”;河之南,是新城区,既有土木结构的老院,也有钢筋混凝土小楼。本地人叫“关外”。
还有一条穿越我整个童年的河流,它从大河分流而出,故乡人都叫它“子河”。原因不言自明:大河是母亲,它是大河的儿子。
它与大河并肩而流,最终在一个类似于小岛的地方汇合。
儿时,小城真正称得上临河而居的,应该就是子河一带人家。
不仅因为子河流经的地面人口密集。还由于子河离开母河不久,又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更小的河流,一条由南向西,一条转北西流,最后在类似于小岛的地方与母河汇合,一路形成人与水相偎相依的景象。
因了这样的原因,子河与我们的关系,似乎要更密切一些,它流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
子河,有两座石拱桥,相距不过百来米。一座在下游,墙体桥栏青桩砌成,中央白色大理石上醒目地嵌有桥名“子河桥”;一座在上游,未刻桥名,乡人同样习惯地称它“子河桥”。
梦中的我,从已经消失的老宅——正阳街16 号出发,沿正阳街往西行约五十余步,到一路口往右转,沿正阳横街往北行百来米,便到了嵌有桥名的子河桥。过了子河桥,沿文献街再行百米左右,就到大河边。
大河边,有一座更大的桥:黑龙桥。它是连接河之北与河之南的主要桥梁。
小时候关外子河片区人家所说的大河边,专指南岸黑龙桥以下洗衣、洗菜的河段,有时干脆称大河边为“玉龙关”,强调“专指”的意味,以区别于河对岸关迤人说的“大河边”——民国初年,当局拆除位于黑龙桥北桥头的龙尾古城南城门,以及城门两侧东至大关邑锁水阁、西至天生桥的城墙,曾在河对岸专开了一条名叫“大河边”的街道。
据老人讲,历史上确有玉龙关,被称为龙尾城的二重关门,与对岸的龙尾古城南城门遥相呼应。我出生时它已不在。看老照片,“玉龙关”三字石刻嵌于城门,城楼两层,下层砖砌花窗围栏,上层悬“龙关晓月”匾额,城楼飞檐斗角,很有气势。
黑龙桥,初为唐代南诏国王阁罗凤所筑,后经历代多次复修,清光绪三年(1877年)水毁,改建为5 孔石拱桥。1979年改建为全长87 米、宽10 米、有护栏围护的钢筋水泥桥。时光流逝,大河两岸的城池、街道、房舍也难遭变化之劫。1936年,玉龙关,以及子河桥南被称为三重关门的铁闸子城楼改修的德盛楼,都在烈火中灰飞烟灭。
“逝者如斯”,竟成了令人心生悲凉的谶语。
梦中月亮,升起来了,大河边有很多洗衣裳的妇人。河边光滑如玉的青石上,“咚——咚——咚,橐——橐——橐”,清脆的捣衣声,一声,一声,被河水拉得很长很远。梦中的我,漂洗完衣物起身,手一滑,“啊呀”一声惊叫,装满衣服的大锑盆落进河里,它定定地停了停,不舍得离去,等我伸出手,却又一晃一晃,渐渐漂向远处。我想追赶,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忽闪忽闪,渐渐消失。
这虽是梦,却是发生在童年的一件真事。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失落。
梦中,流动着一条白晃晃的月光,大锑盆在月光中闪动着,可望而不可及。新买的卡基布学生装,母亲新做的阴丹士林布衣裳,父亲的劳动布工装,都在盆里随水漂走。
次日一早,一阵悠扬的钟声把我催醒。钟声来自离家不远的弥陀寺。这寺在被两条子河包围着的小岛上,是离我家距离最近的一所寺庙。小岛上有所小学——下关一小,与我就读的明德小学隔着子河。课余时分,我和同学经常站在河这边,对着河对岸,扯开喉咙,尖声大叫:“一小一小,像个小岛”。
明德小学校园后面有座清真寺,儿时的我,既可听到子河对岸弥陀寺佛教的钟声,又可听到清真寺伊斯兰教的诵经声。通融与坚韧,悲悯与慈爱,虚无与笃诚,世俗与清洁,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感动着我。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六年时光。
听到钟声,我慌忙起床,沿着大河边,一路寻找。大河下游打渔村,有个河湾,水草丰茂,还停着渔船。母亲说天亮后不妨去看看,大锑盆也许会被水草拦住,或者被渔船上的人捡到。
寻到的却是失望,整条河空空荡荡。满盆衣物早已消失在梦中的河流之中。
这天早上的功课是耽误了,我没了平日大声叫着“一小一小,像个小岛”的兴致,沮丧万分地回到了家。
梦中醒来,往事历历,始觉所梦非梦;不复入梦,记忆迢迢,方知往事如梦。
儿时上小学,要经过子河南岸一条狭窄而干净的街道——文明街。街道两边立着的两层土木结构民居,多数都是本地回民,当地人又叫它“回族街”。从东向西,走过这条长不过两百来米的街道,就到了我就读的明德小学。
街道北侧人家,前面是临街铺面,后门是西流的子河。同学纳万年,家住临河楼房。是我和同学常去闲的地方。他母亲在临街铺面卖零食。我就和几个同学常偷吃他母亲腌的酸木瓜、泡萝卜,盐炒葵花籽、松子,有时还去野外采来一种叫灰条的野菜,洗干净后沸水一烫捞在盆里,几个头围在一起,用调好的酸醋、酱油、辣椒油打蘸水吃。天气热的时候,就在他家脱下衣服,光着屁股,从后门台坎跳进子河。
刚读三年级的我,不会游泳,却极好面子,见到同学像一群快乐的鸭子在河面游来游去,心生羡慕,衣服一脱,便也下了河。在浅水边用右脚尖踮一下河底刨几刨水,踮一下河底再刨几刨水,装出游泳的样子。
事情终究发生:脚尖踮着踮着离岸渐远,再踮却踮不到河底了。心一慌,呛了几口水,一沉一浮间,两岸房屋倾斜,头顶天空变横,耳朵嗡嗡响,还听到无数拉得很长的惊叫声。我被河水拽着扯着往下游漂去,绝望攫住了我的心。
懵懵懂懂间,突然又冒出水面,眼前一亮,恍惚看见一绺柳条在河面飘拂,我本能地伸出手,紧紧抓住了它……
当天下晚,班主任陈馨芬突然家访,在我家小院石榴树下和母亲聊了很久。“要不是那棵横在河面的树”,这句话在她们谈话中出现了好几次。话中惊悚的意味再次让我心惊。
临出门,陈老师扭回头,叮嘱我:“以后注意了。不能再去玩水了嘎?”
与大锑盆随水漂走相比,这是另一种更让人惊心的失落。它让我记忆终生。
之后的我,果然不敢再去玩水。不仅因为对校园后这条静静流淌的小河产生了敬畏之心,还因为每天放学后母亲都要叫我拉起裤腿,用她尖尖的指甲在我的大腿皮肤上划几下——据说游过泳的人,能划出明显的白痕。
不能玩水,就去小街临河的一间书铺看书。书铺的主人,一位双目明净的妇人,是母亲的朋友。向她交两分钱就可看一本连环画。没钱了,她也笑笑说:“你,想看就再看嘛。”然后,坐一旁用明净的眼睛安静地看着我。书屋真静,有时甚至可以听到房子后面子河流淌的声音。
梦醒,惊觉还有一种悄无声息的失落:我的童年,就是这样陪着小河静静地流走的。
子河,最后也无声地消逝了。这是一条全面、真实注解着“逝者如斯”的河流。
失落无处不在。子河桥东,曾有个子河村。历史上,洱海东岸的船只顺着大河来到黑龙桥,因为大河边迎着风口的缘故,大多只能泊于子河河岸小码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子河村。村里居住着来自洱海东岸的渔家、船家,在这里,可以买到洱海的黄壳鱼、螺蛳、螺黄、海菜、刺菱角、腌弓鱼、干虾米、乳扇、霉豆腐……月亮升起,总有三弦声在子河两岸琤琤响起,悠扬高昂的白族调子扯动人的心。如今,昔日景象,已随着子河的消逝而消逝。
失落无时不在。儿时家乡两个名医,就居于嵌有桥名的子河桥两端。桥头北的李品荣,精通伤寒一类疑难杂症。他家庭院,摆着一架铮铮发亮的铸铁船型碾槽,铸铁圆碾轮在碾槽来回碾动,空气里便弥漫着浓浓的药香;桥头南的舒子骧,长于儿科和妇科。伴随河水,他家铺子每天都会响起二胡声。《二泉映月》一响,一条街都安静下来,舒子骧的长子是二胡高手,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当了教授。子河故人,也随着子河的消逝而无处可寻。
失落无刻不在。“躲猫猫,抬耗耗,耗耗紧紧躲,老猫来抬啰。一张纸,二张纸,放到老猫抬耗子,抬得着,吃碗饭,抬不着,吃泡干狗屎。”一声尖利而快乐的怪叫,儿时伙伴——二眼睛、老蜗牛、大象、憨弟四散奔逃,或躲桥头,或躲树下,或躲房前,或躲屋后,忍住暗笑,等待老猫来逮。我的魂至今还躲在老地方,只是老猫已经不来。童年的欢乐,永远隐藏在遥远的梦中。
逝者既如斯,斯亦如逝者。子河的变化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洱河下游建梯级电站需要增大流量,西洱河加宽了河道、挖深了河床,建起蓄水节制闸,洱海从自然湖泊变成了发电调节水库。母河尚且不能再像从前长年奔涌,子河自然也瘦了、臭了,最后像一条干黄鳝,一头钻入了地下。
接下来,子河村、子河桥、下关一小,也相继随着子河消失了。被水泥覆盖的地面,喧闹声腾起,盖起子河菜场,后来又建起正阳时代广场、下关四中……
人可以对一条无名小溪寻幽探微,对眼皮底下一条河流却熟视无睹。这是子河消逝若干年后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突然想到的,这是一个令人惊悚的悖论。
继西洱河电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洱海东岸又历时七载,搞了引洱入宾工程,入不敷出的洱海,水位下降,爆发蓝藻。子河的母河,成为一条发电开闸才流动的河流。
一条失去流动的河流,给人的感觉是别扭的。以致到了后来,当听到要打造“桨声灯影里的西洱河”一类声音,便觉得不过是一种谵语。
就在这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进入下关四中新建成的校园。久违的消逝感再次袭来。因为,我感觉站立的地方,就是当年与母校明德小学一河之隔的下关一小操场。
遥想当年,月亮升起之时,这里可以看见一河明晃晃的月光,从子河桥下涌来,然后又分为南北两岔,把像个小岛的一小校园包围起来。
我试图找到岔河上两座小桥的位置,却印象模糊。逝者如斯,我再也不能沿着南岔子河的石桥走回童年,走回上小学时每天都要走过的文明街;更找不到北岔子河上的小桥走回青年,去汪家里与中学同学汪平、汪伟国聚会聊天。
一河月光,两座小桥,操场东面的石栏干、操场上的大理石纪念碑,身后当年隐藏在教学楼后面的弥陀寺,都消失于无形。
昔日的子河,是一条流着阳光、泻着月光、闪着星光、晃着灯光的河,却在眼皮底下消失了。
子河的消失,其实是洱海生态恶变的预警!
子河桥头一李一舒两位名医,望闻问切,辛劳一生,曾为无数生灵把脉。子河染疾,却无一人来为它把脉问诊。
其实,子河的病因很容易找到,可惜无人认真去找,或者找到了也无人敢说。
子河是永远消逝了。与子河一同流逝的,还有关于它的许多记忆。
据说,子河是为大河造桥而设的辅助工程。建桥时在上游截流凿河引水,使桥基河段裸露便于施工。子河的入水口曾在过几处西洱河桥与闸的上游河段,似乎也在印证这个说法。到了后来,建桥技术进步,再也不需截河引流时,子河也早已消逝于时间,被人们所遗忘。
依此说法,子河的开凿应该与黑龙桥的始建同时,至迟也应成于唐代南诏国王阁罗凤时期。
一条流淌了一千多年的河流,本来应该有一部流动的《子河传》,可惜世代生活于子河两岸的人把它丢失了。
夜渐凉,复入梦,“一小一小,像个小岛。”我又听到了儿时欢快的叫声,
一条河流可以消失,记忆之河则是不能断流的。活着并且记住——这应该是已经消逝的子河给我们的警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预而不警,只能后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