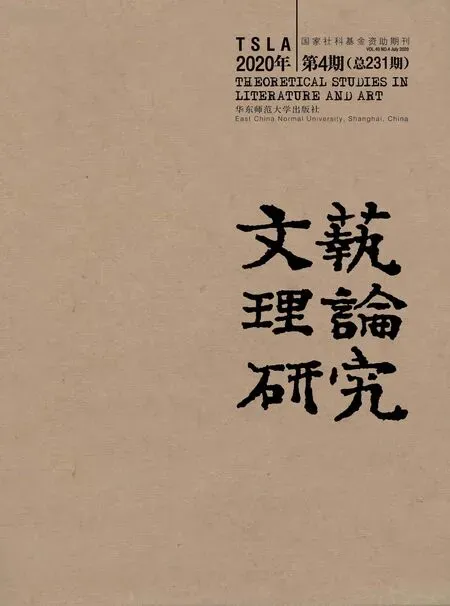论审美体验的非时间性
——以米歇尔·亨利对时间性概念的批判为线索
梁 灿
时间性是现当代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譬如,在现象学阵营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时间性视为审美体验显现自身的先验条件。若是如此,我们对审美体验的研究和考察似乎只能被局限在时间性概念的框架中。然而,当代著名的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对此颇有异议。因为根据不同类型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可知,时间性并非诸事物唯一的显现方式。在亨利看来,时间性只是外在事物特有的显现方式,而对于内在的审美体验,与之相匹配的显现方式是生命的自我显现,后者属于一种非时间性的显现方式。也就是说,审美体验不是在时间性的三个绽出维度(过去、现在和将来)中,而是在内在的生命中显现自身。如果我们把时间性的绽出结构强加于审美体验,只会使其失去自身活生生的实在。比如,当我们去回忆昨天的牙痛时,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的牙痛了。只有在真正的牙痛体验中,我们才能把握到牙痛的活生生的实在。牙痛对自身的体验就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自我显现。
亨利对时间性概念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现象学自身突破时间性概念的束缚,推动生命现象学的构建,从而为现象学在美学和神学等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它有助于丰富当代西方美学的理论内涵,其中,亨利所提出的生命的自我感发概念,或许可以为西方美学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理论维度。
一、 现象学悬置: 世界和时间性
亨利的美学思想奠基于对两种显现方式的严格区分,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的名著《看见不可见者——论康定斯基》(下文简称《看见不可见者》)中发现。在该书的第一章,亨利开宗明义地以康定斯基的著名论断“一切现象都能够以两种方式被经验”(Henry,SeeingtheInvisible5)来展开他的美学思想之旅。亨利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两种经验事物的方式就是事物的两种显现方式: 首先,它在生命的自我显现中显现自身;其次,它在世界的对象显现中展开自身。尤需注意的是,这两种显现方式在本体论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为事物的实在不存在于世界中,而存在于生命中。若是忽略生命的显现,把事物仅仅归结为世界的对象显现,我们就会错失事物活生生的实在。
为什么事物会具有两种显现方式?康定斯基的绘画理论让亨利受到了很大启发。康定斯基以绘画的颜色为例指出,颜色虽然可以在世界中显现为物质性的属性,但它首先却是一种主观的印象。在一篇名为《艺术和生命现象学》的访谈中,亨利对康定斯基的这一洞见大加赞赏,认为这一洞见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不谋而合。亨利指出:“在胡塞尔那里,颜色在成为一个环节或物体的一种性质、一种‘意向相关项的颜色’之前,就是纯粹的印象、一种意识活动,类似于在笛卡尔梦里的恐惧。”(Henry,Phénoménologie290)此处提及的颜色印象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质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238)、感性材料,它们在被赋义为外在事物的感性性质之前首先是一种纯粹内在的印象。亨利对此有精彩的论证,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子: 当我们把手放在一块塑料上时,手会感到一股凉意,但我们不能说“这块塑料是凉的”,而应该说“我感到了凉爽”。因为凉意首先是一种主观的感觉,然后我们才把它投射在手和塑料之上。顺着亨利的思路,以疼痛为例或许更加直观明了。当我们的手不小心被炉火灼伤而产生痛感时,我们不能说“炉火是痛的”。因为这种痛感是人们的一种内在感觉,把它归结为炉火的某种属性显然是荒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指出:“红色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绝对主观的,最初是不可见的。源初的颜色是不可见的,但它们通过一种投射的过程扩展到事物身上。”(Phénoménologie290)
内在的审美体验只有在生命的自我感发中,才能如其所是地展现自身。这是亨利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为了说明这一点,亨利首先指出为什么世界的对象显现无法通达审美体验,即为什么审美体验一旦在世界的视域中显现就会失去自身本真的实在。然后,他进一步论述了世界与时间性的关系,以便阐明为什么时间性无法如其所是地把握审美体验。
亨利的一生著述颇丰,但有一个观点却贯穿始终: 古希腊以降,整个西方哲学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独断的思维预设,即预设事物只有一种显现方式(Henry,TheEssence439;MaterialPhenomenology20;IAm14)。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种显现方式被冠以不同的称号,比如康德哲学中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先天认识形式的十二范畴、胡塞尔哲学中具有意向性结构的意识,以及海德格尔哲学中具有在世结构的此在。不过,不管被冠以什么样的名称,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显现特征,即事物凭借某种异于自身的视域显现为某种可见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归属于世界的对象显现。亨利称西方哲学的这种思维预设为“本体论上的一元论”(TheEssence74)。这种思维预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遗忘了一种更为根本的、不可见的显现方式,即遗忘了生命。
现象学所谈论的世界并非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而是事物显现自身的一种先验条件。根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分析,“现象”一词在古希腊那里意味着“能够进入光明中的东西”(海德格尔34)。因此,光成为了现象显现的先验条件。不难发现,使事物显现为现象的光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光线,而是“世界之光”。在西方哲学中,世界概念一开始并非指称事物显现自身的先验条件,而是仅仅指称诸事物的集合。只有当意识哲学出现后,世界的现象学意义才逐渐显露出来——因为事物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其显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显现条件。对于意识而言,显现就是表象,而表象等同于“把……置于面前”,即置于自身的外面(outside)。这个外面本身就是世界(IAm15)。也就是说,意识之所以能够显现事物,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一个世界的显现结构。在意识的显现中,事物总是向着某个意识显现自身,因为一块石头无法在另一块石头面前显现自身。通过对意识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追问,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揭示世界特有的显现结构。“向某个意识显现”意味着世界之显现具有“一个二元结构”(Zahavi223),而这个“二元结构”意味着世界(显现)与事物(显现者)之间的源初分离。不过,世界与事物之间的分离不能被理解为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因为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属于存在者层次上的两个存在者之间的对立,而世界与事物之间的分离则属于存在论上的显现条件和存在者层次上的显现者之间的对立。
在亨利看来,事物在世界中显现自身以失去自身活生生的实在为代价。因为在世界显现的“二元结构”中,事物不是以自身的力量显现自身,而是依赖于一种异于自身的外在力量。通过对时间性概念的讨论,我们将会对世界所显现的先天缺陷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我是真理——朝向一种基督教哲学》(下文简称《我是真理》)一书中,亨利强调我们不能把世界理解为“某种先于事物的惰性的和现成的环境”(IAm16),即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空间关系。那么,世界究竟是什么?在该书的第一章,亨利在批判世界真理时指出:“时间①和世界是同一的,它们指称‘外在’不断自我外在化的单一过程。”(IAm17)因此,世界的“外在化”就是时间性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绽出过程。不过,这三个绽出维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从将来涌向现在,并持续地流向过去,它们一起构成了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之流。
通过对时间性绽出结构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对象显现对事物自身之实在的破坏。亨利指出:“这种置于自身的外面,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把事物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就好像在这种转换中,它仍然类似于自身,至多是获得了一种显现自身的新属性。”(IAm18)实际上,在世界的对象化显现中,事物进入显现中就是置于自身活生生的实在的外面,即事物与有血有肉的自身之实在相分离,从而被剥夺了自身的实在。譬如,在上述颜色的例子中,当我们把主观的红色印象投射到外在事物的身上时,活生生的主观印象就变成了事物的某种属性。由于事物在世界中显现就是与自身活生生的实在相分离,故而失去自身之实在的事物只能寄希望于在显现中获得新的实在。不过,时间性却无法赋予事物任何实在。亨利指出:“时间流逝,以一种滑向虚无的方式溜走。”(IAm18)一方面,事物自身的实在在显现的过程中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时间性的本质又是虚无,无法赋予事物新的实在,所以事物在时间性中只能以一种图像(image)的方式显现自身。
为什么事物在时间视域中只能显现为一种图像,即“空的显相”?这由时间性的内在矛盾决定。对于胡塞尔,现在(the now)的源初意识能够直接把握事物源初的实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现在意识被理解为一种感知。“感知,从胡塞尔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表示事物在其自身的存在和‘血与肉’之中被给予。”(MaterialPhenomenology25)然而,胡塞尔却又承认,“没有任何具体的意识之流的部分能够使之显现为非流动的”,时间的流动性使得现在成为了一个无限可分的“理想界限”(26)。如果现在意识是一个“理想界限”,这将意味着它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亨利看来,这便与胡塞尔把现在的源初意识理解为一种“在血与肉之中”给予事物源初实在的感知相冲突了(26)。因为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现在意识显然无法通达事物具体的、活生生的源初实在。在源初的感知中,现在意识从来没有如其所是地显现事物自身,而是从一开始就使事物远离其源初的实在,最后使之只能在滞留中获得所谓的“实在”。不过,事物在滞留中所获得的实在并不是它源初的实在。在作为现在的一个变式(modification)的滞留中,事物只能获得一种图像式的存在,而图像式的存在意味着事物源初实在的丢失。在图像中,事物的显现就是不显(IAm19)。例如,一旦牙痛在时间性中绽出,它就不是原来让人死去活来的牙痛了。刚刚发生的体验不断地滑向过去,我们只能意指它,而无法再次体验它。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审美体验不可能在时间性中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如果我们把时间性的绽出结构强行置于审美体验身上,只会使之失去源初的实在。一方面,这是因为时间性的绽出结构使得审美体验必须出离自身,从而使其失去自身源初的实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间性是一种流逝意识,它一刻不停地滑向虚无,而无法赋予事物新的实在。因此,在时间性视域中,审美体验只能以图像的形式而无法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
二、 审美体验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
为什么审美体验只能在生命中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因为审美体验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在亨利看来,审美体验并非外在于生命,而是构成了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什么说审美体验构成了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一个环节?这与生命的本质呈现在审美体验中有关。
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亨利在《看见不可见者》中指出:“它(生命的本质)不仅仅是体验自身,而且它作为自身的直接结果,还是自我的生长。在生命的方式中,体验自身就是进入自身,占据自身的存在,生长自身,被‘更多’的东西所感发,此处,‘更多’的东西指称‘更多的自身’。这种更多的东西不是某种观看或定量测量的对象。作为自我生长和对自身存在的体验,它是一种享受自身的方式;它是享乐。因为这个原因,生命是一种运动: 它是从受苦到享乐的永恒运动。”(SeeingtheInvisible122)也就是说,生命的本质除了体验自身以外,还包括生长自身。生命不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是一种永恒的运动。没有人会一直处于悲伤或高兴的状态中,因为生命总是在体验自身的同时转化自身,以及生长自身。
那么,生命是如何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呢?——通过审美体验。因为审美体验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即作为生命“更多的自身”。在《野蛮》一书中,亨利指出:“作为一种实践,审美(体验)指称感受性生命的一种形态,[……]艺术家或艺术爱好者的具体活动仅仅是感受性生命的一种实现,即生命为了自身和依赖自身的运用,即生命的自我发展、自我充实,从而包括它的生长。”(Henry,Barbarism28)所谓审美体验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是指审美体验构成了生命转化和生长自身的过程,以及构成了生命转化和生长自身的方式。通过审美体验,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和实现。比如,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忽闻琵琶女的演奏,内心的情感体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曲终时不禁泪湿青衫,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就是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实现过程。
不过,审美体验不是通过向我们展现外在的声音或景象来满足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欲望。因为审美体验不是外在事物刺激感官的产物,而是外在事物显现自身的先验条件。在《材料现象学》中,亨利指出,当我们观看某个对象之前,“我们不应该说‘我们看见’,而应该像笛卡尔一样说:‘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观看。’这种自我感发是一种源初的现象性,是源初的作为一种自我给予的给予性。例如,观看自我给予它自身”(MaterialPhenomenology81)。也就是说,只有“观看”事先感受到观看自身,即事先给予自身,我们才能看见某物。例如,当我们在美术馆欣赏展览时,“观看”必须首先感受观看自身,即只有在“观看”这个行为率先发生之后,我们才能看见外在的画像。如果没有“观看”首先感受到观看自身,那么无论一幅画多么绚丽,它也无法激起我们心中的涟漪。这里所说的“观看”对自身的感受或体验就是生命的一种自我感受,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体验。因此,审美体验不是外在事物因果刺激的产物,而是外在事物显现自身的先验条件。
在亨利看来,审美体验通过返回自身来满足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欲望。在《看见不可见者》中,他以绘画为例指出:“绘画并没有向人们展现他们不曾见过的东西,如人们在幼稚的成年人杂志的插图中看到月球的表面。它通过把视觉引向自身来展现。”(SeeingtheInvisible122)这里所说的视觉指称“观看”的能力,而这种“观看”能力首先指称感受自身和体验自身的能力。这种感受自身和体验自身的能力就是审美体验。为什么审美体验能够通过返回自身来满足生命转化自身和生长自身的欲望呢?因为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审美体验在本质上就是生命的一种自我感发(auto-affection, self-affection),而自我感发指称审美体验与体验内容之间的绝对同一。亨利指出:“感受自身以这样一种方式接收自身,并且体验自身。即,这种接收自身、体验自身,以及被自身所感发的能力,构成了在自身中被感发的东西,这就是使它成为感受的东西。”(TheEssence464)在这种绝对的同一中,审美体验不是外在事物刺激人体感官的结果,而是被自身感发之物。总而言之,审美体验就是一种自我体验。
亨利一再强调,审美体验不能被视为某种可以对象化显现的对象。如他在《论野蛮》一书中指出:“这种‘感受’和‘体验’,与诸对象或某个对象没有关系,不具有某个世界或世界的绽出。”(Barbarism14)因为审美体验从来不会在意向性中得到充实。当我们试图去打量审美体验时,它并不会作为一个对象在感知②中被充实。在感知中,“我们仅仅意指生命,而无法亲自给予它”(IAm41)。我们可以看见对方脸上洋溢的笑容,但却无法看见笑容背后所隐藏的情感体验是喜还是悲。一旦审美体验进入世界的显现结构,并外化为可见的对象,它就不再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了。
不过,审美体验的不可见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它无法把自身交付于感知,无法在世界的真理中变得可见”(IAm41)。在亨利看来,不可见的审美体验只能在不可见的生命中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审美体验的显现就是生命的自我显现。
与世界一样,生命不是某种存在者,而是事物显现自身的先验条件。有所不同的是,生命是一种源初的显现。在《我是真理》中,亨利指出:“生命指称一种纯粹的显现,这种显现不可被还原为世界的显现,这是一种源初的揭示,它不是揭示它物,也不依赖于它物。它是一种对自身的揭示,一种绝对的自我揭示,这就是生命自身。”(IAm34)生命作为一种源初的显现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生命不是凭借某种异于自身的视域显现为可见的现象的,而是纯粹依赖于自身的显现力量来显现自身。就像牙痛来袭,我们不是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痛苦的表情才发现牙痛的,也不是通过用手或舌头的触摸才感知到牙痛的存在,而是牙痛直接在自身中显现自身。其次,生命在自身中所显现的正是不可见的生命自身。在牙痛中,牙痛显现自身为牙痛,这是生命的一种自我感受或自我体验。一方面,作为显现者,在牙痛中被揭示的正是牙痛本身。另一方面,作为显现,使牙痛得以被揭示的正是牙痛本身,它是自身显现的先验条件。因此,显现与显现者在生命中达到了完全的同一,不存在任何的分离和绽出。
三、 可能的质疑与回应
当亨利把生命视为一种“从受苦到享乐的永恒运动”时,难免会有人反诘说: 难道这不是正好表明了生命是一种不断流变的时间现象吗?亨利承认生命并非死水一潭。如他在《材料现象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生命的自我感发不是类似于在普遍的时间之流中不变的实体,也不类似于河床中的石头;它是绝对的历史性,是生命面向自身的永恒到来。”(MaterialPhenomenology39)在《我是真理》中,亨利更加明确地指出:“‘体验自身’是一个过程,在其中,被体验的东西总是被当作新的体验。”(IAm56)然而,并非一切运动都是在时间性中展开的运动。在亨利看来,生命的运动是一种源初的运动,它属于生命内在的自我感发,而一切在时间性中展开的运动都要以之为最初的根源。也就是说,虽然生命并非一成不变,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生命是一种在时间性视域中绽出的现象。
首先,在时间性的绽出结构中,事物的显现以失去自身的实在为代价,但生命的自我显现却不是以失去自身的实在为代价。只有在生命的自我显现中,我们才能把握事物活生生的实在,这是亨利的生命现象学最终给予我们的结论。根据本文第一节关于颜色的讨论可知,生命是一种最为源初的揭示,与时间性的图像式显现相比,它不但不会失去自身的实在,而且“一切可能的实在都诞生于生命的自我揭示”(IAm30)。
其次,生命作为一种永不止息的自我运动,它不是一种空的形式。在时间性的绽出视域中,一切事物都变动不居,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不过,这个变化本身是一种空的形式,一切事物在其中注定滑向虚无。相比而言,生命永不止息地体验自身却不是一种空的不变形式,在体验自身的过程中,我们的自我产生了。当我们在欣赏音乐时,一种愉悦感油然而生。这种愉悦感无疑不是别人的,而只能是属于自我的愉悦感。在时间性的绽出感知中,只有他物被给予,自我却不曾出现。即使我们对自身内在的意识活动进行感知,内在意识也只是作为自身中的他者而被给予,但自我却始终阙如。只有当生命在感受自身和体验自身时,自我才会被给予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在《材料现象学》中指出:“源初的自我性(ipseity)诞生于绝对主体性的自我体验中。”(MaterialPhenomenology53)
最后,生命的显现是一种自我显现,它不需要借助任何异于自身的显现力量。如果生命是一种时间性的现象,那么这无异于说生命的显现依赖于时间性的显现作用。但是,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不是时间性为生命奠基,而是生命的自我显现为时间性奠基。因为时间性本身是不可见的,它无法在可见的视域中绽出,即无法依赖自身的显现力量来显现自身。在亨利看来,不可见的时间性只能在不可见的生命中显现自身。
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质疑有待澄清。如果审美体验是非时间性的,那么在没有内时间意识的滞留和前摄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倾听音乐?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曾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倾听音乐时,人们听到的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音符,而是一段完整的旋律。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一段完整的旋律,是因为每个音符在当下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就消失,它仍然以滞留的方式留存在感知意识中。胡塞尔指出:“在这个回坠过程中,我还‘持留住’它,还在一种‘滞留’中拥有它。”(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62)此外,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下一个时间点出现的音符看作是当前旋律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东西,是因为感知意识中的前摄作用,后者指称意识行为的“期待意向,它们的充实会导向当下”(96)。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我们在音乐欣赏中听到的是什么?换言之,在音乐的审美体验中,我们体验到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我们的审美体验中显现出来?根据亨利的美学思想,在倾听音乐时,我们听到的绝不是外在的音符,无论它是某个独立的音符,还是连成一段的旋律。与其他艺术类型一样,音乐也具有外在的要素,例如,某种由乐器振动空气而发出的物理声音。亨利援引叔本华的理论说,外在的要素仅仅是意志的表象,真正的现象是内在的实在。亨利指出:“这种不可对象化的、内在的、隐匿的实在,叔本华称之为意志,而意志仅仅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名称。”(SeeingtheInvisible113)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听到外在的要素(无论它是独立的音符,还是一段完整的旋律),而在于“倾听”内在的实在,即活生生的生命。换言之,审美体验的真正对象不是外在的乐器声,而是内在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荷兰著名的现象学家韦尔滕(Ruud Welten)指出:“艺术不是表象,而是揭示生命最终之所是的内在颤动。因此,亨利说艺术是一种‘生命的强化’。”(Welten275)
在时间性的绽出结构中,我们只能把握外在的乐器声,而无法把握内在的生命。因为在时间性中我们只能意向某物,而不能体验它。比如,当一名钢琴调音师专注于工作时,他听到的是乐器发出的器械声。这并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审美体验,他甚至很可能因为长时间地工作而萌生厌烦情绪。然而,当他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坐在音乐厅时,他听到的却是悦耳的音乐,审美的愉悦感随之不断涌现。两者的区别就在于: 作为钢琴调音师,他听到的是外在的乐器声;而作为音乐爱好者,他忘记了外在的声音,而专注于“倾听”内在的音乐。在亨利眼里,内在的音乐就是“倾听”本身,它的显现先于时间性的三维绽出,因为“倾听”本身属于生命的自我感发,它是一切经验发生的先验条件。只有“倾听”首先发生,我们才能听到外在的声音。
总而言之,在“倾听”音乐时,我们听到的不是外在的音符,而是内在的音乐。因此,“倾听”音乐的前提条件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内时间意识的滞留和前摄,而是生命的自我感发。在每一个活生生的“倾听”把自身投射为外在的音符之前,它首先“倾听”自身,而这个“倾听”自身才是真正的音乐。
结 语
一方面,生命是一种永不止息的自我运动,另一方面,生命的自我运动却不在时间性中展开自身,这意味着生命与一切可能的记忆无关。一种非记忆的生命在本质上注定了对自身的遗忘。不仅如此,当西方哲学被“本体论上的一元论”思维主导时,它对生命的遗忘进一步地加剧了。世间万物不再在生命中被拥抱和感受,而变成了被人们恣意打量的对象,在亨利看来,这就是当今时代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主要根源。
在生命被遗忘的时代背景下,亨利为艺术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回到生命之中。在亨利看来,艺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存在维度,即生命的维度,“艺术实际上使我们返回到一种源初的显现中”(Phénoménologie284)。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感受,即它由自身而非世界触发。不过,如果一切感知、想象和概念等思维都是由世界触发,生命又如何回到自身呢?在《看见不可见者》的导言中,亨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艺术不是通过让我们看见某物,或者通过向我们表象某物的最终本质来实现;相反,通过艺术的最初形式,我们与之同一。”(SeeingtheInvisible3—4)亨利在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中看到了通过艺术让人们返回生命的可能性。因为“抽象绘画”如此启示我们: 绘画的本质不在于模仿外在的可见世界,而在于表达内在的不可见生命,在于唤醒人们对内在生命的感受和体验。
让我们以绘画为例来说明为什么艺术能够揭示不可见的生命。一般来说,绘画由点、线、面和颜色等可见的要素构成。那么,为什么绘画能够以一些可见的要素来表达不可见的生命?在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对两种显现方式的区分中。根据一切现象都具有两种显现方式的原则,康定斯基认为绘画的各种组成要素在本质上首先是不可见的,它们活生生的实在不是存在于外在的世界中。西方传统的绘画理论倾向于把绘画理解为对外在事物的模仿,这样就错失了绘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如在具象主义绘画中,我们看见的是围巾的红色或玫瑰的红色,而不是红色本身。只有当绘画与外在世界的一切关联被切断时,我们才能“看见”纯粹的红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尤其推崇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在抽象绘画中,一切绘画的要素都不再指向外在的事物,因而我们“看见”的是纯粹的红色、纯粹的线条。而纯粹的红色和线条,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印象,就是内在的生命。这就是艺术之所以能够揭示不可见的生命的奥秘所在: 切断与外在世界的一切关联,以回到活生生的生命之中。
在亨利看来,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不但规定了一切绘画的本质,而且还规定了一切艺术的本质。因此,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其本质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亨利对时间性概念的批判,以及对艺术本质的洞见,让人耳目一新,或许会为西方美学的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
注释[Notes]
① 现象学谈论的时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可以量化和无限分割的客观时间,而是指称事物的显现方式。下文将以“时间性”一词来专门指称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以示区别。
② 在亨利的思想中,感知(perception)与感受(feelin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亨利主要是在胡塞尔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感知一词,即感知表示一种意向性活动,它只能把握在意向性结构中绽出的事物。与感知不同,亨利把感受定义为一种非意向性的活动,表示内在生命的一种自我体验。在这种自我体验中,被体验的正是生命本身。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Heidegger, Martin.Beingand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Henry, Michel.Barbarism. Trans. Scott Davison. London: Continuum, 2012.
- - -.IAmtheTruth:TowardaPhilosophyofChristianity.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MaterialPhenomenology. Trans. Scott Davis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8.
- - -.PhénoménologiedelavieⅢ.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 - -.SeeingtheInvisible:OnKandinsky. Trans. Scott Davison. London: Continuum, 2009.
- - -.TheEssenceofManifestation. Trans. Girard Btzkor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3.
埃德蒙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年。
[Husserl, Edmund.IdeasforaPurePhenomenology.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2.]
——: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
[- - -.OnthePhenomenologyoftheConsciousnessofInternalTime. Trans. Ni Liang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Welten, Ruud. “What Do We Hear When We Hear Music? A Radical Phenomenology of Music.”StudiaPhaenomenologica9(2009): 269—86.
Zahavi, Dan. “Michel Henr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Invisible.”ContinentalPhilosophyReview32.3(1999): 223—40.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