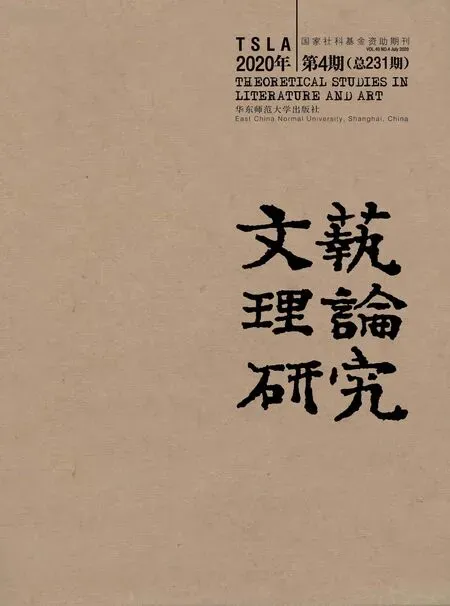略论当代“大众”话语的生成机制
罗崇宏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革命语境中的工农兵大众话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后革命”时代的娱乐大众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大众”话语的这种流变首先源自时代语境的转换,即从革命向后革命转移。此外,大众话语的变迁也与言说主体的更替有关,也就是从革命领袖向人文知识分子转变。这些怀抱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去审视当代大众,并以文化作为精英与大众之间划分的标准。于是,当代“大众”就被视为类似于西方“庸众”(mass)式的消费大众。
不过,在当代文化的斗争场域中,并非只有人文知识分子的大众批判话语,这当中自始自终都存在着大众分析话语。也即一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是简单地对当代大众进行价值批判,而是更加学理性地走进大众,并试图从当代大众差异性的言行中寻找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与内在机理。显然,在以人文主义、后革命为中心的言说语境中,中国当代的大众话语移用了源自西方,尤其是英国的以“mass”和“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理论视角。本文就沿着这种理论视角,展开对当代大众话语生成机制的研究。
一、 当代“大众”言说语境
(一) 人文主义文化语境
大众话语的当代转型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人文主义”(humanism)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可以说,当代知识分子正是秉持人文精神的标尺对当代大众进行文化启蒙,继而对随后出现的消费大众进行文化批判的。
当代人文主义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上海文学》上刊登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驳斥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其主要表现是把文艺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提到人性、人道主义等用语,但它旨在打破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讨论揭开了序幕。同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走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受过19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教育”(季红真56)。正因为如此,当这些知识分子解除了精神枷锁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人文主义密切相关的人道主义(章可125)讨论。正如学者陶东风所说:“‘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几乎是当时的相关文章中出现得最多的术语,且这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自由创造性,而人道主义则是对于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肯定)。”(陶东风,《陶东风学术》149—50)因此,正是“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正好昭示了80年代的时代精神”: 重建人文精神的王国(樊星104)。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世纪末情绪、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大众文化的繁荣,使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等以消费为中心的批判话语甚嚣尘上。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39)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批判意识,促使人文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人文精神重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这一切又以始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晓明64)最为集中。这场人文精神讨论首先关注人文精神的概念问题,对此学者袁进作了如下解释:
我理解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袁进73)
袁进从存在的层面对人文精神进行哲学式思考,并把它视为终极关怀。这既是对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对人的禁锢的反思,同时也流露出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这就使得多数知识分子更多地感受到大众消费时代人文精神所面临的危机,也促使他们对人文精神/文化重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因为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是基于对当代大众/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救赎的心态而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而触发这次讨论的直接原因则是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此,陶东风对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
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化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陶东风,《文学理论》169)
陶东风认为这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截然不同,也即文艺复兴的方向是走向文化的世俗化,而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则是拒斥世俗化。
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人文知识分子秉持人文精神的批判标准,对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进行量度,很自然地把社会文化划分为精英与大众相对立的二元文化模式,由此引起90年代的大众批判话语,以及此后人文知识分子中另一部分人针对大众批判话语的反思。而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一贯的精英立场,也为本文后面论及的以“mass”为中心的大众批判话语提供了言说语境。
(二) 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语境转换
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大众话语基本上是围绕着革命这个主题进行言说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推崇、被颂扬的大众形象表征着中国大众话语/理论的主要特色。到了80年代,这个被一些学者称为后革命时代的新时期,社会的主流话语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因而此时“无论是政府、知识界还是民间,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陶东风,“后革命时代”7)。而告别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对阶级的讨论与批判,这同时也是80年代“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取消阶级论最初在70年代末的高考招生中已初露端倪,随后又在理论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大讨论”“真理阶级性的讨论”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大讨论在客观上促使中国文化发生转型,也即“从一元的文化向多元的文化转变”(周宪主编44)。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阶级论的取消实质上可视为对大众的重新定义。伴随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大众话语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当代大众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许纪霖367)。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知识分子的禁锢也开始松动,使得80年代出现了类似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即所谓的“从共产主义的超越世界回到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理性”(许纪霖367)。
到了80年代中期,“文化热”或者“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使得针对大众话语的反思与批判有了与五四不同的文化启蒙任务。也就是说,与五四对臣民、国民话语的思考不同,新启蒙运动的新就在于它除了关注臣民、国民话语之外,更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农兵”群众话语。因为在工农兵话语时代,革命成为时代的真正主体,个人只是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而80年代所关注的是“那个超越了具体种族、民族与国家界限的抽象的‘人’,启蒙追求的也就是一种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现代性”(许纪霖367)。因此这场新启蒙运动也是对国民性的再反思,并非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当时的历史境况,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徐友渔252)。
进入90年代,以主流意识、启蒙为中心的文化渐次失去了其昔日的主导地位。个中原因首先可归结为社会的全面转型,诸如作为社会前进主要推动力的市场经济得以全面发展,这就使得之前基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而建立的绝对权威也被市场所消解。在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言说语境中,中国的文化模式也逐渐由启蒙向消费转移。同时,这种言说语境的变迁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像王尧在《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中所说:
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的落差是巨大的,几乎从现代化设计的参与者和大众精神生活导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而包括一部分文学读者在内的大众,则越来越沉入世俗化生活中。(王尧70)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80年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被挤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启蒙话语的受挫并不全是“阐释能力的丧失”,“而是肇因于一场重大政治风波后话语环境和格局的巨变”(徐友渔364)。因此,如果说80年代的大众言说偏重个体的终极关怀,那么90年代则是从大的社会层面关注大众的生存。
可见,在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尽管启蒙又一次被提上知识分子的议事日程,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在急剧变幻的时代注定命运多舛。如果说第一次启蒙话语的中断是要让位于急切的革命任务,那么90年代启蒙的受挫则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不无关系。同时,由于后革命告别了革命时代的宏大叙事,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接受提供了一种可能,也即为本文后面的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话语分析提供了言说语境。
二、 以“mass”为中心的“大众”批判
当代大众批判话语可视为以“mass”为中心的言说体系。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mass”一般指的是被动的、含有批判意义的大众概念。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梳理了“mass”在西方语境中语义流变的大致脉络,它常常被用于描述消极的、卑下的受众,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乌合之众”(威廉斯327—35)。而在当代中国,重新取得大众话语权的人文知识分子,重拾自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以“化大众”的精英立场审视当代大众/大众文化,并把他们命名为“某某大众”。这种大众言说消解了革命年代的阶级意识,代之而起的是以文化的高下作为分类标准的批判话语。
(一) 以“消费”为中心的当代“大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社会逐渐迈进大众消费时代。那些身处消费时代的大众不仅仅关注商品的物的实用性,更关注其符号的象征意义。在这种由消费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孟繁华,“小写的文化”36),并且其“表面由巨大的、无差别的大众构成,阶级和种族的身份正逐渐地淡薄,大众生活在由符号编码主宰的世界里,商品成为个人品位和阶层归属的表征,大众出于对具有社会区分价值的商品符号的认可,加入到个人对表明身份认同和阶层归属的商品的无意识追逐中”(王迎新82)。
不过,与革命语境中的阶级大众不同,消费时代的大众模糊了此前的阶级属性,这使得革命时代的阶级话语渐次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继而新的社会阶层——消费大众的生成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新的社会阶层不仅打乱了既有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农民等),同时也是对原有阶层进行重新整合的结果。于是,一些学者将消费大众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的中产阶级等同起来,以突出大众的消费性。正如陆扬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所说,“后现代的‘大众’已每每具有中产阶级的口味”,这些大众与“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所构想的大众文化意义上那个被动的、社会下层的‘大众’,未必是同一个概念了”(陆扬 王毅290)。
实际上,在商品化时代几乎所有人(包括精英)都可能成为消费大众,其区别只在于消费能力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以消费为主导的当代社会,身处某个特定场域中的人们都有可能会褪变为消费大众中的一分子。同时,消费大众的出现也使得符号消费成为当代大众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新标志,从而改变了大众在知识分子/言说者心中既有的形象,那个“我们曾经崇拜、迷信的‘大众’已经散去,时代的转型使那些可以整体动员的‘大众’已经变成今日悠闲的消费者”(孟繁华,《新世纪文学》405)。这样一来,以启蒙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吸收了西方的大众理论资源,尤其是“masses”理论之后,在面对消费语境中寄生于物质外壳上蠕蠕爬行的“大众”时,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些“大众”非理性的“消费”以及膨胀的欲望。这种消费不仅体现在物的消费上,而且人们的消费逻辑已经从对物的痴迷转到了对物的崇拜,也即“从对自然偶像的崇拜转到对商品偶像的崇拜,复又转到对符号偶像的崇拜”(高岭95)。可见,人文知识分子常常从消极的、非理性的角度强调当代大众的消费性,由此而形成针对这些大众的批判话语。而这种批判话语的形成,又往往是建立在“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等理论基础之上的。
首先,当代消费大众与大众社会概念密切相关。大众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最早出现于西方,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邹广文主编37—38),大众社会概念的形成与工业化、城市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当代的消费大众可看作基于大众社会的话语建构:
“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这个词,并非通常说的“群众”的同义词,而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专门术语,它指的是大众社会产生后人在社会中地位与特性的一些本质变化。(张汝伦16)
张汝伦将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与大众社会概念联系起来,凸显其哲学与社会学意义。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民大众/群众话语是生成于革命、阶级等言说语境之中的,而当代的消费大众则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大众社会中生成的。同时,由大众社会中的大众(mass)用语可以看出,这个语式中的大众大体被视为一种无知的群体,也就是以知识贵族自居的知识分子站在精英的文化立场,戴着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大众,因而是从消极、负面的意义上使用大众这个较为笼统的概念的。最典型的是把大众视为一个临时的、同质性的概念,认为他们“始终处于集中和流动的动态过程中,没有固定的人员组成,也不会有明显的人格特征,是一种‘无脸的存在’”(郗彩红92)。如学者邹广文就这样给“大众”下定义:
所谓大众,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来说,特指生活于城市之中处于平均状态的人群。(邹广文主编40)
显然,这种大众定义是把大众视为大众社会的产物,并且是有同而无异的人群。不过也有人从社会整体性的角度对大众有近乎与之相反的描述,如潘知常就认为“‘大众’就是只有异,没有同。对于异质性的重视,使得‘大众’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人心各如其面的零散的群体。它代表着在当代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公共群体,但又是无名的存在;是最实在的群体,但又是查无此人的存在”(潘知常 林玮258)。由此,潘知常也给“大众”下了个定义:
所谓“大众”,就是失去了抽象本质支撑的零散的“我”。(潘知常 林玮258)
可见,如果把当代大众与革命语境中的人民大众/群众作对比,可以看到之前的大众更强调其政治性与阶级性,其明确的话语指向是为工农兵服务等宏大叙事。而当代大众更多的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私人化叙事,“它主要以社会生活及文化消费方式为标准,并不考虑具体的政治立场”(邹广文主编41)。对此,日本学者岩间一弘认为消费大众的生成是基于城市这个消费语境:
大众,是指愿与众人平起平坐的、行为层次与众人相同的人们,它诞生于机制工业和大众媒体发达的,能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的近代城市。(岩间一弘410)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欲望迅速膨胀的场域——城市成为大众社会的典型代表。在这块易于滋生消费欲望的土壤中,消费大众的生成在所难免。
其次,当代消费大众的生成与大众文化关系密切。可以说,大众与大众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关系。如学者旷新年认为当代的消费大众是由大众文化构筑而成的概念:
随着大众文化的概念的出现,“大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扭转和变化,“大众”这一历史主语已经转变成为白领大众。(旷新年12)
在当代,人们几乎把消费大众视为大众文化的产物,因为大众文化首先考虑的是大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消费大众也被视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受众”(邹广文主编42),甚至是大众文化的“隐含读者”,并被置入大众文化的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就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而言,大众既有主动性又有被动性。在主动性方面,“大众的文化需求引导着大众文化的生产”(45);而大众的被动性则体现在,作为“读者性文本”的大众文化以接触的方式强化、控制大众的趣味,从而“塑造”出缺乏创造性的消费大众(4—52)。
(二) 与“精英”对立的“大众”话语
由上述可知,在90年代的消费语境中,生成了众生喧哗式的消费大众,这就使得人文知识分子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是文化的启蒙者和主流价值的引导者。与80年代的启蒙者相比,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们“几乎是从现代化设计的参与者和大众精神生活导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王尧70)。这些“精英”曾经为现代化改革大声疾呼,到了90年代,“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大量知识分子产生严重的受挫感”(高瑞泉15)。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境遇的变迁也改变了他们的大众言说方式,也即从启蒙大众变为批判大众。那种80年代启蒙式的“‘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王岳川352)。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常常看到,“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50、6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那些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莱坞明星道格拉斯、黛米·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马拉多纳”(尹鸿76—77)。很显然,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眼里,那些流行的、娱乐化、商业化的“大众”的文化,是与他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格格不入的。而文化与“大众”之间的影响具有相互性,因为“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霍尔编1),也就是说大众编织了大众文化,而大众本身也成为“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5)。
由此,当人文知识分子将当代流行性的、娱乐性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视为与精英文化对立的、比较“低”层次的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把大众本身纳入低层次的群体之中。也就是说,人文知识分子以精英立场看待大众,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待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 将大众文化视为消费性、娱乐性、缺乏深度的低俗文化。而当代大众又总是与大众文化相伴而生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几乎决定了如何看待当代大众。
这样一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大众言说,常常是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开始的: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尹鸿77)
显然,人文知识分子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把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文化视为文化工业生产的低级产品,而消费这些产品的大众也一同被降为低级人群。它们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逻辑: 文化工业生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又生产了大众。这样一来,大众就自然成为了文化工业的产品。如张汝伦认为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模式,使得大众变成僵化、标准化和同一化的“mass”,而促使“mass”形成的最直接的动力则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性。也就是说,在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之中,大众本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在日趋标准化和同一性的社会生活中“个人”逐渐成为“大众”(mass),从前个人所有的出身、血统、种族、种姓、阶级等等的区别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个人渐渐失去其个别性而成为被操纵的社会原子和单位。(张汝伦16)
在张汝伦看来,大众由于自身的缺陷而成为大众时代的受害者。这些失去“个别性”与“独立性”的大众已经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杂多,而是一个单一同质的集合单位”(张汝伦18),是“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霍克海默 阿多诺131)。在与大众文化的相互塑造过程中,大众最终成为与精英对立的文化元素。
可见,当代大众不仅被定性为与精英对立的大众文化的接受者,而且对大众文化的生成具有反作用。同时,由于“文化场域是宰制性文化或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彼此博弈的场所”(斯道雷270),在当代的文化场域中形成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博弈,最终大众取代了精英的强势地位,成为当代文化的操纵者。在传统意义上,拥有文化优越感的话语生产者(精英)占据着言说的中心,并充当启蒙大众的角色,告知和启蒙大众该如何认识世界,大众是被动的、次要的接受者。然而,在当代消费语境下的大众话语模式却使得精英与大众成了平等合作的角色,并且大众正“越俎代庖地变成了中心角色”(周宪19)。
行文至此,我们已对有关大众的批判话语作了初步分析。如果从文化渊源来看,在当代中国以“mass”为中心的大众批判话语的生成,一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有关,也即秉持一种对大众的启蒙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承续了源自英国的“mass”讨论;再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维模式的移用,把大众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甚至是文化工业中失去主体性的庸众。实际上,当代以“mass”为中心的大众批判话语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它大体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于美国的文化工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出一批千篇一律的文化娱乐产品,而消费这种文化产品的大众则会成为“单向度的人”、异化的人,因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是“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霍克海默 阿多诺107)。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需要的“只是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娱乐,而不再是生活意义的揭示”(张汝伦16)。
很显然,这种批判理论视野下的大众话语,实质上是把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批判理论移植过来,用于对当代中国大众进行文化阐释,其理论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种批判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盛行的原因,学者单世联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兼济意识迄今仍积重难消,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以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受批判理论。(杰伊4)
然而,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经济的遭遇,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批判理论,进而当代大众被视为一种与精英相对立的群体,也即失却主体性的文化受害者。实际上,当言说者在言说大众的时候,他/她也在潜意识中建构了一个与之相对的精英。在精英与大众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中,二者必然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总会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把当代大众看作一群缺乏判断力、知识水平低下的“乌合之众”。
三、 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话语
当代大众话语中心从“mass”向“popular”的转移,一方面是由于后革命语境中大众化的文化逐渐生成,另一方面也与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理论的移用有关,再者,大众话语的转移也与以精英意识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化有关,也即90年代之后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逐渐由精英向大众发生转变,另一部分则继续坚守固有的精英意识。与批判理论视野下的“mass”不同,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话语试图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走进大众/大众文化,从中探寻有关大众/大众文化的诗学与政治学。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将“popular”的现代意涵界定为“受喜爱的”“受欢迎的”(威廉斯327—35),与此类似的是,当代中国倾向于“popular”的大众话语,其语义内核是充分肯定大众的世俗性与抵抗性,并把大众对“符号”的生产与消费视为其自主性的外在表现,因为“大众并非消极被动或孤立无援,他们有能力明辨是非”(斯道雷268)。
(一) 当代“大众”的主体性与生成性
如果把倾向“popular”的大众话语与革命语境中的人民大众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类似的言说姿态,即都把大众作为积极能动的社会力量加以肯定。“革命”语境中的人民大众被言说成“革命主力军”和依靠力量;而“后革命”语境中的大众(popular)则是自主性的消费者,他们常常以消费的方式进行“符号抵抗”。与社会抵抗不同,这种基于消费基础上的符号抵抗,所关注的不外乎意义、快感与社会身份。
不过,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话语主要还是以与“mass”相对应甚至是对立的姿态出现的。与以“mass”为中心的被动、低下的大众不同,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则被视为具有一定经济、文化基础的群体。他们并非“沙发土豆”式的趣味低下者,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艺术趣味比大众文化出现前的人群要低,相反由于比过去更多地接近了文化和艺术,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贾明117)
如前所述,从坚守精英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不再简单地对大众进行文化批判,而是开始以更加理性的姿态看待大众,并逐渐对大众产生文化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大众话语的转向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兴起不无关系,①这是因为“相对于社会文化生产的发展而言,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实践方式往往只是作为‘抵制’或惰性表现出来”(塞托9)。即使是作为消费者的当代大众,他们也并不像大众批判者认为的那样,被其消费的文化所规训,而是“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计谋构成反规训的体系”(35)。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把大众的消费行为称为“实践者的战术”,在这种实践中,“消费的战术,是弱者为了利用强者所采取的机灵方式”(37—38)。不难看出,不论是德·塞托的“微抵抗”还是“亚文化”中的“仪式的抵抗”都表征了大众主体性的存在。在以“抵抗”为中心的大众话语中,大众并不是把媒介所制造的大众文化全盘接收,而是进行意义的再生产。
从另一方面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的繁荣宣告了80年代新启蒙神话的终结,从而改变了大众在文化生产场中的客体地位。正如学者孟繁华所说,当代大众不仅改换了消极被动的受众角色,而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
民众在商品化的社会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主体,不再听凭知识分子的启蒙和引导,80年代的“圣言”已经很少再有听众。(孟繁华,《众神狂欢》28)
可以看出,当代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话语主体,已经从消费者变为生产者。而这种话语言说的理论资源依然可以追溯到米歇尔·德·塞托那里:
还有另外一种生产,它与合理的、扩张的,且集中、嘈杂、壮观的生产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消费”。(塞托33)
与此前把大众视为消极、被动的甚至是被物化的大众话语不同,德·塞托重新定义了消费,赋予消费积极的生产性意义。比如德·塞托认为:“消费并非生产商意志的简单反映,它原本就是一种‘生产’,意义是在文化消费实践中被积极地生产出的。”(陈立旭153)很显然,在德·塞托的大众话语中,消费已经蜕变为一种积极、能动的话语实践行为,而身处其中的大众也重新找回了缺失已久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尤其是随着“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引入,②对待大众的那种“或贬低或美”的非学理化、非科学化问题得以纠正。学者们开始以“文化分析”代替之前的“文化批判”的方式,对当代大众进行重新界定,他们将大众视为一种流动的概念,而不是把某部分人认定为固定不变的大众,从而打破了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言说模式,因为即便是精英阶层,在特定的语境中也会以大众的面目呈现。这也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事实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们看作大众的方式。”(Williams319)实际上,“大众与非大众往往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断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大众,因为他常常既带有大众的特点,又带有非大众的特点”(邹广文主编41),并且,在“大众与非大众之间,也不是敌对关系,而经常是一种相互协调的合作关系”(41)。
基于这种流动的大众概念,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当代大众的生成有其独特的话语机制,并且在特定的“小语境”中人人都可以被建构为大众:
“大众”是被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媒介人和市场依据当下现存“生产”出来的[……]是否为“大众”,就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是否受到所谓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范玉刚100)
从理论渊源看,这种生成论的大众言述借鉴了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理论资源。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费斯克29),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大众的“是”(who he is),费斯克引入了“层理”(formations)的概念来补充说明,“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29)。在当代文化场域中,这种“生成性”大众概念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没有一个截然分离的界线,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人也很难简单地按‘精英’和‘大众’来划分”。(王笛138)
(二) “场域”理论中“大众”分析
以上着重分析了当代以“popular”为中心的大众的“主体性”与“生成性”。近年来,基于“场域”论下的大众分析又渐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种场域论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是一处斗争的场所,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取得文化领导权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谈判、斗争和调停[……]。(罗钢主编21)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把文化中的“斗争的场所”演绎为“场域”论,并用于对大众/大众文化进行解构性分析,从关系、影响和对抗等方面来定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实质就是一些关系(relations),也就是用与主导文化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张力(关系、影响和对抗)来定义“大众文化”的关系[……]这样就把文化形式与活动的主体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的场域(field)。(霍尔449)
实际上,霍尔是把大众/大众文化看作一个动态的场域,并认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霍尔448)。与霍尔的场域论类似的是,2013年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洪恩美(May Ien Ang)也提出“斗争场域”(site of struggle)论,就是“把‘文化’当作‘斗争场域’,将文化理解为‘政治的’与社会争端的领域”(洪恩美100),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是“‘文化’与‘政治’或‘权力’在具体环境中的接合”(101)。为了阐明其斗争场域论的合理性,洪恩美进一步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文化研究的关键矛盾是,当它在特定的“斗争场域”准备大显身手时,总是试图忽视不同的“斗争场域”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忽视不同的文化现实、实践和过程之间是如何彼此联系、产生交集,甚至密不可分的,由此也易于缺乏对更广阔、更整体化层面的了解。(洪恩美103)
当然,洪恩美的斗争场域论主要是用来阐释文化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这一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大众概念,但显然它与霍尔的场域理论有共通之处,也即都将当代大众视为一个斗争的场域。其理论意义在于,避开了此前的大众话语以文化的高低、有无主动性等对大众进行简单的二元逻辑区分的做法,而是把大众看作被“建构”起来的概念。
与霍尔、洪恩美等人的“场域”论一脉相承的是,2013年美国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等人也提出“‘大众’无疑成为政治斗争及其变革的重要活动场域”(哈尔辛 海沃德106)。杰森·哈尔辛等人在《斯图亚特·霍尔的“解构大众”: 30年后的反思》一文中,直接继承了霍尔的“场域”论:
本文承袭了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逐步形成的有关媒介和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将“大众”视为集体运动和个人参与的重要活动场域,并且“大众”以一种横断面的方式直接勾勒了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损益(push and pull)关系。(哈尔辛 海沃德107)
可见,在场域论的理论视域中,大众话语也成为为权力而斗争的场域。它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大众群体的主体性和生成性,而且更加学理性地突显了作为意义生产者的大众在当代文化生产场域中的积极意义。这无疑消解了以“mass”为中心的大众批判话语中,精英与大众、被动与主动等相互对立的二元逻辑。
结 语
中国当代文化场域中所形成的所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与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对立是不同的。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中所确立的大众与“少数人”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模式。从空间来看,这种二元模式中的精英常常指的是人数上较少的“上层”,而大众则指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众与精英之间又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对立。
可见,当代大众话语的理论渊源大多来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即把大众看作“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人,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86)。这种批判大众的精英立场类似于英国“文化与文明”传统的“masses”话语,即都基于精英式的立场,以自己所设定的文化为标准去俯视大众,从而把他们“制造”成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庸众”。当然,这种所谓的精英立场以及对于西方批判理论的移用,最根本的动因在于一批固守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消费语境中深感消费大众与人文精神的格格不入,从而以批判的姿态作出的回应。而当代大众话语由“mass”向“popular”的转移,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中大众文化的持续繁荣,使得一些知识分子不得不更加理性地重新思考关于大众/大众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大众话语的转移也与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旅行至中国,并在中国理论界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有关。
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大众话语的生成经历了以批判、抵抗、场域为中心的生成过程。时至今日,这三种大众言说依然鼎足并存,并且一直延续着,没有形成共时性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言说还会出现新的理论样式,这就要留给未来的研究者继续研究和思考了。
注释[Notes]
① “日常生活审美化,可视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历经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本土名称。这个名称是外来的,但是无论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都显示了地道的中国本土文化的作风。”见陆扬: 《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前言)。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20世纪五六年代,以英国伯明翰大学为中心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它注重考查文本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具有跨学科性。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文化研究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大致在2000年前后,它促使学界对大众的关注方式从“批判”转向“分析”,而对文学的研究方式则从“作品”走向“文本”。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洪恩美:“文化作为斗争场域”,段慧译,《文艺研究》6(2013): 98—104。
[Ang, May Ien. “Culture as a Site of Struggle.” Trans. Duan Hui.Literature&ArtStudies6(2013): 98—104]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Baudrillard, Jean.ConsumerSociety. Trans. Liu Chengf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陈立旭: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9年。
[Chen, Lixu.ReevaluatingtheCulturalCreativityoftheMasse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9.]
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De Certeau, Michel.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TheArtofPractice. Trans. Fang Linl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樊星:“当代文论与人文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1995): 104—111。
[Fan, X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Humanistic Spirit.”ContemporaryWritersReview1(1995): 104—111.]
范玉刚:“当下语境下的‘大众’与‘大众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3(2007): 98—103。
[Fan, Yugang. “‘The Masses’ and ‘Mass Culture’ in Current Context.”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 3(2007): 98—103.]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Fiske, John.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 Trans. Wang Xiaoyu.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高岭: 《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Gao, Ling.CommodityandObjectWorship:CritiqueofFetishismintheAestheticCulturalContex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高瑞泉: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Gao, Ruiquan.SpiritualTransformationduringtheTransitionalPeriod.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4年。
[Gertz, Clifford.TheExplanationofCulture. Trans. Han L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Hall, Stuart.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John Storey.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AReader(2nd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 442—53.
斯图尔特·霍尔编: 《表征》,徐亮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年。
[- - -, ed.Representation. Trans. Xu 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杰森·哈尔辛 马克·海沃德:“斯图亚特·霍尔的‘解构大众’: 30年后的反思”,宗益祥译,《国外理论动态》10(2014): 106—110。
[Harsin, Jayson, and Mark Hayward. “DeconstructingtheMassesby Stuart Hall: Reflections After Thirty Years.” Trans. Zong Yixiang.ForeignTheoreticalTrends10(2014): 106—110.]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Jay, Martin.TheDialecticalImagination:AHistoryoftheFrankfurtSchoolandtheInstituteofSocialResearch, 1923—1950. Trans. Shan Shilian.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季红真:“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论张贤亮的创作”,《读书》6(1985): 53—60。
[Ji, Hongzhen. “Two Mutually Referable Worlds: On the Creation of Zhang Xianliang.”Reading6(1985): 53—60.]
贾明:“对大众文化批评及大众文化特征的思考”,《社会科学》11(2004): 114—18。
[Jia, Ming. “A Probe into Criticism of Public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JournalofSocialScience11(2004): 114—18.]
岩间一弘: 《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葛涛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
[Kazuhiro, Iwama.TheBirthandTransformationoftheShanghaiPublic. Trans. Ge Tao.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6.]
旷新年:“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读书》2(1997): 12—16。
[Kuang, Xinnian: “‘The Public’ as a Cultural Imagination.”Reading2(1997): 12—16.]
陆扬、王毅: 《文化研究导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Lu, Yang, and Wang Yi.IntroductiontoCulturalStud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罗钢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前言)。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Luo, Gang, 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refa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1.]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渠敬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DialecticsofEnlightenment. Trans. Qu Jing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孟繁华:“小写的文化: 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2001): 33—37。
[Meng, Fanghua. “Culture in Lower Case: The Mass Culture in Present-day China.”JournalofHainanRadio&TVUniversity3(2001): 33—37.]
——: 《众神狂欢: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 - -.CarnivaloftheGods:ACulturalPhenomenoninChinaattheTurnoftheCentury.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3.]
——: 《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5年。
[- - -.TreatisesonNew-CenturyLiterature:LiteraryThoughts. Beijing: Modern Press, 2015.]
潘知常 林玮: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Pan, Zhichang, and Lin Wei.MassMediaandMass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约翰·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Storey, John.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5thEdition.). Trans. Chang J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3(2006): 7—13。
[Tao, Dongfe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ContemporaryLiteratureCriticism3(2006): 7—13.]
——: 《陶东风学术自选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 - -.Self-SelectedWorksofTaoDong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0.]
——: 《文学理论的公共性》。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 - -.ThePublicnessofLiteraryTheory.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8.]
——:“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河北学刊》5(2003): 86—92。
[- - -. “Thre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A Response to Zhao Yong.”HebeiAcademicJournal5(2003): 86—92.]
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2009): 126—40。
[Wang, Di. “New Cultural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Mass Cultural History: A New Trend in the West and Its Impacts on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ModernChineseHistoryStudies1(2009): 126—40.]
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6(1993): 63—71。
[Wang, Xiaoming. “Ruins in the Wilderness: The Crises of Litera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ShanghaiLiterature6(1993): 63—71.]
王尧: 《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Wang, Yao.The1980sasaQues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王迎新: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
[Wang, Yingxin.AStudyoftheIdeologicalFunctionofMassCultur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4.]
王岳川: 《中国镜像: 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Wang, Yuechuan.AMirrorofChina:ACulturalStudyofthe1990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Williams, Raymond.Cultureand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 - -.KeyWords.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郗彩红:“西方大众社会理论中‘大众’概念的不同义域”,《学海》4(2007): 90—95。
[Xi, Caihong. “Different Semantic Domains in the Concept of ‘Mass’ in Western Mass Social Theories.”AcademiaBimestrie4(2007): 90—95.]
许纪霖: 《启蒙的起死回生》。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Xu, Jilin.TheRevivaloftheEnlightenmen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徐友渔: 《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9年。
[Xu, Youyu.FreeSpeech:SelectedWorksofXuYouyu.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1999.]
尹鸿:“为人文精神守望”,《天津社会科学》2(1996): 76—86。
[Yin, Hong, “Keeping Watch over Humanistic Spirit.”TianjinSocialSciences2(1996): 76—86.]
袁进:“人文精神寻踪——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二”,《读书》4(1994): 73—81。
[Yuan, Jin. “The Pursuit of Humanistic Spirit: Thinking on Humanistic Spirit (2)”.Reading4(1994): 73—81.]
章可: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Zhang, Ke.TheConceptualHistoryofHumanisminChina.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1994): 16—22。
[Zhang, Rulun. “On Popular Culture.”FudanJournal(SocialSciencesEdition) 3(1994): 16—22.]
周宪:“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文艺理论研究》6(1994): 17—26。
[Zhou, Xian. “Current Cultural Dilemma and the Identity Crisis of Artists.”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6(1994): 17—26.]
周宪主编: 《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 - -, ed.CulturalLandscapeattheTurnofthe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ing House, 1998.]
邹广文主编: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Zou, Guangwen, ed.OnContemporaryChineseMassCulture.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