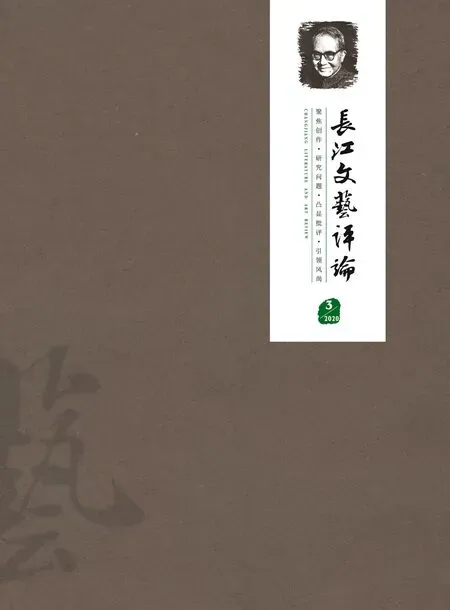语言、象征与北中国乡村
——对吕新近期中短篇小说的一种理解与分析
◆王春林
近几年来,作家吕新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间隙,偶尔也会有一些艺术感特别突出的中短篇小说问世。中短篇小说写作对他而言,应该只是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一种调整写作节奏的偶尔为之。但即使如此,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往往会因别出机杼而引人注目。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先锋作家,他的这些中短篇小说奇特出彩,首先是一种语言运用能力的非同寻常。这一点在中篇小说《雨下了七八天》里有突出的表现。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连绵的雨天里发生在一个村庄里的故事,吕新这样写道:“不用去看,他也能想出它们的那种样子,一丛丛,一簇簇,阴阴的,冷冷的,打着小白伞,诡诡秘秘地站在那里,像一群病人,又像极了一群手拉着手的小孩。”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屋脚边的木头上已经潮湿到了生出小蘑菇的地步。怎么描写这些小蘑菇呢?到了吕新笔下,这些小蘑菇竟然变成了诡诡秘秘地站在那里的打着小白伞的病人或者小孩。这里,与吕新的语言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显然还有作家发达的艺术想象力。再比如:“刘连梅关窗户的时候,望了一眼黑沉沉的夜色,在屋里灯光的映照下,她看见雨是斜着飘进来的,就像从黑暗的天上缓缓降下来的一面斜坡,快要落地时突然分裂出无数的头绪,然后各自行动,深入到地上的千家万户。”作家在这里所描述的灯光映照下的下雨场景,应该说很多人都有过真切的观察体验,但如何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把这种场景形象地呈示给读者,往往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写作才能。吕新艺术想象力的奇崛处在于,他非常精准地把夜色中的雨景比喻为一面自天而降的缓缓的斜坡,而且这斜坡竟然可以如同拥有思维能力的人一样突然就“分裂出无数的思绪”。思绪茫茫如雨丝,吕新这样的语言天才显露无遗。小说的标题是典型的吕新式的标题。舍吕新之外,其他作家很难会以如此充满艺术感觉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小说命名。既然是“雨下了七八天”,那小说文本的很多处,就都会有对各种雨景的呈现。吕新的一种特殊才能在于,他写雨能够鞭辟有力地深入内里把雨的精髓表现出来。《雨下了七八天》中吕新通过自己笔端以出神入化的语言运用,成功地营造出某种阴雨绵绵的阴郁氛围。倘若是嗅觉灵敏者,就会从他的形象化语言表达中嗅出渗透于语言缝隙中的霉味来。
小说集中讲述了三条结构线索上的故事。第一条是村会计因为贪污问题而被关押。村会计的问题是以郭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入驻之后被查证的。根据工作组的调查结果,村会计一共贪污款项四百多元:“那么多钱,他也不是一下子拿走的,今天十块,明天五块,日积月累,还愁不会越来越多么。”既然被认定是贪污犯,会计忠发就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村里一个曾经先后吊死过三个人的黑屋子里。会计被关押在黑屋子里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妻子刘连梅只好让儿子福林按时按顿去给自己的父亲送饭。期间,虽然妻子和儿子曾经数度设法帮助会计改变境况,最终均未奏效。按照看押者裴永会的说法,只要连阴雨一停,县里就会来人把会计押走。然而,没等到雨停下来,会计就已经彻底精神崩溃,在黑屋子里把自己的裤子撕成布条条,编成绳子,上吊自尽了。对于会计之死,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会计的贪污问题正在查证的过程之中,他是否有贪污行为?他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财?都有待做进一步的调查。其二,退一步说,即使会计真的贪污了那么多钱,他也无论如何都罪不至死。就此而言,会计之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那个阶级斗争高压时代的一种无声抗议。在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吕新的悲悯情怀。
第二条线索是村副主任杨跃海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无端死亡。关于杨跃海之死,小说中相关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早在杨跃海死亡的前几天,福林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在他的身上嗅到了某种奇特的死亡气息:“在与杨跃海的身体发生交集的一刹那,福林闻到了一种混合着锯末、衣物、病情、糖水、尿臊、脑油以及酸菜和动物皮毛的气息,顿时就愣住了……在福林的习惯和印象当中,锯末味通常不仅仅是一种气味,更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而那线索的另一端,必然连接着一具簇新的棺材,一具刚刚做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上油漆的棺材。”于是,看着在自己的视线里飘来飘去的杨跃海,福林倍感疑惑:“眼前的这个杨跃海,难道快要死了?”其二,在上级部门那里,杨跃海已经上了某个不足为人道的名单。这一点,在村主任海龙飘忽的思绪中曾经有所流露:“因为他发现自己爱打听事情的毛病又犯了,又在心里抬起了头:他觉得,去公社,应该和村里两个人的材料有关。”哪两个人呢?“按照他的估计,他觉得,如果他猜得没错,其中一份材料应该是杨跃海的。”更进一步说,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呢?小说并没有做明确的交代。但如果把这一信息与杨跃海突然的死亡联系在一起,那么,二者之间便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如果再把杨跃海之死与会计的被查证关押联系在一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可能就是,即使杨跃海不是自杀而是自然死亡,他的自然死亡其实也与工作组的进村开始调查紧密相关。用老百姓的日常话语来说,这位心事重重的村干部杨跃海,极有可能是被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氛围给活生生吓死的。
第三条线索是村主任海龙家亲戚培仁的突然来访。培仁与海龙是表兄弟关系,他们家在路途相当遥远的后草地,“来回一趟差不多得有十几二十天,一路上会十分地辛苦。”但即使如此,培仁却是半年多来的第二次来走亲戚了。这样的一种异常情况,让身为村干部的海龙倍觉蹊跷难解:“培仁越是这样说,他却越觉得培仁是故作轻松,装着没事人一样,实际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呢。他总觉得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中间不知包藏着什么呢。”“培仁一定是碰上什么事了!不然不能这么不辞劳苦地一趟一趟往外跑,好像是在躲避什么呢。”更何况,这培仁前来走亲戚,不仅随身携带着紫药水和一根足有一丈长的绳子,而且晚上睡觉时也都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衣服,一副随时要应对特殊情况的样子:“想来想去,他觉得培仁那种样子只能是一种面对危险时的正常的反应——当一种突如其来的危险破门而入的时候,培仁那样做难道不对么?难道不应该有那样的反应么?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培仁提防了好几年的一直徘徊在他身边的危险?不管是什么,那样做其实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培仁到底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危险呢?对于这一点,小说始终未做明确的交代。但假若联系会计的被关押以及杨跃海的无端死亡,再联系那个阶级斗争的紧张氛围笼罩一切事物的时代,培仁所一直提防着的那种危险的指向大约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注意到,在海龙的一种梦境中:“培仁用两只绿莹莹的手捂着自己的脸,低声说,我不想别的,无非就是想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可是就连这也做不到。”如此一种梦境所明确传达出的,正是培仁内心深处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雨下了七八天,就在这阴雨绵绵的七八天时间里,这座看似寻常不过的北国小村庄,所发生的也不过是以上这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阴郁故事。小说中,连绵的阴雨间隙,曾经短暂地晴过一会儿,海龙开完会后一个人回家:“他走着,有时会抬头看看天上,星星很多,有的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有的却离得很远,独自亮着,像是地上的那些独门独户的人家。他想,星星说不定也以类聚,也以群分呢。有红色的星星,革命的星星,一定也存在着……有问题的星星。有几颗谁也不挨,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看就有问题。”这里,既在描写自然风景,同时也在分析展示当时的社会形态。吕新的小说中,一向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具体到这一篇《雨下了七八天》,那些断断续续贯穿于全篇的雨景描写,一方面固然是对于自然风景的一种展示,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它却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是整体社会存在以及生命存在的象征隐喻。正如海明威颇负盛名的《雨中的猫》一样,作家借雨中的猫表达了“美国太太”的一种无助的生活状态,吕新在《雨下了七八天》这篇小说中,其实也是借雨为掩饰,实质上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一种阴郁的生命存在图景。
其次,就是艺术感的突出表现,就短篇小说而言,艺术感尤其重要。吕新的《幕落时有狗叫,野草呈倒伏状》,就是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其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标题设定的别出心裁。如此一种带有突出描写色彩的小说标题,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是非常罕见的。尽管很难说其中隐含有什么样的微言大义,但作家所描述呈现的,毫无疑问是一种典型不过的乡村风景。又或者,类似于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只有发生在中国的乡村,才能够令人信服。这个短篇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如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对海明威所谓的“冰山原则”极其到位的理解与实践。某种程度上,吕新真正做到了通过海平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成功地暗示表现了海平面之下的八分之七。其二,是吕新一种沉稳至极、极具耐心的叙事姿态。
先来看叙事姿态。比如,小说一开头,写乡村一位早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姜秀山的老眼昏花,通过两个鲜活生动的细节舒缓地呈现出来。一个是坐在门前的他,忽然发现有一只蛐蛐从脚前路过,就伸手把它给捉住了。因为怕不小心把它给捏死了,所以就放在另一个手心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并不是一只蛐蛐,而是一截电线的皮。”只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姜秀山才把它看成了一只蛐蛐。姜秀山由此而联想起去年或者前年,自己也曾经把一只咬人的虫子看成了一颗瓜子壳:“那还真是一只咬人的虫子,而并不是他以为的一颗瓜子壳,看见要捉它,就急了,前面的几根胡须针一样又尖又细,到今天也不知道那一次到底是被那虫子的嘴咬破的,还是被那几根针一样的须刺破的。”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这两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细节,吕新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姜秀山稀里糊涂的老年生存状态。
但任谁都不可能料想到,正是这样一位老眼昏花,总是稀里糊涂,摇晃着站三次才能够站起来的乡村老者,到头来,竟然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凶杀案。他拄着一把锄头走上街头,偶遇已经五十多年相互之间没有说过话的村民黄志勇,在围绕往事进行了一番可谓针锋相对的口舌对垒之后,姜秀山竟然举起锄头,把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大的黄志勇给打死了。眼看着九十好几的黄志勇即将走入坟墓,姜秀山为什么非得要冒险杀人呢?某种意义上,吕新创作这一短篇小说,正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形象回答。
这一桩凶杀案的最终酿成,与姜秀山、姜秀山妻子以及黄志勇他们三人之间的一段情感纠葛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五十多年前,身为村干部的黄志勇,在一年的时间内,曾经先后两次支配姜秀山去后草地买马:“后草地?好差事呀!不仅能出去见见世面,每一天的工分还会额外多出一倍半。姜秀山除了意外的懵懂和惊喜,压根也没有想过这么好的差事怎么会轮到他,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第一次去,姜秀山在后草地呆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时间“有六七十天,比春天那次多出近一个月。”两次加起来,姜秀山的“好差事”时间,竟然多达三个月。事实上,也正是在那一年之后,一贯“心粗得像筛子”的姜秀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关于自家妻子与黄志勇之间的风言风语:“走到街上或者地里,三五个人站在一起正说着什么,看见姜秀山来了,立刻就什么也不说了,或者另起个头,说起一件别的事。”就这样,“一个人,反应再迟钝,再不灵敏,只要时间长了,也总能多少嗅到一点儿什么。”毫无疑问,姜秀山对黄志勇的心生芥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现在。
没想到,这两位再度聚在一起的时候,围绕早已去世了的姜秀山妻子进行对话。尽管姜秀山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听到了关于妻子和黄志勇的风言风语,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都不愿意相信。这一次,因为黄志勇披露的一个身体标志,姜秀山才不得不认同了自己早已被妻子戴上了绿帽子的不堪现实。“黄志勇说,再跟你说一件事,她胯那儿有一颗‘红豆’,这你总见过总应该知道吧?”如此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一下子就把一直半信半疑的姜秀山击晕了:“确确实实,这是真的,姜秀山知道,这一点黄志勇没有胡说。”“那种地方他也见过?那个红色的小点,那可是包裹在她那条短短的内裤里的,要是不脱下她那条短短的内裤,就连她本人也看不见呢。”自己妻子与黄志勇奸情被证实,对姜秀山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而黄志勇竟然继续飞扬跋扈地“跟着就把头伸了过来,嘴里说着,来,你来——有种照这儿打!你没种。一边说着,一边又用头去撞姜秀山的胸前。”原本被戴上绿帽子的巨大羞耻,再加上黄志勇口口声声的“你没种”,实在忍无可忍的姜秀山才不管不顾地举起了手里的锄头,把黄志勇送上了西天:“姜秀山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村庄,看见有一股力量穿过整个村子,像个破衣烂衫的孩子一样,破烂处如翅膀,满头大汗地从村口那边一路跑来,一来了就直接钻进了他的手心里。”已经是耄耋之年的姜秀山,为什么还要激情杀人呢?他在杀人后与本家侄子姜茂顶的对话:“他是把我看扁了,一辈子看扁我,认为我不敢。”当姜茂顶说“他想咋看就让他咋看去,扁的还是圆的由他去”的时候,姜秀山的回复是:“你不懂,你不知道一个人让人看扁的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撑着姜秀山发出奋力一击的,其实是一种积蓄了五十多年仇恨与屈辱的力量。对于姜秀山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民来说,通过如此拼命一击,强力捍卫了一个人类个体的人格尊严。
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姜秀山和黄志勇的对话过程中,那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可能出场,而且也一直处于无名状态的姜秀山妻子的形象慢慢地在小说中浮出了水面。在姜秀山一贯的印象中,自家的女人,不仅总是蓬头垢面,总是不讲究穿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表现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在黄志勇的描述中出现的那个乡村女性,却显得特别虎虎有生气,格外地与众不同。黄志勇首先特别强调:“我只想告诉你,那个春天,那个秋天,是她一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然不止那两个时候,后面还有,我都记不清了。”具体来说,她的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她很会唱,“黄志勇说,她很会唱呢,没给你唱过吧?你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吧?”其二,她还会跳,“黄志勇说,除了会唱,她还会跳呢,这你更不知道吧?更从来也没有给你跳过吧?”其三,她在那个特殊的时候竟然会表现得很有劲,“黄志勇说,她也很有劲,两条腿把人夹住,就像被蟒蛇缠住一样,这你知道么?噢,你要是从来没叫她夹过,从来没让她缠过,你肯定也就不知道。”其四,她身上竟然有个开关,“她身上还有一个开关,具体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哇?平时关着,她就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可只要一摁那个开关,她整个人就像抽水机一样发动起来了,她常说她一伸手就能摸到云彩。”通过黄志勇所披露的以上四个方面的细节,吕新所揭示出的,其实就是另一个姜秀山的妻子,或者说是姜秀山妻子的另一面。很大程度上,只有把这位长期处于压抑与委屈状态的女性,与那位格外地与众不同、生命力特别旺盛的女性拼贴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才是真实的姜秀山妻子。
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点,就是小说别出心裁的结尾方式。小说结尾处,叙述者的视点一下子就从姜秀山杀人的现在跳回到了比五十多年前还要更遥远的姜秀山相亲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媒人带着姑娘还有姑娘的姨姨第三次来到了自家屋里,腼腆的姜秀山根本就不敢进屋去:“屋里有生人在,姜秀山一直不敢进去,更不好意思进去,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用指甲抠着墙上的土。他爹出来,看见他在抠墙,就说他,别抠了,再抠墙就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姜秀山的抠墙,这个动作说明他腼腆至极。再一个则是,他爹的那一句“看你那点出息”。究其根本,这一句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其一,正如他父亲所言,姜秀山的一生的确谈不上有什么出息。妻子红杏出墙那么多年,他竟然都一直半信半疑,长期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其二,姜秀山当年以及一生的“没有出息”,与他耄耋之年的激情杀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很大程度上,通过姜秀山、姜秀山妻子以及黄志勇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彼此缠绕的关系,作者借此而写出的,实际上也正是人性的复杂和脆弱。
越是拥有耐人咀嚼内涵的短篇小说,其人物与情节的构成就越是简单。吕新这篇《正月二十的一次午宴》即是如此。通篇写来写去,也不过只有两个人物在活动,也不过是一次最终被迫泡汤了的没有完成的午宴。小说中其他那些未出场的次要人物,一个个都有着切实的命名。比如,被请客的明娃,比如他们俩的女儿海海,女婿四猴,唯独对出场的主要人物也即这一对一门心思要请客的夫妻俩,没有做专门的命名,从头到尾都是“他”和“她”。明明拥有命名的能力和权力,但吕新却为什么拒绝给主要人物命名?对于如此一种现象,除了可以使人物更具抽象特征和更具普遍的代表性这样的一种阐释,其实很难找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解方式。
除了人物的特别命名方式需要关注之外,这篇小说艺术层面上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对于重复与延宕手法的创造性使用。首先是重复,小说中一再重复表达“他”的做菜尤其是热菜行为。“从上午十点多,他就开始准备晌午的饭了,十二点还差一点儿的时候,已经一鼓作气做好了四个菜。”紧接着,因为躺在炕上的妻子提醒他必须讲究“人三鬼四”的礼数,请客不能只有四个菜,所以就又添加了一个炒绿豆芽的菜。这样,“不到十二点,五个炒好的菜都已经摆到了他们那张用了很多年的小方桌上。还有一瓶没打开的酒,两个酒盅。”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期待如今在村里主事的明娃的如约光临了。约请时明明已经说好十二点左右来吃饭,但这位明娃却偏偏就是怎么也等不来。为了怕菜冷了,“他”便总是在“她”的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去热菜:“他说,我把这几盘菜都再热一下,等热好了,说不定明娃就来了。”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菜热好,“再重新都摆在桌子上以后,明娃还是没有来。”又过了不小一会儿,等到“她说,又冷了吧?”的时候,“他嗯了一声。然后就又把菜一盘一盘地倒进锅里,分别又热了一遍。”到最后,“在她的印象里,这个晌午以来,那几个菜最少回锅了四五次,也说不定有六七次呢,因为她有时候会睡着了。在她睡着以后的那个时候,他悄悄地给那几盘菜回锅加热,她是看不见的,也不一定能听见。总之是一看见凉了,就倒回锅里热一次。”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才终于确定明娃今天肯定不会来,决定不再去热菜了。其次是延宕。具体来说,延宕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请客。“请明娃吃饭,一直拖到今天,并不是他行动得迟,他其实早就开始行动了,从正月初五第一次去明娃家,一直到昨天,这中间他一共去过明娃家六次,但直到昨天才终于误打误撞地把明娃逮住,明娃也总算答应了。”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俩早就打算好的请客行为,也就只能一直延宕到正月二十这一天了。其次是午宴。按照当时明娃的答复,他前来吃饭的时间,是第二天晌午的十二点左右。所以,这老两口方才赶在十二点之前,就把五个菜都炒好了。没想到的是,这明娃怎么也等不来。这也才有了“他”一再热菜的重复行为。关键还在于,到最后,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延宕到下午三点多,明娃也没有来,一次筹划已久的午宴,就此而彻底泡汤。
由以上分析可见,吕新在《正月二十的一次午宴》中所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次一再重复一再延宕的发生在中国乡村的“等待戈多”的故事。正如同戈多到最后没有等来一样,这一对乡村老夫妻所要宴请的客人明娃最终也没有来。那么,“他”和“她”这一对乡村老夫妻为什么一定要请明娃来做客呢?按照“她”的说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事要求明娃去办:“她说,咱们没有事情要让他办,无非就是想请他来吃一顿饭。都这个岁数的人了,还能有啥事,啥也没了,房也不盖了,户口更是不动了。”虽然“她”一力强调不会求明娃办任何事,但从“她”的话语中,我们却可以知道,乡村里的很多事是必须求明娃才有可能办成的。质言之,他们之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请明娃吃饭,只因为“明娃现在是村里的主事”。
更进一步地,如果把这次最终流产的午宴,与他们夫妻俩苦难的生存状态(妻子常年累月地因为疾病而躺在炕上,唯一的女儿海海,因为身患残疾,只能嫁给瞎了一只眼的四猴,而且“四猴好像对海海有些不耐烦呢”),与乡村里请主事的人吃饭的惯例(“不是明娃一个人有这样的待遇,以前赵疯子、郭四、陈敏、王八万、牛兴隆他们主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早就是一种多年的习惯了)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吕新刻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背景,我们就可以断定,作家吕新通过这一次流产的午宴,最终要表达的就是一种长期匍匐在无形的权力之下充满着屈辱感的隐忍生存状态。
仍需赘言的一点,就是一种看似无形的象征色彩的具备。一个是关于菜的颜色的描写:“经过了一晌午反反复复的回锅以后,那几盘菜都已经被折腾得完全不像样子了,除了普遍变黑,变得灰蒙蒙黑乌乌,甚至好像连模样也看不出来了。”再一个是结尾处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她说,我们好像坐在一趟夜行的车上。”“他看着外面越来越阴黑的天气,说,你说得对,这会儿,正在过山洞。”这看似寻常的表达中,无论是“灰蒙蒙黑乌乌”的菜的颜色,抑或还是“坐在夜行的车上”的感觉,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乡村里普通民众苦难生存状态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某年春夏》具体关注表现的是村人返乡后发生的那些后续故事。我们都知道,虽然吕新一向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作家,但他的具体书写对象却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中国那一片厚重的乡村世界。具体到这一篇《某年春夏》,引人注目处,首先就是作家对那些乡村伦理习俗的书写与表达。比如,“魏山水和贺有财他们家沾一点亲,魏山水的奶奶和贺有财的奶奶据说是表姊妹,虽然两边的那两个奶奶都已经不在了,不过两家之间的那种关系却还时隐时现地延续着,若有若无地勾连着。”毫无疑问,如此一种虽然藕断丝连但实际上早已距离遥远的所谓亲戚关系的维系,只有在历史沉淀厚重的北中国乡村世界才有可能。再比如,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及时而尖锐地冒了出来,那就是谁来给贺云保扛起引魂幡的问题。按规定应该是贺云保的孙子,可是谁都知道贺云保连婚都还没有结,哪来的孙子?儿子都没影,更别说孙子。”虽然贺云保没有孙子,但按照乡村的伦理习俗,人死了要出殡,还必须有人以孙子的身份扛引魂幡才行。这样一来,通过乡村长者商议的方式寻找为贺云保扛引魂幡的人,到最后,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来充当这个角色之后,此事方才作罢。
尽管有着关于乡村伦理习俗浓墨重彩地描写,但吕新的书写重心却很显然并不在此。与伦理习俗的描写再现相比较,吕新的艺术旨趣无疑更集中在生命存在所具神秘色彩的探究与书写上,吕新的关注重心是贺云保之死与小毛失踪这两件事情。首先是贺云保那充满诡异色彩的死亡过程。从贺云保扛着那颗肿得就像“量米的斗”一样的头颅“很慢很吃力”地返回黑土巷开始,一直到后来包括使用了大量仙人掌在内的治病过程,到他的死亡,以及死亡后整个乡村葬礼的举行过程,吕新做了事无巨细的展示与描写。唯独有一点,那就是关于贺云保的具体死因,虽然从小说一开始贺云保返乡时就已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但一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作家对此都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在贺云保的葬礼结束后,当贺云保的父亲贺有财出现在街头的时候,还没有等人开口询问相关事宜,就做出了一问三不知的拒绝姿态。“旁边就有人说,还没问你呢,你就说啥也不知道,你知道要问你啥?”“贺有财边走边说,不管是啥,我都不知道。”“要是问你姓甚叫啥,你也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不知道。”事实上,作为如此一种决绝的拒绝姿态,与其说是贺云保的父亲贺有财,莫如说是身为作家的吕新自己,是吕新自己拒绝透露贺云保的具体死因。
同样的情形,也还出现在关于小毛的展示与描写上。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外出的村人都相继回来了,唯独不见自家的儿子小毛,小毛的母亲孙本兰心急如焚。找到王四四去再三询问,王四四给出的答案也只是一个模糊不过的“小毛往东去了”。既然得不到准确的信息,思儿心切的孙本兰三番五次地梦见小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个月里,孙本兰有三次梦见过小毛,每次都是小毛忽然出现,好像是临时请假从远处赶来的,又好像一直就在附近,来到她的梦里和她说话,有时说着说着就不见了。”尽管文本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交代小毛的下落,但依照其中隐约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小毛早已不幸离开了人世。比如,“怎么就忽然有了那么明显那么厉害的抬头纹?再一看,确实比走的那时候老了不少,甚至越看越觉得很像是她从前一个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同学。又看见他湿漉漉的,好像泡在水里,身上有草,还有石头。”再比如,“有一次正说着,忽然听见远处或是附近的鸡叫了,小毛脸上的神情顿然凝住,像冷了的油脂一样,再也不能变化,也变不回去,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无论如何,所有的这一切充满暗示性的描写,其最终指向的方向都只能够是死亡。唯其如此,内心早已明确意识到这一残酷事实的孙本兰,才会那样按捺不住地“嚎啕大哭”。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作家一再地通过各种方式巧妙暗示小毛必然的死亡结局,但关于小毛的具体死因,吕新拒绝做更进一步的交代。
作家为什么拒绝交代贺云保与小毛他们的具体死因。以我所见,吕新的全部努力,除了留下足够大的空白供读者想象填充之外,恐怕更主要地还是要借死写生,借此写出生命存在的某种神秘性来。尽管在很多时候,现代的医学可以给出死亡以种种不同的解析方案,但死亡却总是莫名其妙发生的一种特别现象。正如同某一人类个体的诞生带有不容忽视的神秘性一样,某一人类个体的死亡也携带着难以用现代理性加以言说的神秘性。在这篇《某年春夏》中,吕新意欲借助贺云保与小毛的死亡故事来洞见死亡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神秘性。
吕新的小说是个说不尽的艺术话题。上述的一些分析并不能代表其全部的思想艺术成就。吕新是一个用灵魂在书写的始终保持先锋写作姿态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既有象征手法的巧妙使用,也饱含着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入挖掘与理解,更有那“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方式设定,以及他那出神入化的语言运用能力。正如李锐在《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吕新静静地躺在自己不曾被污染的纯净当中,一任语言的溪流淙淙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