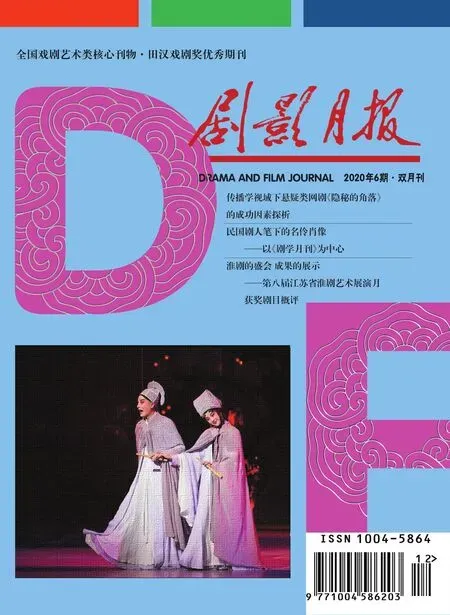“门图”与“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人事”的特定机制
■吴艳
一、上海民俗“音乐人事”
在上海民俗事项中常常可以见到一种情景,同一群民间艺人,他们有时穿上道袍去为丧事做道场,有时又在婚礼场合上敲起扬琴伴丝竹,有时还吹着西洋铜管乐器为庆典仪式添威助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随“机”应变、不成“体统”的状况过去并不如此。据嘉定区石家班第六代道长石季通所说,“清代中叶(1750 年),堂名与散居道院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前者以打唱为主,后者以道业为生;前者以娱人为目的,后者在娱神的同时娱人;前者演唱民间俗曲,后者演唱道教乐曲。堂名班不兼道教法事,道院不兼打唱”;嘉定区梅家班第七代道长梅养岩也说:“道乐是道乐,清音是清音,虽然两者都可谋生,但道不同不可并论,唱道乐是出家道士,不是凡人,唱清音是在家俗子,没有仙气,道士就得以道乐为主”;另,《上海市奉贤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亦载:“旧时习俗把清音班乐手称为‘先生’,把吹打班吹鼓手称为‘六兽人’。因而,这三种民间器乐组织在人员方面一般不流通混杂,只是偶然见到个别道士参加当地清音班活动的现象”。鉴此,不免使人发问:究竟从何时起,不同班社的职能开始流通并转型,又从何时起,同一班社的艺人可以兼职跨业了呢?这个饶有趣味的演变过程与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又存在着何种关联性呢?
对此,笔者查找了上海市各区县志、上海市音乐集成资料以及相关口述资料,将1920 年代以前艺人班社的活动状况概括为:“门图”支撑下的“各安本分”局面。
何谓“门图”?对于“门图”的记载极少,综合已有文献,“门图”主要有以下几种涵义:其一,“门图”是掌管图内婚丧事象的族人;如曹本冶主编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下)》记有:“雍正年间南汇由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分化出南汇县,下设‘保’,‘保’下设‘图’,‘门图’是掌管图内婚丧事象的族人。”其二,“门图”是一种民间鼓手班的营业证明,此证明限定鼓手班的活动范围,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宝山区乡镇卷》上记载:民间鼓手班不论是专业性的,还是临时性的,都有“门图”(一种民间鼓手班的营业证明),指定鼓手班活动范围。“门图”的来源可以由祖传或买卖而获得。民间鼓手班以门户地图划分地盘作为自己控制经营业务范围,包揽了本“门图”内住家的婚娶、丧葬诸事。各鼓手班都不得超越自己的“门图”。
据老艺人们回忆:“门图”有一个门图契据,契中划定纵横多少路,包括哪几个图(如十一图、十二图等),以后图内的养生送死、男婚女嫁的生意,呆定由执据人来包揽,其它人不得染指。松江从城厢到乡村到海滨,到处有“门图”。闵行区祖传道士王利生在“闲聊”时对笔者提及“门图”:现在好了,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动,以前可不行的。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以前不能随便去一个地方,去的话要向当地的人交钱的,当时称为“门图”,就像现在的“黑社会”一样。
从以上的描述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将“门图”理解为旧时民俗艺人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形成了一种行规制度,此行规限定艺人们的活动及范围。所以说,某一地域范围可称为“门图”,控制和负责某一地域范围内婚丧的人也可被称为“门图”。
活跃于上海传统民俗活动的音乐班社主要涉及吹打班、丝竹班和道教班。上海地区的吹打班出现于何时,至今难下定论。据艺人们所述,1920 年以前,上海地区的吹打班(以及道教班)成员已大多成为职业性的和半职业性的艺人。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吹打班的职能范围比道教班和丝竹班更广,既可用于婚礼,也可用于丧葬,还可用于传统节日乃至某些宗教活动。丝竹班在上海地区兴起得较晚,学习丝竹乐被人们认为是一项高尚的事情,其成员也被人们以“先生”尊称,演奏时多穿长衫、戴礼帽,衣冠端正,他们“不进偏房,只坐厅堂”,一般不与地位低下的吹鼓手为伍。与吹打班不同,此时丝竹班大多属于自娱性的业余组织,他们主要参与的活动是婚嫁和节庆民俗,而未见称其参与丧葬民俗事象的文献记载。1920 年代以前,道教班的演奏活动与丧葬及其它信仰民俗事象密不可分,与百姓的魂灵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出殡行葬与祭魂拜祖(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是最具代表性的事象,除此以外,在上文提到的诸如新屋“归土”、春节“拜斗”、生孩子“受箓过关”,年迈长者“念受生经”、患病遇灾时“打醮”等民俗事象,道教班亦常参与其中,但是他们绝少参与婚嫁民俗事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吹打班的职能范围最广,活跃于婚嫁、丧葬及其它节庆民俗事象中;道教班则服务于丧葬、斋醮、节庆民俗和信仰民俗等场合;丝竹班兴起较晚,与前两种班社不同的是,丝竹班成员此时多属业余组织,以自娱为主,偶尔也去应景助兴,参与到婚嫁和节庆民俗等活动中。这些班社在职能范围和应用场合方面不乏共性,却也不无原则性的区别,譬如:道教班无涉婚嫁,丝竹班不务丧葬。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诸班社内部的艺人自身在此时是各安本分、互不越位的,正如前文所述:唱道乐是出家道士,唱清音是在家俗子,堂名班不兼道教法事,道教班不兼打唱。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宗教活动及其他传统民俗活动都逐渐恢复,一些道士和民间艺人都重操旧业。但所不同的是,过去的“门图”制度此时已不复存在。当下,艺人逐渐已不再受到以往参与某一种音乐类型班社的局限,他们往往掌握多种乐器的演奏技术,组成不同音乐类型的班社,以服务于不同性质的民俗事象。这一现象在当下艺人群体中已经形成普遍之势。在田野考察中笔者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名片,如一张名片上同时印有“上海道教”、“中国上海江南丝竹协会上海分会委员”、“伴有军乐队”。可见,同一位艺人通过演奏不同的乐器和乐曲进入不同性质的班社,服务于各类民俗活动。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上海地区的传统民俗活动中。
笔者将20 世纪80 年代之后民俗活动中班社的组织方式称为“搭班”,指由班首(即“接到活的人”)起班,临时召集其他艺人搭班。这种“搭班”形式一般有口头“合同”,按照行业惯例,商定从业时间、内容和价格。“搭班”形式从活动区域上看,已然已不受区域空间的限制,突破了原来的“门图”区域范围局限,促使艺人们可以自由活跃于上海各个区域和角落,其足迹甚至踏入临近城市,如江苏苏州、昆山、镇江和浙江北部一带等;从组成人员关系上看,形成不断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艺人群体关系,突破了“门图”的一个个独立性的班社局限。在“搭班”时期,艺人群体兼职跨业成为一种风气,“搭班”的组合形式成为普遍之势。
二、历史场域
历史场域——“宏观层”,不仅有“历时”的“过程”,而且也表示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它是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时空力量。民俗音乐传统自然逃脱不了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历史场域的角度上看,民俗音乐传统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从作为“四旧”到作为“文化”的转变,这与政府对于民俗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策息息相关。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控制机制。可以说,政府从古至今从未对民俗放弃不管。著名学者顾炎武说:“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民俗的理解已然不是单纯指某种生活上的习俗惯例,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观风问俗以至正人心、厚风俗也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要政务。尤其是近代以来,民俗文化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由此,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其中并进行支配。虽然本质上都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采用的介入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政治文化环境赋予民俗音乐传统不同的意义,这成为促成民俗音乐传统发生变化的直接关联性的历史背景。
政府对民俗文化的政策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即20 世纪初实施的“改良风俗”、新中国时期的“破旧立新”以及20 世纪80 年代的“民俗复兴”。在前两个历史阶段中,在硬性政策和软性宣传双管齐下的作用力下,作为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上海人更是做出了表率作用,从市区至市郊都萌发了反对封建旧礼教和移风易俗的新观念。这正是政治变革上用以推翻封建婚丧礼制的核心,政府选择一些民俗事象作为“四旧”、“陋俗”、“旧俗”要消除的对象,这直接使得“门图”下的民俗事象及控制作用自然消解。直至“民俗复兴”时期,民俗音乐传统在整体上曾经被贴上“四旧”的标签给予破除,现在转而被认为“民族文化传统”加以保护,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候补遗产目录。民俗音乐传统在历史传承和不同空间中,其结构、表象、意义都会产生极为复杂的变化,当下这种新的“环境”“气候”的出现,为民俗事象这一“土壤”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搭班”这种新的班社组织方式。
三、音乐社会
音乐社会——“中观层”,是指在历史环境作用下的特定“社会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地理空间、物质空间,更主要的是社会空间及其关系,这个“社会”是具有音乐属性的,是与所研究的对象——音乐人事直接相关联的,是由该音乐人事的生存及其文化认同范畴所构成的。对于历经千百年的“民俗”,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当地民众所积淀而成的信仰和观念,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具有强烈的稳定性,但是其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如地方民众何以形成“以有西洋鼓吹为体面”的观念?众所周知的是,地方民众的观念和审美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影响民俗主体从而促使其发生、发展、变异。
上海民俗音乐传统是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和自给自足性,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从而造就了符合农业文明的文化存在方式和生存观念。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为家族的繁衍聚居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的农民社会生活中,血缘关系、宗法制度占着绝对支配的地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族田、祠堂和族谱,以血缘关系加以维系,与自然经济的稳固性、内向性、封闭性互为依存体。一族有族长,负责管理、监督本族生产和生活等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所强调的是团体主义,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关系僵硬而紧固。个人置身其中,常是身不由己,只能接受既有的安排。农民的家族观念和小农生产方式,使其活动地域小,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增多,农村社区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相对减弱,原先建立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逐步发生变化。人们走出了以村落和家族为单位的生活空间,进入了一个以经济组织为单位的新的生活空间。由此,原来的血缘社会逐渐向业缘社会演进,人们依靠智力、知识和技能在激烈的竞争下求得生存。
上海开辟中国第一个租界,从此大量西方人涌入上海,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如报纸、杂志都先后出现。媒体对中国传统的旧婚俗多加以抨击,而对西方的婚俗多予以宣传介绍,极大影响了上海地区传统婚嫁习俗。如1875 年1月4 日刊登的《论中西风俗之异》,1881 年9 月11 日刊登的《泰西风俗近古说》,1884 年6 月6 日刊登的《中西同俗古今不同礼说》
,1887 年2 月10 日又刊登了《原俗》等文。虽然普通中国人当时都不能接受和理解西式婚俗,但媒体的这种宣传和介绍,对于上海人慢慢了解西方婚俗,并逐渐接受西方婚俗,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传统婚俗的弊端,并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接受甚至效仿西方婚俗,如《申报》刊登《家庭日新会讨论婚嫁问题》一文记有:“次以上期所讨论未婚男女之交际上、请胡彬夏女士演讲美国风俗习惯、以资借鉴。”西方婚俗观念及仪式会直接导致具体用乐的变化,新式婚礼去除了传统婚嫁仪式中的礼人和乐人,婚礼进行过程中伴奏的乐器一律改用西洋乐,有大铜鼓、小铜鼓、黑管、大小号等。如今,上海市郊地区丧葬民俗活动中请道士做道场的习俗虽然已经复苏,其仪式程序基本按照传统仪式进行。然而,就笔者考察的情况而言,“如何用乐”或具体“用什么乐”,甚至“谁来奏乐”,人们并不再恪守某种规约,这是“搭班”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上海郊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区域逐渐向农村拓展,其表象形式是一个外化的物质建设过程,即城市各种建筑群、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表象形式的背后,其城市化过程,归根结底应是意识领域的演变,即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制度、社会心理等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城市性特点的过程,这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地方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个体素质、价值观念等逐步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无论是作为表象形式的城市空间的扩张,还是作为内在形态的意识领域的演变,其过程都导致由原本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转化为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农村的渗透为农民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改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
可见,民俗音乐传统如果不打算被人们现实的理解,而仅仅是一种绝对存在时,那它就不可能被人们以任何方式所接受。要想被接受,就必须适应现实中人们的感知结构、审美需求及生活欲望,乐于被后者“融合”。有了这种适应性,它就具备了“超越生成它的那个时代”的翅翼,为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民俗事象在不同时期的重复出现中,其具体内容自然会发生改变,不同时期,新的内容会不断加入到民俗事象中,在传统的民俗事象中植入了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音乐形式。
四、特定机制
在“历史场域”和“音乐社会”下,艺人群体的活动又遵循着怎样的“机制”运作的呢?特定机制——“微观层”,特指直接影响和促成及支撑“音乐人事”的机制,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活动或事件等因素。
其一,保图的撤销与移民的涌入打破了旧时的区域自治格局
上海处于吴越交汇之地,其民俗文化传统的形成直接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对上海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封建社会。换言之,上海民俗文化的传统,主要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自然经济和宗族关系,对“门图”制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搭班”制的“市场化关系”促使艺人群体之间形成明显的业缘关系的话,那么与“搭班”相比较,“门图”制从本质上看体现的是地缘关系和宗族关系的结合。首先我们分析地缘关系对“门图”制形成的支撑作用,在此不得不先提到上海地区旧时所实行的保图制度。在实行“市乡制”之前,上海地区使用“保图”制实现区域行政上的管理。“保图”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因为它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为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的状况,以户(家庭)为基本单位,一般以十进位的方式编查户口,具有亦兵亦民甚至亦工的性质,既可以对生产建设和人口户籍进行管理,又具有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统制民力征发徭役,收取赋税,教化居民等功能,民国时期把它概括为“管、教、养、卫”四大功能。因此可以说,“保图”制度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立基层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
具体来说,当时上海县以下实行乡、保、图行政制度,即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图的三级行政体系。清代上海县下共有217 个“图”,上海城厢(城,一般指城内;厢,指县城附近的地区)分别为: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图、十六图。图有“图董”,总管一图事务,以乡、保、图构成了清代上海社会基层组织体系。以下我们以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具体看一下旧时保图与“门图”制之间的关系。北蔡镇旧时按照乡、保、图建制,原为长人乡二十保的一图、十四图、二十四图和二十六图,直至民国。乡、保图制,地方有董事(乡董、经董、图董)掌理。在保图制度下,无论居住、迁移、婚姻情况、嫁娶活动、出生、死亡,都必须受当地的图董地保人员的监督,使之丝毫不敢所有越轨。
然而,在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断由一个个独立区域转化为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城市网络或城市带的过程,其最表象和最明显的特征是农田被一座座工业区、住宅群和各项公共设施所代替,原始的自然村落经撤并调整而形成现代化的住宅区。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改制打破了旧时的区域自治格局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导致了旧时封闭性自然聚落的不复存在。村落农田被征用,农居建筑被废,村民被动迁和重新安置。环境的改变和身份的转化,使原来因为群落形式而保留的民风民俗同样受到了冲击,逐渐被淡化或在年轻一代人中完全消失。
其二,“市场”机制导致了旧时“垄断”格局的消解
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以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法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社会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宗族是有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各聚村落或社区,皆有其原始名称。其名称甚为繁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乡”、“里”、“区”、“社”、“城”、“镇”、“铺”、“厢”、“集”、“图”、“都”、“保”、“总”、“村”、“庄”、“营”、“纤”、“甲”、“牌”、“户”。
以上海县褚家塘村为例,全村居民有姓氏51 个,褚姓153 人,陈姓30 人,张姓、王姓各12 人,陶姓、徐姓、吉姓各8 人,沈姓7 人,朱姓6 人,黄姓5 人,其余41 个姓均不满5 人(其中30 个姓每姓仅1 人)。20 世纪50 年代前所有户主均为褚性;陈姓村民因土地改革时分得没收、征收的褚家塘地主、富农房子,从邻村吴家塘迁入;其余姓(含若干名陈姓)均因婚姻迁入。在宗法社会中,人们从社会地位的确立,到财产的承继,祭祀的排序,直至婚嫁丧葬,均有严格且固定的规范。按宗族渊源,全村主姓褚姓有4 个“系”,每系10-20 户合有一个“老祖宗”,同系内一家有红白喜事,均邀其他户参加。同系内的红白喜事由同族内的艺人操办,其他图内成员不得逾越。由此不难看出,除了保图制外,宗法制度对于“门图”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族内人的婚丧喜事中的所有事象需一律听从族长的安排,某一族内的婚丧喜事活动由同族内的艺人负责,从这点上看,“门图”制下艺人与东家形成一种“垄断”的关系特征。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市场作为主导资源配置方式对传统家族结构进行了解构性的改变,在社会层面上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并促进了社会流动,打破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凝固性和封闭性,从而超越家族体系的社会联系与市场联系进一步增强。自然地从原来以宗族制度所维系的血缘性向以职业所维系的地域性方向发展。由血缘结合、地缘结合到业缘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性质的转变。因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业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其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逐步打破了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促进了宗族组织的分解。
20 世纪20 年代以来,旧时“门图”制下的各班社之间生意的不相往来、互不冲突的稳定局面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班社之间的活动在区域和人员两方面都出现交叉,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各班社之间的利益冲突。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上海各区县兴起了民间音乐团体的管理组织,如嘉定区于1927 年组织建立了“嘉定县音乐会”(于1947 年重新组建改名为“司乐工会”),此组织正是为了协调各班社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民间音乐组织团体进行组织和管理。此外,由于1900 年至1949 年嘉定区道教活动十分频繁,为了协调各班社之间的利益平衡,成立了道教协会,会员全都履行登记手续,颁发道徽,方可正式营业。宝山区的情形也十分相似,为了解决各鼓手班的生意和处理鼓手班间生意纠纷,宝山各乡镇的十多个“鼓手班”,100 多位艺人于1946 年3 月联合成立了“宝山县司乐业工会”。他们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汇集宝山吹鼓手外出活动情况,督促会员缴纳会费和鼓手班会费等。从这些民间团体组织的兴起及管理方式上看,旧时“门图”的宗族垄断性经营逐渐瓦解。
可见,“门图”得以形成,其地缘关系和宗族关系是两大支撑性要素,因此“门图”的丧失正是这两大关系的衰落所致。对于艺人群体的组织方式而言,具体表现在:其一,保图的撤销及移民的涌入打破了旧有的固定区域局限,艺人可以自由地活动于上海整个区域;其二,市场关系导致旧时宗族“垄断”性的消解,艺人可以跨出“宗族”的范围,而形成自由竞争的行业关系;此外,城市化进程自然引起了“农民市民化”,这一形势加促了民俗艺人群体的职业化倾向,由原本属于半农半艺性质的艺人逐渐转换为职业化的艺人群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靠这个活命的”。这些正导致了当下艺人群体“搭班”形式的形成。
结语
“门图”和“搭班”貌似只是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和职能边界问题,但其实牵连着很多更宏观和更深层的文化问题:譬如民俗音乐传统的延续与变迁(因为艺人是这一传统的实践者与传递者);又如民俗音乐生态的现状与前景(因为艺人班社的运作方式直接反映着社会的秩序、艺人的观念和民众的需求);再如音乐在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及信仰世界中所发挥的功能(因为艺人班社的活动状况——特别是其繁荣程度与职业化程度——可以表明艺人的社会地位、民俗事象的重要性及音乐的价值)。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可谓是“民俗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民俗模式而构成的活动过程”,是上海民俗音乐传统变迁的重要机制,一方面维持着民俗音乐传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又会发生适应性的改变,这种适应性的改变导致了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
注释:
[1]结构性地阐述为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参见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音乐研究》,2009 年第6 期。
[2]朱建明、谈敬德、陈正生:《上海郊区道教及其音乐研究》,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年。
[3]同[2]
[4]上海市奉贤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上海市奉贤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内部资料,1988。
[5]曹本冶:《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下)》,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
[6]上海市宝山区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宝山区乡镇卷》,内部资料,1989。
[7]张思莼:《松江的昆曲》,载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编:《松江文史》(第4 辑),内部资料,1983 年。
[8]王利生,闵行区祖传道士,12 岁入道,学习鼓、锣、板、铃等乐器,他父亲王菊祥有四个兄弟都从事道士。笔者经常与王利生QQ飞信联系,他QQ 签名中常出现“累”、“忙”等字眼,问其原因,是由于做道场太多,基本上每天都有,很辛苦。
[9]根据2011 年5 月3 日对王利生采访的录音进行整理。
[10]“搭班”一词来源于戏曲领域,是指民间戏班由班主起班、演员搭班制度。
[11]同[1]
[12]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八)[M],上海:国学整理社、世界书局,1936 年。
[13]同[1]
[14]《论中西风俗之异》,《申报》1875 年1 月4 日。
[15]《泰西风俗近古说》,《申报》1881 年9 月11 日。
[16]《中西同俗古今不同礼说》,《申报》1884 年6 月6 日。
[17]《原俗》,《申报》1887 年2 月10 日。
[18]《家庭日新会讨论婚嫁问题》,《申报》1920 年8 月10 日。
[19]有欢乐之意的曲目如《真是乐死人》不能在丧葬仪式中演奏,或有悲恸之意的曲目如《哭皇天》不能在婚嫁仪式中演奏。
[20]在田野考察中,多次有人主动告诉我,说做法事的这些人都不是真道士,是假的。
[21]王政:《中国古代民俗事象的模式》,《民俗研究》,1990年第2期。
[22]同[1]
[23]顾廷龙、马承源:《沪城风俗记》,上海:上海书报出版社,1991.年。
[24]人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
[25]冉绵惠:《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民国档案》,2007 年第2 期。
[26]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27]今为浦东新区大部、闵行区(原上海县)大部及奉贤区西北部。
[28]北蔡镇人民政府:《北蔡镇志》,内部资料,1993 年。
[29]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
[30]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1]上海市嘉定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上海市嘉定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内部资料,1988 年。
[32]上海市宝山区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宝山区乡镇卷》,内部资料,1989 年。
[33]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