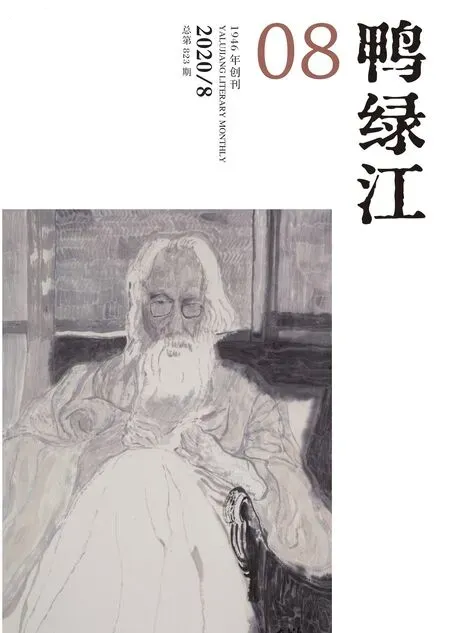起床一种
邵鸿权
涩!眼球实在是干涩,在上下眼皮的包裹之中,每次转动都能感受到阻力和疼痛。口腔也是,舌头像是掉到水泥粉里面挣扎的蚯蚓,绝望而无助。记得五六岁的时候,老家屋子周围时常能看到新建的工地,阴天的时候很朦胧,那是弥漫的水汽和雾;晴天的时候也朦胧,那是烟尘。于是我很早就懂这个,小学科学课上讲到凝华升华之类的章节时,对于我这样一个让老师厌憎的学生来说,那段时间的课程是难得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的。上课经常和别的小朋友开小差,讲空话。讲的闲话自然很没营养,现在想来真是后悔,浪费了我许多学习的时间,如果没人和我讲空话的话,凭我这样的脑子,重点大学都是有可能的,我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当然了,把责任推给他人是很不好的行为,虽然我不知道哪儿不好。而且我也不喜欢用推给他人这样的词语,因为在我看来,有些责任本来就应该算在他人的头上,无须推给。但这个世界貌似是很讲礼貌、很内敛的,绝不先说他人的责任之类的话语,谁说了,谁就是错了,谁就是不知反省。哪有这样的道理?不就是自我反省过了,梳理过了事件来龙去脉之后,才得出他人的责任这样的结论吗?我应该算是个很感性的人,努力回想这些年的种种委屈,眼睛一定会委屈地渗出几滴泪来,这样我眼球也就得救了!不过并没有得逞,可惜啊,骗这肉身的次数太多,这副骨架已经识破我的诡计了。
水,阴雨天,水雾蒸腾,空气很润泽很好闻,这时候蚯蚓就会出来,而且神出鬼没,我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脚的生物能够扭得各个地方都是,而且即便都如此丑陋,还丑得各有风味,有的是细长暗红色的,样貌相对文雅,动作也轻柔,总而言之扭得很有礼貌,是蚯蚓中的学生士子;有的就不行了,粗鄙得很,我并不是以貌取人的人,并不是看它那样的粗鄙样就觉得它粗鄙,而是它的动作确实很粗鄙。我才活到二十多岁,直到现在我都想不到什么东西能比它扭得还要大力,幅度还要大,试想一下,假如你平躺在地上,你可以一下扭出一个头朝地的九十度直角,再往后摔九十度倒下,拢共以头为原点扭出个一百八十来吗?那是蚯蚓里的流氓,黑得发紫,而且粗,皮肤上的环状也比学生士子来得明显,在前端还有一截透明的突出。小时候就觉得恶心丑陋。果然,评价这个动作还是要看评价者的状态,被评价的东西,没什么主导权,可怜得不行。也可能我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对于任何比赛都深恶痛绝吧,偶尔站在台上也时不时地会把自己和其他参赛者比作那条丑陋的黑蚯蚓。以至于哪怕仅仅是看比赛,都替上面那些黑蚯蚓羞耻,怎么可以这么样不知羞耻,丢人现眼呢!书上说它是益虫,要保护它,我倒是觉得那益虫啊,单是指斯文的蚯蚓的,这样的丑陋粗鄙,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话说到这儿显得我还是以貌取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连我这样的知识储备我也知道心理学的“首因效应”。第一印象嘛,但凡是人,那就逃不脱这个所谓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从何而来呢?自然是脸和体态。所以说嘛,我是很讨厌那些自称“不看脸”的人的,怎么可能不看!看人不看外貌看什么,还能看什么,这世界什么时候满大街都是哲学家了。说不看的人,据我的经验,要么是已经有了脸的,要么就是没有脸的。不过相对而言,前者比较多,毕竟若是后者,要说出这话来,还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想到这儿我又担心了,我算是前者还是后者。
喉头就更不用说了,燥得像陈年烟囱。此时我想,若是有鼻涕,那也是拯救。鼻涕也好歹是液体!有白的,有绿的,有黄的,还有红的,其他颜色暂时还没见过。我表哥小时候经常流鼻血的,我也撞见过几次,真是毫无预兆地突然流下来了,有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仰着头匆忙地掏口袋。那是暗红色的,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很壮的人,总是流。我一直以为这家伙吃得太好,想让他和我换一换,我到他家吃,他到我家吃,这样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两个人就均衡了,均衡的英文怎么说来着?上次考试刚考的。他还省得吃各种莫名其妙的中药,我也能因此沾光吃得白胖点。其实也不算是沾光,这叫乐于助人、共同进步、先富带动后富、先壮带动后壮。小时候骑在老爹身上去公园,我被套件花袄子,还被西洋人当作是黑猴子穿花衣,拍了许多照片,真是生气。当然这是我老爹告诉我的,我那时候小,还不记事,所以也断不来这事儿是真是假。不过我一直觉得,老爹讲述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自己的儿子(这点其实我存疑至今)被洋人说黑猴子,而在于在那个年代,被几个西洋人围着拍照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于是那几分钟,貌似就成了这个老农民一生的高光时刻,那时逢人就说:“知道吗,我儿?又黑又瘦的那个!黑猴!”对了,他也有个外号叫“猴子他爹”。用我们浙江方言叫还真是别具风味,音译成普通话叫“猴子赖爹”。
轻轻动一动脖子,我能明显感觉到颈椎骨由于转动而产生的摩擦,像是轴承上的润滑油挥发完之后出现的滞塞。我突然想到,之前在一本闲话杂志上看到运动之前要补充水分,保持关节的润滑,那时还觉得可笑,喝水和关节润滑有什么关系,现在真是恍然大悟。生活有很多伏笔,但发现伏笔只是一部分人的能力。它会静静等在那里,等着,等到最后的时间点;然后,它渐渐透明,那是宽宏大量的平静,不多等一秒,不早走一秒,也叫恰到好处的克制,现在人很少能这样。我如果是日剧中的角色的话,此时就会睁大眼睛,拍一下手,猛抬头望向正俯拍的镜头大喊一声“なるほど(原来如此)!”奈何我现在还没起床,若是旁边有个人在盯着我看的话,一定会认为我还没醒,虽然我的脑子里不知道已经想了多少事情了。思维就是这样的,比物质更极端更剧烈。我记得在白俄首府明斯克地铁二号线列宁广场站台里,我边上这群白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面无表情、身材瘦削的亚洲人会在听佛经;那时候我脑子里全部是如何帮助困难群众,想为人们做些什么减轻世间的苦难;思维在那瞬间成一瞬间佛,被加持无限大的力量。
虽说这睡觉被人盯的场面有点诡异,但我这样经验匮乏的人倒也是经历过的。那也还是小时候(果然是越小越有故事啊),睡觉没有关上房门和窗户,这样一来就通风透气,我是极其厌恶空气不流通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能力,就是透过不经意地闻到对方的呼吸,依据这个味道的好恶,来判决一个人。西洋人好像是很忌讳“判决”这个行为的;至于“如何判决西洋人忌讳判决他人”这个行为,我现在也很忌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接受这样的观念了,所以我也不知应该如何去judge 我的这样的转变。我是很怕这个东西的,不知怎么对付它,这东西是个洋货色,我从小就知道洋货色是难搞的,让我都畏畏缩缩地不敢说话。这样是更好,还是更烂?不知道,反正闭嘴就是了。尽管那次没关门窗的后果是早上起来之后,客厅密密麻麻的脏脚印,我的衣柜和床头柜都被翻乱了,但可喜的是,他们没翻乱我的书桌,也进不去别的房间(父母内间上锁的)。那次之后,父母反倒是比我还要感到后怕,我是不怕的,在我看来不弄乱书桌的窃贼是不用怕的。
我是很忌讳细菌、微生物这样的东西,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看不见,却存在。想象一下,细菌从别人的肺泡里一点点挤出来,顺着呼吸释放到面前的几平方米。听者仔细地听着讲者说话,放心地呼吸,把别人肺泡里挤压出来的微生物吸到自己的肺泡里,让它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气体进入我的身体。关于这一点,我是明确地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概念的。那是中学科学老师,她那时靠在我的桌子上提问我的同桌,正巧我的同桌站起来就打了一个喷嚏,她立马用课本挡住了自己的脸,露出了两只突然变大的眼睛,后退两步。那瞬间,我心底先后抑或同时升起了许多情绪,不好形容,我只能尽可能描述。像是丝带,彩色的超长丝带,彩色的长丝带在有规律地流动,像有生命一样,但是随着那个喷嚏猛地抽动了一下。它就像我,不,它就是我,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向内旋转的彩色同心圆突然崩溃,轨迹变成无规律,黑暗中的无数立体棱角。
要起床了啊!想张嘴打个哈欠,上下嘴皮一动就传来撕裂的痛感。原来已经干燥到了这种程度了,嘴唇都结起来了。猛地撑开眼皮,白俄晚冬的早晨,天是亮得很早的,透过灰色的窗帘布漏进来几束小巧有力的光柱。啊,光啊,圣经里有这么一句:“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从此神睡懒觉就不寂寞了。但是,光柱怎么这么混浊,光柱里一颗颗的都是灰尘吗?我是呼吸了一晚上的灰尘,所以会这么干燥,也一定是由于它被吸进了我的身体,粘在我的鼻腔、呼吸道、气管、支气管、肺泡里吸收我体内的水分!
看着一个个小世界在光柱里旋转飘浮,很自信地从一道光柱跳跃到另一道。
闭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