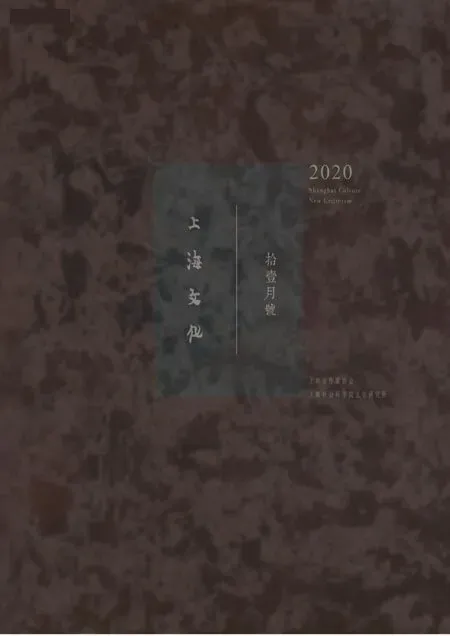在蓝色与空无中:伊夫·克莱因的多重身份建构
张 浩
1.引 言
1962年6月的一天,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巴黎的一处寓所。一个月前,他刚刚过完自己三十四岁的生日。虽然其艺术生涯仅延续了八年,但这足以让他席卷整个欧洲艺术界。关于他的离世,迥异的评价出现在当时大西洋两岸的媒体上。一边是法国艺评人皮埃尔·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克莱因坚定的支持者)断言“他的传奇只会不断生长”,法国《世界报》的讣告称他为“当代巴黎前卫画家中最汹涌不安,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另一边的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和评论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则指出“他不如几位最顶尖的美国年轻艺术家出色,但他仍是优秀的二流艺术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克莱因数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赞美与怀疑的声音也一直伴其左右。正如学者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2007年的文章《克莱因的现实性》中所提醒的,“今天的克莱因与1960年代的克莱因并不相同”。时隔多年,现在的情况不但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更加复杂。除了人们熟知的艺术作品,克莱因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私人日记和书信,相册和影片,以及大量的发言稿、展览声明和文章,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全部作品创作于1954年至1962年之间,即艺术家二十六岁至三十四岁之间。如果遵循克莱因1959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的著名宣言,他的绘画只是他的艺术的“灰烬”,那么他的其他艺术创作是什么?能够凝聚为灰烬的艺术又是什么?是否可以作为扩展领域的艺术从而将他更大范围的实践(文字、展览、表演甚至体育运动)都纳入在内?克莱因处理艺术与生活的方式也导致诸多的解释问题,使得很难用简化的前后一致逻辑去理解其多元策略。如何处理克莱因刻意修订的过往言辞,特别是涉及个人传记的成分?如何看待克莱因管理和传播个人形象时的姿态表现?此类问题不胜枚举。笔者认为,面对把身份作为美学项目加以塑造的克莱因,拆解构成其艺术与生活的悖论性元素,也许可以为重建其在当下的意义提供一定的清晰度。
2.成为画家
伊夫·克莱因1928年4月28日出生于法国尼斯,父母均为画家。父亲的绘画风格(海滨景色或风景中的马)比较具象,母亲的绘画(形式和色彩构成)则更接近抽象。年轻时的克莱因对学校课程没多少兴趣,他在期末考试中未能通过大学申请。从那时起,他便决定不接受任何学校教育。对他来说,这将会是一次解放。此时柔道成为他的新兴趣,1952年在姑姑资助下,他远赴东京学习柔道。也许应该更清楚地强调,根据艺术家自述,克莱因1946年在父母的影响下开始绘画,即便这一开端充满了愤怒(对父母因职业而忽视他而深感不满)。直到大约一年后的一天,克莱因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这样做)?”他的解释是“生活中‘为什么不’是主宰一切的决定,这是命运”。他遵循这一灵光乍现的启示,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想法的画家,他首先将质疑的矛头指向父辈们最为倚重的绘画元素——线条与色彩。“普通绘画是众所周知的监狱窗口,其线条、轮廓、形式和组成均由栏杆确定。这些线条具体化了我们的注定死亡,我们的情感生活,我们的理性甚至我们的灵性。它们是我们的心理界限,我们历史的过去,我们的骨骼框架;它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才能和我们的创造物。”在克莱因看来,绘画中的线条被具象化为监狱窗口栏杆,体现了世俗的秩序,将一切创造力和生命力都禁锢起来。克莱因希望扮演挑衅性的角色,越过边界,与这些弱点做抗争。而色彩就像一个“感性的纯粹空间”,让他拥有“完全自由”的感觉,这些吸引他创作出单色表面去观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绝对中可见的东西”。
另外克莱因还讨论到如何识别“画家”这一身份。他自称,“我将成为‘画家’。人们会说我:那是‘画家’。我会觉得自己是‘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正是因为我不画画,或者至少表面上没有画。我作为画家‘存在’的事实将是当今最‘令人敬畏的’绘画作品”。克莱因在此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作品概念,即作为画家存在本身就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更准确地说,这种存在的事实不是通过具体实在的、可以看到并触摸到的作品来确定,而是通过一个宣言或一个口号,首先自我“封立”而成的。画家,在克莱因这里,作为一种身份,主要是被自我赋予的,在创作经历中得以显现。按照这种被大幅扩展了的作品标准,便不难理解他将艺术融入生活的尝试。作品似乎只是导向更大目标的方法,某些超越艺术的东西才是他所念兹在兹的,比如自由。“艺术是完全的自由,它是生命;一旦有任何形式的禁锢,对自由的冒犯,生命就会随着禁锢程度而成比例地减少。”克莱因将自由视为艺术自身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而他对“作品”的定义恰恰也与艺术的自由本质构成呼应。
3.为何选择单色画和蓝色
克莱因短暂的人生也许是他基本上专注于蓝色的根本原因,因为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供其发展自己的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出发点仅仅是蓝色。即使在色彩上,克莱因仍然具有多样性。应该强调的是,他的第一个单色画实际上是彩色的。蓝色,金色和粉红色成为克莱因的三种基本色。在他脑海中,单色绘画中的这三种基本颜色“是世界的普遍解释原则”。在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这三种颜色的等效性,“蓝色,金色和粉红色具有相同的性质。在这三种状态层面的任何互换都是可靠的。”另一方面,色彩沉浸在巨大的感性当中,而纯粹的感性对于克莱因而言是相当高频的术语。欢快的色彩,雄伟、低俗或甜美的色彩,暴力和悲伤的色彩。将不同的色彩与种种情感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想法。“对我来说,色彩的每一个细微差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个体,这一存在不仅与基本色来自同一种族,而且绝对拥有个性和不同的灵魂。”




4.空间的艺术家


5.讲故事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这堪称一篇精彩的回忆文章,充满戏剧性元素。一切似乎都是合理的。把这一版本与本文第三章提到的版本进行比较,故事(不一定是真相)也许会呈现得更为完整。第一个版本通过巴什拉的作品,注重色彩与情感,空间与灵魂的联系。第二个版本则是对选择过程的补充,主要考虑观众的沉思,服务于更高层次的艺术家的目的,即纯粹的感性。对于这两种叙述,笔者无法断定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也许两者都是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克莱因反复使用的策略,符合他自相矛盾且富含表演力的人物形象设定。同样的策略在日常生活层面也不乏表现,比如克莱因在法国获得的柔道头衔,其实归功于姨妈的来信与适当的幕后操作。

需要注意到,根据学者伊夫-阿兰·布瓦的考察,将整个画布涂成蓝色,克莱因并非持有这种想法的第一人。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曾深入考虑蓝色的问题,可以说克莱因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位前辈的梦想。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通过延展画布直至占据整个墙体,也达到类似的效果。然而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克莱因在画出蓝色单色画之前曾看到过纽曼的作品。
6.历史前卫与新前卫之争中的克莱因
涉及到单色画的发明权,克莱因曾浓墨重彩地宣传自己的独创性。在化学家的帮助下,国际克莱因蓝(International Klein Blue,简写为IKB)也顺利成为克莱因名下的专利。对于来自1920年代俄罗斯至上主义艺术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的影响,克莱因坚称从未意识到。选择性的视而不见,配合对发明权的独占,除了意欲完全隔断与现代主义绘画传统之间的关联,更意味着对自我神话的强烈欲求。诚然,好名声不容错过,即便需要一些夸张,需要施加表演的魅力,这些都发生在克莱因身上。克莱因早熟的复杂性,也使得他作为二战后艺术界的关键人物,被卷入了关于历史前卫和新前卫关系的长期争论中。




7.结 语


Nuit
Banai
,Yves
Klein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 2014,pp
. 171-172.❷Yve
-Alain
Bois
, “Klein
's
Relevance
for
Today
”,October
,Vol
. 119 (Winter
, 2007),p
. 76.❸Yves
Klein
,Overcoming
the
Problems
of
Art
:The
Writings
of
Yves
Klein
,ed
.Klaus
Ottmann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 2007,p
.X
.❹Ibid
.,pp
. 82-83.❺Ibid
.,p
.X
.❻Ibid
.,p
. 45.❼Ibid
.,p
.XV
.❽Olivier
Berggruen
,Max
Hollein
and
Ingrid
Pfeiffer
,Yves
Klein
,Ostfildern
:Hatje
Cantz
, 2004,p
. 48.❾Ibid
.,p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