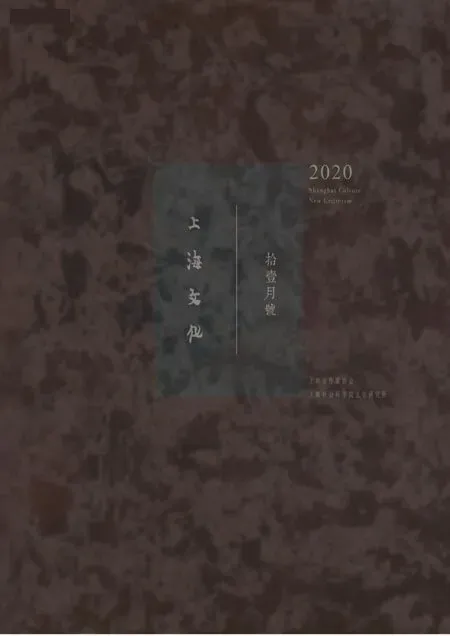日夜无隙,或神话与小说术李宏伟的《灰衣简吏》
吴雅凌
1
我一直对《国王与抒情诗》特别地感觉亲近。
2050年,诗人死在帝国的祭坛上。人类实现了noosphere-“意识共同体”,可也还有信息游击一如既往扎根于“碎片式反抗的虚妄”。2050不再是科幻小说的遥远年份,那么古老而近在眼前的,缪斯养育王者,大卫吟唱诗篇,理想国下驱逐令,萨桑国讲不完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国王与诗大约是世界生成以外讲述最多次的神话。
而小说中有一股诗的苍茫气息在帝国图景之外。
生养和埋葬诗人的草原没有植入“意识晶体”,是国王无法越界的疆土。长夜策马进草原,有星,有酒,有火把,有人影。醉里闯鬼城,九阶墓地,九回循环唱和的丧歌。每个有心的读者在初生的阳光下都见证了那一场献祭仪式。如诗人的诗中,心爱的人或事物的原初之美永驻在时间河的彼岸,而鞑靼骑士再也回不去了——“静默地,对着随时可能湮灭的绝对真理,从胸腔里拿出一片草原那样,吟唱死亡的初生”。
葬礼是死而复生的寄托仪式。诗人为何自我献祭?一支枯梅在其案头不意绽放,仿佛有光的电击,是要传递什么消息?小说似乎将人类命运的秘密筹码悬置于某种选择性未来。
直到这个春天我在《灰衣简史》中读到“起初”。
某个看似和其他春天没有两样的下午,我从十四天穴居走进太阳光下,恍惚听见卡夫卡,“世界之音变得沉寂和稀少”(《误入世界》)。是因为这样吗?我们在“庞大的为人类托底”的文学经验里一次次审视诗人之死的分量,缓慢地感受更缓慢地消化某种宇宙论秩序带来的空旷和悲怆。
2
《灰衣简史》假设不止一次,又一次,创世者“来到/创造”伊甸园。
最初的人早被赶出去了,园中无人的踪影。他以老人的模样出场,亲自为园中的各样活物命名。从前他放任天真的亚当随心所欲,这一回,“老人不轻易说出名字”,一切进展审慎节制。
有一天,他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像蛇的事故,他看见自己的影子。作为有限意义的一,园中本来没有从真身分离出的影子:
每一样东西都是它的自身也是它的普遍,是它的抽象也是它的具象……它们就算有影子,也不在它们之外,也不在地上显形,它们是自身又是自身的影子。(《灰衣简史》)
但该来的总会来,全在他的运筹中。最初的人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不该出现的影子不停出现,从一到九个,恰如其分地影射人世之多。
影子被打发出园子,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创世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影子来处不是别的,是园子外头的人间世,亚当的孩子们的意识共同体。人出园子之后的种种思虑反向渗透进园子,而最幽暗的一种指向那隐匿的,沉默的,数千年来被杀死不止一回却总绕不过去的……影子是人追问神的形状。
被赶出去的影子名叫蛇,或梅菲斯托——“最失败的,莫过于园中那次目睹;最著名的,莫过于对博士的那番协助。” 小说中统称灰衣人。他们在大地上收成颇丰。在彼得·史勒密尔和浮士德博士之外,我们可以把不分成败的暗经验清单无限扯远,奥德修斯海上听闻塞壬,苏格拉底申辩说起精灵,雅各夜里摔跤,耶稣旷野受试探,乃至一切先知预言各种天使显灵……光脚的,或带翅的;生来欠缺的,或致人死命的……直到两个明明有名字却形同无名的人苦等不会来的戈多先生。
3
尽管园中老人数番呵斥,让影子“想清楚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但被赶出园子的灰衣人“不清楚事情的原委与去向”。他们还想要重返园子,把收割人类的影子当成最严肃的游戏任务。他们本是有魔性的属灵一族,出使是天职。既然会错了意,所传消息一到九,九归一,循环往复之下愈发含糊了。
难怪小说中被称为“本尊”的出卖影子的“我”和“你”总在困顿中——但因果反之亦然不是吗?人类甚至不如灰衣人了解自己的影子。那平日被看轻的甚至看也不看的影子,
“趋于无限薄,趋于无限轻”,何以在交易的天平上抵消本尊的全部生命重量?乃至无限度地加砝码,让欲望或梦成真,让巨兽得征服,让灵与肉被托举,拥抱“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马太福音》)?
是困顿中才不断追问啊,不断用X光扫描人世空间的存在法则。和灰衣人交易的王把自己囚禁在玻璃宫殿里,痴迷地窥伺一头被囚禁的老虎。如套中的套。那丛林的王被X光追杀无处遁形,就像本尊在太阳光下暴露出卖影子的真相。他想赎回影子,为此恋上暗经验,把认知黑暗当成最严肃的游戏任务。
依据别的古代版本,黑夜生出一群暗物质,其中一种叫人的命运,而命运有个姐妹叫不和,不和又生下诱惑……这个影子家族在宇宙起源秩序中施行暗经验,谁也替代不了,历代的王只能服从(《神谱》)。
稍后的炼金传统发展出一种“黑功术”(l'?uvre au noir),如尤瑟纳尔的同名小说,苦炼者倾尽毕生心血,不断追问——那些个无比痛苦的锻造,溶解,分离……直到腐朽的尽头,提炼出一点自我的纯黑,或灵魂形态的暗物质。
而这也仅仅是初阶段。从来点石成金的少,走火入魔的多。像爱伦·坡同名的那只猫,没有活活被砌进墙中的黑,先白了,透明看不见了……
4
眼睛与纯黑的深渊相抵(《苦炼》)。这是尤瑟纳尔笔下的主人公在正午时分获得的神启。在一只放大镜中无限逼近自己的眼睛,那里头有整个世界的形状,有一的认知和多的观念,有小宇宙和大宇宙的相互辉映。眼睛看见光。在摆脱一切惯常视角时,眼睛看见黑暗。
《灰衣简史》以交易之说区分看见的不同阶段。一开始,“我”最舍不得出卖的是眼睛:“谁能生生将世界从自己眼中挖出?”直到最后一刻方才报出最高价。灰衣人没有接受“我”对眼睛的报价,而同意“你”用眼睛换回影子撤销交易——“我”在交易的开端尚未真正地见识光,“你”在交易的尽头已然看见黑暗,承担起眼睛与深渊相抵的代价:
那黑暗,那由影子开启的黑暗,要求我在大地上走来走去,漂泊为生,乞讨为食。不要问我既然在黑暗里,还有什么必要四处行走,告诉你吧,这才是黑暗应当有的含义。(《灰衣简史》)
如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暗经验,在见识过“真相和真相背面的样子”之后,自行刺瞎了眼。那是人眼对上“上帝之眼”,是老虎最后一次跃起,“发出倾尽黑暗之所有的吼声”——
影子,影子,谁不是影子?(《灰衣简史》)
如果用柏拉图那个古典的比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第几重影子?(《国王与抒情诗》)
让人玩味的互文。又如《暗经验》被退稿的诗人说真话:“沉默的眼睛只看到一双更大的更沉默的眼睛在洞穴的尽头注视着……”
总是这样,迷宫外是更大的迷宫,做梦的人在别人梦中,诗人和他诗中的骑士一样,无数次渡时间河,找不到回去的路。几部小说中都提到《环形废墟》,博尔赫斯是这样为小说开场的:“纯黑的夜里没有人看见他上岸……”
5
于是有诗人绝笔:“就此决断。保重。”
三十年前,诗人和国王同系帝国文化构想的发起者规划者。某次夜饮,理想国的烟花点燃又散尽,一个醉了,一个还醒着,分歧就此显露,从来如此。
醉意朦胧中,诗人畅言诗歌永在;他甚至断言,只要诗歌在,国王的商业帝国终将是沙上帝国,人类幻影。国王当时并无醉态,也不可能被如此话语激起怒火……他淡然反问:“谁来保证诗歌永在?”言辞间一派索然。(《国王与抒情诗》)
那夜过后,诗人与国王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不朽路。国王缔造了功名显赫的文化帝国。诗人远离喧嚣,过一种去政治性的自在生活,写了长诗《鞑靼骑士》,得了标志性的文学奖。
直到他发现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他的诗作不过是帝国文化工业的实验产品,甚至他对诗的理解没能跳脱国王的预先设计。三十年来,国王以“机械般的精确与冷酷”,在诗人身上试验一种帝国策略,一项类似暗经验局或灰衣人的秘密操作。通过碎片化无效重复经典文学模式,不为人察觉地摧毁诗本身。作为某种暗经验理论,诗或“抒情性是上帝驱逐亚当、夏娃时铭刻在他们身上的诅咒”。
这个发现要了诗人的命。
只是,假设帝国阴谋不在,诗人与国王有可能就此决断吗?诗的抒情性有可能真正挣脱政治性吗?我想到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论断:“一个时代往往在那些受其影响最小、离它最远、因而也受难最深的人身上打下最清楚的烙印。”
6
诗人以死捍卫文学的尊严,这样的决断让人肃然起敬。不过,有世界图景志向的小说总是还想往前多迈进一步。《国王与抒情诗》重提古老的追问:“凡人如何不死”,把诗人与国王的紧张关系指向帝国继承人的政治哲学问题。
“凡人如何不死”是永在的哲学拷问,和多数哲学命题一样,其意义大抵首先在追问本身。小说中的国王有政治家的气度魄力,或如追随者所言,某种“人类之神的气质”。依据其战略部署,文化帝国终将消除文字差别,回归“巴别塔之前的神话状态”,为此要消除文学所代表的个体诗性。面对永生拷问,国王一如既往着眼于历史终结性质的落实:“不追求个体生命的永在,而是取消死亡对人类的意义。”——取消死亡对人类的意义,不是形同取缔哲学吗?
而诗人针锋相对,以“仪式化的祭祀性的死亡”,加深后来人“对抒情性的理解”。
在必然紧张的撕扯中,新国王显得不乏自信和坚定,“这种撕扯完全可以归拢成一股合力,而合力抵达的,将超越诗人的意图与国王的意图”。这是写下《面对死亡的十二种抒情》的人应有的信心和坚定,与其说他为诗人所代表的抒情性申辩,不如说他宣告了某种哲学的新抒情,某种“对待世界对待自我的方式”,像那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不再追问,而是凭借真诚“断定一切皆善”,幸福就此成为信条(《西绪福斯神话》)——“重要的不是在那之后,而是在那之前。”
几部小说不同程度地关注继承人问题。《暗经验》中的张力在暗经验局被提拔成为诗歌部负责人。《灰衣简史》的戏剧导演替换商人与灰衣人交易。他们天生有暗经验直觉,有“浑身勃发的欲望”,有“饱满健壮,吸附黑暗,迅速增加浓度的影子”。他们胆敢做不平等交易,也就有资格成就超凡事业。他们是历史偶然中的优秀者。他们看见我们会说:“通过那些仍旧浸泡在日常生活流中庸常的脸,我才醒悟自己已经占得先机。”他们对抒情性的深刻理解已经通过暗经验局的考核,接下来是帝国志向与个人心性的抵牾,更艰难也更黑暗的试炼。
一种非政治天性能否为帝国政治解难?一种放弃追问的现代哲学抒情有可能实现老国王在终场预言的“帝国的抒情”吗?在时间河的此岸,一切差别源自又归向善恶树的神话悖论。
7
小说中还有一类物和人,如园中天然缤纷,不融入暗经验,与灰衣人的灰无缘。
蓝色气球和棕朱雀,蝴蝶的白翅膀,石榴红透的滋味,海棠开又败,少年的鸟哨有淡玫瑰色纹样,眼珠以两滴草汁点活,日光下的世界和世界的影子……
还有女人们,几部小说中几无例外。是应了“世代为敌”(《创世记》)的咒语吗?她们不受诱惑,灰衣人对她们的影子未必有兴趣。她们深情,会心痛地嚎啕大哭,为被囚困的老虎哭,为老虎面前的羊羔哭。她们幼稚,但“幼稚自有无法推拒的生长的力量”。她们脆弱又强大,哀而不伤,为亲人唱挽歌,与从前郑重道别。她们敦促人们问自己:“她们的心所容纳、眼所朝向,是不是有什么早就彻底从你的灵魂和世界消失?”
当她们有信心时,就像“羊羔的柔弱散发出的力量如此持续、绵延、强大,让老虎相形失色”。好比那对母女行奇迹,单凭对老人的信任走进园子,反转了人类保全影子方能进天堂的认知,也颠覆了灰衣人在大地上的操作程序。好比义人的母亲,纯朴不过的正义常识,却是何等温和坚定的洞见!
犹如另一种继承人统绪。从在路上寻找园子的母亲,到自在追逐白蝴蝶的小女孩。从传授何为无价之宝的母亲,到出让影子赈灾的义人。灰衣人两次无偿帮助义人,先后救义人的父亲母亲,以此实现自我救赎。义人去世前苦寻他三年,留下一句话:“不要躲起来,要和把影子交给你的人一起经历人世。”是提醒,是邀请,是一句解咒语,如诗人葬礼上族人反复吟唱的灵歌:“回到光那里吧!”
这样从末尾到起初,在倒叙的世界起源神话中,灰衣人获得名曰“他”的第三位格。
8
小说术的探究和讲究,一端是虚实黑白,是尺度界限,是隐忍和审慎,另一端是开放的诗性可能,是勇于冒险。作为文学炼金术的一种配方形成努力,在这里,诗与小说的撕扯也想要“归拢成一股合力”,以此抵达超越诗或小说的文学意图。
《国王与抒情诗》含“本事”和“提纲”两部,前小说,后诗歌,相互唱和。“本事”是故事本身,也是叙事技艺。小说共四十五节,每节以单个的字起头,并列出该字的多种本义或引申义。如首节“思”,末节“数”,“想念”的尽头连接上“责备”,委实有趣。前部穿插神话叙事诗《鞑靼骑士》,后部是哀悼诗和诗人的《面对死亡的十二次抒情》,恰对两种最古老的诗歌形式做出身体力行的回望观照。
《暗经验》有读者视角和作者视角的区别和纠结。开场分析文学经典,结尾改写《黑猫》,一千多个“黑”字扑面而来,犹如惊心动魄的逆转。同样是书中有书的迷宫结构。暗经验局新人审稿中,《宠人》和《身体繁史》都涉及洞穴主题,前小说,后诗歌,遥相呼应。传记小说《命运与抗争》作为某种暗经验主旋律,其创作本身进一步影射洞穴主题:小说第三部分采用新闻纪实写法,本是作者心目中的成败关键,用来“平衡整部小说,撑起结构和空间”,最终被文化帝国国王批示全文删除。——是偶然吗?《灰衣简史》第三部分“旁白”弥补了这一让人难以释怀的遗憾:“如实得如同虚构”。
《灰衣简史》表现出更整全更庞大的谋篇志向。为了上演一出影子交易的戏,导演本人出卖了自己的影子。而这只是开头。戏中戏的复式结构,从我到你,从你到他,从末尾回到起初,从外篇映照内篇,从戏剧走向神话。有独白,有自白,有旁白,有对白。蓝气球和鸟的幕起幕落,循环往复,没有间隙。第五部借世界生成神话搭建文学空间构造,犹如迄今诸小说的总纲。开篇匠人造木鸟,终场创世,不但“构造”篇是倒叙,整部灰衣简史也可以倒过来读,反复地读,犹如古代循环史诗的一种提示。
9
《灰衣简史》的开场戏:“那么,推开这扇门之前,我想再问一句”……
就在阅读的结尾接上写作的开端吧。阅读如写作是重复推门的动作,哪怕我们以为推开的是同一扇门,我们无法预知每一次门后的光景,而这几乎是最好的期盼了。小说中的国王把重复用作摧毁文学的手段,但重复也有可能是死里复生的仪式,差别也许就在于那一点牺牲。问题是我们要拿什么献祭。因为文学是自带魔性的啊,好比从一到九的灰衣人,在“黑白之间,非黑非白,可黑可白”……在推开这扇门之前,我们也要忐忑不安地自问这一句。哪怕日夜无隙,而阅读者如书写者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