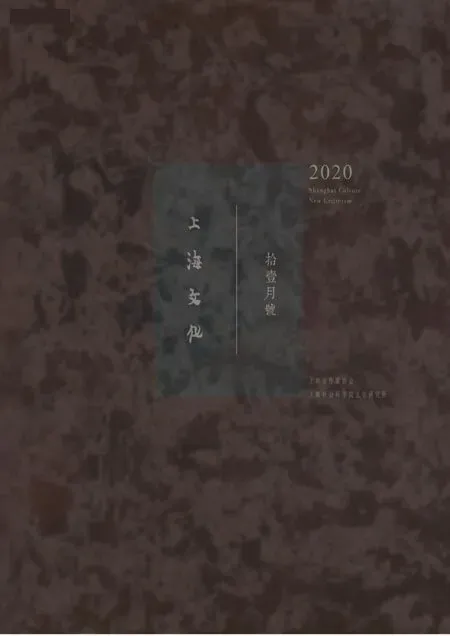“退后半步”、交界与不及物
评张楚《过香河》
刘卫东
《过香河》中,弥散着一种“张楚气质”,即“当下”与“命运”不断互否、激发产生的氤氲。张楚展示的是市井细民、引车卖浆、茶余饭后,对接生活“根部”,但背景却是旷远、模糊,有着淡淡的虚无。“自然主义”与“诗化”,看似不相干的两种审美风格,集中于张楚作品,也成为他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符号。从这个角度说,张楚是“退后半步”的写作。张楚的个性特征很明显,因此很多研究者对他的关注,都集中于阐释个中原委。写“现实”而保持某种疏离感,并不能轻易做到,也绝非刻意所能为;更多时候,“现实真实性”需求强劲,挤压作者,令其叨陪末座、无所适从。相对而言,张楚之于“文本现实”,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形成了独到处理方式。
一
张楚建立了一个“县城人物志”,将身边人喜乐悲欢,逐个展现。据资料,他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唐山滦南县从事税务工作,业余写小说。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那里,有大量人物、故事——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张楚写作的主要资源。这种貌似古老的“记录人”模式,已经并不常见,因此,在当前作家普遍陷入“写什么”焦虑状况下,张楚却能够拿出原创性很强的故事,似乎还源源不断。不一定所有故事都来源于观察、听闻,但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张楚稳定发挥的“保证”。不过,问题也可能存在于此: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如同此前的“三言二拍”,盖因“传奇”性,或曰耸人听闻。“猛料”跌宕起伏,戏剧性强,具有命运感,但毕竟是“故事”,不是“文学”。对张楚来说,如何对一个“粗糙”材料加工,使之成为艺术品,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以著名事件改编的作品,大多因为公众过于“熟悉”,不尽如人意。而张楚更关注小人物“长时段”命运浮沉,不求一事之形似,而求整体之神似,故而,绕开了暗礁。
可以说,《过香河》基本承继了张楚一贯风格。小说以“我”为观察点,借“云落”县城与北京之间“活动”的人物蜜蜜,用“浮世绘”笔法,寄寓了多种个人情思、生命感喟。就人物来说,蜜蜜很“有戏”:大学时酷爱音乐,组建乐队,吉他弹得很棒;后来在北京开办公司,装作“发达”;又转回云落,承办大型文化活动,盛极一时;最后经营失败,公司倒闭。他始终徘徊在光与影的交界,有时随波逐流、俗不可耐,有时又带有前乐队歌手的艺术气息,放荡不羁。蜜蜜在作品中不是思考者,并不输出“思想”,他仅是作者用来观察的工具,或者说,他是由张楚派来,穿梭于各个阶层,携带了众多问题的“小白鼠”。他如同盛夏的植物,叶绿素充盈,荷尔蒙横溢,动感热烈,呼应着当前生活的各类“问号”。他不断“折腾”,包括换女友,都是时代“症候”反应,而其遭遇及命运,也隐含了某种“趋向”。虽说文学作品可以独立常青,但终究难以逃脱隐喻之网。作品描述“我”与蜜蜜一起看电视,看到纪录片中一只老鼠被毒蛇追杀,“那只吓破了胆的老鼠上蹿下跳,东躲西藏,每每险象环生处又能安然脱身,让人觉得仿佛是上帝的那只手在庇护着它,看着看着蜜蜜转过头,看着我。他的眼睛眨了眨,说,舅,我就是这只耗子”。“死不了的皮耗子”,正是蜜蜜这个小人物的自我鉴定。这段描述颇有跳脱之感,也是作品中少有的“操控”读者桥段,正因如此,才显出张楚“带入”的苦心孤诣。事实上,蜜蜜的各项选择不算被动,他本身缺乏必要经商能力,才是失败的关键——“死不了的皮耗子”便体现他对自己认知的错位。蜜蜜其人及其命运,实际是“装置”本身的必然结果:他可能“成功”吗?
同样,与张楚此前作品相似,《过香河》并不着重打造人物,而是把力量用在人物与环境之间,试图描述一种“结构”。《过香河》中,人物的活动分成两个区间:一个是“现实区间”;一个是“虚拟区间”。前者采取叙述人“我”的视角,基于亲自见闻,因此细节饱满、穷形尽相;而后者则以“听说”、“传闻”为主,有“戏剧化”、“不连贯”之感。一种“复调”对照因此产生:现实与虚拟轮番出现,共同作用于人物、事件,类似手风琴,形成了“伸缩性”叙事节奏。张楚是一位演奏家,对此得心应手,收放自如。《过香河》开端是“我”和蜜蜜开车过香河,“我”一面讲述“现实区间”的蜜蜜,一面回溯“过往”,回忆小时候的蜜蜜,把二者打散、组装在一起。由此,“他往地上啐了口痰,又擤了把鼻涕,抬脚在鞋帮处抹了两抹”的蜜蜜,与“长大后只考上了普通本科,学的机电,却天天打篮球,要不就抱着吉他唱民谣,还组了支乐队,乐队的名字叫‘夏天的云梯’。据说毕业前他们举办过一场校园演唱会。我从没见过他在舞台上的样子,按照他的说法,那至少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的蜜蜜,交替出现,互相映衬,形成完整“拼图”。类似“虚实互参”的叙事方式,较为常用,《孔乙己》作为经典,有精彩演绎。《孔乙己》中,只写了“小伙计”看到的孔乙己,而孔其他活动,则交给“虚拟”空间,由“听说”补充。至于“听说”,无法判断真伪,却留给“我”评判的余地。这种“虚”,就是“退后半步”,卸下了“实”的力道。正如《孔乙己》结尾,充满了不确定,“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之死,非常确定,却被表述得模棱两可。《过香河》中,叙述人具有更大权力,不仅观察主人公,还参与叙事,使得作品在现实/虚拟之间游弋,建构起独特的“张楚气质”。
《过香河》的“退后半步”,还在于张楚“向前半步”,以自身情感投射人物命运。作品中,“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故事,需要有一个比例;不同作家,有不同处理方法。《孔乙己》中,“我”就极少参与,恪守观察视角,零度叙事。鲁迅发表时特意声明并非“人身攻击”,“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污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怜可叹的事”。鲁迅对笔下人物之冷峻,可见一斑。张楚处理小说中人物时,往往带有一定温度,而“我”的设定,也与自己身份互文,增加代入感。这些特质,在《野草在歌唱》、《曲别针》、《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关于《过香河》中“我”的问题,下文将详述,此处不赘。《野草在歌唱》是作者潜自传,堪称小城文艺男标本:一个在日常中困窘的个体,仰望星空,热爱文学,寻找同路人;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痛并骄傲着。文学这个似乎被摒弃的“力量”,在张楚这里却十分招摇,这是他个人“私货”,但正由此,张楚与现实、小说之间达成某种“黏着”。张楚“向前半步”,并不是让现实更清晰,而是让自己拥抱现实时,更为有力。可以说,文艺浪漫与小人物命运偃蹇,构成张楚小说之两极,稍加“点染”,便成风景。
二
就20世纪文学传统而言,“乡土小说”源远流长,跟踪了“乡土中国”的现代进程,以及“农村”与“城市”的复杂纠葛。改开以来,《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开启了新一轮“城/乡”之间爱恨描摹,所涉及问题之广博,难以在此文备述。不过,在此叙事线索中,“中间状态”——县城却被忽略,游离于文学视野之外。如果细究,可以发现,所谓现代转型中,县城变迁力度一点不弱,包含着另一番不能化约的图景。县城处于城乡“交界”,“不上不下”、“亦城亦乡”,因此,其中人物带有“两栖”意味。县城的生存状态,不能为“城”、“乡”所概括,自有其“路向”,却长期得不到文学重视。张楚创作之特殊,其一就在于他始终不断书写县城,讲述身边人物命运,不仅为“城/乡”特定思维模式带来新的阐释,还关注到他们“两栖”生活本身的精神内涵。
《过香河》中,“北京”、“云落”属于高频词,不断出现,但很明显,分属不同意义系统。“北京”在很多作品中出现,但之于《过香河》或张楚,可能意义更为复杂。在小说中,“北京”不但是“远方”,还是另外的生活方式——只有将“当下”/“云落”放弃,才能达成。“去北京”意味着对“当下”自我生活意义的否定。“我”介绍蜜蜜,“毕业后他去北京混日子。我搞不懂为何这些孩子都喜欢到北京扎堆,哪怕住地下室吃咸菜,哪怕送快递送外卖。那时我还在县城里当公务员,跟他往来稀松。我向来对年轻人的热忱充满了怀疑。我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后来,“我辞了公职,跑到这个在儿歌里咏唱过的地方,住在一所比麻雀肠子还细的学校里,念狗屁编剧班,在我那些亲戚们看来,也许比蜜蜜强不了多少”。在张楚这里,“北京”是信手拈来的地域概念,隐喻着“县城”对“城市”的想象。但与以往不同,在《过香河》中,“北京”不是梦想,不是征服对象,而是一个“别处”。来到“北京”后,蜜蜜和“我”并无惨烈“北漂”心态,更重要是生活状态变化。蜜蜜在北京开公司,一度生意兴隆,父母都从老家云落前来帮忙。王如云、邹姑娘两个北京女孩,相继成为蜜蜜女朋友,也颠覆了类似叙事中关于爱情、性别的定位。当“北京”出现时,展开的是日常生活场景:蜜蜜开办公司、恋爱、住院、老艾和老叶前来帮忙,“我”在学校进修编剧、参与新剧炒作。在生活表层,“北京”承载了小说人物对生活的最高追求。“我”见到蜜蜜时,“才晓得蜜蜜在北京过得不错”,“你在北京买房了?我惊讶地盯着他,在哪里买的?哎,三环内的房价比纽约都贵,我在通州买的,不大,一百八十平米,够我住了”。小说后来交代,房子是租来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来自“县城”的蜜蜜和“我”,不仅没有受到来自“城市”的压迫和困扰,还相当大程度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如果将《过香河》中的“北京”与张楚其他作品对比,能够发现,他其实一直没把“城市”(北京)当作地域,而是当作“另一个选择”。“县城”中生活安逸、岁月静好的人,如果“驿动的心”难以平静,渴望改变生活,那么,“到北京去”,就成为毫无争议的替代。“北京”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代表对目前“不满足”。《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对当下的否定,就借助了巴黎,“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得无法衡量!她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自得其乐;这个名字在她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包法利夫人艳羡的背后,是对自己呆板、无趣丈夫的厌弃,认为巴黎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包括“更适合的男人”。只有沉浸于文学想象,才能获得批判性,对“当下”持续否定。如此推论,住在“北京”的,一定会把“乡村”作为理想之“别处”。因此,“北京”和“云落”之辨,乃是一个哲学问题:不是哪里是栖身之地,而是什么才是“想要的生活”。
张楚并非站在某个立场反对另一方,他作为作家,更愿意在作品中加深这种迷惑。与以往不同,在《过香河》中,“云落”作为“老家”,不是“北京”的反面,而是承担了更多值得仔细分析的内容。作品中,人物时常回忆过去的时光,指向一个不存在的“云落”。“云落”在蜜蜜看来,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因此,他拒绝“我”的劝告,坚决不回去。但是,“云落”对于他,也不是可有可无。蜜蜜有个双胞胎姐姐,不幸夭折,他把与姐姐的合影随身携带,“舅啊,我可从来都想着我姐呢,我常常跟她唠嗑,她只听我说,却不搭腔,不过,我知道她想我,她还像小时候那么爱我,总是趁我睡着时偷偷亲我。她其实一直在想着我们,对不?”蜜蜜看似玩世不恭,内心却保留了一块留给“云落”的温情记忆。那个遥远的“云落”,载满了一家人的幸福。而当代“云落”之荒诞,正好颠覆了此前的温情脉脉。蜜蜜搞到批文,决定到“云落”办歌手大赛,获得了县里的支持,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决赛当天,我们家的亲戚、村中睦邻、村两委班子全体成员赶着马车、骡子车、开着拖拉机、三马子车、面包车或者轿车纷纷奔往云落县城。他们穿着过年才穿的衣帽,包里装满了瓜子、糖块、手纸和饮料”,“当五名决赛选手之一的副县长穿着马褂登场时,现场的观众沸腾了,他们还从来没在现场听过大官唱歌呢,他们忙不迭肃然站立,双臂如麦浪般左右摆动,整齐划一地呼喊副县长的名字,同时将绿色荧光棒和LED广告牌高高举起,他们激昂的呼喊声几乎淹没了副县长的歌声……”后来,这个活动叫停,提供赞助的网站也被封了。小说在这里,模拟了一档娱乐节目,把“高大上”的环节从“北京”移到“云落”,恶搞了当代文化,充满魔幻气息。因为“我”未到场,所有“云落”的活动,都由“听说”渠道而来,当代荒诞滑稽与儿时亲切浓情,混杂一处。小说的结尾,邹姑娘怀孕,蜜蜜陪她去医院,意味着他将留在“北京”,永远告别“云落”。“我”则相反,放弃了编剧工作,谢绝“送戛纳主竞赛电影”导演邀约,与老艾、老叶驱车回香河。“我”跟导演说准备回去跟老艾一起“卖烧鸡”,作品至此戛然而止。由于叙事的虚拟性,从始至终,“云落”并不真实,是撕裂、碎片状的。以前的事若有若无,缥缈如梦;最近的事荒诞离奇,不可思议。
如上所述,在《过香河》中,“北京”与“云落”虽是地理名词,却被掏空、虚化。二者并不构成对立,更多隐喻“白玫瑰”与“红玫瑰”,陈述一种意义困境。无论“北京”还是“云落”,一方为“实”,则意味着另一方为“虚”,必然产生对照、互否。哲学问题随之而生。相比起来,明显与城/乡叙事传统不同,带有张楚特有的处理现实方式。
三
不仅《过香河》,在张楚很多小说中,叙述人“我”都相当抢眼。张楚更愿意以“我”的身份,参与作品,形成与人物间映射关系,增加声道,扩展维度。《过香河》中之“我”,暗中操盘,驾驭、调度着故事。“我”身份独特,从“云落”公务员系统辞职,来“北京”学习“编剧”,“快五十岁”了。很明显,从这个叙述人“我”的角度看,无论“北京”还是“云落”,势必是“文艺”和“抽象”的。“我当初来这里,只是不知道我还能干点什么。我对写剧本一无所知,兴趣也不大,上这个学凭的是在单位写材料的一点基础。不过我知道,这是个赚钱的行当,当然,也是个杀人的行当。要想老老实实写出来,大概相当于让老叶去当省长或书记。后来我不再追查所谓的‘意义’了,人没死,总要干点事,无论这事喜不喜欢。”应该说,这个“我”的状态有很大问题:他不是一枚“镜子”,仅仅发挥反射的功能,而是具有强大“过滤”、“整合”的能力,将文本中的“现实”提前进行了删削、修补。“我”喜欢哲学,熟悉维特根斯坦、萨特,并以此看待自己及“存在”,因此小说时常跳脱,藕断丝连。就此而言,在张楚的设定中,《过香河》的读者并非蜜蜜及其家人,而是知识分子。如果对当前文学创作有所了解,就知道张楚此举是在玩“信任游戏”:“我”,一个佛系、被动又神神叨叨的编剧,又能讲出怎样的故事呢?可是,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不是这个“我”,还有谁更适合讲这个故事?
由此可知,《过香河》中的场景及价值观,与“我”有直接关联。而“我”,除了参与故事进程,还承担思考、评判责任,无疑是《过香河》的“立法者”。犹如“三言二拍”,《过香河》中,渗透了作者的价值观——命运叙事的目的,就是阐释一个道理。这件事不好干,其他人干不了,只能请一个喜欢哲学和文学的编剧。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中,论述了“立法者”的衰落和“阐释者”的兴起,颇有洞见,但他的结论,对于当前语境过于超前。恰好相反,当下“立法者”缺失,价值观撕裂,各行其是。《过香河》中,老艾、老叶从“云落”到“北京”,在儿子公司干杂活。他们纯朴、勤恳,待人真诚,虽然对蜜蜜各种行为看不惯,但毫无保留地支持儿子。无疑,他们对周围,也有自己的“看法”。老艾、老叶从“北京”回“云落”,打算借钱开店,“老艾说,跟四舅家的二姐少借点,二姐夫小脑萎缩,去年夏天把农药当雪碧喝,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呢,命差点没了,老叶沉吟着说,三千;老艾说,三舅家的三妹,男人得了癌症,住院化疗欠了一屁股债,老叶说,免了;老艾说,大姑家的大姐,孩子在深圳开公司,大姐夫在施工队当泥瓦匠,没啥缴费,老叶嗯了一声,一万;老艾说,五妹家的房子拆迁,闹了三套房,听说刚卖掉一处,老叶想了想说,两万……”这段貌似絮叨的对话,一石多鸟。从寥寥几笔的“听闻”中,“云落”普通家庭及其境遇,隐约可见,如果仔细揣摩,当能管中窥豹。在老叶看来,每个家庭的状况,都可以用金钱的方式评估出来,而标准,则是朴素、美好的情感。或许为此打动,不断在作品中游离的“我”,忽然做出决定,不再参与虚幻、可笑的编剧工作,明确告诉导演,“我真的要跟俺姐去卖烧鸡了,你再找别人吧大哥!对不住了”。在选择中,“我”用脚投票,做了发言。这个投票听起来很爽,符合流行审美观,不过,“我”是否代表了作者,却需画上问号。尽管说,“我”是张楚的影子,但不能等同于张楚。作者处理《过香河》时,手法巧妙,他近距离观察当下现实,却避免直接碰撞,在暗中遥控着作品人物,包括“我”。
“我”是在特定情境下表态的,可能没有意识到,正好犯了“生活在别处”的“错误”。在“北京”、“文艺圈”看到某些问题,抽身而去,回到“云落”、“卖烧鸡”,是否可以如愿,寻找到哲学上的安宁?很明显,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次“摹仿”。“我”曾崇拜的维特根斯坦,有此先例,“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战场上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初稿。他认为所谓的哲学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无生趣,就去小学教书”。虽然都有“事了拂衣去”的脱俗,但毕竟不能比拟。对于“我”来说,返回“云落”卖烧鸡,远离文艺圈,如同来到“北京”,可能都是“换种活法”的冲动。“我”是否真去“卖烧鸡”,或“卖烧鸡”会是怎样的结果,并不难以预料,但文本却空缺。如果通读过张楚,就能知道,他并非“强硬”介入,以“非虚构”方式书写现实,而是将其“虚化”,形成带有哲学追问、悲剧意蕴的氛围。多数情况下,张楚虽讨论现实,但并不“及物”,保留了抒情地带。因此,张楚的“虚无”感,始终与他笔下热气蒸腾的现实并存。张楚钟情于“失败的小人物”,不留余地,且将内心温暖藏得很深,很少主张“人性温情”及其廉价“救赎”。能够看到,张楚在《过香河》中,有所变化。他试图借助质朴的生存本能,回应某些伪饰、空洞,不惜生硬,也要凭空增添些许暖意。此举是否意味着,张楚在调试自己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张楚毕竟仍在“发展”,适当的调整和变化,反而可以增加讨论力度。
四
《过香河》中,“云落”和“北京”分别是精神寄寓所在,很难说哪个是起点、哪个是终点。或者说,作为常人,多数是钟摆一样晃动,狼奔豕突,不断辗转,寻找能够“安妥”自身之地。这样,“香河”不单是“云落”与“北京”交界,还是一种中介,甚至肉身,具有多重意义。过香河前后,可能意味着两个世界,两个人。老艾说,“只有过了香河,我这心里才踏实些,像老做梦的傻子,激灵下就醒了,你说怪不怪?”看来,老艾是找到“幸福”的人,难怪,“都奔六十岁的人了,笑的时候,还那么羞涩”。不过,她仅是小说中设置的一个人物罢了,而大部分人,似乎也包括张楚,未必都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