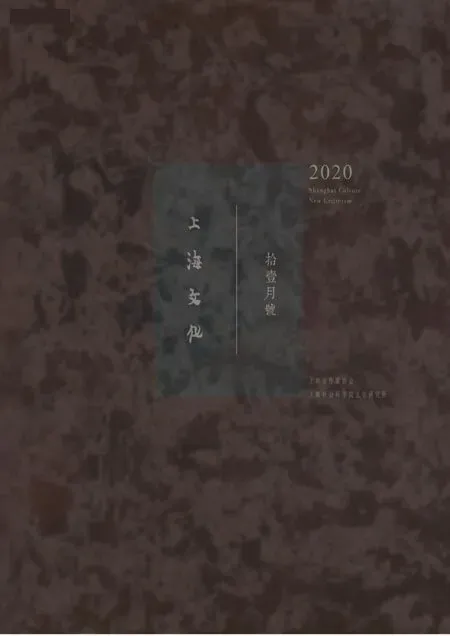趋近于幽暗而透明的微光
读赵松小说集《隐》的笔记
赵冬妮
1
赵松始终在不断扩展他的文学创作。这一回的《隐》,就像有一大把残篇断简,把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带回到现代世界里来,以往我们从未看清过的一些面容,现在从平缓的水面上浮现,那些裂开的历史碎片被粘合到一起,虽是道道弥痕,遍布沧桑,但新的气息灌注其中,生动细微的神情里融有现代人的手感,很显然,这里面丝毫没有对两千多年前面孔的简单复制。《隐》基本采用《左传》素材,那些人物身上自然带着其特有的气息,子不语怪力乱神,《左传》从不乏巫术、祭祀和占卜,看看赵松笔下的夏姬,从中可以捕捉到这类事物的无所不在,“巫臣命人把夏姬带到了现场,她穿着最朴素的白麻衣裙,缓步从容地登上了木头搭建的高大祭台,用郑国方言平静地唱诵了雨神与风神在这之前向女巫们暗示的内容,令所有在场的女巫都感到震惊并拜服在她的周围。”祭台,女巫,雨神风神,郑国方言,甚至预言的神力,这现实生活中早已消失了的一切,现在围绕着夏姬纷纷涌出,也是在要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左传》的夏姬,而是《隐》的夏姬,她随时可以跟神灵发生感应,跟神灵直接对话,她以绝无仅有的神秘气息形成了对我们的包围。
“男人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可在我这里,没有一个不是令人怜悯的小动物。”这是夏姬在说话,重新展现出她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这里有一份安歇,散发出女性甚至是母性的温暖和力量,已远远脱离了红颜祸水的定义,更与《左传》相去甚远。在世道衰微的时代,生命处处破碎,安歇几乎成为一种奢侈,而夏姬能保全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使我们相信,她身体里肯定有一颗发光的隐秘星子,仅仅在此意义上,她与我们比邻而居,甚至是她比我们的住所更高出一些。
2
赵松这样写夏姬,我看到的是他把笔锋深深楔入人的个体生命里,楔入个体生命与其所处的时代。他只是取材于《左传》,然后纵身一跃,在他自身的想象空间里完成对人物的塑造与对生命价值的求索,于是那些历史人物纷纷有了生命,有了清晰的呼吸。一些人物,赵松确信他们身上藏着恒久的光辉,虽然距离久远,他还是要扫除岁月沉沙,他希望我们感受并去接近人性中的温暖,甚至是牺牲,哪怕他们是君王,哪怕他们生于君王家,哪怕他们活在春秋乱世。
这部小说集含八个短篇,《泛舟》的核心人物寿尤为鲜明。他是卫国公子,当听到父亲卫宣公颁旨要太子急子出使齐国,寿连夜请命,去拜求母亲,然后又去跪在父亲寝宫台阶上求替太子出使齐国,直至东方既白。他知道,只要太子动身,在路上等待着的就是死亡。后来在都城外饯行时他灌醉了太子,登舟赶往莘地,被准备射杀太子的黑衣人所杀。急子匆匆赶到后,看到的是寿的遗容,他对黑衣人说,“我是太子,你们杀的,是我弟弟。”当有人说“他已经替你死了”时,他仍旧请求杀死自己。“这对兄弟的遗体被抬上了小船,覆以素缟,还有很多从田野里采集的艾蒿与野花。他们在黄河上逆行了数日,艰难地进入淇水。”以命相交,即便是死,也还是兄弟,拥有共同的河流与舟子,田野与植物。那时寿十七岁,心中澄明,他知道身边到底有多乱,对发生在父辈身上的兄弟残杀从不陌生,但没什么能改变心中笃厚的兄弟情深,在以身赴死那个夜晚,他回想起少年时代与太子泛舟淇水,那里有两岸风物,有太子的低语。
“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这手足情义千年修得,于动荡不安的河流中对抗着风刀霜剑。赵松相信这个稳固的存在,还是在期待、在祈盼?不管怎样读了一本小说,能看到人性熹微之光,这也是小说家给出的福祉。我们从小就读《郑伯克段于鄢》,知道“克之者何,杀之也。”知道杀克互训。打打杀杀自君王家里发轫,从伯仲间开始。后来从苏轼兄弟身上看到那份真挚的手足情加知己,便觉人间温暖,弥足珍贵。从鲁迅周作人之间又看到兄弟阋于墙,亦不能不扼腕叹息,人间大痛莫过于此。寿十七岁,我想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干净的年龄才能葆住一份纯然的挚爱,生命才会高于现实?当然不对,急子可以逃走活命,但是他没有,他请求死于刀下,最终兄弟同行,共同平静地面对苦难。按规矩礼数,寿与太子非同母所生,不可兄弟相称,饯行宴急子酒醉,他拉着他的手跟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好兄弟寿,你们要记住。在喧嚣声中,他最后辞别道:“好兄弟,我得走了。”两句话真是力透纸背,写尽了手足兄弟之情。
而《泛舟》开篇写淇水的动荡,船夫们的歌唱,写一只“刚成年的老虎,正拖了只山羊,往松林中去。这一切,有点像幻觉。看不到羊头。老虎咬着羊脖子,看情形羊脊骨都已被咬断了,老虎倒也不急切”。这是由寿的视角所见,自然界的杀戮形成层层暗示:有一种痛,感受到了羊脊骨的断裂;相比而言,人世间的痛则更锥入灵魂,因为那是生命与生命的叠加,血与血的混杂;更深层的指向是结局,即注定的毁灭,死亡的不可挽回。而这一切的呈现,却是不多言多语,笔触简逸又细致,赵松冷静地借这样一幅自然场景带出他的悲悯和同情,使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在小说中得以复现,且完全是以文学的方式。在另一方面,这又使我看到了人是如何顺从自然的,像一个垂下双手的人立于天地间,或许赵松望断的尽头正是老子,他的人物才有了一种柔顺自处的状态,在其他短篇的人物身上这柔顺也不难见,比如公子兰,比如随侯。
3
我很注意小说中出现或未出现的“隐”。“隐”是一块幽暗的小多面体。不同的“隐”折射出不同的层面,慢慢转动,看看里面一块块不住闪耀的微光。
先是史书之隐。《左传》为《春秋》作传,《春秋》记史,盛大的历史庄严地做着游戏,简略到只留下符号,把人藏起来,哪怕是君王也只剩有君王的符号。再是《左传》之隐,《左传》既为史也为文,既为补笔也有意留白,话不说尽,文学笔法上的隐已现端倪。鲁隐公即位,《春秋》不书一字,因其摄政,隐公死亦仅记一笔“公薨”,《左传》便说,“不书葬,不成丧”。不正式为国君,命该如此,隐公遭遇雪藏直至淹没,他像不像是个隐喻存在,形成了某种封闭,阻止所有的尤其后来者的进入,我们被隔离在外,钩沉或皓首穷经不仅困难,更与文学大相径庭。
赵松从文学角度去触动这个隐,揭开隐的秘密。他敏锐地抓住了隐公,写隐公也不在于隐公,而是在隐公身上那个的隐。所以寥寥几笔,他以淡墨渲染鲁隐公,从外表上来说,“鲁公面相平淡。说话也平淡”。他到棠地去观鱼,当遇到劝阻时,他只是“有些尴尬,我只是去巡视啊”。他还微微探入隐公的精神世界,“神也会说人话么?”“神不会像人这么愚蠢的。”至于隐公的悲剧性命运,就在于他是个“没有野心的摄政者”,本可以坐上君子宝座他却没这样做,“在庙堂之上没有退路”。他的死渗透着那个时代血腥的气味,被追杀的结局早已注定。赵松通过想象力重新构建起隐公形象,隐公是个隐喻存在。他不过代表了《左传》里所有曾经活着的人物,郑穆公,夏姬,棠姜,公子寿,太子急子,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左传》里都深锁于幽暗之中。所以关于“隐”,赵松曾经说过:“这个字充分概括了我们这个社会从春秋时代到当代始终如一的状态,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日常中,也包括在文学里,真实的人与事总是会轻易就被淹没的。”这是个大隐,归根结底,隐就是人在现实和历史中存在的状态,每一个人每一代,不曾有多少改变。隐是一种关系的展现,人不是赤裸裸的,人是在包裹之中的,包裹于现实和历史、日常与文学里,隐是从不会停息的雨,人走在雨幕中,直至他走出去,直至他消失。这才是人的真实生存境况。所以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层面上,真正意义上的接近都十分艰难,消失极其容易。《晋书·羊祜传》曾有一句,“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早已说得十分透彻。在与小说集同题的短篇《隐》中,赵松将笔锋抽回落在现实生活上,他讲了个现代故事,其中插进个偶然的小事件,一个死人被抬出了货用电梯,“他们都不让声张”,“没人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么变成像没发生过的一样” 。这个被抬出电梯的人浑身裹着白布,甚至不清楚是男是女,连性别都已消失,而谁又知道这种湮灭消失呢,只有在这时,“隐”才构成一种擦亮,才被迫转为呈现。这就是赵松的“隐”。
“隐”同时是人的生存状态,在小说集选录的古诗句里,这个隐会直接显露出来,呈现出人所选择的生存,如“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身隐穷居”。你会极自然地想到陶渊明,但陶渊明之前,早有他的先人存在,早在那里隐隐生辉。鲁隐公无法抽身撤出庙堂,然而他使人看到,消失又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啊,在那样的乱世,有时身隐穷居的确是种比消失更好的存在。“隐”甚至成为一块安歇之地,人得以藏身进去。短篇《兰》中的郑穆公名为兰,他像一棵兰草,但他始终是“美好而适时的隐遁”,这里有他性情的质地,同时亦有他的选择,保全性命于乱世。就是他的整个郑国,都是这样存活下来转危为安的,“甘居于柔弱之位”。这个短篇很巧妙地使用了“我们”的叙事口吻,扩大了的声音,那是一个群体在说话,从审慎之中你能听出屈辱和被践踏,也能看到在晋国楚国两面夹攻中,一株株兰草在泥土中柔韧生长。
“隐”真是个好字,丰富而充满变化。一切虚位以待。无论怎样幽深黑暗,最终都会敞开,直至获得最终的绽放。
4
文学也会成为人类的见证者。在小说集中,赵松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变化抵达对文学意义的呈现。那篇《隐》是个不容忽视的短篇,这里有三个叙事者,驯鹤人“我”,现代人“我”,和现代客观叙事者。客观叙事几乎减去了个人的声音,只是一个巨大的摄影镜头安放在那里,缓慢地推拉摇移,以不带任何情感的目光注视着一切,巨大的建筑,森林一样的水泥柱子,空中花园,虚弱的灯光,有人走进来,随后走出去,自然在那里丢失,日出日落则显出苍白。这大镜头的注视有着巴赫金所说的“外部”性质,也让人想起诗人兰波,“站在一旁”。那么大的眼睛,试图在撑破隐,试图彰显出更大的亮度,试图充当见证者。这个客观叙事者是相当有力的,在一道冷峻的注视下,城市那么硬性,那么冰冷,那么静止,又那么梦幻。意外地会有巫师出现,他也可能是道士,“舞动桃木剑,念起咒语,随手把有形之物化为沙砾,化为无形。”城市里的一个异质存在来得多么不真实,好像个荒谬的招魂物。让人想起古代,想起夏姬时的通灵和卜术,那一切在今天并不存在,早已消失。偶尔会有个别人如同被巫师附体,会去拿起桃木剑,戴上面符。
今天的人还会走回去么。短篇《隐》里的“我”住在巨大的建筑里。他弄了套法器,像个让人不安的道士,就连他母亲也不知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话颠三倒四,“你们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只是块正悄悄烂掉的肉,艳若桃花,骨子里正在生蛆,到时我会为你们接生的”。这是自波德莱尔开启的时代,悲哀的风直接吹过来,这个“我”在风中里里外外破碎成沙,他的话全是疯言疯语,而那个默默注视着的大镜头却根本无法捕捉。若是跟《狂人日记》相比,狂人还只显现为臆想迫害狂,他不断在发出质疑,这个“我”则又有不同,“我”不单是个言语者,更是个行动者,比起鲁迅的那个狂人,“我”走得更远,更有行动能力,“我”早已放弃,早把肉体当成了个空壳子,悄悄谋划着,细致地着手,一步步走向对这具空壳的彻底放弃,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短篇《隐》同时并置着两种死亡,现代人“我”和驯鹤人“我”及鲁隐公,后两者的死是以身赴死,舍生取义,是羽化为鹤,飞入云端;而前者就显得复杂了,他要做个飞行器,他知道个别人有成为鸟的可能,“她是只鸟啊”,所以哪怕她从楼上跳下来那也是一种飞翔,而他自己则要借助于器物。小说里出现过很多鸟,但鸟又与鸟有着不同之处。即便是鹤本身也并不单纯,它们好看,自在优雅,然而哀鸣令人哀愁甚至恐怖,它与死亡绑在一起。哀鸣毕竟是哀鸣,毕竟轻盈,没有沉重的肉身,羽化才成为可能。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社会,现代人“我”在自己不能成为鸟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器物,列子御风而行尚还“有待”,“我”早已丧失一切,更不敢奢望“无待”。他曾借助过大麻,在迷幻中产生过飞行,那么通过科技手段,飞行器或许是最有效最可完成的飞行。他走向一百层高的大厦,带上飞行器。在他向人描述飞行器的声音里,带有悲哀的沉醉:“它是用最好的材料制作的,做工精细,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哪怕是有洁癖的人也挑不出毛病,非常干净,近乎完美啊,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羽毛,它的形象,就是一只白色大鸟。我最近的所有工作,都是计算它的受力结构,我也得仔细计算我的身体能承受的重量是多少,……我还要节食,为了到时体重能降到最轻,要保持锻炼,让肌肉有力,这样到时我才能张开双臂……你看啊,就为了这些细节,我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像在准备一个从未有过的复杂仪式……”这是死亡前的声音,它不是通过镜头,而是在“我”的胸膛里发出的。为了让这声音能够有个见证者,这个从未和女孩睡过觉的男人找了个女人,让她见证一个时刻,“这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破碎而沉重的肉身。他甚至可以让我们想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疯癫得以观察自己,但却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在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无根据的要求,换言之,表现出一种荒谬。”是的,一种荒谬。在我看来,短篇《隐》是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文本,唯独在这个短篇里,现实直接被投放进来。天地古今打成一片,历史人物的复活才现出生命意义,现实中的我们也才能发现或找到自己,就像自己对自己说,哦,原来你也在这儿。这篇小说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发掘,尤其鹤的意象,驯鹤人“我”的叙事语气,特别是艺术之美。
“那些坠落的石头,都是星星。大风里,鸟倒退着飞去。此梦复现。冬季,我逃离卫地。初春,我藏身鲁国的棠地。这里有湖,有山。春季,雨水过后,近千只鹤迁徙而来,留此月余,又北飞。在湖边,我筑茅屋,围院子,做驯鹤人。”
这是驯鹤人在说话。这叙述有如诗歌。我曾反复读,甚至想把“大风里,鸟倒退着飞去”拿来做文章的标题,那么“此梦复现”四字,岂不更好?人生如梦,像做了一场大梦,人从中醒来,亦真亦幻,不尽沧桑在无力感之中慢慢融化,又重新聚起。如此反复地淘洗过后,叙述者的声音清晰而确切,确切到他知道他自己,他能说清他自己。
5
像《隐》这样一部小说集,的确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单纯靠挖掘情感,尤其是靠挖掘记忆,根本无法完成这种写作。可以设想一个作家从小在河边长大,但那条河其实是贫瘠的,现代城市的河流从来都兀自空流,从来没有过渡口,渔家子,摆渡人,没有泛舟和醉饮和浅吟低唱,而且想想上游的那些水库,河流被控制起来,除了流淌,除了风及河面上的薄雾,河流比人更寂寞。人的身体不会湿的,他根本无法进入那真实的河流。
作为小说家,赵松把自己放回到古老的过去,放回到溱水、淆水、淇水,那是《诗经》里的河流,也是《左传》里的,他不仅要握到草木花鸟,他还需要进入河流的空旷和沧桑,用这些像补仓一样来补充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他的想象力全部张开,调动起自己的视觉、听觉和感觉,所有与之相对应的器官全部都要发出震荡,这样我们才会触及到那些有质感的人物,尤其是书中的女性,夏姬,棠姜,夷姜,每个人都有着超强的直觉能力,直接呈现出最原始最隐秘的生命力,每个人都像团火,熊熊燃烧,给攻城掠地活在杀与被杀的男人以常人的安稳……在《隐》中,多少男人气若游丝,声音里都充满倦怠,甚至是一出生就衰老,他们站立或倒下,哪怕一动不动,也能听到他体内在隐约唱着衰老经。无力感,梦幻感,大雾般包裹着这些人,时时使他们进入大梦方醒的那一刻。这衰老根本与年龄无关,在乱世里倾轧凌乱破碎,早使他们倒在地上,况且在他们之前还有着更老的人和事,巨大的梦幻感时刻会降落下来,罩在身上。赵松在这种转瞬即逝之间深入并洞察着这些人,强有力的如巫臣,柔顺自处的如公子兰,内心又都在发出渴求的声音,哪怕在身边女人的怀抱里取暖,沉沉睡去,不再醒来,每个声音都带着人性里最微弱的幽光,赵松趋近于它们,让不该消失的留存下来。应该说,赵松是个有穿透力的造梦能手。
他有滋养的源头,就是在《诗经》、《易经》、《左传》这里。《隐》在形式的创造上,比如《诗经》、《易经》的引入和化用,应该说是对古代经典的遥远而有深意的呼应,或者说是致敬,“诗”的气息,“易”的神秘,春秋时期的世道人心,至少这三点构成了《隐》结构稳固的美,及气息绵密的古意,由此也可以说,《隐》不失为一部有着如此质地的小说文本。但是身为现代小说家,一旦把目光和笔触投向过去深入历史,他就要额外生出另一双眼睛,来凝视他自己的时代,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设法/注视你的双眸/用他自身的鲜血,黏合/两个世纪的椎骨?”这是时代的痛楚,也是时代对一个诗人的严格检验,而这在《隐》中始终不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