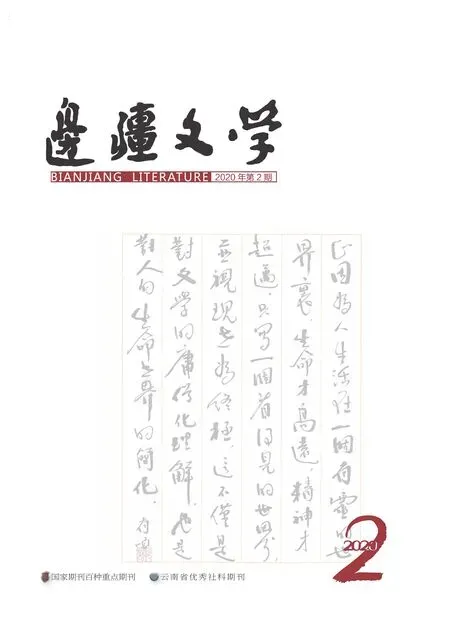月亮的心结
[散文]……………………………………………·哈尼族
1
在乡村,月亮是吉祥物,它皎洁,明亮,寄寓着幸福、圆满;它驱散黑夜,给人以光明和勇气;它陪伴着夜行人赶路,就像你不离不弃的爱人。它把银辉和群山相融,营造出和谐自然的夜晚。
我对月亮的记忆,是从一年的中秋节开始。记忆中的月亮特别大,明晃晃的,像群山中的清泉水濯洗过一样明洁。
农历八月十五。天近黄昏,我就急切地等待着月亮出来。一个贫穷的年代,八月十五对我们是何等的诱惑。
乡村八月十五的月亮,要天黑一久才会出来,时辰还早。母亲在厨房里已磨好了米面,盛在簸箕里。舂好了红糖,盛在白碗里。清洗好甑子,支在灶上。但灶锅里的水还没有烧热,离蒸糕粑粑还有些时候。
家门前的核桃林和那棵枝繁叶茂的大青树微微地起了一阵风,树叶“簌簌”抖落的声音,像一条小青蛇爬过石棉瓦顶,落日陷落的天空蓝里带灰,像久旱无雨的中秋扬起了白色的沙尘。暮色四合,群山渐渐被漆黑的魔法所笼罩,一切都似乎在为迎接中秋夜的到来。
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像无事儿似的,吃过晚饭,他们也许是被一天的劳动折磨累了,这会儿有的坐在门前的凳子上清洗手脚,有的在看书。那个年月,家里也仅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的故事》和几张翻得不能再烂的报纸,但哥哥姐姐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早晚翻看,就仿佛纸上的文字,是他们对付时光的唯一食粮。那时,我识字不多,对文字还似懂非懂,读书还停留在看图的阶段,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外译书藉还提不起兴趣,常常只能翻阅《雷锋的故事》这本画书,他手背上被地主老爷划伤刀疤、怒发冲冠义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我童年的心灵。我小小的心中从小就装下了英雄的形象。
夜黑到一定的时候,天幕渐渐开始变白,群山泛起青灰,乡村就像沐浴过一样朦朦胧胧。大家都觉得天似乎是要变亮了的时候,月亮已从东山天际升起来了。脱出群山的月亮就像一个懒汉,慢腾腾的,发出一轮清冷的银辉。它从核桃林梢闪动着升起来,就像树梢上挂上了一个圆盘。
月亮出来了,乡村立刻热闹起来,听到了狗和小伙伴的欢叫声。山村氤氲着一股糕粑粑的清香,带点红糖的浓香味,带点糯米的黏香味,带着节日的喜庆味。父亲已在屋檐下支了四方桌子,桌面摆上米升子,摆上果糖,就等母亲把蒸锅上的糕粑粑端出来敬献月亮。甑子里的糕粑粑散发出阵阵红糖和糯米的香味,但母亲说,只能献了月亮才能吃。
献月亮,是要月亮保佑我们全家一年平安、幸福、团圆。
母亲把热气腾腾的糕粑粑端放到桌上,父亲恭恭敬敬地往升子里点上三炷香,然后在桌下烧了三份黄纸,并用麻布口袋垫着跪下叩头。此刻,穿过林梢的月光射向桌上的香火,桌面上升起了三缕袅袅的蓝烟。寒气里的月色越来越明了,它们就像水银一样不断地往桌上倾泄,光亮照亮了糖果,照亮了热气腾腾的糕粑粑,照亮了父亲下跪的白发,时光在那一刻像一幅画一样凝固了,乡村的中秋,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祭过月亮,我们一家便围着桌子分糕粑粑,吃糖果、赏月。母亲匀称地切好,一人一块,放到碗里。我和哥哥姐姐端到各自的糕粑粑,先还舍不得吃,接着却狼吞虎咽。等吃饱了,才坐到门前的台阶上赏月。
中秋的月圆得动人,圆得可爱,那么大,那么亮,那么明,就像天幕上打开了一盏探照灯。四周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就连平时密密闪烁的星星,也因为月亮的圆满而羞于露头。我们发现,月亮里还有一棵树,它像精心镶嵌上去似的,枝繁叶茂。母亲说,那是娑椤树。娑椤树?它能长在月亮上,我们对它肃然起敬。
月色中的山村,月亮表达了它对世界的美好,吉祥、圆满,皎洁、明亮。我走到哪里,月亮就跟我到哪里。我扶住门檐,月光就静静地照在门檐上,温柔地扶摸住我的手;我走到屋檐下,月光就跟到檐下。月光淡淡的,就像要为我单薄的身子涂上一轮青矍的装饰。我走进家,月光也跟着我。隔着屋瓦,它不能全部的挤进来,月光就打个小洞,一束光亮像电光一样斜射到我的床上,在铺面上形成一枚花钱般大小的亮光。我伸出手,想用手掌接住这一缕穿过屋顶的月光,月光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掌心里。我晃了晃手掌,掌心里的月光也跟着我的手心晃了晃。我想握住月光,不想月光却逃出了我的掌心,停在了我的拳头上。村庄的月光是这样的俏皮,我动它动,我晃它晃,我想捉住它,它却会逃开。
父亲建盖的瓦房铺了木板楼,夜里,我睡在板床上静静地听着屋外月光的声音,和秋天落叶翻卷着跑过场院的声音,我发觉月光散发着娇柔的气息,它温柔、明丽,它走过的地方,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这一间老屋,是父亲一生积蓄所建,虽然破旧、粗陋,但瓦面和瓦面接触的地方,恰好留给了月亮可乘之缝,有月的日子,月光总能抓住这些瓦匠们疏忽的间隙,把圆柱般的光亮倾泄下来。突然想起了一位资深的摄影家的留言,他说:瓦片缝里渗出的炊烟,才是萦绕人生最久远的温暖记忆。细细品来,那些从瓦片缝里渗出的炊烟,在傍晚月亮刚刚升起时,带着人间烟火最朴素的气息,在忙碌的都市生活的人们很难体会到。而此时,在深夜的月光里,看见了那丝丝月光,也将是萦绕人生最久远的记忆吧。
我得感谢父亲,他从小就把我安排在楼上居住,让我无意间感受到了月光的美好,同时也适应了月光和黑夜不断交织的变化。有月的夜晚,我舒心而睡,没有月光的夜晚,我绻曲着身子等待着月的日子。漆黑的夜,屋顶上的老鼠活动得很厉害,它们会悄悄潜进楼台上偷食玉米,“咯嚼咯嚼”,它们啃动玉米棒的声音,就像恋人在亲嘴。
2
居住在乡村,人生就必须经历几场月光,看到几轮不圆满的月亮。就如是个男子,就必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是个女人,就必须操持更多的家务。世界就是这样,冥冥中总有一些规则,必须去承接和面对。从我家到小学校,途中要经过两座坟墓。坟墓周围荒草萋萋,长满了蒿草,还有一小片密密站立的桉树林。每次从坟旁经过,我观察着这两座密密挨在一块的荒坟,心里七上八下,有说不出的害怕和空落,总担心坟里会突然跳出两个人来拉我。就因为这两座坟,我夜晚就很少外出,去大寨子里和小伴相会。
小学将毕业那年,班主任刀老师却突然通知大家晚上要上晚自习。无奈,我只能硬着头去学校。
我埋怨父亲,很多年前把我家建成了独家村。父亲却说,怕什么,世上并没有鬼。父亲说,生人怕水,熟人怕鬼。鬼有什么可怕的,人死了都变成了灰。父亲回忆说,他年轻时在哀牢山里赶马,山里下大雨,他和马帮夜里只能扎营。马帮们摸索着,寻找平整的地方铺毡而睡,早上雨停起床一看,才发现所有的人都睡在了坟头上。他们常年行走在山里的坟地里,从未看见过鬼。
尽管父亲这样安慰我,但夜里经过坟场,我后背发毛,心底还是不停地打颤。我走过坟墓旁的小路,山月明亮亮的挂在夜空,似在对我鼓励;我看看路旁的坟,坟头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月光,它也为坟墓披上了一层朦胧的夜色。我走过坟墓两三夜,再也不怕了路旁的坟墓,心中却装满了明月。
月亮是心,心情有好有坏,所以月亮有圆有缺。满月固然美好,半月也是一种富饶。多是残缺的心里,才会少了有温度的话。心怀美好的人,所看见的万事万物都带着光亮。人生亦如是。想起那年,小学高年级的班要毕业了,考完试,就要各奔东西。按惯例,班级里都要开个联欢会,把小学校里的四五个老师一同请去吃糖果,作最后的相聚。在这样的晚会上,就得请两个低年级的学生去为大家烧水、沏茶。班主任指定了我,另一个是我班的彩梅。
这个决定老师才宣布,我们的脸红了。那时候,村庄学生大多都很玩劣,情窦初开,男女情谊,似懂非懂。男女生划上了三八线,相互不讲话,暗地里并互相搭配了“对象”。彩梅就是平时班里配给我的“老婆”。
烧水、沏茶的待遇是能和毕业生一起吃糖果,因此老师选中当班长的我和水灵灵的彩梅是理所当然。不过那时我不谙世事,而水灵灵的彩梅却已出落成大姑娘,平时她的一颦一笑,都能让我失魂落魄心跳加速。晚上,我和彩梅早早的就聚在学校的楼下,她虽然是班上搭配给我的“对象”,但其实我们都好久没有说过一句话了。我们聚在一起,尴尬至极。一见面,脸就红了。我们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她拎起扁担,要去校园上面的沟里挑水,我只能跟着她去,手心里不知什么时候却也拿到了一口水瓢。取好水要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东山上托起了一轮圆圆的月亮。月亮黄绒绒的,像她一样美。我鼓起了勇气,我对彩梅说,“我来挑水。”彩梅笑了一下,她说,“不用,我挑行了。”
彩梅说这话时,大辫子前面的脸上流露出了一对大大的酒窝。她身材高挑,担起水来桶底不会撞击地面,这对于后发育的我来说可能是不行的。我们挑回水,然后用茶壶在三脚上烧,投上茶,一齐端到教室里给师生上水。彩梅上一组,我上一组,她上一组,我再上一组,我们轮流着,完了回厨房里享受糖果。毕业晚会是如何散场的已不记得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记得彩梅和我分开时校园上空的月亮正明,月光就像寒盘里散落而下的银辉,斑驳陆离,一部分洒在校园的六角楼上,一部分洒在校园的桐子林里。我们的家在村庄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夜深了,我要送彩梅一程,她却说不用了,她回家的路经过大寨子,不会害怕的。而我,还要经过那段村外的小路。我们在校园的场院里分开,她踏着月色回家,我也在月色中向另一个方向的家走去。我们分开的方向,就是人生的追求方向,我们分开的距离,就是人生的现实距离。后来我们毕业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记忆里完美无缺的她,美丽的彩梅,就只剩下梦一样模糊的印象。
3
时日的更替就像月亮的圆缺,在不知不觉中演变。在乡村,月光能帮我们抚平一些思念与失落,重温一些人和事,也会让人反思。读月光,是读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是让人抛开责任和理想躲避世俗,而是让人勇敢地行走在纷纷攘攘的人流里,心也能悟透平淡与真实的恒久。我离家那天,母亲老早早就起床,她生火,要为我做饭。那是月尾,银亮的下弦月照在窗棱上,折射在母亲的白发上,就像暗夜里一点点炽热的光。母亲一生操持家务,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夜辛劳,岁月过早地在她的头上添上白发。她在灶前生着火,想了一下,便取下火塘上晾着的一串一直舍不得吃的干黄鳝。母亲往锅里下油,然后把干黄鳝一条条放入油锅里,顿时,一股喷香的鳝鱼味从油锅里升起,飘出窗外。
我要去的地方叫漠沙,是个花腰傣聚居的小镇,听说那里气候炎热,夏季平均气温都在40度左右。我嚼着干黄鳝下饭的时候母亲絮絮叨叨,她一会儿问我干黄鳝油煎得怎样?一会儿又教导我参加工作了要认真负责,对老师,对学生要充满爱。我一一点着头。口中的鳝鱼却嚼出了焦糊味,显然,老花的母亲已把部分鳝鱼炸过了头,她在匆忙中已没有把握好油炸鳝鱼的火候。
我走出山村的时候天空中涌动着片片白云,一抹山岚就像海船一样穿过红河谷的坝心。出门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前的大青树下目送我,东方的一抹红霞金灿灿地印在母亲的脸上,她像青树一样平静安祥。我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走出村庄,往坝子里走去,走出好远,回头看我老家的地方,半枚残月就像一把勾镰挂在苍穹,故乡,是月亮下的一粒乡愁。
那年我23岁,其实已长成了一个唇边长毛的男子。
我任两个初中班的语文老师,一天两节课,一星期12节。课不算多,但是主课,有一定的压力,必须全力以赴。
安顿好住处,我就去看教室,这个地方刷新了我对教育的认识,一幢能容纳全校18个班的教学楼,没有一道门和一扇窗是完好的,教学楼建在一座热气腾腾的荒丘上,风呼啦着大嗓门一个劲地往里吹,许多学生坐在教室里,一不小心纸页就被风掠走和吹散。更要命的是一到刮风就停电,夜自习,许多学生点上蜡烛,用课本从页心打开拢住烛火不让风吹灭,教室里夜风呼啸,烛火晃动,好在,很多个夜晚,透过空荡荡的窗框,能看到一轮明月冉冉升起。
小镇风情万种,傣雅们在梯田里种稻谷,在江边种西瓜,火红的木棉,摇曳的凤凰树,大片大片的槟榔林,密密的土掌房,让这个地方充满了诗情画意。一些课余的时间,我们老师都会趿拉着拖鞋,穿上半截裤,走出宿舍到校园的凉风台上一排排坐起,然后一起聊天、兜风,看星星,听月色朦胧的山寨葫芦丝响起,穿坝而过的红河往南奔腾。有时,我们三两个老师也会一起相约着到镇上看电影、溜旱冰,喝咖啡,小镇是单调的,同时也是纯朴的。常常,我们回校的时候,灯火里的小镇,已被月色照明。
4
在小镇工作生活,渐渐的心底便生出些思悟。月光会照亮身置黑暗中的人们,无论是归途还是失意。它仿佛告诫着我,成功固然好,应当珍惜,失败会失落,更应快乐。最美丽的给予是慨然的传递,勇往直前才是最有义务的担当。
那是一个周末,刚吃好午饭,窗前就有一个怯生生的女生来喊我。她叫陈秀,苗条而秀气,是我教的另一个班的女生,平时读书很刻苦。她站在一楼过道我的窗口,邀我去她家。
我问她,你家在什么地方?
她说,胜利村黑查莫。
我谢绝她,说不去了。但陈秀一直站在我的窗外,磨蹭着不走。我转念一想,就算家访,跟着她去山后面大山里的黑查莫。
我在她的带领下,先从小镇乘拖拉机到14公里的三级电站,然后再下车进山。山路曲曲弯弯,就像羊肠,又陡又艰险,好在我从小走惯了村庄的路,才勉强能应付。同路的还有几位男女同学,但走进大山里,在各个岔道口,他们就一个个离开了陈秀和我,一个个向山里走去。不知趟过了多少条流水,翻过了多少座山,才在傍晚时分到达黑查莫的村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原以为到家就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米饭,但一进村我才发现家家户户房门紧锁,山里人外出打工的打工,在家的都到离村几公里以外的田房去薅苞谷去了。陈秀的爹妈也一样,他们去田房做活,根本不知道家里今晚来了老师。
我和陈秀只能在村中等待她父母的回来,尽管等待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但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时间是不会等我们的,太阳渐渐从后山上一点点落下去了,苍茫的群山盘旋起几只黑鸟,紧接着暮色就像海潮一样弥漫过来,夜色吞噬了村庄。非常狼狈的是陈秀竟然没带钥匙,我们连家都进不去,只能在门口找了两支破烂的凳子坐在门前的猪厩平顶上。夜黑了,陈秀手足无措。我安慰她说,不用急,再等等。我们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过了很长时间,渐渐的便看到有村民抬着锄头摸进村来了。陈秀急着上前打听,知道她父母随后就到。家长回来的时候,微微起风的夜黑得看不清彼此,我仅能从陈秀的模样来辨别她父母的模样。一听说孩子的老师来了,陈秀的父亲手足无措,放下锄头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女主人反应快,她慌慌忙忙去开门,引我进去就去生火做饭。
火光升起来,家立刻亮堂起来,我环顾屋内,空当当的并没有一样值钱的家什。女人的米,是从墙角的一小袋子里取出。松明火苗晃动着,我的心也暖起来。男家长说,黑查莫还没来过家访的老师,我是第一个。陈秀的母亲看着我,问我咋能走这样艰辛的山路呢,黑查莫,就是很远的地方,摸黑赶路的意思。山高路远,城里人根本不会走这种路。我笑着,心里暖和和的,我告诉两家长,我的老家也在乡村,村庄的路也一样的不平。
家长迟疑着,大约是还想去抓鸡来杀,但被我制止了。一是太晚了,二是我们三四个人,根本没有杀鸡的必要。家长拗不过,便去取蛋来煎,陈秀帮忙着拣菜,我们围火而座,慢慢的熟悉对方。
吃饭的时候,陈秀的母亲突然对我说,不想给陈秀读书了,陈秀也不想读书了。我心头一惊,为啥?
女人说,她那成绩,读了也是白读。
她成绩也不错的啊。我说。女人说,再说我们这种家庭,供她读书也不容易。
见我要说话,陈秀突然开口了,她笑着说,老师,是我不想读书的,我也觉得自己读了也是白读,成绩不好,还不如早回家。
啊,我对陈秀说,你怎能这么想呢!你这个年龄,是读书的年龄啊。
陈秀支吾着,说,反正我不想读书了,过几个星期就想回来。
你?我涨红了脸,不知还能说什么。
吃好饭,家长就叫陈秀给我打洗脚水。他们也不再多说话,似乎不读书已成为他们心中早已的决定。黑暗里,主人摸上篾笆楼,为我铺床。陈秀挑灯为我引路。我看见女人从箱里取出她儿子结婚时留下的床垫、棉被、枕头,一一为我铺好,然后安顿我休息。女人说儿子和媳妇都到城市打工去了。女人和陈秀下楼去了,她们踩在篾楼上的声音,木梯上的声音,和那种挟裹着一股风穿过的气息,让我心里起了湿湿的心绪。是什么绕乱了我的心呢?我在黑暗里恍惚着,一下子又说不清楚。
村庄安静得只能微微地听到屋外的风声,主人们都累了,我也累了。似乎只挨着床,我便听到楼下房里传来一阵的鼾声。接着一股困意萦绕着我,我便迷迷糊糊地沉入到了梦中。我是被一两只跳蚤咬着度过的,迷迷糊糊的梦中,我一夜都感觉全身痒,似睡非睡,似梦非梦,但又无法清醒过来,圈圈圆圆的梦境,寻觅不到光明的出口。下半夜,屋外像是起风了,树木“哗哗哗”地吹响,我睁开眼,清醒过来,突然庆幸天亮了。我坐起床,定定神,伸头往木窗外望,突然才发现这不是天亮,而是山中的月光挤进屋来了。山村的月色很独特啊,几点残星稀疏地步在夜幕之上。睡前我乍以为今夜没有月色,而此刻几缕游云依稀地映照着点点星光。突然间使我想起了孟浩然的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不经意之夜,却发现山村最浓重的乌云异常明亮,它的背后,是一片澄澈的月。是的,纵使生命中的阴霾可以遮挡心中的明月,它也无法阻挡那无边流淌的月光。有时,我们不能自怨自艾,其实阴霾背后的月光,在映衬下更加美丽动人。我重新和衣睡下,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陈秀留住。
山村来了老师的消息,不知怎么就在村子传开,第二天太阳出山的时候,已有很多家长在陈秀家门口守候,他们要见我,要问娃们的成绩。夜里有了折腾,并被凌晨陈秀和她母亲在楼下一起磨面和碎猪食的声音弄得恍恍惚惚,我思前想后,辗转难眠,早上却睡过了头,等我出门,家长们便围住了我。很多家长夸奖我能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他们村庄。我竟然是第一个来黑查莫家访的老师啊。我说应该的,这是我应该的。我们寒喧着。家长们却突然提议要带我去看看村后的大草坪,还有一棵四五人才能合抱的大椿树,我推辞不过,便跟着村民上山。陈秀的家长和陈秀跟在我后,我们边走边谈,渐渐的话题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爬到村后山顶,森林环抱的山间,豁然出现一个大草坪,野性的草蔓长得矮矮浅浅的,细密的根系毯一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绿茵。听说每到过节或祭祀的日子,村民们就在这里集中活动。那棵林边上的大椿树健壮挺拔,树身笞色如鳞,树冠枝繁叶茂,如草坪的一把巨伞,撑开来。多好的风水宝地呀,我们在草坪上走,心像草坪一样安静,又像山风一样自由。
5
我到黑查莫的消息,一天就传遍了整个胜利村,就连我所在的小镇中学,我还没回到学校,许多老师都知道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阴谋,不然消息咋传得那么快,或是乡村的月光长了脚长了嘴,它把小镇人都告诉了。
我回到宿舍,隔壁邻舍的易老师就来问我,去陈秀家干什么?
我说家访呀。易老师笑笑,白了我一眼就不再说话。
我没有过多的和易老师解释,因为平时她就是这样一个随便的女人,终年穿一身洗得不能再发白的牛仔服,不好好教书,又不喜欢与人来往,独来独往,我行我素,不太讨人喜欢。
我继续上课,陈秀跟我回校读了一个学期,在我的说服下,下学期她也回校上课了。她读书越来越努力了,成绩也在不断进步,如果她把握得好,中考是会有好结果的。每次我去看她,都鼓励她要好好学习。从破旧的宿舍走回的时候,心里装着的还是这个从前说起不读书还一直笑着的女孩,她苗条而清秀,就像春天的一枚新月。那晚我在她家床上看到的月光,是她淡淡的忧郁和浅浅的笑。
单身汉抬大碗吃饭的时候,谈起陈秀,易老师对我说,山村都是重男轻女,女孩子家长都不重视,要求她们不读书很正常。
那一刻我突然怜惜了面前的易老师,如果她是个男的,也许学校的师生不会对她产生偏见。
6
人生如月光,无常如是说。戏谑的漩涡,不经意间却出现在你的身边,不知觉。迷惘世界,已酝酿了另一个悲剧的到来。等夜晚一个校园都乱起来的时候,我预感到一场小风暴降临了。我急急忙忙地跑出宿舍,踏着月光,穿过校园,在学生宿舍楼前看到一个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大喊大叫的女人的时候,我的心几乎崩溃了。这是易老师啊,她疯了。月光下她变成了一副狰狞的模样,她被几个男老师扭扯着,嘴里不断地吐着白气,不断挣扎,要去抓面前月光中虚无的虫子吃,力量之大,简直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这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村庄的憨二姑奶,她也是这样一个疯人,常年被她的家人用大铁链拴在木桩上,或关在黑屋里,“嘻嘻嘻”地傻笑着,我去逗她,她还会用大铁链子来打我,有时又会翻出大白奶团来给我和小伙伴们看。
易老师是怎么会疯的,老师们一个也不愿说。
校领导要把易老师送往镇卫生院,可救护车迟迟不来,男老师们死死扭住易老师,像扭住一个杀人犯一样不让她跑掉。我排开人群,走上前帮忙。我抓住易老师的臂,易老师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喊她,她竟然也不认识我,看到我就像看到白痴一样毫无反应。她嘴里忽儿嘻嘻、嘻嘻地笑,忽儿怒目而视,像要杀人一样凶,四肢却在本能地用力挣扎,完全就像一个刚得到强制控制的死囚犯。易老师胡言乱语搏了一会儿,大约筋疲力尽了,她软下来,要瘫倒在草地上。我急切地喊她,她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拉住她白皙的手,想扶正她月光下歪倒的头,不想她却把一大口白沫子吐在我脸上,易老师嘻嘻地笑了,苍白的脸上滚下一串浑浊的水,然后又开始拼命地挣扎。
救护车不来,我们只能把易老师连抬带拖地送往镇卫生院,灯火通明的小镇吹起江风,月色惨白,远山灰暗,夜凉如水,易老师的手也如夜风一样冰凉。卫生院医生不急不慢地走出来,知道是易老师,询问了详细情况,就给她强制注射镇定的针水。反复注射了三次,剂量都是超几倍了,但易老师还是不听使唤地挣扎,她折腾后的脸庞寡白而惨淡,不时暴露出的乳房就像架上白花花吊着的玻璃瓶。一直到第三只小针水打完10多分钟后,易老师才渐渐安静了下来,她不再过份挣扎,喘着粗气仰面瘫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她突然不乱了,大家又担心她会不会休克,看她苍白无神的鱼眼睛,凌乱不堪的长发,死人一样可怕。静了一会儿,老师们把话题转移到她疯的问题上来。听一位男老师说,下午她去了一趟她男朋友家,回来的路上就疯了。那她男朋友呢?男朋友早就溜了。有人说。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易老师和她的男朋友好了四五年了,就因为她生活邋遢,不善言语,一直遭男方家人反对,因此她的婚姻一直没有结果。我看着易老师,希望她打了针后赶快醒过来,这对她是多重要啊。但易老师一点反应也没有,针水打在她手上,就像白开水流走一样。
校园里疯传着易老师的病是不会好了,据说她是被男方家下了药。除非她要脱离现在的男朋友,病情才会好起来。
易老师的母亲从外县赶来服伺她女儿了。大约乘了两天的车,这位60多岁的女人才来到小镇学校。这是一位心态平和的母亲,它头发花白,白净的脸上神态却超人的安祥。她来了也不哭不闹,不问我们她女儿的犯病情况,她每天忙里忙外,在房里给女儿洗脸、煎药、做饭,照顾她安睡。易老师从镇卫生院用车拉回来后,一直睡在她的房里,见不到,也不听她再乱,似乎她和这位远来的母亲,已达成一种默契。易老师从此再也没在我们学校上过一天的英语课,大家都知道她病得不轻,只有离开这个地方,她的疯病才会好转。
7
我是在那年的初秋离开小镇的,我调离学校那天,我留恋起我隔壁的易老师来,我很想看看她,她长时间没露面了,清冷的宿舍拉着严实的窗帘,我一点也没有她的消息。我想和她偶尔出门的母亲说说话,安慰下她。但她的母亲似乎不愿过多的和我交流,我们双方仅是笑笑,算是作最后的告别。
那年我二十六岁,调到离小镇近百公里外的县城工作。
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县城,对于许多乡下的教师来讲,能到这样的县城工作是多么的幸福和不容易。我住进了学校的宿舍,结实坚固的水泥平顶房让我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这样的水泥房晚上是没有月亮可欣赏的,月光被城市完全地挡在了外面,我们留意到的黑夜和白天一样都是灯光。办公室的灯光,电梯的灯光,汽车的灯光,广场的灯光和路面的灯光,灯光白天黑夜无处不在。即便是暗夜,我也不用借着月光去赶路,摸着黑去上厕所,点着蜡烛指导学生和批改作业,城市的公共灯光为我免费打开一切,这大约就是人们羡慕或钻营城市的原因。我居住的窗外有棵粗大的皂角树,每次从树下经过都会感觉到黑暗的阴凉,夜里睡醒会听到风乍起时叶片相互撞击的簌簌声,那声音若即若离,就像被月光被风追赶着奔跑,就像月光水银般一样氤开,淹没平静的村庄一样迅疾。这让我心头顿生失落,像掏空一样每夜每夜都睡不好觉。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这些年她一直住在村庄里,住在我家破旧的老屋里面,此刻,村庄的月光一定平静如水,星光一样落在楼板上,制造出千疮百孔的斑斓。
我决定回家。这些年,村庄里来了大批的干部,他们把村民集拢在场院里,大青树下,给村民讲政策,说道理,要求村庄搬迁到集镇河谷去居住和生活,不搬迁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祖祖辈辈的村民生活在山上,餐风露宿,披星戴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来也没有富过。扶贫搬迁,是贫困村脱贫致富的一道出路。年轻的村民到举双手赞成,可那些年迈的却不愿意,他们担心搬到集镇河谷,热了受不了,且怎舍得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山地和家。是的,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留下了他们许许多多的故事,是这些故事构成了乡村的历史和文明。
不过搬迁是大势所趋,两年后村庄里的人还是一批一批地迁走了,迁到红河谷边的集镇上。平时热闹百年的村子瞬间安静了下来,成了一个空壳的村庄。我大哥家及我的侄子们也都搬走了,我姐姐家也搬走了,红河边上形成了一个机场一样庞大的千家寨。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搬走,一些家里买了轿车和儿女在外工作的家庭就因为达不到政策条件又被留在了村庄。他们就像迁徙路上掉队的赶路人,被村庄永远留在了山梁上。我的父母就留在了村庄里,他们本来是想随儿孙们离开村庄的,但是我在外工作拖累了他们。
我回到村庄。村庄空空的,就像一个热闹的家庭,突然走了儿女一样静寂。
留下也好,村庄凉。母亲说。
我在村庄周围游走。一些被遗落的村民,看到我回来,很快集拢来,打听山外的信息。我看到,这些遗落的人,和他们的老屋,已成为昔日生活时光留下的残余印记。昔日和我家产生过矛盾的一位大叔,这会儿反而亲和了,主动过来和我说话,和父亲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是分离,让看见与看不见的沟壑弥合了吗?是分离,让过去的恩怨不再有人计较了吗?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昔日路旁的那两座坟,隔了这么多年,它们是否还如村庄一样存在?走出家门,山上是四通八达的公路,过去的坟场,种满了绿油油的橙,已找不到荒芜怕人的景象。晚饭的时候,我突然向父亲问起了彩梅,我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不知她过得怎样?父亲说,她嫁了乡糖厂的一个工人,生了一个孩子,但后来离婚了,现在就不知道怎样。
回家来,狗一直对着我叫,感觉就像天上的月亮在叫。就像平日里偶尔飞来叼鸡的老鹰在啾。我安慰父亲,村庄也变了,山岭上是一片片绿旺旺的褚橙,村脚下是一片片起伏的稻浪,还有这些年不断修通的公路,村庄在不断改变。我走进老屋的木板楼,鼻孔里突然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是什么味呢?楼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不甘心,四处嗅,四处寻找,像一只讨厌的土狗。有点像厨房食物的腐味,也有点像空气流动中木质的气味,有点像……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睡在这上面,不也是嗅到过这样的气味么。夜里月光浅浅地挤进来,落在雨水渍过的木板上,那氤开的圈圈点点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气味在穿行。我决定要为父母翻了屋顶。母亲却说,不用了,屋老了,人也老了,都习惯了生活啦。下雨,毛毛水滴落进了屋里;天晴,太阳月光会掉到木板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漏大了,再在瓦上面铺上几片石棉瓦,日子不就是这样过么?我吃好饭,就要驱车离开村庄回城。父亲和母亲还是站在那棵大青树下送我,今天是好日子吧,空廓寂静的远山,月色苍茫,哀牢东山上空,圆圆的挂着一轮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