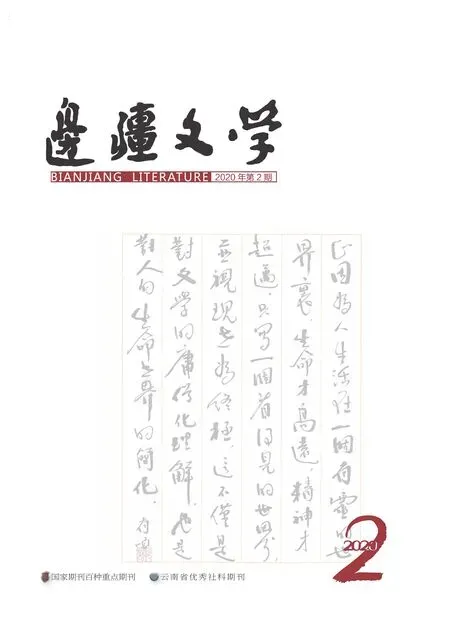明如白昼
[短篇小说]…………………………………………………………………·
1
“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手机屏幕上赫然出现这行字。
路平似乎并不觉得意外,干脆地点了“返回”键。屏幕随即出现他一开始点进去的那行字:“今天全福源县都在疯传这个畜生”。这行字的前面有张正方形的小图片,图片上,一个小孩骑坐在一个男子双腿上,男子赤裸上身,肥腻得要流出油来,小孩很小,面朝男子,从头发判断,应该是个女孩。
路平盯着这张图和这行字陷入了思考。难道这男的强暴了这个小女孩?那他当然是畜生了,毫无疑问。看起来,也还有另外的可能,比如说,这男的是小女孩的父亲,那么他就更是畜生。如果说前一种情况他是一条狗,那么,后一种情况,他只能是一条疯狗了。他究竟是哪一种狗,很难得出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男的是福源县人。你看,是福源县人而不是别个县的人在疯传他嘛,那他当然是福源县人了。咦?不对,不对,也有可能,小女孩是福源县人,她被这男的害了,福源县人为她愤愤不平。啊!不对不对,根本就不是这男的把小女孩害了,而是其他的什么人,用了极其下作的手段,而这男的是孩子的父亲,她正在安慰自己的女儿!这么一想,这张指甲壳大的图片好像没有那么糟糕,甚至还有点温馨,看啊,做父亲的那巨大而温暖的怀抱……
越想约没头绪。类似的故事,他看得太多了,以至于随便提供点信息就可以有无数种拼凑组合的可能。况且世界这么奇妙,手机上信息这么多,还有多少故事是他没看过的呢。总的来讲,他怎么想象这些人都不过分,现在的人,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路平在心里嘀咕着,一边用手写输入法打了一行字,打完后小声念了一遍,点击发送:“万能的朋友圈,请问谁知道,2017年6月20日,全福源县都在疯传的那个男人是谁?”发送出去后,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在评论区加了几个字:“哦!不对,不是那个男人,是那个畜生。”
路平是在刷自己的朋友圈,那条关于畜生的消息是他自己以前分享出来的,显然,他早已忘记了所有的细节了,脑海只留存着一个极模糊的印象——好像点进去看完以后,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
他接着往下刷。接连刷过好几个小视频,都是他在温州录的。“这么大的胶带,你们猜咋用?”“好大的雨”“没有办法了先来工地上混两天”“出车祸了”“专业办各种会员卡正规工厂”。他点开“出车祸”那条小视频,只见一个人被大卡车碾压在地,一个女人抱着婴儿坐在旁边,掏心掏肺地嘶吼。“我操,太惨了!”他摇着头,不禁说出声来。再往下刷,看到一张照片,一碗红汪汪的面条,面条里埋着个鸡蛋,像个小光头露出后脑勺,配文:“吃早点了,大家”。他舔了一下嘴皮,喉结鼓动了一下,又接着往下刷。
他在这条上停留了很久:“杀鸡吃”。一只被开膛破肚的光鸡仰在砧板上,被掏空的胸腔首先抢占了路平的注意力,从这个中心点向外,能看到两支鸡腿,两支鸡翅和一截鸡脖子。鸡脖子没有连着头,鸡头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是两个月前在义乌杀的鸡,路平一个人杀,一个人吃。一刀从中间砍成两半,左半边做黄焖鸡,右半边做辣子鸡,鸡脖子、鸡脚、鸡翅放在一起卤了。路平做菜是不错的,他总和别人说,他还没学会说话就先学会做菜了。他还记得那只鸡的味道,只能说一般般。卖家说是土鸡,但他知道不够土,顶多是土杂鸡。要命的是,那只土杂鸡一般般的味道现在却从他的牙根深处直往外冒,搞得两腮一阵发酸。他用拳头揉了揉腮帮子,叹了口气,抬头看路,正巧看见一家鸡排店,快十二点了,还有人在排队。他能听到油炸鸡排的滋滋声。
还有肚子的呱呱声。
2
路平在等路宽的消息。
路宽是路平的堂哥。说起来,给路平取这个名字,是家族几代人第二次发现,姓氏还有这等妙用。第一次自然是给路宽取名字的时候。路宽的路还真是宽,前两年在一口煤窑上做事,后来煤窑垮了,又钻到镇上当起了交通协管员。路平有时害怕想起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个名字,也觉得这个名字对不住自己。路平想起自己名字的时候还一定会想起路宽,他讨厌想起路宽,但他总忍不住追根溯源,哦,我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路平现在就顺藤摸瓜想到了路宽。啊,多拽啊,这张车罚两百,那张车罚两百,天天公款吃喝开警车,作威作福啊。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念头:路宽对不起他!路宽占尽了家族智慧首次升级的所有便宜!他面有愠色,愤怒的斤两加重到了脚步上。他觉得三千块钱借少了。不,那根本就是路宽欠他的。
“你的账户已入账3000.00元。”路平在等的是这条信息。它还没来。那个该死的小数点让他很是纳闷,但他还是忍了。两个小时后,他懊悔地告诉自己,别说小数点,就算把那五个零都全部去掉,他也是能忍的。就好像路宽给了他三块钱而他嫌太少没有接受一样。事实上,从始至终,路宽连三分钱也没有发给他。
路平同时也在等段小超的信息。段小超是他的小学同学,在大理卖牛奶,混得还不错,过年回家常常把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也总是他买单。路平在和人谈起身边的牛人牛事时,段小超总是在榜的,“小学都没读完,现在干大老板”,这句话是标配。只有一点,路平对段小超感到不满——这人太喜欢讲笑话了。见人就讲,不等讲完就笑,重复讲,重复笑。可恨的是,挂在他嘴边的诸多笑话中,有一个是路平小时候的真人真事。只要他们两个同时出现,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在场,不管在场的是其他的什么人,段小超的脸上都会挂起无比真诚而疑惑的表情。粗声粗气地把这个笑话演出来:“大妈,不知道我该怎么称呼您?”然后放声狂笑。一想到自己不在场的时候段小超也一定把这事当笑话和形形色色的人讲了无数遍,路平就恨得牙齿打颤。但不管怎么说,段小超混得好,又是同学,他这里机会比较大。
从云大医院出来,沿西昌路、滇缅大道已经走了很远。具体有多远,路平没概念,前天,飞机降落长水机场,他才第一次到昆明。他只觉得路灯越来越少,越走越暗了。再走下去,没准就出了昆明城了。于是他向东拐到了学府路上。学府路的路灯也特别稀疏。这让他想起温州来,温州很亮,哪怕在他们偏僻的胶带厂附近都灯火通明。
朋友圈有了新的动态提示,在他最新发出的那条消息下,有了两个新的回复,分别是“狗”和“狗日的”。他给“狗”回了表情“机智”,给“狗日的”回了表情“笑哭”。
他把提示音调到最大,一路上都捏着手机。他衣服上有好几个口袋,还背着个包,但那手机无疑是一件不能被遮蔽的东西。他还在等另外好几个人的信息,对于这几个人,他几乎没有把握,也许人家早睡了,根本不会理他。但没有句准话,他还是不死心。
除此之外,他还在等凌晨一点二十五分的到来。
3
借着家里取名的智慧,路平早就想好要给自己的子女取什么名儿了,男的就叫路路通,女的就叫路通露,他确信,叠词和谐音的巧用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家族智慧。但,说一千到一万,在此之前,他得先找个媳妇。
在学府路上,他想起了四年前的那次逃婚。
四年前,他从广东转到浙江,跟家里汇报的原因是:他不太听得懂粤语,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展,换一个讲普通话的地方,肯定会做得更好。家里信了。就算不信,他们也决计想不到,路家最急人的老大难,千真万确经历了一次逃婚,亲手把做梦才能到手的肥肉扔了。
那时路平在深圳一个电子厂做工。如果你有他的微信,现在还能刷到他当年晒在朋友圈的两块工牌,一块晒于2009年2月12日:莲花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第四车间,装配工,路平,工号2503;另一块晒于2013年5月5日:莲花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第四车间,装配小组长,路平,工号2503。
他认识肖红燕,正是在2013年5月5日。那天,电子厂开职工大会,唱响“劳动者之歌”,职工们看了热热闹闹的表演,吃了很多瓜子、水果,喝了很多饮料。最令人激动的环节,是宣布职位调整的决定。路平听到自己的名字后,一口气喝了半瓶雪碧,打了好几个嗝。当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三点,他用手机扔出了三个漂流瓶,瓶内装了同样的内容:“2013年5月5日,我成了我们车间装配组的一个小组长了。”其中一个漂流瓶马上被肖红燕捞了起来:“恭喜!不容易吧?”当然,那时路平还不知道她叫肖红燕,她的网名叫“习惯囿你”,头像是脸部自拍,但用美图软件做了不得了的点缀,鼻子上是颗黑色的爱心,两颊各长出三根黑须。
路平被这只猫打动了。世上所有的打动大概都源自对比,这一次也不例外。只需看看另外两个漂流瓶的回复便可明白——“恭喜!”
此后将近5个月,每天晚上他们都聊至深夜,路平一辈子也没打过那么多字,没对着手机说过那么多话。他们具体聊了什么,我只能摘要说明。而他们对对方的称呼的变化,我倒是可以全部列举出来:你,你;路平,肖红燕;大路,肖红燕;大路路,肖红燕;路路,红燕;小路路,红燕;亲爱的,红燕;老公,燕燕;老公,你;你,你。
肖红燕比路平小七岁,是深圳华强北一家品牌服装店的销售员,家在清远市阳山县,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全都成了家,就她一人在外打拼,无牵无挂。她说她是一个“等待被人领养的大龄孤儿”,问路平敢不敢要。路平说:“你知道的,我胆子不大,但心肠最好了。”
他们俩最终还是确实面临了“领养”的问题。那天,肖红燕发来一大段话:“老公,明天,就明天,你和我一起回阳山,我们把证领了吧。这一次,我是非常认真的。虽然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但我无条件相信你,这在别人听来可能太荒唐了,但是,你不也是同样的相信我吗?我知道你工作很不容易,家里负担也重,我不想也不会成为你新的压力,相反,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这几年,虽然苦,虽然累,但我还是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卖出来大几万块钱了,咱俩凑一凑,在深圳找个小生意做起来,日子不会差。或者,只要你愿意,都听你的,留深圳也好,回福源县也好,去别的任何地方都行,只要跟你在一起。老公,我最后警告你一次,我跟定你了!明天,我在华强北等你,你不来,我就自杀。”
看着这条信息,路平陷入了幸福和惊慌。如果这幸福和惊慌可以放到天平的两边去称,那么我们将看到难以置信的一幕:天平变成了跷跷板,翘翘板上还装了永动机。
第二天,路平来到华强北,战战兢兢地路过了所有的服装店,把服装店里所有的店员匆匆瞅了个遍。华灯初上,他颓坐在一把公用椅子上,把肖红燕满屏的信息又看了一遍,终于回了一条过去:“对不起,我决定离开深圳了,明天就走。我无法面对你,因为我一无所有。我相信你会好好的,因为我永远爱你啊。”
第三天华灯再上的时候,路平已经到了温州,在村里一个叔叔的工棚里住下了。出乎意料地,他没有过多地想和肖红燕的事,他静静躺着,在回味坐飞机的感觉。原来,坐飞机和做梦差不多,一个恍惚,就相隔千里,就是两个世界。
前天到昆明,是他第二次坐飞机。他现在的感觉是,如果真有选择,他也许不会做这场梦。
眼看着时间走过了凌晨一点,这座城市显出昏沉的睡意,不时有车驶过,刷刷刷地,但并不真切。偶尔出现的路人就更不真切了,他们更接近鬼魅和黑影。路平脚下一阵酸痛,便在一个路障石球上坐了下来。一坐下来,他就感觉前胸、后背、肚子全都贴到了一起。但也只是贴着,太晚了,连饥饿也折腾不动了。路平点开一个对话框,在手写板上画了两笔,一撇一捺,正欲写第三笔时,他猛然注意到手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电量了,便立马按了锁屏键。
4
凌晨一点十分,电话响了,路平猛地从石球上跳了起来。电话那边吵得一塌糊涂,像是从酒吧、KTV之类的场所传出来的声音。手机听筒明显驾驭不了那声音,忽远忽近,忽大忽小,不时还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
“路老表,回来么,来,来喝酒了嘛!”段小超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像面坨被拧成了麻花。
“段老表,喝酒好说,好说,你在哪里,老表来找你!”路平提起一股气来。
“苏,苏荷,酒吧,赶紧来,学生妹,妹多得很!”段小超显然是醉了。
“好好好,一定来一定来。是在哪里?哪里的学生妹酒吧?”说这话的时候,路平心口纠成了一团,左手扬到心口握起了拳头,像监考老师使劲憋着一个答案想告诉某个急死人的学生,这个答案就是:“昆明啊,我在昆明!”
但电话里传过来的是:“大理啊,老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老子在,大理!你来不来?不来算毬!”
“老表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想来跟你喝酒啊,问题是,老表混得惨了,现在连昆明到大理的车费钱都没有。你看——”路平还没说完就被段小超抢了话头:“莫废话了,老子还认不得你,发个支付宝账号来,我一分钟打给你!嘟——嘟——嘟——”
这电话挂得猝不及防,路平刚要切入正题,但终究没能切入正题。不过也不错了,段小超还算仗义,哪怕他随便打个一百两百过来,也能饱餐一顿,找个地儿睡上一觉,明天再从长计议。路平忙不迭把支付宝账号给段小超发了过去。
一点十五分,他的耳边开始出现硬币落入存钱罐的声音,一遍又一遍,振聋发聩。那是支付宝款项入账通知的声音。夜渐渐凉了,他揉了揉太阳穴,转了转眼睛,搓了搓耳垂,甩了甩头,生怕幻听盖过了款项真正入账的声音。
一点二十分,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一,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二,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三,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四,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五,没有钱入账。
一点二十五?一点二十五!
路平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心狠狠地跳了几下。凌晨一点二十五分已经真真切切地到来了。
他慌忙打开微信,快速发出了一条信息:“欣欣,我到了,安全落地。我几分钟就到住处了,你早点歇着,晚安。”
5
除了善意的谎言,三十五岁,路平再一次一无所有。
他肚里泛起一股自怜自艾的胃酸,这胃酸正蚕食着他的五脏六腑。凉风习习,他的皮肉正一层层变薄。他有预感,再坐下去,整个人将会毫无声息地化掉,剩下一套衣服、一个包、一部手机落在石球上。
他起身继续往前走。
欣欣还没回信息过来,她现在会在干什么呢?也许太困了睡了?也许黄大妈又呕吐了又抽搐了她根本腾不开手回信息?真是够人受的。
有些人就是命好,像路宽那样的人,要不是命好,他凭什么?有些人就是命差,且不说自己,欣欣就是个命差到极致的可怜人。路平会这么想,并非因为欣欣很可能要和他订婚,要成为他的未婚妻了(他们的孩子将取名路路通和路通露),哪怕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十分同情欣欣。
欣欣比路平大一岁,但看上去始终是个小孩。她很早就停止长个儿了。这也许是她全部不幸的根源所在。因为不长个儿,玩伴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她,议论她,开她的玩笑。后来就干脆没有玩伴了,她童年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小皮球。因为不长个,老师、同学、整个学校都把她视作某种焦点,她受不了陌生人的逼视,以至于念到三年级就退学了。因为不长个,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也不会饶过她,去ATM机上取个钱,都得带着个小板凳。因为日复一日地不长个,家人们耗尽了怜悯和耐心,心里日复一日憋起来的怨气,一次爆发,便次次爆发。人们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外表不重要,外表确实不重要,但人们永远抵抗不了外表带来的感官反应,这是本能,而不承认本能是虚伪透顶的。有时候,欣欣倒愿意有个人跳出来,手指头挖到她额头上骂一句:“你他妈真丑!”但是没有,从来没有人这么堂堂正正地骂过她,这正是这个世界全部恶意的真正所在。
同情归同情,必须承认,与欣欣有关的一切,路平从来都只是远观,他最多能做到,别人调侃欣欣的时候,借机走开,或至少不附和他们。直到路宽妈和黄大妈成为了好朋友。
路宽妈和黄大妈是突然成为好朋友的,促使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路宽在镇上当协管员,欣欣的二哥是县里的正式交警。也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欣欣的二姐在镇上跑黑车。总之,她们俩突然就像村里的每一对老闺蜜那样,无话不谈,并且看起来永无尽期。
自然而然地,她们谈到了各家的烦心事。其实也就是欣欣嫁不出去、路平娶不着媳妇这两件事。她们在同一瞬间发现,只要把两家的烦心事进行并置,就会得到一个欢天喜地的结果。她们都在心里暗喜,但也都感到难以启齿。紧接着,她们又在同一瞬间发现,原来双方都把自己看得很低,并不存在心理上难以调和的错位,于是她们坦诚相见,路平和欣欣几乎就成了一对。
路宽妈先斩后奏,以不容商量的好意施惠的口吻和路平妈说了这事,路平妈十分感激,当即在今年过年前把路平召了回去。路平得知此事后,有点难以接受。这是必须承认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但当他心里隐约泛上瞧不起欣欣的情绪时,又不免质问自己,人家都没有嫌弃你,你凭什么瞧不起人?他卡在了可否之间,无法决断。路宽妈不厌其烦地冲到家里来警告:“可以了,路平!你还有什么可挑的?癞蛤蟆是吃不到天鹅肉的,这人呐,要认命,要看清楚自己的条件!”表面上看,路宽妈这话所蕴含的道理,和卡在路平心里的东西是同一内涵,但他又明确感觉到某种差异,苦于他说不出来这差异在哪里,他恼怒极了。而越恼怒,他就越是迷惑,脸就越是胀红得像一个气球,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路平答应和欣欣好,是因为他最终想明白了那份差异之所在:他自怜,但他对自己还有心气;他或许真瞧不起欣欣,但他始终承认欣欣拥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但路宽妈不一样,她发自内心地将他们视为了丑小鸭和癞蛤蟆。路平为此义愤填膺,他青筋暴起,突然决定要证明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他斩钉截铁地答应和欣欣好的瞬间,他感到自己变成个一个骑士,身穿宝甲,手提长戟,扬鞭跃马,踏上了复仇之路。
6
学府路好像比滇缅大道长多了,又走了许久,依然在这条路上。
路平合计着,要是黄大妈不生这么重的病,最多再过一个月,他的钱也就差不多够回家订婚了,甚至可以接着就把喜酒办掉。现在,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过年的时候,他将仅有的五万块存款尽数交给了老父,请他在家扩修房屋,再打个水泥院子,这样,结婚的时候就能“亮堂些”,“远亲来了也有个在处”。2月,他离开工地,进了一家胶带厂,胶带厂不算工时,领计件工资,多做多得。半年来,他开源节流,横竖存下了八千块钱。他看过一个奶茶广告,说一年卖出去的杯数可以绕地球一周,他照这个例子算了一下后发现,这奶茶也不过如此。很有可能,他半年做过的胶带可以把整个地球蒙得严严实实的,而他闻过的劣质PVC的气味,可以把地球上所有的会动的东西通通毒死。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路平很久:“不断朝银行卡里打钱,卡会不会越来越重?”那八千块钱最终证明:卡确实会变重。但就在昨天,那张沉甸甸的卡变成了纸片。人们常说“花钱如流水”,其实配说这话的,须得是真正的有钱人,钱没多到一定程度,又如何能像水一样流起来?看吧,路平这八千块钱,水龙头还没拧到底,就宣告结束了。一千块买了机票,三百块买了探望病人的脑白金,三百块请欣欣一家吃了顿饭。剩下的六千四百块钱,是这么花掉的。
在三百块钱的饭菜前,人们埋头苦吃,一言不发。这些人,路平早都是见惯了的,但在那张饭桌上,他又对他们大感陌生,可能是因为对他们的称呼变了吧: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二姐,小姐,小姐夫。路平感到一阵局促。欣欣坐在他旁边,他很快觉察到,欣欣同样局促不安。路平想,这样不行,必须有人先开口,说点什么。
于是他开口了:“哥,嫂,姐姐姐夫,随便吃点了哈。”
“这就不随便了,小路平,让你破费了!”小姐抢先应了他,速度非常快,仿佛前面所有的沉默都是为了说这句话。
“就是就是,你看看,这虾子,大个大个的,这火腿,红汪汪的,大鱼大肉的,样样都好得很。”小姐夫附和了一句。
“哪有哪有,大家随便吃点,随便吃点。”路平笑笑。
“小路平,你在大城市混过,你给我们讲讲,这不随便的,该是怎么个吃法?”大嫂埋头啃着炸排骨,没拿正脸对人。声音实在太尖,直让人想蒙耳朵。
路平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大嫂,那我哪能知道,有钱人嘛,总归是什么都吃得起的,鱼翅燕窝啦什么的。”
大嫂吞了一口苦荞茶,抬起头来,一本正经地说:“可以了,我觉得这些也就够可以了。我们一个农村人,追求那些干啥,真有个好歹的时候,你都恨不得把吃进去几十年的东西拉出来。”
二嫂哈哈笑着补了一句:“大嫂啊,我们这些老农村人的吃食,你就是把几十年的油汤油水一次性拉出来,买得着妈妈早上那小支针水?”
二姐骂了一句:“这些狗日的药,卖的是仙丹的价格,起的是面粉的效果。你看妈妈这几天,花了多少钱了?还不是话都不会讲一句!”
大哥无奈地叹了一声:“才开始咯——”像格里高利圣咏里的持续低音。
二哥附议:“是了嘛,天晓得还要花多少钱。老人家还受罪。”
“嗯!”齐活了,欣欣补上这一声“嗯”,每个人都算是发过言了。
于是,二嫂对着二哥开始了第二轮发言:“算起来,每家花了多少钱了?”
二哥支支吾吾算了一下:“一时算不清啊。”

谢有顺 书法
大嫂语速极快:“算不清?我看太好算了!告诉你,我看了,我们男的两家,有十文百文,迟早都是要见底的,而且只会早不会迟。想想,真见了底也好,见底了也没有说头了,总不能逼人卖身嘛。”
小姐:“哎哟,大嫂,你太夸张了,二姐我不敢讲,就我自己,出着多少我都和你们摊。”
小姐夫连连点头:“摊!摊。”
二姐表态:“真的是,我大嫂说得太难听了。是不是男丁不管,妈是大家的妈,我家条件不如小妹家,但心都是一样的。”
大哥又唱起了圣咏,这次只有一个字:“哎——”
众人再次陷入沉默。每个人找一个地方盯着,此起彼伏地咽咽口水。
第二轮谈话还剩欣欣和路平。
路平感觉椅子上慢慢长出刺来。他意识到,欣欣的椅子上可能早就荆棘丛生了。
他在刺丛里忸怩了几下,随即果决地抓过背包,拿出那张沉甸甸的卡递给了欣欣:“欣欣,这个里面有几千块钱,不多,你先拿着。能帮哥哥姐姐们一点是一点。”
路平这话一说完,席上所有的椅子都长出刺来,或柔软,或坚硬。
7
满脑子装着黄大妈惊厥的脸,路平艰难地走到了一个公园门口。他又在门前的阶梯上坐了下来。
手机只有百分之十的电量了。
段小超依然没有打钱过来。会不会是他玩得太疯,挂上电话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要不我还是提醒下他?路平拨通了段小超的电话,这一次,电话那头很安静,极轻微的窸窣声衬托着这份安静。安静了有两三秒钟,段小超都没说话。
“段老表,睡掉了?”路平压着声音试探道。
“嗯——嗯——”段小超这两声像在打鼾。
“段老表,不行,你还是得帮我想想办法!”路平急切地说。
“嗯——嗯——你是,哪个?”段小超貌似还醉着。
“我操,老子是路平啊!”路平急了。
“哦,路平。”听得出来,段小超讲话根本没动嘴唇。
“段老表,我是问你,你那差不差卖牛奶的,我来和你卖两天。还有,你讲给老表打钱的,打到哪里去了?”路平有点在吼的感觉,企图叫醒段小超。
“嗯——嗯——账号,你发,账号,嗯——嗯——”段小超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电话挂上,路平喘着粗气,把手机拍在了大腿上。
等气喘顺了,他下意识地扭头,想看看这是个什么公园。他一字一句读出公园的名字:“莲花池公园”,读完一遍,又从头读了“莲花”两个字。他想起了莲花电子厂。
想起莲花电子厂就等于想起了肖红燕。
他无法抑制地想起了肖红燕。她的漂流瓶回信,她的文字、表情、语音、照片、视频,她的电话号码,她的生日,她扬言要自杀的求婚短信,还有她卖衣服的华强北。肖红燕从来没有这么真切过,肖红燕仿佛第一次具有了肉身,路平只要伸出手去,就能感受到她的体温。
他突然决定联系肖红燕,他决定把最后百分之八的电献给她。他点开对话框,打了又删,打了又删,耗去了百分之一的电,终于打出来两个字:“在吗”。
点击发送的时候,路平的心砰砰直跳。本来以为会跳上好一阵的,但就在消息发出去的同时,回复过来了。
“系统提示: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才能开始聊天。”
“她把我删了。”路平心想,“也是我该。”
在要不要重新添加肖红燕的问题上,又耗去了百分一的电。最终他决定添加。
他一点击添加按钮,屏幕上就弹出来一个小框提示:“该账号经多人举报,已经被封号。”
路平的颅内进了一阵冷风。他身处一个谜局,开始时战战兢兢,现在,他被这个谜吸引了,他甚至开始蔑视这个谜,他要把这个谜揪出来踩在脚下。
他义无反顾地拨打了肖红燕的号码。
手机里当即传来同样义无反顾的回应——“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8
路平直挺挺地坐在莲花池公园门口的台阶上。
直挺挺地坐着,连眼皮也不动一下。
终于动起来的时候,手机还有百分之三的电量。他打开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畜生。”
接着,他背起包,捏着手机,重新回到了学府路上。
时间早已过了两点。车道上依然少不了刷刷声。
路平加快了脚步,很快。
他一边疾走,一边扫视四周。他希望路上出现一个黑影。
黑影出现了。黑影似乎是突然出现的,路平感觉自己盯住了所有的角落,却是在恍惚间确认了那个黑影的出现。说“出现”,或莫不如说是某种“降临”。
深夜的空气很好,路平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放慢脚步,力图自然而然地靠近黑影。他目测着那个矮小的、干瘦的、丑陋的、愚蠢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死活的、踽踽独行的黑影,设计了一万种擒住他的方式。
越来越近,学府路昏暗的灯光还是让黑影显出了一点人形。估计那人只有十七八岁?大概是个逃学出来玩的高中生?他终于扔掉可恨的双肩包,换上了心爱的束口包?束口包里没准放着一台打游戏的高配平板电脑?或者会有从家里偷出来的几千块钱?谁知道呢。现在能确定的是,他低着头,仅有的一点儿侧脸被手机屏幕照亮了。
路平这才意识到,自己仍然把手机捏在手中。他按亮屏幕看了一眼:时间两点五十九,电量百分之一。他迅速把手机滑进了裤袋里,他决定,在一分钟之内完成这件事。他健步上前。他脑袋里只有这个黑影。
距离黑影最多三米的时候,路平感到一根滚烫的血柱从心里直直冲上天灵盖。就是现在了!他决定下手。他刚想跑,却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窄小路口,而黑影一侧身就从那儿拐了进去,身法很是敏捷。借着那根血柱的强大冲力,路平终究跑了起来,他像一道闪电,飞快地闪进了路口。就在闪进路口的一瞬间,他感到眼前一阵刺亮,紧接着,他听到了自己倒地的声音。
三五个少年干净利落地拿走他的包和手机后,他发现自己可能被人敲了一棍。
他躺在坚硬的地板上,后脑勺突突突地跳,像要把地心钻通。他睁不开眼睛,他感觉有个太阳一样的大灯照耀着眼皮外的一切,让这世界明如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