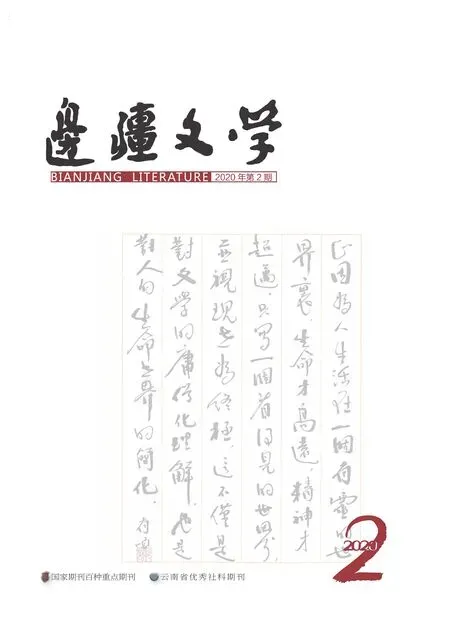飞鸟集
[散文]…………………………………………………………………·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泰戈尔
麻 雀
我开始认真注意起麻雀来,是我在绥江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在我们班,有一位姓周的同学,使得一手好弹弓,他时不时就会带我们几个同学去打麻雀。我没有记错,这位同学确实姓周,门吉周。这位姓周的同学,来自当时的绥江县城。本来当时把县城所在地,归为上半县,这里的中学生读书在县城的第一中学,不用跑很远的路。周同学不应该到第二中学来上学的,可他却偏要在这里上学,这成为我很长时间都没法解开的谜。
可能因为来自县城,周同学和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比,还是会有很多不同。比如,他穿的衣服就比我们光鲜。我记得,周同学的衣服一直都很新,夏天总是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米色裤子,据说布料是凡尼丁,裤线熨得很平直;冬天穿着毛线衣,外面是一件铁灰色夹克衫。我就不行了,经常穿的是毛蓝布裤子,是当时在乡下比较流行的那种笼扣裤,腰上缝了松紧布,这样就不用系皮带了,那时我买不起皮带来系。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穿在身上的衣服,还打着很大的一块补丁。照毕业照,对一个学生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人看来,会有很强的仪式感。同学们都把最好的衣服穿上了,唯有我,穿着这打了补丁的衣服,但肯定也是我那时最能穿得出来的了。若干年后,生活明显好转,有时翻看毕业照,我只会不甚唏嘘。
周同学不仅穿着跟我们不一样,一些举止也不一样。比方他爱玩弹弓,而且玩得很好。下课了,或者放学了,他会提了弹弓去打鸟,这样有不少的鸟就会死在他的弹弓下。周同学由于生活在县城,优越感十足,在班上成了不少同学追捧的对象。特别是他的弹弓玩得很好,弹射出去的石子,时不时就会把鸟打下来,让我们这些同学刮目相看。那时候,他用的石子,都是从金沙江边拣来的,非常讲究,一般都是指头般大下,呈扁平状,大了和小了都不行。那时候,能够给他拣石子,会是一种荣耀,特别是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就更会是一种幸运。我时不时也会去江边拣石子送给周同学,周同学从我的手里接过石子,看了看,就揣进了口袋里,不说话,但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我于是就远远地跟着,看周同学打鸟。
小麦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小麦不像水稻,成熟了会低着头。小麦总是昂着头,一点也不懂得低调。可这最能够招来鸟雀了,特别是这些叽叽喳喳吵闹个不停的麻雀。最喜欢到麦田里啄食的也自然是这些麻雀。而麻雀也是周同学最愿意用弹弓射杀的。麻雀总是站在麦穗上,用尖尖的嘴啄食金黄色的麦粒。它不知道,这时候会有一张弹弓正对着它,那一粒冰冷的石子正在飞快地向它飞来。只听得啪的一声,一只麻雀应声掉进麦地里。也有往前飞一小段距离的,那更多的倒像是在扑腾,更像我们所形容的,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麻雀被击中以后,去捡麻雀的,大都是跟周同学走得更近一些的同学,这会让捡麻雀的同学像喝了兴奋剂,飞快地向麻雀被打中的地方跑去,很快就会把麻雀捡回来。捡麻雀这样的机会,一般都轮不到我。
一群同学还在麦地里走动。往往一只麻雀被击中了,没被击中的会很快飞走。不过它们很快又会在不远处的麦地里开始啄食麦粒,这金黄的麦穗实在太诱人了。我想,做为鸟,也很难躲开这种诱惑。鸟为食亡,我算是真正看明白了。就在它们满心欢喜地啄食麦粒的时候,一只麻雀又被周同学击中了。这回周同学要我去捡被他击中的麻雀。周同学指着我说:“这回你去。”见我没动,又说,“别站着,说的就是你。”我看见周同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我却像得到了一件很早就想要得到的礼物一样兴奋。
我赶紧往麻雀被击中的麦地里跑。跑到麻雀被击中的地方,我看见有两株麦穗的麦杆被折断了,麦穗向下耷拉着,不像其他麦穗那样骄傲地昂着头。我知道这两株麦穗被周同学的弹弓击中了。我开始在地上寻找被周同学击中的麻雀,我在一蓬蒿草下面看见了这只麻雀。这只麻雀还没有死,它只是一只翅膀被弄伤了,只会在地上扑腾,却飞不起来。受伤的麻雀先是用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就更加疯狂地扑腾,可这些都没有用,它根本就飞不起来。麻雀扑腾累了,就不打算再扑腾了,而是用一双绝望的眼睛看着我,全是愤怒和恐惧。不经意间,我看见从麻雀的眼里流出来了泪水,亮晶晶的,我相信这一定是麻雀伤心的泪。当我抓住麻雀的时候,它先是挣扎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它或许知道再挣扎也不会有用。这只麻雀还活着?它是这么可怜!我没有多想,就把麻雀放在旁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再捡来一块石头把石缝严严实实地堵住。我跑回来对周同学说:“没有找到,只是打中了麦穗。”周同学说:“这怎么可能,你是在怀疑我的眼力不是?我亲眼看见打中的,你们哪个再去找。”周同学回过头来对我说:“不是我说你,你确实没用。”
后来我还知道,周同学打麻雀,不是简单地打着玩,而是把它当着一种野味来获取。据跟他走得近的一位同学说,他常常会打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然后做成红烧,味道好极了。我说:“麻雀就这么大一点点,还要去毛、去内脏,有什么吃头?”同学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麻雀要是像我们喂的鸡一样大,这才没有吃头。”我知道这位同学住在一个小集镇里,父亲和母亲都有一份工作,有工资收入,时不时的,就会买一只鸡来改善生活,所以同学说起来才会这么轻描淡写。我们家那时也养鸡,可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吃,母鸡就让它下蛋,公鸡长大了就捉到乡街上去卖。卖鸡蛋和卖公鸡的钱,那可是我们一年的油盐钱、衣服钱,也可能是我读书的书学费。同学还说:“把麻雀做红烧,一定要多放些油,说是红烧,更像煎炸,还要多放些辣椒、花椒、葱姜蒜,这样的麻雀吃起来会很香很脆,你都可以不用吐骨头。”不知道为什么,听同学这样一说,我忽然想吐,我忽然想起那只被周同学打断了一只翅膀的麻雀,它曾经在我面前扑腾,它看我的眼光是那么迷离,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我记得,就是在那次我忽发奇想,宁肯失去周同学对我最初的信任,也要放那只被他打伤的麻雀一条生路。把麻雀藏进石缝以后,我回来佯装没有找到,这让周同学非常不满。他让其他同学再去找,可又怎么能够找到。等同学们都散完了,我悄悄走过去看。我取下那块堵石缝的石头,我希望这只受伤的麻雀还活着,然后我就会摘一株或者两株麦穗来喂它,一定让它吃饱。可是石缝里已经没有了麻雀,我用眼睛看,没有看见;我又用手去掏,也没有掏着。我不知道这只麻雀是死是活,或者是去到了哪里?我怅然若失地离开那块麦地。没有找着,周同学肯定不会再让我跟他去打鸟了。事实上,我也懒得再跟他去打鸟。我时不时会来到金沙江边,看浩淼的江水怎么东流。有时候在江边还会看到很多好看的石子,我也懒得拣。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拣那些很薄的石块,在江水里打水漂玩,看石块到底能漂多远,能够漂得很远我就会很开心;如果这些石块在很近的地方沉入水底,我就会觉得很没劲,觉得这太没有意思了。
再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我们也好像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前途。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都开始认真读书,认真听老师讲课。周同学也想认真读书,认真听课,但他平时野惯了,已经很难得安静下来。他还是要跑出去用弹弓打鸟,打那些麻雀,可已经没有同学愿意再跟着他了,他一时间成了打鸟的孤家寡人。我记得,初中毕业,我们不少同学都考上了高中,可周同学却没有考上,这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周同学来自县城,是城市户口,考不上高中对他不会有丝毫的影响。据说他回家以后,很快就被招工安排了工作,我们对此都很羡慕。谁叫我们这些同学都来自农村呢!我们只有努力学习,把高中读完,然后再考上中专或者大学,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作。
前几天,我们一群同学在一家餐馆聚会。席间,忽然有同学说要点一盘麻雀,称这家饭店的麻雀做得很不错,口味地道,特别好吃。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些不法餐馆会悄悄弄一些野味来卖,这我是知道的。还没等有人表态,我第一个站起来反对。我说麻雀就不要点了,个头这么小,骨头又多,还肉少,有什么吃头。我这样说话,再没有人说要点麻雀。不过吃着饭,有同学忽然提起这位周同学,说那时他可是玩得一手好弹弓,一些鸟雀见了他,都会怕他呢!尤其是那些个头很小又飞不高的麻雀,这周同学简直就是它们的天敌。我们忽然想起来要打听一下这位周同学的近况,可没有一位同学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在做什么工作?
麻雀是雀科雀属的鸟类,俗名霍雀、瓦雀、琉雀、家雀、老家贼、只只、嘉宾、照夜、麻谷、南麻雀、禾雀、宾雀,亦叫北国鸟(个别地方方言又称呼为:家雀、户巴拉)。雌雄同色,显著特征为黑色喉部、白色脸颊上具黑斑、栗色头部。喜群居,种群生命力极强。是中国最常见、分布最广的鸟类,亚种分化极多,广布于中国全境,也广布于欧亚大陆。世界共27种,其中5种分布在中国境内。其中树麻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麻雀,其他种类如山麻雀、家麻雀比树麻雀少见,生活环境也有所区别。
这段文字是我无意中在电脑上百度到的内容。麻雀还有这么多名称,这么多种类,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真是长知识了!更重要的是,我还知道麻雀已被国家列为二级保护鸟类。用法律来阻止人类的杀戮,也许这才是对麻雀最有效的保护。麻雀,你此时应该感到幸运才好。我想起当年藏在石缝里的那只麻雀,它当时的眼神是那么无助和悲伤。事实上,麻雀并没有妨碍我们什么,即使就是偷食了几粒麦粒和稻谷,我们也找不出对它进行大肆屠杀的理由。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窗外忽然飞来一只小鸟。我看清楚了,竟然是一只麻雀,要知道这是在城里啊!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飞来的,一只麻雀。
乌 鸦
好久无梦,忽然做起梦来,可梦见的却是乌鸦。梦中,我和一群乡下孩子,在一个名叫杉树坪的地方,正在一棵杉树上掏乌鸦窝。杉树坪长满了杉树,杉树长满了针叶,像刺猬的刺。一个名叫华金的熊孩子,正在攀爬一棵杉树,这棵杉树无疑是最高的,真的都可以称之为参天大树了。在这棵杉树的高处,枝丫繁密的地方,有一个乌鸦筑的窝。此时,华金像一只灵猴,一双脚夹住树干,一双手紧紧抱住树干,奋力地往上攀爬。爬一段,就停下来歇息,可能是太累了。我们在下面给华金加油,我们不停地喊:“加油,华金加油!加油,华金加油!”华金在我们的加油声中,又费力地往上爬去。这时,忽然从乌鸦窝里飞出来了一只乌鸦,朝华金飞去,看样子是要飞过来啄华金。一会儿,又从外面飞来一只,同样向华金飞去。华金很快就要面临两只乌鸦的攻击。我们这会不是在给华金加油,而是齐声喊华金快下来。可是晚了,只见两只乌鸦向华金飞去,华金发出痛苦的一声喊,就从杉树上栽了下来,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看见两只乌鸦在我们的上空,划出两道黑色的闪电,那一刻我好像还听到了雷声……
窗外这会下起了雨,还伴随着雷声。刚才听到的雷声,不知道是在梦境里还是在现实中。但在我的记忆中,却真真切切有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掏鸟窝捅蜂巢,确实是我们这一群熊孩子爱干的事情。掏鸟窝被倒挂刺划伤了,捅蜂巢让马蜂蛰了,不知道痛定思痛,更多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我行我素,照样掏鸟窝捅蜂巢。我们一群乡下孩子在干这些烂事时,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危险。那次,我们一群熊孩子割猪草到了杉树坪,华金忽然看到在一棵很高的杉树上,有一个很大的乌鸦窝,还看见有黑色的乌鸦在窝里飞进飞出。华金说:“你们在下面等着,我上去掏。我敢肯定,窝里不是乌鸦蛋,就是小乌鸦。是乌鸦蛋我们就烧着吃,是小乌鸦我们就抓回去喂养。”我们一群小伙伴听华金这么说,都很兴奋。在我们这一群孩子中,只有华金最大。到那么高那么粗的杉树上掏乌鸦窝,也只有华金才有这个能耐。
华金说完,就把猪草背篼放下了。华金说:“你们等着,什么地方也不要去,等我掏到了乌鸦蛋,或者抓着了小乌鸦,见人有份。”我们被华金说得动心起来,都说不走。本来我的猪草还没有割满,还想找个地方割猪草。听华金这么说话,我也懒得割猪草了。接下来,就有点像我在梦中见到的情景了,唯一有出入的是,华金并没有从树上掉下来,而是他自己下来的。那时,只要华金往上攀爬,两只黑色的乌鸦就会飞过来啄他。这时,他就会腾出一只手来驱赶乌鸦,但不会有用。我们在下面见了,除了大声喝斥,还捡起小石子来向乌鸦扔过去,想把乌鸦赶走,可同样没用。只要华金还要往上面爬,乌鸦就会飞过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都要华金赶紧下来,说再这样往上爬会很危险。华金又试着爬了几下,无果,只好灰溜溜地从杉树上下来了。我们一群孩子望着那树枝上大大的乌鸦窝,第一次发现那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攻破的堡垒。
尽管我已离开故土,出来工作生活好多年了。可杉树坪和华金,就是我的梦魇。杉树坪一点也不平坦,而是非常陡峭。为什么要叫杉树坪,我想肯定是杉树多,还有就是在山顶有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平地。早些年,乡下人缺心眼,一小块平地,就要赋予杉树坪这样的地名,也没有什么好笑的。不像现在乡下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满世界跑,看到的东西多,经历的事情复杂,说起话来,比我这种住在城市里的人说起话来还要陡峭。还在乡下的时候,我们会时不时地到杉树坪,去弄一些杉树的枝丫,来作为烧饭用的柴禾。那时候,杉树坪的杉树,被划为国有林,比集体所有的林木还要高贵。那时,如果有人要盗伐杉树,是要以盗伐林木罪入狱的。实在是穷狠了,我二哥就因为砍伐过几根碗口粗的杉木,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在昭通一个名叫板板房的监狱服刑。若干年后,我二哥看见杉树,看见那密密麻麻的针叶,就会有如芒刺在背,不敢再去想那一段往事。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当时像他那样砍伐杉树的,还大有人在,有的比他砍得多多了。可最终去监狱服刑的,就只有我二哥。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替人背黑锅,这个世界不会完全公平。不过你要是只爬上杉树去砍枝丫,用来做柴禾烧,却不会有人管。可真正要爬上杉树去砍枝丫,却要吃很多苦,好在农村人从来就不怕吃苦。杉树坪留给我的记忆,永远都是那蓊郁的杉树林,那有如芒刺一样的针叶,和那爬上杉树砍枝丫的人们。
前几年,我忽然迷上了看足球比赛,尤其是欧洲的五大联赛。像英超、西甲、意甲、德甲和法甲,差不多都看。按说,我应该对曼联、巴塞罗那、尤文图斯、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尔曼这些著名足球俱乐部感兴趣,可我却偏偏记住了一个名叫皇家贝蒂斯的足球俱乐部。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位名叫华金的足球名星在这家俱乐部踢球。要是这个华金就是和我从小在一起玩的华金,又有多好。我是相信爱屋及乌的,我时不时就会联想到在乡下的华金。特别是联想到他在杉树坪攀爬杉树,准备掏乌鸦窝的情景,我就想,乡下的华金要是有机会到足球场上去踢球,说不定也会成为球星的。直到后来华金患上一种怪病,一直没有医治好,后来还为此陨了命,我就知道,同为华金,可这命却是完全不同的。每每看到踢足球的华金在绿荫场上卖力地奔跑,把足球踢成了一门艺术,我就会想到在乡下的华金,想到乡下华金的那种破烂不堪的境遇。后来,华金年纪大了,已经很少踢球了,我才知道,过得风光的华金和乡下过得潦草的华金,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走。和强大的时间相比,我们这些人其实就是一些过客,匆匆复匆匆的过客。
我记得,我当年在上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乌鸦喝水》。老师总是这样读:“一只乌鸦口渴了,它想喝水……”我们也就跟着老师拉长声调念:“一只乌鸦口渴了,它想喝水……”我那时就知道乌鸦确实聪明,为了喝到水,知道把石子衔来放进瓶子里,让水位升高,这样就能够喝到水了。联想到华金去掏乌鸦窝,乌鸦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节制,我就知道这乌鸦确实聪明。为了不让华金掏到它的窝,它会奋不顾身地飞过来阻止,只要华金不再往上爬,它就不再飞过来。它好像知道什么是适度,什么是分寸,所以它并没有啄华金,只是不断地向他示威。它或许也知道,真要把华金惹恼了,把我们这一群熊孩子惹急了,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就要学会悠着点了。
在我老家,乌鸦一直就没有什么好名声。我们那一带的人,都叫它老鸹,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吉利、阴森森,十分恐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们那一带,有两种乌鸦,一种全身羽毛都是黢黑的,这一种比较多;另一种在脖颈上会有一圈白色,我们就叫它花颈子老鸹。按说,那时候,生态环境还不错,适合各种鸟类生存,可不知为什么,乌鸦却很难得看到,偶尔会听到乌鸦的鸣叫,那都是从离我们很远的树林子里传来的。这时候,我爹或者我娘会说,老鸹叫得很狠,又有人要死了。以前我会深信不疑,乌鸦叫得很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看见有人送葬。送葬队伍一长溜,披麻带孝,空气都会被弄得很压抑。我那时还小,会感觉到非常害怕。后来读了一些书,才发现这乌鸦鸣叫,和死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能说是凑巧了。后来,我爹我娘再说,我就对我爹我娘说,这些都是谜信,不可信的。我爹我娘说,你不信就算了,我们其实也懒得跟你说。
我不知道,乌鸦总是离我们远远的,喜欢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树林里,是不是跟我们人类不待见它有关系。当然,也可能是它本来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性,要不怎么说得通呢?偶尔会有乌鸦飞到村子里来,不知是不是林子里已经没有食物了,所以要飞到村子里来寻找,然而还是离得远远的,一团黑影落在树上,时不不时会“呱哇——呱哇——”地叫上一声两声,弄得村子里的人更不高兴。这时候,就会有人向它扔石子,有更厉害的,会跑回家去把火枪抱出来,让乌鸦看见了,会大叫一声“呱哇——”,飞快地飞回到很远的林子里去。也可能是乌鸦感觉到了悲愤,回到林子里以后,会“呱哇——呱哇——”地叫个不停,这时,村子里的人就会非常紧张,他们知道,又有人不久将会离开人世。
我一直以为,乌鸦在我们那一带不受待见,跟它一身黑色的羽毛和叫声难听有关。至于乌鸦叫得太凶是不是一定会死人,这毫无根据,尽管老辈人总是这么说。但是,乌鸦长着黑羽毛和叫声难听,这是可以改变的吗?我想当然不可能。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对乌鸦的看法,表现出对乌鸦的善意。有一回,我回到乡下,又见到了华金。这些年,因为退耕还林,林子好像绿色的海水,正在从四面八方向村子四周漫漶过来。我见到华金的时候,他正在家里养病。他得的是一种名叫骨结核的病,到一家医院住了半个月,截掉了两个脚指头,还不见好,就跑回来了。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病,用不着总是待在医院里,花钱不说,人还遭罪。我在华金的屋子里坐着,忽然从远处飞来了一只乌鸦,站在屋子外面的一棵桤木树上聒噪,“呱哇——呱哇——”阴森而恐怖。华金说:“要不是我的火枪让派出所的搜去了,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华金的话我相信,想起当年像灵猴一样上树掏鸟窝,他差不多都可以说是无所不能。华金说,你就别提了,你忘了我们在杉树坪掏老鸹窝,又是多么狼狈,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尴尬得很。我当然知道,这是华金掏鸟窝遇到的最大一次失败。
我从乡下回到城里,不久就得到了华金的死讯。不就是患个骨结核,会有这么夸张吗?也许还有其他什么毛病,但他的死最终还是算在了这该死的骨结核上。我又想到了那天在桤木树上聒噪的乌鸦,是不是来给他报丧的?我记起来了,当时站在桤木树上的是一只花颈子老鸹,脖颈处的那一圈白,看上去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说来,华金的死,是早就有预谋的。只是我和华金并不知道,在有些方面,我们真的还不如一只乌鸦,就比如这只花颈子老鸹。
斑 鸠
应该是秋末冬初,大地一片萧瑟。天上下着冷雨,但还不至于会绽放为雪花。天有些发灰发暗,一如乡下久病的妇人,让人内心顿生惶恐和不安。斑鸠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们飞到桤木树上,或者飞到白蜡树上,三三两两,也可能是十只八只形成一个小的群体。这时候,却很难得听到它们发出任何声音,它们安静得倒像是一些很听话的孩子。那么它们“咕咕——咕咕——”的叫声呢?
沐浴着秋风,或者冬的寒意,我和一群乡下孩子,到田埂上去安地笼套。安地笼套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说法,这个表达或许不够准确,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反正就是去地里给斑鸠挖坑下套。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比,物质生活条件确实不如现在的孩子,但那时候的孩子动手能力却特别强,不像现在的孩子,尽玩一些现成的玩具,动手能力是明显弱化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现在我还回忆得起那时安地笼套的一些情景。其实,套有两种,天笼套和地笼套。套斑鸠一般是安地笼套,天笼套太明显了,一看就是人类不怀好意设下的陷井。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斑鸠还是很聪明的,它能够识破天笼套这种伎俩。安地笼套先要弄来一根母指粗的水竹,这样的水竹弹力比较好。还要用竹片做一个有点像南瓜米形状,但需要大上上百倍的一个机关,做好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在田埂上挖一个很小的坑,然后安上地笼套,在坑里撒上一些苞谷或者稻谷,还在坑外面也扔上一些苞谷或者稻谷,当然这只能是很少的一点。作为诱饵,重点是要引诱斑鸠去吃坑内的食物,这样就能够把斑鸠套住了。
安好地笼套,我和一群孩子躲得远远的,准备看斑鸠怎么被地笼套套住,看它怎么挣扎,最后怎么痛苦地死去。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了某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我记得,还在村里,有一位被认为不守妇道的妇人,被人捉了奸,不好意思活下去了,就用一根棕绳拴在屋后的一棵梨树上,把自己吊死了。我没有去看,我害怕。我只是听我娘说,这个妇人死得很惨,舌头从嘴里伸出来,足有半尺长,真是吓死个人。我想像着斑鸠被套住被水竹弹起来,吊在半空中的情景,那一定是在不停地扑腾,然后就像一个秤陀悬挂在空中,无声无息地死去。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我是不是有些残忍,还有些幸灾乐祸?不过那时我除了兴奋,就是还有些害怕。因为在我的心中,一直还在纠集我娘说的那个上吊自杀的妇人。
不过,让我们一群孩子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安好了地笼套,却不见斑鸠上套。每天傍晚,我们都要去看我们安的地笼套,那根水竹竿还是那么老老实实地躬着,好像是在给我们陪不是,在说对不起。还有那撒在小坑边的苞谷或者稻谷,好像一粒也没有少,更不要说放在坑内的了。莫非斑鸠也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节自然是生命,并非我们说的气节。我们在田坎上走着,看那一排地笼套始终在那里引而不发,就感觉到很悲哀。看着那一群群斑鸠在桤木树上歇息,或者不分晨昏,在不远处“咕咕——咕咕——”地鸣叫,我们就会越发感觉到很失败。原来和天笼套比,安地笼套也一样无用。人类有下套的毛病,并非只有大人才会。不过我们这群熊孩子,只是把下套作为一种游戏,只会给斑鸠和一些鸟类下。不像大人下套,为的是让自己人让身边的人上套。我们那时下的套,连斑鸠都不肯上套,足见我们这一群孩子的低能和无用。
那阵,我们一群乡下孩子,时不时就会看到有一个穿着光鲜的人,据说是来自乡街上的一个同志,那时我们称有工作,能够吃上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为同志。这个同志闲了,总是会拿着一管火枪,到我们乡下来乱转。看见树上站着斑鸠或者竹林下走着竹鸡,他就会开上一枪,常常会看见一只或几只斑鸠应声坠落,或者就是有竹鸡在竹林下扑腾。还不无得意地说:“确实不错,又打到了斑鸠!”也可能说:“今天运气真好,打到了竹鸡。”我们这时就会想,不上我们的套,这下挨枪子儿了不!也很得意。但很快又非常生气,远远地对那个穿着光鲜的人投去不屑和鄙夷。
那个穿着光鲜的人,到我们乡下打斑鸠和竹鸡的日子多了,原本站在桤木树上的斑鸠或者在竹林下走着的竹鸡,会很快飞走。但无论怎么躲避,总有斑鸠和竹鸡死在他的枪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看见斑鸠站在桤木树上,竹鸡在竹林下走动了。只有在天快下雨的时候,我才会听到从杉树坪的丛林里传来“咕咕——咕咕——”的叫声,听起来是那么悲凉。斑鸠应该站在桤木树上叫,不该在杉树坪的丛林里。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穿着光鲜的人的枪口,把斑鸠赶到了丛林里去。有好一阵,这个穿着光鲜的人,拿着枪在我们乡下转,可是一天两天,手里还是空空如也,一片斑鸠毛和竹鸡毛都没打到。那时,我们一群孩子都很兴奋。我们在心里骂这个穿着光鲜的人活该!后来这个穿着光鲜的人好久不来乡下,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就这么不来乡下了。再后来,听说这个穿着光鲜的人因为强奸妇女,被送去劳改了。我们就又在心里说,真是活该!斑鸠或许就是在这个穿着光鲜的人被送去劳改以后飞回来的,因为它们失去了天敌,理所当然应该飞回来了。我们那时不再去安地笼套,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兴趣。
在乡下,有“天上飞的斑鸠,地上跑的竹骝”的说法,说是在天上飞的,只有斑鸠最好吃,而在地上跑的,就是竹骝了。竹骝是我们乡下人的说法,书面语大概是叫竹鼠什么的。这种东西大概也就一两斤重,个头很小,但看上去胖乎乎的很可爱,有点像乡下人养的兔子。这种竹骝的牙齿特别厉害,专吃竹子;竹笋出来以后,也吃竹笋。还善于在竹林里打洞。要弄到这种竹骝,据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烟熏,让人在一个洞口烧上火,使烟雾能够往洞里灌,再让另外的人守住另一个洞口就可以了。竹骝受不了这滚滚浓烟的熏闷,就会从没有被烟熏的洞口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它捕捉到了。我曾和几个孩子试过,但却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在燃柴火的时候,倒先把我们自己熏得泪流满面,还差点酿成了一场火灾。我们在另一个洞口守了好长时间,却没有看见任何竹骝的影子,我们觉得好没意思。我们都知道,中国吃货众多,以吃好好吃为乐事,甚至以吃不敢吃不能吃的东西为荣。因此这句话,确实道出了这两种东西的好吃,吃货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为吃不到发狂的。在我的老家,还有一句话,名叫“斑四两竹半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据说就是斑鸠最多能够长到四两,竹鸡最多可以长到半斤。这句话的意思是,斑鸠和竹鸡都长不到好大,也就是四两或者半斤。竹鸡我见过,有点像家里养的长到半斤的小鸡,只是竹鸡会飞,看上去羽毛色泽淡,颜色成麻斑色,一点都不好看。这点看上去倒有点像斑鸠,斑鸠羽毛成灰色,淡灰或者铁灰,这有点像一些城市人养的鸽子。我在进城以后,曾把鸽子误认为是斑鸠,让城市里的朋友笑话;回到乡下,又把斑鸠误认为是鸽子,让乡里人觉得好笑。正在感叹乡下人也养鸽子,却有人站出来说,我不懂你说的什么鸽子,我只知道这是斑鸠,这让我弄了一个大红脸。
秋天过完,冬天过完,春天就来了。一天傍晚,我忽然听见了“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这是斑鸠在岩边的一丛竹林里叫。好久没有听见斑鸠这样叫了,斑鸠的声音虽然没有喜鹊的叫声那么喜庆,但也不像乌鸦的叫声那么碜人。在乡下,这三种鸟的声音,在乡下人看来是很有讲究的。乌鸦叫是报丧,会有人死去,喜鹊叫是报喜,会有贵客或者喜事临门。那么斑鸠叫呢?我们那里的人一般认为是天要下雨了。要是天气晴得久了,听到斑鸠叫,我爹我娘就会说,天要下雨了,斑鸠叫得狠呢!一般来说,第二天就真的会下起雨来。那时候,不像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视,看看天气预报,就知道天气会怎么样了。那时,斑鸠时不时就会为我们预报天气。那次听到斑鸠叫,第二天是不是下雨了,我倒是记不得了。人们传说中的天上飞的第一味,我是不是吃过,我也记不得了。我这人历来就属于口福很浅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还真的没有吃过斑鸠。
前几年,我去市文联公干,当时在沈洋副主席办公室的窗外,就看见了一对斑鸠宝宝。在这之前,就曾听说过有一对斑鸠飞到他办公室的窗外,并很快就在窗台上筑起了窝。后来就不断有斑鸠宝宝被孵化出来,这成了市文联的一件奇事也成了一件趣事,时不时就会成为一群文朋诗友的话题。这次我到市文联,吕亚平主席带着我去沈洋副主席办公室谈工作,算是亲眼目睹了这段有关斑鸠的佳话,也可能是神话。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透过沈洋副主席关得很严实的窗玻璃,我看见了斑鸠窝,看见了斑鸠窝里的一对非常可爱的斑鸠宝宝。我们一直在看,却没有看见斑鸠妈妈或者斑鸠爸爸露面。我想,斑鸠妈妈或者斑鸠爸爸,这会可能正在去给斑鸠宝宝找吃食呢!
现在我住在城里,时不时就会看见有鸽子从我的窗前飞过,可我这时却会更多地想到生活在乡下的斑鸠。这段时间我们这里天气异常闷热,我真希望从我窗前飞过的不是鸽子,而是真正的斑鸠。并且还能很真切地听见斑鸠那预报即将下雨的“咕咕咕——咕咕咕——”的鸣叫声。
喜 鹊
忽然忆起乡下一个名叫喜鹊的女人,也可能不是这个名字,哪有这么称呼一个人的,何况还是一个女人。但那时,在乡下,很多人都喜欢叫她喜鹊。她也应答得干脆,好像并不在乎这个称谓。她属长辈,我一直称呼她为喜鹊婶子。
不过,我这里还是要先讲到真正的喜鹊。在我老家,喜鹊无疑是最受人们喜爱的鸟类。喜鹊和乌鸦不同,乌鸦全身黢黑,叫声恐怖阴森,即使就是被我们称之为花颈子老鸹,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羽毛的乌鸦,也同样不受村人待见。因此它们总是躲到很远的林子里去,不敢招惹我们这些村人。还有就是被我们称作老鹰的鹰,也是喜欢待在更遥远的高山上,也不知是害怕我们这些人,还是根本就不屑与我们这些人为邻。有时候,会有一只或者两只鹰,飞到我们村庄的上空来,在很高的天空俯瞰我们,往往会吓得在地上觅食的家禽不住地往堂屋或者柴禾堆里躲藏,而我们一群村里的孩子全都向天空仰望,不住地感叹这老鹰怎么可以飞得这么高。只有喜鹊,它好像天生就知道人们喜欢它们,所以从来就不会躲避村人。它们或站在房前屋后的梨树或者桃树上蹦跳,一张嘴不停地欢叫个不停,像极了嘴甜的小女孩,在不停地说着话;或是在房梁上走来走去,抖动着黑白两色羽毛,嘴里还是不停地欢闹着,就像是一位流行音乐歌手,在边走边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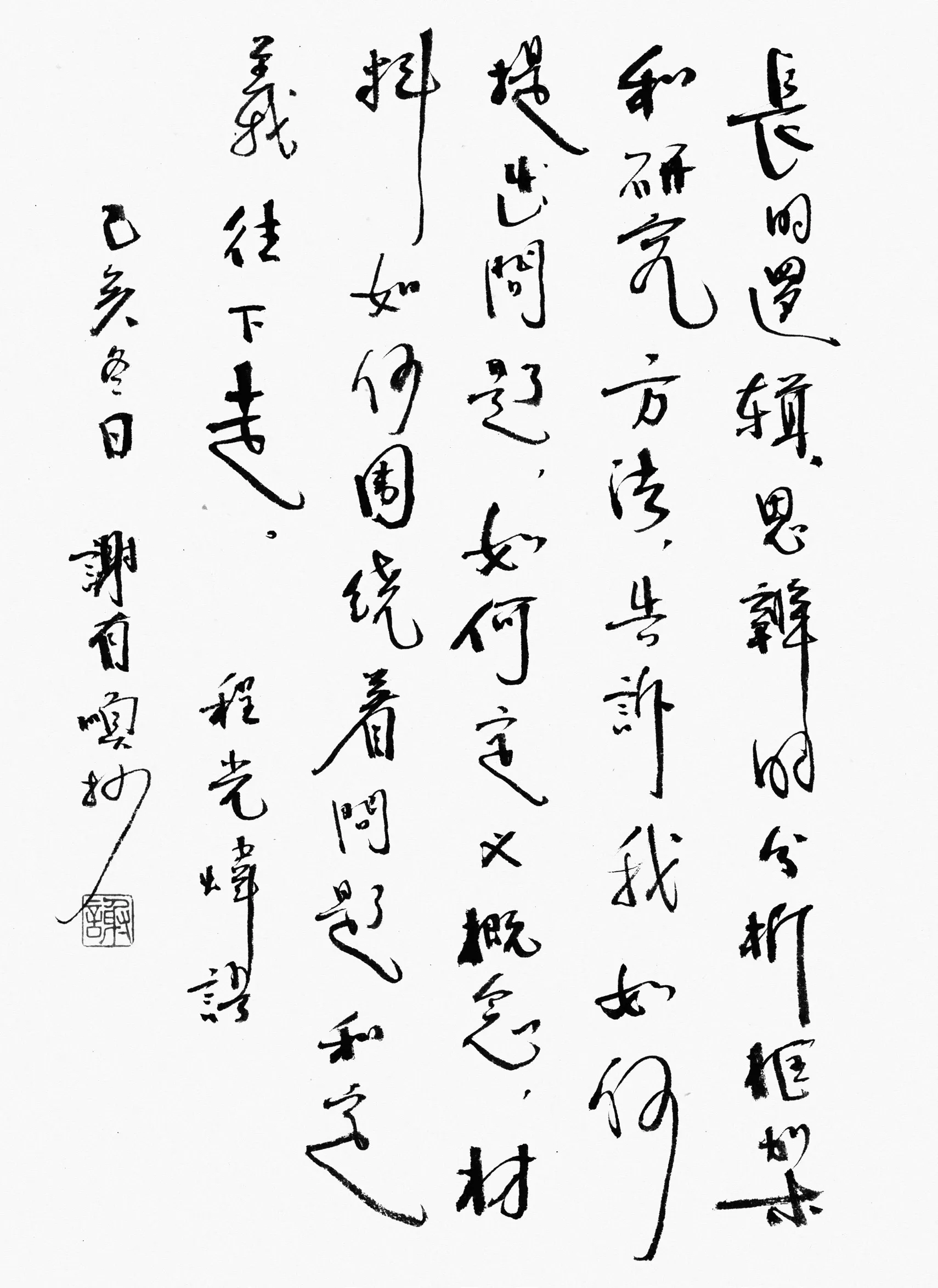
谢有顺 书法
春天来了,我爹会不失时机地在田里耕种,这时一点不怕人的喜鹊会飞过来站在牛背上,用嘴啄牛背上的蠓虫。时不时的,还会从牛背上飞到水田里,要么是有蚯蚓被翻到了水面上,也可能是有泥鳅被犁到了水面上,这就会成为喜鹊的美食了。我看见爹从不会吆喝喜鹊,这成了乡间一幅最美的水墨画。想想吧,春天,早晨,淡淡的晨雾,白色的,像极了泼洒的牛奶,但没有牛奶那般酽稠,水牛,我爹,在牛背上或者水田里站着或者走着的喜鹊。有时候,在这个画面里,可能还会有几枝翠绿的垂杨柳。这个画面很多年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曾多次到乡下去寻找这样的画面,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么安静、干净的农耕图,我再也没有见到过。
在民间,喜鹊从来就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喜鹊登枝,喜鹊登梅,那都是吉祥如意的意思。那些年,过年比较喜欢张贴年画,而这些年画大都是红底,在上面画着梅花,在梅花的枝条上画着喜鹊。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也曾喜欢画画,就经常照着年画,临摹喜鹊登梅。我曾辍学过两个月,现在之所以还记得有这段经历,是因为在辍学的这段时间,我曾受邀到当时的绥江县文化馆学习过一周的绘画。要知道,在当时我所居住的太平公社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在绘画班里,我还是年龄最小的,很得绘画老师喜爱。一周学习结束,按要求每一位学员都要作一幅画。我记得,我那时画的就是喜鹊登梅。我画得很用心,画喜鹊自然不是问题,因为在我们乡下,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喜鹊,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它们的样子。可在我们那一带,却没有梅花,又怎么画梅呢?正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想到了春天在乡下开得如烟似雾的桃花,三月桃花开,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句子。我觉得桃花和梅花其实是很相像的,只不过梅花开在寒冷的冬天,桃花开在温暖的春天罢了。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自然说的是梅花,而春天来了以后,那就是百花盛开了。因此,我觉得桃花是梅花的延续,是另一种性质的梅花。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画梅花的时候,就总是想着乡下的桃花。我把喜鹊登梅画出来以后,培训老师先说不像,后来又说画得太美了,也怕只有你才敢这样画梅花了。
我把我画的喜鹊登梅拿回家来贴在堂屋正中,很快便引得左邻右舍的来我家堂屋驻足观望,无不拍手叫好。那个被村人称作喜鹊的女人,对我画的喜鹊登梅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她在嘴里不住地说着好,倒真有点像我画里的喜鹊了,在我画的喜鹊登梅中,我画的喜鹊正在张嘴鸣叫,好像还能听到喜鹊欢叫的声音从纸面上传来。若干年后,当我不停地在方格稿笺上写字,后来又是不断地在电脑上码字,为很长时间三分钱一个字不断地写作的时候,我还在想,我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从事画画这个职业,却偏偏会热爱上了这写字呢?回答自然是家里太穷,买不起画纸和颜料。写字就不一样了,即使是在废弃的纸烟壳上,也照样可以写出一段无病呻吟的分行文字来。
在我老家,更是相信大凡有喜事要发生,就会有喜鹊飞来报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9年8月初,一天早上,我到责任山地里去砍了一枝斑竹来做钓竿,准备吃过早饭后就下河钓鱼。因为头天晚上下了大雨,离我家一公里远的小河涨了水,非常适合去小河边钓鱼。吃过早饭,正准备去自留地挖蛐蟮回来,这时一只喜鹊飞到我家门前的桤木树上,正在欢天喜地地叫着,像是有什么要向我诉说似的。我抬头看着在桤木树上蹦蹦跳跳,欢天喜地叫个不停的喜鹊,我在想,莫非今天下河钓鱼会很顺利,会钓到很多的鱼,很大的鱼。我知道,前几天,也是下过雨,小河涨了水,我们村一个男人下河钓鱼,那天他钓了十多斤鱼,有一条大鱼,据说有三斤重,还是第一次有人在这条小河里钓到这么大的鱼。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在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喜鹊来给他报喜。我希望我下河钓鱼能够钓到很多的鱼,也钓到这几斤重的大鱼。可正待我要出门,住在村街子上的我干爹却来了。我干爹说:“老三,你又要下河钓鱼?这回不用去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去县城体检,填报志愿。你知道不,你考上大学了。”
后来,我成了我们生产队,我们盐井大队,甚至是我们太平公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若干年后,在我们那里考取大学的人开始多起来,但很多人还是会拿我说事。我知道,大凡第一个或者第一次,常常能够让人记住。我们生产队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今年春节,我回到乡下,适逢他从北京回来探亲。好多年没有见面,见了面自然会很高兴。他对我说,我那时受你的影响很深,你不是说做记者好么,是无冕之王。所以我听你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做一名记者。我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可是真的记不得了。也许我真说过,只是时间太久了,记不得有这回事了。也可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说过就算了,可他却记在了心里,成为了他以后努力学习的动力。我工作后确实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但只是小报记者,自己都觉得没劲。他据说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是不是做记者,我不知道,也不好问。我俩在乡下见面,已经物似人非,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而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年人了。我俩正在攀谈,有两只喜鹊飞到门前的桤木树上,它们在枝丫蹿来蹿去,唱唱跳跳,好像开心得很。也许它们是一对情侣,可我们却是两个多年不见的故人,在这里漫无边际地叙旧。
回到小城,我一直在想那天早晨的事情,特别想到了那两只喜鹊,它们飞过来站在桤木树上,总是欢叫个不停。是有什么喜事要发生吗?后来我才想,我和这位故人在很多年以后,能够在乡下,能够在老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晨相遇,这本身就是喜事。谈起往事,我们都不甚唏嘘。当然,我们也谈到了未来。按说,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再谈未来,可我们就是谈到了未来,而且谈得还非常兴奋。我们都说,等退休了,就回到乡下来住。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也许,只有我们两个人才会这样忽发奇想。现在更多的人都一心想往城市里挤,乡村正在变成空壳。我和故人想重新回到乡下去住,这或许是另一件喜事,我相信这喜鹊报喜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被村人称作喜鹊的女人,后来怎么会和真正的喜鹊结下了冤仇,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我记得,在喜鹊家房前屋后,有两棵很大的桤木树,平时总有喜鹊飞到这两棵树上不停地欢闹蹦跳。有一年,喜鹊种下的四季豆,才刚刚出土,她看见这些才出土的四季豆苗,差不多都倒在了地里。喜鹊以为是被土蚕子咬了。可后来,喜鹊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土蚕子咬的,这分明是正在房前屋后聒噪过不停的喜鹊所为。不知是不是喜鹊找不到吃的了,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荒啊,那时人都快要没吃的了,更何况这喜鹊。原来喜鹊以为四季豆苗下都有土蚕子,因此把没有土蚕子的四季豆苗也弄坏了。那时,在喜鹊家房前的桤木树上有一个很大的喜鹊窝,最初看见两只喜鹊辛勤地垒窝,估计现在已经孵化出小喜鹊了,因此要忙着找虫子来喂小喜鹊。喜鹊弄坏了喜鹊的四季豆,喜鹊自然是怒不可遏,她让华金上树去掏喜鹊窝。那天,我也正好在场,华金在掏喜鹊窝的时候,两只喜鹊在华金的头顶飞来飞去,试图阻止他掏喜鹊窝。喜鹊、我,还有几个熊孩子在下面呼喊,捡起小石块往两只喜鹊投掷。两只喜鹊抗不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华金把小喜鹊从窝里掏出来,然后把窝掀掉,不留下任何痕迹。小喜鹊没有了,喜鹊窝没有了,两只喜鹊这才无比悲伤地飞走了。
喜鹊在她的自留地里重新点上了四季豆。可四季豆苗刚出土,喜鹊又飞来把她的四季豆苗全部啄坏了。还不解恨,喜鹊在家孵化的小鸡,刚能下地走动,来到院坝内,两只喜鹊竟然飞下来把小鸡啄得惊叫,满院坝乱跑。还像老鹰一样,把一只小鸡叼起来,飞走了。很久都还能够听见小鸡被叼走留下的凄厉的叫声。那段时间,喜鹊确实和喜鹊结仇了。喜鹊一飞到房前屋后的桤木树上,喜鹊就要拣石块、土圪垃往树上扔,可喜鹊站得太高,喜鹊怎么扔都够不着,就只会干瞪眼。还叫来生产队一个很会使用火枪的,来打树上的喜鹊。枪响了,只见喜鹊惊恐地飞走了。喜鹊问:“怎么会打不着,你平时枪法不是很好的么?”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打着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很会使用火枪的人,根本就没有在枪筒里装铁砂,这当然就不会对喜鹊造成伤害了。后来,我听这个人说,这只是喜鹊和喜鹊有仇,我和喜鹊又没有仇,为什么要伤害喜鹊,我可不敢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后来,喜鹊干脆把房前屋后的两棵桤木树砍了,甚至一段时间不在自留地里种任何东西,把小鸡关在堂屋里喂养,不给喜鹊留下任何的机会,这样才慢慢消停下来。那两棵桤木树,是喜鹊要用来解瓦格子,好盖新瓦房的。没想到因为和喜鹊纷争,只好提前砍了。真没想到,这喜鹊和喜鹊缠斗,两棵桤木树却遭殃了。我记得,这两棵桤木树被砍掉以后,村里再没有长出这样大的桤木树。那时,我对参天大树的理解,就是从这两棵桤木树开始的。
再后来,我就到外面读中学去了,后来又读大学,在外面工作,就很少回到乡下去了。有一年,我爹进城来,忽然聊起乡下的一些事情。我爹忽然说:“你知道不,你喜鹊婶子死了,死在了山坡上。那天她去坡上放羊,你可能不知道,你喜鹊婶子那时已经是远近有名的养羊专业户了,她养的可是黑山羊,一种很好的肉用羊。那天她跟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就出去了。按说,她到中午应该回来吃饭的,可你叔在家等到下午两点,都不见你喜鹊婶子回来,他走出门去,听到在你喜鹊婶子放羊的山坡上,喜鹊正叫得很呢,就像有什么天大的喜事要发生一样。你叔觉得奇怪,就去了你喜鹊婶子放羊的山坡上,发现你喜鹊婶子已经死了。更奇怪的是一大群喜鹊站在附近的一棵五倍子树上,正在发疯似的鸣叫。一根很大的蛇正在往你喜鹊婶子倒下的地方游过去,有勇敢的喜鹊飞过去,不停地用尖嘴啄那条大蛇,直到大蛇逃走。
我想起喜鹊曾经和喜鹊的那一段恩怨,就觉得这很有些不可思议。在我们乡下,只有乌鸦才是报丧的,这喜鹊从来都是报喜鸟。可在喜鹊婶子死亡这件事情上,喜鹊却实实在在做了一回报丧鸟。我爹说:“我似乎听出来了喜鹊这种听惯了的叫声中有一种幸灾乐祸。”可我爹又说:“要不是这些喜鹊报丧,谁知道你喜鹊婶子会死在山坡上,死后还会怎样?会不会被大蛇咬野狗啃也未可知。”据说喜鹊死于心脏病突发,也有说死于脑梗塞的,自然这些都只是猜测。
画 鹛
早晨,陪岳父到公园走走。岳父难得到我这里来,他在乡下住惯了。更难得让我陪他到公园去走走。早些年,岳父在乡街上开铁匠铺,专门打些锄头、镰刀和耙钉之类的铁器卖给乡里人。要种好庄稼,就离不开这些农具,因此岳父很受人尊敬。岳父还善于做火枪,这很受三角、二溪一带苗族同胞爱戴。那时,能够做火枪的不仅只是岳父,其他开铁匠铺的铁匠也会。但这些苗族同胞更喜欢用岳父做的火枪,据说是他做的火枪好用,用来狩猎很实在。不像其他一些铁匠做的火枪,不是枪管被打爆,就是射杀不了猎物。有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个猎人在轿顶山脚下打猎,半下午,猎狗追着一头黑熊过来,近了,猎人对着黑熊的脑门开了枪。枪响了,黑熊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疯狂地扑过来,两只前爪用力从猎人手里抢下火枪,再一掰,就把枪管弄成了九十度角,之后把已经像烧火棍一样的火枪一摔,就向猎人扑去。猎人惨叫一声,就滚下山去了。这猎人被黑熊抓去了一块肉,医好了,脸很难看,像山鬼。岳父做的火枪,从来没出过事故,因此深得猎人喜爱。
在公园里,这会已经有了不少人。有做早操的,有打太极拳的,还有几个遛鸟的老人,把鸟笼子挂在树上,就坐在一边聊天。岳父对做早操和打太极拳不感兴趣,他早年一直在铁匠铺打铁,身体好得很,根本用不着做早操和打太极拳来锻炼身体。岳父的理论怪得很,他说身体好哪里是锻炼出来的,分明是劳动得来的。只要你坚持劳动,这身体还会不好。岳父还说,你看我就从来不锻炼,这身体还不是一样的很好。岳父对做早操和打太极拳不感兴趣,但他对挂在树上的几笼鸟儿却非常感兴趣。听叫声,就知道是画鹛鸟。岳父说,走,我们去看看那几笼子画鹛,我可是有好多年都没有养画鹛了。
岳父除了打铁,还有一项爱好,就是养鸟,而且专养画鹛。岳父养画鹛,不像公园里遛鸟人养的画鹛,是用钱从花鸟市场上买来的。岳父养的画鹛,是他自己从山上弄来的。那时候,在我们居住的乡下,有很多的鸟,其中就有这种叫声悦耳的画鹛。要从山上把画鹛弄来其实并不容易。岳父在不打铁的时候,会用从供销社买来的毛蓝线来织一种网,一种专门用来捕鸟的网。我们时不时地就会说到一个词:天罗地网。我不知道天罗是什么样子,地网不知道是不是岳父织的这种可以把画鹛捕到手的网。要捕到画鹛,就需要拿了这种用毛蓝线织的网。一般是先把网牵开,用两根竹竿牵伸了固定插上,这网会有两三丈长,六七尺宽,牵开来其实就是把画鹛要飞过的路口拦住。岳父通常会守在牵了网附近的树林里,岳父家的几个孩子去追赶,画鹛就会向着有网的地方飞,撞到网上,很快就掉进网兜里。还在拼命扑腾,岳父已经从树林里钻出来,很快就把画鹛捉来放进从家里带来的鸟笼子里,这下画鹛就只有在笼子里扑腾的份了。
有时候,画鹛并不会按岳父给它设定的路线飞,而是向着其他的方向飞走了。这时候,岳父就要把网收起来,重新预估画鹛飞行的路线,在可能经过的地方,再次把网张开。然后,他的几个孩子就又去追赶画鹛。总有画鹛会飞进岳父预先为它张开的网里。岳父不贪心,一般弄上一两只,就不会再去张网了。那时岳父家孩子还没有成人,不知道画鹛失去自由会有多么痛苦,看见画鹛被关进鸟笼子里扑腾,会变得非常开心。这下家里要养画鹛了,每天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画鹛在笼子里跳跃,听到画鹛在笼子里唱歌了。
养画鹛是一个技术活儿。我不知道孔武有力把铁匠活儿做得很棒的岳父,怎么会把养画鹛这样很细致需要有耐心的活儿也做得这么好。我知道,就连养画鹛的鸟笼子,都是岳父自己在做,不像现在养鸟的,都是跑上街买,虽然也很精致,但和岳父手工做出来的比,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岳父做的鸟笼子,有竹制的,也有木制的,能够嗅到从竹子和木头里散发出来的竹香和木香。做鸟笼子的竹片和木板,岳父会用桐油先浸泡上一阵,这样看上去才会有光亮,而且还会防虫。我曾经把岳父做的鸟笼子和街上卖的鸟笼子做过比较,我发现,街上卖的更多的只会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鸟笼子,而岳父做的既美观又大方,更是非常实用。
画鹛从山林里弄回来,被放进家里真正的鸟笼子里。可真要养好画鹛,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画鹛作为生长在山林里的鸟儿,野惯了,充满了野性。不过,岳父却对养好画鹛非常有信心,他把养好画鹛跟养好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还能养不好画鹛吗?我岳父这一生,不仅铁打得好,画鹛也养得好,更重要的是他养育了八个孩子,在困难时期,他要让这八个孩子吃饱穿暖,确实非常不容易,可他却做到了。每忆起这件事,我就禁不住感叹,岳父太了不起了。我父亲只养育了我们三个孩子,吃尽了苦头,可我们还是时不时地感觉到吃不饱穿不暖,以至于在我们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把身体完全发育好。岳父把画鹛关进笼子里,便和画鹛开始了进食和绝食的斗争,只有闯过了这一关,岳父养画鹛才可以说是大功告成。
岳父为了把画鹛养好,他把家里最好的苞谷拿出来,在石磨上精心地把苞谷磨成苞谷面。岳父用来养画鹛的苞谷面会磨得很细,不像我们用来做苞谷饭的苞谷面,可以磨得比较粗糙。苞谷面磨好了,岳父便开始找来两个鸡蛋,在苞谷面里加上一些水,再把鸡蛋打了和苞谷面搅拌均匀。做完这些,岳父就要把它做成苞谷面团放在锅里蒸熟。这拌了鸡蛋的苞谷面团在锅里会蒸得很香,这让他的几个孩子直喊受不了。老实说,那些年,这些孩子要吃上鸡蛋,也往往是要过生日了,才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被煮在猪食锅里,煮熟了就成了过生日孩子的生日礼物。没想到这画鹛一下子就可以吃到两个,这到底又是谁家的小祖宗啊!这还不算完,岳父等苞谷面做的面团蒸熟了,就拿出来在微火上烤干,再捏成颗粒状,然后才装进鸟食碗里,开始给画鹛吃。一般来说,画鹛在很长时间都不会买岳父的账。这段时间是岳父和画鹛最难熬的。直到饿得不行了,快要饿死了,这画鹛才会悄悄地吃上一口。也许是画鹛还不够坚强,也许是岳父做的鸟食太好吃了,这画鹛吃上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人和鸟进食与绝食的斗争,这时候才会正式宣告结束。
我每次去岳父家,都要去看他喂养在鸟笼子里的画鹛。甚至还会学着画鹛的叫声,逗画鹛也叫上几声。可有一次我去岳父家,要去看画鹛,却没有看到,甚至连鸟笼子也没有看到。后来问岳父,这是怎么回事?岳父说,那阵他的铁匠活儿多,可能是没有照顾好笼子里的画鹛,先是发现画鹛羽毛不够光亮,后来就死在笼子里了。岳父难过了好几天,就把鸟笼子送了人,干脆不再养画鹛了。那段时间,岳父的铁匠活儿多得很,要忙着打锄头,镰刀,耙钉,特别是还要给三角和二溪一带的苗族同胞制造火枪。因为那段时间正是狩猎的最好时节,时间宝贵得很。那时候,已经有人可以从市场上买到指头大小四五尺长的钢管了,用这种钢管来做火枪的枪筒,比用钻子去钻指头粗的铁棒,会节约出很多的时间,而且钻出来的枪管根本就没有用钢管做的质量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苗族同胞都能够弄到这种钢管。那时岳父做出来的火枪,都是用钢管来在做枪筒,那时苗族同胞打到的猎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知是用钢管做的枪筒好,还是岳父的造枪技艺又有了提高,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后来,深山里的很多动物和鸟类,都成了国家保护动物,一级二级三级都有。派出所还在乡下开展了几次大的搜缴枪支的行动,火枪全部被搜缴上来了。三角、二溪的苗族同胞打猎,已经成为了往事。岳父为苗族同胞制造火抢,已只会成为他铁匠生涯中曾经的一段美好时光。岳父不再制造火枪了,他全身心地为农民兄弟打制锄头、镰刀和耙钉,可后来乡街上开始出现很多用机器生产的钢板锄,随之各种机制农具在乡街上泛滥,来找岳父打锄头、镰刀和耙钉的人少了。再后来,乡下掀起了外出打工潮,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家里种庄稼了。岳父的铁匠铺整天看不到有一个人来打锄头、镰刀和耙钉。岳父本来有心让我孩子的小舅继承他的衣钵,但看到这种情况,就让小舅也跟着出去打工了。再后来,岳父年纪大了,打不动铁了,就干脆关门歇业。
岳父不干铁匠活儿了,苦了几十年了,也该歇歇了。这时候,忽然有人知道岳父会织捕捉画鹛的网,还能够上山用这种网捕捉画鹛,因此找上门来,要岳父帮他们捕捉画鹛。还说价钱好商量,不会让岳父吃亏。我听说了,以为岳父会接这个活儿,虽然岳父年纪有些大了,但身子骨还硬朗,去山上捕画鹛,不仅可以有点经济收入,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是一件两全齐美的事儿。可后来我知道的情况是,岳父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人的请求。岳父说我早就不织这种网了,我都记不得怎么织这种网了。还有你看我这把身子骨,莫非还能上山去蹦达,不合适吧!据说找我岳父帮忙的人非常失望。那时品相和声音好的画鹛,已经能够卖到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对。岳父不干,这么好的生意让这个人做不成,肯定会很失望。我不知道,以前岳父对养画鹛情有独衷,现在有时间养了,可不仅自己不养,连有人请帮忙,还愿意给岳父很多钱,他却可以做到对这事无动于衷。
岳父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子女都在外面,虽然有岳母陪着,可还是开始有了孤独感。岳父在家里闲着,子女们生怕老人闲出病来了,想到老人不是曾经养过画鹛吗,何不让他养养画鹛对抗孤独。有一户亲戚住在山上,经常有画鹛在四周鸣叫,正好可以弄到画鹛。子女就找岳父商量,说是弄一两只画鹛给他喂了玩。可岳父坚辞,说我早就没有这份心性了,不会再养画鹛的。岳父后来爱好上了打麻将,我和妻子,还有妻子后家的几位兄弟姊妹,都没有反对,只是劝他要注意休息,不能坐得太久了。可岳父说:“没有关系,我身体好。”岳父的身体确实不错,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好,这都是那些年打铁打出来的。现在岳父可以说是在吃老本,不过我很担心这老本能吃多久?因此就劝岳父还是应该适可而止。
我妻子的几个兄弟姊妹,有的在工作,有的在打工,应该不缺钱花。完全可以给点钱让岳父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他却坚决不出门。有一段时间,为了照顾在县城读中学的孙子孙女,岳父岳母老两口也曾住进了城里。我以为他们会很快适应这城市生活,可孙子孙女考上大学,就又回乡下去住了。有一次,在浙江结婚的我家孩子的小姨回家过年,准备接他们过去住一段时间,可岳父就是不肯。一大家人劝说,直到岳父非常生气,才作罢。我对岳父说,等再过几年我退休了,我陪你去。岳父说要得。可我不知道,真要等到我退休了,是不是还能够成行。我知道,人生充满了各种变数,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岳父在我家住的这段时间,早晨去公园,他总是会在那些遛鸟人的鸟笼子前站上一会儿,和养鸟人谈论怎么喂养画鹛。有人感慨,真看不出来,这个来自乡下的老人,居然还会养鸟,养画鹛。离开这些养鸟人,岳父却发一声叹息,这些画鹛太可怜了,成天呆在鸟笼子里,完全失去了本应属于它们的自由。我忽然想到,岳父这一生,何尝就不是一只鸟,一只画鹛。同样成天呆在一只巨大的笼子里,尽管这笼子看上去无形。我忽然想到早些年读过的一首名为《生活》的诗,这首诗的内容就只有一个字:网。在我看来,生活不仅是一张网,同样还是一只鸟笼子,虽然这只鸟笼子看上去无形,但却始终把我们关得死死的,经常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这会还想到了我自己,其实也是这鸟笼子里的一只画鹛,我也会在这只名叫生活的笼子里来回走动鸣叫。我终于知道以前乐于喂养画鹛的岳父,为什么现在却不愿意再喂养了,可这还会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