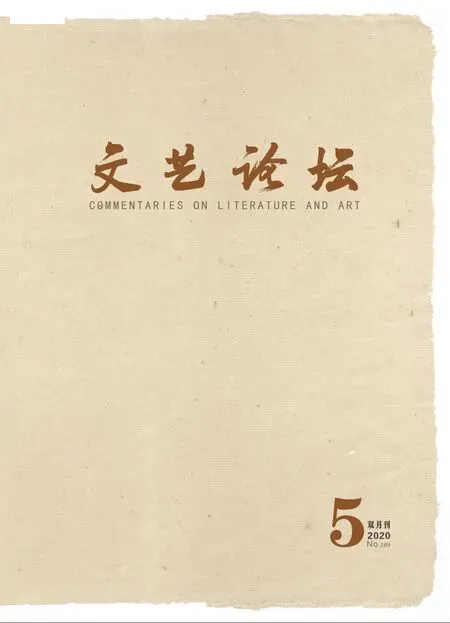在两盏街灯之间
◎ 樊晓哲
一、时间
或许,一切都源自那一块怀表。
2015 年秋初,“一个时光凝固的下午”,写作的欲望捕获吴亮:“把无法重现的昨天——这个昨天包括一切刚刚过去的那个瞬间——从记忆的混沌牢笼中解放出来,不依靠影像与图片,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早在2009 年秋天,吴亮就曾经做过尝试,一组二十个篇目的回忆文章辑录于《我的罗陀斯》;六年以后,吴亮打算借用小说对这一段记忆做新的想象:这一次,上海的1970 年代从“后窗”给了作家重大发现,“挥之不去迤逦意象,寻常、不引人注意、易被忽略、尚未受到惊扰”“惊觉四十年前遗韵犹在”,如梦一场。
于是,轻悄悄地,小说第一段文字现身,“醒来头一天,他就似乎感觉原有生活的痕迹统统被抹去了”。上海腹地密密麻麻的隐秘街巷,各式各样小作坊,一切陈旧破碎的物件,有待领会,有待治愈。小说《朝霞》32 节:1974 年岁末,在顺昌路的杂铺店,邦斯舅舅淘得一块浪琴怀表,原配的链子没有了,说是上了发条还能走。邦斯舅舅宁信有。吴亮也信有。像是一个钟表修理工,吴亮用文字打开了邦斯舅舅那一块怀表的后盖。齿轮运转,一段沉睡着的时间跳动了。“推开窗户大千世界向你自动走来”,果然还能走。一部小说启动了。一个梦,一段萦绕不散的记忆,这就是2016 年发表于《收获》的小说——《朝霞》。
长篇小说《朝霞》从-1 节开始至99 节结尾,共101 节623 段。单单从这个数字的选取设置上,吴亮就成功阻拦了懒惰的阅读经验:为什么不是从0 到100 呢?不,就是不!没有解释。如果一定要,那你得耐心,并且细心读到小说的第36 节,“把生活并不存在的逻辑打乱,才能接近那万千生活之流”;小说的第63 节,“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是,吴亮想要在《朝霞》中召回的是一段生活,1970 年代上海的生活。这段生活与我们此前此后看到的生活并无二致:少年人的永恒成长、成年人的永恒挣扎、时代喧嚣的强力携裹、日常生活的有效解构。但它又的确很异样,这不在于它包涵了什么,而在于它在这个世界运行时空中的坐标点。正因此,它例外地孤悬在那里,像是一个梦,有物理上相对的封闭时间;也还是像一个梦,它尊享人内心深处永远开放的灵魂时间。它是这个世界众多影子中的一个,已经隐身,但并没有离开,时常现身给那些认识并了解它的人,在那个“离你大概两盏街灯的距离”“隐藏在逆光的暗处”。太多次的遇见,那就不是偶然,而是那段生活还有话要讲,除却音乐家、画家、建筑师等,小说家,是它在文字方面拣选的最佳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朝霞》 36 节中的这句话,“一个宏伟的小说构思,不会是某个夜晚降临的偶然意念所能推动得了的”。一个好的小说家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主动者,创作的艰辛,正在于内心是一个战场,这两种力永在角逐。
世界的自然状态就是混乱和动荡,为尽可能展现那一整段的生活,吴亮不介意向电影学习,把这101 节当成镜头,整个创作的叙述启用了跳跃的剪辑风格,通过不断地打破时间来重新拼接时间。于是,在现实时间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小说意外被加赠了很大的空间。这些空间里,回响着大量叙述人的议论,密植在人物行动以及事件蠢动的链条中,横冲直撞。不管不顾闯进来的还有:读书笔记,内心独白,对话、书信、写作提纲,诗篇,歌曲,以及祈祷。与其说吴亮是一个专横的导演,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诚实而又谦卑的作家,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之中有无数的小世界,如同邦斯舅舅所讲的植物分类,目、属、科直至个体:最后的单元,所有的戏剧性,都浓缩在每一个瞬间即逝的有形无常的情节中”,而所有的渺小和凡庸,都值得肯定和赞赏,它们与那些宏大和传奇,一起构成着谜一般的生活。面对一段已经看不见的生活,“我只能谈论它们。我不能断言它们。命题只能说出一个事物如何是,而不能说出它是什么”。
因此,在《朝霞》中,你所看见的情节不是一个线性的平滑呈现,当然有线,也不是说完全不按时间序列走,而是从体量上来讲,小说展现的不是时间截面上的一根事件线条,而是很多根事件线条,而且它们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各自沿着各自的速度向前推进,共同在一个半径很大的块茎状的时间流中向外涌出,最终点亮的是这个时间的整体。在这些事件的序列中,读者很少能获得因果关系带来的那种熟悉的清晰美感,吴亮通过调度时间给出了那个年代的氛围和地图,声音和颜色,以及更多曲线的情绪,更多姿态的情感。这些计有:知识,悬疑,动人的爱,原始的力,绝望的等待,疯狂的堕落、纯真的躲避,淡冶的自持。它们提供一种散漫的、沿途的、无法预设的阅读美感,富丽又丰饶。讨论一个作品的形式,其实就是在讨论它的内容。吴亮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是一个评论家。他知道太多关于小说创作的技术密码,当然也知道很多阅读的自然规律。现在,他要花点力气,规避它们。为了呈现一个崭新的旧时光,他只能冒险,创作一个新的叙事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吴亮可谓一个体贴的作家。他尊重他小说的人物——他们;尊重阅读小说的读者——你们;尊重美,而美是难的。《朝霞》的这101 节623 段,并不是事先写好,事后剪辑,它们汩汩流出,一气呵成,真如一段生命。正如所愿,这是一个时间的活的泉眼。
二、他们
《朝霞》40 节,“他才是古典的而不是现代的,他遵循叙述的古代观念,事物与人的肉身可以朽坏,以往的一切轰轰烈烈声色犬马也已化为尘埃,此时此刻它们虽然早不在场,因为有了叙述者招魂般的叙述,那些肉身才开始像鬼魂一样在午夜游荡,你们借此叙述得以窥见死去的亡灵与每一道消失的晚霞,它们全是绝对的在场者”。想必,这就是在两盏街灯之间,小说家吴亮所看见的,“火焰般的女人和金属般的男人”,还有那一群游荡的银色少年。大楼被洗劫一空,旧古董失了踪,花园破败,校园荒芜,他们统统被赶出来了。世界将他们遗弃,仿佛消失了,那么,“他们在过去了的那个最为怪异最为枯索最为难以命名的时代,究竟还做过些什么惊天动地和不值一提的无意义的必须之事”?
他们返回书本,马立克、江楚天的读书笔记真是别有洞天;他们借着阅读而秘密交谈,林林、东东、牛皮筋都是阿诺交流的伙伴;他们返回音乐,张曼雨家里走失了那架德国钢琴,但唱片还能流淌古典音乐;他们返回宗教,李兆熹向洪稼犁牧师供出自己尘世的迷惑;他们返回身体,李致行爸爸、沈灏妈妈瞬间点燃欲望,翁柏寒苍白的脸映照出翁史曼丽艳红的唇;他们丢失欲望的初夜忽然成熟,探寻爱情又复原了单纯;他们阳光灿烂地幻想和烦恼,他们在艾菲家的天井打牌,他们画地图、搭航模、看电影、逛商店,他们坐火车探险,他们集邮、养金鱼、练书法,讨论鲍勃迪伦。他们逃离这个城市的寒冷与萧瑟,又返身于它的温暖和安详。他们在多雪的冬天,等待那风中的答案。
黑塞在《荒原狼》中曾有撰文,分析过这样的“他们”。“他们”是市民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的特殊时期,软弱而胆怯的普通市民很容易被驯服和统治,“他们”自私又庸俗,远远不能自立自卫。但每一次社会危机过后,市民阶层依然存在,而且还不断发展强大,最关键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正是这些充满生命力和智慧的“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之间不断转场,在不幸和厄运中洗练和检验了自己的文化和教养。“他们”给了所有的市民阶层充满信心的安慰和耐心的勉励,为了挣得共同的未来。“他们”多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既反感市民阶层,想要挣脱,但又无奈地隶属于市民阶层,并服务于它。是“他们”在那些无用的知识、过时的道德里躲藏,又凛然在凌乱的现实中,发出无声的口号:“通向真正的未来(须知还有虚假的未来) 的唯一正确之路也就是你为之心惊胆战的路。”(帕维奇《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之恋》)
现在明白了,他们是如此核心,但又绝不显要。吴亮安排给他们的出场,都是漫不经心,混迹在缭乱叙述的密林中,不做体貌描写,也没有彼此关系的介绍。他们每一个都单独上场,径直说话行动。读者要了解他们,请自己费点心,察看他们的行踪,倾听他们的交谈,阅读他们的书信和笔记,然后,忘掉自己的成见,体贴他们的软弱,再然后,他们就是你们在所有小说中要找的“人物”了。至此,吴亮成功把他们交托给了你们。在《朝霞》创作的五个多月中,每天,吴亮出门,这些人物都穿戴整齐紧跟着他。随着小说创作的深入展开,这些人物的所有心事和秘密,彼此之间交集出的错综关系,都成了吴亮的行囊,先是越来越沉重,等到他们一个个自行其是,又越来越轻盈。最后,他们离开作家,来到了你们面前。所以,这些人的眉眼、着装、姿态,又有哪一样不历历在作家眼前,清晰可见?但是需要略去。吴亮说写作就是一个删减的过程,简洁就是效率。他生怕那些廉价的冗余的细节,掩盖了这些人物的精神温度。与内心所经历的波澜相比,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看什么,谈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才至关重要。正是这些人物内心的生产,给了1970年代这一段贫瘠乏味的时间以能量,他们是这个城市暗自跳动的心,这一段的生命时光中,不管怎样压抑或者流放,总算有了重量。
创作结束时,吴亮发了一次高烧,他醒过来,小说中的阿诺睡着了。这场写作真像是一场带有招魂色彩的梦,这个梦,是那些人物给予作家的报答,还是创作给予那些曾经受伤的灵魂以报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该由阅读作品的你们来评测。
三、你们
《朝霞》82 节:“它向过去开放,它等待过去的读书人,它无意诉诸今天的新一代人,它宁可未来三十年的年轻读者忽略它怠慢它,它或许会以出土文物的形式出现在一百年以后。”“它一直在那儿,它根本上排斥阅读,如生活本身一般无意义。”排斥阅读?怎么可能呢?请不要轻易相信小说家的话,他们都惯用虚构抵达真实,是狡猾的猎人。任何一部作品,都在静待它的读者,而且满怀深情。《朝霞》 也一样,以至于因情深而起了闺怨,如“他们只是不读内行小说家而已,鬼晓得他们在读什么故事呢”,“各自制定各自的生活计划吧,不要梦想抓住所有人的目光,更不要梦想抓住所有人的心”。小说的创作,本来就如同造梦,所有的小说家都首先是一个为梦而苦想的人。读者当然不会是所有人,而是要在文字里追梦的人,就是那些共鸣的“有心”的读者——你们。所以,就把这些幽怨当成是一种诚挚的邀请吧。
你们用心就会发现:是在事后,牛皮筋与江楚天的闲聊中,交代了是黑皮阿龙把阿诺领到了殷老师那里;除了邦斯舅舅,阿诺的二舅舅劳尼舅舅不仅熟悉上海,还熟悉广州、重庆的往昔;阿诺楼上失踪的邻居原来并没有死去,而是隐逃了;不辞而别的艾菲回来了(他全家家搬去了香港),他给大家带回来太阳镜和电子表;东东的爸爸是成都0978 工厂副总工程师林之遂,阿诺一家原来是姬姓,邦斯舅舅抗战时期重庆读了大学的,军训课掌握很多野外生存知识。像是一个密室逃脱的设计高手,吴亮在小说中密布了太多的线索,而又从不着急提示。他期待你们用心阅读,并获得货真价实的读后快感。
这本来是所有创作许诺的礼物,但实际上,阅读的这一高光时刻很难降临。帕维奇说:“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小说本身。处在危机中的是那种单行道式的小说。”“要改变阅读的方式,我就必须改变写作的方式。”吴亮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朝霞》54节:“小说写作据说已经停滞不前了,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他们不是不畏艰险但恰恰认为写小说是一件人皆可为之事。”所以,吴亮用碎片化的写作形式,试图改变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朝霞》放弃了集中讲一个连贯的故事,“请不要急于听故事”“让叙事夹杂无关之物,保留应该大刀阔斧删除的冗余段落”(《朝霞》20 节),为此,他引入了大量的知识和思辨,把小说的搭建期许给了读者。有心的读者的确是担负着一部分责任的,与作家一起面对一部作品。金宇澄曾多次警戒作家的创作:有很多读者无论在知识水平、阅读范围、鉴赏能力方面,都高于作者,读者是一个藏龙卧虎的群体,一定要重视和尊重小说的读者。耐心的读者捧读《朝霞》,一定会感受到来自作家的这份尊重。吴亮素来以雄辩著称,自然,在他创作《朝霞》时,你们,就是他预设的对手。
在小说中宋筝老师说:“她一直渴望一个拥有华丽的头脑和专横的语言的人,来将她带走。”她真是道出了一个优秀读者的心声。帕维奇说:“有些艺术是可逆向复原的,是可以让受众从不同侧面接近的作品;甚至是可以围绕着它,通过变换观察视角,对其好好观赏的作品,而观赏者的观看方向取决于他个人的偏好,诸如建筑、雕塑或者绘画便是这样。”“我一直希望把文学——一门不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做成可逆向复原的艺术。正是因此,我的小说一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尾。”这是不是就是吴亮说的,“各自制定各自的生活计划吧”?文学永远期待这样的力学分析,还有实践。
四、时间
吴亮给小说《朝霞》最初选取的名字叫“无处藏身”——“对过去的捕获充满狂热,历史即对缺席者的研究,让缺席者无处藏身,比当时的隐秘在场更加醒目,让他们再次存在”。《朝霞》81 节:“以一种不知道其来源的神秘力量,紧紧攥住那些已经不存在,而曾经存在、就像我们每天尚能确证它确凿的存在,让它们复活,复活在此时此刻的写作中。”他们和它们,是一段灰色记忆中卑微的人和同样卑微的生活,在历史中出现的那一刻就隐隐约约,仿若不存在,只在喧闹消沉的深夜或者黎明时分,在两盏微弱的街灯之间,现出影影绰绰的影子,分明在,又看不分明。如果说“遗忘是一种神力”,那么写作就是另一种神力,它要让那在时间彼岸的,跨越遗忘,在此岸复活。
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中说,写作是一种指向未来时刻的行为,它向未来索取过去。因此,昨日重现,只是开始,重现昨日的晚霞是为了明天清晨有朝霞升起。《朝霞》95 节:“朝霞满天,一个新世界在悲剧之泪中诞生。”正因此,小说在行将收尾时,忽然迸发一种舒展而又饱满的张力,似乎是要讲的故事刚刚开始,一切都在返回途中。艾菲从香港回到了上海,“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最后回到这个地方”(《朝霞》96 节)。林耀华对父亲说:“五年了,爸爸妈妈才回来上海一次,就请一次假,也不行吗?林之遂说,好,我现在就去党委书记那里请假。”(《朝霞》99 节) 阿诺家里有了其乐融融的气氛,朱莉提议阿诺妈妈唱一唱周璇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自己哼的是《何日君再来》。马馘伦和张曼雨在闲聊中甜蜜忆及两人的初次相见。那些之前弥漫在行文中的紧张、压抑、阴郁似乎一夜之间消散,那些在昏黄街灯下面目模糊的人,忽然有了生动的眼眸。“仿佛没有目标,只是一种不肯放弃的期待!”在这舒缓的笔调中,一切,渐渐明朗。在一种沉浸着的宁静中,钢琴的声音不再胆怯断续,渐渐化开,温柔笼住这个萧瑟中渐渐苏醒的城市。阿诺睡着了,小说悄悄结束了,生活开始了。
裘帕·拉希莉在小说《低地》中反复强调:在英语里,过去的是单边的,而在孟加拉语里,昨天对应的单词,“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语中,你需要一个形容词,或者依靠动词的时态,来区分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汉语是没有时态的,而吴亮更是在创作中明确指出,要少用形容词,谨慎定义,少下结论,这就难怪《朝霞》的读者也找不到通常的那个小说结尾。好的小说,并不会真的结束,它不过是把那些往事变成潜流,在交与读者的时候,文学中的生活与现实生活彼此淹没、交汇,形成陆地,长出植物,结出果实,在这世界繁衍生息。
作家刘亮程曾说,文学是人类的往事,正是藉由文学的创作,往事并不会死亡,记忆也不会消失,这是世界赋予文学的权柄。凡那些来过的,发生过的,都散播在每日每夜在我们身边流淌的生活中,并适时现身,而且说法。小说中劳尼舅舅不知道怎么坐新的公交车回旅馆,可这并没有关系,上海滩、跑马场就在他的记忆里,不要担心他会迷路,因为往事永刻在心,它们会给熟人指路。文学还是无用的消遣么,谁敢这样说?《朝霞》 99 节“果品杂货仓库现在是一派狼藉工地,脚手架围困了巍峨钟楼”,2017 年2 月,在小说的写作结束后,徐家汇教堂真的被脚手架团团围了起来。果品杂货店,正是徐家汇教堂。文学在现实中得到了时间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