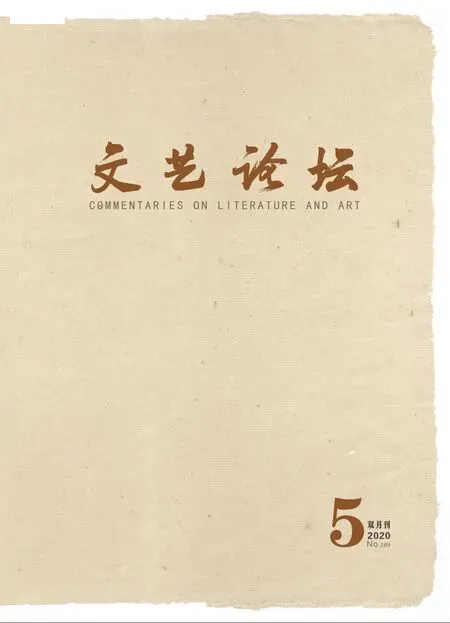格非小说叙事的时间寓言与哲学
◎ 周显波
从1986 年发表《追忆乌攸先生》 到近作《望春风》,格非创作了30 余年,比较完整地经历了自1985 年以来的当代文学进程。在这个过程里,他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个从先锋实验到注重向写实和向传统学习的转向。在格非的叙事世界里,时间是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在格非的作品中已有明显的呈现,除了理论论述外,其作品也显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说,时间问题之于格非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且成熟的主题,对此话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格非的创作思想。”可以说,通过思考格非小说叙事对时间的关注与使用,能够发现作家30余年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追求,另一方面,讨论时间之于格非叙事的意义,可以进一步地探索作家在创作主体方面的秘密,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话题来思考当代作家在小说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时间之于格非叙事的意义,不亚于人物形象之于小说文体,可以这样说,在格非叙事里,时间正如同人物一般重要。格非叙事始终把时间放置在叙事关注的中心,读者很容易地就能够从格非小说中解读出时间意识和时间思维。不同于大多数致力建构地域风格的当代小说家,格非始终具有着一种对时间的敏感度。他不是在单纯怀旧式地书写,或者努力构筑有关未来的乌托邦故事,而是充分利用时间这一角色,质疑、反思甚至抵抗一成不变的认知和思想成规,以及和这一认知和成规伴随或固着在一起的人性问题。
格非的创作在1980 年代登场时就被批评家雷达称为“格非迷宫”,这一称谓也成为先锋时期格非的标签之一。格非小说的“迷宫”性,在于他的叙事里“总是浸透着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东西,它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人进入迷阵”。在格非的小说“迷宫”之中,“迷宫”的塑形当然在于关键情节的有意缺失以及作家始终拒绝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上。作家如同一个旁观者一般,并不一定比读者知道更多。但若从情节的推动作用和小说的时间线索角度来看,在格非叙事中起推动作用的不是人物,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格非在小说的时间问题上,像一个手艺精湛的魔术师,在他自己的叙事逻辑里,抽掉了大多数作者关注的那个核心时间点,而这个时间点才是构成叙事线索完整链条的核心,正是因为缺失了这个时间点才形成了叙事的谜团。显然在格非看来,核心时间点的空缺正是构筑他“迷宫”的关键所在。在《迷舟》 里,旅长萧消失几天的“下落不明”是解开“迷舟”之“谜”的钥匙,但作者恰恰在这里和小说里的警卫员一样对萧的失踪真相一无所知。萧的失踪成为了整个叙事的盲区,“迷舟”的意义也因这个时间的缺席而直接导致了萧的被杀。《大年》中,豹子杀死丁伯高后,唐济尧将豹子按在水里呛死,豹子的罪行以布告的方式贴在墙上公之于众,而唐济尧和丁伯高的二姨太玫一起神秘地失踪。我们可以看到,叙事完整线索链条构成的重要时间节点“完整”地空缺了,这种空缺让小说叙事无法形成闭环,因而,传统叙事里明确的因果叙事意义缺位造成了《大年》故事意义的神秘感和无常感,小说的故事迷宫因此得以搭建成功。先锋时期的格非叙事的在时间关键节点处空缺,让他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迷宫风格,在这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偶然性和神秘感的特殊偏爱。进入1990 年代的格非,时间仍然在他的叙事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敌人》讲述了一个大家族衰败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是对五四时期逃离家庭主题的重复,而是一个难逃劫数式的宿命故事:赵家成员相继神秘地死亡,原因无从探明,在赵家长期生活的哑巴,神秘地来,神秘地离去,所有人都冷漠而缺乏交流,只是等待命运的降临。整部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不再重要,叙事不再是被揭露真相的冲动所推进,因此,与其说《敌人》是在表现大家庭衰败的过程,不如更准确地说,小说是在表现一种先锋叙事智慧。《敌人》的故事一方面在内容上延续了1980 年代先锋小说的主题,另一方面在这个貌似写实的小说里,依然在关键时间缺位的前提下呈现格非的世界观。《边缘》《欲望的旗帜》也都可作如是观,尽管格非在《欲望的旗帜》已经展露了对回到写实传统的兴趣,但小说情节围绕的中心——贾兰坡教授的神秘自杀场景和自杀原因——依然全部游离在叙述视野之外。
在格非的笔下,叙事者的自信与优越感不再是天然的,而是首先要被怀疑的对象,所以在作家的笔下,始终缺席的时间就如同一个黑洞一般,成为了生成故事意义的重要来源,也是唯一来源,而这个黑洞自始至终都无法被叙述者,也无法被读者探测到全貌,探测到秘密的全部答案。在作家看来,小说中的世界正如现实存在本身一样,是神秘且布满偶然的。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里这样写道:“作为再现现实传统的延伸,现代小说记述常人尚未来得及思考的真实,记述了尚未渗入人们意识的现实本质和现实关系。”那个作为事件核心的时间,是黑洞似的存在,正是它吸引着作家一次次用语言去试探并书写,而且在作家看来,这个黑洞“尚未渗入人们意识”,因此如同李商隐笔下的锦瑟一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巧合的是,格非的一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做“锦瑟”,这篇小说就是对诗歌《锦瑟》的小说化改写和格非式的演绎。
格非通过时间缺席的表达,以叙事的形式书写了时间的质感,时间在故事流程中的状态不再是像传统叙事里那种可以宏观把握与捕捉的对象,而变成了叙事意义的构成之一,甚至是意义生成的关键。可以这样说,时间成为了作家探索世界的工具,变成了小说自身表达的一部分。
二
苏童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马原笔下壮美且粗犷的西藏,洪峰的瀚海一般的东北……尽管先锋小说家们注重形式的创新,但通过以上几位小说家的创作可以发现,先锋小说家们依然有意无意中使用了地域风格元素,这些元素也成了识别他们书写个性的标志之一。与其他先锋作家有所不同,1980—1990 年代的格非叙事里,地域/空间因素是非常弱化的,尽管他的小说里并不拒绝对地域的表现。格非小说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南方特有的风景和文化,但与苏童、马原、洪峰等作家相比,格非小说里的地域风格是非常弱化的。正因为核心时间的空缺,空间连同着关键性情节一道隐身了,因此可以这样说,格非的故事里,空间也被时间化了。正如叙事学研究告诉我们的那样,文学叙述过程本身是空间化的存在,作家本质上是在线性叙述空间的魔术里进行意义的传达、对客观时间的模仿、对主观世界的刻画,所以,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时间不是思考的首要问题。格非则不同,他是想要在叙述里通过对时间的激进实验来达到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所以,时间成为了格非叙述第一主角,而空间、人物都成了配角,成了时间的玩偶。
格非对时间问题予以了充分热情的关注,因此在1980 年代先锋小说退潮之后,格非的创作在1990 年代后依然被视作先锋小说的代表之一。但格非又有了明显的变化,《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为代表的“江南三部曲”成了格非创作转型的标志。在“江南三部曲”里,格非表现出对传统叙事学习的热情,他开始注重故事氛围的营造、故事性的表达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叙事追求方面来看,作家格非告别了先锋格非,如若从对时间问题的关注来看,格非显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时间问题的关注。
“江南三部曲”最初被命名为“乌托邦三部曲”,贯穿三部长篇小说的是格非对现代中国乌托邦想象与实践的思考,可以说,三部曲中每一部里作家都通过安排对不同乌托邦思想冲动的表现,来对之进行批判与反思。从陆秀米的乌托邦社会冲动,到谭功达的乌托邦狂想,再到谭端午以诗歌为乌托邦,乌托邦想象越来越与具体的现实割裂开来,越来越不再指向具体的实践空间,而指向人的思想意识深处,特别是人思想意识里对当下的思考与对世界的期待。恩斯特·布洛赫是较早在哲学领域深入研究并拓宽乌托邦含义的。在他看来,乌托邦意味着希望和存在,“乌托邦的(utopian) 通常与精神、意识和期盼连续使用。所谓的乌托邦意识,也能被叫做乌托邦期盼(anticipation) 或乌托邦精神,还泛指其对更美好、更完美的将来的期盼、预感、预显(pre-apparance)”。就“乌托邦”一词的原始意义来说,乌托邦本来就含有着时间性的意义,所以,与其说乌托邦指向着某一具体的空间,不如说它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期待与想象,它向着的是时间的深处。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在三个代表性的现代时间里,不论是传统的乌托邦、人民公社乌托邦,还是被商品大潮裹挟的诗歌乌托邦,最终全部破灭和失败。乌托邦的冲动伴随着对未来的冲动,而事实上每一个阶段的乌托邦实验或实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它们实际已经构成了对当下的破坏,甚至这种破坏对未来都有所影响。格非通过表现现代乌托邦冲动的失败,同时藉由这一冲动的主体,检讨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缺陷和不足。在格非看来,这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冲动的失败,必然和知识分子精神、性格及人性弱点密切相关。
从“江南三部曲”中可以看到,尽管格非的叙事逐渐走向了写实,降低或压抑了对世界偶然性揭示的冲动,但格非小说中的那种因时间问题而带来的悬疑效果依然存在,而另一个与前一阶段创作近似的特征是,格非始终关注着时间问题,只不过他对世界偶然性的关注更多让位给了对历史推动力的揭示和思考。1980 年代的格非惯用的是“回忆—回溯”的方式展开叙事,即以人物为中心追溯某个时间点,由此展开叙述,因此格非的小说具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述氛围,同时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特征。小说《青黄》从煞有介事地寻找一个词语“青黄”的意义开始,继而涉及植物学、民俗学、历史等知识和内容,最终,“青黄”的意义并未被探明,所以,有关“青黄”的诞生时间及其意义来源始终处在建构和推翻之中。1980 年代格非叙事中那个与故事起源、核心情节线索有关的时间一直处在正式叙事之外,但那个时间节点始终控制着正式叙事的进程和节奏,掌控着故事情节的走向。所以,时间给“格非迷宫”带来了留白,这种留白也带来了明显的悬疑效果。在《欲望的旗帜》 之后,特别是在“江南三部曲”里,格非也并没有在叙事里排除掉“回忆—回溯”方式。在《隐身衣》《望春风》等作品里,我们依然能够读到这样的书写方式所造成的留白效果。但与先锋时期的格非叙事稍有不同,新世纪后的格非不再刻意用缺席的时间来制造留白和悬疑效果。他在叙述上依然把时间问题作为角色之一来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比较多的是尝试使用交叉的叙述方式,也就是不同的时间点穿插在一起,以此来解放叙述的人为性,同时让小说拥有了一种有张有弛的叙述节奏。在《望春风》里,贯穿始终的是主人公赵伯渝母亲出走之谜、父亲自杀之谜以及父亲经历之谜等,这些谜团也是伴随着赵伯渝自少年至壮年成长始终的。一直到小说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告别”中,父亲自杀之谜才被彻底揭示,而母亲的秘密在小说中是慢慢揭示的,全部的秘密与“隐情”则要在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三章“余闻”里才被全部揭开。由此可以发现,格非叙事不再是刻意去通过隐藏有关故事的起源时间和核心时间来制造叙事的动力,以此获得悬疑效果,继而完成“格非迷宫”的制造。是的,如果作家仍然一再重复这样的方式,的确让小说显得太单调了。告别先锋的格非在1990 年代中期之后通过不同故事时间的交叉,让叙述变得更加自然和平顺。时间中的谜依然是格非叙事的中心之一,但有关这个谜的时间不再是叙事空缺,而是以交叉的方式,徐徐地如同呼吸一般自然展开,而编织在时间中的事件显得更加丰满——这是先锋时期格非叙事所缺少的。
三
从先锋格非到告别形式迷宫的格非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表面来看是他的创作开始偏重写实性和故事性的经营,叙述上也不再追求形式上的实验性。的确,告别先锋后的格非有意识地注重对传统叙事的借鉴与学习,这一点不止在格非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在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几部文学研究论著里也可以发现。这里可以试举一例。格非多次称赞《金瓶梅》的“草蛇灰线,千里伏脉”结构方法。“草蛇灰线,千里伏脉”,也被格非称为“草蛇灰线、千里埋伏的线索”,指的是叙事上的布局方法,作者通过故事线索的精心设计,达到对人物和事件完整度的把握,从而增强故事的有机性。“草蛇灰线,千里伏脉”是格非对传统叙事的学习和领悟,他把这种叙述方式应用到了自己的写作之中。“草蛇灰线,千里伏脉”,是格非告别先锋的重要表现,这一结构方法标志着他对小说中时间问题处理方法上探索的改变。这表现为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里关键时间空缺不再出现,核心时间的空缺也让位给了具体历史时间的表现,同时,作家时间的结构实验开始有意变为注重时间线索的整体布局。
叙事布局不只是一种方法,在方法选择的背后本质是世界的思想、立场对于主体的变化。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的那样,“我们关于叙事和历史的概念依赖于一整套有关因果性、同一性、起源和终结的共享假定,他们是西方思想所特有的”。格非叙述方法的改变背后,是思想、立场的迁移和变化,尽管历史中的谜依然存在在他的小说之中,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中都不难找到这方面的例子,但历史的随机性、命运的偶然性开始让位给了作家对更深历史动因的探索,欲望、人性、革命都成为格非意欲探究的对象。
《欲望的旗帜》和“江南三部曲”开始,时间之谜不再是缺席的,而是格非在小说里极力要探索的对象,这种解谜的过程成为了他小说叙述的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结构的背后不再是对世界之谜的叹为观止和对无常命运的无可奈何,而是叙述者拥有了对世界探究的动力和主体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贾平凹与格非的小说来尝试说明问题。在《高老庄》《古炉》《老生》《山本》等小说里,历史是纯粹无序的存在,道德伦理和文化规范不再重要,历史的变化只是人欲望的镜像,人在历史中无可作为。既然历史是无序且不可把握的,那么,在其中生存的人必然生成宿命感、虚无感与无力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历史体验,贾平凹在叙事中才要频繁使用到鬼神、通灵、卜卦、幻觉和梦境等元素,并把这些元素作为展现与思考历史的重要手段。这些元素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作家重复使用。也正因为这样,贾平凹小说才被有的批评家称为“故弄玄虚”“为神秘而神秘地充满了‘人工气’”。与之相比,格非则不同。告别先锋的格非对历史始终具有探究的热情,尽管历史背后的动力不一定是作家所喜爱或认同的,但作家依然毅然决然地要去揭示。如果说先锋格非时期那种“格非迷宫”在他个别创作中也存在“装神弄鬼”的嫌疑,那么告别先锋形式之后的格非显然不再注重形式上的时间空缺实验,转而关注历史的构成之谜。对后期的格非来说,时间不是空缺的,而是有形状的,他的小说就是要书写来自历史深处的问题。“江南三部曲”书写了乌托邦冲动与知识分子精神;《隐身衣》探究了艺术在商品社会的逻辑和意义;《望春风》表达了乡村在现代性冲击之下不可避免地衰败,以及在这种衰败形势之下,乡土之子试图用情感与记忆反抗这一过程,当然,这种反抗是脆弱且注定失败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分析的那样,格非没有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书写之上,而是关注生活之下“草蛇灰线”一般的内在规律。格非在与张清华对谈时谈到,“我固执地认为,生活其实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空间之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飞升之中”,“敢于描述这种飞升,不是对生活的想当然,恰恰是对生活的尊重。其实,在现代小说诞生之前,这种飞升感一直是民间故事的专利。何况,生活,哪怕是最枯燥的生活,其实也是神秘的。我曾说过,每一扇夜幕中的窗户都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阿甘本认为,“现代人的根本矛盾恰恰在于他仍然没有获得与历史观念相当的时间经验,因此被痛苦地分裂成两半,一半是作为难以捉摸的瞬间流动中的时间中的存在,另一半是作为人类起源的历史中的存在。迷失在时间中的人无法拥有自己的历史本性”。齐格蒙特·鲍曼干脆就将现代性称之为时间的历史——“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置身在流动不居的历史中的当代作家,试图把握和书写时间是一项特别有难度的挑战,稍有不慎,或者被当下的热潮裹挟,或者变成一个宿命论者。当格非的写作越来越回到故事性的同时,他也越来越关注小说与真实生活的联系。或许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格非小说才不再执着依靠用时间的空缺制造悬疑效果,转而探究时间之下历史的真正动力。正是这一点,格非的叙事才没有迷失“历史本性”。
通过对“历史本性”的思考,加之格非对小说文体和语言的自觉追求,格非的小说赓续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先锋阶段的格非受西方文学影响巨大,后期的格非对中西小说方法的兼容并蓄,依然有着明显的“方法派”痕迹可循,这些是格非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标识。在小说思想内容方面可以看到,格非写作受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影响重大,这导致他的写作带着非常明显的知识化、理论化和方法化特征。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格非所追求的生活中的那种“飞升”,那种对时间穿透的追求并没有彻底超越既有的精英知识—话语的框架,也就是说,这种框架既是他认识—思想方法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一种限制。在《春尽江南》里格非书写了知识分子精神的颓靡和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挫败,《望春风》里作家把垂老的乡村之子安排返回残破的乡土上,以此来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相抵抗。我们在这些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了作家的努力,看到了他力图通过揭示当代问题的复杂和困境,以此来召唤失去的诗意时间,哪怕作家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间一去不复返。但应该看到,“江南三部曲”也好,《隐身衣》《望春风》也好,这些小说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和知识,与主流知识界的视角、思想框架太过贴近,直接影响到了他对历史本质探究的深度与思考的个人化。需要注意的是,突破流行的思想框架,这不止是格非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当代小说家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因为当视角和思想框架难以拥有个性化和创造性的突破时,那些在叙事里的生活经验就往往会如同碎片一般散落。
注释:
①王健:《论格非写作中的时间问题——以<江南三部曲>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10 期。
②雷达:《动荡的低谷》,《小说选刊》1989 年第2 期。
③钟本康:《“格非迷宫”与形式追求——<迷舟>的文体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89 年第6 期。
④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
⑤李丹:《乌托邦思想研究:理论探微·发展脉络·殊异甄析》,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第18 页。
⑥[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89 页。
⑦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99 年第5 期。
⑧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 年第2 期。
⑨[意]吉奥乔·阿甘本著,尹星译:《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94 页。
⑩[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1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