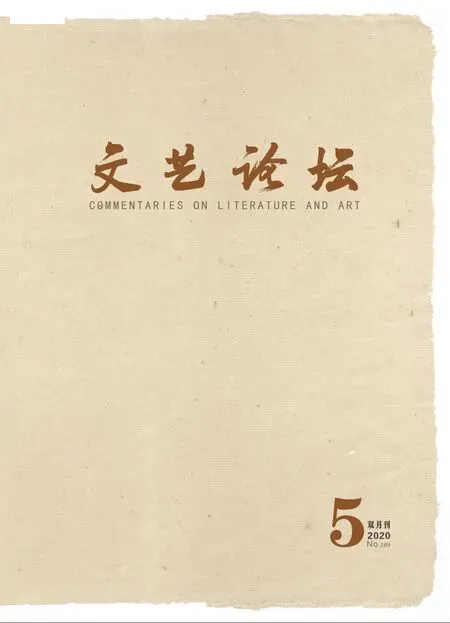存在之路的抵达:朱文小说创作的意义生成机制
◎ 熊龙英
救赎:日常行为的存在性
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的勘探。刘小枫说:“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从日常的现世虚空进入歌唱的现时状态有如祈求意义的冒险,诗的活动随时可能丧失现世,成为一种意义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一切应该实现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各类富有活力的“存在的图”的历史。
人的存在与虚无的悖论关系是存在主义文学最大张力所在。作家所要画出的“存在的图”就是作家用文字描述的人的存在的精神轨迹,即在存在与虚无的悖论之中,人如何携带自身来往穿梭,如何穿越虚无走向存在。朱文的小说是对“日常行为”的关注。文学既然被认为是对人的存在的研究,就像萨特从康德的“自在之物”以及康德作品中得出的:作品首先存在着,然后作家才将其制造加工成作品,从而作品本身是作家存在本身对其真正存在的一种要求和执着的呼吁。所以,朱文小说中的“日常行为”必然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在的表现式的,即小说人物外在的行为表现,以及小说人物生活的场景;第二个层次则是内在的存在式的,即外在表现所折射出来的存在的意义。第一个层次属于生存层面,是第二个层次构成的基础,而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必然超越。小说即是通过对第一层次“日常行为”的表现的研究,实现第二层次的存在性的超越。换句话说,小说的经验是突破日常经验而又离不开日常经验的超越经验,是对有可能实现的意义秩序的呼唤。
小说对存在的研究是通过对生存世界的“翻转”而实现,而这个实现的过程又是小说人物行为的结果。西西弗神话作为存在主义的中心神话的实现是通过无休无止推石头的动作,《等待戈多》的完成是徒劳无益的等待,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逃离是通过对没有尽头的沙穴的挖掘,存在的瞬间实现是对生存世界的不停反抗,如此才能走向生存的另一面——存在,从而完成存在主义所提倡的拯救。但在朱文这里,“行为”的路径被隐藏起来,“日常行为”以一种非“行为”的方式呈现,“行为”的模式无从概括,相对于“存在性行为”的“自为”地从虚无向存在攀升,“日常行为”被“行为”本身的物质性所遮蔽,显现的是“自在”的状态,形而上的意义不可寻找到。那么,拯救将如何实现呢?
日常行为属于生存性行为,而写作属于典型的存在性行为。通过存在性行为对生存性行为进行展示,生存性行为将丧失本身的原初形态,即现象学的质朴表象,而被引向到意义的探讨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写作的行为使得日常行为获得了存在性的意义。当被作家的存在之光照耀、穿透的时候,日常行为就脱离了生存的现世而实现了存在性的超越。但当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审视朱文的小说的时候,意义仍然被日常行为的质朴性所阻碍,存在的路径依然无法觉察,存在的地图被生存的地图所遮蔽。如果说贝克特对生存世界的荒谬的不断重复是要表达他对生存的悲观与绝望,从而获得最荒谬的存在意义,那么,朱文的小说摒弃了一切外在的作家价值判断也放弃了内在的价值审视的时候,存在的意义该由什么来承担?
重复:荒诞与意义的建构
小说是对生命的拷问,是对个人的命运、心灵内在事件的探究,对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的揭示,对历史禁锢的接触,对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的触摸,对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和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状态的思考,这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当朱文对着日常生活的角落里的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而仔细琢磨的时候,这些细节的纹理被一层层铺平,铺成一幅属于朱文的地图,但是这又是一幅若隐若现的地图,因为,作为朱文小说里的人物的“小丁”并没有用他的行为来完成这幅地图,小丁的重复出现似乎只为出现而出现,出现的意义就像他在大街上游荡一样毫无方向,也毫无归宿。
如果硬要追寻朱文小说里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荒诞,而重复是荒诞意义产生的开始。朱文小说中的重复性首先体现在他对小丁和关于小丁的没有多少意思的故事的反复书写,对无意义的重复本身既消解了意义也建构了一种新的意义,如《西西弗的神话》中所重申的就是西西弗受罚于“重复”的悲惨命运。人们每一天从梦中醒来,生活沉重的石头依然在山脚等待,于是“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存在主义哲学或者文学里,生存重复性动作是荒诞的开端,因为对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活动产生厌倦后,“它同时启发了意识的活动。”但对于小丁来说,他生活的中心就是无所事事,在日常生活中他过得稀里糊涂,精神上除了不断强调他在写作以及对自己的写作充满恶狠狠的信心外,他就像他的朋友反问他的那句:“你不是个闲人是个什么?”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的开头和结尾重复这样一段话:“小丁坐在窄窄的满是烟头烫痕的木桌边,用左臂撑着脑袋,几次想张大嘴巴惊叫上几声。当然最终没有声音,他只是重复着张大、张大、再张大的动作。”这是朱文的小说人物典型的动作方式——近乎无动作的动作,或者是无声的动作。没有声音的动作意味着动作的无意义,而对无意义的重复是重复的最荒诞的意义,就像贝克特从《莫菲》到《瓦特》再到《莫洛伊》,反复表现了人类所有重复的荒诞性一样,小说的意图是把重复推向极致,从而也推向意义。但是在朱文这里,早已消失了贝克特对自己对生命虚无的悲观体验的沉溺,也不再是加缪的对荒谬的反抗,而是赋予重复或者无意义本身合理性,重复因此并不是迈向荒诞而是追求其合理,或许这才是朱文对日常生活的无意义的重复所要真正达到的小说意图。
刘小枫认为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典型: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理性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另一种类型是齐克果的信仰跳跃或尼采的生命沉醉。而对于朱文来说,终极悖论的生存问题已经过于沉重与庞大,他关注的始终只是生存,终极悖论已经不是他所要解决或者反思的问题。在朱文的小说里人物只是在生活着,而没有人会追究为什么而生活,没有反思,也没有价值的判断,朱文所要揭示的只是在这个生活世界上有这样的人,过着这样的浑浑噩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与你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没有关系。朱文把这些东西的出现归结为他“不容混淆的内心感受”,这种内心感受也就是他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物注定是与你有关系的,而另一些注定是没有关系的。注定与你有关系的迟早会与你有关系,注定和你没有关系的就是与你有了关系也还是没有关系”。这或许是朱文的小说、朱文笔下的小丁生活的最好的注脚。
那么,混沌不堪是否就是小丁的全部,或者混沌不堪就是朱文所要说的全部?朱文的小说只是让人知道有小丁这样一个灰色调的人物?对于这个在日常生活里冲冲撞撞又时常流下眼泪的小丁,这个觉得自己毫无希望又莫明其妙地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小丁,这个满口否定爱情、否定亲情却又对肉体也时常产生厌恶的小丁,这样没有多少意义又充满矛盾的意义的小丁,朱文所要跟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隐藏在小丁背后的已经不断地闪烁出来,而隐藏在朱文背后的又是什么?
式中,vid定义为当Yp≤α0时,弹体侵彻靶体的最小速度,即,当冲击速度低于该临界速度时,弹体不能侵彻靶板,此时弹体行为类似于泰勒圆柱撞击。u=0时,可以得到:
其实当小说只是叙述个体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织在其中的终极悖论,这种叙述不需要消除、解决,也不一定需要反思。当小说可以不承担沉重的外形的时候,意义已经在零星的叙述中挥洒出来,就如同小丁无端涌出的泪水,没有人感动自己,也不用去感动别人,自己感动自己就已经足够,生活中的灰尘不需要消除、解决,甚至不需要反思,在一种对生活的直接叙述中意义如汗水一样开始挥洒出来,或许,这才是朱文小说真正的意义。
沉沦:存在之路的抵达
现实世界(日常生活) 意义的拯救在朱文的小说里既然已经被取消,这就意味着在朱文小说文本里现实的地面与存在的天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缺失,现实的生存行为无法被存在的光芒照耀而得到超越而飞升到存在性行为,这种缺失构成其小说存在主体(日常现实存在) —客体(日常现实存在)—小说世界(日常现实存在) 的平面模式。然而日常生活既然被小说这样一种作为存在的方式所观照,那么必然有另外一条引领的路径在向着朱文的小说敞开。小说文本本身无法在作家渗透其中的主体关怀下抵达存在之路,存在之路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诗学意义上的混淆而只能秘密地彰显,这种彰显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沉沦的方式,即作家以非自传的形式把自身投入到小说中去。这也就是说朱文把自己作为连接文学世界所要达到的“存在性”观照与小说的“日常现实性”之间的桥梁和通道,而这条通道是把小说的表达带到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如果作家渗入小说中的关怀意识可以称作拯救的方式的话,那么作家潜入式地游走于小说中就是沉沦的方式了,当大多数作家选择作为拯救的圣者而存在的时候,朱文选择了沉沦于小说现实中,与他笔下的小丁一起呼吸着混杂着灰尘的空气。前者是向外的占有、扩张式的,而后者是向内的拥有、怀抱式的。“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断地回到自己……他的写作是把自己当做了一条道路、一座桥梁或是一块铺路的石子,那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洪流将从此经过,伤及自身、流血流汗,甚至被完全碾碎也在所不惜。”“不断地回到自己”意味着朱文的创作方式是从自身出发的,是内在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朱文小说里的那个小丁充满了单调与复杂的悖论。在铺天盖地的没意思的小丁故事的叙述中,一个沉闷、混浊、游荡、莫明其妙的“小丁”无法形成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小丁和他背后的精神像碎片一样散落在空阔的虚无中,唯一给予“主体”“主体感”的是言语,话语像一种直接的分泌物一样将暧昧矛盾的主体涂抹出来。在小丁的故事中,“小丁”或“我”被叙述出来,就像“小丁”或“我”分泌出有色的汗珠,即使它是单调的白色,“我”也沉沦于现实的目光中,而目光散射出了“主体”,这个微薄的“主体”并不希冀获救,就如同朱文所说的:“‘小丁’的卑微不想感动任何人,甚至不想感动他自己。”
朱文的大多数作品其实是一部作品,都是模糊的“主体”由内向外分泌自己的现实,即使这种现实仍然是暧昧不清的。小说语言对现实进行验证,但语言本身并不能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划出界限,所以这种讲述的努力所给予的“主体”仍然是“主体”的幻象。言语创造出?“存在”的纤细核心又向外辐射出更为有力的“虚无”。这个“存在”交织在“现实虚无”与“幻象虚无”之间,“存在”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若隐若现,自相矛盾,在词汇的流动中发出微弱的阵颤,在句子的延展中留下模糊的身影。它虽然若隐若现,但在每一次显露之时都能挥发出诱人的光芒,虽然自相矛盾,却正是如此自我的悖论形成了存在动人的张力。如果正如韩东所述:“朱文曾这样对我说:真实的写作将与你的生活混为一谈,它们相互交织、互相感应,最后不分彼此。”那么就不难理解自我的悖论在朱文这里是如此明显又如此隐晦,一方面作者的意识在小说的言语中毫无觉察(《到大厂去到底有多远》《去赵国的邯郸》《三生修得同船渡》《五毛钱的旅程》等),或者用一种夸诞的语气覆盖作者的主体意识(《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等);而另一方面作家又并非作为一个旁观者(少数作品如《单眼皮,单眼皮》《大汗淋漓》等除外),而是以深入其中的姿态来参与他的写作。用朱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所强调的就是我的写作跟我这个人的关系,我所信赖的一种写作方式与我的作品之间有某种必然性和必要性。”
所以“沉沦”的方式并非堕落的方式,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生活、对于写作的更内在的沟通与感悟,这也就是朱文在他寥寥几篇关于写作的散文随笔里不断地强调沟通的重要性的原因。朱文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是卑微的存在,在这种卑微的背后并不需要去营造一种强加的意义,卑微本身完全可以活得稀里糊涂又理直气壮,承认卑微的品质要比在卑微之上营造一种虚无高蹈的光芒更重要。在小说里的那个“我”以一种夸诞的语言把金钱和性作为写作的外套穿起来,而狂妄气焰的欲望外套背后却是一种放低姿态的本质,道德上的低姿态意味着对生活本原状态更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狂欢而又节制的叙述中,欲望化的词语被朱文当成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就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和其他的写作区分开来。所以在朱文看来,太多的作品由于作家的高蹈姿态无法与真实的生活很好沟通,所以“往往会使非本质的,貌似深刻的,貌似博大的因素渗入到你的写作中,左右你的写作,让你为自己无端地感动,却使作品品质堕落”。
所以,当朱文说出“作家毕生的努力也许就是这样一项工程:不懈地用词语的铁锨挖掘一条通向自己、通向自己的心灵的隧道,让心灵固有的光芒喷薄而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朱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深入到生活中,从而挖掘出一条通往存在光芒的道路?在朱文这里,挖掘的动作靠词语的“铁锨”来完成,这是一个向下挖的动作,而这个向下挖的动作正是靠朱文投身到小说中去完成。
所以,以沉沦的方式所抵达的存在之路在暧昧的表象背后只能若隐若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朱文的存在是由内向外的,而不是相反;是体液的分泌,而不是涂抹在身上的外套;是身体运动后汗液的挥发,而不是照耀在身上的温暖的阳光。探讨朱文的小说的存在是以存在的方式的独特而具有独特的意义魅力的,这种魅力在不断地产生各种表象化幻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洒落意义。
注释: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著,陈永国译:《德国悲剧的起源》,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第7 页。
②在刘小枫这里,“诗”是在原初意义上来使用的,指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目的行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7 月版,第52 页。
③[法]萨特著,施康强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什么是文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4 月版,第102 页。原文为:康德认为艺术品首先在事实上存在,然后它被看到。其实不然,艺术品只是当人们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它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
④⑤[法]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10 月版,第14 页。
⑥⑦朱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华夏出版社2004 年1月版第164 页、第265 页。
⑧朱文:《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一个介绍>(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10 月版。
⑨⑫韩东:《弯腰吃草·序》,参看朱文:《弯腰吃草》,华艺出版社1996 年3 月版。
⑩林舟、朱文:《在期待之中期待——朱文访谈录》,《花城》1996 年第4 期。
⑪张钧、朱文:《写作是作家最好的自我教育方式——朱文访谈录》,参看张钧:《小说的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 月版,第7 页。
⑬⑭朱文:《关于沟通的三个片断》,《作家》1997 年第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