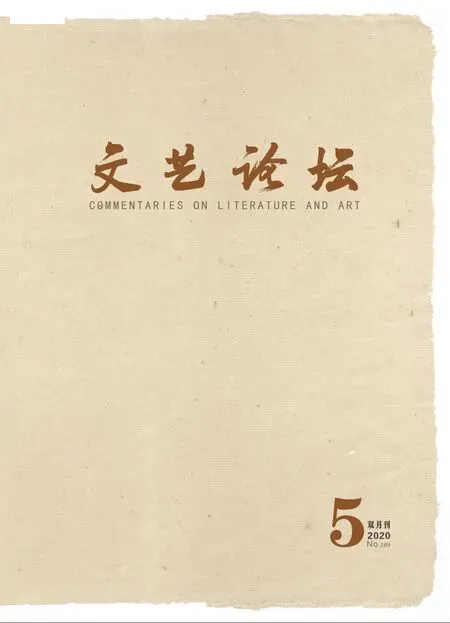虚实之间的性别隐喻
——评格非的《春尽江南》
◎ 李彦文
每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会思考所处时代的一些大问题,格非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人与自己的时代到底可以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人能否抗拒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现身方式以及它们的影响力,人对最高价值的向往与物质欲求等等。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又如此众多,一个主人公显然难以胜任,格非明智地把这些问题分别放在主人公谭端午和庞家玉身上,让他们以男女/夫妻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这样一来,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两性关系就构成小说中颇具象征意味的隐喻。探究格非如何通过男女主人公讨论这些问题,以及他们负载的性别隐喻,是本文的兴趣之所在。毕竟,格非思考的这些问题困扰着这个时代的几乎每个人,而当他的思考通过虚虚实实的性别隐喻表现出来,就格外令人着迷。
一、价值理性与时代
小说的男主人公谭端午在1980 年代大学毕业时已是著名诗人,他也的确以诗人之名享受了那个时代大众的崇敬与膜拜。但1980 年代的辉煌只是谭端午的前史,当下时代的谭端午与时代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现时代的谭端午虽然依旧写诗,却已经被这个崇尚成功的时代抛进失败者的行列。他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每个月的工资只够买烟。
谭端午在现时代出场时,正赖在家里的床上不肯起身。他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物品的杂乱是已婚男人惯有的毛病,不过,杂乱也同时意味着随意。在刻意为之的整齐消失之后,谭端午更容易放松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谭端午的家类似于本雅明的“室内”,那个相对于外部空间的内部空间。本雅明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在世界’”。谭端午躲在自己“室内”做的,是读书、思考、听音乐和写诗,它们是“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是他真实的精神需要,也是他确证自我存在的最佳方式。他在小说中一直在阅读的,是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他喜欢听的,则是西方古典音乐,如海顿、莫扎特等。谭端午喜欢的都与现时代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做这些事情时的谭端午,犹如本雅明收藏和阅读图书一样,让“灵魂徜徉在过去的精神财富的丰富之中,并让这个过去成为自己生存的土壤”。不过谭端午并不是怀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
当下时代的工作单位是大部分人疲于奔命的地方,但对谭端午而言,它是他的另一个“室内”。他的单位“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弥漫着颓废的气息。这个空间为他隔开了日趋忙乱的时代,他可以在这里享受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寂寞与自在。谭端午在自己的资料室里,“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本雅明的图书馆。本雅明喜欢收藏图书,把它们随意摆放在图书馆里。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从实用性的单调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让他“把这种新鲜直接带入思想的行文中”。而谭端午在自己的资料室里感受着“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这种美对于诗人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如果说让谭端午躲进室内有利于保持他的真实自我的话,却也有切断他和时代联系的危险,更何况,格非还要让谭端午发挥文学知识分子的功能,只有这样,他的姿态和沉思才是这个时代的,因此他必须让谭端午走到室外。格非为此在谭端午身边聚合了文学知识分子、精神病人、教师、律师和市民等各种角色,他们分别是他的诗友、同母异父的哥哥、上司、儿子的老师、妻子和母亲。与这些人的日常相处,可以让他走向大街、城乡结合部、朋友的客厅、诗歌研讨会、花家舍等人群聚集的地方。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可以尽量将观念之虚落实为细节之实。
外部空间中的诗人谭端午,就像现代派诗歌的鼻祖波德莱尔一样,是穿梭于都市中的浪荡子,是格非找到的观察这个时代的风景、人及其精神状况的最佳人选。
诗人往往对风景有着特殊的敏感。然而,谭端午在郊外见到的是一座挨一座新建的店铺和工厂,他厌恶地把它们比喻成“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城市中曾经孕育了古典诗意的运河,在夜里散发出“恶之花”式的美感,“两岸红色、绿色和橙色的灯光倒映在水中,织成肮脏而虚幻的罗绮,倒有一种欲望所酝酿的末世之美”。小说中有一个谭端午和文学女青年绿珠一起在深夜寻找渔火的情节。“渔火”意象凝聚着“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古典诗意,然而二人探寻的结果,却是发现“渔火”的所在地是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所谓的“渔火”,不过是运送垃圾的卡车的大灯。
格非还让谭端午一再进入各种人群聚集的地方——诗友陈守仁家的客厅、宴春园饭店和聚集着诗人的酒店。不过,谭端午并不像波德莱尔那样乐于享受人群中的孤独,而是在人群中随心所欲地走动或离开,他和人群的关系是疏离的。在陈守仁的客厅里,他听官员和商人们大谈水、牛奶不能吃,豆芽、鳝鱼有添加剂,癌症发病率等时代问题;在宴春园饭店,他听到房地产商陈守仁大谈读《资本论》的体会、黑社会老大感叹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一向风流惯了的徐吉士呼吁重建社会道德,看到秃头老板趁着教琴占小史的便宜;在酒店,他目睹刚刚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专业问题的诗人和评论家们,转眼就集体跟着徐吉士去找妓女。面对表里不一的人群,谭端午选择沉默。
在漫游中观察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的谭端午,更多的是这个时代的沉思者。譬如他在听了周围人对人的分类——“人”和“非人”、“活人”和“死人”、“旧人”和“新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加以抽象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种种生存智慧”。谭端午的思考逻辑清楚,直达本质,像极了那把庖丁解牛的尖刀,直指现时代的病症:这个世界比布莱希特时代更坏了一点,它不仅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而且“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在此意义上,谭端午是这个时代价值理性的代言人,在边缘处对这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和精神状况做出判断。
二、庞家玉与工具理性
小说的女主人公庞家玉毕业于理工科大学,她一再变换职业身份,最终选中了律师行业,与人合伙开了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符合时代标准的成功者/新富人。庞家玉尚未出场时,小说就从叙述者/ 谭端午视角对她进行了描述:“凡事力求完美。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时常暴怒。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这段为庞家玉定性的话蕴含了丰富的信息。
“一步都不能落下”作为庞家玉的人生信条,说明了她和当下时代之间的关系。她抱着不能落伍、争取领先的心态,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这样的庞家玉是居于时代中心的,也是无比忙碌的,犹如“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机器”“运转”这些语词的使用,表明叙述者把庞家玉视为一个被时代和自我役使的工具,一个被异化的人。
事实上,按时代标准看颇为正常的庞家玉,在叙述者/谭端午眼中是不正常的。荷妮给神经症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神经症乃是正常人的偏离”。那么,何谓“正常”,荷妮认为,“我们关于正常的观念,就是通过认可在一特定团体之内的某种行为和情感标准而获得的……但是这些标准因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的不同而大异其趣”。荷妮抛弃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从决定人存在的文化、时代等结构性因素重构“正常”的标准,“正常”或“不正常”的人因此成为环境的造物。荷妮还敏锐地指出,很多看来非常适应现存生活模式的人可能具有严重的神经症,而神经症的基本因素是焦虑和抗拒它们的防御机制。
庞家玉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适应现存生活模式却具有神经症的人,她身上表现出了种种焦虑症候。首先,她经常陷入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并因此表现出一种矛盾冲突的特征。譬如她在准备买第二套房子时曾一度亢奋,为了力求完美,费心费力地看房、比较,几个月后她身心俱疲。在这种虚弱状况下,她莫名其妙地被一个房子广告打动,闭着眼睛付了定金。如此草率地做出重要决定,与她的力求完美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庞家玉对待儿子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她对于儿子在学校排名的直线下降既痛心又熟视无睹;她逼儿子背《尚书》和《礼记》,却对儿子身上已经很明显的自闭症兆头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与“熟视无睹”,可以有效地降低庞家玉的焦虑,可谓一种有效地防御机制。其次,庞家玉经常暴怒,暴怒是她焦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非理性的。小说中庞家玉的暴怒往往发生在儿子若若身上。每当看到若若偷偷玩PSP,或给若若辅导功课时,她就会对着儿子责怪、怒骂、狂叫、拍桌子,陷入一种疯狂状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目的是让儿子好好学习,而不是无休止地打击他的自信,蹂躏他的自尊。庞家玉的暴怒表现出的是焦虑的侵略性,即“反对他人、攻击、损害和侵犯他人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敌视的行为”。而且,庞家玉的暴怒越到后来越无法控制,其侵略性也不断增强。
那么,庞家玉为什么会患上神经症?在荷妮列出的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等因素中,现时代的文化与性别是重要原因。现时代与庞家玉关系密切的文化是学校老师的教育观念。若若的老师们都是极端功利主义者,他们看到了升学与将来社会竞争的残酷,把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鲍老师要求庞家玉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孩子学习,姜老师要求她“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现时代的文化与性别文化构成了冲突,功利主义文化要求她严厉地对待儿子,性别文化则要求她温柔地爱护儿子。当然,格非把温柔与爱视为女性的本性,这恰恰说明这种性别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已经让人忘记了它的起源。
按照格非的叙述,不仅顺从老师的要求不是出于庞家玉的本性,她追求的做新富人也同样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虚假需要’,‘虚假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春尽江南》中虚假需要的社会内容,是鼓励所有人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追求成功,它无关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它的功能则是有效的压抑性的社会管理。因此,庞家玉的神经症的起因,是虚假需要压抑了她的真实需要。她内心中有着对最高价值的向往,她渴望去西藏这个灵魂净化之所,却按照时代的要求追求世俗的成功。作为女性,她同情弱者,希望法律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却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作为女性,她被男性合伙人徐景阳视为情感过于纤弱(这当然又是一个本质化的女性特征) 因而不适合做律师的人,只有徐景阳这个男性能够道出法律的实质——“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这个说法表明了现代法理社会的工具理性原则。
格非还令人惊讶地把工具理性的原则放在了灭门案罪犯吴宝强身上。吴宝强仅仅因为女友手机中的一条暧昧短信,就杀死了女友上司王茂新一家六口和保姆,连2 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不少论者指责他没有人性,或者把他说成人性恶的代表,但必须注意到,吴宝强在杀死王茂新及其父母后没有丝毫恐慌,而为了杀死他的其他家人,耐心地躲在立柜里等了3 个小时。在杀人时表现得如此贪婪而冷静,支持他这样做的观念是什么?吴宝强声言“杀人就好比赚钱,多赚一点是一点。多赚一个是一个”。表面上看,这个比喻显得荒诞不经,实际上,吴宝强在杀人时的贪婪与冷静算计,与资本主义精神如出一辙。韦伯曾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在于它那“理性地而且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人不是因为需要去追逐利益,而是“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吴宝强体现的正是以工具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精神。小说还别出心裁地从庞家玉作为律师的视角,让吴宝强看起来像“上帝”,又像“先知”,这无疑既突出了工具理性的冷酷无情,也表现了格非对工具理性的极端憎恶。
更重要的是,庞家玉的焦虑及其表现——矛盾冲突和非理性——都不是属于她个人的,而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恰如荷妮所言,“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这个文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处境所造成的”。那么,格非何以要让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以隐喻的方式放在庞家玉身上?换言之,女性和大多数人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大多数人”换成“群众”一词,则可以发现,那些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家——勒庞和莫斯科维奇——都认为群体具有女性的特征,如此说来,格非和他们持有类似看法。
三、婚姻与性的隐喻
《春尽江南》开始于谭端午与庞家玉第一次性爱的场景。那时候,庞家玉名叫李秀蓉,是个稚气未脱的19 岁大学生,她对诗歌未必真正理解却极为热爱,谭端午则是来自上海的著名诗人。谭端午是他们的性关系中的主宰者和发起攻击的一方:他突然紧紧地搂住她,“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任由他摆布”,她的羞怯、挣扎以及最后的屈服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是神对待凡人的态度。他怜悯她,如同神怜悯自己的牺牲品。他说出的“我爱你”是在欺骗她,李秀蓉回应他的“我也爱你”却怀着百分之百的纯真;他享受着性爱的愉悦,她没有快乐,但“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地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她被动地承受,慷慨地自我牺牲,只等待有机会仰望着他说出“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她“仰望”的姿态是凡人面对神的姿态,她说出的这句话不知已经流传了多少世纪,那是抱有传统性观念的女人在这种情境下必然要说的,它表达着女人放弃自我从属于男人的愿望和喜悦。然而,谭端午这位时代之神对李秀蓉的抛弃果断而冷酷。他不顾李秀蓉发着高烧,甚至在临走前把她口袋里的钱搜刮尽净,根本不考虑她怎么活下去。即便是戴着诗人的桂冠,谭端午所为也是彻头彻尾的流氓行径。这个性爱场景因此成为一次祭礼,谭端午“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贡品的祖先和神祗”,而李秀蓉,则是那个纯洁无辜的牺牲者。这个性爱场景既是写实的,又充满隐喻意味。无论是李秀蓉对待谭端午的态度,还是谭端午对待李秀蓉的态度,都是1980 年代价值理性与大众关系的隐喻:占据神位的价值理性粗暴而无耻,大众纯真而顺从;大众因为崇拜神而成为神控制下的木偶,进入被催眠师催眠的状态。莫斯科维奇曾论述大众易被催眠的特性,在催眠师的暗示下,大众“完全服从命令,做别人要求做的事,说别人要求说的话”。被抛弃的李秀蓉的伤心、痛楚与无路可走,则隐喻了1980 年代末价值理性离场后大众的失落与迷惘。
从本性而言,诗人、神或价值理性并不愿降落世间,他们对婚姻这一人间秩序没有多大兴趣,然而,谭端午没能逃过命运/格非的安排,和改名为庞家玉的李秀蓉结婚,就此跌进了婚姻那可怕的现实感中。
现实感对谭端午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他感到自己在面对现实时“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这种无力感,在象征的层面隐喻着价值理性在现时代的无所作为,恰如本雅明所言,“在科学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于一个价值世界中……价值可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但它们不是现实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甚微,它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越小,对现实就越是高高在上”。不过,谭端午和他代表的价值理性确实作用甚微,不能因此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反而经常遭到被工具理性殖民化的庞家玉的反对和鄙视。
谭端午拒绝承担的婚姻之重,全部落在了妻子庞家玉身上。她负责赚钱养家,解决全家的衣食住行,在她多年的努力下,家里已经相当富裕;她也负责儿子谭良若的教育——给他转学转班、辅导各门功课和联络老师;她还负责所有的家务;甚至是谭端午的母亲,她那刁钻而市侩的婆婆要求和他们一起住,她也得为此去买第二套房,买房中的所有事务也都由她一手操办。庞家玉当然不是万能的,她在艰难时刻——他们想要回被占的房子——曾“用哀求的目光召唤丈夫,想让他一起去”,然而她得到的回应却是“谭端午也用哀求的目光回敬她,表示拒绝”,最终的结果是庞家玉独自前去。谭端午从来不想也不愿成为庞家玉在现实生活中的有力支撑。格非由此写出了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婚姻是多么令人失望。
作为价值理性代言人的谭端午与工具理性时代追随者的庞家玉,在婚姻之内很少合作,而是相互反对,“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庞家玉不满谭端午拒绝跟随时代一同前进,把他写的诗歌称作“没用”的东西,试图把他拉进现实和自己一块解决日常生活事务,谭端午因此感到妻子带给自己的只有“猜忌、冷漠、痛苦、横暴和日常伤害”。而谭端午作为丈夫,虽然深知自己的母亲市侩与专横,也经常目睹母亲折磨庞家玉,但他对庞家玉的遭遇没有丝毫同情;庞家玉患癌症后每晚熬中药,谭端午也从不问她哪里不舒服,“似乎这样的询问,让他感到别扭和做作”。对妻子如此漠不关心,说明谭端午从不曾爱过庞家玉。事实上,他在结婚第二天就想离婚,此后离婚的念头也从未消除。
饱受婚姻现实感压迫的两个人,都需要婚姻之外的补偿,于是,性再次出场,承担拯救功能。谭端午在婚外性问题上,是贾宝玉的当代传人。他欣赏同事小史的憨媚,喜欢时不时和她当面或电话调情。如果说小史有点像史湘云的话,让他动心的则是当代黛玉——陈守仁的外甥女绿珠,绿珠有一种落拓不羁的美,是个能从头到尾背诵艾略特的《荒原》、品味不俗、患有抑郁症的价值虚无主义者,她常常主动约会谭端午,和他谈论文学,似乎是这个世界为谭端午留下的唯一精神知己。但绿珠是聪慧的,她有能力看穿谭端午的内心:“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还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在绿珠玩世不恭的质问中,谭端午的欲望、怯弱和不负责任无处遁逃。
作为女性/妻子的庞家玉,在性问题上从不曾有过谭端午的幸运。她一再在病中最无力的时候,遇到不怀好意的男性:唐燕升和黑车司机都曾趁人之危侵犯她;教育局侯局长当然不是她钟情的人,但她为了儿子不得不自我牺牲。不过,格非还是为庞家玉设计了一次拯救:她在北京开会期间遇到了年轻的小陶,二人之间的蓬勃情欲让她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获得了“偷着活了一次”的生命体验。
谭端午在与绿珠谈论诗歌时,曾说过结尾是最困难的。对格非来说,怎样结尾或许也是一个难题。他最终给出的结局,是庞家玉主动和谭端午离婚后孤独地死去。值得注意的是,格非让庞家玉在离婚前扮演了一次贤妻良母与好儿媳的角色,并让她在临死前说出唯一不曾后悔的是生下了儿子。看来格非在寻找用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价值时,只能诉诸于传统的性别观。而庞家玉之死,则凸显了她作为两种价值的牺牲品的性质:工具理性具有杀人本性,它让人疲于奔命,患绝症而死;价值理性软弱无力,如果不是谭端午把世俗生活的重担全推到庞家玉一个人身上,她完全不必活得那么辛苦而忙碌。庞家玉在临死前反叛了工具理性——她拒绝按姜老师的要求写检查,但是她自己的爱留给了价值理性,她在留给谭端午的最后一封信中对他说“我爱你,一直”。由女性说出的始终如一的爱,是格非留给价值理性的希望——庞家玉把把自己所有的钱转到了谭端午的银行卡上,让他这个价值理性的代言人活下去,与工具理性对峙。
格非抓住了现时代价值理性退居边缘、工具理性统治大众并使社会趋向“单向度”的特征,这种严肃的思考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让男女主人公在小说中分别扮演价值理性与大众并结为夫妻,表现他们之间的陌生感与彼此伤害,并让庞家玉之死构成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批判。如果考虑到从鲁迅的《伤逝》起,百年中国文学就开启了性别隐喻的书写传统,作家们总是让男性扮演自己最看重的价值,让女性充当某种价值的表象和牺牲者,则格非的《春尽江南》也构成了这一传统的一部分。
注释:
①②③[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12 页、第11 页、第13 页。
④⑤⑥⑨[德]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年版,第5 页、第7—9 页、第20 页、第16页。
⑦⑪[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版,第6页、第117—118 页。
⑧[德]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刚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46 页、第37 页。
⑩[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译:《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