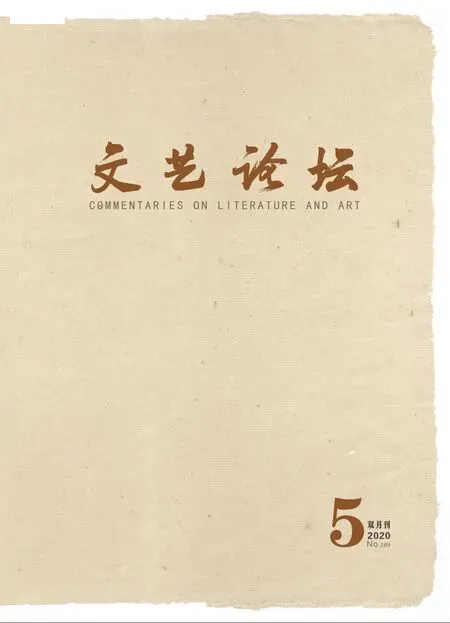简议《大地颂歌》的艺术追求
◎ 邹世毅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为全剧的主旨、主线,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脱贫致富历程为全剧表现基点,全中国扶贫脱贫的现实盛况在全剧得到推演漫延,扶贫脱贫中涌现的公仆、平民英雄在剧中得到崇高的形象刻画和人情呈示,构筑出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艺术演出,主旨深邃,艺术精良,制作精致,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确确实实让观众感受到舞台艺术主导者、组织者和创作者的大局观念、政治敏悟及艺术智慧。深邃的主旨追求、灵动的艺术追求和新颖的美学追求,融汇成《大地颂歌》铸成艺术精品、收获辉煌成就的深蕴潜力和巨大动能。
一、深邃的主旨追求
新中国在新时期开展的扶贫工作,肇基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1986 年5 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1993 年12 月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其日常工作部门,属国务院副部级的议事协调机构。其机构职能主要是研究、拟定、组织实施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规划,协调社会各界的扶贫工作,拟定扶贫标准,确定或撤消扶贫重点县,动态监测贫困和扶贫情况,分配和监督扶贫资金等。到2013 年,全国各省、市依贫困情况的分布也相应地建立了扶贫办公室,全面开展扶贫帮困脱贫致富工作。近30 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各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对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存在许多盲点,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扶贫制度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呈现的总体局面是粗放、表面;解决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现时的贫穷,未能实现永久脱贫,经济上脱了贫,思想上未能脱贫,很有点“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的味道。
针对上述种种粗放、表面的扶贫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断。2013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花垣苗族自治县排碧镇十八洞村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 年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 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 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了云南,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 个月后,他又到贵州省考察,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 年如期脱贫;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做到“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注重“六个精准”(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精准扶贫”于是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2015 年10 月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讲话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实行“五个一批”(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在2020 年底,要确保7000 多万人全部如期脱贫。
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断的首倡地。他的“精准扶贫”系列讲话和指示,从理论方略到规划措施,从宏观把握到微观实施,既高瞻远瞩,又内涵丰富;既高屋建瓴,又实践操作性强;既阐明了“精准扶贫”的要义(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谁贫困就扶持谁的治贫方式),又深化和扩展了扶贫开发工作的内涵(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既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大现实意义(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又昭示出精准扶贫划时代的国际影响和意义(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树立起国际形象,为国际消除绝对贫困树立起中国式“样板”和范式)。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在十八洞村出发、落实、践行,数年间,延展到湖南的石门、溆浦、炎陵等数十个县,随后扩大到云南、贵州、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山西、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等全国存有绝对贫困的省市区,形成了精准扶贫、脱贫的全国性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开发建设大潮,战果辉煌,成就巨大,影响世界,熔铸成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厚重历史价值、现实价值的英雄史诗。运用合适的舞台艺术形式,生动真实形象地呈现这部“精准扶贫”的英雄史诗,向党中央、习总书记汇报,是湖南党政领导必须担当的政治责任,也是湖南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创作任务。因此,就有了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的策划和艺术构思。艺术策划和艺术构思要解决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生活背景、矛盾冲突、事件选择、情节安排等一系列问题;而提炼主题则是艺术构思的中心环节,是中枢神经,是从内部联系各方面的纽带。《大地颂歌》的组织者和创作者十分明了:“只要抓住主题思想这一环,其他许多方面,就会依着它的要求,合乎生活逻辑地被提起来,明确起来;主题思想的每一次深化、变动,其他那些方面,也必然会跟着变动和深化起来。”“精准扶贫”,从十八洞村出发,漫卷湖南,走向全国,到2020 年底,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就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举世瞩目,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际上也有典型意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较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全社会的动员合力,在全世界能够率先成功地消除绝对贫困,中国脱贫的经验必将成为国际社会期盼了解的热点内容,自然也成为其他国家引以为用的典范。将《大地颂歌》的主题建立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主旨的追求深邃宏阔无可置疑。
二、灵动的艺术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大地颂歌》在艺术构思中,除了着意追求深邃的艺术主旨外,另一煞费苦心寻求的点是全剧的艺术结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大地颂歌》呈现的全部内容是以十八洞村为艺术表现的基点,表现其在“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指引下,怎样扶贫、脱贫、发展、致富的历程,并通过这个基点的形象艺貌映照湖南省乃至全中国的扶贫、脱贫概貌,通过十八洞村地理、物情、人道的巨大变化映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浸染和积淀。因此,《大地颂歌》在艺术构思对现实生活作艺术概括的过程中,“为高度的思想内容寻找尽量完美的艺术形式,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高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把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结合起来”等方面,遭遇到一系列的难题:任何单一的艺术结构、任何一种舞台艺术样式或艺术表现方法都不可能满足或完成这种思想内容的表达或呈现,必须在结构、形式、手法上作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
首先,表现在艺术结构上,《大地颂歌》选择了点、线、面、体全方位综合运用、递进织网的结构方式。其优点在于:既可全面提纲挈领地表达拟定的思想内容,又可为灵活选用适合表达内容的任何舞台表演文艺样式,还可为艺术表演和真实呈现互相引带,互藏其宅,互发其华,相得益彰。全剧8 个部分,作艺术表现和表演的部分或以此为主的部分就有6 个,其中个别部分穿插有真实呈现的LED 画面和电视晚会节目式的片段,2 个部分以电视节目、主持人讲话和宣介推广场面为主,个中以歌曲、舞蹈串联,力争各部分在样式、风格上融为一体。例如,从全剧的场景安排上看,十八洞村是“点”,村民们出山打工、扶贫村支部第一书记龙书记和村主任劝阻是“线”(动作线,事物发展的脉络),修路、修水渠、通水通电的实体场景,LED屏的转换和组合,就是“面”和由诸种“面”组合成的“体”;从地理位置看,十八洞村是“点”,十八洞村的各种变化是“线”,石门、炎陵、溆浦等县的扶贫情况呈示是“面”,这些面的舞台呈现组合成“体”;从艺术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真实人物形象展示观察,龙书记是扶贫英雄的“点”,他的一切扶贫行动是“线”,而真实的扶贫英雄石门的义务扶贫村主任王新法、炎陵的县委书记黄诗燕、溆浦的县委书记蒙汉等则是“面”,上述艺术形象和真实人物等群体呈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初心和扶贫精神便是“体”,是光辉璀璨的精神实体;还可以从选用的诸种艺术样式及其艺术方法中得到印证;等等。总体串联、组合的手法就是运用艺术创造彰显基点,延点为线,点线成面,诸面组体,是典型的见微知著,管窥全豹,由表及里,昭彰神理,实现艺术创作的真谛。
其次,是辩证选择适合表达全剧思想内容的舞台艺术形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同一内容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的性质、变化,形式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当形式适合内容时,促进内容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内容的发展。内容是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对内容是相对稳定的。基于对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大地颂歌》为表达广博富宏却又分散零乱的扶贫、脱贫内容,选择了话剧、音乐剧、歌曲、舞蹈、电影、电视晚会节目等多种舞台艺术表演样式,进行艺术跨界融合,做到了只要于表达内容有益,就拿来我用,表面混搭,实质神会,在表现艺术、再现艺术之间架设起天衣无缝的津梁,显示出形式选择上丰富的灵活机动。例如,音乐剧、歌唱的表演主要是表现艺术,动作上是点线组合;舞蹈本是再现艺术,但舞蹈有动作程式和形体规范,这又与戏曲表演类的表现艺术十分近似,成为半体现半表现艺术,动作属于点、线、面组合;话剧是典型的再现艺术,团块式结构,动作是面、体组合;电影艺术最初是从话剧表演艺术脱胎而来,也是再现艺术;而新出现的电视节目,则是剧、声、光、影、道、化、荧屏等面、体的组合。将这么多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舞台表演艺术样式组合在一起,靠的是运用得体的艺术方法,寻找到能使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在恰切表达思想内容上相互转化的契合点,并在创新手法上得到发展。
再次,是创新艺术形式串联、转化的手法。主要表现在:以戏剧对话引出歌、舞,让再现转化成表现;让歌、舞蓄积戏情,使表现转化为再现,推动剧情发展;运用“蒙太奇”进行视听对接,将表现艺术、再现艺术转化为电视节目形式,或反之。例如,当剧情进行到龙书记带来的猕猴桃种子发芽了,生长了,村民们欢欣鼓舞,舞台上迅速呈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音乐和载歌载舞,以戏引带歌、舞,歌舞动作仍在戏中,无缝对接的艺术形式转换,恰切地传达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衷的剧目主旨。又如,当舞台上响起《苗岭连北京》的山歌时,载歌载舞的场面引出全中国扶贫脱贫辉煌业绩的播放宣传,由此串联展示扶贫成果的电视节目。电影能由摄影技术进化为电影艺术,主要靠的是镜头组接技术的巧妙运用,如:将一双静止的脚的照片接在一双行走的脚的照片上,就变成了一双正行走的脚;一把没有子弹的枪对准一个倒地的人,组接起来的镜头就是开枪把一个人打倒了。组接前是单个的镜头,彼此没有关联,当单个镜头被有机地组接起来,就产生了动作,构成了故事,被赋予戏剧性时,就形成了电影艺术。同样,对于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样式的艺术表演,当找到它们能够互相转化的契合点时,它们就能像镜头组接那样,产生不可意料、出神入化的艺术表达和戏剧性。《大地颂歌》的第6 部分,就将舞台上作戏剧表演的黄诗燕妻子、王新法女儿同黄桃树、村长桥以及LED屏上的黄诗燕、王新法、村民代表等真人影像作了蒙太奇式的视听镜头组接。熨帖得体的电视节目式舞台呈现,贴骨巴肉的视听冲击,怎不让现场观听的人感动肺腑、摇动心旌而热泪千行呢!
三、新颖的美学追求
美学追求是一切舞台表演艺术的最高追求。例如,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追求主要是形式的优美、情感上的壮美和秀美,而话剧艺术、歌剧艺术则追求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侧重于内容上的感动和情感的升华,电影、电视节目与话剧艺术差同。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让观众得到的美感享受既有崇高,又有壮美、秀美和优美,而且呈现出的总体美学追求是秀美、优美和壮美的结合,并以秀美、优美为基,托出的壮美居于峰巅。在该剧中,居于峰巅的壮美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它虽然重视形式美的规律,但又具备西方“崇高”的一般特点。《大地颂歌》在美学追求中传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将“崇高”与“壮美”结合在一起,只是“壮美”比“崇高”来得缓和些,是美与崇高之间的过渡形式。“崇高是感动人,美则使人品味,欣赏。”因此,《大地颂歌》浓墨重彩,大笔如椽,将扶贫、脱贫的艺术英雄龙书记,真实英雄黄诗燕、蒙汉、王新法捧上了“壮美”和“崇高”的艺术高台,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行动打上了“壮美”和“崇高”的标志,将中国制度、党的领导、全民合力进行的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的“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精准扶贫”工作演绎成壮美和崇高的英雄史诗,将全剧打造成气势恢宏、“壮美”“崇高”兼有的艺术佳构。
秀美,在抒写人们理想、信念、心灵的时候集中显示。《夜空中最亮的星》,演唱出儿童期望美好未来的一种心理,即儿童的理想追求、对幸福的憧憬、对前程的展望、对成就的自信,这属于秀美。以十八洞村民为代表的贫困民众,希望走出大山,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又渴望回归大山,爱恋故土,面对青山绿水,建设金山银山,构筑幸福祥和,这种追求也是秀美。受益于“精准扶贫”,且已脱贫致富的广大民众,对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对党的正确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作的感恩歌颂,对扶贫英雄龙书记、对奉献一生于扶贫事业的英雄黄诗燕、蒙汉、王新法等共产党员的深切思念和追忆,更显秀美。
优美,主要呈现在载歌载舞场面及舞台布置、电影式视听镜头组接和电视节目设置之中。村民送龙书记参加国庆观礼、合唱《思情鬼歌》庆新婚、欢天喜地迁新居、欢歌乐舞《苗岭连北京》等歌舞翩翩的场面和画面,优美满满;声、光、电、道、妆和LED 屏影像频移变换、综合组合,把舞台装帧成五光十色、内容丰满、变幻多姿的艺术世界,优美如溢。它与秀美相映生辉,以此为全剧美感基调,将壮美和崇高烘托得如当顶铜钲,温暖、滋润着观众的心脾灵囟。
注释:
①②王汶石:《漫谈构思》,《延河》1961 年第1 期。
③秋文:《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问题》,选自《戏剧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