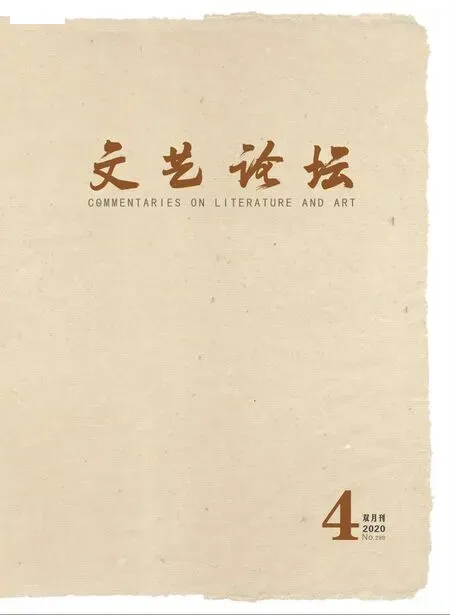“青年写作”的再分化
——从“断裂”到“后浪”
韩松刚
“青年写作”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随着这些年来文学界对“青年写作”的过度关注,则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其中,《中华文学选刊》2019 年针对117 位当代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以及随后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笔谈;后浪、文景、译林、理想国、上海文艺等众多出版机构对于青年作家原创文学的支持;2020 年由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与《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研讨会,等等,都显示了“青年写作”在当下的热闹、重要和迫切。
关于“青年写作”话题的源起,我无意去考证。这是一个具有进化论意味的概念,就像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一个关于“80 后”的“青年写作”问题,谈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年危机”。因此,“青年写作”的问题,不仅仅是“写作”的问题,还是“青年”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很多文章都谈到了,比如何平的《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杨庆祥的《21 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何同彬的《关于青年写作“同质化”:作为真问题的“伪命题”》、李壮的《呼唤常识中的犄角:青年写作关键词》、颜炼军的《“阿多尼斯的死与生”——青年写作刍议》、行超的《探索文学写作的边界——当下青年创作的几个面向》等等,都极具思辨性和启发性,他们的深入讨论延伸了关于“青年写作”的思考路径,同时引发了更多的相关问题。
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写作,也都可以谈论写作的时代,青年作家和“青年写作”一样,正在经受更为复杂、更为细致,也更为严峻的现实考量和思想检验。青年作家正在不可阻挡地成为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等众多部门争相抢夺的“人才”砝码,似乎有得“青年作家”得文学天下之势。而与此同时,青年作家本应肩负的文学抱负和艺术理想却在无意和无形中被忽略、消解,逐渐沦为速朽的消费时代和名利场域中缺少精神附加的衍生品。似乎没有哪一个时代的青年写作正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分化。而我打算谈的,就是“青年写作”的再分化。
之所以说“再分化”,当然是针对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的分化而言。那就是20 世纪末轰动中国文坛的“突发”事故——断裂。“断裂”事件源起于1998 年的《断裂:一份问卷》,主要发起人是韩东和朱文,这份列有13 个问题的问卷,以朱文的名义发表在《街道》《文友》和《岭南文化时报》上,《岭南文化时报》还特辟了专栏进行讨论。问卷一经发出,便得到了不少作家的回应和文坛的热议。此后,关于“断裂”的讨论不绝如缕。之后的1999 年,海天出版社还出版了由韩东主编的“断裂丛书”,推出了6 位作家的小说集。
今天,当我们以奇异而凝重的目光回眸这段历史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代青年作家的现实处境、精神姿态和价值追求。其时,韩东37 岁,鲁羊35 岁,朱文31 岁,朱朱29 岁,魏微27 岁,一个个青春飞扬的面庞,昭示着一个名副其实的青年写作群体。他们旗帜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写作姿态——断裂——这是属于他们的精神宣言。如果我们再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弄20 年,回到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现场,那可能是更早先一步的“青年写作”分化,伤痕文学、现代文学、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各类写作喷涌而出,其中尤以先锋小说与传统文学的分化最让人称赞。只不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技法,压抑已久的内在激情的快意释放,并没有让这一时期“青年写作”在各种文学思潮的奔涌中,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价值支撑和精神突围。而这一分化持续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几年。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分化,为1998 年的“断裂”事件在历史的脉络里埋下了寂寞的种子。相较于新时期停留在文学层面上的分化,由“断裂”开启的分化,更为民间化、精神化,也更彻底。正如韩东所言:“断裂,不仅是时间延续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空间,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上断裂开。”
断裂,是最为彻底的分化。他们要和腐朽的文学秩序断裂,他们要在这一秩序之外创造新的文学和艺术。因此,他们有自身文学观念的认同和不认同:“和我们的写作实践有比照关系的是早期的‘今天’‘他们’的民间立场,是真实的王小波,不为人知的胡宽、于小韦,不幸的食指,以及天才的马原,而绝不是王蒙、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炜、莫言、王朔、刘震云、余华、舒婷以及所谓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这种不无偏激却不失偏颇的激烈态度中,隐含的是那一代“青年写作”的理智、激情和理想。“我们的目的在于明确某种重要分野,使之更加清晰和突出,我们反对抹平以及混淆视听,反对暧昧圆滑的世故态度。”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2020 年。2020 年5 月3 日(“五四”青年节前一天),哔哩哔哩献给新一代的青年宣言片《后浪》 在央视一套播出,并登陆《新闻联播》前的黄金时段。在此段视频中,国家一级演员何冰登台演讲,认可、赞美并寄语年轻一代。何冰坚定而深情的声音,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让不少青年看得热泪盈眶。随后,这段演讲在朋友圈刷屏,甚至被网友称之为现代版的“少年中国说”,而“后浪”一词更是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的代名词。但视频同样引发了争论,不少网友表示出不认可和不赞同。5 月4 日,《后浪》主要的策划人之一杨亮表示,“这个片子主要是希望让看到的人能够被视频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和精神所鼓舞,通过这段视频让公众重新认识大多数年轻人并引起共鸣”。而对于视频刷屏所出现的一些不同的理解,他援引了视频中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君子和而不同,年轻人应该容得下更多元的审美和观念。”
与“断裂”这个剧烈而有冲击力的“文学事件”不同,“后浪”的走红,更像是一个群体自我眷恋的“文化事件”。“前浪”主动走向“后浪”,开始表现出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和祝福,并主动认可他们多元的“年轻”价值观,似乎值得欢呼雀跃,但我们同样要反省的是,在巨变的时代和复杂的现实面前,这些所谓的“赞美”和“鼓励”是否仅仅就是一碗对于精神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无用的心灵鸡汤呢?我们不会否认和拒绝青年人参与一个时代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理性而切实的反思,尤其必要而可贵。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没有反思的写作,就是平庸的写作,没有思想的生活,就是颓废的堕落。我们不会拒绝生活的幸福,就像我们不会拒绝正当的文学利益,但我们同样不能拒绝思想的危机,就像我们不能拒绝文学的抱负。当下的青年写作,正在名利的喧嚣和利益的蛊惑中,走向新的分化。这种分化的面貌是多种多样的,有作家的分化、文体的分化,以及文学分化之下的内容的分化、风格的分化,等等。与上个世纪末相比,新时代的青年作家面临着不可同日而语的时代境遇,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日新月异,媒介的无处不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存困境、价值混乱、精神弱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青年作家”。在这种复杂的现实氛围中,青年作家如何自处、如何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决定本身很多时候可能无关乎文学。因此,有的青年作家,选择投入体制的怀抱,在体制的保障和温暖中,在各种文学奖项的簇拥下,做着美好的文学梦;有的青年作家,选择游离于主流的文学圈,要么在新的媒体空间中挥洒自我、享受新文艺的欢呼,要么在艰难的文学环境中,坚持标榜自由身份,寻觅关于写作的新曙光。其实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身份之外的“写作”所体现出来的“内容”才更能证明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于大部分青年作家来说,他们既不与时代亲密相拥,也不与体制直接对抗,与各种精神的捆绑保持一种若即若离、貌合神离的姿态,也不介意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眼花缭乱的利益驱使中,青年作家似乎很难拒绝现实的诱惑,而且很容易在自我安慰中将文学的精神抱负偷换成平庸的成败得失。当然,我承认,青年作家对体制的态度会影响到写作本身,但我也不会固执地认为,体制会最终决定一个青年作家写作的上限。写作,说到底还是关系才华和能力的事情。
如果说“断裂”是一次精神层面的文学分化,那么当下青年作家的分化,则是一次由技术、资本、市场和名利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的生存分化,这种分化是具体的,也是庸俗的。如果说“断裂”代表了一代作家的写作姿态,是一次带有创造性、反叛性精神目标的文学实践,那么“后浪”作为一个时代不可回避的“文化现象”,则呈现了这个娱乐时代光怪陆离的“思想贫瘠”,这个现象背后是已经躺下的中国当代青年的精神。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去确立当代“青年写作”的未来,这个问题让人困惑。而以当下的文学态势来看,杀死“青年写作”的不是时间的消逝和随消逝而来的生命敌意,而有可能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各个角落里自以为是的“扶持”和“溺爱”。“青年写作”的未来,只需要“青年”自己踏出一条路,“扶着走”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这未可知的青年精神,其实是一眼便能看得出来的,作者只是没有直接道出罢了。一百年过去了,在告别了那个物质贫乏时代的同时,当代青年的精神并没有在这个物质丰盈的时代随着体魄的健壮而强劲起来,相反,从《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到《野生作家访谈录:我们在写作现场》 (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该书以访谈、人物报道的形式集中介绍了袁凌、康赫、杨典、朱岳、孙智正、盛文强等14 位非职业写作者的文学之路),再到《中华文学选刊·青年作家问卷调查》,及至哔哩哔哩弹幕网带来的青年宣言片《后浪》,也就是从60 后、70 后,到80 后、90 后、00 后,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精神的多元分化,以及这多元之下不可遏止的思想衰退。在这个衰退中,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好好地睁眼看世界,不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困境、生命的迷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仍然很重要。
与作家的分化相伴而生的,还有文体的分化。“断裂”时代的分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和独立,而“后浪”时代的写作分化,精神上的“断裂”已经不是十分明显,一切的写作都被死死焊接在秩序的接口上。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文体的多元和丰富上。与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写作不同,这个时期的文体在新媒体、市场、资本以及相应的消费刺激下,显得琳琅满目。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等类型写作,已经具备了十分强大的文体力量,彻底改变了在传统文体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尴尬处境。我们可以对孱弱的“青年作家”表达不满,但我们要理性而客观地承认他们在文体分化中的文学实践。这确实是不可忽视,也是十分重要的存在。
文体的分化,意味着表达路径和方法的多元,意味着对于缤纷现实的接纳和融汇,意味着各种写作手法的肆意和可能。这相对于传统的写作文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丰富和进步。文体的变化,体现了“文学观”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文学,已经不是传统文学的旧有面貌。我们不能四处挥舞着传统的“文学”棍棒唯我独尊。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文体的多元,并不代表着取消和混淆“文学”的边界。“文学”是有限度的,就像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中所言:“‘文学’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但这并不等于说它的使用方式完全是随意的。即便是那些持最慷慨的多元论观点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可能把火腿三明治称为文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漠视或者放任这种“限度”,比如关于网络文学的争论、比如关于非虚构文学的非议等,都源于这一“限度”。
文体分化的背后,还涉及各种各样的操纵,就像生活的背后永远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虚无的时代”,但却已经实实在在地技术化和资本化。就像我们必须要承认,网络写作正在通过市场和资本的运转,依靠点击率和浏览量,戏谑化地侵占我们最后的精神堡垒,“而这堡垒本可以用来保存一种道德、一种伦理、一系列超越性价值或者保住可以在蒙昧当道的年代照亮社会的火种:诗歌、文学、艺术”。
对于“青年写作”,过度悲观和盲目乐观都不合时宜。我们终究要正视那些已然存在且一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写作趋于容易和简单的时代,一切认真的思考都变得越发艰难和肤浅。“青年写作”似乎正在成为“平庸的写作”的代名词,他们更乐于享受秩序的安逸和荣誉的快感,从而取消了文学本有的理想和目的。“这是一个普遍缺乏勇气的时代,也许还是一个不再需要勇气的时代。”可是,与“断裂”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青年写作不仅仅缺少勇气,还缺少智慧和能力,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再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后浪”时代呢?
“断裂”时代的青年作家们,对既定的写作秩序表现出了满满的敌意。“我们不是现存文学秩序的受益者,而是这个秩序在利用我们的年轻、才华。它想与我们做交易,只要我们俯首称臣就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利益补偿。的确,我们的写作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整个文坛正虚席以待,只要你向在座的敬酒致意,便能坐下来与他们共享名利的盛宴。”当下的青年作家们,大部分显然已经闯过了这个关口,参与并制造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和精神狂欢,其乐融融。当然,总有一些“落伍者”,被卡在了关口之外,他们或落寞、或庆幸,但是否会成为未来写作的另一道景观呢?
当下的青年写作,有着强烈的个体意味,也因此呈现出固执己见的审美趣味,这都无可厚非。但是,“为了个人立场而个人立场乃是为了提高自我重要性的努力,因为拒绝承担责任实际上是个人立场的丧失”。作家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但是留给青年作家的时间和空间确实不多了,那些虚拟而多维的网络世界,并没有给文学留下充足的精神余地。
从“断裂”时代到“后浪”时代,我们一直在目睹“青年写作”的发生,但“青年写作”“发声”的机会并不多,即便是有机会,发出的声音也是微弱而无力的。今天,青年的日常生活与自身的理想写作,正在发生或者已然发生真正的“断裂”,一种难以回应自身所处的时代氛围、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所面对的生活难题的“世界性欲望”已经幻灭。
写作说到底是关乎“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个人”已经无法摆脱时代与社会的总体性景观,因此,一切写作包括青年写作,虽然都是从文学开始的,但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意味的精神命题。“断裂”之后,精神何为?“后浪”来了,文学何为?关于这个命题,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限于篇幅,留待将来。
注释:
①②③⑦⑧⑨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308 页、第309 页、第315—316 页、第333 页、第315 页、第321 页。
④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1 页。
⑤[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阴志科译:《文学事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 页。
⑥[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著,赵振江等译:《批评的激情》,燕山出版社2015 年版,第3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