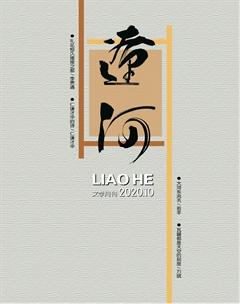年少趣事
索付
我年少时光,是在乡下小村度过的,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制造着欢乐的天堂。我们这群小孩,一玩起来,和孙悟空差不多,簡直可以闹上天去。从早晨起床,玩到晚上睡觉,没有哪个人说累,疲倦好像不是小孩拥有的。让大人们头疼的是,换身干净衣服,半天都维持不到。从头到脚,除油渍就是尘土,脏兮兮的,像一个个小乞丐。淘小子和野丫头,是他们的口头禅,看我们形象,这个称呼是当之无愧的。
捉迷藏、过家家、弹玻璃珠以及老鹰捉小鸡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这些游戏和我们的关系,就像磁铁和铁,有强大的吸引力。
捉迷藏,我们在院落里玩。分成三伙,一伙躲,一伙找,一伙当监督的评委。躲的时候,监督的评委查二十个数,找伙的人就开找。找的时候,监督的评委查三十个数,如果在这三十个数内,找到了躲伙的人,监督的评委就要往躲伙的人脸上贴纸条。如果在三十个数内找不到躲伙的人,监督的评委也要往找伙的人脸上贴纸条。
鸡窝,马棚以及柴草垛都是躲的地方,有时藏住头却没藏住脚,暴露了目标,找到时会忍不住嗤嗤笑。头发和脸及衣服,沾上了鸡毛,马粪和柴草叶,比清理圈舍和抱柴草的人还脏。
玩这个游戏,一次躲的时候,趴在村西头王叔家干旱的黄瓜地里。黄瓜地全是搭起的藤架,王叔看不见里面有人,开始往里浇水。流淌的水很快将我泡上了,水很凉,冻得我直哆嗦。但怕暴露目标,也像烈火中的邱少云一样,强忍着,不敢动身。王叔扒开藤架查看水淌的是否均匀时,发现了我,此时我已冻麻身子,不能动了。王叔惊得张大了嘴,见我不能起来,将我抱出藤架。之后,一边找棉袄给我穿,一边派人去我家通知。父亲没在家,母亲赶来时,我身子已经暖和过来,但发现全身起满了疹子,非常刺痒。母气的骂我傻,伸出手却舍不得打。回家盖棉被捂了一宿,疹子也没下去。父母带我去医院,医生说是湿疹,口服的药片和外抹的药膏开了一大包,连续用一个多月才好。
玩过家家,年幼的我们,虽然没有生活经验,但有极强的想象力。我们聚集在村后的坨坡上,每人用木棍挖一个或深或浅的小洞,当房子。之后在洞口前插上树枝,将洞围起来,作为篱笆墙。最初玩,篱笆墙没有口,是死的。后来,我们觉得不符合生活逻辑。篱笆墙若是死的,人从哪里进屋呢?就将篱笆墙留个口,用树条编个小门,挡住留口。采集一些树叶,草穗和野花,放进洞里,当做家里的生活用品。我们会彼此交换,你送来几片树叶,我送去几根草穗,他又送来几朵野花,实行过日子的礼尚往来。
我会制作钱币,找来纸,按钱币各种面值的尺寸,剪成大小不同的块。之后由小到大,分别在纸块两面写上五圆,十圆,五十圆,一百圆。有钱,我就开厂子,让玩的人过来打工挣钱。有时是米面加工厂,草籽当米,白沙子当面。有时是酒厂,拿水当酒,清水是白酒,泥水是啤酒。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卖给打工的,钱还能挣回来。
我家邻居史三爷的外孙女顺梅,在镇里生活,隔三差五和她妈来村看姥爷时,就和我们一起玩。顺梅懂的东西比我们多,她知道有税务所这个单位,每次玩,都成立个税务所,前来上税。我的钱除给工人开支,还得交税,就不够用了。家里废纸被我收集一空,最后找不到,偷了父亲的抽烟纸,为此挨了一顿打。
没有制作钱币的纸,玩的时候就不能开厂了,钱币多的人会开厂。我心里有个目标,是将我制作的钱币都挣回来,于是去厂里打工。可是,开厂的人都狡猾,比我开厂时的工资低很多。尽管我再努力,挣回的钱币也很少。我开始灰心失望,慢慢的,少了这个游戏的兴趣。
玻璃珠大小不一,种类有单色的,珠里带花瓣的,还有瓷珠。玩弹玻璃珠,几乎都是男孩,这个游戏像赌博一样,是有输赢的。玩的时候,要在地上挖个玻璃珠大的小坑,玩的人可多可少,在同等距离上,按顺序往坑里弹。弹进坑的人,有权弹撞玩家的玻璃珠。弹进坑一次的,只要能连续弹撞上同一个玻璃珠十次,这个玻璃珠就可赢到手。两次弹进坑的人,连续弹撞上同一个玻璃珠五次,可以赢到这个玻璃珠。三次弹进坑的人,权利就大了,只需弹撞上一次,就能赢玻璃珠。
我舅舅是卖玻璃珠的,他每次来我家,我都缠着他要几颗。慢慢的,各式各样的玻璃珠积攒到一百多颗,是小伙伴们最多的。我弹技差,最初不敢玩,但经不住别人鼓动,还是加入了这个游戏队伍。很快,我的玻璃珠从一百多颗变成几十颗。我心疼,哭丧着脸。昏了头的我,不在弹技上找原因,一心想将输掉的赢回来。最后,一颗也没剩,全输光了。
没有玻璃珠,我只能成为看客,但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旁观者。玩者跪倒爬起地奋战,我就跟着跪倒爬起地指挥,赢的人感谢我,输的人讨厌我。有次废寝忘食了,母亲见我没回家吃饭,害得她满村找我。
老鹰捉小鸡这个游戏,要挑选两个高个子的人分别扮演老鹰和鸡妈妈,个子矮的扮演小鸡。游戏开始,所有小鸡都要一个一个手搭肩,躲鸡妈妈身后。老鹰捉小鸡,鸡妈妈需挥舞双臂,挡住老鹰。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小鸡被老鹰抓住,老鹰就获胜了。若老鹰抓不到小鸡,则鸡妈妈获胜。
我的个头高,每次玩这个游戏,我都扮演老鹰或者鸡妈妈。扮演老鹰时,奋力抓小鸡,一副凶残的样子。扮演鸡妈妈时,聚精会神地保护小鸡,不敢有一丝松懈。有次,我扮演老鹰,想从鸡妈妈胯下钻进去抓小鸡。钻的时候,一蹲,裤裆开线了。我尴尬得满脸通红,顾不上玩了,手捂着裤裆往家跑。鸡妈妈和小鸡见我狼狈的样子,用手指着我,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轻易蹲着,生怕裤裆再开线。这年春节,母亲给我买条新裤子,我感觉裤裆缝的不结实,让母亲再缝一遍。母亲不肯,我就将裤子拿到村东头做衣服的马婶家,让她缝。马婶看了看裤裆,和母亲一个观点,说很结实,不必再缝。我坚持让她缝,她没办法,一边缝,一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踢毽子和跳绳也是非常有趣的游戏,然而,这些并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走出村子,茂密树林和绿草如茵的甸子,是另一片岭区。爬树掏鸟窝,个个都有攀爬的本领。有时会失手,从树上摔下或被树枝划破皮,疼的龇牙咧嘴,也不会流泪。
读初中时,我家走了官运,父亲当上村长,母亲当上妇联主任,我也当上班长。父亲经常接见领导,为体面,穿西服系领带。母亲作为妇联主任,也时尚起来,穿流行的衣服,梳着时髦的卷发。生活在这样家庭的我,效仿起来,开始擦胭抹粉,注重起外表。我们班的同学,很快被我带动起来,变得爱美了,打扮的一个个都很漂亮。以前那些游戏不再玩了,镇里的录像厅和台球厅,是我们节假日光顾的场所。
初二那年夏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省城重点中学,参加学习交流会。来到省城中学,我们发现那里的学生,没有擦胭抹粉的,都很朴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像是上台演出的演员,显得另类,以前没太在意的班主任,现在下不来台了。他生气地对我们说,在这里给你们留面子,等回去收拾你们。学校太大了,和我们的村子差不多,一座座高大的校舍和园中美丽的景点,让我眼花缭乱。自认为见过世面的我,却和班里的同学失散了。班主任急红了眼,到处找我,最后通过保安才找到。
从省城学校回来,我感觉抬不起头,变得少言寡语了。同学们没人再擦胭抹粉,像城里学生一样,朴素起来。有天中午,我发现班级门上贴了张纸,纸上写着:油头粉面,省城现,脸丢遍。这是谁贴的?我气愤的将纸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
不久得知,纸是一个外班的女同学贴的,我去找那个同学理论,却不打不相识,成了好朋友。
毕业分开多年以后我们见面,回忆年少,她说:“油头粉面,省城现,脸丢遍。”她笑我也笑。